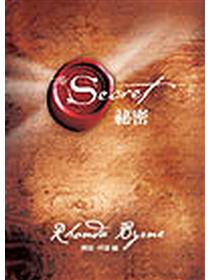3年前,全球文化評論者龍應台,面對18歲的兒子安德烈,覺得她完全不了解兒子的內心世界。她想重新認識這個18歲的人。一次又一次的越洋電話、一封又一封的電子郵件;3年36封家書,讓龍應台與安德烈,重新有了連結。
眼看著兒子從少年變成人,龍應台發現她完全不了解兒子的內心世界,新時代,新世界,新人類。
在封閉的兩代關係中,青年兒女的煩惱和中年父母的挫折,有沒有一個可以打破沉默、開始溝通的窗口?
你呢,MM?在匱乏的年代裡成長,你到底有沒有「青少年期」?你的父母怎麼對你?你的時代怎麼看你?十八歲的你,是一個人緣很好的女生?的最讓人討厭的模範生?一個沒人理睬的邊緣人,還是最自以為是的風紀股長?--------安德烈
人生,其實像一條從寬闊的平原走進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結夥而行,歡樂地前推後擠、相濡以沫;一旦進入森林,草叢和荊蕀擋路,情形就變了,各人專心走各人的路,尋找各人的方向。--------龍應台
上個禮拜,我又失戀了。雖然我的理智告訴我:沒關係,你們本來就不很配。更何況,我愛的其實是另一個女孩,她只不過是一個假想的替身。我覺得,我恐怕是一個在感情上不太會「放下」的人。現在的麻煩是,我不知道接下來要怎麼辦?--------安德烈
我願意和你分享的是我自己的「心得報告」,那就是,人生像條大河,可能風景清麗,更可能驚濤駭浪。你需要的伴侶,最好是那能夠和你並肩立在船頭,淺斟低唱兩岸風光,同時更能在驚濤駭浪中緊緊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換句話說,最好她本身不是你必須應付的驚濤駭浪。--------龍應台
一本跨世代、跨文化的兩代交鋒對話即將登場。你從來沒有想過,兩代人是可以這樣面對面的。藉著《親愛的安德烈》的書寫,龍應台和21歲的安德烈共同找到一個透著天光的窗口。透過36封電子家書,兩代人開始──打開天窗說亮話。
透過《親愛的安德烈》的天窗與天光,親愛的青年子女,或許你可以帶著這本書去敲敲爸爸媽媽的門。親愛的天下父母,也許這本書就是你晚餐桌上的讀書會,從此開始進入兒女的心靈世界。
作者簡介:
龍應台
33歲寫《野火集》,34歲第一次做母親,從此開始上「人生」課,至今未畢業,且成績不佳。
安德列
1985年12月生於台灣,8個月大移居瑞士及德國。2006年秋進入香港大學經濟系,認為經濟學很「好玩」。
章節試閱
親愛的安德烈:兩代共讀的36封家書
第1封信
十八歲那一年
親愛的安德烈:
你在電話上聽起來上氣不接下氣:剛剛賽完足球才進門,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裡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駕照,秋天會去義大利,暑假來亞洲學中文,你已經開始瀏覽大學的入學資料。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將來要做什麼,」你說,「MM,你十八歲的時候知道什麼?」
安德烈,記得去年夏天我們在西安一家回民飯館裡見到的那個女孩?她從甘肅的山溝小村裡來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一個月賺兩百多塊,寄回去養她的父母。那個女孩衣衫襤褸,神情疲憊,髒髒的辮子垂到胸前。從她的眼睛,你就看得出,她其實很小。十六歲的她,知道些什麼,不知道些什麼?你能想像嗎?
十八歲的我知道些什麼?不知道些什麼?
我住在一個海邊的漁村裡,漁村只有一條窄窄馬路;上班上課的時候,客運巴士、摩托車、腳踏車、賣菜的手推車橫七豎八地把馬路塞得水洩不通,之後就安靜下來,老黃狗睡在路中間,巷子裡的母豬也挨挨擠擠帶著一隊小豬出來遛達。海風吹得椰子樹的闊葉刷刷作響。海水的鹽分摻雜在土裡,所以椰子樹的樹幹底部裹着一層白鹽。
我不知道什麼叫高速公路。二十三歲時到了洛杉磯,在駛出機場的大道上,我發現,對面來車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燈,而自己這條線道上看出去,全是車的尾燈,一溜紅燈。怎麼會這樣整齊?我大大地吃驚。二十三歲的我,還習慣人車雜踏、雞鴨爭道的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麼叫下水道。颱風往往在黑夜來襲,海嘯同時發作,海水像一鍋突然打翻了的湯,滾滾向村落捲來。天亮時,一片汪洋,鍋碗瓢盆、竹凳竹床漂浮到大廟前,魚塭裡養着的魚蝦也游上了大街。過幾天水退了,人們撩起褲腳清理門前的陰溝。自溝裡挖出油黑黏膩的爛泥,爛泥裡拌著死雞死狗死魚的屍體。整條街飄着腐臭腥味。然後太陽出來了,炎熱毒辣的陽光照在開腸破肚的陰溝上。
我沒有進過音樂廳或美術館。唯一與「藝術」有關的經驗就是廟前酬神的歌仔戲。老人坐在凳子上搧扇子,小孩在廟埕上追打,中年的漁民成群的蹲在地上抽煙,音樂被劣質的擴音器無限放大。
漁村唯一的電影院裡,偶爾有一場歌星演唱。電影院裡永遠有一股尿臊,揉著人體酸酸的汗味,電風扇嘎嘎地響著,孩子踢著椅背,歌星不斷地說黃色笑話,賣力地唱。下面的群眾時不時就喊,扭啊扭啊,脫啊脫啊。
游泳池?沒有。你說,我們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來游泳的;台灣的海岸線是軍事防線,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說,沙灘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漁村沒有垃圾處理場,人們把垃圾堆到空曠的海灘上去。風刮起來了,「噗」一下,一張骯髒的塑膠袋貼到你臉上來。
我也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學處裡的。
離漁村不遠的地方有條河,我每天上學經過都聞到令人頭暈的怪味,不知是什麼。多年以後,才知道那是人們在河岸上焚燒廢棄的電纜;我聞到的氣味是「戴奧辛」的氣味,那個村子,生出很多無腦的嬰兒。
我不知道什麼叫環境污染,不知道什麼叫生態破壞。
上學的時間那樣長,從清晨六點出門候車到晚上七八點天黑回家,禮拜六都要上課,我們永遠穿著白衣黑裙,留著齊耳的直髮。我不知道什麼叫時尚,化妝,髮型。因此也不知道什麼叫消費。是的,我沒有逛過百貨公司。村子裡只有漁民開的小店,玻璃櫃裡塞得滿滿的:小孩的襪子、學生的書包、老婆婆的內褲、女人的奶罩和男人的汗衫。還附帶賣斗笠塑膠雨鞋和指甲刀。
我的十八歲,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零年的台灣。你或許驚訝,說,MM,那一年,阿波羅都上了月球了,你怎麼可能這樣完整地什麼都「不知道」?
不要忘記一個東西,叫城鄉差距。愈是貧窮落後的國家,城鄉差距愈大。我的經驗是一個南部鄉下漁村的經驗,和當時的台北是很不一樣的。更何況,當時的台北也是一個閉塞的小城啊。全台灣的人口一千四百萬,國民平均所得只有二百五十八美元。台灣,還屬於所謂「第三世界」。
我要滿十八歲的時候,阿波羅登上月球,美國和越南的軍隊侵入高棉,全美爆發激烈的反越戰示威,俄亥俄州有大學生被槍殺;德國的布朗德總理上台,到華沙屈膝下跪,求歷史的寬赦;日本赤軍連劫機到了北韓而三島由紀夫自殺。還有,中國的文革正在一個恐怖的高潮。這些,我都很模糊,因為,安德烈,我們家,連電視都沒有啊。即使有,也不見得會看,因為,那一年,我考大學;讀書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要滿十八歲的時候,台灣高速公路基隆到楊梅的一段才剛開始動工。台獨聯盟在美國成立,蔣經國遇刺,被關了近十年的雷震剛出獄,台南的美國新聞處被炸,我即將考上的成台南功大學爆發了「共產黨案」,很多學生被逮捕下獄。保釣運動在美國開始風起雲湧。
那一年,台灣的內政部公佈說,他們查扣了四百二十三萬件出版品。
但是這一切,我知道得很少。
你也許覺得,我是在描繪一個黯淡壓抑的社會,一個愚昧無知的鄉村,一段浪費的青春,但是,不那麼簡單,安德烈。
對那裡頭的許多人,尤其是有個性有思想的個人,譬如雷震、譬如殷海光──你以後會知道他們是誰,生活是抑鬱的,人生是浪費的。可是整個社會,如果歷史拉長來看,卻是在抑鬱中逐漸成熟,在浪費中逐漸累積能量。因為,經驗過壓迫的人更認識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難得。你沒發現,經過納粹歷史的德國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沈一點嗎?
那個「愚昧無知」的鄉村對於我,究竟是一種剝奪還是給予?親愛的安德烈,十八歲離開了漁村,三十年之後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這個漁村的關係。
離開了漁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後的悠悠歲月裡,我看見權力的更迭和黑白是非的顛倒,目睹帝國的瓦解、圍牆的崩塌,更參與決定城邦的興衰。當價值這東西被顛覆、被滲透、被構建、被解構、被謊言撐托得理直氣壯、是非難分的地步時,我會想到漁村裡的人:在後台把嬰兒摟在懷裡偷偷餵奶的歌仔戲花旦、把女兒賣到「菜店」的阿婆、那死在海上不見屍骨的漁民、老是多給一塊糖的雜貨店老闆、騎車出去為孩子借學費而被火車撞死的鄉下警察、每天黃昏到海灘上去看一眼大陸的老兵、笑得特別開暢卻又哭得特別傷心的阿美族女人。。。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實的面貌存在我心理,使我清醒,彷彿是錨,牢牢定住我的價值。
那「愚昧無知」的漁村,確實沒有給我知識,但是給了我一種能力,悲憫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後面對權力的傲慢、慾望的囂張和種種時代的虛假時,仍舊得以穿透,看見文明的核心關懷所在。你懂嗎,安德烈?
同時我看見自己的殘缺。十八歲時所不知道的高速公路、下水道、環境保護、政府責任、政治自由等等,都不難補課。但是生活的藝術,這其中包括品味和態度,是無法補課的。音樂、美術,在我身上仍舊是一種知識範圍,不是一種內在涵養。生活的美,在我身上是個要時時提醒自己去保持的東西,就像一串不能遺忘的鑰匙,一盆必須每天澆水的植物,但是生活藝術,更應該是一種內化的氣質吧?它應該像呼吸,像不自覺的舉手投足。我強烈地感覺自己對生活藝術的笨拙;漁村的貧乏,造成我美的貧乏。
而你們這一代,安德烈,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網絡讓你們擁有廣泛的知識,富裕使你們精通物質的享受,同時具備藝術和美的薰陶。我看你和你的同學們會討論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正義問題,你們熟悉每一種時尚品牌和汽車款式,你們很小就聽過莫札特的「魔笛」、看過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去過紐約的百老匯、欣賞過台北的「水月」也瀏覽過大英博物館和梵諦岡教堂。你們生活的城市裡,有自己的音樂廳、圖書館、美術館、畫廊、報紙、游泳池,自己的藝術節、音樂節、電影節。。。
你們這一代簡直就是大海裡鮮豔多姿的熱帶魚啊。但是我思索的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你們這一代「定錨」的價值是什麼?終極的關懷是什麼?你,和那個甘肅來的疲憊不堪的少女之間,有沒有一種關連?我的安德烈,你認為美麗的熱帶魚游泳也要在乎方向嗎,或者,你要挑釁地說,這是一個無謂的問題,因為熱帶魚只為自己而活?
MM
2004-05-12
第27封信
二十一歲的世界觀
MM,
你說五十四歲的你,實在無法理解很快就要滿二十一歲的我,腦子裡想些什麼,眼睛看出去看見些什麼(你說這話的那個感覺,好像我們是不同的動物種類),所以我們來彼此「專訪」一下。
好,可是你給我的十個「專訪安德烈」問題裡,第一個問題我就懶得答覆了。你問我,「你對於男女平等怎麼看?」這個問題有夠「落後」,因為,「男女平等」是德國七十年代的問題,最關鍵最艱苦的仗都在那個時候打過了。我是二十一世紀的人了。
然後你還不甘心追著問:「譬如結婚以後,誰帶孩子?誰做家務?誰煮飯?」
這樣的問題在我眼裡是有點好笑的。當然是,誰比較有時間誰就煮飯,誰比較有時間誰就做家務,誰比較有時間誰就帶孩子。完全看兩個人所選擇的工作性質,和性別沒有關係。你的問法本身就有一種性別假設,這是一個落伍的性別假設。
我知道,因為「男女平等」的問題對於你,或者你所說的中文讀者,還是一個問題,但是對於我或者我的朋友們,不是討論的議題了。
所以我就挑了下面幾個還有一點意思的問題,看答覆讓不讓你滿意。
問題一:你最尊敬的世界人物是誰?為何尊敬他?
我記得在一個朋友家裡看過一本書,書名叫「影響世界的人」──你知道,就是那種不知名的小出版社出的打折書,在地攤上亂七八糟疊成一堆讓人家挑的那種。書裡頭的人物,就包括耶穌、穆罕默德、愛因斯坦、馬丁路德。金、巴哈、莎士比亞、蘇格拉底、孔子等等等。朋友和我就開始辯論,這些人物的歷史定位,有多少可信度?
有很多人,不管是耶穌還是孔子,都影響了人類,但是,你怎麼可能把他們的重要性拿來評比?這本地攤上的廉價書,把穆罕默德放在耶穌前面,理由是,穆罕默德靠一己之力去傳播了信仰,而耶穌依靠了聖徒彼得的幫忙。笑死人,能這樣來評分嗎?再說,你又怎麼把莎士比亞和孔子來比對呢?
你現在大概猜到我要怎麼接招你的問題了。我如果回答你一個名字或者一組名字,那麼我就犯了這個「評比」的謬誤,因為不同歷史和不同環境下的影響是不能評比的,而且,天知道世界歷史上有多少值得尊敬的人──我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存在。
我可以說,好,我覺得「披頭四」很了不起,但是你馬上可以反駁:沒有巴哈,就沒有披頭四!那麼如果我選巴哈,你又可以說,沒有Bartolomeo Cristofori發明鋼琴,哪裡有巴哈!
MM,假如你對我的答覆不滿意,一定要我說出一兩個名字,那我只好說,我真「尊敬」我的爸爸媽媽,因為他們要忍受我這樣的兒子。我對他們一鞠躬。
問題二:你自認為是一個「自由派」、「保守派」,還是一個「什麼都無所謂」的公民?
我自認是個「自由派」。但是,這些政治標籤和光譜,都是相對的吧。
每一次德國有選舉的時候,一個電視台就會舉辦網路問答,提出很多問題,然後從你選擇同意或反對的總分去分析你屬於「保守」還是「自由」黨派。我發現,幾乎每一次,我的答案總結果都會把我歸類到德國的自由黨去。可是,我對德國自由黨的支持,又向來不會超過六十分,意思就是說,我的總傾向是自由主義的,但是對於自由黨的很多施政理念,不認同的地方在百分之四十上下。
問題出在哪裡?我支持自由黨派的經濟和政治立場,簡化來說,就是在經濟上我贊成自由市場機制,在政治上我支持小政府,大民間,公民權利至上。但是,我又強烈不認同自由黨派對很多社會議題的態度,譬如婦女的墮胎權、死刑,甚至於環保政策──這些議題在自由主義者的清單上沒什麼重量,我卻覺得很重要。所以看起來,我在經濟和政治議題上屬於「自由主義」,但是在社會議題上,.又有點偏激進。
很多人投票給某一個政黨,只是因為他們習慣性地投那個黨,有了「黨性」。我投票則是看每一個議題每一個政黨所持的態度和它提出的政策。所以每一次投票,我的選擇是會變的。你可以說我是自由、保守、甚至於社會主義者,也可以批評我說,我善變,但是,我絕不是一個「什麼都無所謂」的人。生活在一個民主體制裡,「參與」和「關心」應該是公民基本態度吧。
問題三:你是否經驗過什麼叫「背叛」?如果有,什麼時候?
我的童年經驗是極度美好快樂的。從小我就在一個彼此信賴、彼此依靠的好友群裡長大。這可能和我成長的社會環境、階級都有關係,這些孩子基本上都是那種坦誠開放、信賴別人的人。在一個村子裡長大,從同一個幼稚園、小學,一起讀到高中畢業,我們有一輩子相知的友情。
我從來不曾被朋友「背叛」過。
你想問的可能是:如果我經驗了「背叛」,我會怎樣面對?我會反擊、報復,還是傷了心就算了?假定我有個女友而她「背叛」了我,我會怎樣?
不知道啊。可能還是原諒了、忘記了、算了?
問題四:你將來想做什麼?
有各種可能,老媽,我給你我的十項人生志願:
10. 成為 GQ 雜誌的特約作者 (美女、美酒、流行時尚)
9. 專業足球員 (美女、足球、身懷鉅款)
8. 國際級時裝男模 (美女、美酒、美食)
7. 電影演員 (美女、美酒、尖叫粉絲)
6. 流浪漢 (缺美女美酒美食粉絲,但是,全世界都在你眼前大大敞開)
5. 你的兒子 (缺美女美酒美食粉絲,而且,超級無聊)
4. 蝙蝠俠 (美女、壞人、神奇萬變腰帶)
3. 007 (美女美酒美食,超酷)
2. 牛仔 (斷背山那一種,缺美女,但是夠多美酒,還有,全世界都在你眼前大大敞開)
1. 太空牛仔 (想像吧。)
如何?以上是不是一個母親最愛聽到的「成功長子的志願」?
問題五:你最同情什麼?
這個問題有意思。
無法表達自己的人──不論是由於貧窮,或是由於不自由,或者單單因為自己心靈的封閉,而無法表達自己的人,我最同情。
為什麼這樣回答?因為我覺得,人生最核心的「目的」──如果我們敢用這種字眼的話,其實就是自我的表達。
這個世界有那麼多的邪惡,多到你簡直就不知道誰最值得你同情:非洲飢餓的小孩嗎?某些伊斯蘭世界裡受壓迫的婦女嗎?被邪惡的政權所囚禁的異議份子嗎?而這些人共有一個特徵:他們都無法追求自己的夢想,無法表達自己的想法,無法過自己要過的人生。最核心的是,他們表達自我的權利被剝奪了。
對他們我有很深的同情,可是,我又同時必須馬上招認:太多的邪惡和太多的災難,使我麻痺。發現自己麻痺的同時,我又有罪惡感。譬如你一面吃披薩,一面看電視新聞吧。然後你看見螢幕上飢餓的兒童,一個五歲大小的非洲孩子,挺著鼓一樣的水腫肚子,眼睛四周黏滿了黑麻麻的蒼蠅(這樣描述非洲的飢童非常「政治不正確」,但是你知道我對「政治正確」沒興趣。)
你還吃得下那塊油油的披薩嗎?可怕的景象、你心裡反胃的罪惡感。。。你會乾脆就把電視給關了?
我就是把電視給關了的那種人。
在這麼多邪惡、這麼多痛苦的世界裡,還能保持同情的純度,那可是一種天分呢。
問題六:你。。最近一次真正傷心的哭,是什麼時候?
從來沒哭過。長大的男孩不哭。
好,MM,現在輪到我問你了:
反問一:你怎麼面對自己的「老」?我是說,做為一個有名的作家,漸漸接近六十歲──你不可能不想:人生的前面還有什麼?
反問二:你是個經常在鎂光燈下的人。死了以後,你會希望人們怎麼記得你呢?尤其是被下列人怎麼記得:1)你的讀者;2)你的國人;3)我。
反問三:人生裡最讓你懊惱、後悔的一件事是什麼?哪一件事,或者決定,你但願能重頭來起?
反問四:最近一次,你恨不得可以狠狠揍我一頓的,是什麼時候什麼事情?
反問五: 你怎麼應付人們對你的期許?人們總是期待你說出來的話,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獨特見解,有「智慧」有「意義」的。可是,也許你心裡覺得「老天爺我傻啊──我也不知道啊」或者你其實很想淘氣胡鬧一通。
基本上,我想知道:你怎麼面對人家總是期待你有思想、有智慧這個現實?
反問六:這世界你最尊敬誰?給一個沒名的,一個有名的。
反問七: 如果你能搭「時間穿梭器」到另一個時間裡去,你想去哪裡?未來,還是過去?為什麼?
反問八:你恐懼什麼?
安德烈2006/09/20
第33封信
人生詰問
親愛的安德烈,
我今天去買了一個新手機。在櫃臺邊,售貨員小伙子問我「您在找什麼樣的手機」,你知道我的答覆嗎?
我說,「什麼複雜功能都不要,只要字大的。」
他想都不想,熟練地拿出一個三星牌的往台上一擱,說,「這個字最大!」
很顯然,提出「字大」要求的人,不少。
你的一組反問,真把我嚇到了。這些問題,都是一般人不會問的問題,怕冒犯了對方。我放了很久,不敢作答,但是要結集了,我不得不答。
反問一:你怎麼面對自己的「老」?我是說,做為一個有名的作家,漸漸接近六十歲──你不可能不想:人生的前面還有什麼?
我每兩三個禮拜就去看你的外婆,我的母親。八十四歲的她,一見到我就滿臉驚奇:「啊,你來了?你怎麼來了?」她很高興。我照例報告:「我是你的女兒,你是我的媽,我叫龍應台。」她更高興了,「真的?你是我的女兒,那太好了。」
陪她散步,帶她吃館子,給她買新衣新鞋,過街緊緊牽著她的手。可是,我去對面小店買份報紙再回到她身邊,她看見我時滿臉驚奇,「啊,你來了?你怎麼來了?」我照例報告,「我是你的女兒,你是我的媽,我叫龍應台。」她開心地笑。
她簡直就是我的「老人學」的power point示範演出,我對「老」這課題,因此有了啟蒙,觀察敏銳了。我無處不看見老人。
老作家,在餐桌上,把長長藥盒子打開,一列顏色繽紛的藥片。白的,讓他不暈眩跌倒。黃的,讓他不便秘。藍的,讓他關節不痛。紅的,保證他心情愉快不去想自殺。粉紅的,讓他睡覺。。。
老英雄,九十歲了,在紀念會上演講,人們要知道他當年在叢林裡作戰的勇敢事蹟。他顫顫危危地站起來,拿著麥克風的手有點抖,他說,「老,有三個特徵,第一個特徵是健忘,第二個跟第三個──我忘了。」
他的幽默贏來哄堂大笑。然後他開始講一九四零年的事蹟,講著講者,十五分鐘的致詞變成二十五分鐘,後排的人開始溜走,三十五分鐘時,中排的人開始把椅子轉來轉去,坐立不安。
老英雄的臉上佈滿褐班,身上有多種裝備,不是年輕時的手槍、刺刀、竊聽器,而是假牙、老花眼鏡、助聽器,外加一個替換骨盆和柺杖。
老人,上樓上到一半,忘了自己是要上還是要下。
老人,不說話時,嘴裡也可能發出像咖啡機煮滾噴氣的聲音。
老人,不吃東西時,嘴巴也不由自主地蠕動,做吸食狀。
老人,不傷心時也流眼淚,可能眼屎多於眼淚。
老人,永遠餓了吃不下,累了睡不著,坐下去站不起來,站起來忘了去哪,不記得的都已不存在,存在的都已不記得。
老人,全身都疼痛。還好「皺紋」是不痛的,否則。。。
我怎麼面對自己之將老,安德烈?
我已經開始了,親愛的。我坐在電腦前寫字,突然想給自己泡杯茶,走到一半,看見昨天的報紙攤開在地板上,彎身撿報紙,拿到垃圾箱丟掉,回到電腦邊,繼續寫作,隱隱覺得,好像剛剛有件事。。。可是總想不起來。
於是你想用「智慧」來處理「老」。
「老」,其實就是一個敗壞的過程,你如何用智慧去處理敗壞?安德烈,你問我的問題,是所有宗教家生死以赴的大問啊,我對這終極的問題不敢有任何答案。只是開始去思索個人的敗壞處理技術問題,譬如昏迷時要不要急救,要不要氣切插管,譬如自身遺體的處置方式。這些處理,你大概都會在現場吧──要麻煩你了,親愛的安德烈。
反問二:你是個經常在鎂光燈下的人。死了以後,你會希望人們怎麼記得你呢?尤其是被下列人怎麼記得:1)你的讀者;2)你的國人;3)我。
怎麼被讀者記得?不在乎。
怎麼被國人記得?不在乎。
怎麼被你,和飛力普,記得?
安德烈,想像一場冰雪中的登高跋涉,你和飛力普到了一個小木屋裡,屋裡突然升起熊熊柴火,照亮了整個室內,溫暖了你們的胸膛。第二天,你們天亮時繼續上路,充滿了勇氣和力量。柴火其實已經滅了,你們帶著走、永不磨滅的,是心中的熱度和光,去面對前頭的冰霜路。誰需要記得柴火呢?柴火本身,又何嘗在乎你們怎麼記得它呢?
可是我知道你們會記得,就如同我記得我逝去的父親。有一天,你也許走在倫敦或香港的大街上,人群熙來攘往的流動,也許是一陣孩子的笑聲飄來,也許是一株紫荊開滿了粉色的花朵在風裡搖曳,你突然想起我來,腳步慢下來,又然後匆匆趕往你的會議。那時,我化入虛空已久。遺憾的是,不能像童話一樣,真的變成天上的星星,繼續俯瞰你們的後來。
可是,果真所有有愛的人都變成了天上的星星繼續俯瞰──哇,恐怖啊。不是正因為有最終的滅絕,生命和愛,才如此珍貴,你說呢?
再這樣寫下去,就要被你列入「Kitsch十大」排行榜了。
反問三:人生裡最讓你懊惱、後悔的一件事是什麼?哪一件事,或者決定,你但願能重頭來起?
安德烈,你我常玩象棋。你知道嗎,象棋裡頭我覺得最「奧秘」的遊戲規則,就是「卒」。卒子一過河,就沒有回頭的路。人生中一個決定牽動另一個決定,一個偶然注定另一個偶然,因此偶然從來不是偶然,一條路勢必走向下一條路,回不了頭。我發現,人生中所有的決定,其實都是過了河的「卒」。
反問四:最近一次,你恨不得可以狠狠揍我一頓的,是什麼時候什麼事情?
對不起,你每一次抽煙,我都這麼想。
反問五: 你怎麼應付人們對你的期許?人們總是期待你說出來的話,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獨特見解。可是,也許你心裡覺得「老天爺我傻啊──我也不知道啊」或者你其實很想淘氣胡鬧一通。
基本上,我想知道:你怎麼面對人家總是期待你有思想、有智慧這個現實?
安德烈,一半的人在讚美我的同時,總有另外一半的人在批判我。我有充分機會學習如何「寵辱不驚」。至於人們的「期待」,那是一種你自己必須學會去「抵禦」的東西,因為那個東西是最容易把你綁死的圈套。不知道就不要說話,傻就不假裝聰明。你現在明白為何我推掉幾乎所有的演講、座談、上電視的邀請吧?我本來就沒那麼多知識和智慧可以天天去講。
反問六: 這世界你最尊敬誰?給一個沒名的,一個有名的。
沒名的,我尊敬那些扶貧濟弱的人,我尊敬那些在實驗室裡默默工作的科學家,我尊敬那些抵抗強權堅持記載歷史的人,我尊敬那些貧病交迫仍堅定把孩子養成的人,我尊敬那些在群眾鼓譟中仍舊維持獨立思考的人,我尊敬那些願意跟別人分享最後一根蠟燭的人,我尊敬那些在鼓勵謊言的時代裡仍然選擇誠實過日子的人,我尊敬那些有了權力卻仍舊能跪下來親吻貧民的腳趾頭的人。。。
有名的?無法作答。從司馬遷到司賓諾沙,從蘇格拉底到甘地,從華盛頓到福澤諭吉,值得尊敬的人太多了。如果說還活著的,你知道我還是梁朝偉的粉絲呢。
反問七:如果你能搭「時間穿梭器」到另一個時間裡去,你想去哪裡?未來,還是過去?為什麼?
好,我想去「過去」,去看孔子時期的中國,而那也正是蘇格拉底時期的歐洲。我想要知道,人在純粹的星空下是如何作出偉大的思想的?我想走遍孔子所走過的國家,去穿每一條巷子,聽每一戶人家從廚房傳出來的語音,看每一場國君和謀士的會談;我想在蘇格拉底監獄的現場,聽他和學生及友人的對話,觀察廣場上參政者和公民的辯論,出席每一場露天劇場的演出,看每一次犯人的行刑。我想知道,在沒有科技沒有燈光的土地上,在素樸原型的天和地之間,人,怎麼做愛、怎麼生產、怎麼辯論、怎麼思索、怎麼超越自我、怎麼創造文明?
但是,我也想到未來,到二零三零年,那時你四十五歲,地第四十一歲。我想偷看一下,看你們是否幸福。
但是,還是不要比較好。我將──不敢看。
反問八:你恐懼什麼?
最平凡、最普通的恐懼吧?我恐懼失去所愛。你們小的時候,放學時若不準時到家,我就幻想你們是否被人綁走或者被車子撞倒。你們長大了,我害怕你們得憂鬱症或吸毒或者飛機掉下來。
我恐懼失去所能。能走路、能看花、能賞月、能飲酒、能作文、能會友、能思想、能感受、能記憶、能堅持、能分辨是非、能有所不為、能愛。每一樣都是能力,每一種能力,都是可以瞬間失去的。
顯然我恐懼失去。
而生命敗壞的過程,其實就是走向失去。於是,所謂以智慧面對敗壞,就是你面對老和死的態度了。這,是不是又回到了你的問題一?二十一歲的人,能在餐桌上和他的父母談這些嗎?
親愛的安德烈:兩代共讀的36封家書第1封信十八歲那一年親愛的安德烈:你在電話上聽起來上氣不接下氣:剛剛賽完足球才進門,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裡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駕照,秋天會去義大利,暑假來亞洲學中文,你已經開始瀏覽大學的入學資料。「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將來要做什麼,」你說,「MM,你十八歲的時候知道什麼?」安德烈,記得去年夏天我們在西安一家回民飯館裡見到的那個女孩?她從甘肅的山溝小村裡來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一個月賺兩百多塊,寄回去養她的父母。那個女孩衣衫襤褸,神情疲憊,髒髒的辮子垂到胸前。從她...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221收藏
221收藏

 12二手徵求有驚喜
12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