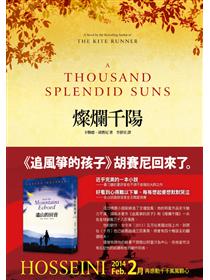所有的顛沛流離,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車站、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
從1949年開始,帶著不同傷痛的一群人,在這個小島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
六十年來,我們從來沒有機會停下腳步,問問對方,你痛在什麼地方?
是時候了,在歷史的這一頁即將永遠地翻過之前,我們還來得及為他們做些什麼?
龍應台,華人最犀利的一枝筆,繼思考家族情感的暢銷書《親愛的安德烈》、《目送》之後,龍應台再度推出15萬字新書《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醞釀十年、走過三大洋五大洲,耗時三百八十天,行腳香港、長春、南京、瀋陽、馬祖、台東、屏東…..從父母親的1949年出發,看民族的流亡遷徙,看上一代的生死離散,傾聽戰後的倖存者、鄉下的老人家。
龍應台說,「我再怎麼寫,都不能給他們萬分之一的溫情與正義」。藉由文學的溫熱,龍應台希望引領讀者一同誠實地、認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這段歷史,看見一整代人「隱忍不言的傷」,重新凝視關於人的尊嚴以及生命價值,用最謙卑的心,寫出跨民族、跨歷史、跨省籍的一本書。
作者簡介:
出生在高雄大寮鄉,讀過的小學有:新竹東門國小、高雄鹽埕國小、苗栗苑裡國小。
童年在台灣中南部農村度過,少女時代在高雄茄萣的海邊漁村度過。
「龍應台」不是筆名,是真名;父親姓龍,母親姓應,她是離亂中第一個出生在台灣的孩子。
留學美國九年,旅居歐洲十三年,在台北做公務員四年,以香港為寫作基地快滿七年。
她今天還歪頭在想:到底要在哪裡種下一株會開大朵黃花的絲瓜?
章節試閱
1 行道樹
我真的沒有想到,你是認真的。
你把錄音機架好,小心地把迷你的麥克風夾在我白色的衣領上,「這樣收音效果最好,」你說,然後把筆記本攤開,等著我開講。
我注意到,你還記下了錄音機上顯示的秒數,方便回頭做索引。
這都是歷史課教的嗎?
我實在受寵若驚。這世界上怎麼會有十九歲的人對自己的父母感興趣呢?
我自己十九歲的時候,父母之於我,大概就像城市裡的行道樹一樣吧?這些樹,種在道路兩旁,疾駛過去的車輪濺出的髒水噴在樹幹上,天空漂浮著的濛濛細灰,靜悄悄地下來,蒙住每一片向上張開的葉。行道樹用腳往下守著道路,卻用臉朝上接住整個城市的落塵。
如果這些樹還長果子,他們的果子要不就被風刮落在馬路上被車輪碾過,要不就在掃街人的咒罵聲中被撥進垃圾桶。誰,會停下腳步來問他們是什麼樹?
等到我驚醒過來,想去追問我的父母究竟是什麼來歷的時候,對不起,父親,已經走了;母親,眼睛看著你,似曾相識的眼神彷彿還帶著你熟悉的溫情,但是,你錯了!她的記憶,像失事飛機的黑盒子沈入深海一樣,縱入茫然──她連最親愛的你,都不認得了。
行道樹不會把一生的灰塵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們會以石頭般的沈默和冷淡的失憶來對付你。
你沒把我當行道樹;你想知道我的來歷。這是多麼令人驚異的事啊!
休息的時候,你靠到窗邊去了,坐在地板上,舒展長長瘦瘦穿著牛仔褲的腿,然後把耳機塞進耳朵,閉起了眼睛,我看見陽光照亮了你濃密的頭髮。
因為你認真,所以我打算以認真回報你。
我開始思索:歷史走到了二零零九年,對一個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一個雖然和我關係密切但是對於我的身世非常陌生,對於我身世後面那個複雜的歷史網絡非常模糊的人,一個生命經驗才剛剛要開始、那麼青春那麼無邪的人,我要怎麼對他敘述一個時代呢?那個記憶裡,有那麼多的痛苦、那麼多的悖論,痛苦和痛苦糾纏,悖論和悖論抵觸,我又如何找到一條前後連貫的線索,我該從哪裡開始?
更讓我為難的是,當我思索如何跟你「講故事」的時候,我發現,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代人,對那個「歷史網絡」其實知道得那麼支離破碎,而當我想回身對親身走過那個時代的人去叩門發問的時候,門,已經無聲無息永遠地關上了。
所以說,我其實是沒有能力去對你敘述的,只是既然承擔了對你敘述的我稱之為「愛的責任」,我就邊做功課邊交「報告」;夜裡獨對史料時,山風徐徐穿過長廊、吹進室內,我感覺一種莫名的湧動;千軍萬馬繼續奔騰、受傷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溫柔無助的心靈仍舊懸空在尋尋覓覓。。。
我能夠敘說的,是多麼的微小啊,再怎麼努力也只能給你半截潑墨山水,不是全幅寫真。但是從濃墨淡染和放手凌空之間,聰慧如你,或許能夠感覺到一點點那個時代的蒙住的心跳?
2 住在一張地圖上
我的名字裡有個「台」字,你知道,「台灣」的「台」。
我們華人凡是名字帶著地名的,它像個胎記一樣烙在你身上,洩漏你的底細。當初給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單純地想以你的名字來紀念他們落腳、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長大以後,人們低頭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為本地人,在這裡生生世世過日子,一切理所當然、不言而喻,沒理由在這地方特別留個記號說,「來此一遊」。紀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來軌道、不同尋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輩人裡,你會碰到不少女孩叫「麗台」或「台麗」,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這「台」字一亮出來,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中陸陸續續流浪到這個島上的外地人。嬰兒的哭聲,聽起來像雨後水溝裡牛蛙的鳴聲,那做父親的,把「台」字整整齊齊用黑墨寫在紅紙上,你可以想像那命名和寫字的手,在一個勉強遮雨的陋屋裡,門外兵荒馬亂,一片倉皇,寫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顛沛流離的困頓,也表達了對暫時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計程車,不妨看一下司機的名字。我每次看,每次都有發現。有一回,碰見一個「趙港生」。
嘿,「港生」啊,你怎麼會在台灣開計程車?
只要你開口問,他就「啪」一下,打開一個流離圖。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動亂中從滇緬叢林輾轉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調景嶺難民營去,一兩萬難民在荒山上那A字形蓋著油布的木棚裡戰避風雨。你知道,難民營裡也是有愛有情有慾的;港生,就出生在調景嶺那遮雨棚下。兩年以後得到入境許可,來到台灣,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台生」反而在香港做生意。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龍的本名是什麼嗎?如果我告訴你,他叫「陳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嗎?稍微打聽一下,你就會知道,他的父親房道龍,在戰亂的一九四七年隻身離開了安徽和縣沈巷鎮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兒女,隨著戰爭局勢的漂洗,最後到了香港,改名換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嬰取名「港生」。和他安徽妻兒的那一邊,是一個生離死別的悲劇,和成龍這一邊,是個患難興邦的傳奇。
今天我從台北的青島東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機,名牌上寫的是「問中原」。
「問中原」?
中原,是一個地區,指的是中國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個概念,指的是中國的文化和權力道統。姓「問」名「中原」,激發的想像就是一個氣勢萬千、躍馬中原的光復圖騰。他的父母是江蘇高郵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亂流中擠上了船,渡海來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復故土的悲壯期待,織進了小小孩兒的名字裡。
在台北街頭,你只要有一點好奇,開口敢問,一問就是一個波瀾湧動的時代傳記。戰後這一代「台兒」,你幾乎可以說,整個人就是一枚會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開的歷史地理課本。
我這「台妹」所居住的這個城市,叫做「台北」,更絕了,它是一張大大攤開的中國歷史地圖。地圖有多大?橫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張兩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圖。
為什麼稱它「歷史地圖」?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歐洲全圖,就是一張「歷史地圖」,它裡頭的「奧匈帝國」,現在沒有了。台北城這張街道大地圖上的中華民國,是一個時鐘停擺在一九四九年的歷史地圖。
你把街道圖打開,靠過來,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東西向的忠孝路畫出一個大的十字座標,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塊,那麼左上那一區的街道,都以中國地理上的西北城市為名,左下一塊,就是中國的西南;右上那一區,是中國的東北,右下,是中國的東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國地理,找「成都路」、「貴陽路」、「柳州街」嗎?往西南角去吧。找「吉林路」、「遼寧路」、「長春路」、「四平街」嗎?一定在東北角。要去寧波街、紹興路嗎?再笨也絕對不會往「西藏路」那頭去找。「甘州街」、「涼州路」、「哈密街」、「蘭州路」、「迪化街」,哈,猜猜看他們在哪個方向?
我們很多人對國民黨的過去的統治歷史是有反感的,我們都說,你看,打仗打敗了,逃到這個島上,便淘空了本地人的記憶,把中國地名強加在台北城上,滿足自己「勿忘在莒」的虛幻想像,充分殖民主義的嘴臉,可悲可惡。
我一直也以為統治者把台北變成一個中國地圖,是一九四九年的一個傷心烙印。失去了實體的萬里江山,就把這海角一隅畫出個夢裡江山,每天在這地圖上東南西北走來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可以用來臥薪嘗膽,自勉自勵。
做了一點探索之後,我大吃一驚,唉呀,不是這樣的。你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竟然會錯。
原來國民政府在日本戰敗以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頒佈了「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要求各個地方政府在兩個月內把紀念日本人物、宣揚日本國威的街道名改正。學者還會告訴你,其實用「改名」來稱,是錯的,因為日本人的都市規劃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復以後,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命名的最高指導原則,就是要「發揚中華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個上海來的建築師,叫鄭定邦,授命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張中國地圖來,浮貼在台北街道圖上,然後趴在上面把中國地圖上的地名依照東西南北的方位一條一條畫在台北街道上。
鄭定邦又是哪兒來的靈感呢?
不奇怪,因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國省分和都市來命名的;南北縱向用省分,東西橫向用城市。
把整個中國地圖套在上海街道上來命名的這個「靈感」,又是哪裡來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借合併成公共租借,各區的街道都得改名,英美法幾路人馬各說各話,都堅持保留自己原來的街名,英國領事麥華陀於是訂了「上海馬路命名備忘錄」,乾脆用中國地名來命名,以免白人內訌。上海街道,從此就是一張攤開的中國地圖。
讓我意外的是,甚至連「建國路」、「復興路」這種充滿政治企圖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之後國民政府給上海街道的名稱,而不是為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北所量身訂做的。
所以台北城變成一張中國大地圖的時候,國民政府根本還不知道自己會失去中華民國的江山。一切竟然是歷史的意外佈局: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崩潰而撤退到這個島,以這個島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把「光復河山」變成此後最崇高的信條,而台北的街道以完完整整的「河山圖」大大地張開,接受這個新的歷史命運到來。國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正式遷台在台北辦公以後,就更詳細地把大陸的地名慢慢填了進來。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們,就在這樣一個已經搭好的歷史架構裡,在這樣一張浮貼掃瞄的歷史地圖上,長大。
38 最底層的竹子
最近一直在思索「罪與罰」的問題。你出生的時候,一九八九年深秋,我躺在法蘭克福的醫院裡一面哺乳,一面看著電視,那是不可置信的畫面:上百萬的東德人在柏林街頭遊行,然後就衝過了恐怖的柏林圍牆,人們爬到牆頭上去歡呼,很多人相互擁抱、痛哭失聲。在那樣的情境裡,你在我懷裡睡覺,長長的睫毛、甜甜的呼吸。初生嬰兒的奶香和那歡呼與痛哭的人群,實在是奇異的經驗。晚上靜下來時,我聽得見日光燈發出滋滋的聲音。
後來,人們就慢慢開始追究「罪與罰」的問題:人民逃亡,守圍牆的東德士兵開槍射殺,這些士兵本身有沒有罪?所有的罪,都在他們制訂決策的長官身上?還是每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東德共產黨的決策高層一直說,他們要求衛兵防止人民離境,但是從來就沒有對守城士兵發佈過「逃亡者殺」的命令。很多法庭的判決,是判個別士兵有罪的。
你知道嗎,飛力普,一直到二零零七年,才在一個當年守城衛兵的資料袋裡找到一個文件,文件寫的是:「面對逃亡者,使用武器不需猶豫,即使是面對婦孺,因為叛徒經常利用婦孺。」
昨天在電話上跟你提到柯景星這個台籍監視員。他被判刑十年,罪行是他和其他十幾個台灣兵在日本已經知道要戰敗的最後時刻裡,為了湮滅虐俘的證據,屠殺了四十六個英澳俘虜。那個下指令的日本隊長,在法庭上主動承認是他下的令,一肩挑起罪責,但是那些奉命動手的台灣人,還是被判了重刑。
。。。
喔,昨天終於找到了小洋!他住在澳洲雪梨,是個八十二歲的老人家了。一九四五年從俘虜營回到家鄉以後,變成一個木匠,幫人家設計家具,做門窗。他在俘虜營裡零零星星所做的素描,後來就用他做木工、畫家具設計圖的本事,重新畫過。他很開心我可以採用他的俘虜營素描。
我問他:「在山打根俘虜營裡飽受虐待的時候,你知不知道很多穿著日軍制服的監視員其實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兵?」
他說,「知道的,因為他們自己常常被日本長官揍,刮耳光。老實說,日本人對待這些福爾摩沙監視員的態度跟監視員對待我們這些俘虜的態度,一樣的狠。」
「那麼,」我再追問,「如果我說,這些福爾摩沙監視員在某個意義上,也是一種『被害者』──被殖民制度和價值所塑造、操弄,因而扭曲變形,你身為一個曾經受過凌虐的人──會反對嗎?」
幾分鐘之後,他的電郵就回覆了:「教授,我當然不反對。他們同樣地身不由己啊。」
「那麼,六十年過去了,您對那些福爾摩沙監視員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
他回信:「有一次我跟兩個英國人從俘虜營逃跑,被搜捕回來,我們都以為,唉,這回死定了,因為我們都看過逃跑的俘虜被活活打死。而且,如果當場沒打死,傷口發炎,他們不給藥,潰爛沒幾天也一定死。可是奉命管教我們的是幾個福爾摩沙兵,他們年紀很輕,而且個子都比較小,抓那個粗大的藤條抓不太牢,所以打得比較輕,我們運氣還不錯。」
「有沒有可能,」我說,「是這幾個福爾摩沙監視員故意放你們生路呢?」
「很難說,」小洋回說,「教授,所謂操弄,就是把把一根樹枝綁到一個特定的方向和位置,扭成某個形狀,但是我相信人性像你們東方的竹子,是有韌性的,你一鬆綁,它就會彈回來。不過,如果你這根竹子剛好是被壓在最底層的話,那可是怎麼奮鬥、掙扎,都脫不了身了!」
1 行道樹我真的沒有想到,你是認真的。你把錄音機架好,小心地把迷你的麥克風夾在我白色的衣領上,「這樣收音效果最好,」你說,然後把筆記本攤開,等著我開講。我注意到,你還記下了錄音機上顯示的秒數,方便回頭做索引。這都是歷史課教的嗎?我實在受寵若驚。這世界上怎麼會有十九歲的人對自己的父母感興趣呢?我自己十九歲的時候,父母之於我,大概就像城市裡的行道樹一樣吧?這些樹,種在道路兩旁,疾駛過去的車輪濺出的髒水噴在樹幹上,天空漂浮著的濛濛細灰,靜悄悄地下來,蒙住每一片向上張開的葉。行道樹用腳往下守著道路,卻用臉...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349收藏
349收藏

 20二手徵求有驚喜
20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