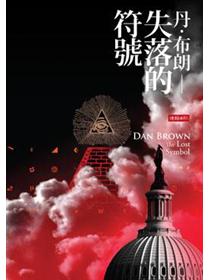◆〈特稿〉作者越洋專訪
★那多先生,您經常被媒體和讀者拿來與倪匡做比較,不曉得您對於這位前輩作家有何看法?
那多:我大概是在中學時代開始看倪匡的作品,一看就放不下手,因為此前沒有看過類似的東西,其實此後也沒有,似乎這個類型就只有他在寫。剛剛看的時候非常激賞,有一個人的想像力可以去到那樣,特別是在當時大陸的讀書環境比現在要刻板一些,就更是感覺如此。
記得那時從各個圖書館找他的書,最後還利用父親的關係,從上海作家協會的圖書館去借他的港版書看。
他寫了非常多的東西,這點至今讓我驚訝。但也許人的新奇無法長久,又或者是開始給我的期盼值太大了,所以當看過了他的幾十個、一百多個故事之後,就覺得漸漸可以猜到他的故事了。所以我一直在想,有沒有另一個類似的作家寫類似的作品,不同人的想像力總是會有不同的方向,那麼就又可以帶給我一些美好的體驗。可惜倪匡竟然只有一個,沒有後來者。
於是在某個時候,我也回憶不起是什麼時候,在心裡就有了這樣了個想法,也許我可以試一試。雖然我也有其他類型的創作(編按:如《那多三國事件簿系列》《星座愛情故事系列》),不過回想起來,如果沒有像他,像金庸、古龍這樣的通俗小說作家給了我很美妙的閱讀體驗,我大約也不會走上這條路吧。
★您的父親趙長天的作家身分,是否也在您成長過程中產生影響呢?
那多:有影響,但並不是直接的。因為他寫作的小說和我不同類型,在他的時代,很難靠寫小說來養活自己,所以他並不建議我繼承他,一直說這是件很辛苦的差事。但如果不是有這樣一個父親,我會覺得一名作家離自己是非常遙遠的,或許更不容易提筆去寫。
★您曾考慮創作金古那樣的武俠小說嗎?尤其您似乎不再繼續寫《那多靈異手記系列》(編按:即台灣版的《那多探奇系列》。原書共十冊)了。
那多:我不會寫武俠小說,實際上我覺得自己已經找到了長久的寫作方向,就是懸疑小說。或者說帶有神秘色彩的懸疑小說。是在寫作那多手記的過程裡,我對自己這一方面的能力開始有了認識和肯定。而那多手記實際上也能歸入這一個定義裡去。並不是一定不寫那多手記,我目前的確暫時停止,因為有更讓我感興趣的題材去寫。但也許有一天會繼續吧。
★您在那多手記系列裡的人物個性活靈活現,請問是取材自您自己和朋友、周遭嗎?還是純粹憑空想像?
那多:實際上就我現在的看法而言,我手記系列裡的人物形象是遠稱不上活靈活現的……人物形象的刻畫在我寫手記的時候是一個弱項,現在正在改進中。書中的人物並沒有刻意地取材於誰,手記實際上是以整個故事的創意見長的,至於人物,可能是因為我一口氣寫了那麼多本,所以給大家一些印象,就單本而言,還談不上什麼人物的塑造。況且,我身邊可沒有那麼多美女。
★您書中提到那多會看台灣的綜藝節目,這是您自己的嗜好嗎?
那多:因為有一段時間,我家裡裝了能看到台灣一些節目的衛星天線,所以就常常看。確實台灣的綜藝是兩岸三地最好看的,新聞和政論也是。我看了「超級星光大道」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因為蕭敬騰的關係,我現在把曹格的〈背叛〉唱得很好呢!
我最愛的綜藝實際上是「全民大悶鍋」,現在的「全民最大黨」。
★請教您是否也看台灣小說?
那多:實際上我很喜歡九把刀的小說。我起初是在網路上看的,後來出版我小說的接力出版社也出九把刀的,就送了我一些。他的《都市恐怖病系列》我都很喜歡,當然最喜歡的還是《樓下的房客》,太讚了,有一種變態的快感。
他的想像力很讓我讚賞,因為我自己覺得也是有一些想像力的人,所以就格外不容易在這方面佩服別人。我指的是通俗小說領域。就現在的類型小說家而言,好像就他一個。
★您實際上有過靈異體驗嗎?
那多:沒有,讀書時有過一段時間夢魘,但我不覺得那是被鬼壓呢。但朋友有。很矛盾的心情,對於自己遭遇這種體驗。因為我是一個特別怕死的人,所以就很希望真的有鬼魂在,免得一場空。不過要是自己真碰到了,大概也不會是特別愉快的體驗吧。
★當初聽說您的作品要在台灣出版,您的第一個感想是?您有沒有什麼話想告訴台灣的讀者?
那多:我很高興自己的作品能被另一個華文圈的讀者看到,對我來說這是另一次創作水平的被檢閱,有點惶恐,希望台灣的讀者會喜歡。老實說手記系列是我過去幾年中寫的,這是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一個創作階段,我的想像力在這個系列裡是體現得最充分的,我也很希望在這一點上被更多的讀者承認。當然在創作手法上總還有不成熟的地方,我很希望今後我的新作品也能不斷被介紹到台灣來。
(整理自二○○八年十二月十日訪問稿)
*****
好在我以前去過幾趟上大,很快便趕到了蘇迎所住的女生宿舍樓。遠遠地便能聽到陣陣尖叫聲,一大群人圍在樓下,不時有男生衝上樓去,想必是被女友叫來的。我趕到門口,守門的大媽還在攔阻門口要往上趕的男生。我向她亮了記者的證件,說要去看一看,她立刻放我進去。我往樓上跑著,聽見大媽還在說著「活了幾十年都沒碰上過這種鬼蟑螂,真是邪門!」之類的話,我也不顧這兒是女生宿舍樓,不由得加快了腳步。
整棟大樓燈火通明,尖叫聲不絕於耳,樓梯上不斷有驚慌的人跑下,好些男生牽著女友跑下樓並說著安慰的話,也能聽到一些男生在大吼:「踩!踩死牠!」
我來到三樓,一路上許多寢室都是雞飛狗跳,然而我想像中的蟑螂鋪天蓋地的景象卻並沒有出現。一隻蟑螂從我腳邊爬過,我看與普通的蟑螂也沒什麼兩樣,頓時放下心來,還感覺有些好笑。
來到蘇迎寢室門口,蘇迎見到我猶如見到救星,急忙躲到我身後,她的一些室友也紛紛站到我後邊,這時我看見房間裡確實有三五隻蟑螂轉悠著在地上爬。
我忍不住笑了起來,一邊說道:「這有什麼好怕的!」一邊抬腳就踩下去。女生們都莫名其妙地驚呼起來。
然而在踩住蟑螂時感覺有點異樣,沒有聽見清脆的哢吧一聲,感覺卻好像踩住了一塊橡皮糖一般,牠在腳底下還在有力地蠕動。我抬起腳來,牠赫然還若無其事地在地上爬行。
這下我大吃一驚,奮力再踩了幾下,那蟑螂除了每被我踩一下就加快幾分爬的速度以外,一點事也沒有,倒好像更加生龍活虎了。這情景使我再次想到那隻軟骨貓,卡車軋不死的貓和踩不死的蟑螂,難道蟑螂也和貓一樣,變成了打不死的軟體動物?我不由得一陣噁心。
就在這時有一隻蟑螂爬進了一隻打開的抽屜,蘇迎的一個室友尖叫了一聲,搶上前來,想要保護自己的抽屜。眼看那隻蟑螂爬向一遝信封之類的檔,那個女生從抽屜裡拿起一把水果刀尖叫一聲切了下去,一刀把蟑螂切成兩半。這一刀切得很準,但是造成了反效果。這隻蟑螂身首異處之後,卻分成了兩半速度絲毫不減地爬開,腦袋帶著幾隻殘肢爬出抽屜,身子的大部分還在裡面打轉,然後很快地從抽屜的另一邊爬了出來,絕不像是死前掙扎,而是精力充沛的樣子。這麼一來簡直好像多了一隻蟑螂一般。
兩半蟑螂分頭爬來爬去,爬到我的腳邊,我本能地又狠踩了幾腳,毫無效果,但我總得保護一下我身後的女生,於是起腳把牠踢開。看牠們很亢奮的樣子,我感到一陣毛骨悚然,蘇迎和她的室友們紛紛掩口。
現在我確定這絕對不是我們平時概念中的蟑螂,也許是蟑螂的某種變異體。牠不但像那隻貓一樣變成了打不死的軟體生物,甚至身體分開後仍然能夠繼續生存,生命力實在強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一般的昆蟲也許分體後會動彈一下,但僅僅是動彈一下而已。我已經沒有辦法猜測牠們變異的原因,只能預想:好像恐怖電影中的生物變異,又好像驚悚恐怖故事中被殭屍咬傷後也會變成殭屍去咬人的連鎖反應一般。先是貓,再是蟑螂,然後會是什麼?
而且變異了的蟑螂一下子全都鑽了出來,也使我想到那隻貓對我的突然襲擊。莫非牠們都是出於同一原因而異動起來?
我還未來得及進行具體的聯想,走廊裡傳來了看門大媽的喊話聲。原來校方反應極為迅速,已經找人配好了殺蟲藥水,準備給全大樓進行噴灑。但殺蟲水的毒性非常強,現在要求所有人馬上撤離大樓。於是所有人爭先恐後地逃了出去。我看著蘇迎臉色蒼白緊咬下唇的模樣,估計是受了驚嚇,便想說什麼安撫她一下,卻想不出用什麼來解釋這件離奇的事件。
我和蘇迎打車回到志丹苑。一路上我腦中翻來覆去地就充斥著那只貓被卡車軋過的畫面,以及那只蟑螂被斬成兩段之後分開爬來爬去的畫面,真是噁心。然而真正的原因還是一團謎,令我感到惶惶不安。這時車停下,我望見離門口不遠的考古工地,隱隱覺得其中必然有隱藏的秘密關聯。
本來到我住進志丹苑之前一切都很正常,但就是這短短的幾天,發生了這麼多怪事,我唯一能聯想到的就是考古事件。(這應當是一種直覺,其實我現在覺得,這也是一種自找麻煩的惡習。)可沒有跡象表明這些怪事與考古有關,我還是應該多考慮貓和蟑螂之間的潛在聯繫。
走到樓下,一路上一直一言不發的蘇迎忽然開口道:「那多,能不能到樓上坐坐,陪我一會兒?」看來她驚魂未定,這種情況下我當然更是不能拒絕,便陪她一同到了她家中。
一走進她家,最先映入我眼簾的還是那只巨大的水族箱,然而今天只有零星的幾條魚在缸內冷冷清清地遊蕩。也許是這兩天她無心餵養,魚死了不少吧。這種事已是無關緊要,我也不想問蘇迎。我們坐下來,我發現蘇迎的神色已經平靜了許多。我決定告訴她那隻貓的事,一來可以幫忙想想,二來我也需要緩解一下精神上的壓力。
「今天怪事真是多。」我搖頭道。
「你是說蟑螂?是啊,太噁心了。」蘇迎應道。
「不止如此。我今天還碰到一隻怪貓。」我認真地看著她道。
「怎麼?」
「很奇怪,牠和蟑螂差不多,卡車軋不死,從十二樓摔下來也摔不死,我還摸過,是只沒有骨頭的軟骨貓。」我向蘇迎解釋。
蘇迎露出噁心的神情:「也就是說,那貓也和蟑螂一樣了。」
「我認為牠們都發生了一種變異。就是變得像軟體生物一樣改變形狀而不會死,生命力強得可怕。」
「嗯,有可能。」蘇迎同意道,一副心有餘悸的樣子。
「而且這一切都發生在我們離這麼近的地方,妳不覺得太巧了嗎?」
「我覺得這些都與志丹苑考古有關係。雖然現在還不知道,但我相信最近只有志丹苑考古可能和牠們存在某種聯繫。」蘇迎突然說道。
我吃了一驚,蘇迎提出的想法我也考慮過,但已經否定了,所以我不免有些不以為然地搖了搖頭。
「妳為什麼會這麼認為?」我問她。雖然如此,我心中倒是真的動了一動,她說不定會有什麼新奇的想法……
「就像你說的,太巧啦,所以一定會有些關聯啊。」
「雖然這些怪事情都發生在這附近,但不一定是同一原因造成的,而且也沒有任何證據啊。所以我覺得這兩件事應該和考古沒有任何關係。」我歎口氣說道。
「其實不僅如此,事情沒那麼簡單。」她像下結論似地說,「志丹苑考古還和海底人有關係。」
——又是海底人。
我有些失望,因為蘇迎不同意我的觀點,而且又提出所謂海底人的老套,使我有些不快。但是蘇迎的表情卻十分自信,令我起了疑心。
「妳是不是知道些什麼?」我盯住她問。
她立刻有些不自然起來,卻也顯出一股掩飾不住的得意。
「妳到底知道些什麼秘密,或者妳發現了什麼,所以妳堅持找海底人?」我追問道。
蘇迎又咬起嘴唇,隨即大聲道:「有些東西是我的秘密,絕對不能說。你不要問了。」
我見她有些激動起來,便不說話了。
蘇迎猶豫了一下,見我一臉誠懇,便又開口道:「有一個關於海底人的傳說,我可以悄悄告訴你。」
「什麼?」我將信將疑地問。
「嗯,傳說中,海底人是可以變成人的。本來海底人的樣子和人不一樣,但他們可以通過某種儀式變成和我們一樣的樣子在陸地上生活。我認為這次的志丹苑遺址很可能就與海底人舉行的儀式有關。說不定這裡就是他們舉行儀式的地方。」她很肯定地說道。
我有點被搞糊塗了,仔細盯住蘇迎,從她臉上胸有成竹的神情無法看出她是在開玩笑或幻想。我突然說了一句一開口就讓我感到自己很愚蠢的話:「妳怎麼知道的呢?難不成……妳就是海底人吧?」
蘇迎一怔,隨即爆發出一陣大笑,笑得頭髮都散到臉前。她伸手梳理著,那表情比在泳池裡更加放肆,接著她認真地對我說道:「我第一次看到你時,我就知道你會是我的知音。沒錯,還真被你看出來了,我就是海底人。」
「我就是海底人。」
我對這句回答倒是有些不知所措,甚至有些緊張。但要我相信蘇迎就是海底人還是不太可能,我一時說不出話來。
「其實從種類上來看,海底人就是章魚人你知不知道?」蘇迎又笑著對我說。
「啊?」
「真的。我拍廣告的時候頭髮不是飄起來嗎?那些不是特技,不是風吹的,而是自己會動。」
「哦?」我正意外,窗外忽然吹進一陣風,她的頭髮紛紛飄舞起來。一時間我竟有些毛骨悚然,一陣妖異的感覺向心頭襲來。蘇迎淺笑著,頭髮誇張地飄動,我一下子竟然有些分不清真偽,驚疑不定。
十五分鐘後,我躺在一樓我自己的床上。
我看過很多國外的偵探小說,小說中常常會出現這樣的神秘乃至靈異的事件,但那些都是表象,是圈套,其中常常是藏有某個陰謀。現在我的處境好像就是如此。當然我感覺不到什麼犯罪的氣息,我也不是明智小五郎,但有一點可以借鑑,那就是發生的種種一切都應該會有內在的聯繫。但我現在的麻煩在於,分不清目前哪幾件可以歸為一談。究竟是貓發生在先,還是志丹苑……仔細想來,志丹苑根本是很早的事,我會把考古都考慮在內,完全是受了蘇迎的影響。想到蘇迎,我不禁哭笑不得。
但是志丹苑考古和這兩件事有關的想法也不是不可能,因為不考慮時間的因素,還有地點的因素——畢竟事件也都發生在志丹苑附近。究竟如何我已經無精力再去思考了。
在經歷過一些常人難以想像的事件後,我早已養成無論怎樣也要逼自己去睡覺的習慣。畢竟保證精力的旺盛是最重要的。所以即使今天經歷了許多不可思議的事件,怪貓、不死蟑螂、蘇迎是否是海底人的疑問……我暫時不去想而是上床就寢。雖然腦子裡充滿疑問,我相信只要那隻貓不吵鬧,我還是可以入睡的。
然而有些出乎我意料,這天晚上我睡得還算不錯,那只貓一點動靜也沒有。想到那隻貓,頭腦就更亂了,卡車軋過、高空墜落……我打起精神,暗自下定決心今天要把這幾個謎團弄個水落石出,至少也要理出點頭緒來。條件允許的話,把那隻貓捉來,研究一番。我洗漱完畢,打算先去報社一趟,剛走出門口,看見一群人圍在樓門附近的綠地旁的水池邊。
我有些好奇地走過去,卻發現是幾個保安,拿著很長的竹竿,竹竿上套著網兜撈著什麼。邊上有幾個老大媽圍著看熱鬧。
我正想離開,聽見一個保安喊道:「有了,有了!」隨即是老大媽們的一片驚歎聲。我回頭一看,吃了一驚,他們撈起來的網兜裡竟然是那隻黑貓!
保安們把貓屍倒在地上,我從那隻貓身體極不正常的彎曲判斷,這就是那隻貓。看起來牠的屍體已經有些僵硬了,但前足仍然呈弧形地捲曲著,十分怪異。
「這隻貓……怎麼回事?」我問那個撈起牠的保安。
「哦,我昨天晚上巡邏時發現這隻貓掉到水池裡,晚上找起來很麻煩,又怕吵到人,所以早上來撈。都死了半天了。我看見牠倒好像是自己跳到水裡去的,真是隻笨貓。」他解釋道。老大媽們在一旁念叨著「作孽啊,作孽」。
看來沒有人注意到這隻貓的問題。
這隻貓淹死了這麼久,屍體僵硬,就算有人願意摸牠,也未必會發現牠的怪異之處。更何況一具濕淋淋髒兮兮的黑貓屍體,誰會願意碰呢?看來這隻黑貓的線索就只能這樣斷了。那麼,是不是應該把貓屍送到有關部門研究……我腦中膠著著,也許是男子漢的自尊心作祟,我還是決定隱瞞這個可能只有我知道的事實。
但奇怪的是,這隻卡車軋不死、摔又摔不死的貓,怎麼會莫名其妙就這樣淹死了?若說哪隻貓會遲鈍到失足跌落水池,我不相信,更何況這隻貓非同一般。
去單位的路上我苦苦思索。這隻怪貓的死亡一定有某種原因。難道是變異產生了問題,導致牠在水池邊走動時死亡後再跌入水池的?然而現在任何疑問都已經無法解釋了。
我苦苦回憶有關這隻貓的一切:被卡車軋過,夜半的叫聲,從樓上跳下向我襲擊,最後一次見到的牠悲哀的眼神、仿佛要流出眼淚般的無助……我突然產生了一個念頭。
也許,這隻貓是自殺的。牠的身體變異一定帶給牠難以忍受的痛苦,折磨得牠每天夜裡哀叫不止。牠衝出去被卡車軋、從樓頂上跳下來也不是為了攻擊我或是什麼,而是想求死。所以牠甚至沒有動用自動維持平衡的本能。然而牠還是沒有死成,反而憑添了痛苦。最後牠選擇了淹死。所以保安說看見牠「好像是自己跳到水裡去的」,所以牠昨晚沒有發出一點聲音。如果是失足落下,一般都會發出叫聲拚命掙扎一下的,然而牠很安靜。這一點也非常合理,足以證明我的結論。
悟到了這隻貓自殺的原因後,我不禁對這隻貓產生了同情。但同情的同時,對這條重要線索的失去我還是感到非常遺憾。真相的揭開變得更加困難重重。
回到報社,我的精神好不容易放鬆了下來。辦公室裡閒適的氣氛和同事們中午家常的談話,使我暫時又有了一種踏實的感覺。這幾天的一些經歷使我好像有點脫離現實,正需要在這樣的環境中冷靜一下。
但說到底,那些怪事已經發生了,我還是必須投入到其中去。我遇到過很多奇異的事件,所以我確信這個世界充滿未知的事物,包括一些往往早已被人喜聞樂見其實又忽略了的細節。盡力去發現這些東西是我的樂趣之一,是我生活、工作的動力。我想我不妨進行個大膽的假設:如果蘇迎的確像她所聲稱的是海底人,那麼志丹苑遺址就一如她所講的與海底人有關。而之前我已經認定貓和蟑螂是與考古事件有關,所以海底人與貓和蟑螂之間一定有著某種聯繫。
這樣猜想著,我順手拿起一支筆,抽出一張紙隨意地寫起來。但其中的疑點太多了,再說供研究的物件也實在太少,我很難判斷究竟是貓和蟑螂這兩種生物種類與海底人有關係,還是牠們的變異過程與海底人有關係。從現在來看後者應該可能性比較大,因為不死之身的蟑螂出現了很多隻,而貓卻只有一隻。那麼牠們究竟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變異呢?我竭力用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去解釋,直到眼前一陣發暈。
當我回過神來時,看到坐在我旁邊的同事都一臉怪異地看著我,想來是從沒見過我如此發憤圖強的神態。我連忙把紙揉起來。
我想不如把昨天到上大看蟑螂的事告訴他們,雖然他們只是當笑話聽,但說不定會歪打正著地想出些什麼來。平時我們在工作時不大交談,但私底下我們還是非常隨便的一群。
「嗨,我說……」我剛一開口,沒想到平時和我比較要好的同事小張走到我身邊拍了拍我肩膀,壓低聲音說道:「小子,豔福不淺,昨天和女大學生一起風流快活去啦?」
「啊?」我吃了一驚,「沒有!你聽誰說的!」嘴上說著心裡卻虛得要命,心想這小子怎麼這麼神通廣大。要是我真和蘇迎有些什麼給他們說說我也就認了,怕就怕這麼莫名其妙、子虛烏有地把我的名譽給敗壞了。
「嘿,瞧你小子急的,我開玩笑試探試探你的。真的沒有?」
「沒有。」我已是一身冷汗。
「唉,是這樣,這兩天不是來了個上大影視系的女實習生嘛,她說她昨天還在她們寢室樓見過你呢。」
「實習生?我怎麼不知道?」
小張笑起來:「你每次來待不到半個鐘頭就走了,又老是心不在焉的,看見你也不會注意的。」
我無言以對。不過我倒很想從那個上大影視系的女實習生那裡再問一些蘇迎的情況。
很快我便見到了這個女孩陸燁。平心而論,這女孩長得比蘇迎差了不止一個等級,好在還是人模人樣的,於是我客氣地向她打招呼。
簡單地聊了幾句之後,我了解到她確實是蘇迎的同學,而且也經歷了那次蟑螂事件。於是我們大起知己之感。我在詛咒了一會兒蟑螂後,問起她蘇迎的情況。不料她眉頭一皺,神情立刻顯得不大自在。
我馬上想起在學校碰到蘇迎的那些同學的情景。這中間一定有什麼問題。
「你和蘇迎很熟嗎?」陸燁倒先問起我來。
「不熟。我只是她的鄰居,隨便問問罷了。」我連忙解釋。
「哦……是這樣啊。其實我跟她也不太熟的。但是……」那女生的表情又變得很猶豫,好像有什麼又不大好說的樣子。
「怎麼了?她是不是有些什麼地方不大對勁?」我追問道。
陸燁果然改變了態度。她湊過來,小聲地對我說:「她可是個神經病。真的。」
「哦?」我有點意外,但也沒有很奇怪,大致上我猜得到原因。
她看我的表情不像是相信她的話的樣子,便愈加認真地對我解釋:「蘇迎她真的在精神方面有問題。大一剛入學的時候她就因為住院休學了一年,所以我們都和她不太熟。但她這個人真的很怪,整天神神叨叨的,就喜歡說什麼海……海底人什麼的,好像是那種強迫症吧,常常說這個和海底人有關、那個也和海底人有關,可別人一說她,她就激動。你和她說話時你沒覺得嗎?」
這番話猶如當頭一記悶棍,令我愣在那裡出聲不得。原來……原來所謂海底人是這麼回事。這個打擊太過突然,我愣了半晌才回過神來,也顧不得避嫌,好不容易又問了一句:「那她的水性怎麼那麼好?」
陸燁的回答是:「蘇迎她以前是專業游泳隊的,好像進大學前一直是市隊的。聽別人說,要不是她精神有問題,憑她的實力早進國家隊了。她還老說自己是海底人,真是笑死人了。」
我極為勉強地擠出一個估計比哭還難看的苦笑。我覺得我好像徹底被人愚弄了。要怪,就怪蘇迎長得漂亮,令我不忍輕易質疑她。現在我再次回想蘇迎的一舉一動,一些神經質的細小動作啦、講話有時顛三倒四啦還有容易激動等等,都可以解釋得合情合理了。還有昨天晚上她自稱海底人,看來她對好些人說過她的這個「秘密」了。
我再次給自己敲響警鐘,不斷自責,下次絕不能輕易相信女色,同樣的行為要是發生在一個長得歪瓜裂棗的女人身上,我早罵一句「神經病」然後拒不理睬了。話雖如此,蘇迎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原本是充滿神秘色彩的美女,一下子變成了有血有肉的神經病,倒好像是真實了不少。
最可氣的是,她偏偏在我被捲入一些怪異事件時出現,硬是牽著鼻子把我拽進了所謂「海底人」的思維怪圈裡,使我大走彎路、白費腦筋。現在想來我一開始以海底人為出發點根本就是錯誤的,這麼一來還怎麼想得出正確結果?
話雖如此,但我很快發現,即使排除海底人的因素,僅僅在怪貓、蟑螂和志丹苑考古之間,同樣還是理不出什麼頭緒來啊。我暗自歎了一口氣。
陸燁見我不語,以為我不高興了,忙又說:「不過她現在應該好了,既然能讀書也就不會有什麼事了,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立刻正容微笑,不能讓人誤會,確實我也沒怎麼放在心上。接下來要做的就是把這件事情再放在沒有海底人的前提下找出聯繫來。我又在報社待了一會兒,左思右想,自從大學畢業以來我很久沒有這樣用腦了。待了許久,我還是決定再回志丹苑發掘工地去看看。傻坐著也不是辦法。
來到社區門口差不多是五點左右,天還沒有開始暗下來。我趕到工地,裡邊的工作還在進行。遠遠地還是看到考古隊隊長張強站在上次見到他時的那個老位置。不過這次他身旁多了一人。我一眼就認出那是阮修文。阮修文的膚色和張強的相映成趣,一個像是白巧克力而另一個像是黑巧克力。再走近幾步一看,發現阮修文的手臂略微黑了一些,有點向牛奶巧克力靠近,不過看上去還是好像與張強不是同一個人種,也許是因為兩天來他一直在工地的關係吧。
阮修文的神色凝重,手裡拿著一張地圖。他一見到我便客氣地招呼,張強則只是點了點頭。
「我就住在這裡,順便過來看看,不會耽誤你們工作的。」我笑著解釋了一下,阮修文剛才的神色引起了我的好奇,「有沒有什麼新進展啊?」
「唉!」阮修文直搖頭,「這個工地的開挖規模是有限制的,不能再往這條延長路方向挖過去。」我往地圖上看去,延長路上用紅筆打了個顯眼的「×」。
「這樣原地挖掘下去進展也不會很大了。基本上主要構造都已經開掘出來,現在這樣只是例行公事。雖然如此,我始終認為在這個方向開掘下去會有新發現。」阮修文繼續道,口氣中充滿掩飾不住的失望。
張強也在一旁插嘴說道:「估計要到一個月後,等市政府有關方面統一協調過後,檔批下來了,才能把延長路挖開。到那時可能會找到一些新的發現,你到那時再採訪吧。」他顯然還是不太歡迎我的到來。
我裝做沒有聽懂他的意思,試探性地追問彬彬有禮的阮修文:「在這兩天考古的過程中,你有沒有碰上一些奇怪的現象?」
「沒有啊。你是指哪方面?」阮修文一臉迷茫。
「嗯……」我看阮修文的神態不似偽裝的,但仍繼續補充道,「奇怪的昆蟲啊,或是和平時不一樣的現象之類的?」
阮修文和張強都是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看來兩人什麼也不知道。我在失望中與他們告別。
然而我再次回頭觀察整個工地,總覺得有點彆扭,也就是說隱隱約約地覺得有些什麼地方不太對勁。可究竟是什麼呢?也許是阮修文穿著襯衫、打著領帶,卻頂著安全帽的不和諧?或許是兩人的皮膚色差太大?不是。我不能再為這種無聊事平白浪費我的腦細胞,還是先回家再打算。
才走到我家樓下,又聽見蘇迎在樓上喊我。
「怎麼樣,上樓坐會兒嗎?」她依然興致勃勃地要我去陪她聊天。
但下午從實習生那裡聽到的話確實對我產生了影響。她就算現在好了,但她畢竟是有精神病病史的人,我不清楚這樣的人會不會把病態時的思想載入現在還算正常的腦子中去。當然我相信她不是故意拿海底人來消遣我。想著想著,我不可避免地在心裡對她產生了一點排斥感。
「我今天有重要的稿子要寫,沒時間了,對不起。」我不好意思正面看她,第一次拒絕了蘇迎的聊天邀請。
「啊,是嗎?你要寫多久?」她似乎仍不願放棄。我大聲道:「今天恐怕是來不及了。」她顯出很失望的表情。
儘管心裡有些歉意,但我絕對需要時間來好好思考一些問題。我原本以為和蘇迎這樣熱衷神秘事件的人交流會得到啟發,現在想來根本都是在浪費時間,只是聽她固執地堅持海底人云云,毫無有價值的線索。我一向都相信我的腦袋在夜晚效率比較高,所以要好好地利用這段黃金時間。
然而光是我手上的資料實在是太少了。我除了蒐集一些大同小異的有關志丹苑考古遺址的新聞報導,剩下的也就是關於一隻怪貓和一群怪蟑螂的一段身受其害的親身體驗罷了。難以下任何結論。冥想了幾小時,和白天一樣茫然無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