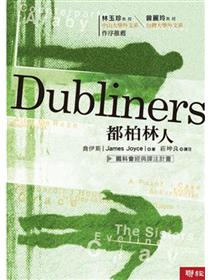致父王,加爾尼西亞國王陛下
幾個月前,父王曾召我至議事殿,並命我與眾大臣一同列席。當時我以為父王有意准許我參與商討國政大事、學習行使權力。我心想,「父王知道我長大了。我已經十五歲,他認為我能和大臣一樣提出自己的看法。」我感到惶恐,但是受寵若驚。我終於得到父王的重視!
但我錯了。
怎麼也想不到母后也走進了大殿。她帶了厚厚一疊筆記與紙張,我頓時醒悟而臉色發白。
原來母后奉您的旨意搜索了我的房間。她手上的文稿全是我這些年來所寫:我的日記、我的秘密、我的夢想、我的詩、我的故事。
我的靈魂赤裸裸地攤在那兒,在桌上,在您面前,在所有議事大臣面前。
我不禁全身顫抖。母后抱著手,以嚴厲的眼神打量我──而她看我的眼神何曾不嚴厲?
您翻閱手稿,嘴角微微揚起,表情古怪。您站起身來,一眼也不看我,便開始高聲念出我的筆記內容。
起初眾大臣保持沉默,全神貫注。他們不明白父王您的目的,但我立刻瞭然於胸。
您朗讀之際,多次不經意露出輕蔑的笑容。您刻意加強某些字眼,並強調青澀笨拙之處,以致大臣們也一一笑了起來。
拜父王之賜,我驚愕而無助地楞在當下,而您卻是滿臉愉悅,一面手舞足蹈,一面以裝腔作勢的語氣來強調我字字句句的荒謬。我唯恐自己出聲怒吼,不得不咬緊牙關,上下顎還因此疼痛多日。
突然間,您闔上手稿,臉上重現嚴峻神情。「玩笑到此為止!」接著您對眾臣說,「各位可能感到好奇,這些曠世傑作出自何人之手?作者就在這裡。大家一起為我們的……小公主喝采吧。」
大臣們驚訝萬分,一雙雙眼眶發紅、泛著淚光的眼睛紛紛朝我看來。有人咳嗽,有人仍忍不住大笑。其中還有一人,我記得是農業大臣,甚至嚇得連口水流到襞褶上亦不自覺。
當時您命我起身,對我說,「公主,妳該停止這種幼稚行為了。妳是加爾尼西亞唯一的王位繼承人,不久之後,妳將正式代表這個國家。我們的國家不需要這些無聊廢話。」
您將手稿遞給我,命令我擲入火中。
我朝著壁爐走了幾步,一面走,一面盯著掛在牆上的加爾尼西亞國旗,心中暗暗詛咒這面畫著兩支箭射穿黃綠條紋的旗幟所象徵的一切。
我跪下來。當我放開手中的筆記時,火焰輕掠過我的手,那灼燙的感覺痛徹心肺。當我重新起身時,您顯然十分滿意。
就在此時此刻,我拋下這幾個星期以來的猶豫,下定了決心。
我走出議事殿,眾大臣與母后以輕蔑眼神目送我離開,但我已毫不在意。
好了,親愛的父王,這便是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您是個好國王,所有的加爾尼西亞人民都這麼想。他們是對的。您以公平正義治理國家,您的行為舉止充滿寧靜詳和。然而身為父親的您卻截然不同。
這封信就任憑父王處置吧!您樂意的話,盡管連同其他筆記一起燒毀。我只希望您會因內疚悔恨而難以入眠。
我要享受我的自由了。這個字眼何其美麗。從現在起,您將有充裕的時間好好思考。
瑪爾娃叩上
第一部 出走
一、刺蝟頭
城堡北邊,城牆高聳於一處危崖上。位於峭壁頂端的城堡彷彿一隻伺機而動的老鷹,有如翅膀一般的塔樓與側翼俯瞰著河谷,巨大的身影倒映在平靜的格達維河上。自古以來,無論是丹布拉文或是諾治王國的入侵者,都因這面城牆而粉身碎骨,戰士與畜牲在此喪命。數月間,不斷有頭盔、甲冑與人畜的屍體順著格達維的河水而下。
但位於城堡南邊的景致便截然不同。它的正面有許許多多扇窗戶洞開,緩坡上綿延不斷的梯田盡收眼底。那兒有一排排整齊的杏樹、橄欖樹和檸檬樹,樹下長滿肥美的青草。還有鋪設著藍綠色馬賽克磚的水池,不僅讓人在散步時神清氣爽,也引來不少鳥兒聚集。不久前,國王開始熱中於熱帶植物,並且分別將兩塊梯田改種稻米與棕櫚,四處可見高大的竹林在初夏微風中搖曳不定。
這座城堡正是加爾尼西亞王國的核心。這幾年來,國王謹遵國內人民最敬重的「寧靜女神」與「和諧女神」的訓誡治理國事,向來國泰民安,人民也過著幸福的生活,然而……在這天夜裡,誰也沒料到這個國家無憂無慮與和平的日子即將結束。
瑪爾娃終於躲開了母后的監視。
這在平日已經不容易辦到,尤其是這天,瑪爾娃更覺得希望渺茫:除了在裁縫和舞蹈老師身上浪費時間之外,她都被罰在神壇前面祈禱。王后逼她趴在冰冷的石板地上,覆誦禱文五十多遍。瑪爾娃原本已經習慣公主應學習的禮儀規範,可是這一天,卻難掩心中的不耐。她握緊拳頭,心中不斷暗想,不久這一切都將只是惡夢一場。
夜晚終於來臨,王后有事先離開。由於她忙著指揮下人,竟沒看見瑪爾娃從精巧殿逃走,在那兒,有一班僕役正在為明日的慶典做最後的準備工作。
小公主像個幽靈似的,悄悄地往南翼建築奔去。她經過廚房,再爬上舞蹈廳,只見十來個安靜無聲的女僕跪壓著裙襬,努力地打亮鑲木地板。在走道上、階梯上、長廊上,她遇見一群又一群的侍從,他們用滑輪將吊燈放下、換上新的蠟燭,或是清除地毯的灰塵。誰也沒有注意到她。
在城堡外頭,修剪完樹籬的園丁,正把彩色燈籠掛上橄欖樹。瑪爾娃經過一扇敞開的窗戶時,聽見大水池開始噴水,遠一點的涼亭裡則有樂師在演練小夜曲。那音符飄進溫暖的暮色,和茉莉的香氣揉在一起。
瑪爾娃感覺得到城堡裡外的加爾尼西亞都瀰漫著一股興高采烈的氣氛。這個好日子與她切身相關,但她卻感覺不到絲毫喜悅。老實說,她腦子裡想的是另一件事。
當她來到南翼的凹室,才鬆了口氣。有個高瘦的女孩站在房間中央,兩手緊抓著圍裙。那是小公主的貼身侍女菲樂曼,她依照計畫在那兒等著。
瑪爾娃沉默地關上門,然後走到鑲螺鈿框的長鏡前坐下。她摘下頭上的髮夾,拿起剪刀遞給菲樂曼。
「快。」她輕輕地說,「動作快。天就要黑了,而執政官還在等我們。」
菲樂曼站在她身後,動也不動,瘦削的臉龐似乎比平時更加蒼白。
「我……我不明白。」她囁嚅著說。
瑪爾娃不耐地從她手上搶過剪刀。「什麼嘛,妳當然明白!快點!」
菲樂曼伺候小公主多年。從公主還是小嬰兒就開始了,而當時的她也不過是個小女孩。瑪爾娃一直把她當作親姊妹般信任,菲樂曼也對主人忠心耿耿。但有些事情卻是她的信仰所不允許,例如嘲弄和諧女神的規範。
「不行,我做不到。」最後她痛苦地說,「除了這件事以外,要我做什麼都可以……」
鏡子裡映照著她二人的臉。瑪爾娃那張十五歲的臉龐仍保有童稚的圓潤與細緻,相較之下,侍女的臉就顯得病懨懨了。
「拜託,菲樂曼,妳就照我說的做,執政官也說過──」
「之前沒有說到要剪頭髮!」侍女打斷她的話,同時把剪刀往梳妝台上一丟,好像那是件不祥之物。
她雙臂抱胸。見她這副固執的神情,瑪爾娃知道她沒辦法讓菲樂曼改變主意了。
「妳真好笑。」小公主氣惱地嘆了口氣說,「這幾個星期,妳一口答應跟我去冒險,結果現在呢,只為了頭髮這點小事!」
菲樂曼猛搖頭。頭髮可不是小事!沒錯,最近無論要她做什麼她都答應了。瑪爾娃叫她說謊就說謊,要她行賄、偷東西,她也都照做。她已經準備好,即使為公主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可是剪頭髮這事實在太強人所難。
「從妳出生到現在我替妳梳頭多少次。」她回想道,「為了讓妳的頭髮服貼、光滑、柔順,我用盡各種髮蠟和香脂……妳也一直引以為豪的呀!」
「一直都很引以為豪的是母后。」小公主反駁道。
「那又怎麼樣?」菲樂曼生氣道,「又不是非剪不可!妳可以──」
她兩手捧起瑪爾娃的頭髮,在頸後盤成髮髻。瑪爾娃照照鏡子,在蠟燭的橘色微光中,她彷彿頂著一圈絲綢。她想起了去年十四歲生日,有個畫家為她畫肖像。為了讓她的髮色更美麗,畫家特地從遙遠的奧尼安王國,訂購一種由術士製造的特殊黑墨。「彷彿是黑夜的精華呀。」他一面揮動畫筆一面讚嘆。這幅畫像的名氣不僅傳遍全國,甚至成為重要的象徵,小公主的頭髮代表令加爾尼西亞人民自豪的美。
「妳換裝之後有風帽蓋住,誰也不會發現。」菲樂曼接著又說,擺明是想說服小公主。
瑪爾娃猛地掙脫她,一手抓起剪刀,一手握住頭髮,毫不猶豫一刀剪下。
那綹頭髮留在她手裡,隨即如花瓣一樣散開,就像剛摘下的花朵。菲樂曼抽噎著。在她眼裡,瑪爾娃剛犯下褻瀆之罪,但小公主卻毫不在乎。頭髮一束接一束掉落在腳邊,她一刀又一刀隨意亂剪,琥珀色的瞳眸散發出一種令人驚懼的狂喜。有幾撮頭髮從她領口掉進去,沿著兩側肩胛骨之間直滑到臀部,搔得她背癢癢的。
最後當瑪爾娃放下剪刀,鏡中出現的是一個頂著刺蝟頭的女孩。樣子看來好奇怪,好可笑,她忍不住便笑了出來。
「這就是失去了美麗娃娃的加爾尼西亞啊!」她大喊道。
這時她真想跑到城堡另一頭讓所有人(特別是母后)看看自己。可以想見王后驚慌尖叫的模樣,「瑪爾娃!神聖的和諧女神保佑,妳看妳做了什麼好事?」不過,她當然不能讓這樣挑釁。會壞了大事。
「現在,」她對菲樂曼說,「去把我喬裝用的東西拿來。」
侍女雖然情緒激動,還是遵從吩咐。瑪爾娃看著她打開凹室深處的暗門,走進密道,她覺得充滿信心。這幾個星期以來,這些動作她們複習太多次了!而且執政官也在,有了他,一切都會順利。
房裡只剩她一人,瑪爾娃從長裙褶縫中拿出寫給父王的信。紙都皺了。她把它攤開在梳妝台上。「致父王,加爾尼西亞國王陛下……」她再看一次信的開頭,卻覺得噁心。該怎麼做才不會讓這封告別信馬上就被父王發現?瑪爾娃想不到任何可以交付的人。執政官也許會有辦法吧?她暫時先把信塞到鏡子背後。
她的目光再次落到鏡中人影。這是瑪爾娃第一次注意到自己的耳朵形狀奇特。平常有頭髮遮住,而現在卻從臉頰兩側冒出來,好像在頭上插了兩支怪異的小旗子。
「就算逃亡失敗,誰會想娶一個長著大耳朵的刺蝟呢?」她噗哧一笑,「絕對沒有!」
她腦海中浮現明天眾多賓客魚貫而行的畫面:加爾尼西亞的所有貴族進入聖堂,男士的粗壯脖子縮在硬領子裡頭,女士則戴著羅紗帽,屈膝行禮,面帶甜美的微笑……她想像著有如看家狗一樣看守著她的父母親站在神明面前。「國王與王后的獨生女就要出嫁!真是令人雀躍呀!祝新人百年好合!」
瑪爾娃克制住尖叫的衝動。她緊握雙拳,重重壓在胸口。
「呼吸,呼吸!」她大聲命令自己。「這一切都不會發生。妳不會穿上禮服,也不會戴上貝殼皇冠,更不會有神聖祭品。妳誰也不嫁。」
所有的一切發生在幾個月前,寧靜女神祭期間。當時執政官一時失言,意外說出事實真相──。至今瑪爾娃依然能聽到這句話在耳邊迴響,
「小公主,妳該為新婚之夜準備了吧。」
瑪爾娃不覺打了個冷顫。
「怎麼?」執政官驚訝地問,「王后沒有告訴妳嗎?」
沒有。王后認為沒有必要告訴她正在為她安排婚禮!至於國王,他從來不曾騰出時間和女兒說話。對他來說,小公主不過是手中的籌碼,只是用來換取政治利益的東西。
瑪爾娃震驚之餘,不禁勃然大怒。而且還是在寧靜女神祭進行之際,這是多大的褻瀆!幸好執政官是個幹練的人,又受人尊敬,而且自從國王命令他負責教導公主以來,始終對公主忠心不二。他對聚集在聖堂裡的親信解釋一番之後,議論便平息下來。只有瑪爾娃心中的怒火依然熾熱。
接下來幾天,執政官不時到她房裡探視,希望能讓她恢復理智。
「所有的公主都年紀輕輕就結婚。」他說,「妳母后結婚時也不過十三歲!據我所知,她也過得很幸福!所以我不明白妳為什麼反應這麼激烈。」
「你知道的。」瑪爾娃哭著說,「你很清楚這個婚姻對我會有什麼影響!我將必須放棄目前為止生活裡的樂趣。我再不能學習、看書,不能盡情地表達我的想法,也不能獨自外出!」
執政官煩惱地嘆息,「我知道,公主。但妳別無選擇。」
瑪爾娃強忍憤怒,執政官怎麼能這麼快就放棄投降?
「你教了我那麼那麼多!」她對他說,「因為有你我才發現讀書、寫字、思考是多麼幸福的事!你甚至讓我渴望旅行,渴望一嚐自由的滋味!」
執政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不過是個卑微的教師。教妳這一切的不是我,而是那些書的作者。但是公主,書本畢竟不是人生。妳必須捨棄童稚的夢想。妳必須履行義務。」
瑪爾娃頓時感覺自己遭到背叛、拋棄。
「妳要相信妳的母后。」執政官再次以溫柔語氣對她說,「她為妳挑選了最好的伴侶。安德馬克王子才三十三歲,聽說他舞跳得很好。」
瑪爾娃根本不在乎安德馬克王子和他的舞技。每當她閉上眼睛,就會看見自己在新婚之夜被關在房間裡,這時胃便會因為過度恐懼而開始絞痛。
她小時候有一次參加納貢禮:來自舊世界各地的使者排隊將禮物送進城堡中庭。其中有一個人牽著一隻巨大的爬蟲。「這是我在亞雷米克地抓到的母鱷。」他說完便搬出一個籠子,有隻嚇壞了的兔子蜷縮在裡面。使者將兔子交給國王,說道,「請您將兔子拋到空中,再看看有何結果!」國王果然將可憐的兔子拋出,只聽到喀喇一聲,巨鱷已經將獵物吞下肚去。
活生生地。
貴族們掌聲如雷。
瑪爾娃覺得自己的處境和那隻兔子一模一樣:他們想把她餵給一個陌生人,而這個陌生人將會一口吞掉她。
最後,執政官終於明白她打算不顧一切逃婚。有一天晚上,他向公主坦承自己的憐憫之情:
「妳這麼年輕、這麼美麗……這麼有天份,妳的個性非常獨立,妳不想一輩子在一個對妳來說年紀太大的男人懷裡扮演花瓶的角色,這點我可以理解。」
瑪爾娃抬起琥珀色的雙瞳看著他,眼中滿是淚水。
「去跟母后說!去跟父王說!」她哀求道,「請他們取消婚禮!」
執政官搖搖頭。他的權力很大,但這還不夠。加爾尼西亞需要與安德馬克聯姻,國王是不會改變心意的。
「妳的父親要求我教育妳,但其他的……我無能為力。」
「那怎麼辦?」瑪爾娃絕望地大喊。
「我不知道。」執政官回答,「但我要妳知道,不管妳決定怎麼做,我都站在妳這邊。」
瑪爾娃不斷從各種角度考慮這個問題,她想了好一陣子,最後只想出一個解決的辦法:逃走。這的確是躲避這樁婚姻的唯一方法,但瑪爾娃卻無法下定決心,恐懼一直折磨著她,於是她一再將決定延到第二天。
直到國王召她前往議事殿,並逼她燒掉筆記手稿,這莫大的羞辱瞬間驅散了她的恐懼與猶豫。她一走出議事殿就立刻去找菲樂曼,告訴她自己的打算。
「這樣的話,」菲樂曼馬上低聲回答,「我也跟妳一起逃走。」
於是她們倆便一起在執政官的協助下,展開縝密的逃亡計畫。
瑪爾娃突然出手將鏡子翻倒,因為那個模樣到底還是讓她不舒服。那封告別信也因此滑落到梳妝台後面,但她沒發現。她起身走到窗戶旁邊,拉開窗簾。
月亮尚未升起,地平線那端的果園背後,仍殘留著一道細細的黃昏微光。東方有山陵起伏,當中有幾處因格達維河蜿蜒流過而中斷。「我可能永遠不會再回來了。」她心想,「我再也嚐不到園子裡的水果,再也看不到加爾尼西亞的夏天……」忽然感覺喉嚨梗塞,連忙吞了一下口水,現在就開始懷鄉未免太早了。於是她將窗簾放下。
此時,菲樂曼從暗門後面出現。她一言不發地將裝著喬裝用品的小包袱放下來,裡頭有一條棉褲、一條粗麻布裙、一件袖子樣式簡單的卡其色上衣、一頂沒有繡花的軟帽。瑪爾娃還在外頭披上羊毛斗篷,那是菲樂曼在牲畜市集上從農婦那兒偷來的。穿上這身破舊的服裝,就不會引人注目了。風帽很寬大,頭一低就會蓋住眼睛。
「我看起來怎麼樣?」瑪爾娃問道。
「像個普通的女孩。」菲樂曼仔細打量後說。
小公主不禁露出微笑。從此以後,瑪爾娃──加爾尼西亞唯一的王位繼承人,將只是一個普通女孩。
菲樂曼收拾公主的衣服,把一綹綹的頭髮捲在裡面,全部一起用包袱包起來夾在腋下。她們的家當都在這個包袱裡頭:幾件換洗衣物、一塊麵包、幾顆橄欖、執政官給她們的好幾塊金幣,和幾本新的冊子好讓瑪爾娃記錄她的冒險歷程。
「走吧。」她說著便往秘密通道的入口走去。
菲樂曼跟在後面,隨手將門關上。當她們步入黑暗時,瑪爾娃猛然發現這已不只是單純的排練了。
致父王,加爾尼西亞國王陛下幾個月前,父王曾召我至議事殿,並命我與眾大臣一同列席。當時我以為父王有意准許我參與商討國政大事、學習行使權力。我心想,「父王知道我長大了。我已經十五歲,他認為我能和大臣一樣提出自己的看法。」我感到惶恐,但是受寵若驚。我終於得到父王的重視!但我錯了。怎麼也想不到母后也走進了大殿。她帶了厚厚一疊筆記與紙張,我頓時醒悟而臉色發白。原來母后奉您的旨意搜索了我的房間。她手上的文稿全是我這些年來所寫:我的日記、我的秘密、我的夢想、我的詩、我的故事。我的靈魂赤裸裸地攤在那兒,在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