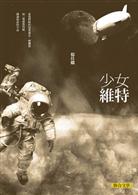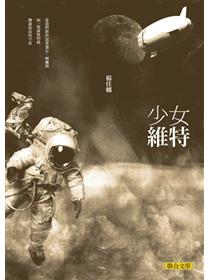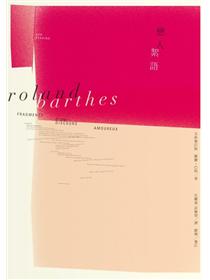輕騎士
我突然明白,這世界原來是眾神合資經營、管理的一個小小的摩托車出租站。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台不佔什麼空間、不佔什麼時間的輕型機車,雖然我們的行李無比沉重。我們的靈魂騎著我們的身軀,輕輕騎過這世界凹凹凸凸的山嶽河谷高樓低田陰道陽貨日日夜夜。像一件薄紗輕輕掠過膚淺的肌膚,像輕風掠過薄薄的水面,我們輕薄地對胯下世界做植物性、動物性、礦物性、寵物性、精神性、肉體性、宗教性、哲學性、嚴肅性、趣味性、商業性、學術性、結構性、策略性、理論性、臨床性的「一次性」騷擾。你好,親愛的氣候,我會載著你們厚厚的祝福與束縛;你好,親愛的師長,我會載著你們厚厚的教誨與後悔;你好,親愛的祖母,我會載著你們厚厚的裹腳布與電話簿;你好,親愛的窺淫者,我會載著你們厚厚的臉皮與眼皮。穿過陰影的地圖,經度緯度如此重,速度如此輕;穿過光的地球儀,海與天的床榻如此重,藍色如此輕。在愈來愈輕的引擎聲中輕輕進入愈來愈輕的輕金屬,輕工業,輕音樂,輕歌劇,輕文明,輕道德,輕死亡,輕永恆……
二OO六.三
輯二
隱私詩
八
我不是鬍子
我是鬍子後虛掩的口
也有嘴唇,也有口水
跟山頂洞人住的地方一樣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洞穴
藏在一個不動時像屍體的
活動山坡裡頭:尸——
什麼東西吊在我前面
晃來晃去,自以為屌?
還不趕快閃開
或者進來
吊
好累
吊在這裡這麼久
像一個乏人觀看
不斷變化字與字體的
告示牌
有時爆滿如粗黑體30級的
窘
或勇
有時稀疏如細明體7級的
丁 或 卜
依附著一具尸體
是死是活,前途未卜
放我下來,不然把我處死
口吐白沫,樂死爽死
比
這是公平的
你的屁股鄰著我的屁股
平起平坐
你有的,我也有
你會的,我也會
你聽得到的,我也聽得到
你聞得到的,我也聞得到
嗯?這是什麼味道——
佛曰,不可說
子曰,不可說
耶穌也說,不可說
他說:這是公平的
皇帝有的,你們也有
米
民以食為天
在地上播種灌溉
長出米,變成飯
進入我們的嘴巴
進入我們的身體
像進入一座環保回收場
分門別類,加工回收
液體類:從眼睛出來
軟體類:從耳鼻出來
硬體類(¬及其軟化、液化的瑕疵品):
從肛門出來
人在做,天在看
看人人勤做環保工作
一樣米,屎百款人
這迷人、迷你的米
從地上來又回到地上
千變萬便
與天人同在
水
如果我被邀請/創建一種宗教/我將利用水。
——Philip Larkin(1922-1985)
所以我們都是拜水教徒
我們身體百分之七十由水構成
一如我們星球表面十分之七是水
我們的身體就是我們的教堂
水是我們的聖餐
飲酒喝茶,吃湯喝水
以水連禱,相濡以沫
我們是天生的罪人
需要懺悔,洗罪
用聖潔無比的水淨化我們的罪孽
每一天都是禮拜日
對著形形色色聖杯似的便器或曠野
緊縮快放,用力告解
二OO七.十二
註:此詩所隱五字分別是屄、屌、屁、屎、尿,五種身體情態;它們是隱字詩,也是隱私詩,隱尸詩。
輯三
慢陀螺
夠慢了,這一生
在有限的土地上打轉
慢慢地,以一向下
之軸為筆心,書寫
停頓,書寫,在直徑
大於七尺小於夢的
透明稿紙上,以一
偶然飛起之陰莖
釘向天空,犁開田畝
挖掘生之快與不快
慢慢地,編纂不被
出版的網誌地誌
鳥獸誌,以虛擬的
海面,地平線,以斷
斷續續的高潮,迴響
夠慢了,這單調而
重複的旅行文學
窄窄地,在家鄉翻轉
異鄉,在此際呼喚
他日,慢慢習慣以
工作為遊戲,以遊戲
為工作,以痛為不痛
當那鐵軸釘向自己
夠慢了,這排版
校對,列印,廣告
關於唯一又不斷修訂
的路線問題,關於風
慢慢剝落,風化,慢
慢漫遊,纏繞,開放
朝遺忘自轉的圓錐體
轉旋交織出一個圖案
一個複雜又簡單的
輪圓,一株恍惚而
窈渺的看不見的花
他們說,曼陀羅
二OO八.六
註:「曼陀羅」(Mandala),梵語,意為「圓形」或「中心」,是諸佛設壇修行成佛的地方,亦指在畫面上繪方形或圓形土壇,在壇內繪諸佛菩薩之像,並加以供奉;引申為宇宙整體之縮影,或個體內在的小宇宙。
後記:片面之詞 陳黎
《輕/慢》是我第十本詩集。這本詩集寫作過程與成書方式,和我先前詩集似乎稍有不同。這本詩集第一首詩寫於二OO六年二月。次月,在寫完第二、三首詩——〈輕騎士〉和〈慢板〉——後,我就想好要以「輕/慢」做為這本詩集名稱。「輕/慢」一方面是「輕或慢」,「輕和慢」,一方面則是「輕慢」。從小到大,我被許多人視為對許多人、許多事態度輕慢。「輕慢」做為我做人或作品調調的標示,似乎也算適切。而年歲漸長,對於過往自己個性的焦躁不安,過度看重某些事物,頗覺不滿,亟盼能慢下來,輕下來,從容面對世界。輕、慢就成為令我嚮往的兩個語詞或情境。
想好以「輕/慢」為名的同時,我還想到讓這本詩集的詩依著寫作時間,一路排列下來。我感覺這本詩集可能有三輯,一端是「輕」,一端是「慢」,但什麼時候完成一輯,進入下一輯,就讓它順其自然,止於所當止,行於不得不行。如此,從二OO六年二月到二OO九年三月,以三年時間,完成了這本詩集。
輯一中〈夜歌二題〉裡「不眠女之歌」一詩是看了日本古代繪卷《病草子》後所作,繪卷裡諸奇病中有一為「不眠症の女」;「夢遊女之歌」寫時則希望是一首可以被唱的歌,我心頭一定閃過義大利歌劇作曲家貝里尼的名作《夢遊女》,雖然我的詩與其無關。後來果然變成了歌:我女兒的老師,北藝大潘皇龍教授,在聲樂家協會二OO八「我們的詩人,我們的歌」委託創作發表會中,選了此詩譜曲,由作曲家妻子女高音林玉卿教授首演。
〈荼蘼姿態〉一詩的寫作是由於香港《字花》雜誌二OO七年初的約稿:以「爛」字為主題寫一篇文字。我即刻想到我女兒二OO五年所作的薩克斯風獨奏樂曲《荼蘼姿態》,我記得當她寫好樂曲叫我幫她去影印樂譜時,看到她在樂譜前面打列的文字,我驚覺我的散文集《立立狂想曲》裡那個國小三年級女孩一夕間變成大人了。她樂譜前寫著:「荼蘼。植物名。薔薇科懸鈎子屬,落葉小灌木。葉為羽狀複葉,柄上多刺,夏初開黃白色重瓣花。/姿態。姿容態度。阮籍詠懷詩:『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荼蘼姿態。含苞。盛放。腐朽。開到荼蘼花事了。荼蘼過後,韶華勝極,無花開放。」我在電腦前很快地寫成了〈荼蘼姿態〉一詩。我隨後又寫了一首以「開」字為主題的〈開羅紫玫瑰〉。
〈五行〉一詩則是應「現在詩日曆」之邀寫的,他們約寫五行以內的詩五首,好印在小日曆書上。我寫了五首(或五段)五行的詩,合為一首,以為他們會在日曆上相連五日將之印出,沒想到被拆散到春夏秋冬不同季節裡,這樣就看不到我構築此詩的原意了。「五行」是五行(ㄏˊㄤ),也是「五行」(ㄒーˊㄥ),我讓被稱為五行的木、火、土、金、水五元素,在五首五行詩裡運行輪轉,依次出現(或不出現)。跟〈荼蘼姿態〉一樣,它是無格律的自由詩,但自有其規律和節制。
〈盆地頌〉、〈愛蘭台地〉、〈澀水〉等三首是二OO七年五月我在暨南大學擔任駐校作家期間所寫。我沒想到會在島嶼中央埔里寫出〈愛蘭台地〉這首詩。二十年來我試圖透過書寫,重組、建構島嶼台灣的圖像,此詩是其延續,是我的另一小塊台灣詩拼圖。
輯二「隱字詩」可能是喜歡買字典、喜歡給學生猜謎的我,積累多年迸出的戀(漢)字癖併發病。離開中學教職後,這幾年經常到島嶼各地談詩唸詩,很多時間都在火車上。在火車上想詩、寫詩,成了新的習慣。輯二中的詩絕大多數在二OO七年底、二OO八年初寫成,而且許多是在旅途中發想或完成:在一個多月間寫了七十多首詩,在我生命或寫作經驗裡相當獨特。我在嘉義旅店大廳的電腦裡寫成了〈片面之詞〉三首,在台北回花蓮的火車上寫了〈隱私詩〉五首,在另一次火車上寫了〈三合〉三首……。火車上也許很無聊,但當我一口氣把屄、屌、屁、屎、尿五字寫成五首「隱尸詩」時,我自己也覺得驚訝。這大概是第一次有人把這五個形似的中文字集合在一起為題材寫作吧。
輯二的詩可分四類,第一類從〈片面之詞〉到〈隱私詩〉共二十五首,以字的局部為題,將「謎底」的字隱在詩中,算是狹義的「隱字詩」;第二類包括〈字俳〉、〈廢字俳〉、〈十種援ㄐㄧㄠ的方式〉共五十首,是以一個「字」為題,延續我先前《小宇宙:現代俳句兩百首》寫作的新款俳句;第三類是隱唐詩之字而成的〈唐詩俳句〉十二首;第四類從〈國家〉到〈長日將盡〉,共七首以字構圖,隱字圖中的圖象詩——後三類算是廣義的「隱字詩」。這些狹、廣義「隱字詩」的寫作有時候是很武斷或自動的。譬如,從〈五胡〉、〈四季〉、〈三合〉、〈兩拍〉、〈單字〉,從「五」到「一」,先訂立了詩題以及各子詩所隱之字,詩就從這些做為主題的字一一分裂出來了。造字的人自然是巫師、乩童,人與天之間的媒介,後來解字、寫詩的我們也是巫師、乩童,在沒有詩的地方找詩,重審漢字,在平常的地方挖掘不平常。一個小小的漢字常常就是宇宙或部分宇宙的縮影。譬如,寫〈夢蝶〉這首詩時,我發現,一個「蝶」字就是一本生物課本。
有些詩真的是翻字典(紙上或線上)寫出來的。〈字俳〉裡的「卌」、「丼」兩字,我本來也不認識,不會唸,更不用講〈廢字俳〉裡那些廢字、罕字。〈四季〉第四首詩,「冬」底下的兩點,居然就是古「冰」字(我以前自然不知),太妙了,正是我這首詩所需,如是有了這樣的句子;「我們在夜底下取暖/兩根互相鑽火的冰棒」。我不知道是我在寫詩,還是字在寫詩,還是鬼神在寫?
為了寫〈唐詩俳句〉,我一個晚上在電腦上重看數遍《唐詩三百首》,結果得詩十二首。前面幾首可算將唐詩俳句化,到後面就漸成「現代詩俳句」了。這些「俳句」並非自動寫作,也非舊酒新瓶,而自有其成詩規則。寫第十二首時,我覺得我遇到了一首好詩,但依照前面規則卻無法成詩,靈機一動,用一條表示對調字詞的校對符號(S形的線),將「線」與「遊子」二詞對調,如是本來沒有什麼意思的「慈母線遊子上密密言」,變成了非常當代的「慈母遊子線上密密言」。那一條S形的線剛好從原詩中慈母「手中」穿引到遊子「身」上。
輯二最後七首圖象詩成於二OO八年一月的三、四天內。〈一O一大樓上的千(里)目〉一詩,我先有題目,電腦上建構成詩後,我仔細算一算,天啊,這「更上一層樓」後總共一O二層的大樓,居然真的有一千個「目」!這是數學,還是詩?是人在寫,還是天在寫?這首詩寫完幾分鐘,我忽然有一種衝動,想讓這大樓樂不可支的飛起來,遂在底下加了一排「八」字,成為〈噢,寶貝〉這首詩。
這些圖象詩寫完不久,我在新竹遇見了正在進行拙詩法譯準備在法國出版的法國里昂第二大學助理教授Marie Laureillard博士,對台灣圖象詩素有研究的她對這些詩頗感興趣,雖然它們似乎不可翻譯。今年她還在她在法國發表的論文裡討論了它們,特別是〈秒〉與〈白〉兩首。〈秒〉以「禾」、「口」、「少」三者為元素,交疊出「秒」、「和」、「吵」三個字,整首詩可說「和」與「吵」的拉鋸,某類的《戰爭與和平》。〈白〉這首詩我自己相當喜歡:由塊狀的「白」、「日」逐漸剝落成線、虛線,乃至於空白。這是由白日到黑夜,由光到暗,由生到死……的過程,但弔詭的是,在書寫此詩的紙上,最後一行虛線底下象徵黑夜的空白,恰好也是真正的「白」。所以,周而復始地,白日重現,再生。寫完此詩後,我想起了我喜歡的美國畫家羅斯科(Mark Rothko, 1903-1970),他的畫也許冥冥中影響了這首詩。
寫完〈長日將盡〉後,我很想把這首詩的名字叫做「夜歌」。我發現夜到臨,並非日變暗,而有音樂從幽遠處徐徐,斜斜飛來。
這本詩集的寫作大概就像輯三〈慢陀螺〉一詩中所說:「慢慢地,以一向下/之軸為筆心,書寫/停頓,書寫……」,慢慢「漫遊,纏繞,開放」,「轉旋交織出一個圖案/一個複雜又簡單的/輪圓……」,由「慢陀螺」慢慢轉成一株「曼陀羅」。寫完〈慢郎〉、〈慢陀螺〉二詩,我覺得僈得有點重,遂寫了〈慢城〉一詩,讓它「輕/慢」些。如果說我一九九五、九八年寫的兩首〈小城〉,是對我住的小城的版畫與快照,那麼〈慢城〉大概是長鏡頭的「慢照」了。
我的《小宇宙:現代俳句兩百首》涵括了我在一九九三年、二OO六年寫成的兩集三行小詩,輯三〈閃電集〉裡的詩,則或可算是一行之「小宇宙」。在為我詩作的外文譯本準備詩時,我發現〈閃電集〉裡有些詩要翻成法文似乎不太容易,但翻成日文似乎可能,起碼我的朋友上田哲二博士做到了。這本詩集裡的詩其實很多是無法外譯的(譬如輯二裡那些詩),部份因為從詩集《苦惱與自由的平均律》以來,我嘗試在詩中挖掘中文字特性或中文性(Chineseness)所致。
我與上田哲二認識於二OO七年十一月我參與策劃的太平洋詩歌節。他後來又來花蓮,給大家介紹了一些日據時期在台日人寫的短歌,讓我興趣盎然,邀他合作在去年編譯出版了一本收錄一百七十多首短歌的《台灣四季:日據時期台灣短歌選》。去年太平洋詩歌節,我們更一起商討邀請了日本女詩人平田俊子與會,且合譯了多首她的詩作。我發現上田哲二不只與我同年,也跟我一樣,同為好奇兒與工作狂。《台灣四季》中我們選譯了四十幾首與花蓮有關的短歌,後來我又邀他合譯了一些日據時期花蓮日人所寫俳句。他對台灣現代詩以及日據時期在台日人所寫詩歌的熱情一點都不輸給我。結束中研院中國文哲所兩年博士後研究工作後,今年二月他遷來花蓮,任教於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近一年來,承他不棄,陸續日譯了我的一些詩作,預計年底在日本出版。我與他由同年,同好,逐漸情同手足——或者,對於從小聽父母親以日語交談的我而言,他的日本元素起碼讓我獲得了「義肢」之情。〈海濱濤聲〉一詩,如是,是對上田以及我們共同所愛的詩與人,以及我的家鄉的致敬。我在一九九四年寫過一首〈花蓮港街.一九三九〉,這首〈海濱濤聲〉算是〈花蓮港街.二OO九〉。
有了網路和網路上的搜尋引擎後,我很早就發現早在清朝台灣就有「陳黎」其人,更不用說流行單名,人山人海的當代中國大陸。但當我真的在現實生活中收到「陳黎」寄給我的email時,我還是覺得很奇特。「回陳黎email」就好像是對鏡自言自語,然而鏡中的陳黎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這「複數」性的我,象徵性地鬆動了對「一次性、單一的人生」之焦慮。〈隋朝〉一詩中,這渴求「以有限之體/而啟無盡之慾」而未必能的焦慮,讓古往今來帝王或平民,試圖透過後宮或性幻想,建立一個不朽的感官帝國:「我,一個人/而我的陰莖是複數的/我的帝國是複數的……」
〈白No.2〉一詩是詩集中類似主題的圖象式再現與匯聚。跟輯二中的〈白〉一樣,它既是生之讚歌,也是哀歌:對生之歡愉、昂揚、苦惱、衰頹、死之陰影……的詠歎。是節慶似的噴灑,也是剝落、凋離……。但多希望這些普遍性主題的呈示、發展與再現,速度慢一點:「它們來得太快,慢郎,教我如何/慢一點,讓它們慢一點……」我因此在詩集最後安排了〈最慢板〉,希望一切慢一點,再慢一點,再更慢一點,再輕一點,再更輕一點,再更輕/慢一點……
二OO九年四月 花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