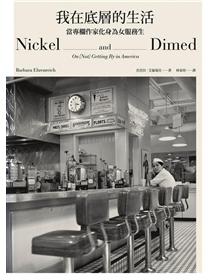本書特色由宮崎駿最親密的工作夥伴、吉卜力工作室製作人鈴木敏夫詳細陳述與宮崎駿、高(火田)勳之間的合作與互動關係,透過他的文字,讀者可以進一步瞭解動畫製作的種種過程,同時也藉由這些幕後花絮看到宮崎駿不為人知的一面。內容介紹鈴木敏夫,這位曾參與製作「魔法公主」、「神隱少女」等知名動畫的製作人,是如何踏入動畫這一行?又是如何成為宮崎駿‧吉卜力工作室不可或缺的得力夥伴?本書由鈴木敏夫親自陳述他進入日本德間書店後,因為負責『Animage』動畫雜誌創刊的編輯工作而得以認識手塚治虫、宮崎駿、高畑勳等動、漫畫家,並進而參與動畫電影製作的種種過程。書中詳細敘述他與宮崎駿、高畑勳之間的各種互動,藉此除了可以知道吉卜力工作室製作動畫時的狀況,更可一窺宮崎駿不為人知的一面,並進一步瞭解動畫大師的創作想法。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鈴木敏夫1948年出生於日本名古屋市。1972年自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畢業後,進入德間書店工作。曾於『Animage』等編輯部擔任編輯一職,之後藉由『風之谷的娜烏西卡』的機會轉往電影製作發展。1989年起全心投入STUDIOGHIBLI的工作,並以製作人之姿接連製作出『魔法公主』、『神隱少女』等叫好又叫座的動畫電影。現任STUDIOGHIBLI代表取締役製作人,著作有『電影道樂』(PIA)。
章節試閱
4
「半徑3公尺內遍地是企畫」
──宮崎駿的電影術──
他不信任邊看資料邊畫圖的人。
或者應該說,只要有志從事繪畫這一行,就會對各種事物抱持好奇心,日常便時時在觀察著。
那樣的日積月累才是最珍貴的事。
(「宮崎駿的情報源」二○○二年)
在創作『霍爾的移動城堡』裡的那座城堡時,是先創作城堡頂部之後,再一樣一樣地慢慢增建,之後才組合成一座城堡。
而且,竟然完全沒有考慮到城堡的內部構造。事後才為了「裡面要怎麼辦?」而煩惱不已(笑)。
結果,儘管那座城堡外觀看上去雄偉高大,但裡面卻只有兩層樓。
(與山田洋次對談「熱愛電影的兩人對電影製作的建言」二○○四年)
發想是從極細微處開始
製作電影之際,宮崎駿的發想最先都是從極細微的地方展開。穿怎樣的服裝?有著什麼樣的髮型?吃什麼東西?住在什麼樣的房子裡?腦海中的影像就從這些小地方開始逐漸膨脹擴大。
以前我曾寫過一篇名為「漫畫電影與動畫電影」的文章(二○○四年),那個時候記在我心裡的自然是宮兄這樣製作電影的方法。
將一個人腦子裡所想的東西集眾人之力來完成。這似乎是日本長篇漫畫電影的最大特徵。而且是鉅細靡遺。或者應該說,電影製作即是從非常具體的細節開始。例如在作品的架構還不清楚、腳本尚未完成之時,就先講究男主角身上穿的西服款式、女主角的髮型、他們身處的環境。於是,這類細節和腳本便會相互影響。或許可以這麼說吧,作品的主題是在製作的過程中逐漸明朗化。因此在日本,即使另闢蹊徑,選定一位劇作家來寫故事,他大概也派不上用場。
有時他劈頭就問我:「鈴木兄,這次的女主角你打算怎麼做?」這種時候他想問的通常是女主角的髮型。也就是說,是要綁兩條辮子呢?還是剪個馬桶蓋頭?或是留長髮?故事大綱都不知道,要我想我也想不出來。可是在宮兄心裡,這些細節很重要,一直苦苦思索。有時過了很久之後我才漸漸發覺,原來女主角的髮型在故事裡具有很大的意義。
原創造型從記憶中誕生
宮兄的特色在於,描繪這些細節時不看任何資料。只依賴長期累積下來的知識、資訊所建構而成的記憶,逐步創作出屬於他原創的造型。
例如『魔法公主』裡的製鐵廠、『神隱少女』裡的湯屋、『霍爾的移動城堡』裡的城堡等等,一般認為設計新穎的建築物,都是這樣誕生的。
對他而言,重要的不是記錄,而是記憶。曾經發生過這麼一件事。將近二十年前吧(一九八八年),包括宮兄和我在內的一群人一起去愛爾蘭的阿蘭島。它位在愛爾蘭的西邊,以阿蘭毛衣的發祥地而聞名於世。島上人口八○○人,沒有任何交通工具。有一天晚上,大夥兒一起上酒吧喝酒,回程的路上走著走著,我們投宿的那間民宿出現在眼前。當時雖然已經是晚上十點左右,但六月的愛爾蘭天色卻還很亮。雖然一直覺得這棟民宿毫無特色,但那當下我突然驚豔於它的美。於是我很難得地拿出相機拍照,結果這麼一來惹得宮兄不高興了。「鈴木兄,相機的聲音很吵耶。」他目不轉睛地盯著民宿看。真的就只是盯著看而已。我也在一旁默不作聲地看著。這時剛好有隻達烏里寒鴉振翅飛起,於是氣氛又熱絡了起來。那真是無可言喻的美妙時光。那段時間裡,宮兄始終默默地凝視著。
回到日本不久之後,開始著手製作『魔女宅急便』。電影中有一幕是要將和奇奇一模一樣的布偶送去某戶人家,他要畫出那戶人家的樣子。畫了一個大概之後,他罕見地帶著草圖來找我。
「鈴木兄,你還記得嗎?」
「啊,這不是阿蘭島的那間民宿嗎?」
「就是啊。不過有些地方我想不起來了。」
然後,他繼續說:「鈴木兄,你有拍照吧?」接著就一邊比對照片,一邊說著「啊,是這樣啊」。
他真的很認真在「看」。不是隨隨便便看一看,而是啟動所有感官功能,動用至今所累積的知識、情報,然後去抓住事物的形貌。在國外尤其如此,比方說,每個世紀的屋頂形式都不一樣。懂不懂得其間的差異應該會影響到觀看建築物時的樂趣吧。宮兄在這方面十分有研究,於是他以此為基準去記住那棟建築物的屋頂樣式、屋內隔間的情形,或是窗戶的樣式等許許多多的元素。這樣一來,大約記得十樣、十五樣左右,可是過了半年之後,頂多只想得起來其中的七、八樣。有些部分記憶鮮明,有些則是模糊不清。記憶模糊的部分就靠想像來描繪。反過來說,自己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會變得格外突出。所以,最後才會畫出獨創的建築物。
如果是照片,就只是單純原封不動地複製影像。唯有仰賴記憶才能成就獨創性。這部分我也多少受到他的影響,這一陣子開始盡可能不帶相機出門。我心想,一旦透過相機的取景視窗觀看便無法留下記憶,所以最好還是要珍惜用自己的眼睛觀看後所留下的記憶。
他偶爾會覺得有趣,和我們玩起這樣的猜謎遊戲。走在路上有時不是會看到有趣的人家嗎?這時他就會問:「你想那間屋子裡的隔間如何?」不過,製作『霍爾的移動城堡』時,在畫完那座城堡之後,他可是為了內部隔間而苦惱不已呢。
事實上,他也是用同樣的方式來看電影。以前我曾經談過這件事,所以在此加以引用(前述之「宮崎駿的情報源」)。
偶爾他會一大早就提出「今天我要去看電影」。然後,晚上一回來就向我報告。
「雖然看了五部,但有趣的卻好像只有一部。」
關於他看電影的方式,總之就是不怎麼注意放映時刻,比如說到了新宿就隨便走進一家電影院,也不在意電影是不是已經開演一半了。如果覺得無趣,就立刻走人,再去看下一部電影;有趣的話就繼續看。可是不看電影的開頭怎麼知道有不有趣?就連他對有不有趣的標準也與眾不同。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
「成吉思汗的電影很有意思。我一直很好奇那個時代的鎧甲長什麼樣子,今天我知道了。」
「那電影內容呢?」
「我不是很清楚在演什麼。」
也就是說,他是對鎧甲長什麼樣子,或是騎馬怎麼騎有興趣才去看這部電影。所以他才會完全不排斥中途進場。
說一個我覺得可能和這個有關的故事。關於宮兄的『卡里奧斯特羅之城』,有許多評論認為它受到戰後不久的傑出法國動畫長片『斜眼暴君』的影響,對此高畑兄是這麼說的(『漫畫電影志』二○○七年)。我想這大概是最適切的說法了。
在極短暫的時間內將並非看過很多次的作品的表現方式運用到自己本身的世界裡,宮崎氏這種驚人的領悟力和影像記憶力,令我十分佩服。
從不經意的對話中得到靈感
他常常無意中脫口說出「半徑3公尺內遍地是企畫」。我想所有人都很好奇他那豐富的靈感到底從何而來?其實,他的資訊來源只有兩個。朋友說的話,以及與工作人員日常不經意的對話。
宮兄曾經這麼說過,「在GHIBLI發生的事,東京也會發生。在東京發生的事,日本各地都會發生。在日本各地發生的事,八成在世界上也會發生」。就是基於這樣的理論才會說半徑3公尺內遍地是題材。
比方說,『神隱少女』。獲頒奧斯卡獎的話題告一段落,周遭的氣氛總算平靜下來時,宮兄有別於平日地懇切對我這麼說,「一切都是緣於鈴木兄在酒店說的那番話」。我剎時不知所措。「我說了什麼?」我已忘得一乾二淨了。原來是我的年輕朋友中有個很愛上酒店的小子,根據他的說法,「在酒店工作的女孩,若要歸類的話,肯定是內向害羞的女孩居多;她們在為了錢而接待男人的過程中,慢慢學會了原本不拿手的人際溝通。上酒店花錢的男人也有同樣的情形,也就是說,酒店是學習溝通的場所」。我覺得這段話很有意思,於是說給宮兄聽。據說,那段話便成為他創作『神隱少女』的動機。
的確,主角千尋被扔進了一個荒謬的世界,被迫不得不和身邊的人來往。所以在過程中她的溝通能力愈來愈好。而另一個重要角色無臉男,則因不懂得該如何表達自己內心的情感而發飆,與千尋成為對照組。宮兄覺得我在酒店的那番話很有趣,始終記在心裡,因而引發一連串的聯想。
藉著與工作人員的交流
平時,他也時常在工作室裡四處走動。除了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之外,其餘的時間都是如此。因為是工作室,所以有許多幕後工作人員。雖然光是動畫師或畫背景的人等繪圖者就有一百多人,但他會走到每個人的作畫桌旁觀看。桌上都會擺放各式各樣的物品吧,並非只有工作上的用具。
比方說,放了漫畫書之類的好了。這時他會立刻拿起那本漫畫,問都不問一聲就啪啦啪啦地開始翻閱。「問都不問一聲」這點很不可思議吧。然後,他會問對方:「這本漫畫你看了多少?」現在的年輕人即使買了一本漫畫也不一定會全部看完,通常都只看自己喜歡的部分。他隱約知道這一點。「我看了這些。」「喔∼這樣啊。」然後就一直站在原地把漫畫看完,同時還會問一些「那,你覺得這漫畫哪裡有趣?」之類的問題。之後,就再往下一個走去。
接著,這個情況則大多發生在繪圖者身上,那就是一邊聽音樂一邊工作。因為很專心,所以有時候沒注意到有人來了。這時宮兄就會突然一聲不響地把臉湊過去。嚇死人了。何況宮兄的臉那麼大,突然把臉湊過去時還會感覺到風壓。但既然是宮兄,自然趕緊卸下耳機。這麼一來,他又「問都不問一聲」就戴上耳機聽音樂。然後又問:「這音樂好在哪裡?」
這舉動可能多少會造成別人的困擾,但我認為其中蘊含許多意義。但究其根本還是在於他想要了解他或她是怎樣一個人的渴望。最單純的動機或許是這樣沒錯,可是在日復一日的過程中,難保不會自然而然地將它視為一種情報:「啊,現在大家喜歡這種玩意兒呀!」然後慢慢地變成自己創作的養分。所謂「半徑3公尺內遍地是企畫」,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事實上,作品裡出現的人物多半都有其範本。當他覺得工作室的新進人員或是偶爾來訪的人有點奇特或是好像很有趣時,就會突然對那個人很好奇。他真是好奇心旺盛又喜歡研究人。有時很想知道那個人是怎樣的一個人,便沒事也會跑去人家身邊晃。總之,他的「求知」欲望非常強烈。
最近也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我們現在正在製作『崖上的波妞』(二○○八年夏天上映。以下簡稱『波妞』)這部電影,主角是個五歲男孩。宮兄的年紀也大了,自己身邊沒有這樣的小男生。有一天,幫我管理日程計畫的助理白木伸子小姐帶著孩子來公司。是個六歲的小男生。宮兄瞬間臉色一亮。「來這邊跟我玩一下嘛!」他玩得很高興,同時在玩的過程中觀察著。嘴裡說著「現在六歲的小孩原來是這種感覺啊」。
後來他還問白木小姐:「下次什麼時候再來?」最後,竟演變成白木小姐不得不每個禮拜六都帶孩子過來,真是折騰人。有一天,那個小男生帶來自己做的禮物送宮兄,說:「爺爺,謝謝你陪我玩。」宮兄可高興了,畢竟受到孩子喜愛是一件令人開心的事。這個小故事也確確實實地搬進了電影裡頭。
結局尚未決定就開始作畫
宮兄製作電影的有趣之處,就在於分鏡圖畫到一半即開始作畫。也就是說,結局尚未定案。
製作電影時是分段之後再繪圖。大約以二十分鐘為一個段落。每二十分鐘分成A段、B段、C段的段落。這大約二十分鐘的單位其實和電視卡通劇集一樣。電視上一個三十分鐘的節目,其內容大概是二十分鐘。宮兄和高畑兄都是過來人,所以做二十分鐘左右即可自成一個段落。做到這個程度時就會進入作畫的階段。
最早的『天空之城』和『魔女宅急便』都有腳本。第一部沒有腳本就開始製作的影片是『紅豬』。剛開始是因為擔心進度趕不上才先繪圖。況且大致是個什麼樣的故事已心裡有數了。所以才會說什麼「做到一半再開始畫分鏡圖也沒關係」。哪知製作到一半主客易位,或者應該說是目的改變了。宮兄竟然說出「鈴木兄,製作已經知道結局的影片一點都不好玩」這樣的話來。結果,這變成了一種製作手法。
一開始即擺明要用這種手法製作的影片是『魔法公主』。電影製作如同船隻航行在大海上,不會只有晴天,也會遇上雨天和暴風雨的日子。船上坐的是工作人員,航行到了尾聲,都還不清楚這故事的結局會是什麼樣子,那種緊張刺激又懸疑的感受,導演之外的全體工作人員都體驗得到,這會讓電影變得更有趣,並為作品帶來某種好運。宮兄是這樣考量的。
結局不明朗的確會讓人感覺很刺激。用航海來比喻雖然高明,不過以此來比喻的話,也就會有遇難的危險性,也就是演變成電影製作不下去的窘況。
製作『霍爾的移動城堡』時也是,有趣是有趣,卻讓人很頭痛。電影全長一小時五十九分鐘。但只畫了一小時半左右的分鏡圖,還看不到結局。他一臉嚴肅地來找我。關上門,問我:「怎麼辦?要怎麼讓它結束才好?」這種時候的宮崎駿真的好可愛。結果,聊著聊著他突然靈光乍現,想出了結尾裡約十分鐘的情節。
對出場人物用情至深
我說過從『魔法公主』那時開始就刻意在結局尚未定案前展開製作,不過這對宮兄來說畢竟是一大壓力。想當然耳,影片製作到一半就會感到不安。於是,我告訴他:「想像成在畫連載漫畫不就好了?」因為連載漫畫就是在看不見結局的狀態下持續創作。這下子宮兄便安心了。「沒錯,連載漫畫啊」。
不過,故事結束的方式依舊難產。事實上,影片一度幾乎要完工了,但我就是覺得差了點什麼而沒辦法同意殺青。於是,我便對宮兄說了。主角之一的黑帽大人之死和火燒製鐵廠,沒有這兩者故事便不算完結。尤其是像黑帽大人這樣的人,在歷史上大多死於非命,但因為她的想法部分是正確的,所以就讓繼承那些想法的阿席達卡與魔法公主小桑一起活下去。我認為這麼做才是一個正統的敘事方式。話一說完,宮兄立刻反應道:「果然鈴木兄也這麼覺得?」
其實時間已經很緊迫了,如果加入這段插曲再製作的話,不僅會超過原定的時間,趕不上公開上映日期的風險也增大許多。身為製作人,這是一場豪賭,但畢竟製作出一部好的作品才是最重要的事,所以我個人也做好心理準備,知道接下來的作業將會十分辛苦。
接下來的三天,宮兄很苦惱。真的歷經一番痛苦掙扎之後得出的結論是,黑帽大人被扯斷一隻手臂這樣的結局。宮兄還是沒辦法殺死黑帽大人。他整個人投入故事裡,化身為那個角色了。所以就故事性來說本應非死不可的人,他無論如何就是不忍心把他殺了。宮兄對我說:「這樣就好,饒了我吧!」那句話我沒齒難忘。
關於宮兄對角色所投注的感情,高畑兄的評論講得很好。我在此引用一小段(「愛的火花」一九九六年)。
他的人物所擁有的驚人現實感,並非來自於對對象的冷靜觀察。就算他的敏銳觀察結果已投射進那個角色裡,但他附身在那個人物上進而融為一體之際所激起的愛的火花,也會讓理想變得有血有肉。
所以他會對為戲劇角色而設定的人物投入感情,賦予那個人物個人的魅力、煩惱或主張,不知不覺間,連壞人都變得不像壞人了。
創造一個複雜有深度,或是饒富興味又有人情味的人物,也許是優秀作家普遍有的傾向,但以宮兄的情況來說,我想他應該也是因為無法忍受對自己所創造、不得不在漫長的製作期間與他相處的人物放手不管,完全不投入情感地畫吧。
「這樣五月就不會變壞了吧?」
最讓人能感受到宮兄性格的小故事,可能還是『龍貓』時期的事吧。
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這部電影,故事設定主角是五月和小梅這對姊妹,她們的媽媽因病住院。五月是個六年級生,姊代母職十分能幹。看著分鏡圖逐漸完成,我卻覺得它的內容有違常態。
小孩子做事就是會力不從心,老是失敗。這才像是孩子不是嗎?像五月這樣可以做得盡善盡美的孩子讓我覺得非常不自然。我把這種感覺告訴宮兄。「現實中怎麼可能會有這樣的小孩?」那個時候我也年紀輕,所以更進一步說道:「這種事小的時候就全都會做的話,長大之後五月會變壞唷!」
那時候,宮兄真的很生氣。「不,有這樣的孩子。真的有。」我還以為他要說什麼,沒想到竟然是「我就是這樣」。宮兄家都是男孩子,母親長年生病,他一個人要煮所有人的飯,或是代替母親做家事。因為有這樣的經歷,他才會塑造出比母親還要優秀這樣理想化的五月。
那時宮兄雖然生氣,但一直把我的話記在心上。原本他就是會誠心接受他人指教的人。有一次他叫我:「你來一下。」還以為是什麼事,原來就是有一場五月因為擔心媽媽會死而在哭的戲,那場戲的分鏡圖畫好了,所以要我看一下。
「哦,她在這種時候會哭呀。」我一這麼說,宮兄立刻回我:「我讓她哭的。」接著又說:「鈴木兄,這樣五月就不會變壞了吧?」「不會。」才說完,宮兄便開心笑道:「太好了。」這麼大的人了卻像個孩子似的。我再次體認到他真是個純真的人。
圍繞著『龍貓』的記憶
『龍貓』是一部有許多回憶的電影。多到實在讓人傷腦筋哪。
剛剛說了五月的故事,但如果要講到和腳本(分鏡圖)有關的故事,我想到最早的企畫是安排龍貓從電影一開頭就出場並且縱橫全片。也就是說,戲分過多。這種時候我還挺老實的,看了分鏡圖之後心裡有所質疑,臉色便跟著暗了下來。宮兄問:「鈴木兄,怎麼了?」我回道:「沒什麼,只是這種角色通常不會一開始就出場不是嗎?」我實在說不出「這東西出場這麼多要幹嘛!」的話來。
宮兄說:「這樣啊,那要怎麼做?」我說:「沒有啦,通常都是在中間才出場啦。」我這麼說並非有什麼根據,只是不小心就說出口了。宮兄沉思了一下,隨即逼問似地問我:「為什麼?」不得已之下只好回他:「史匹柏的『E.T.』也是在中間出場的呀。」宮兄這才說:「原來如此,這樣啊。」
宮兄接下來可了不起了。他啪地攤開一大張紙,從中間畫一條線,然後寫上「龍貓登場」。四周一大堆工作人員,所有人都在聽我們對話。但他一點兒都不覺得丟臉,喃喃自語著:「是這樣嗎,中間啊。」這點看似容易實則不容易做到。我覺得那很了不起。
然後他更進一步問我:「那在這之前呢?」「手或是什麼的出現一下下。」重申一次,我其實沒有什麼高深的見解,只是單純地舉『E.T.』為例。結果,既然已決定影片中段再出場,就必須思考在那之前要有些什麼畫面。因此慢慢加入搬家,或到新家之後的第一天等諸多場景。
之後,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因為種種緣故,『龍貓』決定搭配高畑兄的『螢火蟲之墓』兩片聯映。對GHIBLI來說,是冒險的好機會,不過這倒在其次,主要是宮兄開始在意高畑兄製作文藝作品這件事。他一臉認真地這麼說。
「鈴木兄,『螢火蟲之墓』是文藝片吧。」
「算是吧。」
「我也要拍文藝片。」(!)
「耶?你要怎麼做?」
「不能出現龍貓公車這種玩意兒。那種東西一出場就不是文藝片了。」
我大吃一驚。不僅是龍貓公車,據說連乘著陀螺在天空飛翔的場景也不要了。「乘著陀螺飛上天這種愚蠢的畫面,我沒辦法做啦。」這下真難辦了。我最喜歡「龍貓公車」了,何況他打算怎麼樣讓「龍貓公車」不會出現呢?我開始忐忑不安。於是,我試著去找執導『螢火蟲之墓』的高畑兄商量。
「高畑兄,真傷腦筋耶。」
「怎麼了?」
「高畑兄也知道『龍貓』的企畫吧。」
「喔,那部片子啊。」
「現在說不要龍貓公車和陀螺了。」
「那豈不可惜嗎?」
「就是說呀。啊,可惜,對對對,這句話好耶。」
因此我跑去找宮兄,「宮兄,關於龍貓公車和陀螺呀,」「怎樣?」「高畑兄直說太可惜了耶。」宮兄對高畑兄的話最沒輒了。「那就讓它們出現吧」,於是事情就解決了。
『龍貓』裡所描繪的大自然
負責『龍貓』美術設計的是當時年僅三十來歲的男鹿和雄先生。相信沒有人會懷疑,『龍貓』的一大魅力即是電影中所描繪的里山自然環境。他畫的就是那麼出色。在大自然的背景下,觀賞者不知不覺便感受到季節轉變和時間流逝。他是個擁有驚人力量的藝匠。前一陣子(二○○七年七∼九月)他在東京都現代美術館舉辦個展,展品以GHIBLI的作品為主,現場擁進爆滿的參觀人潮,據說是美術館開館以來入場人數之最。當然不只是因為『龍貓』的關係,但我想「龍貓之森」的粉絲占大多數吧。
宮兄對男鹿先生只有一個要求,就是泥土的顏色。由於屬於關東土壤層,泥土是紅色的,而男鹿先生卻畫成黑色。他那麼畫是有原因的,因為男鹿先生是秋田縣人,說到土壤,直覺就是黑色。我清楚記得宮兄說「我希望改成紅色」時,男鹿先生一語不發地改成紅色的那個景象。
就這樣,以里山作為故事舞台的『龍貓』殺青了,不過試映時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即尾形英夫先生的反應。試映結束後,宮兄的心情很亢奮。「尾形先生覺得如何?」「最後那一幅大家一起泡澡的畫很棒。」宮兄對這冷冷的回應很火大,不過在一旁旁觀的高畑兄冷靜分析道:「尾形先生是在大自然中成長的人,恐怕這部電影無法勾起他對童年的回憶。」
換句話說,這部電影對親身體驗過鄉間自然環境的尾形先生來說,少了那麼一點說服力。姑且不論里山風景如何,但講到真實感,不說別的,光是因為有蟲就不可能像影片中那樣穿著短袖跑進草叢或樹林裡去了。不管再怎麼熱都要穿著長袖長褲。由於畫的時候將一切理想化,心裡渴望著那樣理想中的自然風景,尾形先生當然不會因這部電影而回想起他的年少時光。「我看不懂這部電影在拍什麼」。尾形先生還真是實話實說的人哪。順帶一提,宮兄其實對鄉下懷有憧憬,對自己在東京長大感到自卑。因為這個緣故,他還嘲笑在名古屋長大的我說:「鈴木兄也沒用,因為也是個都市俗。」
不過,高畑兄當時雖然說了那樣一番話,但在日後卻如此描述『龍貓』這部電影的意義(前述之「愛的火花」)。我也同意他的看法。
我認為宮崎駿帶給人們的最大恩惠就是龍貓。龍貓並非普通的偶像人物。他讓龍貓遍布日本全國近郊的山林裡,而不只是在所澤而已。龍貓在全國孩童的心裡面生了根,只要看到樹,便感覺有龍貓躲在裡頭。這麼美妙的事世間少有。
高畑兄還有過這樣的說法:「『龍貓』是我們努力要達到的頂點。」聽到他這麼說,宮兄非常開心。
4「半徑3公尺內遍地是企畫」──宮崎駿的電影術──他不信任邊看資料邊畫圖的人。或者應該說,只要有志從事繪畫這一行,就會對各種事物抱持好奇心,日常便時時在觀察著。那樣的日積月累才是最珍貴的事。 (「宮崎駿的情報源」二○○二年)在創作『霍爾的移動城堡』裡的那座城堡時,是先創作城堡頂部之後,再一樣一樣地慢慢增建,之後才組合成一座城堡。而且,竟然完全沒有考慮到城堡的內部構造。事後才為了「裡面要怎麼辦?」而煩惱不已(笑)。結果,儘管那座城堡外觀看上去雄偉高大,但裡面卻只...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6收藏
16收藏

 12二手徵求有驚喜
12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