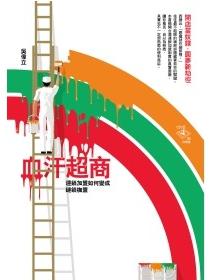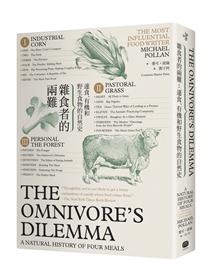愛人和被愛都是一種令人感動的能量,
信德、望德的基礎全來自於愛德……
有這麼一群人,在二十世紀五○年代,跨過半個地球,千里迢迢地從富裕的瑞士抵達貧脊偏僻的臺灣東部海岸山脈。正值青壯的他們,為信仰獻身,在風光明媚的海岸線上建立美麗的教堂、醫院、學校、智障中心。他們並非不想念瑞士的家鄉,但若你有機會遇見他們,他們會異口同聲地告訴你:「臺灣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而臺東縱谷更是臺灣最漂亮的所在。」
在全盛時期,東海岸有近五十位白冷會士在此服務,他們為沒有血緣關係的臺東人們付出全部,經過近六十年,而今只剩寥寥可數的幾位老人家仍在這兒繼續做他們該做、能做的事。社會大眾對恪守獨身誓願的修道人,總有一種伴隨神祕而來的好奇。然而,對這些終身奉行神貧、貞節、服從的神職人員而言,人們欠缺什麼,他們就努力奉獻什麼,包括生命,包括愛。
這是一本關於神職人員的書,然而,被它感動的人,大多不是天主教教徒。擅長捕捉宗教文化壯觀之美的范毅舜,在「歐洲三書」時,總帶著一種旁觀者的冷眼;然而到了《海脈山岸的瑞士人》,范毅舜首度觸及私密和經歷,他將圖片和文字沉澱為一種樸實無華的媒材,與讀者分享他與這些神職人員互動,進而成長的歷程。
透過鏡頭,這些修道人被歲月刻劃出的人生軌跡面貌,不需要透過言語,就足以讓人感動。所有故事的感染力,都必須回歸到人物本身的人格與情操,誠如作者所說:「好的故事是相處來的。」
作者簡介:
范毅舜(NicholasFan)
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美國加州布魯克攝影學院碩士,作品常見於國際知名攝影雜誌,他曾先後在台北美國文化中心、誠品藝文空間、美國華府參議院、德國Leica藝廊與法國尼斯AlainCouturier藝廊舉行攝影個展,而德國Leica、美國Sinar、德國Hasselblad等知名相機公司及Illford、柯達軟片公司都曾以其作品為年度月曆或產品代言。除了專業攝影作品外,范毅舜的出版資歷也相當豐富,過去數年,他曾以歐洲為主題,出版近四十本的著作,已出版的作品有:《走進一座大教堂》、《法國文化遺產行旅》、《德國文化遺產行旅》、《攝影行遊間──旅遊攝影的技法與欣賞》、《歐陸教堂巡禮》、《老家人》、《漫步普羅旺斯陽光中》、《悠遊山城》等書。
章節試閱
一封白冷會士的家書
親愛的母親,
自拿波里上船後,穿過蘇彝士運河,陸續經過北非、印度孟買、雅加達、新加坡、香港,經過一個多月的日夜兼程,我與其他會士弟兄終於抵達了台灣的東部。眼前這片美景只能用「歎為觀止」來形容啊!青翠的海岸山脈與瑞士的高山差不多,但美麗的太平洋卻是家鄉所沒有的。
天氣很悶熱,熱得讓人受不了,很多時候我都覺得自己快被烤焦了,而且這裡沒有會院,我們住的地方相當簡陋,更別提伙食了,為了控制預算,我們的長上讓我們真的是吃不飽也喝不好,完全無法與在瑞士時相比擬;不過,這裡的人很窮,很多人都沒有鞋穿,相較之下,我們小小的犧牲刻苦,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雖然如此,我難免想著:如果偶爾能享用一塊家鄉的巧克力,搭配一杯香醇的咖啡,該是多麼美妙的事!
這個調皮的念頭,還不足以成為「距離」的對比啊。親愛的媽媽,或許未來我們不是那麼容易見面了(對不起,想到這裡,我的眼睛又濕了起來),但我相信您為我所流的思念淚水,將是天主胸前最美麗的一串珍珠。
親愛的媽媽,感謝您的捨得,好讓您最親愛的孩子能到異國遠方為天主的子民服務,好天主定會賞報您的犧牲與奉獻。
我就要開始學習這裡的語言與文化,請為我祈禱,我可是一點把握也沒有。
想念爸爸與弟妹們,我將在每晚的夜禱中與你們重逢。
您遠方的孩子敬上1954.6.9
二○○七年春天,神父好友雷保德罹癌逝世,我在他病危前特地飛往德國探視,得知他過世的消息,為遣懷而寫了篇紀念文章傳送給幾位好友。朋友們對文章的反應超乎想像,他們不約而同地要求我發表,好與更多人分享。朋友們的讚辭,我淡淡地以「日行一善」看待。
積木文化總編輯蔣豐雯小姐為我每回返台無論如何總得擠出時間去拜訪神父而感到好奇,因此聊及傳教士攝影專題,蔣小姐為其中幾位修道人的胸懷感動,鼓勵我出版此書。
我將紀念德國神父的文章傳給蔣小姐,對她說:「這本書全然以個人觀點出發,我實在沒什麼把握。若妳為這篇與自身毫無關聯的文章感動,也許我們可以談談。」不可否認,我當時的態度其實有點推托。
蔣小姐對這篇文篇的回應出乎我意料的熱烈,她所感動的是字裡行間不經意流露的感情與誠摯友誼。我真沒想到在這個八卦成主流、價值觀混淆的社會裡,被我視為平凡而且理所當然的真情友誼,竟是許許多多人的嚮往。
二○○八年初,在美國接獲蔣小姐從台北打來的電話,討論這本以為約好卻被我置之腦後的書。在她的鼓勵下,我認真地著手進行這些故事,原先以描述台灣外籍修道人的生平事蹟為架構,寫著寫著,延伸成了我與他們互動,進而成長的經歷素描。
社會大眾對這些恪守獨身誓願的修道人,總有一種伴隨神祕而來的好奇。我實在不願再將他們描繪成偉大、超越人性的類型化人物,甚至為他們因不願辜負人們期待而故作堅強的談吐舉止感到難過。為此,讀者若想從我筆下的修道人身上獲得一個速成的、可奉為圭臬的人生指標或信仰準則,恐怕要失望了。當然我也懷疑:若他們告訴你「信耶穌得永生」,你會相信嗎?此外,在行樂主義的時代裡,又有多少人在乎「永生」的意義呢?
也許你會好奇,如此個人的經驗如何能引起共鳴?這也是我擔心的。
每個人成長歷程都有許多令人興奮或不足為外人道的故事,我是位藝術工作者,衷心希望這些個人經驗能如藝術般帶給人們不同的靈感與動力。我對書中收錄的攝影作品相當有信心,不論是不是我拍的,鏡頭中人物被歲月刻劃出的人生軌跡,不需要透過言語,就足以讓人感動。
沒有使命感負擔,驅使我下筆的最大動力,是因為我深愛這些修道人並蒙他們所愛,我更打心底敬愛他們從不求己益的獻身精神。其中有些人已不在人世,我不想讓自己陷在難過的情緒裡太久,然而就像思念我過世的母親般,我日夜都忘不了他們。
在《舊約聖經》裡,大衛王心愛的兒子病逝後,他反常地梳洗並大吃大喝。先前極力勸他保重身體的大臣不解,為什麼兒子生病時,他日夜誠心祈禱,食不下嚥,而今小孩剛斷氣,他就像換了個人似的!
「孩子病時,我禁食禱告,以為上帝會醫治他,但現在他死了,我豈能使他回返?我必往他那裡去,他卻不能再回到我這兒來。」大衛如此回答。
天邊來的異鄉人
不知是忘了或者根本沒有知覺到?就是不會有人告訴你,他們是來自歐洲的瑞士人,因為當地人早已視他們為自己的一份子,甚至有過世的會士被當地人奉進了自家的祖墳地,要晚生好好守著有如父執輩的神父墳塋,永誌不忘。
有這麼一群人,在二十世紀五○年代,跨過半個地球,千里迢迢地從富裕的瑞士抵達貧瘠偏僻的台灣東部海岸山脈。他們當中有的正值壯年,有的只不過是二十歲出頭的小夥子。這群鼻子尖挺、金髮碧眼的「阿凸仔」為信仰獻身,在風光明媚的海岸線上建立了美麗的教堂、醫院、學校、智障中心。他們並非不想念瑞士的家鄉,可是只要你有機會遇見他們,他們會異口同聲地告訴你:「台灣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而台東縱谷更是台灣最漂亮的所在。」
這群終身奉行神貧、貞節、服從的神職人員,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若不是凋零,就是生理年齡的龍鍾老人了。幾位少數依然健在的人,縱使傳教事業今非昔比,卻沒有絲毫老態,精神奕奕地繼續做他們該做、能做的事。
至於那些逝去的人,他們大多長眠於這片生前摯愛的土地上,化成海岸山脈的一部分,在風裡,在驚濤駭浪裡,更在當地人的腦海裡。認識他們的當地人,總愛對後人訴說種種軼事── 他們的脾氣,他們的好,他們的歡笑與淚水。
不知是忘了或者根本沒有知覺到?就是不會有人告訴你,他們是來自歐洲的瑞士人,因為當地人早已視他們為自己的一份子,甚至有過世的會士被當地人奉進了自家的祖墳地,要晚生好好守著有如父執輩的神父墳塋,永誌不忘。
來自瑞士的白冷外方傳教會
我認識位於台東的白冷外方傳教修會是九○年代初,它的全盛時期有將近五十位會士在此服務,而如今會士大半凋零了。
創建於一九二一年的白冷外方傳教會,在古老的羅馬天主教會體系裡,算是個相當年輕的修會。一九二五年,這個只收瑞士籍的白冷會到中國東北齊齊哈爾開教,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後,當年遭驅逐的神職人員陸續遷移到台東。白冷會為什麼會選擇在無論是交通或民生條件都相當落後的東部呢?除了花蓮主教當年的邀請,更因貧困地區更需要支援。於是幾個會士弟兄搭著瑞士的貨輪,就這麼千里迢迢地來到台東縣。
若以今日的眼光看來,上帝真的有祂自己的主意。當年還有哪個傳教修會比白冷外方傳教修會更適合來此工作?以基督誕生地「白冷城」(或譯伯利恆)為名的宗教團體,在他們的會憲裡所強調的精神,就像兩千年前誕生在白冷城外馬槽裡一無所有的小嬰兒,對於世俗人嚮往的物質,他們追求謙遜、簡單,就像成年的基督一樣,所有的會士更避免靠別人的權柄甚至自己的能力去追求權勢。
白冷外方傳教修會如此描述他們的工作精神:孩童的精神:白冷會士以類似孩童完全信任的態度,幫助他們忍受巨大的困難和克服失敗。單純的精神:專心追求福音,卻除自我煩惱的恐懼,更為他們帶來服事別人的自由。貶抑的精神:讓白冷會士在投入別的文化、宗教及社會階級時,可以放棄自己的習慣。(這方面白冷外方傳教修會倒是奉行得相當徹底,從修院裡那些褪色的照片中,幾位穿著原住民傳統禮服做彌撒的白冷會士,簡直就是不折不扣的原住民長老模樣。)
永遠年輕的歐思定修士
歐思定修士(Bro. Buchel Augustin, 1936~) 歐修士在台東生活了四十多年,他熟悉東海岸每個角落。因為曬得黝黑,而且國、台語都非常流利,經常讓人無法確定他究竟是不是「老外」?例如,歐修士在田野間與一位歐吉桑以台語交談,臨別前,歐吉桑不好意思地對他說:「你長得很像外國人呢!」歐修士淘氣地回答:「很多人這麼說呢!」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從不向人傳道的歐修士是如此地熱愛自然與生活,除了照顧自己的花園,也會為朋友的庭園盡心盡力。朋友們需要種花種草,都會前來向他請益。他的朋友有一處位於群山之間的庭園,綿延半座山的樹木都栽自歐修士之手,景象宛如電影《魔戒》的翻版,我稱這為修士的「祕密花園」。我們的歐修士相信天堂裡的花園更漂亮,他將樂意在那裡當個小小的園丁。(攝於1993 年)
和白冷會結緣,得歸功於在此擔任總務的歐思定修士。 我們的修士今年七十三歲,算是可以享受眾多福利的老年人階層了,但是所有認識歐修士的人(包括我在內),每回和他相處時完全遺忘了他的實際年紀,甚至有爬山活動時,大夥都要事先鍛鍊自己一番,免得到時成為這個「年輕人」的負擔。
六○年代初來到台東的歐修士,在修會裡掌管會計大職。酷愛大自然的他幾乎爬遍了台灣百岳,基於對大自然的熱愛,修士強調環保,更創立了在台東相當著名的「向陽登山社」,這個有近四十年歷史的社團迄今仍經常舉辦活動,有意思的是,這個由修士帶頭建立的團體,成員中只有一位是天主教徒。我們的修士從來不會藉此機會向人傳教,但所有的人只要在路上看見他,都會親切地喊他「歐修士」,好像這就是他的名字一樣。
說來慚愧,身為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我對台東海岸山脈的認識,完全來自這位瑞士人。嚴冬裡,歐修士會帶我找尋隱藏在山谷裡的野溪溫泉;春天時,他知道何處可以賞梅;秋夜裡,他知道何處可以觀星;就連觀看台東飛機起降的地點,他都知道。此外,歐修士對花草植物更有特殊的愛好。台東市白冷會的會院裡,四季都有盛開的花朵,其中的蘭花更堪稱奇景。這些繁花盛草,讓白冷會成為一座小小的伊甸園。
我慫恿歐修士以「我的台東後花園」為題,創作一本書,保證它成為暢銷名著。修士總是搖搖頭,名利對他而言,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東西,每個白冷會士都是如此。
順著歐修士的分享,我逐漸勾勒出白冷會士早期在台東傳教的輪廓,那些過往雲煙經歐修士平淡的言詞,化為令人回味再三的傳奇經典,更重要的是:它讓人有機會領略到這些修道人看似卑微卻不平凡的一生。如今,白冷會仍有幾位依舊健在且被視為「人間瑰寶」的長者在此服務,就讓我從那些無緣親睹的老人家說起吧。
開路先鋒錫質平神父
錫質平神父(Fr. Hilber Jakob )是白冷會在東部海岸山脈的開教者,一九五三年,錫神父的長上應花蓮主教的支援請求,權且派遣這位能力超強的老兄自瑞士到台東來「瞧瞧」,評估此地情況後,再看是否要安排會士來台?沒想到正值壯年的錫神父一到台東,還未經瑞士長上許可,就單槍匹馬地在這裡大興土木,進行前所未有傳教的計畫。
白冷外方傳教會與台東近半世紀的深情交會,就從錫神父的到來開始。
天邊來的異鄉人
錫神父當年騎著重型機車,跑遍台東每一個角落。據一位女士回憶:幼年住在台東康樂農校宿舍時,每天下午總會看見這位大漢騎著機車經過門前,鮮少接觸外國人的孩子們,每回看見錫神父,總會高聲大喊:「神父好!」而神父則興高采烈地回答:「小朋友好!」然後猛按兩聲喇叭,逗得孩子們大樂方才呼嘯而去。就這麼一聲溫柔的﹁小朋友好﹂,在幾十年後,成為女士移居國外時無法磨滅的鄉愁。
從歐修士的描述中,我猜想自己會害怕與這位以嚴格紀律著稱的神父成為朋友。修士對我說,早年東部的民生落後,為了節省開銷,以及更融入當地人的生活,身為會長的錫神父對會院的伙食相當苛刻,即使是不講究飲食的修道人都感到吃不消。
錫神父生前在台東完成了眾多不可能的任務,例如,在六、七○年代,他創辦了以培養優良技工聞名的「公東高工」,其師資堪稱全省職工訓練學校之最,這些教師大半來自瑞士及歐洲學有專精的年輕技工。當年台東學子不需出國留學,就能從這些具有宗教情懷的傑出技工身上,習得足以謀生的一技之長。有位在家具業表現非常傑出的企業家回憶:他們當年在公東高工就讀時,簡直怕極了錫神父,無論是做人處事或生活習慣,他都要管,而且嚴格得很。昔日學生而今已近花甲之年,卻都記得這位鐵漢的柔情,每晚錫神父巡房時,一定會注意這群寶貝學生是否把被子蓋好?若是被子踢到地上,神父二話不說,為他們蓋結實了,確定每一位孩子都就寢後,他才會上床休息。某些小鬼頭就喜歡這樣的溫柔,老是故意把被子踢下地,閉著眼享受神父的照顧。
在那個普遍窮困的年代裡,錫神父幫助過不少繳不起學費而失學的孩子。當今某位成為輔理主教徒眼裡,他們理所當然地懷抱著基督的感召,救人靈的熱火,好似他們從未遭受挫折一般。然 自西方的信仰,根本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們很難了解這群傳教士當年的終極心態,在一般的天主 今日海岸山脈沿路可見由白冷會興建的天主教堂,但早期要在這偏僻的東部傳播一個全新、來 的瑞士籍神父。 以大禮迎進自家的祖墳地。在劉氏私人墓園裡,居中為首最大的一座墳,就是他們稱為「錫公」 養育這孩子直到大學畢業。錫神父故去後,劉家人浩浩蕩蕩地將這位來自天涯另一方的瑞士人,而劉先生的兒子壯年辭世前,將只有幾歲大的唯一孩子如託孤般交給錫神父,錫神父不負託付,這其中有個感人的故事:錫神父當年初到台東傳教時,受到南興村排灣族頭目劉先生的支持,當年的葬禮盛大得驚人,錫神父被鄉民迎進了台東大武鄉、南興鄉排灣族頭目的祖墳地。長辭,病逝在他奉獻大半生的台東縣。 神父認真地感謝與徐先生幾十年的友誼,送他一只刻有感謝字樣的金戒指。兩天後,錫神父與世 首往事般,一一說著眼前的房子是什麼時候蓋的,不遠處的那座樓又是什麼時候興建的,最後錫 用餐,回到醫院時,錫神父問老朋友是否還有時間?他想坐著輪椅在醫院四周逛逛。錫神父像回 神父的電話,希望能到他家吃頓最愛的餃子。每天給神父送補給品的徐先生,於是將神父接回家 每天仍掛記著公東高工的學子,不時地叫學生到病床邊,一一問候鼓勵。某天,徐先生突然接獲 擔任錫神父的翻譯而與他成為忘年之交的徐先生告訴我,錫神父在聖母醫院的最後兩個星期,會聽到從神父房間傳來的哀號,既無助又痛徹心肺。 台東。有位公東高工畢業、回母校任教的老師日後回憶:神父的癌症蔓延到骨頭,每天夜裡,都 父一心掛記東部,要求院方讓他﹁死也要死在自己的故鄉台東﹂,於是不顧醫生警告,再度回到 一九八二年,錫神父在瑞士募款時被檢查出罹患腎臟癌,院方預估神父只剩六個月的生命。神 究竟幫過多少失學的孩子?沒有人做過確切的統計。
以小米酒傳教的姚秉彝神父
日後東海岸教堂一座座興起,某些神父的開教經歷,被他們自己當成趣事,流傳在會士之間,例如,姚秉彝神父當年傳教並不順利。
姚神父初到台東時,很多阿美族的部落根本不歡迎外國佬入村傳道,他日後對人說:「我的傳教大業是拜一瓶微不足道的米酒所賜。」
一九五七年,姚神父到花蓮大港口附近的村莊,所騎的摩托車莫名其妙著火了,兩位在村前閒聊的原住民青年基於人道幫忙滅火。眼見機車成為爛鐵,姚神父絕望無比,但他仍得謝謝這兩位年輕人,便就近在雜貨舖裡買東西,走進店裡,神父在汽水與米酒之間掙扎,最後索性買了可安慰自己的米酒與他們對飲。兩位年輕人因為神父的分享,感動而開心地回去告訴頭目:「這個老外會喝我們的米酒哩。」為此,他打開了傳播福音的大門,適時維護住了他飽受挫折的傳教熱火。
美聲系澎海曼神父
Fr. Brun Hermann 另一位神父的開教方式也相當傳奇。一九五六到台東傳教的澎海曼神父,講著一口東北普通話,同樣不為阿美族接受。直到一場意外而悲傷的葬禮,才打開了長濱附近南竹湖部落的心防。
原來澎神父的一位教友,入贅到此部落的一戶人家,某天年輕人出海捕魚時意外喪生,澎神父特別帶著聖歌隊到這戶人家為死者舉行追思彌撒。南竹湖的村民們為葬禮優美的禮儀與詩歌著迷,對這外來信仰產生好奇,進而主動地想了解。澎神父日後編著的《阿美聖歌集》,是他留給阿美族同胞最美麗的資產,而他所調教出來的合唱隊,更是此間最強勁的聖歌詩班。
當人們揭開神祕面紗來看待這些有異於常人的修道人時,我們較敢臆測,這些看似不畏死生的傳教士除了有異於常人的信仰外,其實是相當浪漫的。在電力不普及的年代裡,修道人披星戴月的代步工具就是雙腳,以及踩起來相當吃力的腳踏車。我們當然無從得知他們當年長時間在
Fr. De Boer Jorrit 姚秉彝神父(De Boer Jorrit, 1911-2002)(攝影/林志柔修士) 深山裡、海岸線上,頭頂烈日,遙望星空,踽踽獨行,一村又一村傳播福音,心裡究竟在想些什麼?他們不畏失敗,奮力傳福音的動機,究竟是到人性裡亟欲征服的虛榮優越感驅使?還是,他們真的超越自我,完全無私、真誠地想與異鄉人分享讓自己得救的訊息?
下面這位神父的故事,也許能提供我們一個較清晰且讓人信服的參考。
蘭嶼之父紀守常神父
紀守常神父(Fr. Giger Alfred )是白冷會早期的傳奇人物。這位長得英挺,薄唇和眼睛總散發出無限魅力的神父,活潑得不得了,他幾乎將壯年歲月全獻給了東部,尤其是位於蘭嶼島上的達悟族同胞。
歐修士說,半個世紀前(一九五四年)在馬蘭天主堂服務的紀神父未經由長
上的同意,一個人從高雄偷偷搭了漁船到蘭嶼。在漢人眼裡,島上居民飢荒時得以山藤裹腹的蘭嶼島,是片不折不扣的蠻荒之地。
從早期遺留下來的某些影像中,後人幾乎可以斷定,當年正值壯年的神父一定愛極了他的達悟同胞。有幾張照片是紀神父頭戴達悟族銀頭盔與族裡老人面對面、鼻子碰鼻子地摟著合影。
八○年代之後,為了慶祝發現新大陸五百年,全球陸續出現許多檢討:殖民及外來宗教究竟是破壞當地文化,還是真的幫助弱勢民族?台灣也不例外。難得的是,東部人(尤其是早期的達悟人)對紀神父的印象,竟不是他所傳述的基督救恩道理,而是這位有血有肉真情壯漢的種種軼事。
為了維護達悟族的權益,紀神父常與駐守蘭嶼的軍警大打出手,我很難想像在高壓的戒嚴時代,氣急敗壞的老外與軍警打起架來會是什麼模樣?
「能給的全給了!不該給的也常不見。」歐修士說他當總務的時候,就常與對財物輕重毫不在乎的紀神父起衝突,因為這老兄三天兩頭把屬於修院的財產往外送。有時看歐修士氣急了,紀神父只是不好意思地聳聳肩:「天主還會再給我們的。」就這麼一句話打發過去。
六○年代,天主教會在梵二大公會議召開之前仍相當保守,除了全世界統一奉行沒有太多人懂的拉丁禮儀外,其教義也是唯我獨尊,非常排外。在嚴守戒命教條的保守氣氛中,紀神父的彌撒卻異常地開放。據達悟族人回憶,紀神父在蘭嶼開教初期,獻祭彌撒到了聖餐禮時,無論對方是教友或純粹因為好奇,只要前來領受,紀神父都會欣然地將白色麵餅分給他們。在他眼裡,基督是屬於眾人的,沒有甚麼教內和外邦人之分,受他幫忙的人也不一定得是教內的人。此外,他參加了達悟族所有的慶典(諸如飛魚祭、新船下水),就連一些不容更改的傳統禮儀,都順應在地文化而加以調整。
紀神父從一九五四年起,前後在蘭嶼服務了十六年。在那個原住民(尤其是男性只著丁字褲的達悟族)飽受歧視的年代裡,紀神父早將蘭嶼同胞視為自己的手足。多少次遇到達悟族同胞沒有足夠的裹腹食物時,紀神父總是噙著淚水咬緊牙關丟下一句:「我來想辦法!」就這麼把這重任扛了下來。
一九六七年蘭嶼的紅頭天主堂落成時,紀神父在傳統的迎賓儀式中,不小心坐空了椅子而摔倒,看在傳統的耆老眼中,這是個不祥之兆。
一九七○年三月十日,對蘭嶼教友來說,真是個悲痛逾恆的日子。紀神父自台東搭夜車送兩位原住民女孩到西部就業,在高雄坐上一部自嘉義送客來此的計程車,清晨,一夜未睡的司機在台南縣附近衝撞了路邊的大樹,紀神父被送到鄰近小診所後死亡,那時他不過五十歲。診所醫護人員自神父身上找到一串鏈珠,推斷這沒有任何身分證件的老外是位神父,於是輾轉聯絡台東的白冷會。
噩耗傳回東部,尤其是蘭嶼的教友,大家都悲慟不已,全鄉在紅頭天主堂為神父祈禱,當地政府更是極不尋常地以降半旗致哀。蘭嶼的信徒們為這位深受他們喜愛與敬仰的神父冠上「蘭嶼之父」的尊稱。他們深深記得,這位與他們同歡笑同哭泣的瑞士人帶領他們與窮困奮鬥,對抗外來的欺壓與歧視,更因神父的熱情與開放,重振了他們失落已久的自尊與自信。
紀守常神父過世的時候,我才十歲,當然沒有機會見到這位已成海角傳奇的瑞士人。多年前,
一封白冷會士的家書親愛的母親,自拿波里上船後,穿過蘇彝士運河,陸續經過北非、印度孟買、雅加達、新加坡、香港,經過一個多月的日夜兼程,我與其他會士弟兄終於抵達了台灣的東部。眼前這片美景只能用「歎為觀止」來形容啊!青翠的海岸山脈與瑞士的高山差不多,但美麗的太平洋卻是家鄉所沒有的。天氣很悶熱,熱得讓人受不了,很多時候我都覺得自己快被烤焦了,而且這裡沒有會院,我們住的地方相當簡陋,更別提伙食了,為了控制預算,我們的長上讓我們真的是吃不飽也喝不好,完全無法與在瑞士時相比擬;不過,這裡的人很窮,很多人都沒有...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47收藏
47收藏

 33二手徵求有驚喜
33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