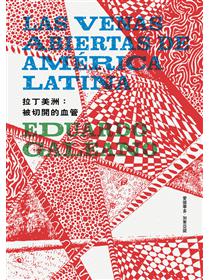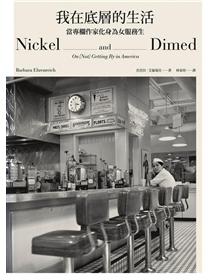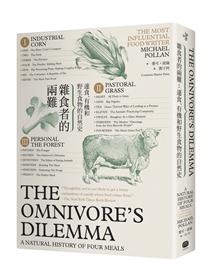特別推薦:南方朔、孫大川、陳光興、陳芳明、廖咸浩
印刻文學誌、破周報、中時開卷嚴選、優活健康網、中央廣播電台全球文化網好書推薦。
《大地上的受苦者》是弗朗茲‧法農的最後一本著作。早在《黑皮膚,白面具》一書中,法農便提出對於種族主義的反思,他認為種族主義並非偶發事件,亦非恣意妄為,而是一種宰制的文化體系,這種體系也在殖民地運作。若是不看清統治文化所帶來的壓迫效應與奴役現象,那麼對於種族主義的抗爭便是徒然,因為這種壓迫的觸角廣及社團、政治與文化,甚至也會影響個體的精神狀態。
在全球化對弱勢地區已然形成新殖民剝削的今天,法農的諸多觀點,都能讓我們看清當前的許多現象,原是源自整個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的淵藪。
作者簡介:
弗朗茲.法農(FrantzFanon),二十世紀最出色的後殖民主義論述先驅。1925年出生,1961年因血癌病逝。短短三十六年的一生,只留下四本完整的著作:《黑皮膚,白面具》、《阿爾及利亞革命第五年》(L'anⅤdelarévolutionalgérienne)、《大地上的受苦者》,以及過世後出版的論文集《邁向非洲革命》(Pourlarévolutionafricaine)。西蒙‧波娃譽為當代最傑出的人物之一。
一生充滿悲劇的法農,誕生於加勒比海的法屬殖民地馬提尼克島,二次世界大戰中,他自願入伍,在激烈戰役中受重傷幾乎喪命。戰爭結束後,他到里昂大學攻讀精神醫學,遭遇了不可理解的經驗:他發現他的法國「同胞」因為他的黑皮膚而疏遠、歧視他,對戰爭中死對頭的義大利人的親熱程度,更遠甚於他。1952年,法農寫下了震驚黑人世界與歐美知識份子的經典之作《黑皮膚,白面具》。1953年,他到阿爾及利亞一所醫院工作,目睹殖民地的悲慘情狀,開始思索殖民主義,而主要工具之一,就是精神醫學。他從精神醫學裡習得了關於壓抑、認同、反彈發洩與人格扭曲等概念,以過人的洞見與創意,將這些原本處理個人、家庭關係的分析方法,擴大運用在集體的殖民與被殖民現象上,並對暴力重新詮釋。1961年,他飽受血癌折磨,仍在生命最後一刻,奮力寫出了至今仍極具影響力的《大地上的受苦者》。
章節試閱
第一章 論暴力
被殖民者居住地帶與殖民者居住地帶,並不呈現互相補充的狀態。這兩個地帶互相對立,但這樣的對立不是為一個更高的統一而服務。這兩個被純粹亞里斯多德邏輯所支配的地帶,都遵守相互排斥的原則:無法和解,多說一句也是無益。殖民者的城市是石塊和鋼筋打造的銅牆鐵壁,燈火通明、舖上柏油。而城裡的垃圾箱總是塞滿了從未見過,甚至是從未夢想到的、不知名的殘渣。殖民者的雙腳從不被人看見,可能只在大海裡才展現;但我們從未足夠靠近到可以看見它們。結實的鞋子保護殖民者的腳,城市街道乾淨、光滑,沒有坑洞,沒有石子。殖民者的城市是座吃飽沒事幹又輕鬆的城市,肚子總填滿了好吃的東西。殖民者的城市是白人的、外國人的城市。
被殖民的城市,或至少是土著的市鎮、黑人的村子、阿拉伯街、印地安人保留區,則是聲名狼藉的地方,住滿了聲名狼藉的人。人們在那裡隨地、草草地被生了出來。隨地、隨便因某不知名原因死去。這是個沒有間隔的世界:人挨著人,小茅屋挨著小茅屋。被殖民者的城市是座飢餓城市,渴望著麵包、肉、鞋子、煤炭和光明。被殖民者的城市是座蹲下來的、屈膝的城市,一座躺臥著的城市。這是黑人的城市、阿拉伯人的城市。被殖民者以淫蕩、羨慕的眼神望著殖民者的城市,夢想佔有它。用盡所有佔有的形式:坐在殖民者的桌旁、躺在殖民者的床上,可能的話和殖民者的妻子上床。被殖民者是嫉妒的,殖民者不是不知道,在他瞥見被殖民者那失控的眼神時,酸苦地見識到這點,但他始終保持警惕:「那些傢伙想奪取我們的地位。」的確,一個被殖民者至少每天一次夢想處在殖民者的地位。
這被分割、被一分為二的世界裡,住著不同類別的人們。殖民地狀況的獨特性就在於:談經濟現實、不平等、生活模式極大的差異,都無法做到遮掩一個屬於人道這個層次上的現實。當我們快速審視殖民脈絡時,即可明白地看到,分隔這個世界的,首先是屬於或不屬於這個類別、這個種族的事實。在殖民地,經濟的下層結構同時也是上層結構。原因即結果:因為是白人而富有,因為富有而成為白人。所以,每當討論殖民地問題時,馬克思主義分析總是應該稍微放寬些。馬克思對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探討,並沒有到概念的層次上,我們在此也不是要去重新探討這個問題。農奴和騎士的本質不同,但兩者都必須借助神權來正當化身份的不同。在殖民地,從外地來的外國人,用槍砲和機械來強制統治。儘管他成功地制伏和據為己有,他始終是外國人。首先構成了「統治階級」特徵的,既非是工廠,也不是財產,亦不是銀行裡的帳戶, 。統治族群首先是外來的,那些不像當地人(autochtones)的,那些「他者」(les autres)。
暴力主宰了殖民地世界的佈局,不懈地破壞當地人的社會形態,毫無保留地摧毀了經濟、衣著和外表原先的參照座標。然而,當被殖民者決定成為歷史的舞台,奮力衝進禁區的一刻,被要求以及承受的,同樣是這個暴力。炸毀殖民地世界,今後將是十分清楚的行動意像,非常可以理解,也能被每個被殖民的構成份子遵循。瓦解殖民地世界,並不意味著在撤廢邊界線後,人們會整治兩個地帶間的通道。摧毀殖民地世界,不多不少,就是要取消一個地帶,把它埋在泥土深處,或把它趕出土地。
被殖民者對於殖民地世界提出的質疑,並非是觀點上的理性較量。那不是有關普遍概念的論述,而是一種把獨特性提出,當成絕對的瘋狂論證。殖民地世界是摩尼教的善惡二元論世界。殖民者對被殖民者做肉體上的限制,也就是藉由警察和憲兵,限制被殖民者的空間,這還不夠。就好比為了闡明殖民剝削的極權主義特點般,殖民者把被殖民者描述成一種「惡的精髓」。被殖民者社會不只被描述成一個沒有價值標準的社會。殖民者斷言,在被殖民者的社會中,這些價值標準不是被拋棄了,就是根本不曾存在過,這樣說還不夠。被殖民者被宣稱為,對倫理學是抵制的,不僅缺乏價值,也是對價值的否定。他是,讓我們敢於承認這點,價值的敵人。在這個意義上,他是絕對的壞。他是腐蝕成份,破壞一切接近他的東西的,是扭曲成份,使一切與美或道德有關的東西變了形,是一切不吉祥力量的受託人,是盲目暴力的無意識及無法回收的工具。梅爾先生(Meyer)可以在法國國會上嚴肅地說,不應該讓阿爾及利亞人進來國會殿堂嫖淫共和國。的確,自從和被殖民者接觸過後,所有的價值就不可逆轉地中了毒和被污染了。被殖民者的習俗、傳統、神話,尤其是神話,就是貧困、體質敗壞的標誌。所以,這也就是為何,要把下列兩件事放於同一平面上來看:用DDT消滅寄生蟲、疾病的媒介,以及基督教在異端邪說、本能、邪惡等等還在萌芽的狀態時就把它們給扼殺了。黃熱病的消除和福音佈道的進步,分屬同一份決算表。但是,佈道團的捷報實際上告訴我們在被殖民者內部引進異化酵素之重要性。我談基督教,誰也沒權利對此感到驚訝。殖民地的教會是白人的教會、外國人的教會。它並不召喚被殖民者走向上帝,而是走向白人的道路、主人的道路、壓迫者的道路。如眾所皆知的,在這一歷程中許多人被徵召,卻很少人入選。
有時候,這個善惡二元論竟然達到邏輯上的極端,將被殖民者去人性。確切地說,把被殖民者動物化了。因此,當殖民者談到被殖民者時,他使用的語言是動物學的語言。他影射黃種人的爬行、土著住所散發出的氣味、游牧部落、惡臭、大量繁殖、亂鑽亂動、比手畫腳。當殖民者想描述或找出一個恰當的字眼時,經常參考中世紀的動物寓言集。歐洲人很少依靠「形象化了的」詞。但是,領悟了殖民者計畫的被殖民者,理解了人家對他興訟的意圖,立刻知道對方在想什麼。這個爬升的人口統計圖,這些歇斯底里的群眾,這些完全沒有人性的面孔,這些胖得什麼也不像的身體,這群沒頭沒尾的人,這些似乎不屬於任何人的野孩子,這種攤在太陽下的懶散,這種植物般的韻律,這些都成了殖民辭彙當中的一部分。不久就要湧現了,那些戴高樂將軍講到的「黃色人群」、莫里亞克先生(M. Mauriac)講到的黑色、棕色和黃色群眾。被殖民者知道一切,並且呵呵大笑,每當他們在他者的話語裡發現自己成了動物。因為他知道自己不是動物。更確切地說,恰在他發現自己的人性的同時,他擦亮武器,做好戰鬥準備,要讓人性獲勝。
一旦當被殖民者開始搗亂,開始讓殖民者惶恐不安時,我們就會派出一些善良的靈魂,在「文化大會」上向他展示西方價值的特殊性及豐富性。但是,每當話題牽涉西方價值時,立刻就會在被殖民者身上產生一種僵直、肌肉痙攣現象。在去殖民階段,被召喚的則是被殖民者的理性。我們向他們提出一些確切的價值,充分向他們解釋:去殖民不該意味著倒退,而是應該建立在一些經試煉過、牢靠、受評定的價值上頭。然而,目前的情況是,當一個被殖民者聽到一段有關西方文化的論述時,他就抽出自己的大砍刀,或至少要確保刀子在隨手可拿到之處。白人價值之所以擁有優越性,是受到暴力的保證,白人價值在對決的過程中勝過被殖民者的生活或思想方式,是浸滿在侵略性中的。暴力、侵略性,透過復返,使得當我們在被殖民者面前提起這些價值時,不免換來冷笑。在殖民的脈絡中,殖民者從未停止過對被殖民者的攻擊,除非被殖民者高聲清楚地承認白人的價值優越。在去殖民時期,被殖民大眾對這些價值不屑一顧、蔑視並唾棄它。
這種現象通常被掩蓋起來,因為在去殖民時期,一些被殖民的知識份子已經跟殖民國家的資產階級建立了對話關係。在這個期間,當地居民只被視為面貌糢糊不清的群眾。殖民的資產階級有機會在各處認識的幾個土著,不足在立即的感知上發揮作用,使得差異化得以產生。相反地,在解放時期,殖民主義的資產階級熱切地尋找與「社會菁英」們接觸。
那著名的、針對價值的對話,是與這些菁英進行的。殖民資產階級認識到自己不可能在殖民地維持統治時,就決定進行文化、價值及技術各領域的後衛戰。然而,絕不應該忘記的,是佔極大多數的被殖民民眾,他們對這些問題漠不關心。對被殖民者而言,最根本的價值,首先是土地,因為這最具體:土地保證了麵包,當然,也保證了尊嚴。但這個尊嚴與做為具「人道的人」的尊嚴無關。這個理想的人,他從未聽人說過。他在自己土地上看到的,是我們可以抓他、打他、使他挨餓,卻不受懲罰;從未有過任何一個倫理學教授或神父,過來代他被打,並跟他分享麵包。對被殖民者而言,作為一個倫理學家可以十分具體,就是使殖民者的傲慢噤聲,使他行使的暴力粉碎,簡單地說,就是直接了當地把殖民者從全景圖中驅逐。人人平等這一著名的原則,在殖民地會找到對此的闡釋,只有當被殖民者提出,他與殖民者是平起平坐之時。再進一步,他想要為超越殖民者而戰鬥。事實上,他已決定代替殖民者,並佔據他的位置。正如我們所見,整個物質和道德的世界崩潰了。一直在抽象普遍性方面遵從殖民主義者的知識份子,如今為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能夠在新世界和平共處而奮鬥。但是,他沒有看見,因為確切地說,那是由於殖民主義已經滲透到他所有的思想模式中了,他看不到一個事實:殖民者,一旦殖民的脈絡消失,也就沒必要與他們共存了。這個情況的出現並非偶然:在阿爾及利亞政府和法國政府談判以前,歐洲少數所謂的「自由主義者」已經清楚地表態:他們要求,不多不少,雙重的公民資格。就是由於我們局限在抽象的層次上,才想迫使殖民者在未知中做一個十分具體的飛躍。讓我們這麼說吧,殖民者完全知道任何浮誇的詞藻也取代不了現實。
第一章 論暴力
被殖民者居住地帶與殖民者居住地帶,並不呈現互相補充的狀態。這兩個地帶互相對立,但這樣的對立不是為一個更高的統一而服務。這兩個被純粹亞里斯多德邏輯所支配的地帶,都遵守相互排斥的原則:無法和解,多說一句也是無益。殖民者的城市是石塊和鋼筋打造的銅牆鐵壁,燈火通明、舖上柏油。而城裡的垃圾箱總是塞滿了從未見過,甚至是從未夢想到的、不知名的殘渣。殖民者的雙腳從不被人看見,可能只在大海裡才展現;但我們從未足夠靠近到可以看見它們。結實的鞋子保護殖民者的腳,城市街道乾淨、光滑,沒有坑洞,沒有石子。...
推薦序
永遠追問的人
書序作者:精神科醫師、《黑色吶喊:法農肖像》作者 艾莉絲‧薛爾齊(Alice Cherki)
《大地上的受苦者》一書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月底,由法國馬斯佩羅出版社(Editions François Maspero)出版,當時作者弗朗茲‧法農罹患白血病,正在美國華府附近的貝塞斯達醫院與死神奮戰。為了避免一出版便被查封,這本書是在半隱密的狀態下很艱辛印刷出來的,但還是一發行便以「有害國家內部安全」的主要罪狀遭到查禁。這種情形早已發生在法農的上一本書《阿爾及利亞革命第五年》(L'An Ⅴ de la révolution algérienne,一九五九年同樣由馬斯佩羅出版),其他一些有關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書籍亦同(比如:墨利斯‧馬辛諾〔Maurice Maschino〕的《拒絕》〔Le refus〕、亨利‧阿萊〔Henri Alleg〕的《問題》〔La Question〕)。這種查禁在當時是屢見不鮮的。
然而,這本書仍開始流通,並且在媒體引起極大的迴響。經過一番非常繁瑣的運送過程(甚至繞道土耳其),法農終於在十二月三日收到一本樣書,另有一些剪報,其中包括一篇尚‧丹尼耶爾(Jean Daniel)寫的長篇論述,發表於十一月三十日的《快訊》(L'Express),可以算是一篇褒揚的評論。法農讓人把這篇文章唸出來給他聽之後,說道:「沒錯,但這也不能喚回我的骨髓。」幾天後法農便與世長辭,日期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當時他三十六歲。
精神醫學與政治之路
法農於一九二五年出生於馬提尼克島的法蘭西堡,來自一個富裕的小資產階級家庭,手足眾多,成長在一個老殖民世界裡,還沒開始對奴役的現象提出質疑。不過,法農倒是在十分年輕的時候,便參加了「第五部隊」(Le bataillon Ⅴ)—由戴高樂主義力量(Les Forces gaullistes)整編的加勒比籍自願軍。參與這個活動的過程,培育了他的反抗意識,但也讓他體驗到層出不窮、無所不在的種族歧視。復員之後,他於一九四五年戴著十字軍勳章返回馬提尼克(頒給他勳章的人就是後來的沙隆將軍〔Le général Salan〕,他後來常說這是他和對方唯一有過交集的東西),通過高中會考並經常與埃梅‧塞杰爾(Aimé Césaire)往來(他十分欣賞塞杰爾,不過當時已經很不認同對方的政治觀點)。彼時,塞杰爾選擇把馬提尼克視為屬於法國的一個省份。
很快的,法農來到法國,於里昂攻讀醫學。除了這門科目之外,他也非常熱愛哲學、人類學與戲劇,並且很早就投入精神醫學的專業。與此同時,他雖沒加入任何黨派,卻參與了所有反殖民主義的運動,還編輯了《達姆|達姆報》(Tam Tam)—一份屬於殖民地留學生的小期刊。特別是,一九五二年他在《思想》(Esprit)雜誌發表了第一篇文章〈北非症候群〉(Le syndrome nord-africain),探討的是來自北非的勞工:這些人離鄉背井,承受著「每天每日都死去活來」的痛苦,和自己的原鄉切斷了聯繫,與他們的終極目標相距甚遠,成了一件給乒乒乓乓扔掉的東西。
他在聖亞爾邦(Saint-Alban)精神病院待了十五個月,並認識一個很重要的人:托斯克爾(François Tosquelle),原籍西班牙的精神科醫師,也是一位反佛朗哥派的鬥士。這對法農之所以走上精神醫學這條路,以及他後來對於政治的投入,都是個關鍵性的過程。他在這裡得以從各個層面研究精神疾病,這裡是精神與肉體、歷史與社會結構的交會之所。一九五三年,他通過精神科醫師資格考,接著被派往阿爾及利亞的布里達(Blida,阿爾及利亞布里達省省會)精神病院。不過早在一九五二年,在弗郎西斯‧瓊松(Francis Jeanson)的奔走下,法農的第一本著作《黑皮膚,白面具》已由法國門檻出版社(Editions du Seuil)出版。
在阿爾及利亞,他不僅發現自己與院方的傳統精神醫學格格不入,同時也不太認同阿爾及爾學派那些精神醫師對於「土著的原始狀態」的理論。他逐漸洞悉當時阿爾及利亞作為一個殖民地的現狀,隨即全力改造院裡的精神科,並負責引進他與托斯克爾共同實行的「社會治療法」。他因而不停修正醫護人員與精神病患之間的關係,他不僅和歐洲人,同時也和信奉回教的那些「土著」一同試圖恢復他們的本土文化、他們的語言、他們的社會生活組織,亦即所有能夠形成意識的東西。這一場小型的精神醫學革命,獲得了醫護人員的贊同(他們絕大部分都很關心政治),同時也得到當地政治活動份子的認可。法農的名聲從此遠播。當時是一九五五年,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已然開打。
面對阿爾及利亞人追求獨立的希求,法國社會黨政府竟視若無睹,讓法農感到相當不解;此後他的反殖民立場愈來愈聞名。後來「阿爾及利亞之友」(Amitié alg ériennes)的運動找上了法農:這是一個對政治犯家屬提供物質協助的人道主義協會,領導者是主張國家主義的政治活動份子,與占領布里附近那些基地的游擊份子有所聯繫。他們對法農的第一個請求,是要他負責醫療那些飽受精神錯亂之苦的游擊隊員。
就這樣,在精神醫學及政治活動的交替作用之下,法農投身於阿爾及利亞追求獨立的奮戰之中。一九五六年年底,在一封寫給總督侯貝爾‧拉寇斯特(Robert Lacoste)的公開信裡,他辭掉了精神科醫師的職務;他在信中寫道,他已經無法解救某些人,「使他們等到應有的待遇,這是一個把剝奪人權及不平等和謀殺當成合法原則的國家,當地人在自己的國家裡永遠都是瘋子,生活在一種完全沒有人格的狀態下。」於是法農被趕出了阿爾及利亞。
接著,一九五七年的第一季,他在法國度過三個月的時光;雖然他堅信阿爾及利亞的獨立已然勢不可擋,然而旅居法國這段期間,這樣的立場卻沒獲得任何迴響。在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陣線(Front de Liberation Nationale, FLN)法國總會的幫助下,法農得以前往突尼斯—那裡是國族解放運動境外組織設置的地點。與法國正式決裂。
法農在突尼斯同時從事精神醫學及政治這兩種活動。後來他成為國族解放陣線的刊物《鬥士報》(El Moudjahid)工作團隊的一員。他從內部親眼目睹國族解放陣線的所有矛盾之處,其中包括了政治代表和軍隊之間愈來愈嚴重的爭執。儘管經常大失所望,他仍舊繼續支持阿爾及利亞的解放運動,同時也是一位不斷創新的精神科醫師。他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愈來愈感到興趣,並於一九五九年年底由阿爾及利亞共和國的臨時政府任命為黑色非洲的巡迴大使。那是非洲各國爭取獨立的年頭。法農成為一個貨真價實的巡迴大使,盡心盡力從加納趕至喀麥隆,從安哥拉趕至馬利,為真正的獨立而鼓吹戰鬥。他甚至還想出一條可行的路線,由馬利出發,穿越撒哈拉沙漠去和阿爾及利亞的反動份子會合。
然而一九六○年十二月,法農於旅居突尼斯期間,發現自己罹患骨髓性白血病。他僅存一年的生命,並於這段時間寫了《大地上的受苦者》這本書。
為受苦者所發的吶喊
這是唯一一本由他自己選擇書名的著作(而非由出版社決定)—身為醫師,他很清楚自己的病,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
法農與時間及死神展開一段真正的競賽,一邊還期望著要向外傳遞一個最後的訊息。傳遞給誰呢?給那些不幸的人。然而這裡指的,絕大部分已經不再是十九世紀末工業國家裡的那些無產階級,那些高唱著「起來吧,大地上受苦的人;起來吧,飢寒交迫的人」的無產階級。法農想要與之對話的,那些在大地上受苦的人,是指貧窮國家裡那些不幸的人,那些真正想要土地和麵包的人;彼時,西方世界的勞工階級大多有種族歧視,而且顯然對海外的人民一無所知,再加上殖民地能間接帶來一些利益,因此他們對這些殖民地的命運,都表現出某種程度的冷漠。
這本書並非經濟論述,亦非社會學或政治性的評論,而是對殖民地國家的現狀與變化所發出的呼籲,甚至可說是吶喊。在整本書中,法農著力研究政治、文化與個人的關係,而且很強調經濟、政治及文化等層面的控制對被殖民者產生的效應。他的分析,注重的是奴役制度的後果,對象不僅包括各種國族也包括個人,同時他也強調這些人要獲得解放的條件,首先在於個人的解放,亦即「人的去殖民化」。
《大地上的受苦者》是弗朗茲‧法農的最後一本著作。他在一九五二年,年僅二十五歲時,便寫了《黑皮膚,白面具》;一九五九年寫的《阿爾及利亞革命第五年》,則是馬斯佩羅早期出版的書籍之一。此外他還發表了為數眾多的文章:包括先前已提過的〈北非症候群〉,以及一些相關精神醫學的文章,特別是一九五六年在第一次黑人作家與藝術家研討大會發表的〈種族歧視與文化〉;接著是〈文化與國族〉,於一九五九年在羅馬召開的第二次黑人作家大會上發表。在所有這些文章當中,論據的推展並非建立於理論之上,而是以實務經驗作為基礎;這些經驗同時也是他思想發展的起始點。早在《黑皮膚,白面具》一書,關於種族主義的反思,便聚焦於某些文化片面宣告的文化統治:種族主義並非偶發事件,亦非恣意妄為,而是一種宰制的文化體系,這種體系也在殖民地運作。若是不看清統治文化所帶來的壓迫效應,那麼對於種族主義的抗爭便是徒然,因為這種壓迫的觸角廣及社團、政治與文化,甚至也會影響個體的精神狀態。
《大地上的受苦者》一書,持續對統治階層所造成的奴役現象提出上述質疑;這個統治階層,能同時使團體與個人在各自的變化中遭受破壞、有所轉變。本書提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的現況,也提出解放的條件,除了政治文化的解放,還要加上個人的解放,政治鬥爭更為激進。此外,最後兩個章節當中,一章是探討文化及建構國家的關係,另一章則是闡述阿爾及利亞戰爭所造成的心理創傷。
法農由自己的特殊經歷出發,從最貼身的故事寫到他投身其中的過程,而這樣的經驗也是他不得不書寫出來,並傳達給旁人知曉的。他的書寫依循著以下的脈動:組成本書的五個章節各有不同主題,一段一段,有如詩歌裡的段落,穿插嚴謹的分析,書寫的語言,總是企圖在意義之外,能促進了解,而非只是玩弄抽象觀念,正如同年輕的法農提到自己的第一本書《黑皮膚,白面具》時講的那樣。
有人曾經責備,也有權責備法農將不同文類及不同層次的論述混為一談(政治、文化及心理分析),責備他援用了自己作為精神科醫師的經驗,將這些關於精神錯亂的素材引入政治領域。有人曾經責備過他的風格,認定他的文字很激情,而且極富預言色彩。然而,矛盾的是,這正是法農的現代性所在。作為一個精神科醫師,他苦難的主觀性經驗,使他與苦難的人直接接觸。
也有人責備他過於強調暴力。然而法農卻是由實地經驗得知對一個個體行使暴力所造成的後果:這個個體沒有出路,只會漸失人性,變成鐵石心腸,或充滿可怕的暴力衝動,終而付諸錯誤的行為。這種暴力,不應加以否定,而應該加以組織,進行解放鬥爭,從而超越暴力。在〈種族主義與文化〉一文,法農對自己的醫療行為做出如下結論:「占領者那種既扭曲又僵硬的文化,在解放之後,終於對另一個國族的文化開放(這個國族已經成為他們真正的兄弟)。這兩種文化能互相對立,也能彼此相長。
〔……〕一旦將殖民統治永遠排除,決定包容不同文化的相對差異,就能找到普世共存的價值。」另外在《黑皮膚,白面具》一書,他也同樣提出這種存在於黑人世界與白人世界的超越:「這兩者必須脫離他們各自的祖先曾經有過的非人聲音,讓真正的溝通誕生。」這種超越的觀點,彼時,已存在於《大地上的受苦者》一書當中。雖然後來在政治鬥爭中變得更為激進。
法農當時很希望沙特能為這本書寫序,豈料過去這些年來,這篇精彩的序言竟比本書內文還擁有更多讀者。然而,那篇序文多少扭曲了法農的關懷和語調。這篇序言主要是寫給歐洲人看的,因而與書中內容並不是很協調。至於法農,他發表言論的對象,其實是除了歐洲人以外的所有人,他是在跟他們談論未來,而在那個未來,他們終將超越「對他者的恐懼」。沙特的那篇序言尤其還誇大了法農對於暴力的分析。事實上,法農對暴力進行分析,沙特卻是在為暴力辯解,法農並未將暴力當作目的,而是視它為一種無可避免的過程。沙特的文字有時充滿鼓吹犯罪的口氣。比方如下的句子:「讀一讀法農的書吧!你們就會知道,被殖民者在無能為力的時候,殺人的瘋狂念頭,就是他們的集體無意識。」或者還有這一句:「殺死一個歐洲人,這是一舉兩得的—同時清除一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一個人死了,一個自由人活下來。」這其實都削減了法農那些主張的真義,因為看起來這些句子要辯解的已經不再是暴力,而是個人的謀殺行為。它所辯解的已經是那種犯罪的行為,而不再是人人天生都有的暴力—這種暴力喚起了人類自身內在可能存有的個性。法農當初閱讀沙特這篇序文時,並未做出任何評論,甚至還一反常態,保持極度的沉默。不過,他倒是給出版社寫了封信,希望將來時機成熟,能有機會說明自己的看法。
為被壓迫的人而戰
《大地上的受苦者》被視為七○年代的指標性書籍,內容主要在探討第三世界主義,然而政治議題掩蓋了他對被壓迫者之所以精神錯亂所提出的強烈質疑,這本書隨即遭人遺忘,法農的全部作品也都被視為不合時宜。他的政治膽識關注的是一個已過去的去殖民化時代,因此也被視為陳腐過時,而他本身的期待也迫於現實而無法實現。那麼對於爭取解放的那一大群農民,法農是否高估了他們的力量?我們可以發現,在當時阿爾及利亞爭取獨立的政治現狀中,大部分參與奮戰的鬥士皆為農民。別忘了法農所寫的是一個特定的歷史經驗。況且,在他看來,農民的活動力也能與革命的作用互相輝映,正如同他在本書第二章〈自發性的偉大與弱點〉解釋的那樣。
那麼他是否低估了宗教的力量?事實上,他所參與的阿爾及利亞解放運動,呈現出來的並不是一種回教徒的革命,反倒結合了各種不同潮流—一九五六年的蘇盟河(Soummam)大會綱領,雖然發起人立場不同,但沒有特別強調宗教定於一尊,反而主張應該尊重多樣化的意見。法農曾呼籲那些正在進行去殖民化的國家革新,並要他們創造出一個全新的人,然而非洲國家後來的演變,不正否決了這樣的呼籲?此後在地緣政治上的發展,不正好與他的期待背道而馳?事實上,這樣的發展,倒是證明了他所提出的那些警告並非憑空無據(請見第三章〈國族意識之厄運〉)。
法農分析的是一件偶發的事實,因此我們若是只把他的作品局限在當時的時代背景,沒有將之視為對於一切可能變革的呼籲,那麼他的著作就很容易被評為與時代脫節。難道由於他的期待並未實現,我們便認定他針對現實所提出的那些論點謬誤百出?我們都很明白,這個現實(其中也包括暴力)在今日,已經不再是「殖民壓迫」或「第三世界的未來」,而是「愈來愈嚴重的不平等」、「南北之間愈來愈大的差異」、「被邊緣化」、「把人類物化」。
去殖民化運動及阿爾及利亞戰爭經過四十年後,在一個朝著全球化經濟的「強權」邁進的世界裡,這個事實不斷出現在南卅北的關係之中:浮上檯面的那種有計畫的腐敗,乃由非洲國家的政府一手安排,並由已開發世界的那些大型石油企業、醫藥企業及其他大公司一手促成。與此同時,對一切有害於民主解放運動、有害於人民主動參與政事的行為,這個已開發世界卻以不主動干涉作為藉口(尤其是以維持經濟帝國主義作為藉口),表現出無動於衷的態度,而那些民主解放運動及人民主動參與政事的行為,正是法農所鼓吹的,並使他從一個關心時事的精神科醫師,變身為政治活動份子,為那些被壓迫的人民而戰。
然而這件事實並不僅僅與那些所謂的「開發中國家」有所關聯。它同時也攸關所謂「已開發世界」裡愈來愈嚴重的不平等現象,在這個已開發世界,不幸的人必然生活不穩定或失業,他們的位置沒有任何前景—被排斥、被邊緣化。法農嚴詞批判這種現象,因為他不希望對每個人而言,生活都像「死到臨頭」一樣,每天每日苟延殘喘,使得生命看起來「並非朝氣蓬勃或方興未艾,而是不斷和無所不在的死神奮戰」。法農希望每一個人在他的歷史中都是主角,在政治上都是主動的參與者。
跨時代的思想論述
從盧安達到波士尼亞,從阿富汗到中東,連美洲與歐洲也不例外,處處都是分裂的世界,戰火綿延,血流成河,暴力事件層出不窮,那些國家對於它們所挑起的一切感到既震驚又憤懣,而那些人民的暴力也導致一種沒有人性的惡性循環,使二十一世紀那些世代的思想、生活與未來都為之崩解,無論就個人或集體的層面來看都一樣。
現在還是有人在討論阿爾及利亞戰爭;曾經有三十五年的時間大家都把它稱為「事件」,如今終於為它正名了。大家又重新描述了那件事實,揭發那個酷刑。然而許多時事評論,對於當時敵對的那兩個陣營的暴行,各打五十板,卻忌談兩方的「不對稱武力」。對於當時那兩個彼此隔絕、拒絕溝通的世界,法農曾經針對它們的武力關係作出分析,而那種武力關係,在當今世上的許多地區,不是也依然存在?當那些已開發的社會與國家,發現自己的領土竟慘遭暴力威脅而感到震驚之際,他們心中的憤懣難道不會取代原有的理性?試想:當兩個世界之間無法締結任何條約,當透過對話而進行調停的空間關上大門,當實力較強的那個世界自詡為另一個世界的主人時,會有什麼結果?這可預見的前景,使法農憂心,並促使他撰寫《大地上的受苦者》,正是對於這個世界的先見之明。
法農也見到戰爭(其中也包括國族解放)所帶來的創傷性後果,造成無止境的後遺症,招來不斷重演的暴力及種族及身份認同的倒退。而這些倒退,貫穿二十世紀的歷史,並以一個既新穎又十分老舊的想法作為基礎,進入新世紀:將他人視為邪惡的化身,並自詡為善良的體現。這些景象,法農在《大地上的受苦者》一書分析殖民地的情勢時,便早已描述過:對殖民者而言,被殖民者就是邪惡的化身。除此之外,他還指出這種形勢在主觀層面所造成的毀滅性效應:被指為邪惡的那一方,由於在他人的眼光下動彈不得,首先會感到極度羞愧,接著就會變成仇恨。這個過程與今日情況,出奇的相似。
因此,閱讀《大地上的受苦者》時,要先超越作者撰寫這本書時在歷史背景所受的限制,而且要根據我們的時代特性來解讀。這本書究竟為我們帶來什麼啟示?我們看到無論在南半球或北半球,因時代發展而受到遺棄的人愈來愈多,而且面對全球化的趨勢,被這個時代特性認定為「一無所有」的人,所受的屈辱及自卑也屢見不鮮:他們沒有祖國,沒有國土,而且也沒有家,沒有工作,沒有身份證,更沒有表達意見的權利。
所以閱讀或重讀《大地上的受苦者》一書,有助於了解這種對人的剝削會有什麼後果:暴力、種族與身份認同的倒退。然而除了書中強調的這些主題之外,法農的思想還有以下的時代性:當大家一方面否定對精神疾病與權力關係做唯物論式分析,另一方面,也否定存在主義或文化主義觀點(或從心理分析角度,將之視為一種與周遭環境完全隔離的主觀探險),法農卻很有遠見的,試圖建立起一個新的知識體系,將身體、語言及「他人」經驗,視為建構未來政治所不可或缺的主觀經驗。這種方式,其實與馬庫斯(Marcuse)學派的方法相去不遠,或者更深入來說,與維也納那些政治精神分析學家的研究課題也所差不遠—後者因二次世界大戰而被迫逃亡至美國,飽受排擠與壓迫。
因此,法農之所以能表現出一種偉大的時代性,並非偶然。藉由自己的出身及經歷,他見證發生於上個世紀的那些事件(他本身就是那些事件的主角之一),對抗那個時代不斷出現的創痛。
若從法農的生活及思想活動來看,他也是極具時代性的:在這個經濟全球化、排斥個體的時代裡,青年法農所寫的那句話,那句代表他所有思想活動的話:「啊!我的身體!讓我永遠做一個追問的人吧!」超越了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垮台的那些東西,並在這個時代許多年輕人的心裡引起共鳴—無論他們講的是哪種語言,出生於何地。
永遠追問的人
書序作者:精神科醫師、《黑色吶喊:法農肖像》作者 艾莉絲‧薛爾齊(Alice Cherki)
《大地上的受苦者》一書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月底,由法國馬斯佩羅出版社(Editions François Maspero)出版,當時作者弗朗茲‧法農罹患白血病,正在美國華府附近的貝塞斯達醫院與死神奮戰。為了避免一出版便被查封,這本書是在半隱密的狀態下很艱辛印刷出來的,但還是一發行便以「有害國家內部安全」的主要罪狀遭到查禁。這種情形早已發生在法農的上一本書《阿爾及利亞革命第五年》(L'An Ⅴ de la révolution algérienne,一九五九年同樣...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38收藏
38收藏

 52二手徵求有驚喜
52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