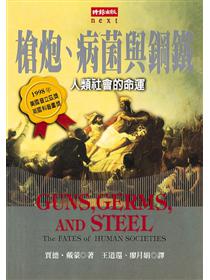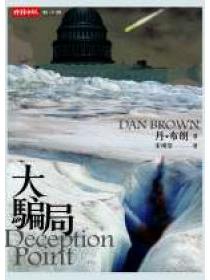●美國亞馬遜網路書店「2008年度編輯選書」
●2008年8月誠品外文館誠品選書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暢銷榜第3名
●《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暢銷榜第2名
●榮獲美國亞馬遜網路書店四顆半星評價,好評不斷!
●全美最大連鎖書店Barnes & Noble四顆星評價
●榮登全美各大暢銷排行榜!《今日美國報》(USA Today)全美暢銷書排行榜第14名!
◎一個發生在歷史狂濤中的故事,一部深刻細膩的成長小說,對男孩蛻變成男人的過程,有十分貼近當代的描寫。
一個是正經八百、賀爾蒙旺盛的少年,一個是油嘴滑舌、人見人愛、瘋狂又大膽的浪蕩子,兩個天差地別的男孩在旅程中結為莫逆。
◎人物角色刻畫生動,城市生活拿捏入味,作者描寫兩名令人難忘的年輕人,還有圍城期間的蘇聯絲絲入扣,小說技藝更上一層。
◎時而機智爆笑,時而驚悚緊張,帶領讀者踏上一段深入二十世紀最黑暗時期的旅程,同時也不忘贊頌動人友誼改寫人生的神奇力量。
一打讓你又哭又笑的救命雞蛋
《竊盜城市》講述兩個本來要被處以槍斃的列寧格勒年輕人,未料握有大權的上校的一道無厘頭命令:想辦法在五天內找到一打雞蛋,以備烘焙上校千金的婚禮蛋糕:給了他們死裡逃生的機會。然而,列寧格勒的物資被切斷,生活匱乏,不要說聽見雞叫聲了,想找到雞蛋本尊更是難上加難,兩位大男孩只好踏上尋蛋之旅的冒險故事。
《追風箏的孩子》作者卡勒德‧胡賽尼在讀了《竊盜城市》(City of Thieves)之後,驚為天人,力讚大衛‧班尼歐夫是個說故事高手,而且要讀者格外小心,因為故事情節驚心動魄。不僅令人手不釋卷,讀完還會久久縈繞心頭。(編輯秀娟)
作者簡介:
David Benioff
大衛‧班尼歐夫(David Benioff)是好萊塢小有名氣的編劇,參與過無數部好萊塢電影的編劇工作,日前參與了改編暢銷小說《追風箏的孩子》的電影編劇。除是編劇家之外,他的第一本小說《25小時》(The 25th Hours)也被改編成電影搬上大銀幕,一炮而紅,之後還出版過一本故事集《When the Nines Roll Over》。有些篇章收入《美國最佳新人小說選》和《美國最佳延伸閱讀作品選》。目前他跟妻女定居於洛杉磯。他的最新小說力作《竊賊城市》(City of Thieves)描寫二位年輕俄羅斯男子在圍剿的混亂列寧格勒市裡被迫偷12顆雞蛋保住性命的不可能指令,是一部帶有黑色幽默的小說。美國出版社Viking在今年五月出版,至今已賣出18國語文版權。
生日:生於一九七○年,美國紐約州紐約市
本名:大衛‧費里曼David Friedman
關於他的二三事
●作品《竊盜城市》(二○○八出版),乃根據俄裔外祖父列夫‧班尼歐夫在列寧格勒 圍城期間的親身經歷寫成
●改寫的劇本有《木馬屠城記》、《追風箏的孩子》,X戰警前傳《金鋼狼》
●改編《追風箏的孩子》獲英國金像獎及金衛星獎提名最佳改編劇本,並贏得二○○八年克里斯多福獎
譯者簡介:
謝佩妏
清大外文所畢,專職譯者。譯有《微國家》、《睡眠之屋》、《死亡的滋味》、《芭樂園的喧鬧》等書。
章節試閱
1
那種餓、那種冷,你一輩子也沒嘗過。一睡著,我們就會夢到七個月前吃的那頓大餐(塗了奶油的麵包、馬鈴薯球、臘腸),當時我們漫不經心,狼吞虎嚥,撒了一盤子碎屑和肉渣。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人登陸之前,我們以為已經夠苦了,但到了冬天,六月簡直有如天堂。
到了晚上,風呼呼吹個好響,停下來那一刻會嚇死人。轉角的咖啡館已經付之一炬,軋軋作響的遮陽板絞鏈戛然而止,不祥的幾秒間,彷彿有獵食者逼近,較小型的動物全嚇得不敢出聲。到了十二月,遮陽板已經被人拆去當柴燒。在列寧格勒再也找不到多餘的木頭。每塊木牌、公園長椅的板條、毀敗屋舍的地板,全都不翼而飛,成了某人家爐裡的柴火。鴿子也不見蹤影,被人抓了,放在涅瓦河取來的融雪裡燉煮。屠殺鴿子這件事沒人在意。引起騷動的是貓和狗。十月時,聽說有人烤了家裡的雜種狗,還把整隻狗五馬分屍當作晚餐。我們聽了哈哈大笑,搖頭直說不信,但也好奇狗肉如果加夠多鹽不知道好不好吃——鹽可多著呢,後來儘管什麼都用完了,我們還是不缺鹽。到了一月,傳言成了擺在眼前的事實。除了關係好的人之外,沒人有能力填寵物的肚子,所以只好寵物來填我們的肚子。
胖子和瘦子誰比較耐餓有兩種說法。一派人說,戰前就胖的人存活機率比較大,因為胖子就算一個禮拜不吃東西也不會瘦成皮包骨。另一派人說,瘦子本來食量就小,所以更耐得住餓。我投後者一票,純粹為了私心。我天生就發育不良。大鼻子,黑頭髮,滿臉痘子;坦白說,不是女生會喜歡的那一型。但戰爭讓我更有魅力。其他人因為食物配給量一減再減而日漸消瘦,占領前壯得跟馬戲團大力士似的人也瘦了一圈。我啊,反正沒多餘的肌肉可瘦,而且特別能吃苦耐勞,就好比鼩鼱,恐龍紛紛在周圍倒下,也能繼續以腐肉為食。
除夕那天,我坐在基洛夫公寓的屋頂上(我五歲就住進這兒了,不過直到一九三四年基洛夫遭人射殺 ,城裡有一半地方都以他命名,這幢公寓才有了名字),看著雲層底下多艘胖鼓鼓的灰色防空飛艇蜂擁而來,等候轟炸機出現。那個時節太陽只在空中停留六小時,光線在地平線間倏忽來去,好像受了驚嚇。每晚我們四個人都會坐在屋頂上,三小時輪一次班,身邊備著水桶、沙桶、鐵鉗、鏟子,把找得到的襯衫、毛衣、大衣全往身上包,然後守望著天空。我們是消防員。德國人後來覺得發動突襲的代價太大,便轉採圍城攻勢,打算利用飢餓、轟炸、大火,逼我們投降。
戰前這棟公寓住了一千一百人,到了除夕只剩四百人左右。大多小孩九月德國人封鎖城市之前都已疏散。我媽和妹妹塔西雅到佛雅茲瑪投靠我舅舅。他們離開前一晚,我跟我媽吵了一架,那是我們第一次吵架——正確地說,應該是我第一次吵架回嘴。我媽要我跟他們一起走,當然是想逃離入侵者,躲到窮鄉僻壤轟炸機找不到地方。但我不想離開彼得堡。我是男子漢,要留下來保衛家園,要成為二十世紀的涅夫斯基也許沒那麼誇張啦。總之,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假如每個身強體壯的人都夾著尾巴逃跑,列寧格勒就會落入法西斯主義者手裡;沒有工人之城幫紅軍建造坦克和步槍,俄軍哪來的勝算?
我媽覺得這理由很不像話。我才剛滿十七,既不在軍工廠製造軍武,要從軍也得再等將近一年。保衛列寧格勒的工作還輪不到我,我留在這兒不過是多張嘴吃飯。這些難聽話我都當成耳邊風。
「我是消防員啊。」我說。是真的,市議會要市民組成一萬個消防小組,我以身為基洛夫五樓的消防小組組長為榮。
我媽四十歲不到,卻已經一頭灰髮。她坐在餐桌前我的對面,雙手握著我的手。我媽個頭嬌小,身高不到五呎,但我從小就怕她。
「你這傻瓜。」她說。聽起來也許像在罵人,但我媽都叫我「她的傻瓜」,在這之前我一直認為這是表達關愛的暱稱。「你還沒出生,這城市就在了;你不在了,它也會繼續存在。你媽和你妹需要你。」
媽說得沒錯。是個好兒子、好哥哥一定會隨他們去。塔西雅很喜歡我,看我放學回家就會跳到我身上,念她寫的讚頌革命烈士的可笑小詩作業給我聽、在筆記本上誇張地描摩我大鼻子的側面圖。大多時候我都想勒死她。我一點也不想跟著我媽和毛頭妹妹翻山越河,長途跋涉。我今年十七歲,滿心相信自己這輩子注定是英雄豪傑命。莫洛托夫開戰那天的廣播聲明——我方開戰有正當的理由。敵人勢必悽慘落敗,我們必將光榮獲勝——印在大街小巷的海報上和牆壁上。我相信開戰的理由,絕不落跑,也絕不要錯過勝利。
媽和塔西雅隔天早上就走了,他們搭一段巴士、招軍用卡車搭便車,再蹬著鞋底開花的靴子走無止盡的長路。他們花了三星期才到目的地,但終究是平安抵達了。我媽寫了封信描寫沿途的驚險和疲憊,也許是想讓我覺得因為拋下他們而良心不安。我確實良心不安,但還是覺得他們走了比較好。大戰即將爆發,而他們不屬於前線戰場。十月七日,德軍占領佛雅茲瑪,媽的信從此就斷了。
我很想說我很想念他們,偶爾夜裡覺得孤單,而且每天都想念我媽做的菜,但其實我從小就嚮往自食其力。我最喜歡的傳說,都是關於聰慧過人的孤兒順利穿越幽暗森林,運用機智化險為夷,擊退勁敵,在流浪途中找到金銀財寶的故事。我不會說自己是開心的,大家都餓到開心不起來,但我相信這樣堅持下去才有意義。如果列寧格勒倒下,蘇聯也會倒下;如果蘇聯倒下,法西斯主義就會征服全世界。大家都這麼相信。至今我仍然深信不疑。
所以囉,我年紀太小不能從軍,但白天挖坦克陷阱、晚上看守屋頂還行。我這組的隊員由五樓的好友組成:維拉•歐斯波夫納是個天才大提琴手,還有一頭紅髮的安托柯斯基雙胞胎兄弟,他們唯一公認的才華就是同步放屁。戰爭初期,我們會在屋頂上抽菸,擺出士兵的樣子,勇敢,堅毅,下巴方正,掃視天空尋找敵軍的蹤影。到了十二月末,列寧格勒已經找不到香菸,至少沒有菸草做的香菸。幾個饞得發慌的人把落葉擣碎,以紙捲起,管這叫「秋光」,說什麼樹葉要是選得對,燒出來的煙就挺有樣子的。但基洛夫公寓離最近一顆安然挺立的樹有段距離,所以連假菸也沒得抽了。閒著沒事我們就去補老鼠,城裡的老鼠一定以為野貓消失無蹤是上天大發慈悲,聽見了牠們長久以來的禱告,直到發現垃圾堆裡沒東西可扒,方才美夢破碎。
經過連月的轟炸,我們已經可以從引擎聲大小來辨認各型德國軍機。那晚天空上飛的是約克八八(幾個禮拜以來都是),取代之前我方戰鬥機越轟越上手的駭克戰機和多尼爾戰機。我們的城市白天滿目瘡痍,入夜竟有一種圍城的詭異美感。如果月色明亮,從公寓屋頂望出去,列寧格勒盡在眼前:海軍部的高塔尖頂(灑上灰彩以混淆轟炸機);彼得保羅要塞(尖塔披上偽裝網);聖以撒大教堂和濺血教堂。我們看得見附近屋頂上有人在部署高射砲。我方的波羅的海艦隊已經進駐涅瓦河,高大的灰衣哨兵在海上漂浮,大槍對準納粹的砲臺發射。
最壯觀的是空戰。約克八八和蘇霍戰機在城市上方盤旋,但除非被厲害的探照燈照到,否則底下根本看不到。蘇霍戰機的機翼底下印上大紅星星,因此我方防空人員不會對他們開火。每隔幾晚,我們就會看見戰場如同舞臺一樣亮起,較笨重、較緩慢的德國轟炸機拚命護航,要讓砲手瞄準神出鬼沒的俄國戰機。約克一中彈,起火的機身如從天而降的天使往下墜,這時各處屋頂轟然響起陣陣怒吼,所有砲手和消防隊員振臂揮拳,向立下大功的飛行員致敬。
我們帶了一小臺收音機上屋頂,在除夕這晚聽著莫斯科斯巴斯基塔的大鐘播放「國際歌」。維拉不知在哪兒發現了半顆洋蔥,她把洋蔥切成四塊放在盤子上,灑上葵花油。吃完洋葱之後,我們拿配給麵包把剩下的油抹得一乾二淨。配給麵包嘗起來不像麵包,甚至不像食物。德軍炸了巴達耶夫的穀倉之後,城裡的麵包店開始發揮創意。只要吃不死人,能加的全加進麵包裡。整城的人都在餓肚子,沒人吃得飽,但大家還是照樣抱怨麵包、抱怨那股木屑味兒、抱怨天一冷麵包就硬得跟什麼似的。為了啃麵包有人連牙都咬斷了。直到今天我連心愛的人長什麼樣都忘了,卻還記得那麵包的口感。
半顆洋蔥加上一百二十五公克分成四塊的麵包,這餐算挺像樣了。我們仰臥著,裹著毯子,看著空擊飛艇拖著長長的繫繩在風中飄送,聽著收音機的節拍。沒有音樂可播或新聞可報的時候,電臺就會放送節拍器的聲音,不絕於耳的答答聲讓大家知道這城市還沒淪陷,法西斯主義者還沒破門而入。廣播傳送的節拍就是彼得堡的心跳,德國人想盡辦法也平息不了。
發現那人從天而降的是維拉。她失聲大叫,手往前指,我們全站起來察看究竟。有束探照燈照向一名往這座城市降落的傘兵,薄薄的降落傘在他頭頂上方,像團白色鬱金香球莖。
「是德國佬!」奧雷•安托柯斯基說。沒錯。我們看見那人身上的灰色納粹軍服。這傢伙從哪裡冒出來的?我們既沒聽見空戰的聲音,也沒聽到有關防空戰的報導,看守將近一個鐘頭更沒聽見轟炸機掠過上空。
「說不定開始了。」維拉說。幾個禮拜以來,一直有傳聞說德軍打算大舉空降傘兵,除掉列寧格勒這個眼中釘,讓節節進攻的德軍無後顧之憂。我們隨時準備一抬頭就會看見成千上萬納粹飄送而來,天空布滿白色降落傘,宛如一場白色雪暴。然而,多道探照燈掃射夜空,半個敵軍也沒發現。只有眼前這個,而且從掛在皮帶上的孱弱身軀看來,裡面的人應該已經掛了。
我們看著他飄下,在燈光下動也不動,一直落到我們看得到他腳上少了一隻黑靴的高度。
「朝我們的方向來了。」我說。風把他吹往維諾瓦街。雙胞胎兄弟面面相覷。
「魯格手槍。」奧雷說。
「是Wather PPK,德國空軍不拿魯格。」格里沙說。他比弟弟早五分鐘出生,對納粹軍武很有研究。
維拉揚起嘴角對我笑。「德國巧克力!」
我們衝向樓梯門,拋下滅火工具,跑下黑洞洞的樓梯。一群笨蛋。一不小心在水泥階梯上滑倒,全身骨稜稜一撞,十之八九會骨折,骨折就別想活了。但我們全不在乎。反正我們年輕,最要緊的是有個斷了氣的德國佬掉在維諾瓦街上,帶來了來自祖國7的禮物。
我們飛速穿過院子,攀越鎖上的柵門。街燈全暗,整座城市黑漆漆,一是為了混淆轟炸機,二是因為電力大多分給了軍工廠。不過,月光明亮,還看得見。維諾瓦街無人管制,門戶洞開,宵禁已經六個鐘頭。四下不見車輛。現在只有軍政人員拿得到汽油,而且剛開戰幾個月,民間車輛就被徵收了。商店窗戶都糊上一張張長條紙,廣播上說這樣比較耐震。大概吧,只不過我路過列寧格勒很多店面,看見窗框上除了垂盪的長條紙以外,什麼也不剩。
到了街上我們仰望天空,卻找不到人。
「他到哪兒去了?」
「會不會掉在屋頂上?」
探照燈搜尋著夜空,但光線都集中在高樓的屋頂,沒有一束的角度照得到維諾瓦街。維拉扯了扯我大衣的衣領,這件又大又舊的海軍大衣是我爸留下來的,現在仍然嫌大,但比我擁有的任何東西都要溫暖。
我轉頭看見他輕輕飄下街道,我們盯上的德國佬腳上那隻黑靴擦過結冰的人行道,白色降落傘形成的巨大頂篷仍然迎風鼓漲,把他送往基洛夫公寓的大門。他下巴垂到胸口,黑髮上有點點冰晶,月光下的臉毫無血色。我們杵在原地,看著他飄近。那天冬天我們看過好多不可思議的事,自認為看到什麼也不至於吃驚,但我們錯了。如果德國佬拔槍掃射,我們誰也來不及逃跑。但沒有生命跡象的那人一樣死沉沉,最後風靜止,降落傘癟掉,他跌落在人行道上,最後又顏面掃地往前拖了幾公尺。
我們圍了上去。這名飛行員身材高大,體格健壯,假如我們曾看過他身著便服在彼得堡晃蕩,一定一眼就看出他是間諜——他那麼壯,看起來就像天天吃肉。
格里沙屈膝解開他腰間的手槍皮套。「看吧,Walther PPK。」
我們把人轉過來。他蒼白的臉上有多處擦傷,皮膚被柏油路磨破,傷痕跟完好無傷的皮膚一樣慘白。他身上沒有淤傷。我看不出來他死時是害怕、掙扎抵抗,還是平靜泰然。他的臉上沒有生命跡象也看不出個性,好像生來就是一具屍體。
奧雷脫去他的黑色皮手套,維拉進攻圍巾和護目鏡。我發現飛行員腳踝綁了一把刀,便抽出這把護指板8為銀色、刃部有十五公分長的輕盈小刀,刀上刻了字,但在月光下看不清楚。我把刀子收入刀鞘,然後綁在自己的腳踝上,這麼多個月來第一次覺得我的戰士命運終於要成真了。
奧雷發現死者的皮夾,邊數德國馬克邊咧嘴笑。維拉把一只比一般手錶大一倍的精密鐘錶收進口袋,德國佬原本把錶戴在軍外套的袖管上。格里沙在一個皮革盒子裡發現一副折疊式雙筒望遠鏡、兩個額外的手槍彈匣,還有一個扁平的攜帶式酒瓶。
「干邑白蘭地?」
我啜了一口點點頭。「沒錯。」
「你哪時喝過白蘭地了?」維拉問。
「以前喝過。」
「什麼時候?」
「我看看。」奧雷說。酒瓶輪流傳送,我們四個人圍著墜地的飛行員蹲在地上,喝的酒可能是干邑或白蘭地或阿瑪涅克白蘭地。沒人知道差別在哪。管它是什麼,反正這東西灌進肚子暖烘烘的。
維拉瞪著德國佬的臉看,表情沒有憐憫或恐懼,只有好奇和輕蔑。這名侵略者到我們的家園投射炸彈,卻反倒把自己投下敵營。人雖然不是我們打下來的,但我們還是很得意。基洛夫公寓沒有人看過敵軍的屍體。天一亮我們就會成了街頭巷尾的話題人物。
「你們覺得他怎麼死的?」維拉問。他身上沒有槍傷,毛髮或皮革也無燒傷,完全沒有打鬥痕跡。雖然皮膚白得不像活人,但全身上下沒有一處傷口。
「凍死的。」我篤定地說,雖然無從證明,但這就是事實。這名飛行員趁夜從列寧格勒幾千呎高的地方跳傘,地平面的空氣太冷,他穿的衣物不足以禦寒——在高空中,一旦出了溫暖的駕駛艙,他就別想活了。
格里沙高舉酒瓶致意。「敬冰天雪地。」
酒瓶又開始傳送,永遠傳不到我手中。宵禁的城市跟月亮一樣靜悄悄,我們早該聽到兩條街外的汽車引擎聲的,但卻只顧著喝酒、敬酒。直到有輛蓋茲軍車轉上維諾瓦街,厚重的輪胎轆轆壓過柏油路,車頭燈射向我們,我們才發現大事不妙。未經許可違反宵禁的懲罰是就地處決。拋下消防工作的懲罰是就地處決。強奪財物的處罰也是就地處決。法院已經停擺;警察都上了前線;監獄半滿,人數銳減。哪有食物分給國家的禍害?如果犯法又被抓,你就死定了。沒人有時間跟你講法律細節。
所以我們拔腿就跑。有誰比我們更清楚基洛夫公寓。只要攀過院子柵門,進入了黑森森又枝枝蔓蔓的建築體內,哪怕有三個月的時間也沒人找得到我們。我們聽見士兵大喊站住,但無所謂,聲音嚇不了我們,只有子彈才可怕,但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扣扳機。第一個跑到柵門前的是格里沙,他是我們之中最像運動員的。只見他跳上鐵欄杆,撐起身體。奧雷緊跟在他後面,我緊跟在奧雷後面。雖然身體瘦弱,肌肉也因為缺少蛋白質而縮水,但恐懼驅策我們以有生以來最快的速度攀過柵門。
快爬到柵門頂端我回頭看見維拉摔倒在雪地上。她兩眼直瞪著我,眼睛又大又驚恐。軍車在德國飛行員身旁停下、四個士兵走下車之際,她的雙手雙膝貼在地上。士兵在二十呎之外,手持步槍,但我還有時間一躍進門,消失在基洛夫公寓裡。
我希望能告訴你,我從沒想過要丟下維拉,見朋友有難我不作二想馬上伸出援手。但事實上,當下那一刻我恨死她了。我恨她在最危急的時刻笨手笨腳,抬頭用驚惶的棕眼瞪著我,選擇我當她的救星,雖然說她只吻過格里沙。我知道我沒辦法帶著那雙眼睛苦苦哀求我的回憶過一輩子,她也心知肚明。甚至當我跳下柵門,扶她站起來,拉她爬上鐵柵欄時,我都好恨她。我全身無力,但維拉不可能超過四十公斤。我把她推上柵門,只聽見士兵大喊大叫,靴跟喀喀扣響了人行道,步槍槍拴刷地拉開,就位。
待續……
1那種餓、那種冷,你一輩子也沒嘗過。一睡著,我們就會夢到七個月前吃的那頓大餐(塗了奶油的麵包、馬鈴薯球、臘腸),當時我們漫不經心,狼吞虎嚥,撒了一盤子碎屑和肉渣。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人登陸之前,我們以為已經夠苦了,但到了冬天,六月簡直有如天堂。到了晚上,風呼呼吹個好響,停下來那一刻會嚇死人。轉角的咖啡館已經付之一炬,軋軋作響的遮陽板絞鏈戛然而止,不祥的幾秒間,彷彿有獵食者逼近,較小型的動物全嚇得不敢出聲。到了十二月,遮陽板已經被人拆去當柴燒。在列寧格勒再也找不到多餘的木頭。每塊木牌、公園長椅的板條...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8收藏
18收藏

 9二手徵求有驚喜
9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