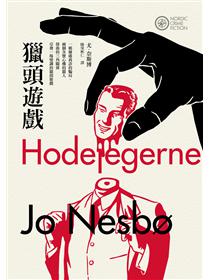原價1000 元 善心特價799元 一部搶手到連《哈利波特6》也被迫停印的超級巨著! 勇奪「龔固爾獎」、「法蘭西學院文學大獎」最高殊榮!像這樣的書,我們一生中看不到幾本!像這樣的書,人一生中大概也只能寫出一本!●讓法國讀者失魂落魄,狂銷突破100萬冊! ●史無前例!同時入圍「何諾多獎」、「費米娜獎」、「同盟獎」、「麥迪西獎」等6大文學獎!●美國《時代》雜誌2009年度十大小說!●英國《泰晤士報》10年來百大好書!●法國《費加洛》雜誌21世紀初最佳九大法文書!●法國《出版週刊》2008年度百大
作者簡介:
強納森‧利特爾 Jonathan Littell一九六七年生於美國紐約,父親是知名間諜小說家羅伯‧利特爾,家族則是十九世紀末從俄羅斯遷居美國的猶太人。三歲移居法國,十三至十六歲回美國就學,並回法國完成中學會考,之後進入耶魯大學,大學時便以英文寫下科幻小說處女作。利特爾認識《裸體午餐》作者威廉‧布洛斯後,受到強烈衝擊,開始閱讀布洛斯、薩德、席琳、尚‧惹內和貝克特作品,致力於將法國經典作家的作品翻譯成英文。在此同時,利特爾計畫寫作一套十部的鉅作,卻在寫到第三部時放棄。他自承《善心女神》的寫作動機,來自於看到一
譯者簡介:
蔡孟貞
一九六五年生。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法國普魯旺斯大學應用外語碩士。喜歡法文,喜歡法國。譯有《往事的力量》、《伊妲莉亞》、《凶眼》、《豹紋少年》、《最後一顆石頭》、《沉淪》、《放手》、《真愛獨白》、《暗夜無盡》、《聖殿指環》等作品。
章節試閱
四海兄弟們,讓我告訴您,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老實說,這段歷史滿悲慘的,但教育意義深遠,可說是不折不扣的寓言故事。過了這麼多年之後,我下定決心把這些寫出來,真正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釐清一切。
我經歷的往事數量驚人。我像一座往事的製造工廠。我一輩子都在製造往事,就算現在,雖然老闆付我薪水製造的是蕾絲花邊,往事的生產仍未中輟。
當戰後一切結束時,我成功來到法國,當個法國人;這其實沒有那麼難,因為當時社會動盪,我跟著一些被囚禁在集中營裡的囚犯回到法國,當局沒問太多的問題。我說得一口流利的法語,因為我母親是法國人,小時候我在法國住了十年,甚至還考上政治自由學院念了兩年大學。
我沒在巴黎逗留,我開始明查暗訪找到了一個舊識。我可不會說那次會面賓主盡歡,我呢,想找個工作,他呢,想保有現在的工作。因此他的表兄雇用了我,這段期間我結婚了,老實說,我還挺不情願的,婚後立刻讓她懷孕生子,目的是想讓她忙得無暇他顧。
年輕時代的夢,早就讓我過去的人生閱歷摧毀得無影無蹤了。從歐洲的這一端走到德國的另一頭,內心的焦慮慢慢平息。戰爭掏空了我整個人,只剩下酸苦和長期糾纏的恥辱,就像咀嚼沙粒般的喀滋喀滋作響。因此在社會規範下規矩生活,我安之如飴,儘管我常以嘲弄的冷眼看待一切安逸的表象,有時甚至感到憎惡。以這種生活步調,我寄望有一天我能夠達到傑洛姆‧納達所言的上帝恩寵的境界,無所畏懼。
基本上,我們活在最悲慘的人間煉獄中。戰爭當然結束了,而且世人也都得到了教訓,這種事不會再發生了。然而,您敢確定世人真的得到了教訓?您真的確定這種事絕對不會再發生了?再說,您真的百分之百確定戰爭已經結束了嗎?
而跟大多數的人一樣,我並不是自己選擇要當劊子手的。
如果可以的話,就像我先前說過的,我想走文學這條路。若有才華,就當個作家,沒有才華,當個教書匠也可以,總之,我想生活在美好安詳的環境中,徜徉人類意志的偉大創作。是啊,除了心理變態之外,誰會想要去殺人?
事與願違,我反而成了法學家,國安署公務員,黨衛隊軍官,最後當上蕾絲花邊廠的廠長。聽來有點可悲,但事情就是這樣。我上面寫的都是真的,不過我曾經愛過一個女人。唯一的一個,我對她的愛遠超過世上的一切。但是,這個女人我卻碰不得。
為什麼一個德國黨衛隊一級突擊隊大隊長不能跟其他的男人一樣,有屬於自己的內心世界、慾望和愛戀呢?後來戰爭爆發,我發覺自己被捲入恐怖又殘酷的暴行核心。然而,我並沒有變,我還是同一個人,我的老問題仍舊懸在那兒,儘管戰爭衍生了新的問題,儘管戰爭的恐怖讓我從頭到腳變了個樣。對某些人來說,戰爭,甚至殺戮,是他們問題的答案,可是我不是這種人,我跟大部分的人一樣,戰爭和殺戮對我而言是個大問號,找不到答案的疑問,因為深夜裡我們的嘶吼得不到任何人的回應。
事情如連鎖效應,一件接著一件,起先只是服國民役,衝突事件接踵而至,壓力驟增,最後不得不跨越兵役的界線。艾克哈特曾寫:煉獄天使乘著一朵小小的天國白雲飛翔。我一直認為反過來說也應該說得通,天國的惡魔繞著一朵小小煉獄烏雲盤旋。但是我不認為自己是惡魔。
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我的熱誠遭人利用,用來落實一個後來才驚覺既醜惡又瘋狂的藍圖,我跨越了黑暗邊界,所有的黑暗罪惡一股腦鑽進我的人生,再回頭一切已經無法補救,永遠無法挽回。
再也無法這四個字,說再多也沒有用了,它們就像落入沙中的水瞬間消逝無蹤,而溼潤的沙子塞滿了我的嘴。我繼續過日子,跟所有人一樣,盡可能奉獻一己之力,我跟其他人一樣,是個平凡至極的人,我是個跟您一樣的人。行了,我都說了,我跟您一樣!
***
開會的日期大概是六月二十七日,接近中午的時候,指揮部全員在學校操場集合,聽黨衛隊兼警察署最高總長訓示。他對我們說,我們的任務在於找出每個躲在我方戰線後面,有可能危害我方弟兄安全的可疑分子,並加以殲滅。
每一個布爾什維克黨黨羽、每一個猶太人,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有可能炸毀我軍的指揮中心,殺害我們的弟兄,破壞我們的運輸幹道,或者將機密情報傳遞給敵軍。我們的任務不是在等對方有所行動後,抓住兇手嚴刑懲罰,而是先一步破獲他們的巢穴,不讓他們有機會得逞。
鑑於我軍行進速度快速,不可能設立集中營集中囚禁管理犯人,因此可疑分子一律殺無赦。你們當中或許有人學過法律,我在此特別指出,蘇聯並未簽署海牙公約,我軍西線將士必須遵守的國際法在這裡並不適用。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我們也許會錯殺無辜,可是,唉,這就是戰爭;我們轟炸一座城市時,平民老百姓還不是跟著受害。
雖然這對我們來說是很難受的情況,身為人,身為德國人,天性中感性和細膩的一面總是深受煎熬,這一切他都知道,我們必須戰勝自己,他只能援引大統領的一句話,以大統領親口說的一句話與大家共勉之:身為主將,為了德意志,絕對不容有一絲懷疑。謝謝大家,希特勒萬歲。
最起碼這話說得夠坦白、說得冠冕堂皇,重點還不是要求我們一定要殘忍冷酷,滿口高調避重就輕,唯獨不肯明講的一點就是,我們即將被派往蘇聯。我們會覺得茫然無所從,其實其來有自,更何況,我們這些人毫無實地作戰經驗。
拿我來說,打從我進入國家安全局以來,我的工作幾乎全侷限在法律的相關文件歸檔,我敢肯定我絕對不是特例。柯赫胥負責有關組織方面的事務,連沃格,我們的第四小隊隊長也是來自文書部門。
我軍抵達時,路茨克仍是一片火海。國防軍的勤務兵負責帶領我們前往指揮總部,我軍被迫繞過老城區和堡壘,路線曲折複雜。先遣部隊忙進忙出,忙得不可開交。國防軍逮捕了數百名猶太人和趁火打劫的滋事分子,希望能交由我們處理。大火熊熊燃燒,火勢絲毫不減,看來破壞分子蓄意不讓火熄滅。
一天早上,詹森邀我加入一次行動。這事遲早會來。我早已了然於胸,也徹底想通了。老實說,我對我軍採取的方法的確有所保留,我敞開心胸誠實地探討過,卻還是無法完全理解。
我曾和牢裡的猶太人談過,那些人對我說,在他們心裡,亙古以來,所有的惡皆來自東方,所有的善皆來自西方。一九一八年,他們歡欣鼓舞迎接德軍到來,把德軍當作解放他們的救世主,那些人也以極為人道的方式對待他們;德軍拔營後,佩利烏哈領導的烏克蘭軍又回到這裡大肆屠殺。至於布爾什維克黨,只帶來飢荒。現在,我們又要殺他們。而且無可否認,我們殺了很多人。
儘管無法避免,也非這麼做不可,我仍然覺得這整件事非常不幸。不幸歸不幸,來了還是要面對,對於無法避免的必要行動,我們只能做好心理準備,隨時隨地準備面對它,接受它衍生的後果。閉上眼睛迴避,絕對不是辦法。我接受了詹森的邀約。
昨天夜裡下了一場雨,不過路還算好走,我們在兩片高聳的綠樹牆籬間緩緩行進,陽光點點,樹林阻隔了我們的視線,田野躲在林子後頭。我已經記不清那個小城叫什麼名字了,座落在一條大河畔,距離以前的蘇聯邊境大約只有幾公里遠。兩大民族共居於此,一邊是加里西亞農民,另一邊則是猶太人。我們抵達的時候,現場已經圍起封鎖線。
納格爾指著小城後方的樹林,「刑場就在那裡。」他顯得有些緊張遲疑,他肯定也還沒有殺過人。那些阿斯卡里已經把猶太人集中在城中廣場上,有成年人,也有青少年,他們都是從猶太人居住的巷弄裡一小群一小群抓過來的,被迫跪在地上,一旁有綠衣警察看守,偶爾會吃上幾記拳腳。除了幾聲哀嚎,一切顯得頗為平靜有序。
每輛卡車擠了大約三十名猶太人,總人數大約是一百五十幾人,但是我們只有三輛卡車,得來回走兩趟。等卡車裝滿人之後,納格爾揮手叫我上車,Opel駛進林間小路,卡車在後面跟著。我們來到一片林中空地,封鎖線已經圍起。卡車卸下乘客,納格爾下令挑幾個猶太人先去挖坑,其他的則在一旁等候。一名一級小隊長選了幾名猶太人,一人發一把鏟子,納格爾組織了一組押送隊,小隊立即深入樹林。卡車發動引擎開回去。
我望著那些猶太人,離我最近的那幾個臉色蒼白,但看起來還頗鎮靜。納格爾走過來,大聲地斥責我:「這是必要的,您懂嗎?要從大處著眼,人類的痛苦根本算不了什麼。」
「說得是沒錯,但生命總還是有那麼一點意義。」我搞不懂的就是這一點,我目瞪口呆看著眼前的景象,殺人之易,受死之難,兩者之間絕對不相容。對我們來說,這只是另一個慘澹的工作天,對他們來說,卻是一切的終結。
「就維持這樣,繼續。」一級小隊長咆哮著喊口令,阿斯卡里再次舉起步槍,架上肩頭。納格爾向前一步。「聽我號令……」他的聲音不帶任何感情,看得出來他很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緒。「開火!」
一陣槍響如狂風掃地,眼前隨即籠上一層槍彈煙霧,霧中一片殷紅。被擊倒的猶太人大多往前飛出去,迎面倒進水裡,其中兩個只是軟軟地躺在地上,四肢捲成一團,穩穩停在壕溝邊。
「清理一下,帶下一批上來。」納格爾命令著。烏克蘭人抓起那兩名死者的手腳,合力拋進溝裡,屍體落底,水花砰然四濺,鮮血從面目全非的頭上汨汨直流,在烏克蘭人的軍靴與綠色制服上凝結成塊。
他們再一次扣下扳機。此時,壕溝開始傳出呻吟。「媽的,有人還沒死。」一級小隊長沒好氣地說。「能怎麼辦,把他們收拾掉啊。」納格爾大聲咆哮。一級小隊長命令兩名阿斯卡里上前朝壕溝裡面開火。哀嚎並未因此終止,他們發射了第三發子彈,幾個人就在他們旁邊清理溝沿。然後,又從更遠一點的地方拉來十個猶太人。「納格爾。」我說。「幹嘛?」他的臉色比死人還難看,手槍掛在手上「我到車上等。」樹林裡又傳來幾聲槍響,是綠衣警察朝意圖逃跑的人開槍。壕溝旁,一名猶太人開始啜泣。
***
類似的生澀很快便成為絕響。幾個禮拜下來,行動指揮官累積了相當的經驗,士兵們也熟悉了行刑的程序,在此同時,每個人似乎都在思索自己在其中的定位,以自己的方式自問這是怎麼一回事。
晚上吃飯的時候,大夥的話題總繞著這些行動轉,互相比較自身的經歷,有些人語帶傷感,有些則談笑風生。還有些人悶著不說話,這是特別需要留心的一群,因為至今已經發生了兩起自殺案例。
還有一天夜裡,一個人突然驚醒,拿著槍狂掃天花板,我們只好用強的,從後面將他攔腰抱住,一名下級軍官差點因此送命。有些人表現得特別粗暴,有時是出於虐待的病態心理,會毆打人犯,行刑前百般凌虐。上面想盡辦法控制此類脫序行為,但是困難重重,失控的情況時有所聞。
我軍的士兵經常將行刑的過程拍攝下來,拿這些照片到總部交換菸草,他們把照片掛在牆上,只要出錢,要加洗多少就有多少。我們很清楚很多人怕受到軍法懲罰,所以把照片寄回德國老家,有些人甚至做成攝影小集錦,圖文並茂。這個現象著實令軍事高層擔憂不已,他們似乎也苦無對策,在地的軍官則多半睜隻眼閉隻眼。至於我,我手上是司湯達爾的書信集。
我靜靜思索。我想到自己的人生,我走過的人生歷程──一段極其平凡的人生,無論是誰都可能有的人生,但從某些角度來看,卻又是那麼不尋常,超乎想像。而儘管超乎想像,我的人生在本質上還是極其平凡──這樣的人生和這裡發生的一切有何關聯?一定有某種關聯存在,這一點無庸置疑。
的確,我沒有親身參與槍決,也不是我下令開槍,但這不是重點,因為我經常參與這種行動,也協助事前的準備工作,還有事後的報告撰寫。再說,我會被調到行動參謀部,而不是到各分區行動支隊,完全是上天偶然的安排。如果上面交付我領導分區行動支隊,我很可能也會跟納格爾和哈福納一樣,籌畫肅清行動、挖壕溝、叫犯人排成一列,然後高喊「開火!」嗎?答案是肯定的,毫無疑問。
至於另一些人,且不管他們是真心厭惡這種事,還是完全無所謂,總之,他們基於義務和職責所在,認真完成任務,然後從對國家忠心耿耿、抑制個人好惡的堅強自制力及任務艱難等理由,找到成就感,敦促自己益發努力完成交託的使命。「可是,殺人能得到什麼成就感?」他們常常這麼捫心自問,事實上,他們在自律的美德和負責任的態度當中找到了成就感。
遇到婦女,尤其是小孩時,我們的行動會變得出奇艱難,十足噁心的差事。大夥的抱怨沒有斷過,特別是年紀較長有家室的人。面對這些毫無反抗能力的一群人,母親眼睜睜看著孩子被殺,卻無能為力,只能跟著他們同赴黃泉。我們的人有一種深深的無力感,覺得自己跟那些人同樣無力。
「我只想保有完整的自我。」有一天,一名黨衛軍一等兵這麼跟我說,他的心情我很瞭解,但我幫不上忙。
就這樣,集中營的人犯一群一群被帶走,每天少一點。就在新年的前夕,正好輪到我監督行刑。槍擊手都是警察第三一四營的菜鳥,他們自告奮勇,卻毫無經驗常射不準,受傷沒死的人很多。在場的軍官大聲斥責,叫人拿酒給他們壯膽,他們的效率依舊不彰。
鮮血飛濺雪白大地,流入溪谷深處,在冰凍堅硬的地上堆積成一個個小血坑,鮮血不會結凍,只是停止流動,變成黏稠的一團。四周枯死的向日葵,灰黑的莖幹還直挺挺地插在雪地上。所有的聲音,就連哀嚎和槍響都像是包了一層布似的低悶,堆積的雪塊腳一踩就茲喀作響。
我必須特別說明,儘管沒有人要求,我還是按照規定,不時親赴刑場監督行動的執行情況。這是我自己要去的。我沒有開槍,我觀察開槍的那些人,尤其是哈福納和詹森,他們倆打從行動一開始就一直在那裡,現在他們對劊子手的工作已經完全無動於衷。
我應該要像他們一樣,逼迫自己直視這些悲慘畫面,我隱約覺得這樣的自我折磨,為的不是想磨滅它的醜惡,剔除這種蓄意滅絕人性中善與美的獸行所衍生的罪惡感,反倒是罪惡感自己慢慢消退,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場面,隨著時間的流逝,感覺變得麻木。
因此,我亟欲尋回卻遍尋不著的那種感覺,原來是行動一開始時我內心的震撼,那種撕裂的感受,整個人彷彿散掉似的五雷轟頂;相反地,現在的我只有隱約的焦慮、煩悶,症狀愈來愈短促,愈來愈加劇,常被誤以為是發燒,或者其他生理上的不適毛病。於是我慢慢在毫不自知的情況下,拚命尋找一線光芒,殊不知我已經身陷泥淖,而且愈陷愈深。
一件小意外讓我看清內心那道日益擴大的裂縫。白雪覆蓋的大公園裡,士兵強押一名年輕的農家女,往契夫成科雕像後面的絞刑架走,旁邊有一群德國人圍觀,除了國防軍的步兵、綠衣警察之外,還有陶德組織的成員、東部佔領區指揮部的那群金雉雞(Goldfasanen)和空軍飛官。
女孩相當瘦,神色驚慌幾近歇斯底里,濃密的黑髮剪得短短的,像是用推子三兩下推出來的。一名軍官綁住她的雙手,拖她到絞刑架下方套上環結,圍觀的士兵一個一個走上前,親吻她的嘴唇。她瞪大了眼睛,說不出話來。有人溫柔印上一吻,畢恭畢敬像個小學生;有的雙手用力的抓住女孩的頭,粗暴地強吻。
輪到我的時候,她望著我,清澈明亮的雙眸澄明無垢,我明白她什麼都知道,什麼都懂,她是如此單純洞悉了一切,我站在她面前,內心頓時燃起熊熊烈焰。我的衣服嗶波作響,腹部肌膚撕裂,脂肪嘶嘶燃燒,火焰肆虐我的眼睛、嘴巴,將腦袋裡的東西吞噬殆盡。
我的吻如此強烈,她被迫別過頭。內心的熊熊火焰把我燒得焦黑,呆立原地的只是殘存的骨骸,這場火來得急去得快,溫度開始下降,我的驅體一塊塊剝落,先是一邊的肩膀,然後是一隻手,再來是半邊臉,最後整個身軀崩塌倒在她腳下,一陣風捲起殘破軀體,飛散各地。
此時,下一名軍官已經上前,等每個人都輪過了之後,我們吊死了她。
好幾天來我一直回想著這詭異的畫面,我自己的影像出現在我面前,好像鏡中反影,永遠只有我自己的影像,這影像當然是左右相反的,卻忠忠實實地反映出我這個人。
那個女孩的身體就是一面鏡子。不知是繩索斷了還是有人割斷,女孩的屍體躺在工聯公園的雪地上,頸骨斷裂,雙唇腫脹,露出半邊被野狗啃去了大半的乳房,參差不齊的頭髮恍如謬思女神的花冠,我覺得她美得出奇,死神在她身上搖身一變成為眾人膜拜的神祇,白雪聖母。
我走回飯店,回到辦公室,無論我走哪一條路,路上都是她橫躺地面的身影,彷彿一個頑固的、獨斷的大問號,將我推進無謂猜測的迷宮,我迷失了自己。剎那間,所有往事的重擔、生命的痛苦和永遠無法磨滅的記憶一股腦兒全湧上心頭。我心下悲涼,說不上是為了什麼緣故。然後,我一個人,在那裡,跟滿地的屍體;我一個人,繼續承受歲月、哀傷和過往的痛苦,繼續承受生命的殘酷,面對進逼的死神。善心女神終於找到我了……
四海兄弟們,讓我告訴您,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老實說,這段歷史滿悲慘的,但教育意義深遠,可說是不折不扣的寓言故事。過了這麼多年之後,我下定決心把這些寫出來,真正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釐清一切。
我經歷的往事數量驚人。我像一座往事的製造工廠。我一輩子都在製造往事,就算現在,雖然老闆付我薪水製造的是蕾絲花邊,往事的生產仍未中輟。
當戰後一切結束時,我成功來到法國,當個法國人;這其實沒有那麼難,因為當時社會動盪,我跟著一些被囚禁在集中營裡的囚犯回到法國,當局沒問太多的問題。我說得一口流利的法語,因為我母親...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0收藏
10收藏

 7二手徵求有驚喜
7二手徵求有驚喜



 10收藏
10收藏

 7二手徵求有驚喜
7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