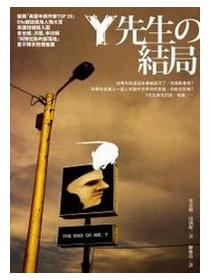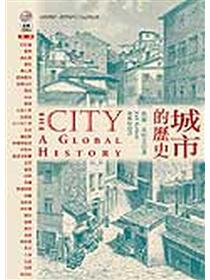【內容簡介】 這是一場不容改變勝負結果的詛咒遊戲。 縱使一切任憑自己做主,人類終究還是擺脫不了命運和無常的操弄。 打從有記憶以來,機運就一直左右著馬帝.史特勞斯的人生。 現在,好運總算站到了他這一邊。 他接下約瑟夫.懷特海德的保鑣工作而獲得從監獄假釋出來的機會。 懷特海德是全歐洲最富有的人,他也在玩弄「機運」這個古老的遊戲,因而取得龐大的權力和財富。 而他所付出的代價,就是他那不朽的靈魂。 現在,與他玩這場遊戲的那股可怕力量又回來了。 它將要索討它應得的回報,在這個虛假的城市裡來去
章節試閱
第一部 殊方絕域
「地獄是那些否認者的落腳處;
他們在那兒找到過去曾栽種和挖掘的,
空蕪的湖泊和虛渺的樹林,
他們踟躕漂泊於其間,永無止息地
為俗事而悲懷。」
──葉慈 ,《沙漏》
一、
偷兒路過的那一天,城裡的氣氛異常凝重;在經過這麼多禮拜一無所獲之後,他確信今晚自己必將能找到那一位賭牌的玩家。這一趟行程可不輕鬆。華沙城裡百分之八十五的建築都被夷平,就算能避開蘇聯在解放這個城市前以迫擊砲連續數個月的砲轟,也難逃納粹在撤退前計劃性的毀滅行動。好幾個區域路況坎坷,幾乎是寸步難行。堆積如山的瓦礫石塊就橫亙在馬路正中央。纍纍的廢墟像是在呵護著埋葬在裡面的死者,就像蟄伏在土壤中的球莖,一等到溫暖的春天到來就要復甦發芽一般。即使是交通較為便利的區域,曾經風光一時的建築物從外觀看來也搖搖欲墜,地基彷彿旦夕間就要毀壞。
然而經過三個月的苦心經營,偷兒也逐漸習慣在此荒涼的市區中穿梭往返。他甚至對這昔時輝煌的荒涼景象感到興致勃勃:依然滿天飄散的飛塵讓這城市染上霧濛濛的背景,還有靜得不尋常的廣場和林蔭大道;打擾此間,他只覺得,如果有所謂的世界末日,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白天時甚至還能找到過去提供旅人規劃行程的地標,儘管這些遺世而孤立的指示牌終將難逃被拆除的命運。鄰近波尼亞托夫斯基橋 的瓦斯公司的遺址依稀可見,河 的對岸也還能找到動物園的頹垣殘瓦;中央車站的鐘樓頂端依然聳立著,但鐘的部分早已佚失;這些斑駁的史蹟在在見證了華沙的城市風華,如此岌岌可危地倖存下來,即便是一個匪類也不免為之動容。
此處並非他的家。他沒有家,而且十數年如一日。他四處漂泊拾荒,而華沙提供了他短期間內繼續留在此地的甜頭。再過不久,等他將近來流浪所消耗的能量補充完足之後,就是他再上路的時候。至於此刻,空氣中依然瀰漫著初春乍到的呢喃絮語,他要把握在此遊盪的時光,享受這城市的自由氣氛。
當然,風險也是免不了的,但是對於像他從事這一行的人來說,又有哪裡算得上安全呢?連年的烽火也讓他練就出一身自衛的功夫,鮮有何事能讓他畏怯。他甚至比那些真正的華沙市民還要來得安全。少數大屠殺的倖存者紛紛返回城裡,尋找他們失去的家園及死去的親人。他們在廢墟之中又扒又挖,或是站在街角聆聽河川悲鳴的輓歌,然後等待蘇聯軍隊能以馬克思 之名與他們會合 。新的路障日復一日地被豎立起來。軍方的速度十分緩慢,但卻有系統地從混亂的局勢中試圖重建起秩序,先是將城裡細分再細分,希望有一天能推展至整個國家。不過,不論是宵禁還是檢查哨都不能有效地嚇阻偷兒。剪裁精良的外套襯底裡藏有各式的身份證件──有些是偽造的,多半則是偷來的──不論遇上何種狀況,他總是能找到合適的文件。受到質疑刁難的時候,就要靠他的機靈應答和隨身攜帶的香菸來補足,這兩樣他都不虞匱乏。任何人只要具備了這幾樣東西──在那個城市,那樣的年代──就可以感覺到自己具有呼風喚雨的本領。
而且是好一個滿城的風雨!這裡可不會有誰的胃口或是好奇心得不到滿足。量身訂做各式的遊戲,呈現出肉體及心靈上最深層的秘密,以饗你窺視的慾望。才幾個禮拜前偷兒就聽說過一個年輕男子的故事,那個男子表演一種古老的杯子和球的遊戲(一下子看得到球,一下子球又不見了的那種遊戲),只不過荒唐的是,他居然是用三個水桶和一顆嬰兒的腦袋來玩這個遊戲。
這還不是最不可思議的部份;至少嬰兒已經死了,而死人並不會受苦。城裡多的是其他任人差遣的娛樂,而且是拿活人當製造樂趣的材料。為了滿足那些付得起價碼的客戶,市面上開始出現活絡的人肉交易。不再受到戰事困擾的佔領軍再度介入性交易,並且從中撈了一大筆利潤。半條麵包就能買到一個流亡的女孩──而且多半是連胸部也沒有的青澀年紀──在不見天日的暗處一再遭到蹂躪,沒有人聽到她們的控訴,直到失去最後那一丁點的吸引力時,一把刺刀就讓她們從此噤聲。在這麼一個死亡人口數以萬計的城市裡,誰又會在意如此漫不經心就被奪走的一條人命?才不過幾個禮拜──政權輪替之間──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無所謂有罪的行為,更無所謂邪惡的禁忌。
佐里波茨區 開了一家男妓院。而這裡也開了一家地下沙龍,用逃過戰火洗禮的畫作為裝飾,六歲或七歲以上的小孩任君挑選,營養不良的瘦弱身軀惹人憐愛,緊實的肌肉更是行家的首選。這在軍官階級深獲好評──但對於其他士兵來說就太貴了,偷兒就聽過這樣的抱怨。列寧的平等教條在男色關係裡似乎並不適用。
諸如體育競技活動這一類的娛樂則較為平易近人。鬥犬尤其是當季最熱門的賣點。四處遊蕩的野狗在回到城裡來撿食主子的肉塊時,遭到陷阱捕捉,被餵食到體力充足時,就送上場讓牠們互鬥到斷氣為止。場面十分駭人,但是賭癮的魅力讓偷兒一再光顧此地。有一晚讓他狠狠賺了一手,他把錢全壓在一頭矮小但身手矯捷的獵犬上,這隻小狗居然打敗大牠三倍的對手,還一口將對方的睪丸給咬掉。
如果假以時日,你對鬥狗或是男孩或是女人的新鮮感開始消退,還有更多不為人知的娛樂。
一處原本是聖母瑪莉亞聖殿的遺址,被挖成一座簡陋的圓形露天劇場,一位不知名的演員單槍匹馬地演出哥德的《浮士德》 ,包括第一部和第二部。雖然偷兒的德文不怎麼精光,但是台上精湛的演出還是讓他印象深刻。他對故事十分熟悉,讓他不費力地就能跟上演出的劇情──與墨菲斯托的盟約 、幾場辯論、施展魔法,然後當約定好下地獄的詛咒降臨時,主角內心的絕望和驚骸。其中許多情節艱澀難懂,但是該名演員沉著自若地分飾兩角──時而演出誘惑者,時而擔綱被誘惑者──出神入化的演出讓偷兒也不禁心潮澎湃。
兩天之後,他又忍不住想要再回去觀看那部劇,或者至少能和那一位演員聊一聊。到那兒才發現幕已落。原來演出者對哥德的熱情被詮釋為幫納粹搞宣傳;只見他一身赤裸地被吊在電線桿上,裸露的雙足和眼睛均已慘遭鳥兒啄食;軀幹上則佈滿子彈痕跡。這一幕反而讓偷兒寬慰不少。他認為這正足以證明,這位惹得他內心如此騷動的演員的確是邪惡的;如果這正是他的藝術的目的,那麼他顯然不是無賴就是個騙子。他的嘴巴依然半敞,不過鳥兒早已奪去他的舌頭和眼睛。所以也沒什麼損失。
此外,還有回報更多的娛樂足以讓他忘了這一切。對偷兒來說,女人可有可無,男孩不合他的胃口,但是賭博則是他數十年如一日的最愛。所以,他又回去鬥狗場,選了一隻雜種狗來試試自己的手氣。試不成,他還可以到某個營區去擲骰子,或是──在迫不得已的時候──找個窮極無聊的哨兵來打賭,隨便一朵浮雲流逝的速度都可以拿來打賭。賭的方式和背景其實並不重要:他只關心能不能賭博。這是他從小就養成的唯一惡習;正因為沉溺在賭博之中,才逼得他不得不當個偷兒來資助這個無法自拔的惡習。戰前他玩遍歐洲的賭場,他的註冊商標就是鐵道牌 ,不過他也不排斥賭輪盤。現在經過這一遭戰亂,他再回頭看,那些賭賽就像是黃梁一夢:不復可得,並且稍縱即逝。
那種失落感總算有了轉變,他聽說了那一位賭牌的玩家──馬默連恩,他們是這麼稱呼他的──據說這個人從未輸過任何一場賭局,並且就好像根本不是真實存在一樣,在這個虛假的城市裡來去自如。
只是,在馬默連恩出現之後,一切都改觀了。
二、
此地的謠言甚囂塵上,更糟糕的是當中連一點真實的根據也沒有。純粹就是窮極無聊的士兵所誑捏的虛詞。偷兒太清楚了,這些人雖然身在軍中,但是他們荒誕新奇的想像力卻可比擬巴洛克詩人,其一針見血的功力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當偷兒聽說這位大師級賭牌行家的一點一滴,說他出身神秘,挑戰天下賭徒而無敵手,偷兒就起了疑心,故事畢竟就只是故事。令人詫異的是這則作者不詳的故事卻一直維持著同樣的說辭,並沒有被加油添醋得更加滑稽荒誕。同樣的情節一再地被傳誦──鬥狗場玩家們的口耳相傳,巷議街談之間的八卦,塗鴉創作的主題。尤有甚者,儘管名字或有不同,但不論哪一個版本,情節全屬雷同。偷兒不免開始懷疑,搞不好這故事還有那麼一丁點的真實性。也許真的有某個技藝高超的賭徒在城裡找人開刀。當然,不可能是真的天下無敵,沒有人是不敗的。但是,如果真的有這麼一個人存在的話,他鐵定是一個很特別的人。人們在提到他的時候總是像出於尊敬一樣地帶著謹慎的口吻;那些聲稱見過他玩牌的士兵們提到他的優雅,還有他彷彿入定般地冷靜。他們在提到馬默連恩時,就好像鄉巴佬在提到王公貴族一樣,而偷兒──原本就從來不肯承認任何人比他優越──他一心想要摘除此人王冠的不服氣心態,更讓他急著想要把這個玩牌人給找出來。
除了從消息來源獲得初步的印象之外,他還聽到了一些小道消息。他決定自己第一步就要先找到一位確實在牌桌上遭逢過這位奇葩的人來問一問,才能在眾口紛紛的臆測之詞當中篩選出真相來。
光是要找到這樣的人選就花了他兩個禮拜的時間。這個人叫做:康斯坦丁.瓦西里耶夫,據說這位少尉在與馬默連恩交手之後,就在賭桌上輸光了所有的家產。這個俄國人像頭牛一樣剽悍,站在他旁邊的偷兒登時矮了一大截。有些大個子會讓人感受到跟身形一樣剽悍的氣魄,這個瓦西里耶夫卻像是個紙老虎一樣空有龐大的身軀。就算他曾經擁有過任何的活力,如今也蕩然無存。在這個軀殼裡面的是一個軟弱不安的小孩。
經過一個鐘頭的哄騙誘拐,一瓶黑市的伏特加附近半條香菸,終於讓瓦西里耶夫的答話不再只是支支吾吾的單音節,只是當他決定要吐露實情時,卻是傾瀉如注,這個男人告白起來就像是處於完全崩潰的邊緣。他的言談之中不乏自憐以及憤怒;更多的是強烈的驚懼之情。瓦西里耶夫宛如驚弓之鳥。這讓偷兒印象深刻:不是他的淚水,也不是他那副窮途末路的德行,而是馬默連恩這個身份不明的賭牌玩家居然能將坐在他對家的這個巨人徹底擊潰。他極盡地安慰示好,希望能進一步從俄國人口中套出所有的細節,好讓他能一點一滴拼湊出他正在調查的這一頭神獸蓋美拉 的原貌。
「你是說他從沒輸過?」
「一次也沒有。」
「那他用了什麼手法嗎?怎麼作弊的?」
原本一直盯著光禿禿的地板沉思的瓦西里耶夫突然抬起頭來。
「作弊?」他用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反問著。「他才不會作弊。我玩牌玩了一輩子,什麼人都見過,什麼把戲也都看過。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這個人絕對是清白的。」
「就算是最走運的玩家偶爾也會落敗。所謂運氣的法則就是──」
瓦西里耶夫臉上閃過一個饒富玩味的純真表情,那一瞬間偷兒彷彿瞥見原本藏在這個巨大身軀裡的那個還沒失去理智的那個人。
「你難道還不明白嗎?所謂運氣的法則完全不適用在他身上。他可不是像你我這樣的凡人。一個總是贏牌的人必定是對賭牌有某種特殊的能力!」
「你真的相信這一套?」
瓦西里耶夫聳聳肩,又彷彿洩了氣一般。「對他而言,」他說,若有所思的口氣像是徹底陷入沮喪,「贏牌是一種美,就像生命本身一樣。」
瓦西里耶夫空洞的眼神又回到地板上粗糙的紋理,留下這一番話還在偷兒的腦海中激盪不已:「贏牌是一種美,就像生命本身一樣。」這番話還真是詭異,偷兒愈是玩味愈是心慌。他還在推敲這番話的含義時,瓦西里耶夫兀自湊了上來,一陣恐懼的氣息襲來,一隻大手拎住偷兒的袖口。
「我已經申請移防,你聽說了沒?再過幾天我就要離開了,沒有人能比我更聰明。我回國後,就等著被頒發勳章。這就是他們要把我調走的原因:因為我是英雄,英雄要申請什麼都能成功。到時候我就走人了,他再也找不到我。」
「他為什麼要找你?」
拎住袖口的那隻手頓時扼緊;瓦西里耶夫把偷兒扯了過來。「我欠了他一屁股的債,」他說。「我要是留下來,他非要我賠上這一條命不可。他也殺過其他人,他跟他那一夥人都是這樣。」
「他不是一個人?」偷兒問道。他一直是把那個玩家想像成一個獨行俠;事實上,他是把那個玩家想像成自己的模樣。
瓦西里耶夫對著手心用力一擤,然後往後靠在椅背上。龐大的身軀壓得椅子嘰嘎作響。
「在這種地方,是真是假又有誰知道?」他說著,突然就眼淚盈眶。「我是說,如果我告訴你說他身邊簇擁著一群死人,你會相信嗎?」他自我解嘲地搖搖頭。「不,你會認為是我頭殼壞了……」
偷兒心想,這個人曾經是呼風喚雨、驍勇善戰、甚至可說是不可一世的英雄。現在,過去那些光環早已褪去:這位冠軍淪落為哭哭啼啼的窩囊廢,滿口盡是胡言亂語。他向來就最討厭所謂的英雄,現在更忍不住為這位馬默連恩如此精采的傑作而暗自喝釆。
「最後一個問題──」他又提了個頭。
「你想知道要去哪裡才能找到他。」
「對。」
俄國人緊盯著自己的拇指根部,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彷彿對這一切不勝厭煩。
「就算你能跟他對賭,你又有什麼好處?」他問道,隨即又自顧自地提出解答。「不過是自取其辱罷了。甚至可能是自找死路。」
偷兒站了起來。「那麼你就是不知道他在哪裡囉?」他問,一邊伸出手來,眼看就要將放在兩個人之間桌上的那半包煙放進口袋。
「等一下。」趁那半包煙還沒從眼前消逝,瓦西里耶夫探出手來。「等一下。」
偷兒又把香菸放回桌上,瓦西里耶夫將手壓在煙盒上,準備佔為己有的樣子。他抬頭直視著緊迫盯人的偷兒。
「我最後一次聽到他的消息時,據說他在北邊城裡,莫蘭諾斯基廣場那邊。你知道那個地方吧?」
偷兒點點頭。那不是讓他流連忘返的區域,不過他知道怎麼去。「等我到了那邊,我怎麼知道哪個是他?」他問道。
俄國人彷彿覺得這是個匪夷所思的問題。
「我不曉得他長什麼樣子,」偷兒進一步解釋,試著讓瓦西里耶夫瞭解。
「不勞你去找他,」瓦西里耶夫回答,對這一切他瞭然於心。「如果他想要跟你玩,他自然會找上你。」
第一部 殊方絕域「地獄是那些否認者的落腳處;他們在那兒找到過去曾栽種和挖掘的,空蕪的湖泊和虛渺的樹林,他們踟躕漂泊於其間,永無止息地為俗事而悲懷。」──葉慈 ,《沙漏》一、偷兒路過的那一天,城裡的氣氛異常凝重;在經過這麼多禮拜一無所獲之後,他確信今晚自己必將能找到那一位賭牌的玩家。這一趟行程可不輕鬆。華沙城裡百分之八十五的建築都被夷平,就算能避開蘇聯在解放這個城市前以迫擊砲連續數個月的砲轟,也難逃納粹在撤退前計劃性的毀滅行動。好幾個區域路況坎坷,幾乎是寸步難行。堆積如山的瓦礫石塊就橫亙在馬路正中央...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收藏
1收藏

 5二手徵求有驚喜
5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