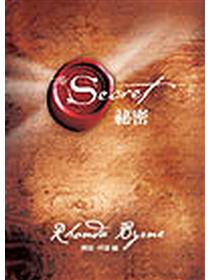第三章 每個人的祕密生活
「說謊的鏡子
說謊的鏡子
這怎麼可能是我喬裝成猩猩的樣子」
─—史提夫.古德曼(Steve Goodman),
《這間飯店房間》(#This Hotel Room#)的片尾曲歌詞,一九七五
我的病人史考特是一名軟體顧問,他的工作讓他得常常在路上奔波。儘管他太太麗莎不是很喜歡他這樣常常不在家,但他其實並不介意。他們的兒子都還很小,每當史考特出遠門時,責任就落在麗莎身上,她得處理大大小小的事情。透過電話,她會告訴史考特他今天錯過了什麼事情,而他則會低聲地講著他忙的事情以及掛心的事。但事實上,他在很多方面都覺得自己很疏遠。從他所待的酒店,無論是四季或是希爾頓,從它們的密封窗戶眺望所看到的某個城市的燈光,都沒有他家的燈光。在晚上,所有的燈光看起來都一樣。他太太的聲音在他的耳邊聽起來很小,而她所說的話似乎有些平淡無奇。他聽到「孩子」、「科學報告」、「一起搭一部車」,然後他便進入了放空的狀態,在飯店的特大雙人床上伸展身體並把眼睛閉上,他的思緒就像藤蔓一樣向外捲曲,漸漸地遠離她、他們的兒子、家,以及所有熟悉的事物。但他自由的思緒其實也沒什麼地方好去。他並不是一個特別有想像力或很會視覺化的人,他覺得自己有點模糊空白且呆滯,跟他的床上方那幅掛在牆上有框的海景圖片沒有什麼兩樣。
一天晚上,大約十點左右,他發覺自己一點也不想睡覺。在房內用晚餐是那晚最有意思的事,只是那已是幾個小時前的事了,現在餐車已經被推出房間,而隨之而去的,是可以報帳的上等肋排及烤馬鈴薯所帶來的片刻滿足。他從酒櫃裡倒出來的威士忌,只讓他有點微醺的感覺而已。現在並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他很不喜歡這種感覺。
史考特瀏覽了一下電視上的頻道,短暫地考慮要花錢玩任天堂遊戲後,便打消念頭。如果他的孩子看到他手上拿著搖桿,他們便會說他是個偽君子,因為一直以來他都會叫他們把電動玩具關掉去看書。只是他們幾乎都沒有心情看,而他也是,至少現在就是如此。他讓CNN小聲地播了一會兒(報的是有關西南部乾旱的災情),然後他看了一下ESPN,播的是他沒有興趣看的大學籃球賽的賽事集錦,最後,他便轉到付費電影選單。
「成人電影,」一個選項這麼寫著。他曾在許多的飯店房間裡看過,但這一次卻很不一樣地吸引到他的目光。「有何不可?」他想:「反正也不會怎樣。」因此,在不到半分鐘的時間,他便開始看著一支有兩個豐滿、金髮、農家女孩型的女人在草棚裡做愛的影片。她們的呻吟聲既虛假又狂放,但這都不重要;他已經著迷了。他是個男人,他提醒自己反正男人就是喜歡這種東西,因此,他此刻便完全地放縱自己,讓影本中誇張的劇情及造作的女同性戀行為,呈現在飯店房裡一位無聊的四十歲丈夫和父親的眼前。
史考特突然不覺得無聊了。遙控器從他的手上掉到床上。他的嘴巴微張,很像一隻想要到水面上呼吸的魚,他奮力解開麗莎在他生日時買給他的腰帶,發現自己已完全沈迷於他面前這支離家有三千英哩遠的電視螢幕上所播的色情影片。他這輩子看了很多色情影片,但不知怎麼地,從青春期以來,他就沒有感到這麼興奮,也沒看過蘇珊.卡希爾(Susan Cahill)在她位於市郊的房子裡的休憩室內裸露酥胸的樣子。
影片結束時,在迅速且滿足地在心裡叫了一聲,並與螢幕上的農家女孩所假裝的高潮幾乎同時達到了高潮後,史考特馬上就睡著了。他早上醒來時覺得精力充沛且異常地愉快,好像這次出差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在他身上似的,但他知道他不可以跟他太太說這件事。難道他得說:「嗨,麗莎,你猜怎麼著,我昨晚看情色電影時真是爽歪了,現在我知道以後出門該怎樣娛樂自己了。」
不會的,他是不會告訴她的;這倒不是因為她會很介意。大部份的女性都能接受男人的大腦不太一樣,且大部份比較會對視覺刺激產生反應的事實。這是他最近在雜誌上讀到的。而且就在下一次他發現自己又在飯店房間過夜時,他就很快地提醒自己這個事實。很快地,每次出差時,看情色電影成了史考特沈迷的一個習慣。事實上,這已不止是個習慣了。白天的時候,在討論軟體時、在會議室用PowerPoint做簡報時,他會發現自己很期待一個人的夜晚─—那些一直到最近之前都覺得很孤單的夜晚。即便他回到家,跟孩子玩或幫麗莎做晚飯時,他都會發現自己想著下次的出差以及他新的例行習慣。現在他只要一走進飯店房間,他便會查看電影的選項,然後依照這些選項計劃他晚上要做的事。他會在吃了晚餐後,從酒櫃拿點酒喝,讓自己進入放鬆的狀態,然後觀賞《里約辣妹》(Hot Girls of Rio)或《衣服溼透的夜晚》(Nights in Wet Satin),或任何可供選擇的影片。
你浮報費用;你說同事的壞話;你討厭你媽媽;你不小心打包帶走飯店的毛巾;你對摯友的小孩幼稚園的戲劇演出假裝很有興趣;你申請的稅務減免可能合法……也可能違法;你覬覦一件衣服、耍手段當上畢業舞會女王、接受奧林匹克賽前訓練時服用類固醇。你打開色情頻道,而且以後還是屢次地打開來看。
重點是,你會做些事,我們也會做這些事,大家都會做這些事。
當然不會是上述的所有事情;因為實在難以想像你們之中,每個讀這本書的人,都是會覬覦鄰居穿的衣服、對幼稚園老師撒謊且會欺騙別人的奧運選手。但事實上,我們每個人的確都會隱瞞祕密,而且我們每一個人每天都會這麼做。
當然,有祕密是很健康的。保守某些祕密是有必要的。保守祕密可以讓我們建立內心的自我──即我們在兒時早期就發展出來,且會一輩子放在我們心裡的身份認同。我們所保守的祕密,最後也會成為共享的自我(shared self)的基本核心─—即我們希望和夥伴一起建立的成人身份。在我們的一生當中,祕密會提供一個建立友誼、商業夥伴關係、以及社群的基礎。
然而,就算保守祕密不會改變人的一生,它仍然有其實用的目的。在幼稚園「灰故娘」中扮演主角的朋友的孩子,會希望人家讚美一番,而不希望一個首場演出的評論家赤裸裸的實話。經理的太太發現他的新祕書很「辣」,大概就不會想聽到這個潔西卡.辛普森(Jessica Simpson)的接班人今天進了他的辦公室。如果史考特與色情頻道之間算是一種「一夜情」的話,他應該就沒有理由去承認他的「不貞」,而他太太應該也會同意這一點。
這類的祕密是無害的。它們不會傷害到任何人,而且事實上,它們也許可以避免他人的感受受到影響,或讓保守祕密的人對自己覺得好過一點。它們也許有完全合理的目的。
然而,灰暗的顏色有可能會很快地佈滿整幅畫作。覺得自己的新祕書很辣的經理,即便是在和太太正在做愛的時候,也許會發覺他的心思遊移到祕書的身上。從心理學的觀念看來,這樣的思緒沒有道不道德的問題;它們不過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幻想並非行為,是無害的。它們是有益的。而且,如果保守祕密的人能正視祕密的存在而不去否認它,那麼祕密往往就會持續地有益。同理,如果保守祕密的人不認為祕密可以真正地解決問題─—如婚姻不美滿、中年危機等,祕密就會是有益的。
但要是這名經理約祕書出去喝咖啡呢?要是他就是碰巧沒有告訴太太有關這個秘密約會的事呢?要是他向祕書透露他沒有和太太分享的私事呢?如果祕密沒有被理解為一個不需要處理的幻想、保守祕密的人沒有正視它的本質、而且該項祕密正在解決保守祕密的人心中的一個問題或衝突的話,那麼祕密便會擴散。這類的祕密,我們可以說是有害的。
有害的祕密是怎麼來的?一個著手找起的好地方便是七原罪:驕傲、嫉妒、憤怒、貪婪、懶惰、貪食、淫邪。西元六世紀的教宗貴格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認定它們有「扼殺」永生的可能。除了其宗教上的意涵外,這七項罪狀存於西方文化已有一千五百年之久,因為它們象徵著心中可能是最普遍且最引起共鳴的誘惑。但重要的是,我們得在此指出,每個人都會而且一定會想到或感覺到這些衝動。(所有認為自己不會想到或感覺到這些衝動的人,有可能極端地壓抑且可能充滿著罪惡感。)由此看來,這些想法及感受根本就沒有什麼好「罪惡的」。只要了解到你會想到且感覺到這些衝動,並且能在心中與這些想法和感受對抗,你就可以避免做出可能會對不起自己或別人的事。
儘管如此,有害的祕密只有可能會散播,它們並不一定會轉移。只有把手伸進充當小費箱用的大咖啡杯一次的星巴克店員,和她經常讓一週利潤的5%就像很多卡布奇諾咖啡的泡沫一樣憑空消失的店經理之間,是有很大不同的。同樣的,旅客帶走飯店的毛巾是很常見的事。但他們卻比不上經常在世界各地跑的人,他們的廁所裡堆滿了從世界各地掠奪來的戰利品:毛巾,這是一定有的;而且還有拖鞋、指甲剪、像試管般大小的洗髮精樣品、氣氛音樂CD、白噪音時鐘、四人份咖啡機、一整個衣櫃的衣架(木製的!)。
祕密和祕密生活之間的差異就在於程度上的不同。這項差異可能無法嚴謹地把它量化。史考特需要幾個把色情電影費用刷到個人信用卡上的夜晚,才能正式地說他在過一種祕密生活?你不能只是給一個數字。然而,如同最高法院對色情場所下的一個典型定義一樣,你看到時就應會知道這是色情─—這也就是為什麼史考特要確定沒有人看到,包括他自己在內。和多數人一樣,史考特往往看到自己美好的一面,而他也會比較希望這個世界也用同樣有利於他的眼光看他。
依心理學的術語來看,這種人在心中所保有的幾分完美的一面,被稱為自我(ego)。史考特希望他的家人和朋友把他當成一個有道德感、穩定、有趣、忠誠且性生活協調的人。他不希望他們瞥見一個疲倦的先生和父親躺在明尼亞波里士市(Minneapolis)鬧區飯店八樓的一張床上,一邊看著假的女同性戀在草棚裡摔角,一邊自慰。他甚至也不希望不認識他的人看到他這樣。每當他辦理退房,飯店人員給他帳單列表時,史考特就會感覺到一股難為情的感受從漿得半挺的衣領往上竄。當然,電影的片名絕不會出現在這樣的帳單上;這項費用只會以「室內電影」這類的名目列出。但對史考特而言,他的帳單卻也可能註明「供中年商人自慰用的色情電影」。所以,史考特大致上比較偏好辦理快速退房所帶來的方便。
此外,這畢竟不是真正的他。要是家人、朋友、同事、陌生人了解真正的史考特,這不可能會是他們所會想到的他的形象。更何況,這根本不是真的很正確,他這樣告訴自己。和大部份持有害祕密的人一樣,史考特比較不希望承認他躺在床上很興奮的樣子,或在飯店大廳遮遮掩掩的樣子就是真正的他。他有他的理由:他覺得很無聊;每天晚上都得在一個接著一個的普通飯店裡度過,換作任何人都會想去消遣一下;男人的大腦就是這麼運作的,他只不過是太晚發現這項科學的真理而已;但不管怎樣,經過緊張的一天,努力說服一整間中級主管之類的人,最近的軟體調整可以讓公司的營收產生重大的改變之後,誰不會需要放鬆一下?
然而,保守祕密的人永遠都有他們的理由─—他們的合理化行為。在辦公室自行拿走剪刀的員工,或在藥局決定不告訴收銀員他應該找一塊錢而不是十塊錢的顧客,都可能告訴自己,他們這種微不足道的小偷行徑不算什麼。畢竟,他們上班的跨國性企業集團,或他們購物的全國性藥品連鎖店,應該能輕易地吸收這麼微少的損失才對。他們似乎「忘了」這些公司都是人在經營的,這些人不是自行吸收損失,就是把它轉嫁給其他下面會自行吸收損失的人。透過遺忘,這些小偷忽視了他們不誠實的行為,並且維持了有利他們的自我行象。
但他們就是小偷。是的,他們的「取」是微不足道沒錯。但道德嗎?作夢也不會想到要去扒走印表機墨水匣,或把前一位客人不經意留下的一分錢放到口袋裡的人,有可能一時衝動,讓某個地方的某人得損失一些錢。但這些小偷之所以會拿他們所拿的東西,是因為他們能拿─—因為當時儲物間沒有其他人,或是因為收銀員沒有查覺他的不小心。除了他們自己以外,並沒有人在監視他們。他們會拿,是因為東西放在那兒就是給人拿的。所以,他們拿個什麼東西就走。那種感覺讓他們很滿足,因為這滿足了一種原始的衝動。生命是不公平的,但此刻不公平卻讓他們得到了便宜。在越線犯規的當下,小偷(惡意道人是非的人、逃漏稅的人、酒駕的人)不僅僅是有道德感、正當、誠實的公民,他們也許會認為自己就是道德的、正當的、誠實的,而且認為自己應該是對的。他們對於自己的這種印象也許是完全正確的─—或可以說是幾乎完全正確,因為某種程度上,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我們同時也是有侵略性的、沒有道德感的小野獸。









 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