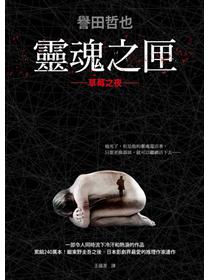向過往的自己說再見。
2001年5月13日,我被宣告罹患癌症。
是的,無法忘記,那是還吹著冷冽寒風的冬末初春時節。
我叫櫻井弘樹,剛滿16歲的高二生。
大家都叫我阿弘。
我有個十分開明的爸爸,和直到現在還深愛著爸爸,純真無邪的媽媽。以及雖然交的都是些不太正經的朋友,卻總是在我最需要的時候,適時伸出援手的姊姊。
還有個心意相通,無可取代的女友。
她叫田原美嘉。
我們上同一所學校,同樣年級,相識於高一剛入學的那年春天,旋即熱戀交往。
這般親密關係轉眼已經快一年了。短短的時間中,兩人經歷了無數事情,擁有各種共同的回憶。
像是一些悲傷的事。我的前女友對美嘉做了非常過份的事。甚至因為無聊的嫉妒,毀了美嘉異性知己的大好前程。
或是一些高興的事。美嘉的肚子裡奇蹟似地有了小生命,雖然不幸流產,小生命去了天國,卻讓我們的感情因為這個回憶變得更緊密。
這一年來,我和美嘉攜手克服了無數次試練,那是散發著甜蜜幸福氣息的愛侶們所無法想像的。
對我們而言,那種悲傷、痛苦是無法估算的。但一路克服過來的種種試練絕對不是白費的,因為我們現在變得更堅強。為什麼呢?因為經歷過如此複雜的回憶,才造就現在的我們。
克服了種種磨難,讓我們的心更貼近,更珍惜彼此。
雖然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不管前方有什麼阻礙,只要我們同心協力就能衝破難關。
這點小事根本無法拆散我們,也許應該說,根本不可能會發生這種事。
所以今後,直到永遠,不管多麼大的阻礙橫亙在我們眼前,只要同心協力便能像以往那般克服。
花了一年構築的羈絆牢實地結合著,不是那種一碰就會毀壞的易碎品,也不像容易崩毀的積木般脆弱。
“結束”這兩個字對我們來說,是那麼地遙遠,也許該用“永遠”這個老套的字眼來形容更適當吧。
我對美嘉的愛意,美嘉對我的愛意,一直都是如此緊密牢實地連繫著。
我們之間的羈絆永遠不會被切斷,如此堅信著。
一直如此堅信著。
明明如此堅信著。
那是升上高二,過了一個月後,五月半的事。
躲過老師嚴厲的目光,偷偷溜出學校的我和美嘉來到河堤,那是對我們而言,最特別的地方。
「今天天氣真好呢!好想睡覺喔~~!!」
我被微熱的風吹得頻頻揉眼,身旁的美嘉也邊輕揉著眼,邊拔著四周細長茂密的雜草。
升上高二後就不同班的我們,總是以見不到彼此為藉口早退,要不就是蹺課,常常像這樣溜到附近的河堤度過只屬於我們的時光。
這河堤是還沒認識美嘉前,放學閒晃途中偶然發現的。
清澄的河水平緩地流著,茂密的草叢中四處可見蒲公英害羞地探出頭來,偶爾有粉色小花散發甜甜花香,隨風輕搖。
初次見到這裡時,我像個孩子般雙眼閃閃發亮,以為找到一處無人知曉的秘密基地而自傲不已。
我沒告訴同學、青梅竹馬的玩伴,甚至連死黨都沒說,不想告訴任何人,總覺得要是讓別人知道就可惜了。
若是要帶外人來這裡的話,一定會帶對自己而言,無可取代、最重要的人,不是嗎?譬如帶心愛的人來這裡。
在這裡吵架,在這裡和好,不管任何時候都能來到這裡,度過屬於兩人的寶貴時間,希望這裡是個只有彼此知道的特別地方。一直在找尋這般存在感的我,暗暗在心裡強烈祈求,做著美夢。
升上高中後,認識了美嘉。美嘉對我而言,是無人可以取代的存在。所以剛升上高二那年的冬末春初,百花盛開的季節,我第一次帶美嘉來到這裡。
美嘉一看到廣闊的河堤,彷彿倒抽口氣般,驚訝地張大嘴。然後像使盡全身氣力般高興地大叫,興奮地雙眼閃閃發光。
於是我們幾乎每天都會來到這裡,不知不覺地,這裡變成了我們約會的地方,有時會在這裡發生爭執,有時會在這裡和好,已經成了不折不扣我們之間最特別的地方。
一下課不是去彼此的家,而是來到河堤;不會想逛街買東西,而是來這裡消磨時光,笑談一些無聊瑣事。
一進學校就得面對一大堆校規、升學就業、前途等許多麻煩事,學級主任、班導總是帶著嫌惡的口吻,囉唆個不停。
就算回家也無法得到慰藉,不要成天只想著玩、也要唸點書啊!這回換媽媽叨念。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難免也有厭倦一切的時候,心中的壓力就這樣越積越多。
可是只要來到這裡,便能將鬱悶的心拋到九宵雲外。
在這裡和美嘉度過的悠閒時光,慰藉、平復了我的心。對我而言,那是不可或缺、最幸福,比什麼都來得重要的時光。
「過來這裡!一起睡個大頭覺吧!」
隨性地躺在草地上,伸手抓住正忘我地拔著草的美嘉的袖子,硬是往自己這邊拉近。
那瞬間,天真無邪的太陽像惡作劇般從雲間探頭,照著我毫無防備的身體,刺眼陽光令人不禁瞇起眼。
美嘉看到我徹底放鬆的模樣,嘴角浮現一抹微笑。
我像要掩飾害羞的心似地,揮手催促她快點過來,美嘉不待我說完,便迅速將頭枕在我的臂上。
枕著她的手臂輕輕地摟著她的肩。
肩膀像長了個心臟,發出咚咚的心跳聲,彷彿傳遍全身各處。
「老天~~我實在太幸福了!」
突然脫口而出的“幸福”二字,這般單純卻又複雜的字眼,並非無聊的原則,也不是只限此刻,而是千真萬確的真心話。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真想永遠都像這樣。
永遠像這樣愉快地談笑,該有多麼幸福啊!
這份幸福要是能一直持續到明天、後天、下個禮拜、明年、好幾年後的話,該有多好。
不需要再給我們更大的試練了。
我愛美嘉,美嘉也是,光這件事就已經讓我覺得很幸福。
也許一個男人祈願這種事,太小家子氣,缺乏男子氣慨,即使如此還是想在心底如此祈願著。
希望這世界真的存在著永遠這個字。
「美嘉也好幸福喔~~!!」
方才還遮著太陽的雲,乘著風往遠方流去,抬頭望見的是一片廣闊的蔚藍晴空。
無邊無界,沒有盡頭。
「這事實在很難啟齒,櫻井弘樹先生,你罹患了癌症。」
因為身體不舒服,前往醫院檢查後過了幾天,5月13日,那是非常晴朗的一天。
我坐在有點生鏽的鐵管椅上,媽媽坐在一旁,只見她提在手上的刺繡包包掉落地上,錢包應聲開啟,零錢滾得滿地都是,發出令人想遮住耳朵的刺耳聲音。
「醫生,你是在開玩笑吧?」
媽媽的聲音顫抖,邊拚命擠出只求醫生能夠回答YES的苦笑,邊這麼問。
雙手交臂倚著牆,站在後面的姊姊,並沒有蹲下去撿零錢,也沒有露出不知所措的樣子,還是保持一貫冷漠神情,只是頻頻更換雙手的姿勢。
這幾年來,喉嚨狀況的確不太好。
也不是很嚴重,只是覺得有點不對勁罷了,也就不以為意,想說身體應該很健康,沒什麼大礙才是。
但最近喉嚨越來越痛,總覺得說話時,喉嚨深處像有什麼東西哽住似的。
有時講起話來斷斷續續,令人不耐。而且咳個不停,睡覺時還會盜汗,甚至發現喉嚨根部有個像疙瘩的小腫塊。
爸爸第一個發現我身體不太對勁,「大概感冒了吧。穿暖一點,睡飽一點就會好了。」丟下這幾句話後,便馬上將視線移向報紙。
至於姊姊的話,「人家說笨蛋不會感冒,看來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嘛!」邊說出這般惹人厭的話,邊不置可否似地一笑置之。
在如此樂天派的家人中,媽媽是唯一擔心我身體狀況的人。
從小到大一直都是如此,不管是吃吃成藥就好的小感冒,還是貼貼OK繃就能癒合的傷口,即使根本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媽媽還是會半強迫地帶我上醫院。
這次也是如此。不,只有這次不同,與其說是半強迫,「小病不看,萬一變成大病就糟了。」不如說是威脅恐嚇。
姊姊雖然嘴上抱怨,還是和媽媽一起陪著我上醫院,甚至回絕和別人早就約好的事。
爸爸大概認為從小任性調皮,老是傷痕累累的我,這次大概也是沒什麼大不了的小毛病吧。
我也是這麼想。
只不過是感冒,出了點小毛病罷了。沒什麼大不了的,一定能夠馬上痊癒的。
「那是惡性腫瘤,病名是------」
醫生邊翻看著病歷和X光片,邊用淡淡的口吻詳細說明著。
說話口氣未免太過公事公辦。
怎麼樣都無法讓人相信這是事實。
一片黑暗的房間。
有種被關進那種房間的孤寂感,無論怎麼跑都沒有盡頭似的。
那裡宛如沉入海底似地靜寂,偶爾還會傳來刺耳到叫人忍不住瞇起眼的耳鳴聲。
「依病理切片診斷來看------可使用抗癌劑化療法------」
總覺得醫生的聲音像從遠方傳來。
啥?這傢伙到底在說什麼無聊話啊!
說了一大串根本聽不懂的醫學名詞,聽著他那一副氣定神閒、自以為是的說話聲,有股想乾脆揍死他的衝動。
黑暗中突然發出激烈的聲音,捲起一陣漩渦,力量強大的像要把我吸進無底洞。
救命啊!誰來救救我啊!
勉強抓住僅剩的地板,拚命大聲呼救。
「不會吧!怎麼可能?!」
這時媽媽突然大叫,開始啜泣。
隨著那悲痛的聲音被拉回現實,多少瞭解自己現在所處的立場的確是事實。
站在後面的姊姊彷彿早就料到似的,從口袋掏出一條棉質手帕遞給媽媽,用紫色繡線繡的葡萄刺繡,不知為何飄著一股哀愁。
------為什麼哭泣呢?
我突然站了起來。
也許那是本能勝過理性的瞬間反應。
鐵管椅應聲往後倒,巨大聲響和媽媽的啜泣聲巧妙地重疊。
那聲音稱不上悅耳,恐怕也不會讓人聽得出神,宛如宣告世界末日來臨般殘忍無比的和聲。
「不要胡說八道!」
怎麼樣也無法相信的我,緊緊抓住還在繼續說明的醫生的肩膀,前後左右用力地搖晃著。
醫生卻面不改色。
要是一切都是玩笑話,該有多好啊!
要是對我生氣發火,反而能讓我好過點。
只見那面不改色,直視著我的眼眸深處失了光輝,瞥見一絲同情。
「我可不是專程來聽你說笑耶!」
不管是昨天還是今天,我不停地吃,吃到肚子都快撐破了。
一直睡,睡到頭都快爆開了。
然後我決定不管明天、後天、永遠都要這樣。
「……喂、說啊!回答我啊?!」
癌症?!我?!騙人?!開玩笑吧?!這是夢嗎?
護士動作熟練地輕撫著情緒激動的我的背,醫生邊嘆口氣邊繼續淡淡地說明病情。突然有股想抓亂頭髮,將病歷和X光片撕個粉碎,盡情大吼,捧腹大笑的衝動。
也許只是有此念頭,絕不會這麼做的我,比自己想像中還冷靜也說不定。
但當腦中純白的畫布開始出現混著多種顏色,近似灰色的獨特色彩時,頓時明瞭自己的冷靜只是裝出來的。
離開醫院回家後,媽媽靜靜地從冰箱拿出冰塊,用薄毛巾捲起來,敷在哭得紅腫的眼瞼上。
沒有人有心情再多說什麼,家裡充斥著彷彿一碰觸就會燙傷般炙熱、沉重的空氣。
我邊將剛放進冰箱不久,還有點微溫的冰咖啡倒進細長形玻璃杯,邊不經意地瞄了眼掛在牆上的時鐘,確認現在時刻。
生活規律的爸爸總是固定時間下班,離他到家的時間還有2個小時。
啊啊!肚子好餓。
但晚餐總是等爸爸回來才開始準備。
要我在這般沉悶的氣氛中待上2個小時等爸爸回來,實在太痛苦了。索性隻手拿著冰咖啡,迅速窩回自己的房間。
一打開窗子,比平常還冷冽的寒風吹得窗簾搖搖晃晃,這情景令人感覺十分虛幻。
腦子深處到現在還殘留著模糊昏暗的影子。
那與剛睡醒時,處於曖昧狀態的現實有何差別呢?彷彿在抗拒腦子能夠理解的事。
從客廳傳來媽媽的啜泣聲。
真是的!幹嘛相信醫生鬼扯的話?
想也知道那是惡意的玩笑啊。
沒錯,這種事怎麼可能落在我頭上,根本不可能。
不想再鑽牛角尖,東想西想了。
…………好無聊喔。
離爸爸回來還有2個鐘頭,來做些什麼吧。
啊啊,對了。最近運動不足,來練練肌肉吧。
在衣服、教科書丟的到處都是的房間裡找到一小方空間,脫光上衣,仰躺,雙手抱住後腦勺。
從國中開始,每天都像這樣鍛練腹肌等處。早上醒來看到這副有做就越健美的單純身體,又有新的肌肉形成就樂不可支。
上體育課時,老師要求運動前各做100下仰臥起坐和伏地挺身。
對於每天練肌肉的我而言,100下根本不算什麼,所以總是嘲笑那種連50下都做不到的胖子和瘦皮猴。
42、43、44、45、46、47……。
做到第47下仰臥起坐時,一股勁做個不停的我,停了下來,用手掌拭去從額頭滑落的汗水。
呼。奇怪。不可能只有這點能耐啊。
48、49、50……。
側腹好痛,快喘不過氣,脖子僵硬,喉嚨好乾。
伸手拿起放在桌上的冰咖啡,先潤潤乾渴的喉嚨。
一下子就流到胃部,感覺口感比往常苦的冰咖啡,瞬間讓全身的汗乾涸,回復元氣。
這時突然瞥見自己那不曉得從何時起就沒再正眼瞧過,映照在立鏡中的身影。
也許是心理作用吧。原本寬闊的肩膀變得又瘦又窄,原本應該很健美的腰部,卻呈現平坦的肌肉線條。
怪了?我從何時開始變得這麼憔悴啊……。
也許在周遭人眼裡,我的身體沒什麼特別變化吧。
因為就連總是暱在一起的美嘉也沒有察覺。
可是我自己一看就明白。
不可能沒察覺已經相伴16個歲月的身體所產生的變化。
映在鏡中的自己彷彿變了個人,看起來就像潛藏在心底某處的另一個自己。
另一個我向現實中的我微笑。
霎時渾身起雞皮疙瘩。
我本能地後退,冷不防撞上鋁製書櫃,架上並排的書應聲掉落,我千鈞一髮地躲開。
課本、漫畫、雜誌,掉的一地都是。
一眼就看到那本書,那本從來沒翻閱過,厚厚的、滿是灰塵的書。
醫學事典。
拿起那本書,開始一頁頁地翻著。
癌………癌………癌。
打開目錄頁,醫學事典裡確實存在著醫生說的那個病名。
光是這樣就已經是個難以承受的衝擊,
“最先發現腫瘤的部位以頸部居多,從軟的到硬的都有”
摸摸喉嚨,頸部發現的硬塊,還有點軟軟的,那是腫瘤。
一排排聽都沒聽過的艱深詞語,不斷喚起醫生說過的話。冷靜,可以冷靜地理解虛無的逃避慢慢地化為現實。
騙人的吧?騙人的吧?騙人的吧?
開玩笑的吧?開玩笑的吧?開玩笑的吧?
不願相信,也不敢相信,無論如何都無法相信。
若一切的一切全是事實的話,那我……。
“頸部發現的腫塊,初期幾乎沒什麼症狀”
那我,
那我,那我,那我,
那我,那我,那我,那我,
“扁桃腺原發性腫瘤,會出現咳嗽、呼吸困難,臉部浮腫等症狀”
到底會變成怎麼樣呢?
啪地一聲闔上醫學事典。
要是沒看就好了。
要是沒看的話,就會永遠相信這只是個謊言。
查了以後又如何?只為了求個心安嗎?還是想確認什麼?如果在書上發現“死”這個字眼,又會怎麼想呢?
懷抱著什麼都不知道的恐懼,和瞭解一切的恐懼,究竟哪個比較沉重,罪孽深重呢?
「怎麼、可能。」
小病魔企圖干擾哽在喉嚨深處的話語,
「我、怎、麼、會、得、癌症……」
從嘴唇迸出怪里怪氣的咳嗽聲,
「明明、這麼健康、怎、怎麼可能。」
決定面對一直想逃避的所有事實。
再次試著觸摸黏在脖子上像橡膠般有彈力的硬塊。
……原來如此,我罹患癌症,不是謊言也不是開玩笑。
我真的得了癌症。
像要弄掉硬塊似地用力捏著,但不管再怎麼用力,還是牢牢地黏著,醫生說這是惡性腫瘤。明明這麼小,這腫瘤卻讓我的人生一夕變色。夢想中的未來就這樣瞬間崩壞,直到昨天為止還以為一如往常的日子卻變成令人無比憎恨的東西。
希望能以某種形式平靜地處理這令人難以招架的焦躁感。再次拿起才剛闔上的厚重醫學事典,用力地向桌子那邊扔去。
擺在桌上的陶製菸灰缸掉落地上,摔個粉碎,黑白色煙蒂散得地毯上到處都是。
「開、什麼玩笑啊!」
舉起手用力一揮,不偏不倚地擊中今天去醫院前才看得入迷,那雜亂地跌放在床邊的100集以上運動漫畫,傳來連續不斷的崩塌掉落聲,那情景好比我現在脆弱的心。拾起的同時,邊發出不成句的吼聲邊使勁地往牆壁扔去。
「開、什麼玩笑啊!開、什麼玩笑啊!開、什麼玩笑啊!」
千真萬確的事實奪走了我的冷靜。正因為遭逢此刻,更無法保持冷靜,也許像這樣情緒亢奮到無法深思任何事物也是另一種救贖。
回復冷靜才是最叫人害怕的時候。各種想法一下子蜂湧而來,搞不好我會發瘋。
罹患癌症並不一定就是被判了死刑,但相較於前幾天還過著的平凡生活,更有種死期迫近的感受,卻是不爭的事實。
「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是我、得了癌症?!要不是我、就好了。為什麼、是我?!」
頭好痛,好想吐。情緒無論如何都無法平復。煩悶的心、黑暗完全沒有消去。
忍不防握拳猛捶牆壁,牆壁發出沉鈍的聲音,撞出一個淺淺的洞。開始領悟一切的我,殘留在心底的是醫生說的話、自己的病情、還有千真萬確的事實。不是不安,也不是悲傷,只是一種想逃離現實,近似無盡的恐怖,叫作憤怒的情感。
不知為何突然想起那件事。
還在唸小學低年級時,有位算是親戚的伯母因病到了另一個世界旅行。
伯母和爸爸情同手足,聽說從小就十分疼愛我。
自從伯母住院後,備受伯母疼愛的我,常常放學後摘束野花去探病。
但日子一天天過去,原本體態豐腴的伯母,隨著病情惡化變得越來越瘦,原本個性開朗的她,不知何時失去了笑容,最後嚴重到連話都沒辦法講。
幾天後伯母安詳地嚥下最後一口氣,周遭人彷彿料到伯母會死似的,平靜地為她籌備喪禮。
沒錯,那位伯母確實也是得了癌症。
那時年幼的我,初次看見親近的人瞬間被奪走性命,心裡從此對死亡懷著強烈的恐懼感,相對地也感受到生命的渺茫。
那像有顆糖哽在喉嚨深處的不愉快感,到現在還清楚記得。
我生病了,而且還是癌症,總覺得是個永遠與自己無關的字眼。就算在電視上看過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如何與病魔奮鬥的紀錄片,也只是覺得那個人很可憐,運氣很差,心生同情而已,感覺像是遙遠世界才會發生的事。
一直以為自己會結婚、有個溫暖的家,過著幾十年幸福的生活,直到成了駝背的老爺爺才安詳地離開人世。
現在想想,覺得自己真是在做白日夢。
不,也許應該說直到剛剛才變成一場夢才對。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剛才醫師所做的說明猶如馬耳東風,全都沒聽進去。
唯一殘留在腦中的記憶就是叮嚀我要有住院治療的心理準備之類,令人聽到就想搖頭的事。
既沒有明白告知還能活多久,也沒有直接聽到「死」這個字眼,所以不需要急著住院,但有一定的療程,而且也有治癒的先例。癌症不等於絕症,就連無知的我也明白這道理。
但「死」這個陰森的字眼卻始終在腦中盤旋。
越想越鑽牛角尖,腦子裡滿是負面想法,內心充斥著莫名地焦躁感。
我戰戰兢兢地鬆開一根根因為緊握拳頭,從第二處指關節開始隱約可見紅黑色血管的手指。
------好瘦,怎麼會變得這麼瘦呢?
手掌雖瘦卻滿是手汗,溫溫的,就連血管也確實流通著。
手指還能像往常般活動,也能拿東西。不管是幫爸爸拿報紙,還是幫媽媽提東西,甚至和姊姊打架也沒問題,當然也能撫著美嘉的頭。
看吧。根本和以前一樣,沒什麼改變啊!
這手指什麼時候會動不了了呢?
這手指什麼時候會失去溫暖觸感呢?
我會死嗎?真的會死嗎?
若真是如此,該怎麼辦呢?
學校怎麼辦?
家人怎麼辦?
美嘉怎麼辦?
還有我……我該怎麼辦?
不想死!
我還不想死啊!
還有很多事想做!
還有很多事還沒體驗啊!
我想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
我不想就這樣結束生命。
現在就跟我說這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在開玩笑!這樣我還能原諒。
好嗎?拜託,有誰這麼告訴我吧。有誰肯幫這個忙……。
「美嘉……」
緊繃的肩膀一下子失了力,原本癱靠在牆上的身體失了支撐的力量,慢慢地往下滑。
現在才覺得握得青筋突起的拳頭有點痛,這痛感以慢速度傳至心底,彷彿在告知這如惡夢般的時間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微微發顫的指尖,一切的一切是那麼地令人厭煩。
從口袋掏出PHS,迅速開啟電話簿。
A、KA、SA、TA、NA、HA、MA……MI ……美嘉、美嘉、美嘉。
B、
美嘉。美嘉的話,一定會安慰我沒事的。
「阿弘不可能會得什麼癌症!!」這麼說。
美嘉。美嘉的話,一定會這麼說的。
我到底該如何是好?
不知道。我到底該怎麼辦?
一味鑽牛角尖真的很可怕,要接受一切真的很可怕。
好怕、好怕、怕得不知該如何是好。
如果把一切全都告訴美嘉的話,她會覺得我是個膽小鬼,瞧不起我嗎?
可是我相信,美嘉一定會陪我一起面對的。
而且我相信只要和美嘉在一起,再大的困難都能克服。
不需要那種虛情假意的安慰之詞,也不想聽些毫無意義的鼓勵話語,沒這必要。
只想……只想聽聽她的聲音。美嘉,現在好想見妳。
按下通話鈕,當話筒貼著耳朵時,突然傳來激烈的敲門聲。一時慌張的我,冷不防掛上已經打通的電話。
「真是的!怎麼搞成這樣啊!亂成這樣根本沒地方坐嘛!」
只見姊姊皺著眉頭,大搖大擺地走進來。
「不要隨便進別人的房間啦!」
「哦------真難得耶,在發洩情緒啊?」
摔得粉碎的菸灰缸,散得到處都是的課本和雜誌。
還有凹了個洞的牆壁,怎麼看都沒無法掩飾自己焦慮的心情。
「少囉唆!沒事的話就滾啦!」
「真是的!傷腦筋啊!」
只見姊姊一腳踹開摔破的菸灰缸,硬是找了處地方坐下來。偶然瞥見掉在腳邊的半透明打火機,從口袋掏出這世上最麻煩的東西,點了根菸。
「我哪有什麼好傷腦筋的!」
「是嗎?啊、你一定以為我是在說你生病的事,是吧?拜託!我說的傷腦筋是指你。」
我像是故意讓她聽到似地嘆了口氣,倒也不是沒有力氣反駁,只是想說至少表示一下自己內心的不爽。
姊姊打開寶特瓶蓋子,拿來代替菸灰缸,順手將剛點不久的菸丟進去捻熄。
總是嫌我「浪費」撿我抽過的菸蒂來抽的姊姊,居然順手丟了才剛點的菸,這般不尋常的舉動不禁令人懷疑她的冷靜是裝出來的。
「阿弘,怎麼啦?一點都不像平常的你。」
「不像平常的我?那平常的我是什麼樣子?」
「現在的你活像隻喪家之犬,平常不是老擺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德性嗎?拜託,癌症又不是什麼絕症,我那夥麻吉中也有人跟你患了一樣的病,手術很成功,現在還活得好好的呢。而且馬上就要出院了。」
要是平常的話,「妳又不是我,懂什麼啊?!」肯定會強硬地反駁回去,但今天姊姊說的每一句話卻微妙地直搗心坎。
「阿弘,你聽過這說法嗎?兩種花以同樣的條件種在同一個地方,如果每天對著其中一種花說:『好漂亮喔!』,不知道為什麼每天被這麼誇讚的花就會開得出奇漂亮哦!」
「到底想說什麼啦?」
「你這麼灰心喪志,就算本來治得好的病也會治不好,人家不是常說什麼病由心生嗎?而且要是你就這樣走掉的話,美嘉搞不好會跟別的男人在一起哦!你甘心嗎?」
「啊?才不可能呢!」
「難說喔。搞不好哪天會出現比你更好的男人,想想美嘉跟妳以外的男人手牽手親密地走在在一起的樣子吧。」
被這麼說之後,眼瞼內試著開始浮現那樣的光景。
美嘉和我以外的男人並肩走著。
沒辦法,沒有特定的對象實在很難想像。
對了。那就試著想像坐我旁邊那個只知道唸書的書呆子吧。
想像那傢伙和美嘉並肩走著,兩人十分親密,手牽手,十指緊扣。
------滾開!
很高興地笑著,一臉很幸福的樣子。
然後想像我硬是插進他們中間,一拳打飛那傢伙,劃下句點。
「不行!絕對不行!不會將美嘉讓給任何人,絕對不會!」
內心深處像被人用手強力扭著,水份全被抽乾似地乾涸,好痛,光是想像就這麼痛苦。
「你要是再這麼一副要死不活的,就完了。不是煩惱究竟能不能治好,而是非得治好。只要有這般堅定的意志,搞不好腫瘤就會消失,不是嗎?」
姊姊晚上和一些太妹朋友鬼混的關係,深受影響所以講起話來有些粗魯。
但聽得出來粗鄙的言詞中藏著鼓勵的話語。
而且一害羞就會用拇指頻頻摸著耳背的習慣,搞不好連她本人也沒察覺。
「……弘樹。」
從半開的門縫傳來熟悉的低沉嗓音。
原來是一身灰色西裝,神情比平常嚴肅,剛下班回家的爸爸。
身後還站著一臉揣測不安的媽媽。
媽媽那張哭腫的臉,含著些許憤怒的情感,八成和現在的我一樣開始面對事實,拚命地思索該如何克服一切。
「喔,回來啦。」
爸爸避開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和書本雜誌,大步地走到我面前,慢慢地坐了下來。
那雙直視著我的眼是那麼地認真,讓人無法移開視線。
爸爸靜靜地執起我那因為捶牆而流血的手,輕輕地握著。
「一定沒事的。」
雖然聲音聽起來是那麼地微弱、不可靠,卻包藏著無比的力量。
「我們家弘樹那麼堅強又勇敢,爸爸保證絕對沒事的。要是討厭住院的話,就不要勉強,固定去醫院看診就行了。但絕對不能自暴自棄,明天開始我們一起對抗病魔,你這小子絕對沒問題的,一定沒問題的。」
爸爸的眼角滾落了一顆淚珠。
那圓圓地帶點鹹澀味的淚水落在領帶上,啊、不知為何突然想起這條花色俗到不行的領帶,是以前我和姊姊湊零用錢合買送給爸爸的生日禮物。
沒錯沒錯。那時我們還故意選了一條花色怪異的領帶,「這種花色怎麼戴去上班啊!」然後爸爸邊說邊露出傷腦筋的表情,馬上將領帶塞到衣櫃最裡面。
明明如此,為何現在要繫呢?
而且早就變得皺巴巴的不是嗎?
繫著這麼一條花色怪異的領帶,不覺得丟臉嗎?
啊、莫非之前就繫過,只是我完全沒注意到罷了。
爸爸明明總是一副凡事漠不關心的樣子呀!
幹嘛偷偷摸摸地繫上這條領帶啊!
還為了我哭到雙肩顫抖,一點都不像平常的他。
爸爸那應該很寬闊的背脊,不知何時怯弱地縮著;原本以為很大的手掌,看起來卻比我這瘦削的手掌還小。
「我、我不想死,救救我!爸爸……」
斗大的淚珠淌落。
那緊緊握住我的小手,像是承受了我所有的不安,也吸取了悲傷。
握住我的這雙手是那麼地溫暖,也溫暖了我的手。
我還活著,確實地活著。
是的,其實最慌張的人是我。
客廳的燈熄滅後,孤零零的房間內聽不到車子呼嘯聲,也聽不到說話聲,回到昨天那根本難以想像,又冷、又沉重、又安靜的時刻。
明明離接受事實的那刻已經過了一段時間,不安的心情依舊持續著。
有時會試著想像這一切都是夢,企圖逃避現實;有時會想說為何是自己……嘟噥著這些無理的想法,一股怒氣湧上心頭;有時恐懼死亡的不安感會像浪般襲來,痛苦地令人招架不住。
這時就會不知不覺地想起父親那雙比我還小、還厚實,卻非常溫暖的手掌,不可思議地就能稍微安心一些。
還無法 面對一切。
必須花上一段時間調適。
但確實比之前更加感受到現實那令人憎恨的恐怖。
從窗簾縫隙探出頭的是,散發著令人心裡有點發毛的朦朧光芒,怯怯地浮在半空中的月亮。
漆黑的夜空稍稍明亮了些。
今天要上學,但實在不想去。問題是就算蹺課一天,也只是圖個片刻休息罷了。
反正該去的還是得去,沒必要耍賴,就算是千百萬個不情願也得上學。
「對了,數學作業還沒做呢。」
我像要吹散什麼不愉快似地這麼說,粗魯地拿出課本和筆記本,決定寫寫總是懶得碰的作業,一掃心中陰霾,迎接早晨到來。
《解開下列方程式》
這題應該解不出來吧。
《求以下立方體的體積》
不好意思,這題也不會。
《列出這個圖表的算式……》
算了!算了!根本沒有一題會。
完全不行,應該說會寫才怪。
課本彷彿反應了我現在的心情。
混亂的算式以圖表為中心軸緊密地並排交錯著。
即使如此,邊邊還是留了一方不知該做什麼的空白。
我試著用鉛筆在這處因為上課不專心,老是打瞌睡而留下來的空白處,寫了些反應心情的話語。
“無盡的絕望”
這是腦海裡率先浮現的話語。
“無盡的ㄔㄣˊ ㄌㄨㄣˊ”
咦?ㄔㄣˊ ㄌㄨㄣˊ的國字怎麼寫啊?
------你這麼沒種怎麼行啊?------
真是的!我在寫什麼啊?!
猛然回神,拚命劃去剛才所寫的那幾句話,再補上幾句新的。
“是生?是死?”
“我所擁有的力量”
------你一定沒問題的------
不對,我怎麼可能會寫這種東西。
將印在課本上的所有算式和圖表全都塗掉,光用一枝鉛筆是不夠的,要用非常粗的黑色簽字筆塗個好幾遍才行。
然後用修正液在上面補上新字句。
字體更大、更粗。
“實現夢想”
“充滿希望的每一天”
“勇往直前”
不知為何,光是胡亂地寫上這些字就有種黑暗中透出一點曙光的感覺。
只要寫些積極的話語,瞬間就會有股向前衝的動力。
沒錯,留下點什麼吧。記錄每一刻的心情與想法,記錄曾活在這世界的證明。
像這樣用文字記錄現在的心情,一吐為快吧。
就算是好幾十年後,我也要一直寫、一直寫,直到嚥下最後一口氣。
我闔上課本,拿出連一頁都沒寫過,完全空白的筆記本,緩緩地攤在桌上,在第一頁上沙沙地寫下,
------2001年5月31日------
今天我被告知罹患癌症。
因為最近老覺得喉嚨不舒服,想說去醫院看一下,沒想到竟然是癌症……。
所以決定從今天開始寫日記。
直到嚥下最後一口氣。
因為不想在畢業之前就住院,所以決定採定期回醫院診療的方式。
開始進行治療。
赤裸裸的日記。
全是自己的真情告白,只在這本日記裡。
若只在這裡吐露心聲的話,一定能夠得到諒解吧。
♪ ∼ ♪ ∼ ♪ ∼ ♪ ∼ ♪
拜輕快的PHS鈴聲之賜,才發現自己竟然想這種事想得出神。
大半夜地之所以鈴聲大作不是因為有來電,而是因為怕自己睡過頭而設的鬧鐘。
對了。因為滿腦子都在想著自己的事,而忘了打電話給美嘉,正準備打給她時,姊姊剛好走進房間,以至於到現在都還沒打。
拿起隨手塞在枕頭下面的PHS。
如果是在剛才那般精神狀況下打給美嘉的話,一定會向她大吐苦水吧。
若是這樣的話,一定會懊悔自己表現的太怯弱。
但現在的我和剛才的我不一樣。
也許會稍微吐點苦水。
但一定能夠展現出堅強的一面。
「別擔心啦」,相反地還會這麼安撫美嘉。
開啟電話簿,試著按了好幾下,PHS卻無法啟動。
看來剛才的鬧鐘設定似乎耗盡了最後的電力。
要在一片雜亂的房間中找出充電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況且已經凌晨四點多了,PHS的電力當然所剩無幾。
想想,想告訴美嘉的事可不是在電話中兩三句就能交待的事。
而且講電話搞不好會引起誤會,看到我開朗的模樣,也許美嘉也能積極地接受事實。
明天,明天去學校當面告訴她一切吧。
花點時間慢慢地、慢慢地告訴她。
看看知悉一切後的美嘉究竟會露出什麼樣的表情,會說些什麼、會怎麼想、會失去什麼、又會得到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