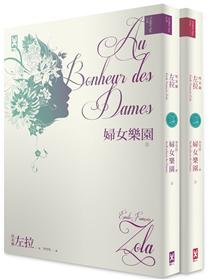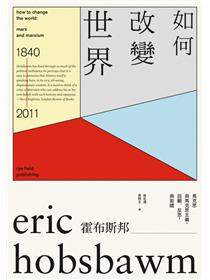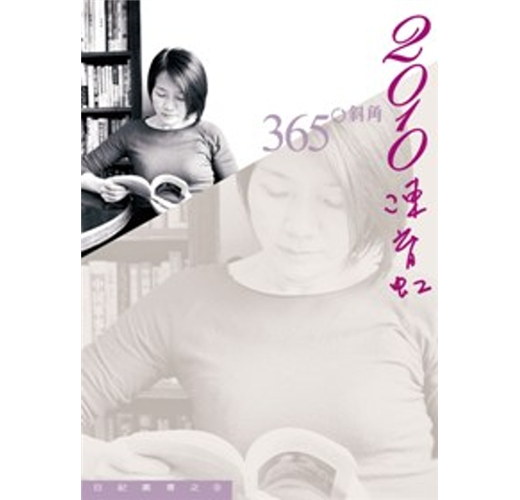日記十七則
―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至十七日
一日(星期六,晴冷)
二○○二年出版爾雅「作家日記」第一冊,轉忽已進入第十個年頭。本來一年前陳文茜女士答應接寫今年的「作家日記」,但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寄雙掛號信給她,盼她告知最後的決定,足足等了一個多月未獲回音,如貿然再請一位作家執筆,萬一文茜年底前按時交稿豈不鬧雙胞?想來想去,還是由自己當備胎,如果她按時交出日記,《/陳文茜》接上前面的九冊「作家日記」,成為圓滿的第十冊,等到二○一二年新書出版時,我會設法辦一場慶祝酒會,邀請十位寫日記的作家全數出席,如臨時文茜未能交稿,至少我的備胎可以派上場,一頭一尾,由我自己串連,也還說得過去。
晚上六時三十分,和貴真一同參加幹校九期同學丁振東長公子莊敬和李波雄先生長女彥瑩的婚禮。席開百桌,超過一千人,婚禮場面可謂盛大,在畢業四十八年之後,振東兄嫂硬是有辦法將當年三百多位九期畢業同學幾乎全數出席,真是一種奇蹟中的奇蹟。四十八年前,我們都是二十歲上下的小夥子,如今,不少同學已拿著拐杖,歲月,把我們的頭髮全染白了。
通常,無論同學或朋友,交往一段時日就不再往來,能保持十年、八年就不容易,而振東兄居然能將四十八年前的同學全拉回來,說來,有點像是神話,但仔細回想,振東兄誠懇熱情,永遠的奉獻精神,以生命結交朋友,難怪他知己滿天下。
二日(星期日,晴冷)
下午在家校對張瑞芬《春風夢田》四校稿,我喜歡這本書,在文學冷寂的年代,出版這樣一本洋溢文學熱情的書,是書評人和出版人聯手向文學致敬,同時也向仍在散文和小說園地寫稿的作家致敬。
三日(星期一,陰雨,濕冷)
讓人的廟
大概從去(九十九)年年中開始,每周一,覃雲生總是會來陪我吃飯。雲生和我有四十多年交情,當年他還在板橋中學讀書,參加救國團文藝營,就和我認識了,他也是最初「年度小說選」的編輯委員,和鄭傑光合編過《六十三年短篇小說選》。在我決定創辦一個出版社之前,需要一個響亮的名字,「爾雅」兩字,正是雲生幫我想的。「爾雅」前二十年所有的封面設計,幾乎三分之二出自雲生之手,後來他進了中國時報,又轉到飛碟電台,中間有十幾年較少聯繫,但若有事找他,總是很快出現在我面前。
今天中午他帶我到圓環的「醉紅樓」吃潮洲菜。圓環改建後,我已經有好多年未曾接近。雲生知道我愛吃辣,特別帶我到法主公廟前購買一對老夫婦製作的獨特辣椒醬。穿過法主公廟廊下,我問「廟在哪裡?」雲生要我回頭向上望,一座高懸在空中的廟共有二、三、四、五樓,至於一樓,為了讓路人通行,廟已成了通路。通常都是人碰到廟轉彎,很少聽聞―廟讓人行路。
年紀越大,我的生活範圍反而越小。這半年多雲生開了車帶我到處跑,讓我見識也接觸到了許多自己幾乎不認識的台北。
進入民國一百年才第三天,讓人喜氣洋洋精神為之一振的消息不多,但負面新聞不斷,除了學校霸凌性侵,更駭人的是,一個二十七歲的年輕人只因父母管教嚴格,居然供稱讀國二時就計劃謀殺全家,他果然殺死了母親和哥哥,也殺傷父親,唯一躲過一劫的是還在當兵的弟弟。
根據聯合報統計,近三年來單單弒親案就高達十件。其他奇里古怪甚不人性的犯罪案件更是無日不在發生,情節常比電影中的更離奇恐怖,這樣的社會似乎告訴我們,人類愈文明,科學愈發達,卻對人類如何遠離痛苦遠離瘋狂完全一籌莫展。
四日(星期二,陰,濕冷)
戰鬥人生
翻讀王盛弘九年前為我的日記而寫的序,他說:「……把一張大桌子整理得眉清目明……將近三十年,桌子還能維持住旁人能夠理解的秩序,靠的是自律。」
這一段文字,真的令我汗顏!看看我現在的桌子,不僅辦公室的一張大辦公桌書稿雜物堆擠如垃圾場,就是家裡的一張書桌也永遠理不清了,原來眼前的我,在時光老爺面前早已豎起白旗,我的自律能力似乎迷失了路。「亂」已成為我生活的常態―不但衣物亂,書籍照片信箋文件全亂了套,有人如突然跑到我辦公室,會讓我心慌,因為實在不想讓人看到一團凌亂,生活真的是一場戰鬥,稍一疏忽,就會敗將下來。
從今天起,我必須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秩序。先從兩件事做起,一、把自己的門面修飾好,頭髮要梳理,鬍鬚每天刮,穿衣更需得體。有了年歲,千萬不可邋遢;其次,辦公室的一張大桌子,隨時隨地要保持乾淨,多餘的東西,不要擺滿一桌子,我要時常記得站起來,站起來,才有能力好好整理四面八方想霸占我桌面的各種古靈精怪的靜物……世上一切靜物,雖不說話,卻最不講理,一旦出現在你眼前,就賴著不走,身上髒了,也不會自我清洗,啊!戰鬥的人生,活著就永遠要和靜物保持美感的距離。
五日(星期三,晨雨,下午陽光出現)
忙中之錯
除了張瑞芬的《春風夢田》,要趕在農曆年後舉辦的「台北國際書展」前出版的書,還有侯吉諒的《神來之筆》,以及余秋雨「新文化苦旅圖文版」的兩本新書《古聖》和《詩人》。四本書稿像打排球般在手上傳來傳去,爾雅編輯部,只有彭碧君和我,真是忙得上氣不接下氣。中午到汀州路的「上海康樂意」匆匆吃了四個包子和一碗酸辣湯,立刻趕到The One找阿強整理頭髮,明明只是想把白頭髮染黑,硬是誤說成燙髮。上卷時因和阿強舅舅聊天,完全未發現錯誤,等到滿頭都上了卷也加了藥水,才發現大事不妙,但為時已晚,只好將錯就錯。
多少年都沒燙頭髮了,從貝多芬式的長髮到貝克漢式的小平頭,看來,三千煩惱絲還有得我忙。
難道潛意識中我還是想繼續留長髮?
(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