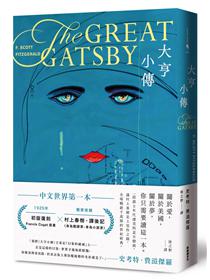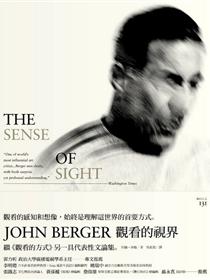本書特色
★諾貝爾文學獎第一位黑人女作家
★《紐約時報》年度十大好書作家
★美國當代最重要女性作家
童妮.摩里森 躍昇文壇巨星關鍵著作
出版時盤據暢銷榜達四個月之久
如果愛情重要無比,是否該將自我無條件捨棄?
潔玎(Jadine)從小因父母雙亡,被白人收養,在白人社會中成長,雖然有著黑人的外表,骨子裡卻是個徹底白化的女子。她比一般身處社會底層的黑人有更多的機會:負笈巴黎求學、當模特兒,處處展現自信、驕傲、意氣風發;然而,潔玎內心卻企求著擺脫一身黑皮囊,期待能找到真正的自我與人生價值。
生(Son)是個浪跡天涯的黑人,因為背負著過往犯下的案件,只能四處流浪打工。他隨性、愚濫、粗鄙無禮,卻仍舊一派真誠,不因身為黑人受到侮辱而消沉過日。
在一個奇特的狀況下,潔玎和生在某個熱島島嶼的莊園裡相遇;她是來探親的借宿客人,而他的出現則是為了要偷東西吃。隨著故事發展,生的勇敢與隨性深深吸引了潔玎,而生也愛上了潔玎的自信與聰慧。成長背景、個性、條件天差地別的兩人陷入熱戀,卻因親友的反對,決定攜手私奔出走,但生命的歸屬去向、文化的認同差異,是否會將他們的愛情消磨殆盡?他們能否突破層層障礙,創建屬於彼此的愛情未來?
故事以美國「後民權時代」為背景,以加勒比海和巴黎為兩個主要場景。藉由描寫女主角(享有白人優勢的「白化」黑種女子)和男主角(出身社會底層的黑種男子)之間的愛情故事,探討如何克服一種本族之內自我扭曲的文化疏離,這是兩個原先頑固地堅持各自文化認同但通過愛情的力量而相互主客轉化,最終尋得自身真實之文化歸屬的過程。故事揉合原始與當代的愛情與現實,將複雜、隱晦、多面向的種族與文化問題以立體的方式呈現給讀者,童妮.摩里森高深的文學素養與文字功力,在本書中展露無遺。
原文書名「Tar Baby」,意為「瀝青娃娃」,原本是一個用來稱呼美國黑人和毛利人的輕蔑語,以「黑油覆身的小孩」為比喻,表示黑人的存在有如殘渣和廢物。但是一方面,瀝青在凝結了碎石之後又是修築道路與橋樑不可或缺的原料,摩里森借用此語是為了表達一種文化融合的期許,寓意深長。
作者簡介:
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
美國當代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諾貝爾文學獎第二位女性得主,同時也是第一位黑人女性得主。
本名Chloe Anthony Wofford,1931年生於美國俄亥俄州樂仁鎮。1953年畢業於華府以專收非裔學生揚名的郝華德大學(Howard University)英文系,兩年後取得康乃爾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專研福克納和吳爾芙意識流小說。1965年起在紐約州雪城藍燈出版社分社擔任教科書編輯,之後並獲聘為紐約市藍燈出版社總社編輯。在工作與育兒之餘,她開始從事小說創作。1970年出版第一部小說《最藍的眼睛》(The Bluest Eye),此後創作不輟,陸續出版《蘇拉》(Sula, 1973)、《所羅門之歌》(Song of Solomon, 1977)、《黑寶貝》(Tar Baby, 1981)、《寵兒》(Beloved, 1987)等四部小說,其中《黑寶貝》的出版,讓她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文學巨星;《所羅門之歌》榮獲美國全國書評家協會獎;《寵兒》贏得普立茲獎小說類獎項。其間,並因其傑出的創作表現,先後受聘於知名大學任教,1989年更榮膺普林斯頓大學羅柏.高欣人文學講座講座教授,在該校教授文學創作,直至2006年5月榮退。1992年,小說《爵士樂》(Jazz)和文學論述《在暗處戲耍:白色和文學想像》(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出版。次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獲獎頌辭推崇其作品具有史詩力量,以精準的對話詩意盎然地呈現出美國黑人的世界。近十多年來,創作力始終亢沛不墜,長篇小說《樂園》(Paradise, 1997)、《Love》(2003)、《A Mercy》(2008,入選《紐約時報》2008年十大年度好書)出版之後依舊佳評如潮。
譯者簡介:
梁一萍
美國麻州大學安城分校美國研究博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專長美國弱勢族裔文學、女性文學、文學與地理、空間之研究及教學。
章節試閱
「你以前是模特兒?」他瞇著眼好奇地問。
潔玎走向一個大藤箱。她的腳步離開克洛斯特地毯,金線拖鞋在瓷磚上發出啪嗒、啪嗒的聲音。她翻了好一陣子,才終於從箱子裡翻出一本時裝雜誌,封面上印著她的照片。她把雜誌遞給他,他在書桌前坐下,從齒縫間吹出一聲口哨。然後,在他的目光從她頭部開始掃視,一直遊走到那(或多或少)由銀色束衣承托著的六公分長的乳溝時,他又吹了另一聲口哨。照片裡她的秀髮熨貼地全往後梳,露出了她整齊的髮線。她的眼睛是貂皮的咖啡色,雙唇濕潤而微張。他繼續一邊吹著口哨,一邊翻開雜誌。匆匆翻了好幾頁後,停在一個共有四頁篇幅的版面,上面印著她不同的姿勢、衣服和髮型,但她的唇總是一貫地濕潤而微張著。
「媽的,」他低聲說。「媽的。」
潔玎沒說什麼,只是緊握著那堆狗繩子。他的表情使她沾沾自喜。他仔細地端詳那些照片,嘴裡不時自然自語地低吟著「婊子」和「媽的」。
「這裡是在說什麼?」他把雜誌平放在桌上,轉向她那頭方便她翻譯。
「啊,這是關於我的介紹。」她面向他和雜誌,俯身伏在書桌邊沿。「譬如以前在哪裡讀書之類的。」
「讀給我聽聽。」
潔玎趴著,快速地翻譯著重點。「卻爾德小姐……畢業於巴黎大學文學院……取得美術史學士學位……是一位景泰藍專家,曾與納皮大師共事……祖籍美國,現居於巴黎和羅馬,在當地一齣戲裡演過十分關鍵的小角色,導演是……」她停了下來。男人的食指遊走到照片中她的襯衣上。
「這個呢,」他問道,手指從襯衣移到下方的說明上,「這句說什麼?」
「只是裙子的描述。天然絲絹……蜜糖色……」
「這裡提到『高速公路』,是什麼意思?」
「喔,他們想用上較時髦的描述。意思是,『如果你想要像潔玎一樣,體驗美國人所謂的高速公路旅行,你需要華麗又輕便的連衣裙。』接著介紹的是珠寶首飾。」
「是怎樣的珠寶呢?」他指著蜜糖色絲綢上那束金色的項鍊。
「這是項鍊總值──」她迅速地把法郎換算成美金,「三十二萬美元。」
「三十二萬?」
「嗯。」
「媽的。耳環呢?有提到耳環嗎?」他正在看她的臉部特寫,從鼻子到胸膛開始微隆的位置,她的耳環,環住喉嚨那雕塑似的項鍊,還有那依舊濕潤而微張的雙唇,都盡收在鏡頭。
「很別致,對不對?這是古董。屬於凱薩琳大帝的。」
「凱薩琳大帝,是個皇后?」
「女皇帝。俄羅斯的女皇帝。」
「她把這些都給你了?」
「別傻了!她已經死了差不多兩百年。」
「哦,是嗎?」
「是。」她以最平板、最美式的腔調回答。不過她臉上仍掛著笑容。
「那一定很值錢了。」
「對。幾乎是無價之寶。」
「沒有東西是無價的。萬物都有各自的價值。」他的手又再度探索起來,食指在凱薩琳的耳環上畫圈圈。潔玎看著他感到耳珠刺刺癢癢的。
「嗯,五十萬,錯不了的。」
「五十萬?媽的!」
「喂,你就沒有其他詞語可以用來表達驚嘆嗎?」她側著頭,一雙性感的大眼睛緊盯著他。
他點頭。「該死的!」
她大笑,這是她第一次笑得如此開懷。而他只是微笑,繼續指著照片問道:「這些衣服都是你的嗎?還是他們借給你拍照的?」
「是我的。有部分是拍攝後他們送給我作為酬金的。」
「首飾呢?他們也會給你嗎?」
「沒有。那些是我自己的─ 除了耳環是他們向俄羅斯那邊借來的。其餘都是我私人珍藏的一部分。」
「私人珍藏?」
「怎麼了?你想做小偷嗎?」
「最好是。如果我懂得偷的話,事情就好辦多了。」
「如果?這些天來,你在這屋子裡不都是在偷東西嗎?抑或是你打算把歐玎的巧克力還給她?」
「你認為我是在偷?」
「你不是這樣說嗎?」
他搖頭。「不,我只是把巧克力吃掉。我要是真想偷的話,我有很多時間和機會。」
「可是你不得不承認你拿了一些什麼。或者你那時只是沒想過要偷什麼。」
「你認為我現在有想要偷的目標?」
「或許有。就看你想在我們這裡得到什麼了。」
「我們?你說你是『我們』的一份子?」
「當然,我住在這裡。」
「但你……你不是這個家的成員。我意思是,你不屬於這裡的任何人,不是嗎?」
「我只屬於我自己。但是我住這裡。我替瑪格麗特.史最特打工。她和范勒瑞安是我的……監護人。你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嗎?」
「他們會照顧你,給你伙食。」
「他們還供我讀書,替我付車費、住宿費、置裝費和學費。我兩歲時我爸就死了,到了十二歲那年,連媽也死了。我是個孤兒。席尼和歐玎是我唯一的親人,范勒瑞安對我的付出更是無人能及。」
男人沒說話,仍舊盯著那些照片。潔玎細看著他的輪廓,同時確保手腕上的皮帶已牢牢縛好。
「你為什麼不看我一眼?」她問。
「我沒辦法。」他說。
「為什麼沒辦法?」
「看照片比較容易。它們不會動。」
潔玎心裡閃過一絲失落。「你希望我不要動嗎?如果我靜止不動,你會看看我嗎?」
他不語。
「看啊,」她說。「我沒有動,真的沒有動。」
他抬眼看她。她有一雙跟照片裡一模一樣的貂鼠色眼睛,雙唇也跟照片上的一樣。
不濕潤,但就像睡著般微張。就像那時他習以為常地溜進她的房間待上幾小時,屏住呼吸,等待破曉時,晨光把她的臉帶離黑暗,讓他看到那兩片沉睡的唇,在等待的當下,他認真地想過要操控她的夢,把自己的夢安插進去,這樣一來她就不會醒來,不會動,不會轉身俯著睡,而是會一直靜靜地躺著,做他想要她做的夢─夢中有幾間黃色的屋子,門是白色的,一個女子打開門大喊:親愛的,進來吧!穿著白裙的胖黑妞們料理著教堂地牢的圓桌,濕漉漉的白床單在繩子上飄動著,晚飯後響起了六弦吉他的琴聲,孩子們從地裡挖出核桃交到她手裡。啊,他用地力、十分用力地試圖將他那關於冰窖的夢擠進她的,使她繼續躺著做夢,當她最後醒來時,她會開始盼望──她這輩子從沒有盼望過什麼──自動唱機的聲音,但不消一會兒,他開始在她的房間裡散發出野獸般的氣味,他害怕這氣味會比陽光更早把她喚醒,使他來不及把自己的呼吸調到她的節拍,把他最後的夢呼進她張開的嘴巴裡去─ 在那夢裡,藍天之下,幾個穿著洋紅色寬鬆長褲的男人站在街角唱起墨水漬樂團的「假如我毫不在意」。他奮力地阻止野獸的氣味蔓延,努力控制呼吸,可是氣味實在太濃烈了,相對於他的肺活量,她的呼吸又是那麼的輕而淺,這裡的陽光不像黎明時那般纏綿,而是像戰士那樣闖進她的房裡,所以他僅剩一點時間把瀝青味的呼吸傳給她,但願它能持續。在他悄悄離開時,他希望她放屁或以為自己放屁,那麼她就不會察覺到野獸的味道,也不會毀了他放進去的夢。可她不在睡夢中了,她現在清醒了──即使她靜止不動,他也知道她隨時會跟他說話,或者,更甚地,她那金色的景泰藍的蜜糖絲絹的夢境會反過來壓制他,這樣還有誰會在意教堂地牢的圓桌呢?
「多少錢?」他問她。「會很多嗎?」他的聲音很平靜。
「你在說什麼?什麼多少錢?」
「那話兒。你要替人口交,才能換來那些金飾和參演電影的機會吧。抑或是上床?我猜模特兒上床比舔老二多吧?」他想要繼續問下去,好知道那些黑妓女掛在嘴邊的話是否屬實,但她已揮出不熟練的拳頭打到他的臉和額頭上,以標準口音罵他「操你娘的蠢貨」。
潔玎從桌面彈起來,趕到他面前想要用拳頭打死他,同時心裡盤算著,這房間裡是否有撥火棒或花瓶或鋒利的大剪刀。他稍微轉過頭去,但沒有舉起手來保護自己。所有他該做的他都做了:站起來,以他的身高,她並不能輕易碰到他的臉和頭部。她竭力伸手想要把他的眼白從眼睛撕出來。他捉住了她的手腕,使它們交疊擋在她眼前。她朝他的臉啐了一口口水,但口水落在他睡衣上那個字母C。腳上的金線拖鞋沒有用武之地,但無論如何,她還是踹了他一腳。他鬆開她的手腕,讓她轉過身去,以手臂將她從後面鉗住。他的下巴貼在她的髮絲上。
潔玎閉上眼睛,屈膝想逃。「你好臭,」她叫:「你是我這生嗅過最臭的。」
「噓,」他在她的髮絲中低吟,「不然就把你扔到窗外去。」
「范勒瑞安會殺掉你,你這猿人。席尼會把你碎屍萬段……」
「不,他們不會。」
「你要是強暴我的話,他們會拿你去餵短吻鱷。走著瞧吧,黑鬼。你死到臨頭了。」
「強暴你?為什麼你們這些小白妞總是覺得別人想強暴你?」
「白妞?」她既憤怒又震驚。「我不是……你明知道我不是白人!」
「是嗎?那為什麼你不好好靜下來,別再掙扎?」
「天呀,」她吼著。「啊,我的天呀,你還是把我扔出窗外好了,因為你一旦放開我,我就會立即殺掉你。只因為你這樣說,就是這點,他媽的在胡說一堆黑妞白妞的。
你先前所說的,是如何的討厭和低劣,我都無所謂,但不要以為你可以在這邊向我說教,告訴我一個黑人女人該做什麼,我就會放過你……」
「我就是要告訴你。」他的臉頰挨近她的頭髮,她仍在他懷中掙扎著。
「你住口!你這赤腳的醜狒狒!你以為你是黑人就可以來這裡教訓我嗎?席尼說得對。他早該一槍斃了你。但他沒有。作為一個白人,他認為你也是人類,應該以人道的方式對待你。他是文明人,可是卻誤以為你也是文明的。那只因為他沒有嗅到你這體味。但我嗅到了,我知道你是頭野獸。」
他的下巴在她頭上來回摩擦,呼了一小口氣進她的耳朵裡。「我也嗅到你。」他說,用力把腰按到她那馬德拉裙子(Madeira skirt)的淡色圖案上。「我也嗅到你。」
他的聲音很輕柔,伴著清晰的呼吸聲,使她覺得好像是來自很高的地方。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比天花板和阿開木樹還要高,這使她害怕。「放開我,」她說,語氣冷靜得連她自己都有點驚訝,更驚訝的是他真的放開了她。
「你以前是模特兒?」他瞇著眼好奇地問。潔玎走向一個大藤箱。她的腳步離開克洛斯特地毯,金線拖鞋在瓷磚上發出啪嗒、啪嗒的聲音。她翻了好一陣子,才終於從箱子裡翻出一本時裝雜誌,封面上印著她的照片。她把雜誌遞給他,他在書桌前坐下,從齒縫間吹出一聲口哨。然後,在他的目光從她頭部開始掃視,一直遊走到那(或多或少)由銀色束衣承托著的六公分長的乳溝時,他又吹了另一聲口哨。照片裡她的秀髮熨貼地全往後梳,露出了她整齊的髮線。她的眼睛是貂皮的咖啡色,雙唇濕潤而微張。他繼續一邊吹著口哨,一邊翻開雜誌。匆匆翻了好幾頁後,...
作者序
前言
我要不就耳朵貼近收音機,近到要別人大吼,叫我離開點,免得聽力永遠受損。要不我就雙腿交叉坐在油布地板上,用嘴呼吸,出神地看著大人說故事時真情流露的眼睛。所有故事對我而言,都是從聽開始的。當我讀的時候,我在聽。當我寫的時候,我在聽。聽寂靜,聽音調的變化,聽節奏,聽暫停。然後就會有影像躍入腦海裡,我必須發明東西的畫面─一個穿著結婚禮服沒有頭的新娘、砍伐清理過的森林,並且表演「嘰!鋸子掃過!」加上一些動作,還有抑揚頓挫的音調,「老傢伙西門.嘰里咖堤,你來抓抓抓我呀!」我要用所有的東西─聲音、影像、表演來完整表達故事的意義,因為我很可能為了討大人高興,還要講第二遍,他們對我的批評是非常嚴厲的。
很久很久以前有個農夫,他為自己開闢了一個果園……
他們等著,我媽媽笑著等著,可是我最想講給外婆聽,讓她開心。
一想到外婆,就想到好吃的東西,獨一無二的關注、好玩,或是充滿愛的嚴厲這些特色,讓我們對外婆增加許多甜蜜的回憶。不管是真的,還是在時間與失去構成的銀幕上,當祖孫畫面出現時,都讓我們覺得溫暖又滿足。我和外婆之間也是如糖似蜜,這種滿足感深刻到我不願意和別人分享我與外婆之間的親密關係。我像一個貪心的小孩一樣,把耳朵貼到離收音機近到不能再近的地方,我只要一個人聽收音機。小時候外婆講故事給我們聽,讓我們可以繼續做一些百無聊賴又很煩人的事,像從一籃籃的野葡萄中,挑出那些被壓扁的,讓我們的腦袋忘記天花或傷口的疼痛,或是把沉寂陰暗的世界打開,露出一個被蠱惑的世界。
我不是外婆最喜歡的孫女,但沒關係,因為她是我最喜歡的外婆。我看她把豬油切成像餅乾一塊一塊的,我看見我的手被她牽著跳舞,我聞到她在春天給我們的糖匙中滴入松節油的味道。她為我和姊姊各縫了兩件學校制服,那是加了白領的蘇格蘭格子花,她還有一次也幫我們做了小女孩穿的套裝。最重要的是,當她玩數數時,她要─只有她要─拿我的夢來分析。我的夢對外婆很重要,所以我回想著我的夢,把它們變成故事;像外婆的故事一樣,我的故事也需要有人來解釋。
很久很久以前的這個農夫,他為自己開闢了一個果園……
嗯,很好笑,很可怕,然後還是很好笑,但卻令人搞不懂。從某個角度來看,黑寶貝(註:Tar Baby,原是一個用來稱呼美國黑人和毛利人的輕蔑語,以「黑油覆身的小孩」為比喻,表示黑人的存在有如殘渣和廢物。但是一方面,瀝青在凝結了碎石之後又是修築道路與橋梁不可或缺的原料,摩里森借用此語是為了表達一種文化融合的期許,全文以「黑寶貝」一詞替代。)故事所提供的說明,遠遠超過所謂「逍遙法外的農夫用機智與狡猾打敗了具有創造力的主人」。為什麼兔子想吃越多越好的萵苣菜和甘藍菜?為什麼農夫一定要阻止兔子?這些原因其實很清楚,可是為什麼要用一個黑寶貝呢?為什麼我聽到這個版本的黑寶貝是穿著女生的衣服?難道是因為農夫太瞭解兔子了,以至於可以引起牠的好奇心?可是兔子卻一點都不好奇,輕輕鬆鬆地繞過了黑寶貝,向她打招呼,「您早呀!」農夫因為自己被忽略,黑寶貝也被輕忽,因此不高興,甚至大怒,他先威脅兔子,然後要打兔子。現在農夫變得很愚蠢,如果兔子其中一個爪子堅立不搖,牠為什麼還要試另一個呢?這個聰明的農夫明明已經成功了,可是卻陷入處罰中,他原來非常暸解兔子的動機,現在似乎完全弄錯了。愚蠢的兔子現在也變聰明了,牠假裝自己最害怕的處罰就是被放回原來的地方,牠知道農夫認為放回牢籠中是最可怕的折磨,比死還可怕,所以農夫很粗野地、很開心地把兔子丟回遍佈荊棘的小徑中。黑寶貝已毫無用處,卻還是故事中奇怪且沒有聲音的中心,也是夾黏在主人與農夫之間的中介,農莊主人與奴隸之間的中介。黑寶貝被農夫創造出來當成陷阱以誘騙兔子,將把戲變成藝術,這主要的關係不僅限於農夫與兔子之間,也發生在兔子與黑寶貝之間。黑寶貝想要誘惑兔子,兔子知道。牠想要解困,卻越陷越深。這是愛的故事囉!真難搞,沒有反應、充滿誘惑力的女人,和聰明亂搞的男人,彼此對獨立與家庭、安全與危險,有著完全相反的定義。這本小說開始的第一句話,「他相信他是安全的」,就點出了這個衝突,「相信」而不是「認為」,像郵戳一樣表明他的懷疑,暗示他的不安。
然而,那卻是瀝青的形象,一個很有藝術感的造型、黝黑,讓人騷動,充滿了威脅感,卻又充滿誘惑的力量,把我引向非洲面具。古老、充滿生命力的,像呼吸一般,誇大的面部特徵,充滿神祕的力量。這個在傳說中喧擾的黑寶貝塑像,變成小說敘述的骨幹,所有的角色都是面具,如同非洲的面具。這本小說揉合了原始與當代的愛情與現實,這個混雜證明是令人飄飄然的,甚至暈頭轉向的。但我相信這本小說中豐富又令人熟悉的情節足以擋住讀者的暈眩,若能如此,那原來的故事就可以獲得了新生,這樣就又把我帶回到童年的油布地板上,傾聽外婆、阿姨們說著、唱著過去被埋葬的歷史,刺痛人心的真相,那個我出生、養育我的、讓人神迷心竅的世界。
他們說她要死了,因為血液中的蛋白,一個來看病的醫生說,絕對不能吃蛋白,這就是診斷與處方,一碗不會煮錯的藥湯,對上帝意志的信心,還有認為疾病是由食物造成的信念。(她的一個女兒死於十八歲,或者因為坐在濕濕的草堆上,讓子宮受了涼,或者因為前天晚上吃的黑莓水果餅,總之,當我外婆醒過來時,發現她可愛的寶貝女兒躺在她身旁,就像霜一般的冷。)不管怎樣,我外婆的身體變得很差,誰有空誰就得照顧她。有一天我被叫進她房內為她朗讀,大人想唸《聖經》來安慰她,我也很嚴肅地唸,卻一個字都看不懂。其實我更想為她說故事,讓她開心,甚至把病治好,或者把我做過的夢再說一次給她聽,可是和《聖經》比起來,這些顯得多麼微不足道呀!她不出聲地在被單下顫動,我認為她想要跑掉,從我這個白癡孫女身旁走開,顯然我被嚇住了,不能好好讀《聖經》。或者她只是想死掉,離開這一切,不幹了。她和先生輪流在孩子家住下,雖然她兩個女兒都很歡迎她,也很盡心盡力地照顧她,可是她和先生還是一樣無家可歸,一張床換過一張床,沒有一張是他們的。這種流浪即使不覺得羞辱,想必也會讓他們有居無定所的感受。那時候我還在想,多可愛的生活呀!在小鎮鄰居間漫遊,不時造訪家人,可是看她拿著床單走來走去,在枕頭上搖頭晃腦地翻來翻去,我就不再這麼想了!當然她生病了,還有蛋白……但她不能死,她也不想死。幾天之後,當他們告訴我外婆死了,我想沒有人會要我的夢了,也沒有人會堅持要我說故事了。
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
我們四個在房裡,我、我媽、我外婆,還有我曾外婆。最老的是最沒節制的,滿腦子艱深得讓人害怕的智慧,最小的我像海綿,我媽則是充滿了才華、喜歡社交應酬,但也為洞見所苦。而我外婆是我的祕密寶貝,她的出現讓這個令人害怕且被蠱惑的世界得以穩定了下來,三個女人和一個從來沒停下來過的小女孩,我不斷地聽,不停地看,尋求她們的教導,熱中於她們的讚美,對我們家族四代女人而言,《黑寶貝》的寫作可以視為見證,挑戰、判斷故事的用處,還有說故事的方法。
可是其中只有一位曾經向我要過我的夢。
前言
我要不就耳朵貼近收音機,近到要別人大吼,叫我離開點,免得聽力永遠受損。要不我就雙腿交叉坐在油布地板上,用嘴呼吸,出神地看著大人說故事時真情流露的眼睛。所有故事對我而言,都是從聽開始的。當我讀的時候,我在聽。當我寫的時候,我在聽。聽寂靜,聽音調的變化,聽節奏,聽暫停。然後就會有影像躍入腦海裡,我必須發明東西的畫面─一個穿著結婚禮服沒有頭的新娘、砍伐清理過的森林,並且表演「嘰!鋸子掃過!」加上一些動作,還有抑揚頓挫的音調,「老傢伙西門.嘰里咖堤,你來抓抓抓我呀!」我要用所有的東西─聲音、影像、...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6收藏
6收藏

 11二手徵求有驚喜
11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