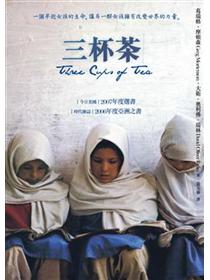每當我看到竹子的時候,就回想起家鄉,好像家鄉的情景,就在眼前。我的家鄉在宜蘭,住的是三合院,四周都是茂密的竹林。微風吹襲的時候,在竹子底下納涼、敘懷心事、拉胡琴唱歌,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這一張畫是小學五年級下學期時畫的,我先用蠟筆畫上星星月亮,當時其實也不知道怎麼畫,就是把水這樣倒上去,用蠟筆點點點地先畫月亮、星星,再加上一些留白……。在這個竹林底下,鄉村裡面的人聚在一起,聊聊天、唱唱歌,當時很習慣把二胡拿來做為樂器,一邊拉二胡、一邊歌唱,加上用竹子「扣扣扣」的,一邊打拍子,一邊伴奏。我從小在這樣的觀察、薰陶之下,還是小學就想畫他們拉二胡的情況。不過當時實力不夠,要畫又畫不像,只是一直塗啊塗的,塗了又改、塗了又改,塗到最後終於把二胡琴師心裡的感覺,也就是他所要敘述的感覺畫出來。
以前,在台灣的夏天晚上常有拉二胡、唱歌的情景,當時很常唱的其中一首就是「丟丟銅」,我畫這個主題就是想要把聲音的感覺,呈現出來。當時另外一首民謠「天黑黑」,也是我們常唱的歌,也成了我畫畫的主題,我用簡單的線條、誇張的造形來描繪歌裡面的農夫臉部、嘴型、他頭上的斗笠等等。(歌)
台灣話講「吹狗鑼」,也就是狗「嗚……」地像嗚咽的長鳴。民間傳說「吹狗鑼」是不好的,是狗看見了地下靈魂或是吠叫地下靈魂的聲音,所以「吹狗鑼」的畫面裡有靈魂的出現,可能是光或是鬼火,我用白色來表示。
這張是初中以後到北師畫的,大約是在一九五七或五八年。那時我常在北師的正對面,也就是和平東路的丁字路口前面的小市場寫生。北師的文風很好,學生很用功,常有女孩子喜歡靠在禮堂舊式的紅色石磚上看書。這畫中的女孩子靠著紅色石磚,拿著一本書在閱讀,當時光線從石磚這樣照射過來,在黃昏的時候感覺很好,令我忍不住的再看她幾眼,想要畫出這種味道。她的頭髮整個流瀉下來,我想畫出那種少女的味道。當時,無關情愛的,我就是這樣一直不斷的畫。
這張畫的是海邊的釣影,比較是用中國的水墨方式來畫的。台灣常有颱風,烏雲整片籠罩下來,但旁邊還留了光,暗示的意義就像台灣有句話說的:「西北雨落未濕土,落未過岸……」。
差不多在六九年左右,我都是來來去去的,七○年以後大部分時間就都留在西班牙了。當時為什麼去那邊呢,是因為對西班牙三大傑的憧憬,還有因為受到達利的吸引。我對這種人性生命的誇張,這種愛、慾融合的呈現,特別想去勾畫。在畫女性的時候,例如這張,我是用毛筆來畫,但用的是鉛筆素描的方式來表現,我覺得這樣應該會有種特別的味道。像這種鉛筆的筆觸,事實上是用毛筆畫的。而用毛筆來畫,有些鉛筆沒有的特性,毛筆能夠表現出來,更能把女性真正的味道很柔和的呈現出來。而這也是畢卡索不足的地方。我想要表現他的不足,必須先要了解他的東西,所以我把這種對女性的歌頌,先畫得有點畢卡索的味道。
大約八○年左右,我到了巴黎,停留在南部海邊。那邊的海水海浪,還有那邊美女的熱情,和西班牙的熱情是不一樣的,比較多了點含蓄的味道。這種情感,很真,但是不大容易呈現。在這個時期,我做的差不多都是類似這個作品。色彩,大部分是單純而強烈的,我用顏色來描寫法國海邊的動物和人的造形,強調法國的這種海邊、這種味道。
一九八八年左右,我決定來到紐約,當時大約是在八八年的九月、十月左右。到了以後,看到那年的雪地,整片雪冰冰的大地,讓我想要把冰雪對於生命的影響呈現在畫布上,所以我決定做「凍動系列」,我想要表現的是,一個生命,經過冰天雪地的「凍」,然後再動起來,再靜的循環。而在動靜之間所呈現出來的這種生命的真諦,也讓我體會到,生命的延續。在這個系列裡面,我特別注意到這個生命相關於《易經》與中醫命脈的生老病死。這個系列的呈現不只是單一媒材的,我做了各種的呈現。
「60.64.2000」的創作靈感來源,事實上是起自於我居所附近的海邊。我每天到那裡觀察海海浪的起落、日出日落,想起我家傳的中國《易經》易理的變化。當我得到這個創作起源時,我先想到的第一個概念,就是六十。六十是什麼呢?六十在中國裡面指的是一「甲子」,每一個甲子、每一個時空,都有它的代表性。這個甲子,說明的是時間,我用繩索來表示一個甲子的輪迴,從起點到終點,用繩圈來表示生命的輪迴。但是每個甲子又都是不同的,又有很多的變化,我想到了用中國的藥材來說明這個變化,因為中國的藥材和我們的生命是脫離不了的,跟大地也脫離不了。每一個甲子、每一個繩子用的藥草,都是不同的藥草,裡面敘述了不同的生命,也敘述了不同的萬象的變化。
六十四,就是六十四卦,每一卦都說明著不同的意象,說明著不同的命運,說明著不同的生命。這個六十四卦,沒有辦法脫離自然,沒有辦法脫離生命,但是在這種生命跟自然當中,具有著萬象更新、最具生命的力量,同時也是最吉祥的顯現,也就是我所取的這個泰卦,也就是天地。泰卦裡面,事實上就是乾坤的組合,乾三爻、坤六段,把六段呈現在上、三爻呈現在下,表示乾三爻由天而呼應地,坤六段由地而生天,而這種氣與運的交會,也就是白天與晚上的這種交會所產生的這種氣、這種力量。人無法脫離天地生活,在這個生命之中,如何讓它茁壯,同時又能吉祥如意,我即是用泰卦來表現。
二○○○年對整個宇宙、萬物都會產生很大的變化,那麼要用什麼東西把它表現出來,讓一般人最能夠了解?我想,這和海浪的起落、和大自然的變化絕對不能脫離關係。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木頭,但這木頭裡面要能表現長年歲月的累積,所以必須用巨大且歲數很大的一個木頭。從這個想法開始,我就去找木頭、踞木頭、砍木頭,先簡單的把木頭砍出一個龍的造形,但是要使它本身的生命跟大地生命形成交會。中國《易經》裡面特別強調的,就是生命,宇宙大地的力量,跟生命的長存,跟過去、現在、未來,都是延續不斷的。除了我的手工雕刻之外,還要藉著海水的力量,讓它自然浮升、化生出來。所以我把這個木頭泡在海邊數年,每一年都會有一些寄生的生命、無數的卵子,寄存在這個木頭裡面,依時乾枯、重生、孕育、消失。這件作品經過八年海水的沖洗、腐蝕,以及大地的造化,除了我之外,事實上是藉著大地的力量來共創了它的生命。
為什麼要放置枇杷葉在這個「60.64.2000」裝置上面呢?枇杷葉,事實上是一種很普通但很重要的中國藥草,而在金龍年誕生的時候,金會生水,水太多會產生人體呼吸系統的問題,而枇杷葉就具有這個作用。此外枇杷葉還有另一個特性,有就是它的香味,而這種香味具有驅邪的作用。所以,枇杷葉在金龍年所產生呼吸系統問題的時候佔有很重要的一個治理身體健康的最大作用,是這件裝置作品不能缺少的元素。這個龍脈靈象裡面,地上三角形的這個黑,指的是《易經》上的陰;牆上的六十卦後面的白,指的則是《易經》上的陽。用黑白對照,在色彩學裡面,黑可以把所有的色彩都吸收進去,白可以把所有的色彩都反射回來,也可以跟中國《易經》陰陽結合,來說明生命的反射與生命的蘊藏與再生。牆上的三角形,代表著三個不同的山,即太宗山、太祖山、父母山。易象的三角形的黑,又代表著天、地、人的結合,這個天地人的結合,跟太宗山、太祖山、父母山山氣的呼應,能夠產生龍脈流向的氣,使每一個人,都能夠感受到這個氣的蘊生以及吉祥。
這三個圓代表天、人、地,而在每一個圓裡面,為什麼又有三個小圓?這三個小圓,就代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天人地交會情況之下,跟大地的呼應寧靜,所以我就用了鏡子。當人站在鏡子前面,跟左右環境的互動的一種照射,也代表了我們的民心所反射出來的,所以我用鏡子。當我們走過龍脈流向的路程以後,也走過了三個不同的山,走向龍脈流向裡面最上上的一個位子,也就是結穴。我把羅盤放在這個最上上的位子,因為結穴可以讓我們體會到,最好的這種氣脈,也可以在羅盤裡面啟示我們各種不同的象。各種不同的象,就是各種不同的好運、壞運,包括人的身體、人的身體與氣候的關係、人的身體與風水的關係,在這裡面都可以得到解答。而最上上的這個結穴,可以啟示我們對未來的期望、對世界的期望,所以我用羅盤來說明、呈現。
我常跟家人到這個海邊來散步,在散步的當中常會看到很多無數的小生命被海浪沖上沙灘、又再被帶回去。在一次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裡面,我看到海龜帶著小孩要回到岸裡的家,牠在沙灘上走得非常的慢。但牠那種堅忍的愛、那種永遠不變的愛、那種刻苦耐勞、盡牠最大力量要把孩子帶回岸上的愛,雖然回到岸上的那一剎那那麼艱鉅,但是這種愛永遠是不變的。牠這樣的愛,觸發我把這個愛的真諦做成裝置,呈現給、分享給每一個人。所以,這個裝置就是要把牠的愛、牠受海水沖激、艱苦上岸的痛苦,以及追尋原來的生命再生的這種真諦,表現出來。
「四綠、五黃」是命理星象裡面的兩項組合,四綠象徵著樹木,五黃象徵著土地,土地要讓樹木長得茁壯,需要光合作用。我用四綠的綠色表現木,用五黃的黃色表現土,因為土木相生要能夠茂盛、能夠茁壯,需要有光、有水,所以把光和水也結合在四綠五黃的燈光呈現裡面,而光合作用,就用後面的燈光來強調出來,讓樹木在土上能長得非常的興盛。要把光表現出來,所以我在四綠五黃的箱子裡面,用燈光的陪襯,與目光飛躍相結合,來說明命相裡面的這種土木相生。
很多人問我說:「你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方式來畫?」這和我的中醫淵源也很深。幾代中醫抄藥譜、看病問診、開藥方,都是用毛筆,我因此對懷素的草書做過很深入的研究。懷素草書的氣脈運動,跟中醫裡面打脈的脈的啟動、氣的運轉息息相關,所以在我的用筆方面,已經跟傳統的用筆有很截然的不同,也就是把中國氣功行氣的用法表現出來。至於我的創新皴法,也和中醫診斷有關,我將現代工業顏料、壓克力顏料混合,畫的時候呈現出水、油脂組合以後的分裂,而這種分裂出來的皴法,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和中醫在診斷人身體病狀時血的流動、細胞的分化、人皮膚肌理血脈的乾濕變化,也有密切關連,這也反映在我所創新的皴法上面。
平時我很喜歡到海邊去走,一方面觀賞海景的變化、一方面看看有沒有喜歡的石頭。像這個石頭,它的造形也滿不錯的,事實上它裡面就有很多的語言,可以說它是一個修道的老人,也可以把它當做一個恐龍的頭。在海邊一看,覺得不錯,所以我就揀了回來。拿回來的石頭,我常常就隨意擺著,有時候放著一年,有時候兩年或更久,也有時候心血來潮,一拿回來我就馬上磨了。我磨石頭不會像一般一樣磨得很規矩、很平,而是盡量保持它原來造形的美。例如這個,多美啊,可以看出裡面的中國水墨的皴法,如披麻皴等等,甚至還有另外的皴法。我從這裡面得到很多,它含藏著很多的造形語言。我揀了石頭回來就是這樣,一方面磨,一方面沉思。
想透徹了以後我就開始刻了,我刻的刀法跟我畫畫一樣,和一般傳統是不大一樣的,我考慮的是要採取怎樣的氣氛,才能強調它的造形語言。當我在刻的時候,我會想到風水的問題,因為在這塊石頭上面,很自然就去注意了它石頭裡面的語言了。我在找石頭的同時,事實上就注意到了這個,因為石頭裡面有它的磁場,它所帶的靈性,再加上在某個時候它會自然與人交會對話,它用石頭的聲音來跟我講話,告訴我要跟我講些什麼東西。它要把它的生命呈現出什麼形貌,在磨的時候它就告訴我了,這是我和石頭中間的溝通,讓石頭上真正的生命被敘述出來、呈現出來。這還算是一種比較創新的刻法,所以不大講究傳統那種規規矩矩的格式。像這樣,即使還沒有刻好,但我大體上會先了解一下它的造形是什麼,讓石頭自己藉著我的手,自然形成它想要形成的樣子。像這個石頭,它已告訴我有一種一帆風順的形貌,在月亮當中表示一種很平靜的水,這個形就像一個帆布,在平靜的水中行萬里路。這個事實上就是一張畫了……。








 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