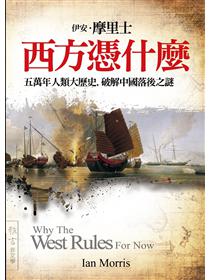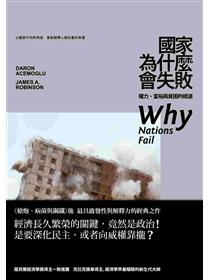中國正在崛起,成為世界強權,不過中國的崛起具有甚麼普世的意義,代表怎樣的歷史突破,仍然並不明朗,更為周邊國家所憂慮。在中文世界內外,關於中國崛起的討論連篇纍牘,但是有一些議題、一些觀察角度似乎乏人問津。本期《思想》有三組文章涉及中國,呈現的正是這類較受忽視的視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色、中國當代國家主義思潮的喧騰、以及中國的左派「反對派」在這個「新時期」如何自處。
章節試閱
兩場革命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章永樂、葉蕤譯
如果說20世紀受俄國革命的軌跡主導的程度超過了任何其他單一事件,那麼21世紀的形貌便將由中國革命的後果所塑造。蘇維埃國家,這個一戰的產兒,二戰的勝利者,於第三次的冷戰中被擊敗,問世70年之後在幾乎未發一顆子彈的狀況下解體,迅速得如同它當初突然出現。現存的俄羅斯,面積小於啓蒙時代所知的俄國,人口不及原蘇聯的一半,而且與沙俄末日相較,如今重建起的資本主義更加依賴原材料出口。即使不排除未來發生逆轉的可能性,至少目前看來,無論怎樣積極評價,十月革命的遺存都十分有限。其最為深遠巨大的成就,是在消極意義上:蘇聯的確擊敗了納粹,這是任何其他歐洲政權都無法與之比擬的。這一點,無論如何都是今天普遍接受的結論。
而中國革命的後果卻提供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對照。在進入第七個10年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世界經濟的一架引擎,對歐洲、日本、美國三地同為最大的出口國,在世界上持有最多外匯儲備,也是有史以來,最大數量的人口在四分之一世紀中保持最快人均收入增長率的國家。其大城市在商業和建築領域有著無可匹敵的雄心,其商品無處不售。它的建設商、探礦者以及外交官為尋求更多的機會和更大的影響力而遊走全球。無論是昔日的敵人還是朋友,此刻都在獻殷勤;這個「中央之國」在其歷史上首次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強權,影響及於所有大洲。關於前蘇聯解體,關於其所標誌的整個局勢的轉折,「共產主義的失敗」成為無出其右的最經典表述。可是20年之後,這個封號看起來有點歐洲中心。從某種眼光來看,共產主義不但仍然存在,而且還成了這個時代的成功範例(譯者注1)。不消說,在這一成就的特質與規模中,有著不止一處令人不快的反諷。但是談到革命在中國與俄國的命運之不同,則是毋庸置疑的。
如何解釋這一對照呢?這個問題儘管有著世界-歷史意義上的重要份量,卻從來沒有被充分討論過。當然,其中關鍵不僅僅是要比較兩次極為相似卻又各有特色的大動盪,比如曾為人熟稔的1789年法國大革命與1917年俄國革命之比較,被考察的兩者在各自不同背景下並沒有其他關聯。而中國革命則直接發源於俄國革命,並且一直與後者緊密相連,從中獲取啓發或教訓,直至二者在1980年代末同時到了見真章的時刻。這兩場革命的歷史經驗並非相互獨立,而是構成了自覺的連續演進1。無論怎樣考察中俄革命的不同後果,二者的關聯都必然要進入視野。而要解釋這些問題,又需要進一步在若干層面上進行反思。本文將分疏其中的四個層面。第一,這兩場革命的政治動力——即兩國各自的政黨,及其各自所採用的戰略——從其主觀意識上講,在多大程度上相異?第二,當兩個掌權的政黨各自開始實施改革時,它們的客觀出發點——包括社會經濟條件以及其他條件——是什麼?第三,兩個政黨各自採納政策的實際效果如何?第四,哪些來自於兩個社會各自漫長歷史進程中的成份,可以被視為是導致了兩場革命及其改革最終結局的內在決定性因素?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仍健在而蘇聯已消失,而且前者的未來似乎也是國際政治面臨的中心困擾,本文結構上將以中國為中心,以俄國為其投影之鏡鑑——俄國並不是唯一相關的鏡鑑,但卻是其他鏡鑑難以迴避的條件,這一點很快就會得以明確。
一、革命的孕育
眾所周知,十月革命是一場極為迅疾的城市起義,僅僅數天就在俄羅斯那些重要城市中成功奪權。十月革命推翻臨時政府的速度與領導革命成功的政黨集結成型的速度恰相匹配。在尼古拉二世退位前夕的1917年1月還只有不超過兩萬四千名黨員的布爾什維克,9個月後傾覆克倫斯基政權時,已經迅速壯大到20多萬人的規模。他們的社會基礎在於年輕的俄羅斯工人階級,而這個階級在全俄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尚不足3%。他們在農村毫無影響,那是超過80% 的俄羅斯人民生活的地方;他們也從來沒有想過要把農民組織起來——至少沒有比社會革命黨做得更多,而後者1917年曾得到農村廣泛的雲集響應。俄國革命僅憑如此單薄的支持力量便迅速獲得勝利,完全是因為一戰中慘敗於德國人的沙俄政權已筋疲力盡:軍事失利引發叛亂,瓦解了沙皇在國內的鎮壓體制,而二月革命也只留下了一個猶如搖搖欲墜的棚屋一般的繼任政權。
然而事實證明,如果權力在這樣的真空中被輕而易舉地奪取,那麼它一定很難維持。大片俄國領土被德國人占領。而當德國本身於1918年落敗時,十個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塞爾維亞、芬蘭、羅馬尼亞、土耳其、希臘、法國,以及日本——分別派出遠征軍前來支持白軍,企圖摧毀新政權。這場艱苦的內戰一直持續到1920年。當戰爭最終結束時,先後經歷了世界大戰和內戰的俄國已是滿目瘡痍:鄉村裡,到處飢饉;城市中,工廠廢棄;工人階級被戰亂以及國家工業化的倒退所摧毀。列寧的政黨,其社會基礎或者被瓦解,或者已被吸收到新國家的結構中,成為孤懸於殘破不堪的廣袤國土之上的權力架構:其統治與內戰的悲慘聯繫在一起,而不再令人聯想到十月革命曾帶來和平與土地的厚禮。
十月革命以超絕努力造就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覆蓋了前沙俄帝國的大部分地區。但是,作為歷史上第一個拒絕以疆界為基礎來界定自己的現代國家,新生的蘇聯並未訴諸愛國主義的自豪感或是民族構建。其訴求是國際主義的:全世界勞工運動的團結一致。布爾什維克在一個巨大的落後國家——經濟幾乎都還是農業,而人口大多是文盲——取得了政權,苦於在這樣一個尚沒有任何完整的資本主義先決條件的社會裡堅持社會主義的激進承諾,曾指望歐洲更為發達、更工業化的國家發生革命,幫助他們脫困。這是個四面受困的執政者很快就輸掉的賭博,而且從一開始便對其治下的大眾沒有多大意義。既缺少國內支持,也無法從國外獲得援助,蘇維埃政黨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一切可能情況下盡快實現向另一種社會形態的轉變。
雖然起源於俄國革命的感召,中國革命卻改寫了幾乎所有俄國革命的條件。成立於1921年的中國共產黨,4年後黨員仍然不足一千;此時她第一次開始成為一支重要力量,既受到中國沿海城市工人階級在1925年「五卅運動」中鬥爭精神大爆發的催生,又得益於至關重要的蘇聯顧問和孫中山領導下羽翼未豐的廣東國民黨政權的物質支援。從這一奠基時刻到中共奪取全國政權,橫亙著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鬥爭。其間的里程碑事件家喻戶曉:1926年的北伐戰爭,聯合了國共兩黨討伐主要的軍閥政權;蔣介石1927年在上海對共產黨人的大屠殺;隨後的白色恐怖;1931年成立的江西蘇維埃共和國,以及國民黨旨在將其鏟除的五次圍剿;1934-1935年間從江西到延安的紅軍長征,以及中共領導下西北邊區的創建;1937-1945年抗日戰爭時期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和統一戰線;還有1946-1949年的最後一場內戰,人民解放軍最終橫掃了整個中國。
將這一經驗與俄國的政權易幟區別開來的,不只是截然不同的時間向度。兩者的奪權方式也是迥異的。按照韋伯的著名公式,如果將國家定義為在確定疆域內對正當性暴力的壟斷,那麼革命就總是要打破這種壟斷,並出現列寧和托洛茨基曾稱之為雙重權力的局面。從邏輯上說,這種局面可以經由三種不同方式達成,各自與韋伯公式中的三個關鍵詞相對應。首先,革命可以用摧毀統治正當性來打破國家對權力的壟斷,造成國家無法使用強制手段來鎮壓反對它的運動。伊朗革命可以視為一個例證,這場革命並沒有發生戰鬥,王室倒台的時候,軍隊一直處於癱瘓狀態。另一種情況是,革命可以使用造反的暴力直接反抗國家暴力體制,在尚未獲得普遍正當性之前,就用一記毀滅性打擊將其徹底擊垮。這就是俄國革命的模式,這種模式只有在對手十分虛弱的情況下才可能成功。
最後,革命還可以在打破國家的權力壟斷時,既不是從根本上剝奪其正當性,也不是暴風驟雨般地解除其武裝力量,而是通過蠶食足夠多的領土來建立一個對立政權,如此一來,它遲早會腐蝕掉國家所占有的勢力和人民的認可。這是中國革命的模式。這並非中國所獨有,而是游擊力量奪取政權的一般路徑,南斯拉夫和古巴的革命者也是這麼做的。中國情況的獨特之處不在於革命在國家內部相繼建立的一系列「反叛政權」,而在於他們交相延續的長久。需要解釋的,正是這種持續性所依託的條件。
在世紀之交,羅曼諾夫王朝無論有多麼孱弱,都無可比擬地大大強於清王朝:作為本土的固有體制,能夠為其所用的不但有若干發達工業的基地與豐富的自然資源,更有龐大的軍隊以及深厚的愛國主義忠誠——這是來源於俄國對拿破崙的勝利。在遠東,俄國在蠶食中華帝國的歐洲列強中最為貪婪。只是因為戰爭中先後面對日本和德國的兩次嚴重潰敗,才引爆了反對羅曼諾夫王朝的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而清王朝則與此不同,早在19世紀中葉就因被看作是外來政權而遭到憎恨,很快又因貪腐到淪為西方列強的附庸而受唾棄。太平天國起義之後,清王朝從來沒能重新獲得對全國各地武力的中央控制。清政府已經變得如此虛弱,以致於1911年,在沒有遭遇到任何協調一致的反抗運動的情況下便轟然倒塌。後續政權沒有一個能夠達到韋伯公式裡的國家標準。中華民國先是分化為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後來又發展為以南京為基礎的混合政權,其中國民黨控制著圍繞長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帶,各地軍人政權分掌周邊地區:蔣介石從來沒有控制過中國傳統上18個省區的一半以上,通常連一半都不到。
正是在這諸多權力中心相爭鬥的迷宮裡,中共才有可能在不同管轄權的夾縫中落腳,並建立起具有機動性的反抗力量。但是,儘管中共從未像布爾什維克那樣,與一個統一的國家機器正面對抗,它的對手卻更難對付,失敗的風險也更高。國民黨政權雖然被局限在由其牢固掌控的戰略要地範圍內,但直到壽終正寢,它都既不是一種絕對主義統治,也不是虛有其名的過渡政府。國民黨和共產黨是與其時代共生的對抗者,它們以相同的組織形式組建而成:這是同等現代的對手,企圖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掌握中國。不過,國民黨有著遠為強大的軍隊,配備有重型裝甲,並在一系列培訓與戰事中受到過德國軍事精銳——馮‧塞克特(Von Seeckt)將軍和馮‧法肯豪森(Von Falkenhausen)將軍——的調教。同時,國民黨還坐擁中國最富庶地區的稅收。假若日本沒有在1937年對南京政府發起全面攻擊的話,則無論長征曾體現出何等的英雄主義,國民黨也一定早在1930年代末就把共產黨掃蕩殆盡了。
在日本入侵造成的緊急狀態中,蔣介石——錯失了他的獵物,卻仍然執著相信共產主義是更大的危險——證明了他抵抗外來侵略者時的無能為力。這位日本軍方的長期合作者——他策劃1927年上海清黨大屠殺時即與日方合作,並曾於事後不久飛往東京與日軍總參謀部簽署一項協議——本來已默認了日本對滿洲的占領,如今只能退守內陸;珍珠港事件後,他更想著坐等美國去贏得戰爭的最後勝利,以便他能用毫髮無損的嫡系部隊繼續對付共產黨。然而,日本1944年在中國發動最後的「一號會戰」(譯者注2),將國民黨的精銳師團重創到難以重建的地步,讓蔣介石的如意算盤落了空。因為拒絕全力抗日衛國,蔣介石獨裁統治所招致的名譽損失不在軍事失利之下。
在國民黨控制與日軍深入的範圍之外,中共則以偏僻的延安邊區根據地為依託,在整個華北展開了日益卓有成效的抗日游擊戰。中共力量的壯大是因為它能夠有效地將農村改革——減租減息,免除債務,有限度的土地再分配——與抵抗外敵相結合。這兩者的結合在占總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階級中,帶來不斷擴大的群眾基礎,為中共提供了俄國共產黨從未獲得過的深厚社會根基。在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間,中共黨員人數從4萬增長到120萬,軍隊從9萬成長為90萬大軍的規模。一旦日本投降,中共撒下的火種就在華北平原發展為燎原之勢:到1947年內戰再次爆發之際,中共黨員人數又翻了一倍多,達到270萬人的規模。與此同時,在中部與南方的國統區,猖狂的腐敗與通貨膨脹摧毀了都市對蔣介石政權的支持;士氣低落的國民黨軍隊儘管擁有美械裝備,仍然不是人民解放軍的對手。隨著解放軍向南方挺進,越來越多的國民黨將領選擇投誠或倒戈: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幾乎沒有用到一槍一炮,中國的大城市一個接一個地從他們手中失落。
俄國的內戰發生於革命之後。就像是對革命的報應,內戰讓俄國陷入了比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之前還要糟糕的境況。而在中國,革命結束了內戰,其立竿見影的效果彷彿是一種救贖。在超過百年的歲月裡,中國還沒有看到過一個能夠對外抵禦列強侵略、對內維持全國秩序的中央政府。共產黨卻同時帶來了國家獨立和國內和平。隨著國民黨的潰敗,美國軍官、英國砲艦、日本滯留人員,全都被迫捲鋪蓋走人了。人民解放軍的勝利,遠沒有對經濟和社會造成巨大破壞,反倒帶來了復甦和穩定。通貨膨脹得到控制,腐敗被消除,各種供給也恢復了。在鄉村,地主被打倒;在城市,並沒有大規模徵用的必要,因為超過三分之二的工業在國民黨治下就屬於國有,而買辦資本已逃往香港或台灣。中產階級在國民黨統治末期早已離心離德,以致於共產黨到來時,許多人非但沒有抵抗,反倒終於鬆了一口氣。隨著生產的恢復,工人回復正常就業,重又領取薪金。體現著愛國主義理想和社會風紀的人民共和國,在其誕生之際,就贏得了蘇聯從未奢求過的大眾支持度。
兩場革命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章永樂、葉蕤譯
如果說20世紀受俄國革命的軌跡主導的程度超過了任何其他單一事件,那麼21世紀的形貌便將由中國革命的後果所塑造。蘇維埃國家,這個一戰的產兒,二戰的勝利者,於第三次的冷戰中被擊敗,問世70年之後在幾乎未發一顆子彈的狀況下解體,迅速得如同它當初突然出現。現存的俄羅斯,面積小於啓蒙時代所知的俄國,人口不及原蘇聯的一半,而且與沙俄末日相較,如今重建起的資本主義更加依賴原材料出口。即使不排除未來發生逆轉的可能性,至少目前看來,無論怎樣積極評價,十月革命的遺存都...
作者序
致讀者
中國正在崛起,成為世界強權,不過中國的崛起具有甚麼普世的意義,代表怎樣的歷史突破,仍然並不明朗,更為周邊國家所憂慮。在中文世界內外,關於中國崛起的討論連篇纍牘,但是有一些議題、一些觀察角度似乎乏人問津。本期《思想》有三組文章涉及中國,呈現的正是這類較受忽視的視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色、中國當代國家主義思潮的喧騰、以及中國的左派「反對派」在這個「新時期」如何自處。
佩里‧安德森的〈兩場革命〉一文,從西方左派的立場對比蘇聯與中國革命的環境、特質與命運。這種宏觀的、比較的歷史─政治分析,比起常見的中國「特殊道路」的論述,視野要更開闊。但是安德森對於中國崛起的理解,受到了吳玉山、王超華兩位的正面挑戰。他們對中國崛起的理解,在歷史詮釋與政治判斷兩方面,均與安德森大相逕庭,也對習見的中國模式論有所質疑。伊懋可教授對中國近代的「革命」,則提出了極為獨特的另一種觀點。這四位學者的論述與攻錯,值得我們研讀比對。
其次,許紀霖教授撰文檢討晚近中國知識界向國家主義輻輳匯流的現象,呈現了中國崛起所帶出來的新一輪思想糾葛。這種國家主義意識形態,貫穿了早先的左、中、右壁壘,統合了民族主義、革命專政與敵我分辨等駁雜成分,在中國知識界引發了巨大的能量。許紀霖的批評深入而有系統,相信會開啟新一波的爭論。對此問題關心的讀者,尚可以參考《思想》16期成慶先生〈當代中國「國家本位」思潮的興起〉一文。
第三,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有人逆流高舉文革的火炬,有人對於體制與政權發出高亢的批判,也有人高度支持民主、自由與人權。但是能集這三方面的訴求於一身者並不多見,袁庾華先生是一個突出的代表。無論他對於文革、毛澤東、改革開放體制、社會主義大民主等等的分析與評價是否服人,也無論今日「毛派」是不是歷史的錯置,但他的「234」要求涵蓋了民主、人權、以及社會保障,在今天的中國無疑是深有意義的。本期陳宜中先生對袁先生的專訪,適足以顯示中國崛起的方向與代價,即使在北京鄰省,也遠遠還不是「共識」。
把視野拉回台灣,本期發表顏厥安教授關於司法改革的「思想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澄清與質疑,對於「司法」是怎麼一回事作了深入系統的分析,然後再對「司法改革」提出方向性的建議。陳正國教授則針對前一期《思想》的死刑專輯討論(特別是陳瑞麟教授的文章),發展更根本的觀點。他把死刑議題從制度以及正義的考量拉到更根本的倫理層面,斷言「不可殺人」乃是無從考慮選項的絕對誡命,因此廢除死刑不是一種「價值選擇」,而只是服從道德誡命。這是一個大膽的建議,預設了人們對於道德誡命的妥當仍有共識。我們期待更進一步的爭辯。
今年年初葛兆光教授出版了《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大著,由於直接挑戰近年有關「中國」的各種新論述,廣受各方矚目。本期張隆溪教授的書評,不僅延伸了該書的問題意識脈絡,剖析該書的主旨,也發揮了他自己對「學術與一時代政治、歷史和思想環境之關聯」的「深切認識」。這篇書評針對性強而致意深遠,請讀者不要錯過。
致讀者
中國正在崛起,成為世界強權,不過中國的崛起具有甚麼普世的意義,代表怎樣的歷史突破,仍然並不明朗,更為周邊國家所憂慮。在中文世界內外,關於中國崛起的討論連篇纍牘,但是有一些議題、一些觀察角度似乎乏人問津。本期《思想》有三組文章涉及中國,呈現的正是這類較受忽視的視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色、中國當代國家主義思潮的喧騰、以及中國的左派「反對派」在這個「新時期」如何自處。
佩里‧安德森的〈兩場革命〉一文,從西方左派的立場對比蘇聯與中國革命的環境、特質與命運。這種宏觀的、比較的歷史─政治分析,比...
目錄
顏厥安 司法改革的幾個思想問題
廖美 凝視巴西
■思想訪談
陳宜中 永遠的造反派:袁庾華先生訪談錄
■中國知識界的國家主義誘惑
許紀霖 近十年來中國國家主義思潮之批判
高力克 「市場巨靈」的挑戰:關於中國經濟奇蹟的奧秘
■從世界革命到中國模式
佩里‧安德森 兩場革命 章永樂、葉蕤 譯
吳玉山 〈兩場革命〉與中國模式
王超華 以革命的名義?——評佩里‧安德森〈兩場革命〉
伊懋可 多重革命:讀佩里‧安德森〈兩場革命〉隨想 彭淮棟 譯
■思想評論
陳正國 死刑之不可能:一個簡單的倫理學觀點
胡昌智 「維基揭密」與歷史的時間
■思想評論
張隆溪 擲地有聲:評葛兆光新著《宅茲中國》
高華 讀王鼎鈞的《文學江湖》:冷戰年代一位讀書人的困窘和堅守
■思想采風
李琳 思考正義的三種進路:桑德爾談正義
陳瑋鴻 從歷史終結到秩序的開端:福山新著《政治秩序的諸種起源》
致讀者
顏厥安 司法改革的幾個思想問題
廖美 凝視巴西
■思想訪談
陳宜中 永遠的造反派:袁庾華先生訪談錄
■中國知識界的國家主義誘惑
許紀霖 近十年來中國國家主義思潮之批判
高力克 「市場巨靈」的挑戰:關於中國經濟奇蹟的奧秘
■從世界革命到中國模式
佩里‧安德森 兩場革命 章永樂、葉蕤 譯
吳玉山 〈兩場革命〉與中國模式
王超華 以革命的名義?——評佩里‧安德森〈兩場革命〉
伊懋可 多重革命:讀佩里‧安德森〈兩場革命〉隨想 彭淮棟 譯
■思想評論
陳正國 死刑之不可能:一個簡單的倫理學觀點
胡昌智 「維基揭密...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4收藏
4收藏

 6二手徵求有驚喜
6二手徵求有驚喜




 4收藏
4收藏

 6二手徵求有驚喜
6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