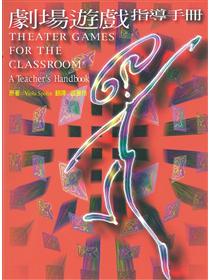十月的上海秋陽宜人,安福路四周的林蔭道邊儘是一個個小院子,裏面座落著頂叫北京人羡慕的那種低矮的樓房——主人憑著窄窄的陽台,常常能從旁邊兀立的十八層高樓(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看到難得的風景。比如十八日下午,香港藝人梁家輝從武康路的住地到藝術劇院彩排,出演香港話劇團《傾城之戀2005》范柳原一角。上海與香港的情迷上海和香港倒像是一根扁擔上的兩個籮筐,相互的需要平衡。這兩座城市對於中國經濟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其所孕育的文化形態和藝術氛圍也叫人著迷。圍繞著《傾》劇,從作者、改編者到導演,都有著生於上海、生活在香港的閱歷。兩個城市同為中國最早開埠繼而走上城市化進程、遭受現代化洗禮的大都市,上海十里洋場、繁華喧囂,香港詭秘陰森、東西混雜,兩個城市既有氣質上的相似,又有氣候與空間上的距離,遙生美感。處於此都市裡的人在領略了富庶的物質文明後,也最先與西方的文化相接觸,在他們的人格上留下痕跡。張愛玲擅長製造的是中西文明碰撞下的人物性格的衝突,只要這種文化的碰撞還在,她作品的號召力便長存,在此種背景下成長起來的都市眾生便不難從中感悟到劇中人與自己生命的意義相關。張氏筆下的女性多是既氣質高雅又獨立而有主見,男性則有著「洋派」的外表骨子裏又很中國化。
《傾》劇中的白流蘇要從大家庭中逃出來,欲對僵化的家長制作反抗,在英國長大的范柳原卻欣賞白是一個「地道的中國女人」使自己的心有了依託。上海雖然日新月異,卻仍然保留著它獨特韻味的亭子間,與那些整舊如舊的小洋樓相安無事,這使每一個回到上海的香港人多了一份故鄉的親切,也使新生的上海女作家自然地延續起這一傳統,在上海、香港兩個地方鋪敍她們的想像,又如王安憶的《香港的情與愛》若能在香港的舞台上演,那也會是一段佳話吧?《傾城之戀》被改成舞台劇是第幾次了?最早是1944年張愛玲親自操刀,在上海新光大戲院公演,連演了80場。
1987年香港話劇團首次搬演,至2002年又再度改編。香港的演藝圈中人張迷頗多,改編張氏小說為影視和舞台劇蔚然成風,許鞍華拍攝電影《傾城之戀》、《半生緣》,林奕華做多媒體話劇《半生緣》(今年年初曾來京演出),毛俊輝做音樂劇場《新傾城之戀》,前衛與主流劇場都相中了張氏。內地的這股熱潮也不減,各地電視台輪番播放各種版本的張劇,而在北京和上海,新生的小資群擁躉張,使她的小說故事大半耳熟能詳。主人翁多在上海和香港兩地遊走,對於今天的觀眾而言這也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這樣看來粵語版《傾城之戀》來滬演出倒顯得十分必然。明星的派之於舞台看到梁家輝從台後一走出來,上海觀眾馬上拍手。說來梁氏參演舞台劇不是初遭,2000年與劉嘉玲、黃秋生主演商業劇《煙雨紅船》,也是由毛俊輝執導。對比國內明星演舞台劇的排練時間大大縮水,導演經常要遷就演員的檔期,毛導直言梁等的時間約定好足夠,不受外界干擾。
「因為他們需要這麼長的時間來熟悉舞台,舞台是有技巧的,而且他們本來就是好演員,作為一個演員,對自己表演的造詣會是他一貫的追求。」不獨排練,演出還要佔據大量的時間,從今年8月到明年3月,梁要一直為《傾》劇效命,為此他要推掉多少的電影片約呢?不過這些對香港的明星沒構成太多障礙,他們都在努力的實踐著,受用的則是觀眾了。選中梁家輝是毛導的眼光,因為他的外型,這點倒是很合女觀眾的心理。確實,即便在時下的女生看來,范柳原依然是理想的「丈夫」人選,從商闊綽,眼界開闊,受西洋教育,有紳士風度,愛玩且風趣,屬於鑽石王老五類型,唯一的缺點是不專情。梁家輝曾因《情人》一片俘獲眾多少女的芳心,那算是法國女子對中國男人理想的投射,事隔多年仍然覺得從他身上來捕捉三○年代花花公子的風度最合適。
「然而並不是你在台上夠帥、多情、很投入、很真誠就可以了,」毛導強調,「范柳原不是那麼簡單,他有這些元素在裏面,但是還有角色的基調和動機。」為此,梁家輝著文到:「范柳原不是等閒可以得到的獎品;他的計算統統藏在心中;范愛上白,因為出身和成長的問題,范柳原看的中國,其實多少帶點外國人看中國人的獵奇成份:旗袍、京劇以及女性的溫柔(低頭)。
」有了這樣的準備,對梁家輝還有什麼不放心呢?由於梁的加入,飾演白流蘇一角的蘇玉華更被帶入佳境,得到「第一白流蘇」的讚譽,所謂對手戲就是給對方製造機會。說來有趣,香港的學者大都讚揚梁氏的表現,李歐梵教授說:「真是找對了人!
我心目中的范柳原就是他這個樣子:瀟灑之中還帶了一點機靈和狡詐。」不過香港的觀眾卻意見不一,除了指出梁的口白有「吃螺絲」以外,對於轉變前的范柳原是應該深情些還是輕佻些各持己見。世故喜劇和音樂劇說《傾城之戀》的風味取自美國三○年代好萊塢電影的「世故喜劇片」是李歐梵的看法,那也不奇怪,三○年代的上海以摩登著稱,張愛玲耳濡目染不說,且由於自己鍾愛服裝,不僅在作品中反覆描寫衣飾,生活中更以奇裝異服炫人,對於交際場上人們的穿著、言談及下面隱藏的動機,女作家洞若觀火,卻又在她的筆下注入同情,這是最為吸引毛導之處。然而隔了這麼多年,范柳二人的愛情角力是不是不再如原著那樣感傷——「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裏,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反而顯得有喜劇色彩呢?《傾》劇演出時不停的有笑聲,有的觀眾覺得很不該,比如梁打電話給白時,「我愛你」這麼嚴肅地表白怎麼可以笑呢?事實上今天我們仍與范處於同樣的心態倒不真實了,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笑呢?布萊希特說,我們被戲劇中的人物感動,這還不夠,要帶著陌生的眼光去看他,找到對事物根源的新解釋。戲劇在這裏不是鋪排張愛玲的思緒,它必須長出自身新鮮的觸角才會有其生命力。這觸角是指《新傾城之戀2005》的形式,即歌者和舞蹈的安排,它的好看全依託於此。
2002年,毛導為找到話劇與歌舞結合這樣的形式而興奮不已。歌者有點類似於西班牙明星班德拉斯在《庇隆夫人》裏的串場,有時是白流蘇的化身吐露心跡,有時是旁觀者對二人加以評述。沒有看過演出前很難想像歌者的效果,此回上海觀眾顯然是被劉雅麗所折服了,每當她唱完一曲退下時就發出由衷的掌聲。在這個戲裏,她是一個好歌手還不夠,還必須是一位好演員,她一舉手一抬足處處是戲,演唱與動作亦十分協調。比照國內很不成熟的音樂劇表演,香港對藝人訓練的功夫可見一斑。港味的歌舞我們能否接受呢?無礙,雖聽不太懂,音樂的氣氛足以統帥情緒。不過,此劇並非音樂劇,不過借用音樂劇的元素而已。在美國學習和工作多年的毛導雖擅長於音樂劇,卻沒有濫用。02版裏歌唱與舞蹈的成份多於05版,那時毛導剛剛確立了這種形式後來不及細調即住進病院2005年他重拾舊作予以濃縮,將歌舞集中到范柳的感情戲上,歌者每一次出現都是劇情的需要,而不是她演唱的需要。對比西方精彩的音樂劇,國內出產一種「音樂話劇」,往往是抱著吉他對著麥克風唱個許久,其實那只是音樂與話劇相混合的拼貼手法,還不懂得話劇與歌舞表演的結合。儘管與方言的距離阻擋了直接聽懂,還是聽得出我們所不熟悉的粵語經香港演員道來有一種韻律感,與粵語歌曲渾成一體。但是,在新添的尾聲裏,音樂上有一個與前面風格很出跳的音符,范柳原抱住白流蘇說「戰爭結束了我們就結婚」,觀眾還沉浸在二人的圓滿結局裏,黑場中突然響起《走進新時代》的歌聲,觀眾愣了一下才回過味來。用這首歌只是為了交待經過這麼長的時間,白流蘇老了回到了上海舊居白公館,然而老城區也都搬空了,房地產開發商催她搬家,白流蘇面臨著一次新的「傾城」。
傾斜的門框下,白流蘇換上旗袍端坐門前,喃喃說道「人走了,心跟著走,空了什麼都不想……」白坐的位置,正是劇中那個大大的畫框的中間,白家人嫌棄她離婚女的日子,與范柳原傾心相愛的日子都是在那個畫框中發生的,隨著舊房子一起走掉了,現實的我們不仍然也是對自己同樣的「做不了主」麼?張愛玲那拉過來又拉過去的胡琴的咿咿呀呀感歎的或許就是這份無奈吧,對舊物的情懷支撐著我們活在當下,城傾而人不倒,舞台劇的象徵意味更勝於小說。








 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