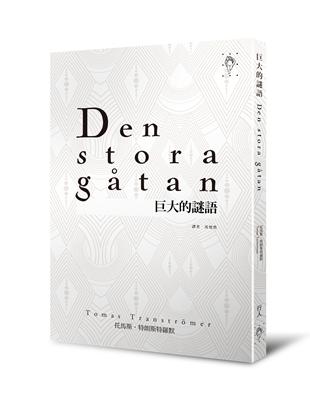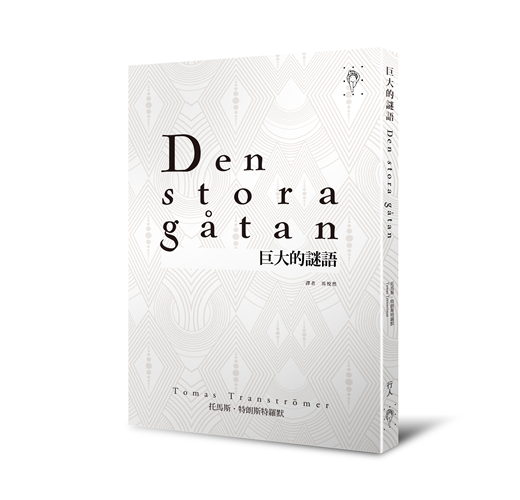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序言
獲得二○一一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著名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後簡稱托馬斯)總共發表了十二部詩集:《詩十七首》(1954); 《路上的秘密》(1958); 《未完成的天》(1962); 《鐘聲與踪跡》(1966);《黑暗中的視覺》(1970);《小徑》(1973);《東海》(1974); 《真理的障礙》(1978); 《狂暴的廣場》(1983);《為生者與死者》(1989);《悲傷的鳳尾船》(1996)與《巨大的謎語》(2004)。這個集子將他最後的兩部詩集介紹給中文讀者。
我相信托馬斯二十三歲時將他頭一本詩集題名為《詩十七首》的時候,一定想到狄倫 托馬斯(Dylan Thomas,1914-1953)二十歲發表的詩集 《詩十八首》(18 Poems)。影響托馬斯的詩人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詩人是艾略特 (T. S. Eliot,1888-1965),帕斯特爾納克 (Boris Pasternak,1890-1960)和瑞典詩人艾克羅夫(Gunnar Ekelöf,1907-1968)。《詩十七首》發表之後,轟動了整個瑞典的文學界。
托馬斯的詩之特色是獨特的隱喻,凝練的描述與言簡而意繁的組成。托馬斯原來是一個優秀的鋼琴家。他的自由詩的音樂性很強。除了自由詩和散文詩,托馬斯常常從古代羅馬和希臘借來比較短的格律形式,也採用日文的俳句。他使用這些詩律的時候,完全模擬原來的節奏形式。托馬斯自己認為他的詩創作,從形式上看,也與繪畫接近。他從小喜歡畫畫。一九九○年八月四日,中國詩人李笠訪問托馬斯的時候,托馬斯說:「寫詩時,我感受自己是一件幸運或受難的樂器,不是我在找詩,而是詩在找我。逼我展示它。完成一首詩需要很長時間。詩不是表達瞬間情緒就完了。更真實的世界是在瞬間消失後的那種持續性和整體性……」(北島《時間的玫瑰》,一九三頁)。
托馬斯詩作裡獨特的隱喻很多。頭一本詩集、頭一首詩的頭一行,容有詩人最有名的隱喻之一:「醒來就是從夢中往外跳傘」。
另一個例子出現在《路上的秘密》中頭一首詩的第五闕的最後一行:
或者一只吠叫的狗上面
一片孤獨的雷雲。
種子在土中猛踢。
(馬悅然譯文)
托馬斯的詩已經譯成六十種語言。李笠把托馬斯詩集譯成中文(《特朗斯特羅姆全集》,二○○一年,南海出版社)。董繼平將托馬斯的詩歌都譯成中文。(《特蘭斯特羅黙詩選》,二十世紀世界詩歌譯叢,二○○二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李笠、董繼平的譯本,當然未及收納托馬斯最近的作品,二○○四年發表《巨大的謎語》;將托馬斯的詩譯成英文起碼有十個翻譯家。其中最優秀的翻譯家,據我看是蘇格蘭詩人兼翻譯家若彬‧佛爾頓(Robin Fulton)。他把托馬斯所寫的詩和散文篇都譯成節奏跟原文一樣的英文。佛爾頓精通與瑞典文很接近的挪威文。
另一位把托馬斯所寫的詩譯成英文的人是美國詩人兼翻譯家若伯‧布萊(Robert Bly)。他的翻譯方法跟佛爾頓的完全不同。從事翻譯工作的詩人有時隨意改他們所翻譯的詩的原文。布萊先生就是他們裡頭的一個。托馬斯一九五八年發表的詩集《路上的秘密》中有題名為〈巴拉基列夫的夢〉的一首詩。其中的一闕佛爾頓譯得很正確: ”There was a field where the plow lay / and the plow was a fallen bird”。董繼平把這闕譯成 「有一片田野放着一台犂/而這台犂是一隻墜落的鳥兒。」我讀這闕詩的時候就看那台犂的一把躺在土地上,另一把以四十五的角度傾斜往上,正像一隻斷了翅膀的鳥。布萊把這個非常戲劇性的意象譯成 ”and the plow was a bird just leaving the ground”,逼着讀者接受那犂垂直地立在田裡。布萊一九七○年初把他的譯文寄給托馬斯看。托馬斯回答說::「你那”a bird just leaving the ground”比我的”a crushed bird”好得多」。托馬斯的回答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認為詩人已發表的詩不屬於他自己,屬於他的讀者,屬於世界愛好詩歌的人。因此,詩人不應該讓譯者隨意改詩的原文。
托馬斯一九九○年中風之後,只會講幾個詞,例如ja,「是的」,nej,「不是」, men,「可是」和 mycket bra ,「很好」。可是只要是托馬斯的妻子莫妮卡(Monica) 在他的身旁,托馬斯會參加任何題目的談話。你無論問托馬斯什麼問題,莫妮卡看了托馬斯的面孔之後,會回答你的問題;「Mycket bra!」托馬斯就說。有時托馬斯會畫一個圖,告訴莫妮卡他要什麼。我記得有一天我在托馬斯和莫妮卡的家裡吃午飯。托馬斯忽然在一張紙上畫了一個馬頭給莫妮卡看。這一次莫妮卡簡直猜不到托馬斯要什麼。托馬斯不耐煩地再畫一個馬頭。「啊」,莫妮卡說,「你要你的眼鏡!」 「Mycket bra!」托馬斯高興地說。我不懂一個馬頭跟托馬斯的眼鏡有什麼關係。莫妮卡給我解釋說:「托馬斯的詩集《黑暗中的視覺》有一首詩叫「打開的窗子」。那首詩的最末了的幾句是:「我不知道我的頭/向哪邊轉—/以雙重的視野/像一匹馬。」我之後問莫妮卡說:「要是托馬斯要他的眼鏡,他為什麼不畫一副眼鏡呢?」莫妮卡回答說:「托馬斯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人!」
今年滿八十歲的托馬斯和他的妻子莫妮卡經濟情況一直都是困窘的。托馬斯的薪水並不高,他的詩集賺不了多少錢。他一九七○年代給他的老朋友美國詩人布萊寫的一封信中說,他和莫妮卡每到月底就得抖一抖他們衣櫃裡的衣服,看兜兒裡有沒有一些硬幣!
我認識托馬斯和莫妮卡快五十年了。這半個世紀,我們夏天有時在托馬斯那當領航員的外公在一五○年前在斯德哥爾摩外的一個海島上蓋的「藍房子」見面。這個海島是托馬斯的真正的故鄉。最近十幾年托馬斯和莫妮卡住在斯德哥爾摩的南區,離托馬斯小時候住的地方很近。從他們的公寓看得見海和港口的一部分。客廳裡有托馬斯的大鋼琴。我們每次去見他們,托馬斯給我們彈鋼琴,他收集很多專門為左手寫的鋼琴曲。見面的時候當然談得最多的是與詩及翻譯詩有關係的一些問題。我一九八三年把托馬斯的詩集《狂暴的廣場》譯成英文,發表在瑞典與英國的雜誌上。一九八七年我把托馬斯的一些散文詩譯成英文,發表在題名為《藍房子》小本子上。
一九八五年,托馬斯和我有機會同時訪問中國。有一天托馬斯在北京外語學院給學瑞語的學生朗誦自己的詩。他朗誦完了的時候,有一個男學生舉手說:「我沒有懂得你剛才朗誦的詩。」托馬斯回答說:「詩是不需要全讀懂的!你接受吧,把它當作你自己寫的!」我願意想像那名年輕的學生後來當了詩人。
這本書包括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兩部詩集,《悲傷的鳳尾船》與《巨大的謎語》和我的漢譯文。我的《悲傷的鳳尾船》譯文是好幾年前譯好的。
我二○○四年訪問台北的時候恰好遇到總統選舉的熱鬧。為了要躲開那奇異的場面,我的妻子文芬和我逃到礁溪去過一個週末。文芬那時忙於寫東西,所以我利用那個機會把我的友人托馬斯當年新發的詩集《巨大的謎語》譯成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