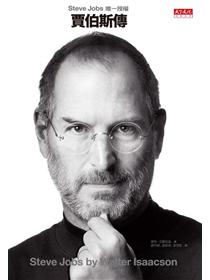約略在四十年前或更早,美羅中華中學的一些班上,有一群學生努力在課餘辦壁報,編期刊,寫文章。辦壁報,編期刊,寫文章,原本稀鬆平常,但姻緣巧合之下,文學活動開始穿梭於山城,慢慢翻掘和延伸到全馬各地,復又萌長於臺灣寶島的沃土。 這些文學活動如詩歌的清脆悅耳,散文的幽谷情歌以及小說的章回餘韻,日夜在不同場景出現,引來了同好者的赴約,星空下、山水間,聚會時感到溫暖,散席後行影孤單。過了一些時日,當中有些人處處展露才情,也有些人卻因理念相脖而跌宕失落,更有風光跋扈於現世,或隱居於都會鄉土者,交錯渡過其斤斤計算或與世無爭的生活。 現在,班上的這些青少年華,好像瞬間全都步入不惑之年,一晃,歲月無須交待,也無從細說,光陰的美目如何塗改他們精緻的一生,甚或是寥落的一世,都交由歷史的列車輾過,當有斑斑痕跡可以追溯。 這就是作者想出版第一本散文集的此刻,最想敘述的重要話題,書寫的故事從美羅開始翻山越嶺,轉程到了臺北後流連忘返,最後是過客般又回到大馬雪蘭莪州首府,那陪伴作者虛渡廿多載的莎阿蘭胡姬花城,生根後始終要作個了結。
作者簡介:
李宗舜 原名李鐘順,易名李宗順,早期另有筆名黃昏星及孤鴻。祖籍中國廣東省揭西,1954年9月7日生於霹靂州美羅瓜拉美金新村。1967年與溫瑞安、周清嘯、廖雁平等創立綠洲社,1972年參加天狼星詩社。 1974年赴臺,肄業於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與溫瑞安、方娥真、周清嘯、廖雁平、殷建波及一班同好共同創立神州詩社,任副社長。爾後負責神州出版社發行部,擔任青年中國雜誌社社長。曾擔任綠洲期刊、天狼星詩刊、神州詩刊、青年中國雜誌,代理員文摘等刊物主編及跨世紀季刊總編輯,現任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行政主任。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書籍推薦人
天狼星詩社社長 溫任平
臺灣小說家 陳正毅
媒體推薦:書籍推薦人
天狼星詩社社長 溫任平
臺灣小說家 陳正毅
章節試閱
前程 來到臺北,正是秋涼天氣,臺北盆地有時還帶著些微侷悶。來到臺北,正是十月天的細雨霏霏,灰濛濛的一片潮濕大地。在白天,去面對高聳入雲的建築和建築陰影下的彩色廣告牌,夜晚燈火上市,五彩繽紛,叫人想盡辦法逃避繁華,一次匆忙的約見,歲月有些晦澀,陰暗。 我和瑞安、娥真及雁平第一次見面,是在臺北旅社,沒有人來接我們,也沒有熟識的人。第二天一大早雁平南下屏東農專註冊去了,剩下我們三人,開始去習慣臺北的車聲人影的來往穿梭,半個月下來,我抱定決心帶著觀光簽證,報名建國補習班,瑞安及娥真暫時有個安定的所在:租了一間房子,在羅斯福路三段。為了要考進大學,我暫時把大部分時間放在功課上,一個星期和他們兩次會面,心中一直在探詢家鄉的是否捎來音訊。 開始來到臺北,我和其他國家的觀光客一樣,雖一心一意要考聯招,也一樣只允許逗留一個月時間。如果還想再留下來,簽證要補辦一個月,這一個期限到了,就必須離開。在大馬辦理觀光簽證,各部門機關百般刁難,使得本來於九月二十九日能和大家同行的我,變得孤單一人,在農曆中秋夜晚,趕搭長途火車南下新加坡辦理出境手續,整夜月亮圓圓懸掛在清冷的天邊,淒風陣陣刮進窗來,那時身心多像吊在空中的物體,一方面牽掛著大馬的詩社和家庭,一方面懸念著已到臺北的兄弟,交錯的心情如火車的時速和風景匆匆錯過,好像一切都那麼遙遠,在火車上長夜漫漫渡過中秋,生平第一次在車廂北望美羅,伴隨着冷風南下,如飲苦酒。 來到臺北,我既沒有一張可依憑的長期外僑居留證,亦無學籍可以進大學,連旁聽踏入校門我都怕被拒絕。眼看著瑞安、娥真及雁平等已經註冊入學了,我還是一無所有,於是決定要好好打拼一段時日,不管考進哪間大學,好歹學籍居留不成問題,可以一起和他們在校園闖蕩天下,而在寒風多雨的臺北,獨自在館前路補習班宿舍,惡補高中三年的課程。每一個課程都是一個沈重的開始,像歷史課,從遠古到近代,當觸及近代史,整本書都翻了臉,改變了原來美滿的面貌,不認識自己似的。 那一役一役的對外戰爭,割地賠款,不平等條約的簽定,中國開始淪為殖民地。然後孫中山先生創導革命,熱血漢子犧牲了性命,最後成了烈士,在黃土中成為七十二塊沉重的碑石,民國建立後,軍閥作亂,北伐成功後,日本鬼來了,八年抗戰勝利後,國共交戰。近代史宛若一雙沉重的鞋子,向逆流的方向轉去,前面是急灘,在地的每個人都須有面對整個現實困境的勇氣。 1975年 臺北
前程 來到臺北,正是秋涼天氣,臺北盆地有時還帶著些微侷悶。來到臺北,正是十月天的細雨霏霏,灰濛濛的一片潮濕大地。在白天,去面對高聳入雲的建築和建築陰影下的彩色廣告牌,夜晚燈火上市,五彩繽紛,叫人想盡辦法逃避繁華,一次匆忙的約見,歲月有些晦澀,陰暗。 我和瑞安、娥真及雁平第一次見面,是在臺北旅社,沒有人來接我們,也沒有熟識的人。第二天一大早雁平南下屏東農專註冊去了,剩下我們三人,開始去習慣臺北的車聲人影的來往穿梭,半個月下來,我抱定決心帶著觀光簽證,報名建國補習班,瑞安及娥真暫時有個安定的所在:租了...
作者序
神州詩社:烏托邦除魅兼序李宗舜的散文集 溫任平
星星們從一所遙遠的旅館中醒來了
一切會痛苦的都醒來了
――多多
(一)
李宗舜,也即是天狼星時期的黃昏星,力邀我為他的散文集《烏托邦幻滅王國》寫序,由於天狼星詩社與神州詩社當年的糾葛,我可能是最適當、也是最不適當的寫序人。我在電話裡提醒宗舜我的處境,他說集子的三十多篇文章已修改了八次,所有過激的情緒語全刪了。我建議他篩選出精品,才傳給我看,「宜乎少些神州的老調,多些生活、生命的感悟之作」。宗舜的回訊讀得出來他的無奈與心虛:「我在七十年代寫的散文只能稱為習作,天狼星和神州是我七十年代生活的主要內容」。
他的回訊使我感到為難。坦率的說,習作應該交給華文老師批改,不宜付梓。這話只差沒說出口,另一個念頭在我腦中閃過:作者通常都不是自身作品的最佳評鑒者,他可能寫了一些連他自己也不太懂、難以估量的東西,我於是發了另一則短訊給宗舜,建議他把稿傳過來給我看看,「讓文本自己說話」。我聽說臺灣《文訊》二九四期(二○一○年四月號)特闢神州詩社專題,內刊長短文章九篇,就發生於一九八○年九月廿六日臺北警總人員突然帶走溫瑞安、方娥真、李宗舜、廖雁平四人的事件發表感想。李、廖兩人受盤詢廿四個小時後釋放,溫方則入獄四個月後以「為共匪宣傳」的罪名遞解出境。這宗發生於三十年前的奇案,由溫方李廖與當年的神州社員和奔走營救的文學界長輩各抒己見,文獻寶貴,我也請宗舜寄來一份讓我細閱。
(四)
烏托邦是海市蜃樓,三十五年後的今天還不徹底「除魅」(disenchanted),謬種流佈,病毒會繼續散播。五百年前的摩爾與拉伯萊相信人類文明具備向善的本能,是「想當然爾」的冀望。楊朱講性惡,佛家講貪嗔癡慢疑,早已洞悉人類的心靈黑暗。二十世紀人類建構的烏托邦一個比一個大,二戰日本提出的「東亞共榮圈」,冷戰期鐵幕與竹幕均異口同聲力倡的「無產階級專政」,美國自許為「世界警察」,只是犖犖大者。擴張勢力,合法化侵略,以公義行不仁不義的這些超級烏托邦,傷害(殺害)的人以億萬計。毛澤東所謂「六億神州俱堯舜」,其實是「六億神州俱芻狗」。右翼烏托邦是「以超真搶救真實」(to rescue the real with the hyper-real)左翼是「以虛擬拯救真實」(to rescue the real with the imaginary),魑魅魍魎,焉可不除?今日工商文教的烏托邦,以各種掩人耳目的姿態出現,體積遠比政治烏托邦小許多,為害社會各階層可十分廣泛,它們政治立場不左不右,反而更便於左右開弓,超真與虛擬並用。威爾斯在其著作《現代烏托邦》裡直言「它們的共同特點是空洞……沒有具有個性的個人,而只有一致化的成員。」成員對大哥只有「不問情由的服從」(unquestioning obedience)。內心有疑惑,震懾於領袖的威權,不敢抗爭,明知錯了還是將錯就錯下去。
武俠小說的情節與武俠小說家的生活沆瀣一氣,情況之詭譎離奇,情節之曲折驚怖,因為毫無前例作為參考,更令人震悚。金庸的武俠人物忠奸莫辨,行事匪夷所思,作為香港明報主筆,查先生的社論於現實時事的真與幻看得真切;倪匡言行偶爾滑稽突梯,但他也沒把現實生活搓捏成武俠的漿糊。三十多年之後,方娥真於《文訊》的神州專輯的一篇文章中兩度提及「溫瑞安魔鬼的一面」,不作申論,我難免這樣想:如果神州時期她願意用一語提醒大家,則不致於有那麼多年輕人剛剛有點理想並仰望偶像,即被殘酷的現實無情地摧毀,對一切失望抑且乎絕了望。一九七五年殷乘風投奔老大,發覺神州提倡讀書不重要,搞活動才是做大事,而他於備考的緊急關頭,社員於門外鼓躁、甚至敲門要他放下書本積極參與社務(九十年代中他來見我,追述往事,不勝唏噓),一九七九年殷同學終於退社,那是發生於一九八○年的九二六事件大約一年前的事。神差鬼使,讓殷乘風躲過了向情治單位誣陷神州的嫌疑。至於因為夾在功課與社務之間分身乏術、三進三出神州的周清嘯就沒那麼幸運了。清嘯已故,於他的懷疑、懷恨宜乎以懷念代之,讓逝者安息。
在此要一提的是,魔鬼撒旦,還未「走火入魔」之前原本是天使,是天地靈氣所聚,英豔動人,豐神湛然,頭上還繞著流金泛銀的光環。誰知堅土竟是流沙,可歌可泣之種種,一返顧間竟成了可笑可憫。楊牧的〈完整的手藝〉,以詩人獨特的直覺點出天使的特徵:「虛幻的全部交給我/現實的你留著」,把兩個主詞對調:「現實的全部交給我/虛幻的你留著」,魔鬼即粉墨登場。魯迅嘗謂創造社成員是「才子加流氓」,神州詩社的問題是人與魔的錯位,令人難堪的是三十多年後,在《文訊》的特輯當事人的文章裡,我看到的是對昔日社友的各種揣測(誰對不起誰?誰可能是向官方告發、「出賣」兄弟的叛徒?),而不是謙卑的自責與深切的反省。太多的witch-hunting,太少的soul- searching。年近六十的人,還重複二十多歲的江湖混混12口吻為自己護短、辯說,令我驚訝悲哀,難以置信。人肯定會成長,可不保證會長進。李宗舜在散文集的最後一篇沉痛地問:「大夥兒在阿里山結義相知相惜,奇緣結社,多的是肝膽相照之士,最後為何除了她自身之外,其他的都是叛徒?」宗舜有沒有讀過下列的歷史故事?史達林有一天撫鏡自照,悲哀地說:「十月革命的同志,現在只剩下我吧了。」
李宗舜這些年對神州感情的付出,構成了他心中無以自釋的情結,神話破滅、偶像是假的,社員之間的情誼是真的。反芻往昔,他難以相信過去的輝煌竟是充斥著高潮與反高潮的野史稗官。出國深造、失學、失業、窮病、困頓、顛沛、流離,對宗舜是混沌迷惘的遭遇。七十年代中下葉,因國土分裂而彌漫臺灣社會的民族危機感,神州詩社恰逢此歷史際遇,得享殊榮盛譽,獲得蔣經國親自接見,集團成員三百餘人,身為集團第二號人物的李宗舜,他的老二哲學(或沒有哲學)是前面掛個「忠」後面吊個「勇」字,以義開道,衝鋒陷陣,由於不夠陰鷙機敏,雖立功無數,但分得的權力紅利不多,與他的二當家身份簡直不成比例,許多時候他扮演的還是個「隻眼開隻眼閉」相當困難的緩衝角色。宗舜的戇直使他沒去多想權勢的問題,他不讀《資治通鑒》,不熟諳傅科(M. Faucault)所言「歷史上各種精密的權力儀式」(meticulous rituals of power),他耽於當下的happy hours,捕捉每次聚會帶點不安的興奮喜悅,由於每篇散文均寫成於詩社活動之後,他拼湊的其實是記憶的碎片,往事並不如煙,而是彌漫著霧樣的哀愁。每篇散文都似乎是他的詩作底後設篇,包括追念葉明、清嘯的悼亡篇章,都有一種要把時間留住、把眼前的歡樂美好無限延續的慾望,那就成為作者的獨特風格。
神州詩社:烏托邦除魅兼序李宗舜的散文集 溫任平
星星們從一所遙遠的旅館中醒來了
一切會痛苦的都醒來了
――多多
(一)
李宗舜,也即是天狼星時期的黃昏星,力邀我為他的散文集《烏托邦幻滅王國》寫序,由於天狼星詩社與神州詩社當年的糾葛,我可能是最適當、也是最不適當的寫序人。我在電話裡提醒宗舜我的處境,他說集子的三十多篇文章已修改了八次,所有過激的情緒語全刪了。我建議他篩選出精品,才傳給我看,「宜乎少些神州的老調,多些生活、生命的感悟之作」。宗舜的回訊讀得出來他的無奈與心虛:「我在七十年代寫的散文...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2收藏
2收藏

 1二手徵求有驚喜
1二手徵求有驚喜



 2收藏
2收藏

 1二手徵求有驚喜
1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