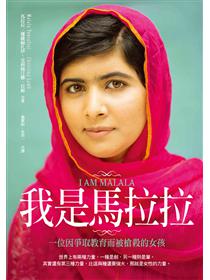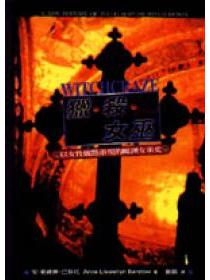原住民作家瓦歷斯‧諾幹:「翁山蘇姬是我心目中的鋼蘭花,因柔軟而強韌。」
高雄市長陳菊:「自由──是我們值得以生命捍衛的價值。」
導演林正盛:「翁山蘇姬,一個看似柔弱的女子,卻展現出溫暖人心的無比慈悲力量。在她身上我們學習柔軟跟慈悲,我們終於懂得柔軟可以成就的力量有多大。」
台中市長胡志強:「希望這個世界因為翁山蘇姬『剛柔並濟、冒死不屈』的精神,而享有更多的民主。」
感動推薦/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理事長林昶佐
本書作者賈斯柏•本特森為一名記者,他經由實際採訪緬甸與和與翁山蘇姬接觸的經驗,貼近緬甸的社會狀況而寫成的翁山蘇姬傳記,呈現了一位當今最重要的政治活動家的形象。他記錄了這位身為緬甸解放英雄昂山將軍的女兒的宿命。為了爭取緬甸人民的自由,她在1989年首度遭軍政府軟禁;而在之後的21年中,她有15年的時間受到囚禁,被迫與她的丈夫和孩子分離。
在如此艱難的時期,翁山蘇姬仍然是緬甸民主運動中一個團結各派的人物和活動家。1991年,她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同時她意識到被軟禁的時間愈長,她的名聲和國際地位愈增。2010年11月13日她終於受到釋放,並立即從事民主運動,證明了她仍然是緬甸最重要的政治力量。
翁山蘇姬對人們的影響和與專制政權抗爭的能力,顯示出她個人的人格魅力和勇氣,她的獻身精神也反映出一個關於時代的重大問題,那就是:從獨裁體制發展到民主的過程中需要的是什麼?
199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我相信,假使我們擁有堅強信念的話,即使一個人也可以撼動全國。
翁山蘇姬:「請用你的自由,促進我們的自由。」
在國家福祉與個人自由之前,我們將如何做出選擇?
緬甸民主運動的領導者翁山蘇姬,在過去的21年間,在軍政府的壓迫下遭受15年的軟禁,被迫與摯愛的家人生死相隔。是什麼樣的力量,支撐著她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為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而持續奮鬥?
從她身上,我們不僅看見傳承自父親翁山將軍和母親金姬的民主薪火,更看見「信念」與「愛」如何成為她與家庭之間超脫禁錮的連結,以及她堅持革命與消除恐懼的力量來源。這是一股能夠撼動世界的力量,來自於一個國家之母無私的愛。
★本書特色
本書在世界民主社會的進程中,特別具有時代的重要性。翁山蘇姬作為民主運動的領袖,在緬甸軍政府的壓迫下,被迫與家庭分離並囚居15年;但在這15年期間,緬甸的民主運動浪潮卻未因此而停歇,反而因為翁山蘇姬受到的壓迫而更激起人民的革命意識。翁山蘇姬承繼遭受政府暗殺的父親翁山將軍的民主運動使命,為民主運動犧牲個人的自由與家庭生活,她所受到尊敬不只來自於個人的領袖魅力,還有為創建新時代而奉獻的無畏精神。
作者簡介:
賈斯柏‧本特森(Jesper Bengtsson)
賈斯柏身為一名記者,十多年來一直追蹤緬甸的發展。他是人權組織「記者無國界」(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瑞典地區的主席。著有《獨裁統治陰影下的緬甸之旅》(2007)(Burma: A Journey in the Shadow of the Dictatorship)一書,另為瑞典晚報(Aftonbladet)撰寫社論。
譯者 連舒婷
靜宜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畢,曾任口譯及商業翻譯,現為自由工作者。專業領域為商業、美食、英美法文學及詩詞。
◎【特刊】翁山蘇姬:請用你的自由,促進我們的自由!
譯者簡介:
連舒婷
靜宜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畢,曾任口譯及商業翻譯,現為自由工作者。專業領域為商業、美食、英美法文學及詩詞。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原住民作家瓦歷斯‧諾幹:「翁山蘇姬是我心目中的鋼蘭花,因柔軟而強韌。」
高雄市長陳菊:「自由──是我們值得以生命捍衛的價值。」
導演林正盛:「翁山蘇姬,一個看似柔弱的女子,卻展現出溫暖人心的無比慈悲力量。在她身上我們學習柔軟跟慈悲,我們終於懂得柔軟可以成就的力量有多大。」
台中市長胡志強:「希望這個世界因為翁山蘇姬『剛柔並濟、冒死不屈』的精神,而享有更多的民主。」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理事長 林昶佐
名人推薦:原住民作家瓦歷斯‧諾幹:「翁山蘇姬是我心目中的鋼蘭花,因柔軟而強韌。」
高雄市長陳菊:「自由──是我們值得以生命捍衛的價值。」
導演林正盛:「翁山蘇姬,一個看似柔弱的女子,卻展現出溫暖人心的無比慈悲力量。在她身上我們學習柔軟跟慈悲,我們終於懂得柔軟可以成就的力量有多大。」
台中市長胡志強:「希望這個世界因為翁山蘇姬『剛柔並濟、冒死不屈』的精神,而享有更多的民主。」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理事長 林昶佐
作者序
隨遇而安:自由在我心中
距我首次造訪緬甸,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回想起來,會踏上那次的旅程幾乎純屬巧合。那時我的女性友人已經在當地待了一年,而且一整年她都在談論這趟旅行。她讚頌緬甸的美,卻痛斥這個國家的貧窮和殘暴的軍政府。所以,當時身為自由記者的我決定啓程一探究竟。
抵達緬甸的第一秒鐘我就深深地被吸引住了。透過民運人士、緬甸流放學生、街上居民對緬甸當局的侃侃而談,經過和不同民族的相識,更讓我知道緬甸的重要性。這不單單是為了這個國家的福祉,雖然那是最重要的,但這更是為了一個全球性的提升。深入了解這個國家,就會發現緬甸存在著許多現今政治上最關鍵的問題。我們要如何在一個非民主的國家推動民主?為何曾經一個有耀眼前景的國家,如今卻灰甸甸?我們如何在後殖民領土解決種族衝突?而中國崛起對國際關係與和平建構的意義又是什麼?
在我首次造訪的九○年代時,最讓我震撼的並不是這些理論性的問題。而是緬甸嚴重的貧困處境。然而,當我在二○一一年二月初再次回到這塊土地,一切並無太大改變。仰光市中心的街道和房屋依舊殘破不堪,而孩子乞討的次數比我記憶中更加頻繁。
但,有一件事情改變了:奢侈的狀況變得更明顯。從這個觀點來看,軍權成功了。從二十年前他們開始效仿中國實行經濟私有化(開放經濟、政治掌控),雖然絕大多數的人還是身處極貧,有少數人卻致富了,且變得貪婪。仰光和曼德勒充斥著投資客,大多是中國和泰國的商人,還有部份的美國人和歐洲人。和軍隊幹部關係緊密的緬甸家庭,住在大城外郊區的舊殖民豪華別墅,過著極其富裕的生活。
搭著計程車從市中心到翁山蘇姬所成立的全國民主聯盟總部(NLD,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看到的全是這般景象:乞討的人、在街上煮食的婦人、修補舊殖民建築的工人們,全被召集裝修著仰光大金寺周遭那些供西方旅客下榻的高級旅館。
相較之下,全國民主聯盟總部是那麼不起眼,甚至一不小心就會錯過它。總部位於一間家具店的頂樓。裡面只有一間翁山蘇姬的小辦公室,和另一間大一些的供黨內幹部開會的會議室。家具店旁的小樓梯連接著總部和外面的世界。只要走上這個小樓梯,任何人都可以和其他黨內的成員會面、成立當地組織、尋求合法協助,或者只是一起喝杯綠茶、吃個咖哩飯。
付計程車車資時,我注意到在對街的一間茶店外,坐著兩個外型嚴肅的男人,戴著墨鏡,身著白襯衫,一見到我,便舉起鏡頭按了好幾次快門。一位友人在幾週前,前往總部時便警告過我,要注意這些情資人員。從翁山蘇姬二○一○年十一月得到釋放的那一刻起,他們就一直從那間茶店監看著全國民主聯盟總部的一舉一動。他們拍下所有和她會面的外國人士照片,好讓這些人無法再次取得簽證進入緬甸。這是和她見面所必須承擔的風險。許多記者為了避免被認出來,戴上墨鏡和帽子,試著偽裝自己,但我一點也不在乎。如果那些情資人員,能從眾多照片中指認出我,並且讓我無法再次造訪緬甸。那就隨他們去吧。
一走進總部的公共空間,我就感覺到生意盎然,完全不同於前幾次來的時候。當時,翁山蘇姬仍遭軟禁在處所,而她的黨員們被政權壓得喘不過氣。現在,壓力仍然存在,但是她的釋放已經為民主運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我端著一杯茶,在一張搖搖晃晃的塑膠椅上坐了下來,等待和她的會面。這是一個得來不易的會面。離開瑞典之前,我和一個在泰國參與緬甸流亡運動的朋友聯繫。他幫我安排了在某個星期五能和翁山蘇姬見面的機會。但是,一抵達仰光,我才了解全是誤會一場。「很抱歉,」接待處的女孩對我說,「您至少必須再多等兩週,夫人(緬甸人對她的尊稱)已經病了一週,才剛復原,所以現在很忙。」
我預定回斯德哥爾摩,中轉曼谷的班機一週後就要起飛,所以無法等那麼久。
我評估過這件事的風險,同時也策劃了多次的會面。但是當我試著說服自己,就算取消了也不打緊時,我活像迪士尼裡的灰姑娘,站在自己的高塔裡,告訴自己皇宮裡的舞會一定枯燥乏味。但事實上,感覺像是被人用榔頭在腦門上重重敲了一記。此書的初版在瑞典早已出版,內容由採訪翁山蘇姬的同事或朋友,或由翁山蘇姬本人、記者和作家所撰寫的文獻建構而成。但我從未親訪她本人。因她長年被軟禁於處所,以至於無人能和她見面。現在我希望能得到她本人對於緬甸現況的見解,以及了解她獲得釋放後的生活點滴。
就在我有幸深入採訪吳文廷(U Win Tin)後,我又樂觀了起來。吳文廷,一個因為參與民主運動的而被囚禁二十年的八十一歲作家兼民運人士。他告訴我他在獄中的生活—他在一部份的服刑期間,在監禁所牆上寫下一句句抗議民權被剝奪濫用的詩句,另外他與他的獄友偷偷用小紙片做了「獄誌」,並且發行供其他囚犯閱讀。最後,一小時後,他承諾安排我與夫人會面。
今天,星期一。我在樓下等了好一會兒,等待時,每回我探出大門,情資人員就會舉起鏡頭,接著一位黨工出現領我上樓。我坐在一個狹小、牆上藍色油漆已經剝落的等候區。倏地,辦公室的木門打開了,我一起身,就和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受崇敬愛戴的女士面對面。
許多和翁山蘇姬會面的記者,都對她的外貌做出了評論,雖然我已決定要避免這麼做(不知為何男性政治家從不會被評論外貌),但她一出場時還是驚為天人。她穿著一席紫色龍基(Longyi,另稱沙龍Sarong),上身搭配粉色的襯衫,髮上繫著象徵她的茉莉花。去年夏天,她剛度過她的六十五歲生日,且過去的二十一年來,有長達十五年的時間,都被軟禁在家裡。但她看起來就像四十五歲一樣,甚至感覺起來更年輕,更精力充沛。去年十一月,獲得釋放後,她於總部前的首次公開演說,當時台下的幾百人,或者是幾千人,一定跟我身有同感。
「她一生中歷經了比大多數人更多的挑戰,但她看起來就像是剛結束為期兩星期的假期一般。」一個參與仰光活動的國際觀察家說。
我們在離對方不到幾尺的沙發上坐下。她看起來輕鬆自若。於是我首先問起她的活力充沛和好心情。
「這一點也不奇怪,」她用一種反諷的眼神這麼說著,「軍隊讓我休息了七年,讓我現在能充滿活力回到工作崗位上。」
這麼長的時間,換作是一個不那麼樂觀的人,就會被定義成浪費生命。但是就她這位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來說,她靠著擁抱接受這個殘酷事實,並且樂觀取見,而非悲觀地生活著,挨過這些年來的孤立。
「隨遇而安,」她笑著說,「我的律師在軟禁期間至處所來探望我時,我可以隨心所欲地談天說地。」
她注意到我臉上疑惑的表情,繼續說著—─
「我認為自由有兩種形式。第一種是心靈上的。如果人認為自己自由,那就是自由。有些時候人會獨處,只要時間是屬於自己的,這時就再自由不過了。另一種是環境形式上的。你所處的環境自由嗎?我的答案絕對是否定的,因為我不認為緬甸是個自由國家。」
我和她會面的同時,大部份阿拉伯的國家,正面臨著革命和人民起義改變政治結構。緬甸當局試著封鎖這些動態,擔憂騷動會散播到緬甸,但人民還是知道了。
翁山蘇姬說:「他們禁止當地郵報刊登任何相關新聞,但許多人還從廣播和網路得到消息了。無論一個政府多極權,人民終究會知道什麼正在發酵。這跟一九八九年,我第一次被逮捕時,很不一樣。事實上,這跟七年前,我最後一次被逮捕時,也很不一樣。」
很顯然,有一個原因導致政府如此積極於控管這些資訊,因為這些在阿拉伯國家的人民起義,和一九八八年在緬甸發生的起義,有很多雷同之處。這些事件,終於讓翁山蘇姬向前邁進,並成為民主運動的領軍人物。但她也察覺到了不同:
「目前在世界的每個角落,人民已經厭倦了壓迫和獨裁。這樣的事一再上演。我認為人民必須切記這樣的進步需要多年努力。例如,埃及從五○年代初期就是軍權統治。某些程度上來說,突尼西亞也是。感覺上,示威群眾似乎以很快的速度扭轉情勢,但所必須考量的是,這些力量是多年累積成就的。還有,埃及的軍隊決定不朝群眾開槍。這是和緬甸差異最大的地方。」
於二○○二或二○○三年,將近兩年的時間,是翁山蘇姬最後一次恢復自由身的時候,且得以繼續她的政治工作。全國民主聯盟在緬甸境內規劃了一連串的巡迴演說,雖然軍政府宣稱她的明星光環已經消失、政治魅力不再,但還是有成千上萬的人前來聽她的演說。這一次,她說她已經不受任何限制。她理應可以為所欲為,在這個國家內到處旅遊。但軍政府早已聲明,讓她自由的前提,建立在她不能明示任何會挑起反動的徵兆。所以當我和她會面時,她仍按兵不動。
她說:「我的行程,已經排滿了在仰光及辦公室的大大小小會面,所以,一定沒有足夠的時間讓我好好看看這個國家。」
她已經會晤了一長串數不可計的黨員、外交官、外國政客和記者。她的臉不是出現在時代雜誌(Times)、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半島電視台(Al Jazeere)、英國廣播公司(BBC)和其他國際媒體的版面上,就是成為頭條。她也和許多緬甸境內其他的政治團體會過面,有來自其他政黨的,以及主要少數族裔人士的代表。
從她最早的評論和訪談中,就可看出,翁山蘇姬對於七年前她所處的政治環境,滿是尋覓和不確定。因為她多次談及對話的重要性。「我想要傾聽人民的聲音。」首演會上她這麼說,「然後我們再決定下一步,我希望能倚靠所有民主的力量。」
最近一次的評論,她直接點出民主運動在緬甸所面臨的困境,軍政府於她獲釋的幾天前全面控制了大選。幾個民主政黨決定參選,有全國民主陣線(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NDF)(由曾參與全國民主聯盟的成員所創立)及幾個少數族群所創建的團體,聯合杯葛大選。她告訴我她也曾和全國民主陣線的黨員見過面,但當時是以私人名義,而不是黨代表的身分。
獲得釋放後,她訴請再次舉辦針對軍政府、民主政黨和少數族群的「龐龍會談」。四○年代時,她的父親──翁山將軍(緬甸語:Bogyoke Aung San,又稱General Aung San),在龐龍(Panglon)組織了一個會談。當時,他說服了數個少數族群加入緬甸新聯邦,並為了少數民族的權利及自治接受聯邦憲法。許多族群期望能再次組織一次研討會,以解決緬甸現況。
抱持著滿懷的寬恕,翁山蘇姬再次強調,一直以來,她從未對鎮壓者懷有恨意。她期望對話,而非報復。她也再次提到,她敬重他們如人一般,即使她無法贊同以及必須批評軍政府的某些決定。過去二十一年來,緬甸軍權首領和國家宣導,試著營造出翁山蘇姬是一個受西方影響的武斷惹禍者。然而,她的求和以及和各少數族裔的對話,始終與政府捏造出的形象,完全不相符。
至少目前在她獲釋後,緬甸有了一個重大改變:那就是,民主運動喚回了一股衝勁。不時能看見亂七八糟的便條紙,堆滿翁山蘇姬於總部辦公室內的地板。結束和我的會談後,她將與兩百位來自緬甸各地的青年積極分子會面。會議結束後,他們將返鄉開始成立各部青年小組。
「我無法拿之前仍受軟禁時的情況和現在作比較」,她說,「但現在一定比較有能量。獲釋後隔天,我說我想要建立一個網絡,而這個計畫已經起步。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加入全國民主聯盟,但已經有許多來自各地的小團體和我們串連。他們希望能成為網絡的一分子,這讓我們振奮不已。」
她對未來充滿希望卻也小心翼翼。每個緬甸人都深記教訓。這些年來,已經有太多次的築夢夢碎。一九七四年的學運、一九八八年的起義、二○○七年的番紅花革命,和不下數次的──當軍權只要備受威脅,便將初獲得自由的翁山蘇姬再次軟禁。
「我冀望在短期內,我們能持續組織重建的工作,並改變更多。」她接著說,「雖然敢肯定這將如以往一般艱難。但是希望來自世界各地的支持繼續湧入。並且不讓所有人被緬甸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政治假象愚弄。」
這些評論,旨在向國際社會上,爭論緬甸已經改變的強權國家揭示真相。二○一○年十一月份大選前,部份外交使節及在仰光地區活躍的商人,強調這次的選舉應被外界所接受。任何想改革緬甸的人,都應該遵守軍政府的遊戲規則,並且和運作大選的政黨合作,而不是和全國民主聯盟與翁山蘇姬。同樣的爭辯同時也針對了美國和歐盟的制裁政策。
對談中,翁山蘇姬表示她很清楚知道,爭論是無用的。選後,新議會與文明政府的誕生理應到位,而非受控於軍權。然而,漏洞百出的選舉過程,導致由軍權操控的聯邦鞏固發展黨(USDP),仍舊佔據了八十%的席次。內閣成員三十位裡,只有四位來自其他領域,沒有任何軍事相關背景。而在國家最高委員會內,垂簾聽政的,就是前軍政府領導丹瑞(Than Shwe)。
她說:「我並不排除這樣的過程也能帶來稍稍正面改變的可能性。但是這樣的結果,想要改變任何的政策言之過早。畢竟,他們仍然有權任意逮捕任何人。所以,每當人們說,緬甸已經在改變,我都希望他們能慎重思考。始終未知何時將面臨無來由的拘捕,真正的民主國家不會發生這種事。」
從那之後,緬甸充滿了開放的徵兆。針對媒體法則的惡法已經減輕,許多新創刊的報章雜誌發芽,翁山蘇姬也和新上任的總統吳登盛(Thein Sein)針對緬甸未來討論了好幾次。她謹慎地描述如此的改變,為八○年代後,東南亞地區躍幅最大的進步。
當我寫此書時,軍政府已經釋放了約兩百名政治犯,且估計還會多釋出四百人。翁山蘇姬的政黨——全國民主聯盟,也在二○一○年大選後,獲准登記議會席次。一位總統諮政,甚至語帶暗示指出,翁山蘇姬很可能得到一個職務,那是軍權有史以來前所未見的。
「對於此事,我樂觀以見但仍抱懷疑。」已在泰北清邁地區,掩護緬甸議題十五年的《伊洛瓦底》(The Irrawaddy magazine)雜誌總編輯翁州(Aung Zaw)回應此事。從一九八八年的起義,至今已流亡二十三年的翁州,第一次覺得自己很有可能再次回到家鄉。但不是現在,如果這樣的改變持續發生,不出幾年他一定可以。
縱使有成千上萬的情境顯示緬甸的未來仍舊烏雲密佈,還是有些許曙光照出前方光明正確的路。
翁山蘇姬當然知道自己必須承擔多大的風險;每次當她獲得自由或部份自由,只要軍隊嗅到她的力量茁壯,她隨時會被再次軟禁。
接受英國廣播電視台訪問時,她告訴媒體:「我並不害怕。我並未因懼怕他們會拘捕我,而中斷這些努力。我知道自己再次被拘捕的可能性很高。當然,我不希望再次發生,因為被拘捕時,能做的事實在有限。」
無論軟禁與否,能確定的是,軍權永遠無法鏟除她。她始終能匯集期望緬甸進步的力量,也就是如此,軍權懼怕她勝過其他。她將緬甸許多政治和民族組織團結起來,對於長年專斷政權來說,她始終是頭號天敵。這是他們過去二十一年來有十五年,將她軟禁於處所最主要的原因。如今,她和政治息息相關,她的名字變成禁忌。仰光街上,大家稱她作「夫人」。在公營報章上,她有幾個不討喜的稱諱,通常是「 麥可‧艾瑞斯小姐」 (麥可‧艾瑞斯(Michael Aris,為翁山蘇姬已逝的丈夫)亦或是「嫁給外國人的女人」。這件事,在她與總統對話後,也改變了。雖然信管部(國家信息管理部,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仍未撤除禁止發行任何和翁姍蘇姬有關刊物的指令,但至少她已經不再像過去一樣遭受誹謗。
翁山蘇姬指標性且意義非凡的事績,遠播綿延,穿越了緬甸的國界。一九八九年,就在柏林圍牆被推倒、蘇維埃共產政權瓦解數個月後,她首次遭到囚禁。一九九一年,她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從此,她成為國際上眾所皆知,為民主及人權奮戰的象徵性鬥士。
她所作的事,同尼爾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當時在南非為了種族隔離政策所做的努力,不相上下、大同小異。他們都是所屬國內最光彩奪目的政治明星。皆受到長期的囚禁。都在爭取自由之路上遭受逼迫,不得不做出無可比擬的犧牲。當翁山蘇姬遭軟禁時,她的兒子亞歷山大(Alexander)只有十六歲,而金(Kim)只有十二歲。從那時開始,他們便鮮少見到母親。最後一次被軟禁,他們則完全沒見到母親。她的丈夫,麥可‧艾瑞斯於一九九九年逝世於癌症時,她也沒能和他見上最後一面。其實翁山蘇姬有幾次機會可以逃離緬甸,但她拒絕了,她深怕一旦她離開了,只要軍政府一日掌權,她就一日無法回來。她很可能會永遠流亡,那就表示她必須放棄她的人民。
同時,世界各地的民運人士全與她站上同一陣線。演藝人員如瑪丹娜(Madonna)、U2、REM都紛紛創作歌曲向她致敬。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和迪斯蒙‧圖圖((Desmond Tutu)則透過專欄、報導及政治活動表達支持。
姑且不論所有的關注、所有的活動、報章專欄、電視節目和動人的歌曲,對大多數人來說,她是一個象徵,是映照出美夢和希望的明鏡。在這些意象背後,真實的她又是如何?究竟什麼在推動著翁山蘇姬,以及為何她能得到這麼多的關注?她對緬甸推翻獨裁政權可能性的重要意義?什麼力量讓她何以在年復一年,遭逢巨變,及軍權強制將她與孩子及朋友隔離後,還能繼續和軍權抗爭?
當我離開全國民主聯盟總部時,我覺得自己真的很幸運。自從翁山蘇姬遭軟禁後,這些年來我一直關注著緬甸的發展,想和她會面,根本不可能。但這一次,成真了。和一個早已經幾乎了解透徹的人,終於見面的感覺很不一樣,畢竟當時,我僅透過和她朋友與同事的訪談,以及她的書寫來認識她。我沒有權力做任何評判,我只能說如出一轍——許多人早在這場會面前便告訴我說,這次的會面將完全證實他們所說,且沒有任何矛盾之處。
此書並非翁山蘇姬的完整自傳。而是一個需要她本人參與以起頭的工程。本書大部份於她仍遭軟禁時禁撰寫而成。二○一一與她會面時,有幸得知她對緬甸現況的看法及對未來的計畫。她並未提及太多獲得釋放後的事情。忙碌的她行程表上,早已排滿密密麻麻的緊急事項,她所有的焦點都放在緬甸政治和民主運動上。
以一個活躍的政治家而言,現年六十五歲的翁山蘇姬,可能已經落後很多年。但是如果軍事政權垮台,她絕對會是成就自由民主緬甸的關鍵性人物。她生命的章節尚未結束。
這是一個關於翁山蘇姬和緬甸的故事,雖然故事起點未從其一。故事從二○○九五月,一個五十三歲的美國男子決定在燕子湖游泳開始說起。
隨遇而安:自由在我心中
距我首次造訪緬甸,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回想起來,會踏上那次的旅程幾乎純屬巧合。那時我的女性友人已經在當地待了一年,而且一整年她都在談論這趟旅行。她讚頌緬甸的美,卻痛斥這個國家的貧窮和殘暴的軍政府。所以,當時身為自由記者的我決定啓程一探究竟。
抵達緬甸的第一秒鐘我就深深地被吸引住了。透過民運人士、緬甸流放學生、街上居民對緬甸當局的侃侃而談,經過和不同民族的相識,更讓我知道緬甸的重要性。這不單單是為了這個國家的福祉,雖然那是最重要的,但這更是為了一個全球性的提升。深入了解...
目錄
第一章 隨遇而安:自由在我心中
第二章 泳(勇)者
第三章 歸國
第四章 宿命
第五章 秘書處槍擊案
第六章 競選
第七章 童年
第八章 緬甸的「蘇」
第九章 背包家庭
第十章 軟禁
第十一章 被喚醒的世界
第十二章 「我的蘇」
第十三章 意圖謀殺
第十四章 番紅花革命
第十五章 所有的這些紀念日
第一章 隨遇而安:自由在我心中
第二章 泳(勇)者
第三章 歸國
第四章 宿命
第五章 秘書處槍擊案
第六章 競選
第七章 童年
第八章 緬甸的「蘇」
第九章 背包家庭
第十章 軟禁
第十一章 被喚醒的世界
第十二章 「我的蘇」
第十三章 意圖謀殺
第十四章 番紅花革命
第十五章 所有的這些紀念日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3收藏
3收藏

 1二手徵求有驚喜
1二手徵求有驚喜




 3收藏
3收藏

 1二手徵求有驚喜
1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