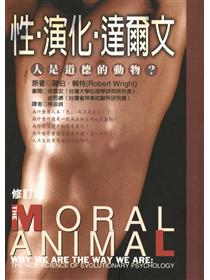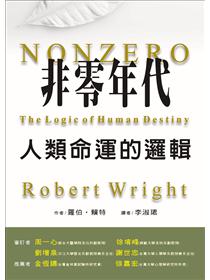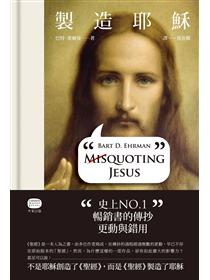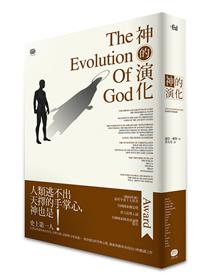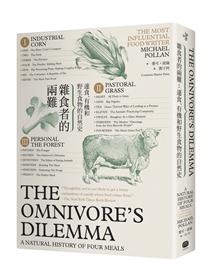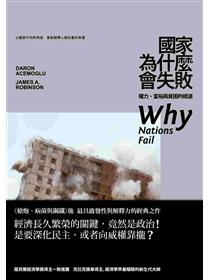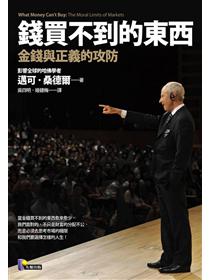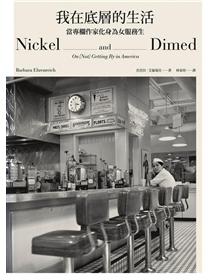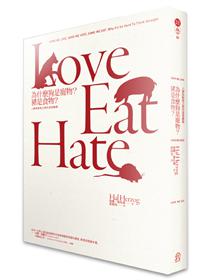人類逃不出天擇的手掌心,神也是!
如果演化是生物存活的最佳利器,那麼,最精此道的就是宗教中的神。
祂的適應力極強,能因應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的變動,開展出最符應當代需求的面目,生存下來。
是永恆不變的神創造並維繫了人類和世界,還是神因應了人類歷史的進展,不斷改頭換面而得以「存活」至今?當我們認為宗教乃超越現世的永恆之道,作者卻發現,宗教起源於一些現世有形可見的因素,並在人類的歷史進展階段,不斷變換樣貌。
部落時期的神祇只需能夠作戰,保佑狩獵採集順利,農耕時期的神祇則需保障作物豐收,君主帝國中的神祇要有助於統馭人民,而工業和資訊時代的神已不再需要扮演物質生活的保障者,卻得填補現代世界帶給人類的心靈空虛,並闡明某種更高目的,某種可讓我們組織日常生活、分辨善惡、弄懂禍福意義的根據。
於是,神祇的功能、意義和面目不斷轉換,而正是這樣轉換讓祂得以在人類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中留存。
因此,當我們認為宗教是神祇對人類的絕對啟示或彰顯,作者卻認為宗教起源於一些可觀察的具體因素,包括人類天性、政治和經濟因素,以及科技的變遷等。也就是說,宗教一開始就是個錯覺,是人類的虛構物以來掌握世界、控制事物,至於神祇觀念及其後續發展,都是這個錯覺的演化。在宗教演化的過程中,原先的錯覺不斷煉淨,變得愈來愈真實。
二十一世紀之後的宗教,神又該換上成何種面目,才能為現代人所接受?如果科學能夠從物質的層次解釋一切,誰還需要上帝?現今各大宗教要怎樣才能繼續回應現代人生存上的需要?各大宗教要怎樣才能彼此調適並跟科學調和?它將會指向何種目的、提供何種方向?真有一種可以通過知性考驗,又確實具有宗教性,也可以在紛亂世局中為個人提供指引並帶來慰藉,甚至讓世界減少一些混亂的世界觀嗎?
作者對於宗教的未來保持樂觀態度,因為道德在過去歷史中的進步,印證了上帝存在的軌跡,而只要人類仍需要神,神就會持續存在,演化出最適應現代人需求的樣貌。至於線索,會在本書講述上帝故事的過程中,自然而然浮現出來。
「本書或許有些惱人、有些爭議,卻是少數能以嚴謹的態度和詳盡的論述,深刻闡明基督和聖戰精神的著作,而你卻不會感到作者在說教。」──《紐約時報》
本書特色
譯者心得
《神的演化》野心相當龐大,把許多學問共冶一爐,處理了許多不同向度的課題,而這些課題又環環相扣。
全書的主幹和一般讀者會較感興趣之處,當然是論人類宗教如何發展演變的部分,先是談了先民社會(狩獵採集社會)、農業初期社會(酋邦)和國家層次社會(美索不達米亞和古埃及等)的宗教特色及其現實根源,然後談了從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一神教各自的內部演化及彼此間的演化關係,非常詳盡。這部分(伊斯蘭教除外)是作者綜合前人成果(包括人類學和聖經考據學等)而得,不算太有創見,但仍然非常有趣而條理井然,涵蓋幅度前所未有。我個人最喜歡談古以色列人(猶太教)的部分,因為類似作品較少見,讓人耳目一新,豁然開朗。
但這書的基本目的不在宗教史本身,而在利用這宗教史展示作者自己悟得的一套歷史哲學,並進而以這歷史哲學服務兩大目的︰論證「上帝」可能存在(至少是論證這宇宙具有意義性而非一死物),以及為處於宗教傾軋狀態的全球化社會指出一條出路。(「歷史哲學」是指探索歷史模式、意義、目的的思考,這個領域在黑格爾達至高峰,但自史賓格勒以後便沒有多少有新意的見解,但作者的歷史哲學卻頗新鮮,而其不同於先前各種歷史哲學之處是它具有開放性。)對於「人類是否一直在進步?」這個老問題,他也一反近幾十年普遍的悲觀見解,大膽給予一個肯定答案。
達爾文的演化論是現代學問的基本基礎之一,任何有關宗教的嚴肅探討都不能迴避,作者沒有迴避,直接站在演化論的立場對付了此問題。
編輯心得
宗教的目的就是處理人存在的問題,解決人存在的焦慮而找到安身立命的方式。因而一般人認定宗教乃是超凡入聖且超然於物外,才能以接近永恆的觀點來考察人世。然而,作者卻舉出多如牛毛的歷史例證,清晰證實了宗教的發展軌跡不但與政治情勢和經濟利益互相糾結,更提出宗教的性格和諸神的面目,是隨著人類文明進程一起演化。
然而,作者認為這樣沾染塵世的宗教,反而是更有生命力的宗教。宗教能在既服務政治又批判政治的緊張關係中,迸發出更貼近人類需求的功能。
過去我們總對於宗教投注過多形而上的幻想,今日,凡是靈性饑渴而又知性嚴肅的宗教人士或信徒,都總得跟這些證據格鬥,想辦法調和信仰和證據間的扞格。
作者於是從交代宗教過往的發展,清晰展演了他調和靈性需求和知性挑戰的過程。不管是信神還是不信神,讀來都讓人覺得暢快淋漓、如獲天啟。
作者簡介:
羅伯.賴特 Robert Wright
在現代知識分子圈內,認真思考上帝存不存在不是讓大家尊敬你的好方法。但作者明知故犯!
出生在美國保守的浸信會家庭,著作中以科學精神檢驗人類道德和宗教的根源,惹惱教會牧師,在台前大肆抨擊!
看似兩面不討好,實則以清晰誠實的科學精神和開放寬厚的宗教情懷,為上帝與現代社會開創雙贏的生存局面。
史上第一人以賽局理論來談宗教和人類道德,以唯物主義來理解宗教的誕生,並以演化的角度來理解人類歷史中的神。
《紐約時報》最佳年度十大作者,曾獲美國國家雜誌獎、入圍普立茲獎、提名美國國家圖書評論獎。
譯者簡介:
梁永安
台灣大學人類學學士、哲學碩士,東海大學哲學博士班肄業。以翻譯為業,譯有《下一個基督王國》《今日,何謂歷史?》《現代主義:異端的誘惑》《李維史陀:實驗室裡的詩人》等。奉編輯之命在此說幾句譯後感:這書給人最突出的印象是「豐富」,涉及面極廣,又能環環相扣,有結構之美,內容亦相當有趣。作者悟得的一套歷史哲學別出心裁,自成一家之言。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基原信仰
西伯利亞原住民楚克奇人(Chukchee)有一套對付狂風的方法。倘若遇到狂風,楚克奇男人口中會念念有詞:「西風,看過來!看著我的屁股。我們準備要向你獻上肥油。停止咆哮!」十九世紀一名到過該地人的歐洲人,對個這儀式做如下描述:「那人念著咒語,又脫下短褲,對著下風處露出光屁股。他每說一個字就拍一下手。」
及至十九世紀末期,歐洲旅行家已經到過許多遙遠而鮮為人知的地區,留下為數可觀的儀式觀察報告。這些遙遠地區的居民有時會被稱為野蠻人(savage),他們沒有文字,甚至不懂農耕,而他們有一些儀式(如上述那個)看起來相當古怪。
這類儀式可以稱為宗教嗎?有些歐洲人對這種類比感到氣憤,認為把他們莊嚴肅穆的的崇拜和野蠻人討好大自然的膚淺舉動相提並論極不恰當。
這也許就是何以約翰.盧伯克(John Lubbock)寫他論「野蠻宗教」的著作時,先在序言裡向讀者提出警告。在《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狀態》(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of Man)一書中,這位十九世紀英國人類學家指出:「討論這個課題時,難免要提及一些讓我們深感厭惡的事情。」但他又向讀者保證,他在探討「粗糙迷信的淒涼景觀和各種粗暴的崇拜方式」時,會「盡可能避開那些使讀者感到不舒服的東西。」
為了不讓讀者不舒服,盧伯克絕不去猜想現代人的腦子和野蠻人的腦子也許會有相似之處,反而表示︰「野蠻人的整個心靈狀態跟我們的差距之大,以致我們常常很難搞懂他們在想什麼,或搞懂是什麼理由驅使他們這麼想。」雖然野蠻人「的做事和信仰總有理由,但他們的理由總是很荒謬。」野蠻人的「智力極端低下」,心智「跟小孩沒兩樣,很容易疲倦」。因此,很自然的,野蠻人的宗教觀念「不是深思的結果」。
盧伯克一再說些讓讀者安心的話:「低下野蠻種族所理解的宗教」不止有別於文明的宗教,而且是「恰好相反」。事實上,如果我們用「宗教」一詞來稱呼他們那些粗糙的儀式和迷信,那麼「我們就不能認為宗教是人類所獨有」,因為你一樣可以把「狗吠月亮視為一種崇拜儀式。」
受過高等教育的英國基督徒會那麼鄙夷「原始宗教」也許不令人驚訝(「原始宗教」一詞泛指無文字社會的宗教,不管是狩獵採集或農業社會都一樣)。畢竟,原始宗教充滿著許多幼稚的迷信,包括常常仰賴意義隱晦的卜兆來決定要不要打仗、相信死人的亡靈會捉弄活人,或相信活人可以透過靈媒從亡靈獲得指引。簡言之,原始宗教充滿迦南(Canaan)多神教所具有的各種糟粕,而誰都知道,這些糟粕後來被摩西帶出埃及的一神教一舉廓清。
但事實上,以色列一神教對迦南多神教的取代並不是一刀切的,而證據就在《聖經》本身(只是相關的經文現代信徒並不常讀)。在《聖經》裡,你會看到以色列第一任國王掃羅(Saul)微服去找靈媒召來先知撒母耳(Samuel)的亡魂,好向他請教國事(撒母耳對此很不高興:「你為什麼攪擾我,招我上來呢?」 )。在另一個地方,《聖經》又記載(這是更明顯的迷信),先知以利沙(Elisha)為了讓國王約阿施(Joash)可以打敗亞蘭人(Arameans),交代他拿箭支擊打地面。但約阿施只擊打地面三次便停住,以利沙為此深感失望,告訴國王:「你應當擊打五、六次,那樣,你就能連連打敗亞蘭人,直至把他們給滅盡;現在你只能打敗亞蘭人三次了。」
就連亞伯拉罕系信仰最終極的神學元素,即「一神主義」,在《聖經》裡也是時有時無。雖然很多經文都認定上帝是獨一真神,但有些經文卻彈著不同的調。例如,據〈創世記〉 所述,曾有個時期,一群男神會跑下凡間,找「人類的女子交合生子。」(這些眾神後代可不是泛泛之輩:「他們都是上古時代赫赫有名的戰士。」)
所以,《希伯來聖經》(它是亞伯拉罕系信仰的最早經典,換言之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起點)不時會流露出一些遠古宗教的殘餘物。很顯然,亞伯拉罕系一神主義乃是從「原始」宗教裡有機地生長出來的,其過程更像是演化而非革命。
這倒不是說,人類學家記錄在案的那些「原始」宗教與我們今日所信奉的現代宗教之間,存在著直接的血緣關係。換言之,我不是要主張,在三、四千年前一神教徒懂得跪下來向上帝說話之前,先經歷了一個脫下褲子對風說話的階段。就我們所知,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文化先祖並沒有對風說話的儀式,而我們也沒有憑據認為,在公元前第一千紀或第二千紀 的時候,西伯利亞的楚克奇文化影響過中東地區的文化。
我要主張的毋寧是,廣義的「原始」宗教(人類學家和其他歐洲旅行家記錄下來的那些)有可能可以讓我們對現代宗教的遠古背景有個梗概了解。由於地理上的孤立,「原始」文化(如楚克奇文化)沒有受到技術革命(特別是文字的發明)的洗禮,因而不像世界其他地區那樣留下歷史記錄和邁向現代性(modernity)。但即使這些「原始」文化」未能顯示出最早有歷史記錄的宗教所從出的史前宗教是何種具體模樣,它們至少能顯示出其大體輪廓。雖然一神教徒的禱告不是源自楚克奇人的儀式或信仰,但一神教徒的禱告邏輯說不定跟楚克奇人的信仰模式相去不遠:即相信各種大自然力量是由某些超自然生靈所引動,並相信人可以透過協商去影響這些力量的運作。
野蠻人的邏輯
事實上,這就是十九世紀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Edward Tylor)所提出的理論。泰勒是大有影響力的思想家,有些人視之為社會人類學的奠基者。他與盧伯克相識,有時會批判後者的觀點,主張最基原(primordial)的宗教形式是「萬物有靈論」(animism)。在當時的學界,泰勒的理論是解釋宗教如何起源的主流學說。一位二十世紀早期的人類學家指出,這理論「一提出便所向披靡」。
泰勒的理論奠基於十九世紀人類學的一個範式(paradigm):文化演化主義(cultural evolutionism)。這主義一度大盛,其後沒落,但最後又捲土重來。其主要觀念是:廣義的人類文化(藝術、政治、科技和宗教等)就像生物物種一樣,是會演化的。新的文化特徵會一再出現,有些繁榮茁壯,有些走向衰微,而整套制度和信仰系統也會相應形成或改變。所以,不管是宗教儀式或神祇觀念也是會演化的,會在經歷一段成長茁壯期以後,演化為新的宗教儀式或新的神祇觀念(如從相信神祇為數眾多改為相信神只有一位)。泰勒的理論正是致力於解釋一神教是如何從原始宗教演化出來。
人們有時會把「萬物有靈論」定義為一種相信死物具有生命的態度:原始人視河流或星辰為有生命之物即是一例。泰勒所說的「萬物有靈論」包含這種意義,但不僅止於此。更充分來說,「萬物有靈論」應是指相信任何事物(不管是活物還是死物)全都內住著一個魂或靈,並由這魂或靈所「活化」。所以,在「萬物有靈論」看來,不管是河流或雲朵,是飛鳥、走獸還是人類,都擁有一個「蒸氣般、薄膜般或陰影般」的靈魂,而「個體會因這靈魂而活化,產生生命和思想。」
泰勒對「原始」心靈的評價要遠高於盧伯克(「人類心靈統一性」的觀念就是泰勒首倡,而這觀念後來也成了社會人類學的一根基柱。根據這觀念,所有人類種族的心智是一樣的,古今中外的人類天性並無二致)。他不認為「萬物有靈論」完全荒誕不經,跟現代人的思維方式背道而馳,反而相信原始人的古怪思辨是人類好奇心的自然產物——現代的思維方式正是源發於同一種好奇心。職是之故,他把「萬物有靈論」稱為「人類襁褓時代的哲學」,又把構思出這套「理論」的原始人稱為「古代的野蠻人哲學家」。「萬物有靈論」具有其他好理論的相同特徵:能以簡約的方式解釋一些看起來神祕的現象。
首先,這個人類有靈魂的假設可以解釋一些泰勒認為早期人類一定會想到的問題,例如:人在做夢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原始社會用靈魂觀念解決了這個難題。有些原始社會相信,人會做夢,是因為靈魂離開了身體,到外頭晃蕩,而夢境的內容正是靈魂離開身體後的遭遇。晚泰勒幾十年的人類學家芮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指出,安達曼群島(Andaman Island)的島民很不願意叫醒熟睡的人,深信不等睡夢中人的靈魂回到身體便把他叫醒,有可能讓他致病。有些原始社會則是相信,人會做夢,是因為有其他靈魂造訪。泰勒指出,在斐濟群島,人們相信人的靈魂可以出竅,去「騷擾其他在睡覺的人。」
另外,大多原始社會都相信,死者會透過夢造訪活人。所以,「萬物有靈論」可以幫助早期人類面對另一個謎題:死亡。根據「萬物有靈論」的觀點,死亡所意謂的是靈魂永遠離開身體。
泰勒認為,早期人類一得出人有靈魂的想法,自然就會把靈魂觀念擴大應用到人類圈之外。這種擴大應用是合乎邏輯的,因為野蠻人自然也會意識到,野獸「具有擁有靈魂的人類的種種特徵,即有生也有死,有意志也有判斷力。」植物也是如此,因為植物「就像動物一樣,有生也有死,有健康的時候也有生病的時候,所以,認定植物具有某種靈魂並非不合理。」
職是之故,從「未開化部落」的觀點來看,認定竿子和石頭擁有靈魂乃是合乎理性的。因為竿子和石頭不是一樣會出現在夢中嗎?我們做夢或發高燒時所看到的鬼魂不是穿著衣服和攜帶武器的嗎?所以,「既然野蠻人的這種觀念是以感官經驗為證據,我們又怎能指控野蠻人的哲學和宗教太過荒誕不經?」泰勒以下的這番話,也許是在暗批盧伯克的觀點:「認定他們的行為是無動機的,認定他們的意見是荒唐的,這本身就是一種理論,而我相信,這種理論錯得厲害,是那些不明白事情來龍去脈的人想出來的,好輕鬆地把問題打發掉。」
泰勒相信,一旦「萬物有靈論」的世界觀確立,它就會開始演化。例如,起初人們都是相信每棵樹皆有一個靈魂,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他們會改為相信所有樹都是由一個「森林之神」所管轄。接著,這種初始的多神教會慢慢成長、茁壯,最終又會經過瘦身,演變為一神教。一八六六年,泰勒在《雙週評論》(Fortnightly Review)發表的一篇文章裡,用一句話概括了宗教的發展歷程(這句話有可能是任何出版過的文字中最長的一句)︰
透過所有這些漸進的階段——即從最簡單的理論(把生命與人格賦予動物、植物與礦物),上升至認定石頭、植物或河流之間住著一個保護精靈,負責照管它們的保存、生長與變遷,再上升至認為世界每個領域都有一個相應的神祇加以保護和看顧,最後進相信有一個最高存有(Supreme Being)負責指揮和管控下面的層級——我們可以看出一趟漫長的角力︰角力的一方是「萬物有靈論」,它認定事物皆具有如同人類一般的生命,以此來解釋所有自然現象;另一方是緩慢成長的自然科學,它在一個領域接一個領域以系統性法則取代獨立自發的活動。
這說法有問題嗎?
有,而且問題還不少。事實上,泰勒的理論在日後未能保有當初的崇高地位。有些人批評它讓神的演化顯得太像一種純理性的思考運作,忽略了宗教一直受到許多因素的形塑,不曉得從政治到經濟到人類情緒等因素皆可影響宗教的樣貌。今日和泰勒時代的「文化演化主義」的不同處在於,前者強調某些「彌因」(meme,指儀式、信念等文化基本單位) 之所以能脫穎而出,是因為它們對人性中的非理性部分有吸引力。
儘管如此,在廣義的角度下,泰勒的觀點至今還站得住腳。因為不管形塑宗教的力量有多麼分歧,它最早的動力確實看來主要是這個:人類理解世界的願望。不過,由於早期人類沒有現代科學的幫助,以致得出一種不科學的結論。隨著人類透過科學對世界的理解漸增,宗教也以演化作為回應。因為這樣,泰勒才會說,在「野蠻的拜物者和文明的基督徒之間」,存在著「沒有斷裂的心智連結性(mental connexion)」。
在這個層次上,泰勒的世界觀不但經得起現代學問的審視,還從現代學問得到了支持。例如,演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即指出,不管原始人的信仰看來有多麼稀奇古怪(或不管「現代」宗教信仰在不可知論者和無神論者眼中有多麼稀奇古怪),它們都是從人類天性中自然生長出來,是人腦(這腦子是天擇過程所設計)的自然產物。在科學尚未出現的時代,人腦想要弄懂世界,可憑藉的只有一些雜七雜八的工具,所以只能得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結論。但就動機而言,他們卻不是不理性的。
本書的「附錄」綜合了現代各種學術研究成果,較仔細探討了「原始」宗教是如何源自人的心智。目前,我要指出的只是,泰勒對於宗教是如何從「萬物有靈論」演化為一神教的猜想,雖然從現代的制高點看起來有其不足之處,很多部分卻依舊說得通。它特別有啟發性的是這一點:想要了解神祇乃至上帝在最早階段的演化,我們就得設身處地想像生活在幾千年前的人是怎樣看待世界,而當時不僅沒有科學,就連文字甚至農業都尚未出現;另外,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憑藉乃是人類學家一直在研究的那些狩獵採集社會 ──即盧伯克和泰勒口中的「野蠻人」社會。
當然,如果我們能夠直接觀察史前社會將是更好不過,那樣,我們將會更具體了解,最早有歷史記錄的那些宗教是如何從史前宗教演化而成。但既然當時還沒有文字,我們自不可能有這方面的詳細資料。它們唯一留存的只有考古學家找到的東西:東一點、西一點的工具和小器物,以及偶爾一見的洞穴繪畫。換言之,人類的前文字階段留下了一片巨大空白,而想要填補這空白,我們只能藉助那些被觀察過的狩獵採集社會,因為這方面我們有大量的文字資料可資利用。
以狩獵採集社會作為了解過去的窗口是有侷限性的。例如,人類學家所研究過的狩獵採集社會文化,沒有一個是「純淨無染的」;換言之,沒有一個社會是完全未曾跟更先進的社會接觸過的。別的不說,人類學家能對這些文化進行觀察,就意味著它們與外界有過接觸。此外,在人類學家能把它們的宗教記錄下來之前,通常已經有傳教士或探險家造訪過。
另一方面,只要某個原住民文化的宗教信仰在外人眼中看來「怪異」,就表示該宗教信仰並未受到外界太多影響。例如,楚克奇人對風奉獻自己光屁股的儀式,就不太可能是從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傳教士那裡學來的。
還有,如果我們在各大洲的狩獵採集社會都能看到某種相同的「怪異」信仰成分,那麼該成分就更不可能是舶來品,而更有可能是狩獵採集居民生活方式的忠實原貌。等一下我們就會看到,許多狩獵採集社會的觀念都通得過上述兩項考驗,也就是不但廣泛分布,而且又很怪異(至少在我們眼中顯得古怪)。所以,我們多少有理由可以認定,憑著它們,可以重建史前時代的宗教風貌。
現在已經沒有人會像十九世紀某些人類學家那樣,相信狩獵採集社會可以活脫脫反映宗教在幾萬年前剛肇始時候的樣貌。但這些社會仍是幫助我們了解宗教在公元前一萬二千年時大體樣貌的最佳線索。洞穴繪畫是引人入勝的,但它們並不會說話。
狩獵採集社會的神
反觀克拉馬斯人(Klamath,住在今日的美國俄亥俄州)卻是會說話的。對我們來說,幸運的是,他們曾經對非常有同理心的西方人艾伯特.加切特(Albert Samual Gatschet)說過話。加切特是語言學的先驅,曾經在一八七○年代為克拉馬斯人的語言編撰了一部字典和文法書。從加切特的記載,我們得知克拉馬斯社會包含著每個狩獵採集文化都具有的某些特徵:相信有超自然生靈,而且相信這些超自然生靈為數眾多(狩獵採集社會沒有本土一神教這回事)。
事實上,從人類學家的記載,我們可以歸納出全體狩獵採集社會至少具有五大類型的超自然生靈,這些生靈大多可以在大部分狩獵採集社會找到,有些社會(如具有豐富神學的克拉馬斯社會)更是五者兼備。
第一類超自然生靈:基本的靈。現代科學家認定是無生命的自然現象,在許多狩獵採集社會看來是具有智慧、人格和魂(soul)的。所以,大自然的運作也儼然是一齣社會互動劇碼。例如,在克拉馬斯人看來,每當月亮被烏雲遮蔽,就意味著穆亞虛(Muash,即南風)想要殺死月亮。雖然南風有時候會得逞,不過到頭來月亮總能死而復生。
第二類超自然生靈:傀儡操縱者。有些狩獵採集社會相信,有一部分自然現象會受到自然界以外的靈體操縱。例如,克拉馬斯人就相信,「西風」是一個腸胃氣脹的侏儒女人所排出,她大約三十英寸高,身穿鹿皮衣,頭戴一頂水桶帽,會化身為岩石,出現在一座山上。克拉馬斯人有時會祈求她把所有蚊子從鵜鶘灣(Pelican Bay)給吹走。
把第一類和第二類超自然生靈結合是可能的。例如,克拉馬斯人相信,旋風是由一個叫蘇克虛(Shukash)的風內靈體所驅動,但住在附近的莫多克人(Modoc)則進一步相信,蘇克虛是由塔希查撒亞虛(Techitchatsa-ash,意指「大肚子」)所控制。後者肚子裡裝著一些會格格作響的骨頭,而旋風的古怪聲音就來自這些骨頭。 這類神學差異不止存在於不同的狩獵採集社會之間,還存在於同一個狩獵採集社會之內。例如,有些克拉馬斯人相信雷神尼米舒(Leme-ish)只是單一個靈體,但另一些克拉馬斯人則把「他」視為是五兄弟,相信他們是因為受到上流社會驅逐,於是製造一些雷聲來嚇唬人(這些詮釋上的分歧乃是文化演化的原材料,一如生物學突變所產生的特徵分歧可推進物種的演化)。
第三類超自然生靈:動物靈。有些狩獵採集社會相信某些動物擁有超自然力量。例如,克拉馬斯人相信,郊狼的身體裡住著惡靈。加切特指出,克拉馬斯人認為郊狼的「悲鳴聲是戰爭、災禍和死亡的前兆。」有些種類的鳥被認為會製造雪,另一些種類的鳥被認為會製造霧。還有些動物靈可以幫人治病。相傳,有個叫亞亞亞艾虛(Yayaya-ash)的靈體會化身為一個獨腿漢,帶巫醫到動物靈的家求教治病方法。
第四類超自然生靈:祖靈。幾乎每個狩獵採集社會都相信,人死後會變成祖靈,而這些祖靈會帶來福氣也會帶來禍患。加切特指出:「祖靈總是克拉馬斯人害怕和厭惡的對象,而因為人們相信祖靈無所不在且無影無形,所以愈發害怕和憎惡。」
第五類超自然生靈:至高神。部分狩獵採集社會相信有至高神的存在。但這個神並不控制其他神祇(二十世紀初有位人類學家在談到克拉馬斯人的宗教時,曾語帶可惜地指出:「他們從未嘗試把各神靈排列成一個高低有序的層級系統。」)至高神只在某些模糊的意義下比其他神祇重要,而且往往是一個創造主。在克拉馬斯人,這個至高神就是住在太陽裡的坎木堪齊(Kmukamth)。坎木堪齊首先創造出世界,再用紫色的漿果創造出克拉馬斯人,此後繼續照顧他們的生活(不過,這個神有時也會生氣而降下燙人的瀝青)。
那麼,這些神與靈的作用何在?(神與靈的界線是極其模糊的,我在本書會一律用「神」來涵蓋兩者)。顯然,對克拉馬斯人來說,這些神的一大用途是解釋一些非如此解釋不了的神祕自然現象。以上提到的超自然靈體(他們只是克拉馬斯人全體神靈清單的冰山一角)解釋了天為什麼會下雪、刮大風、打雷,月亮為什麼會被雲遮蔽,也解釋了人為什麼會夢見已死的人,等等。每個已知的狩獵採集社會都會藉助超自然向度來解釋自然現象。更精確地說,他們都會藉助我們認定的超自然向度來解釋自然現象。我會這樣說,是因為在狩獵採集社會看來,各種超自然生靈是跟自然界無縫地交織在一起的,情形就像是現代科學把萬有引力看成自然界的一部分。
這點引出了狩獵採集宗教一個弔詭特質:這種社會並沒有宗教這回事。如果你問一個狩獵採集社會的居民他信什麼宗教,他會不明白你在問什麼。這是因為,我們所稱為「宗教」的信仰跟儀式,跟他們的日常生活是密合無間的,以致他們根本不會想到要給它單獨取名。對於他們解釋世界的方式,我們也許會區分為「超自然解釋」和「自然解釋」兩種,但「超自然」和「自然」都只是我們的範疇,不是他們的範疇。對他們來說,生病時去找出是哪個神祇搞鬼乃是「自然」不過,就像我們生病時「自然」會想知道病是由哪些病毒所引起。這種宗教與非宗教生活的緊密交織會一直持續到有文字歷史之後的好一段時間。古希伯來文(《聖經》的主要語言)是沒有「宗教」這個詞的。
我尊重狩獵採集社會的風俗,也尊重古希伯文,但還是會繼續使用「宗教」與「超自然」兩個詞,一來是為了方便跟讀者溝通,二來是出於一個層次更深的理由:我相信,狩獵採集文化裡被我們稱為「宗教性」的那個部分,後來透過文化演化,蛻變而成現代的宗教。
第一章 基原信仰
西伯利亞原住民楚克奇人(Chukchee)有一套對付狂風的方法。倘若遇到狂風,楚克奇男人口中會念念有詞:「西風,看過來!看著我的屁股。我們準備要向你獻上肥油。停止咆哮!」十九世紀一名到過該地人的歐洲人,對個這儀式做如下描述:「那人念著咒語,又脫下短褲,對著下風處露出光屁股。他每說一個字就拍一下手。」
及至十九世紀末期,歐洲旅行家已經到過許多遙遠而鮮為人知的地區,留下為數可觀的儀式觀察報告。這些遙遠地區的居民有時會被稱為野蠻人(savage),他們沒有文字,甚至不懂農耕,而他們有一些儀式(...
作者序
序言
一九九四年,家母所屬的教會對我發出譴責。當時拙著《道德動物》(The Moral Animal)剛出版,而且有幸獲得《時代》雜誌摘錄刊出。轉載的那部分內容談到,婚姻制度之所以搖搖欲墜,是因為它不盡符合人類演化而成的天性︰容易出軌乃放諸四海皆準的共通人性。《時代》的編輯部也刻意在雜誌封面凸顯這一點︰除了一幅怵目驚心的圖片(一枚裂開的結婚戒指),封面上還寫著:「對配偶不忠:該因子也許就在你我的基因裡」。
加州聖塔羅莎第一浸信會的牧師讀到了這篇文摘,視之為無神論者的厚顏無恥論調,並在週日早上於會眾面前狠狠數落了一頓。禮拜結束後,家母走到教堂前面,告訴牧師,文章作者就是她兒子。我敢打賭,她說這話時的語氣一定是充滿自豪(這就是母愛的奇妙之處)。
看看我墮落得多厲害!猶記九歲那年,我在德州埃爾帕索的以馬內利浸信會教會,因為感受到上帝的呼召而接受佈道家馬丁內斯(Homer Martinez)的「邀請」,走到教堂最前面悔改認罪,接受耶穌為救主。幾週之後,我在同一教堂受了浸禮。然後,事隔將近三十年,另一位浸信會牧師卻認為我跟撒旦同夥。
不過,我相信,如果這位牧師有仔細閱讀《時代》雜誌的文摘,便不會那麼怒氣沖沖(我在文中主張,通姦衝動雖然屬天性,卻是抗拒得了也應該抗拒的)。然而,也有些人在讀完整本書後還是認定我是某種無神論者。這是因為我在書中主張,人類某些最不食人間煙火的高貴情操(如愛、自我犧牲和道德情感等)都是天擇(natural selection)的產物。該書看來徹頭徹尾是一部唯物主義小冊子,就像是主張︰「既然科學能夠從物質的層次解釋一切,誰還需要上帝?特別是一位可以神奇地超越物質宇宙的上帝?」
我認為,用「唯物主義」界定我的立場不算錯誤。事實上,在各位手上這本書中,我就是從唯物主義的立場來談宗教的歷史與未來。我相信,宗教的起源和發展都可以歸結到一些可觀察的具體因素,包括人類天性、政治和經濟因素,還有科技的變遷等等。
然而,我不認為用「唯物主義」來探討宗教的起源、歷史與未來,必然會否定宗教世界觀的有效性。事實上,我相信,本書所呈現的宗教史雖然是唯物主義取向,它卻又同時承認宗教世界觀的有效性。不過,這裡所說的宗教世界觀並非傳統意義下的那種。
這話聽起來很弔詭。我一方面相信,宗教是起源於錯覺,而神祇觀念的後續發展都是這個錯覺的演化;另一方面,我又相信:(一)宗教的演化故事向我們顯示,有可能真有某種神祇(divinity)存在 ;(二)在宗教演化的過程中,原先的「錯覺」不斷煉淨,變得愈來愈真實。在這兩個意義下,原先的錯覺都變得愈來愈不像錯覺。
這話說得通嗎?大概說不通。但我希望,讀者在讀完本書以後會覺得它說得通。不過,我還是要事先聲明,即便神祇的觀念煉淨後會更有可信性,它仍然不是大多數信徒所相信的那種神祇。
本書最後還會探討另外兩個課題,這兩個課題都跟當代世界的處境息息相關。
一是所謂的「文明的衝突」,也就是「猶太教–基督教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緊張關係,最受到矚目的展現就是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自那之後,人們一直納悶,發源自亞伯拉罕的三大宗教在隨著全球化的進程而接觸愈發頻繁之際,要如何才能和平相處?
其實,文明衝突的事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而職是之故,文明不衝突的事例亦屢見不鮮。在文明有時衝突又有時不衝突的人類歷史裡,宗教觀念所扮演的角色很具有啟發性(它們有時扮演煽風點火的角色,有時扮演澆熄烈火的角色,而且常常隨著大環境的變遷改變角色)。我相信,以這部歷史為鑑,我們將會更知道該如何處理當前的「衝突」,才能獲得較完滿的結局。
第二個我要探討的當代處境是另一種常受到討論的衝突,即科學與宗教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與第一種衝突雷同,其歷史悠久且具啟發性。科學與宗教的衝突至少可以上溯到古巴比倫時代,當時第一次有人發現,日月蝕的出現是有固定週期的,因此是可預測的,從而不再需要用某個不安好心的神祇來加以解釋。
在那之後,有更多這類讓宗教不安的發現出爐;儘管如此,神祇的觀念總是可以挺得住科學的衝擊,繼續存在。在這個過程中,神祇的觀念不得不一再作出若干改動,但宗教卻仍繼續屹立。事實上,同樣的情形也見於科學:科學本身也是一直在變動,不斷修正甚至摒棄舊理論,但沒有人會因此認定科學已經動搖,反而認為科學經過不斷重新適應的過程,會更加趨近真理。也許,相同情形也發生在宗教身上。也許,到最後,科學對人性的冷酷解釋終將跟某種宗教性世界觀並行不悖,而在這個過程中,宗教的世界觀也會不斷獲得煉淨,愈來愈接近真理。
我們可以把這兩大課題綜合為一個問題:現代世界的三大一神教有可能彼此調和,並且與科學調和嗎?衡諸三大一神教的歷史,我相信答案是傾向肯定的。
那麼,在經過這樣的調適後,宗教會變成什麼模樣?出人意外的是,這個問題相當容易回答,至少要勾勒其大致的輪廓並不難。首先,宗教必須能填補現代世界帶給人類的心靈空虛(否則宗教不會獲得接納)。其次,宗教必須要能闡明某種「更高目的」(higher purpose)︰某種可以讓我們組織日常生活、分辨善與惡、弄懂禍福意義的根據(否則宗教便構不成「宗教」)。
接著輪到真正難答的問題。各大宗教要怎樣才能達成這樣的壯舉?(它們最好是能做到,否則我們所有人,包括信徒、不可知論者和無神論者,也許就會陷入大麻煩。)各大宗教要怎樣才能彼此調適並跟科學調和?在一個科學突飛猛進和快速全球化的時代,怎樣的宗教才適合?它將會指向何種目的,提供何種方向?真有一種合乎知性又包含宗教性的世界觀,是可以在紛亂世局中為個人提供指引,帶來慰藉,甚至讓世界減少一些混亂的嗎?我不敢自稱知道答案,但線索會在我們講述上帝故事的過程中,自然而然浮現出來。所以,讓我們開始吧。
序言
一九九四年,家母所屬的教會對我發出譴責。當時拙著《道德動物》(The Moral Animal)剛出版,而且有幸獲得《時代》雜誌摘錄刊出。轉載的那部分內容談到,婚姻制度之所以搖搖欲墜,是因為它不盡符合人類演化而成的天性︰容易出軌乃放諸四海皆準的共通人性。《時代》的編輯部也刻意在雜誌封面凸顯這一點︰除了一幅怵目驚心的圖片(一枚裂開的結婚戒指),封面上還寫著:「對配偶不忠:該因子也許就在你我的基因裡」。
加州聖塔羅莎第一浸信會的牧師讀到了這篇文摘,視之為無神論者的厚顏無恥論調,並在週日早上於會眾面前狠狠數...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35收藏
35收藏

 89二手徵求有驚喜
89二手徵求有驚喜




 35收藏
35收藏

 89二手徵求有驚喜
89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