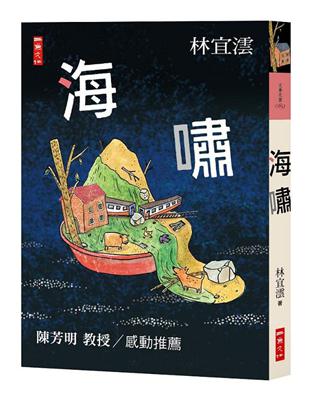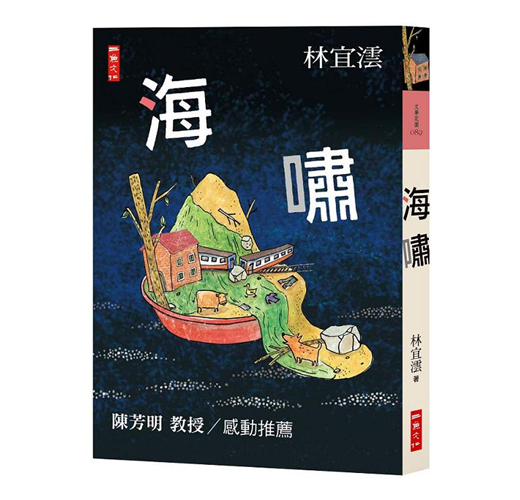內文1
冬冬找媽咪
小甥女冬冬在自己嘹亮的哭聲中聽見鈴響。她坐在倒塌下來的酒櫃旁邊,破碎的軒尼詩威士忌讓她家客廳變成一個陰暗嗆鼻的酒窖。小冬冬讀小學三年級,這種年紀並不真的知道什麼叫危險:如果剛剛酒櫃倒下來的角度再往右偏一些,冬冬小甥女可就要到天堂陪外公玩五子棋了。也就是說,現在坐在地上哇哇大哭的小冬冬渾然不知自己剛從死神的跨下鑽了出來,一股陰森的死亡氣味還圍繞在她身旁猶未散去呢。
鈴聲繼續響,小冬冬決定暫停哭泣,她打算摸黑去接電話,地震造成的停電讓整棟公寓的白天變得比黑夜還黑。可能是媽咪打的,媽咪去哪了?媽咪每個週末下午都打扮得像聖誕老公公那樣出去找男人,這可不是小冬冬自己胡亂猜的,是爸爸說的。爸爸跟媽媽吵了幾年架之後,終於決定不住在一起了。爸爸搬到一位邱阿姨家裡去,邱阿姨每天都穿三條絲襪以維持腿部曲線的優美,並且渾身上下塗抹了各種品牌的香水、乳液、指甲油等等不同的化妝品,搞得全身香氣四溢,讓小冬冬每次在她前面就不停地咳嗽、打噴嚏。不過小冬冬還是蠻喜歡她,雖然她這樣努力打扮自己之後還是難掩年華老去的模樣,比不上媽咪的年輕貌美,但她會買很多東西給小冬冬,芭比娃娃、科學讀物、腳踏車、維他命C、童話錄音帶,各式各樣的東西。
小冬冬當然更喜歡媽咪,她每天都要讓自己的手掌給壓在媽咪肥潤的屁股下一陣子才能安然入睡。所以她到現在還跟媽咪睡一個房間,她熟悉媽咪睡覺時的體味,那種沐浴乳和洗髮精的芳香比邱阿姨的香水味要好多了。小冬冬可以好幾個禮拜沒看到邱阿姨,卻不能一天沒有媽咪。
不久她憑著準確的記憶摸到了電話,這種冷靜而睿智的天賦泰半遺傳自她媽媽,如果像爸爸就糟了,她爸爸的現實比夢境更詭譎難懂。
「喂!媽咪!」小胖妹冬冬篤定地對著電話筒說話。
「媽咪!媽咪!」
「媽咪!媽咪!」
但她很快便發現,這支電話其實早已被割斷咽喉而完全失去了聲音,一點點嗡嗡聲或吱喳的雜訊都沒,話筒裡那個世界跟話筒外這棟公寓一樣,都跌進了一大片的死寂中。而,就如同暴風雨來臨之前多半有一陣可怕的寧靜,眼前這樣的死寂意味著,剛剛那場地震已經為這市鎮帶來一場大災難,只不過在這市鎮驚魂落定,回過神來之前,所有的空氣都暫時凝結成這幅寧靜安詳的模樣罷了。
小冬冬還小,她無法體會這種寧靜裡頭所隱藏的巨大恐怖。鈴聲繼續響著,在這麼安靜的環境中,這唯一的鈴響聽起來竟彷彿也是靜默的。鈴聲靜默地響著。這很弔詭的感覺此時把小胖妹冬冬緊緊裹住。不久後她聽出那是家裡一只鬧鐘的聲音,黃色的、上面印了一隻啄木鳥的小鬧鐘。鬧鐘在黑漆漆的公寓中跟小冬冬玩捉迷藏,鬧鐘在哪裡呢?媽咪又在哪裡呢?媽咪也跟小冬冬玩捉迷藏。一點都不好玩的捉迷藏。小冬冬愈想愈氣,一氣便噘起了嘴巴,那嘴巴愈噘愈高,愈噘愈高,到快要高過自己頭頂的時候,她終於忍不住趴在電話旁邊又號啕大哭了起來。
內文2
A片論述DIY
就像陳新老師在巴哈音樂中渾然忘我,而阿鼻仙仔教練因為惦記著棒球,根本就無視於地震的存在那樣,失業青年毛太郎在另外一個領域裡找到了最可以讓他放鬆身心,忘掉一切煩惱的方式:看A片。看A片讓他不知道地震是為何物,看A片讓他不知道什麼叫做害怕。唉!真是多麼幸福美滿的A片人生啊!
A片由來已久,大概從人類發明電影攝影機之後的第二年就誕生了第一部A片。百分之九十九的A片只需要床和兩個人就可以拍攝(這裡說的是最有效的A片,而不是指那種愈拍愈富麗堂皇,卻與A片的本質愈行愈遠的片子),它雖然簡單,卻完全滿足了人類內心潛在的偷窺慾望。在失業青年毛太郎看來,這種偷窺慾望的存在是一個複雜的社會事件。毛太郎的論述如下:
因為每一個個能擁有不同的基因而製造了不同的內在本質,所以基本上人是孤獨的。但人因為能力的脆弱(想想看幾個看不見的細菌便可以把人搞得土吐下瀉,整個人癱成一堆爛泥。而隨便一顆時速超過五十公里的石頭打中了太陽穴,一個一百公斤的壯漢便曾一命嗚呼),所以必須尋求同類之間的互動以產生更大的生存力量,這時候,「社會化」就變成一種必要的想。
為什麼說是「惡」?因為「社會化」的結果使每個人喪失了大量的自我,每個人對自己愈來愈沒信心,現代人往往搞不清楚自己真正的位置,這肯定是一種讓人恐懼的經驗,當你對你的敵人毫無所悉,一片茫然時,你該怎麼辦才好呢?你不害怕嗎?
因此,偷窺是必要的。毛太郎認為,為了重建每個人的主體性,偷窺是一種必要的手段,人類可以藉由偷窺來了解他人與了解自己。
而A片正是所有偷窺形式中最徹底的一種。這是因為在人類幾千年的歷史文明中,做愛在不知不覺中已發展成最私密的一種行為(所有動物中只有人類的做愛具備這種特質,狗不一樣,牛也不一樣,所有人之外的動物做愛時都不會躲到房間裡),當我們可以偷窺到這種最隱密的行為時,我們還有什麼不能了解的呢?不是嗎?
這種了解更深一層的意義便是自我解放,為什麼?因為當我們在最根源最赤裸的地方看見了人類未經遮掩的本性之後,我們將會對自己一身的罪惡較為釋懷(你看,不是只有我像狗那樣子做愛,所有人都是一樣的)這種微妙的心理機轉對毛太郎來說是看A片一個重要功能;其嚴肅性一點都不下於看希臘悲劇時所謂的淨化作用。
以上便是毛太即看A片的一點小小心得。
這回地震來時,毛太郎跟往常的禮拜六下午一樣,光著身子躲在家裡看A片,因此一點都沒感覺到地震的來襲,他甚至在看過A片後因為覺得身心舒暢極了,還打了一個電話給好友阿呸(阿呸之所以有這樣一個不怎麼文雅的綽號,就是因為這人平常沒事常常以呸呸呸表達對社會上許多人與事的不滿,他跟毛太郎一樣也是A片族成員,這掛人喜歡躲在房間裡憤世嫉俗似乎是一種共同的特點),那電話響了幾十聲之後才被接起來,接著毛太郎便聽到阿呸略微顫抖的聲音:
「嗯!……」喂的尾音拖得很長,像貓叫。
「呸啊?……你是阿呸嗎?」毛太郎有點猶豫。
「誰啊?」
「我毛啦!你怎麼了?」
「天哪!好大的地震。」
「地震?什麼時候地震?」
「你睡死啦?剛才一個那麼大的地震你不曉得?」
聽阿呸這一講,毛太郎倒有點不好意思了。那麼大的地震卻毫無感覺,自然是因為地震來的時候,他老兄那麼剛好正在死命地打手槍囉!唉!難怪剛剛那剎那間覺得特別爽快。
「睡得太沉了。難怪,剛剛做了個夢,夢見上了鐵達尼號,船撞冰山,搖得特厲害的。原來如此。」毛太郎胡亂謅個故事。
「找我幹嘛?」
「沒事,就心情好找你說話。」
「幹嘛心情好?呸!」
阿呸把「呸」字拉了一個長長的尾音。他給地震這麼一搖,憤世嫉俗的心情又冒出來了。
「物極必反,苦悶久了自然就會快樂。你知道嗎?我失業已經超過一年兩個月了,不自己找點樂子,遲早會給頭殼頂上的空氣給悶死。」
「死不見得不好。像你這種人渣,早該自行了結了。活著對社會是不會有什麼貢獻的。」
「我們彼此共勉。」
「快啦!我看這地震那麼大,餘震也不會小到哪裡去,多晃幾下,世界末日也就來了。」
「你擔心嗎?」毛太郎問。
「剛剛搖起來的時候是有點怕,現在想想也沒什麼好怕的。是不是?……你怕嗎?你怕失去什麼嗎?」毛太郎突然在電話這端大笑了起來,那聲音聽起來有點空洞,像個無政府主義的世界,任意中帶點悲哀。
「阿呸,你不要問那麼好笑的問題好嗎?……我現在是靠看A片打手槍度日,你說我會失去什麼?」
「這難說哩!我怎麼知道你肚子裡想些什麼。」
毛太郎忽然聲音一沉:「沒有。都沒有。什麼都沒有想。」
「……」
「……」
兩人沉默半天,毛太郎再開口:「我倒希望真的就來個大地震,或者像彗星撞地球之類的。」
「那就怎樣?」
「毀滅啊!一切都毀滅掉啊!這樣感覺比較有希望。徹底破壞之後就是一個新生命的開始。」
「什麼時候變得那麼虛無縹緲的?」
「虛無是我唯一的契機。」
「哇!毛兄,你A片看太多,變得太有深度了。我沒辦法再跟你談下去了,我要出門看看。」
「看什麼?」
「看看街上劫後餘生的慘狀。唉!肯定會死不少人的,我去探探消息。」
「你還是比我在乎。」
「在乎什麼?」阿呸問。他已經聽不太懂毛太郎的話了。
「在乎你自己。」說完,毛太郎掛上電話,便又再去找另外一部A片看了。
內文3
患了憂鬱症的市長
市長大字形躺著。望向天花板的無助眼神讓他的黑眼珠像害羞的龍眼核,動也不動地瑟縮在眼眶一角。鬥雞眼。一對魂不守舍的鬥雞眼在大地震甫過的空氣中顫抖。這場地震對原本就有輕度憂鬱症傾向的市長而言無異是雪上加霜。市長四十五歲,正是一個很容易就四顧茫然的尷尬年紀。是的。他這種年紀已經沒有辦法跟市公所裡年輕的員公一起打棒球了。棒球太快啦!那種飛快的速度(不論是奔馳的球或衝鋒陷陣的球員)對我們四十五歲的市長來說是個美麗而遙遠的神話。
他現在只能在市長杯棒球賽中開球,用盡吃奶力氣把一個有椪柑那麼大的白球丟出像布魯塞爾小尿童的尿尿那樣的拋物線,然後在四周觀眾的笑聲和一堆充滿馬屁意味的掌聲中提醒自己:年輕時我可也是打過棒球的哩!而他這種年紀又不屑到長壽俱樂部陪阿公阿媽打槌球(一種充滿高爾夫幻想的簡易老人運動),他不宜喜歡老年人那種滿佈著各種雜質的氣味,如果可能,他願意花十億元防止衰老。這個不行,那個不要,這一來他所能做的運動就剩下散步和每半個月兩次的夫妻恩愛體操了。如此稍嫌不足的運動量再加上他因為天生神經過敏所引起的膀胱焦慮症(也就是說我們市長擁有一顆敏感焦慮的膀胱,那個膀胱的平滑肌在夜晚睡覺時無法如正常人那樣地鬆弛,持續收縮的結果使得市長每個晚上至少必須起床尿尿三次,這嚴重影響了他的睡眠品質),終於導致市長最近一年來始終揮之不去的憂鬱症陰影。「膀胱無力──半夜頻尿──睡眠不足──頭痛──全身乏力──焦慮──恐懼──憂鬱」,這樣子的惡性循環像個小魔鬼般盤據在市長的體內深處。
馬納知道這個祕密。他在一次單獨與市長吃海鮮喝丹麥嘉士柏啤酒時,探聽到市長這如詩歌般夾纏的祕密。當他翻牆進入市長公館,遠遠看見市長大剌剌地陷在沙發裡,而一旁或坐或站杵了幾位先馬納而到的記者時,他知道市長這下憂鬱症病情顯然已經急劇升高,這些不知情的記者能問出什麼名堂!他們以為市長在幹嘛?在沉思嗎?一個大字形躺著的市長在碰到這樣的一場大地震時會想些什麼事?這些好奇的記者紛紛提出在馬納聽起來實在是愚蠢無比的問題。
「市長,你還好嗎?」
「市長,你看這震度有幾級?」
「會有更大的餘震嗎?市長。」
「市公所還好嗎?」
「你現在打算怎麼辦?市長。」
「你碰過那麼糟糕的地震嗎?」
「市長,你要趕快展開救援行動。」
「市長,你到底怎麼啦?」
一堆廢話像蚊子般在膛目結舌的市長四周嗡嗡縈繞,就是沒辦法讓市長的嘴巴蹦出個馬字。馬納實在看不下去了,走過去便對這些同業大吼一聲:「安靜點好不好?各位。」隨後機伶地順著市長呆滯眼神的方向在三公尺外的小矮櫃上發現了一包藥袋,立刻心領神會地過去拿出藥袋裡的藥。PROZAC,沒錯,就這玩意兒,一種號稱副作用趨近於零的抗憂鬱劑,據說歐美至少有三千萬人每天都必須依靠它來維持繼續工作的意願。人生太苦了,苦得讓人無法遺忘。這種中文譯名叫做「百憂解」的仙丹可以讓你暫時忘記所有的痛苦,甚至可以使你從肚子裡燃起一股革命的衝動。曾經有一位黝黑而且骨瘦如柴的精神科醫師開了兩個禮拜量的藥給馬納,那陣子他剛跟交往三年半的女友分手,滿腦子都是女友身體的器官(大腿、唇、屁股、手掌、腳踝……),他憂鬱得幾乎想去殺人。馬納走到市長身邊,把藥在他眼前晃了兩下,然後像個慈母那樣將藥片塞進他微啟的嘴巴裡。「吞下吧。」馬納堅定地望著市長:「吞下吧。市長。等一下你就會有勇氣去挑戰一頭野牛。」市長噙著淚將藥片吞下,接著再咕嚕咕嚕喝了一大口礦泉水,時間靜悄悄地流逝,市長的臉龐開始出現了微細的變化。先是牙齒。他兩排牙齒首先發出了纖細的顫抖聲,格茲格茲,格茲格茲,彷彿他嘴裡有一堆話全堵死在牙床上,不得其門而出的樣子。馬納根據自己的經驗知道,這是憂鬱症患者即將跟黑暗說拜拜而奔向陽光的前兆。待會兒,甦醒之後的市長會打開柵門把那一嘴巴的話全放出來,像排尿那樣子地全放出來。
緊接在牙齒之後甦醒的是市長短小精悍的四肢。馬納與他的同業們這時都聽見了一串卡啦卡啦的骨頭關節活動聲,那聲音有一些復古的意味,你可以在六○年代港產的拳腳片裡聽到同樣的聲音,這聲音出現之後,觀眾就會看見渾身肌肉的男主角用舒展過的四肢將敵人海扁一頓,扁到像張紙那樣平擺在地上。市長成長於那個年代,潛意識裡恐怕早已移入那種似是而非的陽性暴力哲學,他這串卡啦卡啦的聲音,恐怕是對自己男子漢身份的高度期許。「我是男子漢啦!」。即將甦醒的市長或許正在那醒與不醒的邊緣這樣吶喊著。
果然,市長醒來後迸出的第一句話便是:「我是男子漢啦!」接著他用疑惑的眼神瞪著圍繞在身邊的每一位記者,包括拿藥給他吃的馬納。然後就開始下指令和罵人:「為什麼?」他的頭髮和鼻孔隨著這句強烈的質問而憤張開來,他幾乎用吼的:「為什麼你們一個個都還站在這裡?」
「不是地震嗎?……怎麼不去救人哩?」市長說。
「報告市長,我們正在等您指示。這城市打結了,我們他媽的實在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一個穿夾克的年輕人兩眼炯炯有神,鼻孔發出嘶嘶聲響,很有鬥志,就是他媽的實在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怪手。把全市的怪手全部找來。到市公所前給我排好。」市長的口氣像個因為落敗而顯得毛躁的棒球教練,焦急的口水毫無顧忌地噴向四周每一個人的臉蛋,他像串鞭炮那樣燃燒自己,也就是說他滔滔不絕地下達一個接一個的指令。
「去挖人。」他意思是讓怪手到瓦礫堆裡救人。
「救人第一。」市長指示。「半個鐘頭之內列出沒有倒塌的診所名單。」他沉吟了一秒鐘:
「當然,還包括醫生。把所有神智清楚,兩手已經不再顫抖的醫生也列出來。」
「然後去找五百個護士。」他眼睛看著穿夾克的年輕人,說:「蘇仔,這事情就交給你了。」市長隨後輕咳一聲:「不要告訴我你這輩子還沒看過那麼多女人。」他繼續叮嚀:「找簡單一點的。不必正牌的啦!會綁紗布,塗紅藥水就可以了。會打點滴的更好。這樣懂吧?去!去!找輛車到街上廣播。」
停了半晌,他突然頓悟般地「啊!」了一聲:
「啊!其他人呢?蘇仔。」市長意思是除了蘇仔之外的其他市公所的人呢?
「報告市長,實在不巧,今天剛好星期六,他們全部在家睡午覺。不過現在可能有幾個沒壓死的正往您這裡趕來。」
「去把董課長找來。挖人的事就交給他。要他看清楚,可以挖才挖,不能挖就不要挖。不要把活人給挖死了。」
在一旁聽到市長這句話的馬納終於忍不住了,他臉上的兩行眼淚像自來水那樣奪眶而出,迅速地在大家前面哭成一個哀傷的史努比。他混亂的腦袋瓜裡這時閃現出許多令人難過的念頭:多麼渺小的人類!多麼無助又無能的市公所!多麼可恨的大地!多麼可憐的同胞!……「現在不是哭的時候。」逐漸恢復冷靜的市長這時在哭泣的馬納身旁冷冷地丟下一句話。馬納沒搭腔,他用手掌抹掉臉上的淚水,收拾起斷斷續續的哭聲,像個影子般靜悄悄地走到另一個陰暗的角落。他有點想家人了,想小外甥女冬冬和咪咪姐姐,想爸爸,想媽媽,想女友麗雲,現在換他陷入和市長先前一樣的憂鬱狀態中了。
憂鬱的馬納坐在靠窗的藤椅上看著屋外,市長連珠炮般的指令有的順著風鑽進他耳裡,有的則像溜煙般擦過他憂傷的後腦勺:「衛生所……消毒……,一個都不能少……怎麼可以?……清潔隊!清潔隊啦!……我市長還是你市長?……消防栓……爆炸怎麼辦?……去海邊看看……海嘯,海嘯懂不懂?……」海嘯?一個奇異的名辭忽然闖入馬納疲倦的耳朵裡。他不覺得會在這時候聽到這個既遙遠又陌生的詞兒,可既然聽見了,不知怎麼地,他剎那間竟隱約覺得有一大片的陰影漫天蓋來……是的!漫天陰影……一大片,一大片地撲來……
馬納沒再想這事。他決定先離開這裡。天黑之前,他想,至少在天色完全暗去之前,他必須找到他那戀愛中的咪咪姐姐和小胖胖鋼琴家冬冬,以及女友麗雲、爸爸、媽媽……等人。否則,一個停電城市的夜晚將比吸血鬼更可怕一萬倍,誰會願意在那種黑暗的壓力下承受骨肉失散之苦超過一秒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