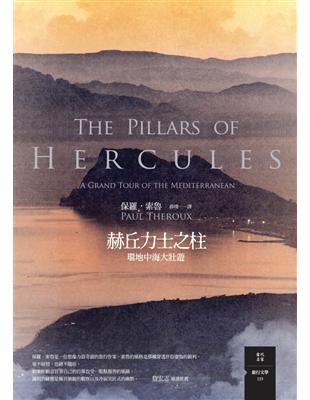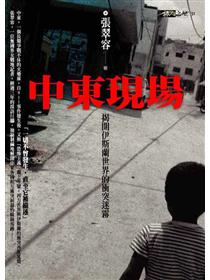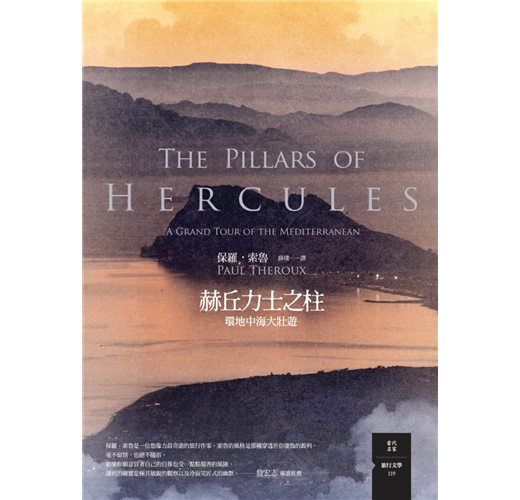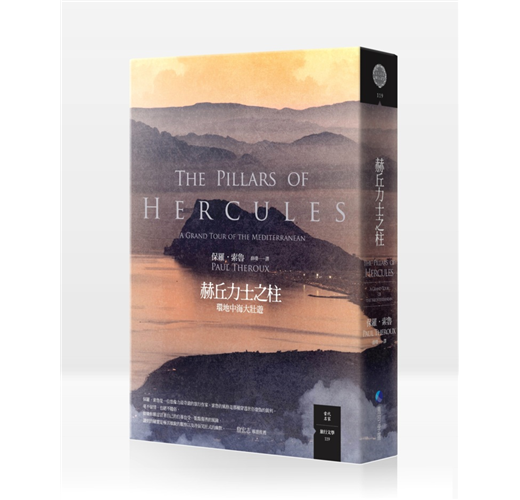名人推薦:
地中海的小宇宙──
我讀保羅‧索魯的《赫丘力士之柱》
/詹宏志
寫出原創性旅行文學的第一個門檻,應該是一條具有獨特想像力的「旅行路線」。
因為真正的「空白之地」(Empty Quarer)或「未測之地」(Uncharted Land)早已隨古典探險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從前,探險家們來到又一個全新之地,大言不慚地宣稱:「我們正進入一個從未被血肉之軀注視過的新地域。」(We were now getting into areas never viewed by mortal eyes.)這種偉大的句型現在只能搬上火星去用,吾生也晚的小輩旅行者,再也沒有資格使用這樣不合時宜的修辭。那麼,現在的旅行者從那裡可以去尋求一種真正的「新經驗」,供我們內思反省,進而產生文學呢?
地域不新,途徑卻是新的;道路不新,理由卻是新的。這是新一代旅行者仍可以源源不絕找到新經驗,更不斷創作出耐人尋味的旅行作品的原因。美國作家保羅‧索魯(Paul Theroux, 1941-)就是其中一位想像力最奇詭的旅行作家,他的其他幾本旅行文學作品,都包含了某一個匪夷所思的旅行路線,譬如在《老巴搭哥尼亞快車》(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 1979)裡,作家索魯從波士頓的自家門口出發,搭乘平日上族通勤的火車,一路接駁換乘,景色更替變化,一站換過另一站,他竟這樣一路穿越整個北美洲,再穿過中美洲,垂直而下數千公里,一直走到阿根廷境內的巴塔哥尼亞高原,直到鐵路戛然而止,那幾乎是道路的盡頭,無人的所在,作家才說:路途已盡,我可以回家了。想想看,這是何等獨特、何等不凡的「旅行路線」。
十五年後出版的《赫丘力士之柱》(The Pillars of Hercules, 1995)一書裡,保羅‧索魯再接再厲,想像那不可想像的路線,這一次,他看上歐洲文明起源的地中海海岸,如同約翰生博士曾經說的:「我們所有的宗教、幾乎所有的律法、幾乎所有的藝術,以及幾乎一切使我們脫離野蠻的東西,都來自地中海海岸。」(All our religion, almost all our law, almost all our arts, almost all that sets us above savages, has come to us from the shores of the Mediterranean)衝著這句名言,索魯因而決定沿著海岸把地中海繞一圈。
地中海不算大,只有將近二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約等於七十個台灣的大小,比新疆則略大三分之一;但它沿岸的民族與文化卻既多元又多彩,上方是歐洲,下方是非洲,東邊則是亞洲,而西邊露出一個極狹的開口:也就是歐非兩洲遙遙相望的直布羅陀海峽。穿過它,你就進入了更浩瀚的大西洋,往北可至英倫三島或北歐,往南可繞過好望角,找到往印度與香料群島的另一條航道;而繼續再往西航行呢,再往西你就和哥倫布一樣準備要發現新大陸了。只是古代歐洲人並無意穿過直布羅陀海峽,他們相信出了海峽,不過是一片空漠汪洋,沒有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一直要等到「大發現時代」,歐洲人才走出海峽,看見全新的世界。
直布羅陀海峽最窄的兩端,一邊是位於西班牙半島卻歸英國管轄的直布羅陀(Gibraltar),另一邊則是位於摩洛哥的休達(Ceuta),兩個地方正是希臘神話中赫丘力士第十件苦勞(捕捉格里奧尼斯的紅牛)時所立的兩根石柱,這也是本書書名《赫丘力士之柱》的由來。作者並不想直接從海峽此岸到達彼岸,他繞了個大遠路,從直布羅陀出發,沿地中海岸向東,經過西班牙的東海岸,然後是法國的蔚藍海岸,你緊接著就遇見義大利,往南你還得看看西西里,然後過義大利的鞋跟來到南歐,包括四分五裂的前南斯拉夫和文明搖籃的希臘各島,再向東,你先遇見的會是既歐洲且亞洲的土耳其,然後你就來到所謂的「東方」(The Levant),包括敘利亞、黎巴嫩、和以色列,再轉了個彎,別管蘇伊士運河的誘惑,你就來到埃及,這時方向已經轉回向西,你現在正沿著北非的海岸,將經過利比亞、突尼西亞、和阿爾及利亞,最後來到摩洛哥,回到直布羅陀海峽對面的另一根「赫丘力士之柱」,這樣,你已經環繞了地中海一周,周長約三千六百公里,不同的國家民族,不同的歷史地理,不同的語言飲食。這就是作家保羅‧索魯從此柱到彼柱的「環地中海之旅」的路線計畫。
旅行文學的第二個門檻是「文學」,但這幾乎沒有方法,也沒有規則,只有文學家自己的體驗和創造。保羅‧索魯出了名的是一個尖刻犬儒的旅行作者,他對路上所見所聞的鋒利言詞有時也讓某些忠厚的讀者無法忍受,他自己也知道他的遊記並不是受到所有人的歡迎,所以他開宗明義就調侃自己說:剛剛讀到這裡就喃喃自語:「他又來了。」的讀者們,您可以放棄了。
但文學有百種面貌,索魯的風格是那種穿透世俗虛偽的銳利,毫不留情,也絕不隨俗。他讓你看見的不是表皮,而是進入皮下組織的顯微鏡;而如果你願意冒著自己的自尊也受一點點傷害的風險,讀到的確實是極其敏銳的觀察以及冷面笑匠式的幽默。索魯的旅行一向別出心裁,但卻深入人群,他流連在觀光客不到的偏城小鎮,繞行到難得邂逅的僻路,與當地人談天辯論,記錄荒謬卻真實的人生面向。他不是美麗景點的描述者,更不是奇風異俗的採擷者,他書中記錄的多半是人物,以及與人的對話;但奇怪的,似乎這種平凡的事物在他的筆下,卻產生比虛構想像更驚人的戲劇性。
我曾說索魯是「反省『旅行』本身的旅行者」,因而他的旅行有時顯得有點「反旅行」;而他的旅行文學也常常反旅行文學,刻意與習見的旅行文學背反。索魯似乎是一位深怕落入「俗套」陷阱的作者,尤其害怕俗套的「結局」。所有的旅行文學都隱藏一場「治療」或「救贖」,旅行者出發是一個人,回來是另一個人(通常是變得更有智慧或更悲天憫人);但索魯絕不掉入這個陷阱,他讓地中海之旅變成一個循環無解的儀式,他在結語時說,中國、秘魯之旅治癒我的中國病、秘魯病,但地中海之旅並沒有治好我的地中海病,他似乎沒有因此完成一個通過儀式,旅程完成,經驗卻未完。他說:「我知道我將像重回博物館一樣重回地中海,去看或去想。」地中海之旅,彷彿是靈魂故鄉的追尋,是祖先崇拜的加強。《赫丘力士之柱》一書止於他去拜訪住在摩洛哥的美國前輩作家保羅‧鮑爾斯(Paul Bowles, 1910-),鮑爾斯也像索魯一樣是位追尋者,他的小說《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 1949)正是一個世代以前流浪追尋的代表之作,保羅‧索魯,看似與其他事物斷裂隔絕,這場拜訪行動卻是傳統的接續。是呀,不要錯看言詞尖銳的人,他們只是需要保護他們脆弱柔軟的內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