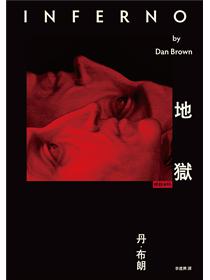唯一能擊敗《格雷的五十道陰影》的作者吉莉安‧弗琳,
你接觸驚悚小說的最戰慄入門。
史蒂芬.金評《暗處》:
吉莉安.弗琳真不是蓋的!文筆辛辣,極盡鋪陳之能事,就是要你毛骨悚然。
史蒂芬.金評《利器》:
光用『恐怖』兩字,根本不足以形容這部小說處女作……
在我關上燈後,故事內容不斷縈繞腦海,不斷發出細微的嘶嘶聲,
擾動著我,彷彿一條洞穴裡的蛇。
美國懸疑小說大師 哈蘭.科本評《暗處》:
繼《利器》之後,又一登峰造極之作。
英國最受歡迎的女性犯罪作家 薇兒.麥克德米評《暗處》:
吉莉安.弗琳出手不凡,處女作《利器》一夕暴紅,《暗處》證明其成功絕非僥倖。
關於《暗處》——
7歲那年,麗比‧天的媽媽和姊姊死於「堪薩斯瘋狂殺人事件」。就在兇手大開殺戒之時,小麗比從小小的農宅逃了出去,還上法庭作證,說15歲的哥哥班恩就是兇手,並因此聲名大噪。25年後,靠著慈善捐獻過活的麗比發現,世人已漸漸遺忘她的存在,捐款日漸稀少,眼看就要用完了……
就在這時,殺手俱樂部登場。這個病態的地下組織,對於惡名昭彰的犯罪事件特別感興趣。他們找上麗比,想從她嘴裡證實班恩的無辜,麗比則想趁機大撈一筆。她要求俱樂部出錢,讓她調查當年捲入這樁滅門血案的人物,並允諾定期向俱樂部回報……或許,她會坦承當年的證詞充滿漏洞。
隨著調查行動展開,麗比發現自己回到故事的起點——她最崇拜的哥哥身上。
關於《利器》——
13歲那年,卡蜜兒最疼愛的妹妹久病過世,就在同一年的夏天,她找到了解放生命痛苦的出口——她上癮似的,無法自拔地用尖利的器具在自己身上刻字,唯一完好無缺的部位是上背部一小塊皮膚跟她貌美的臉龐。
18年後,在三流報社擔任記者的卡蜜兒,極不情願地奉命回到故鄉追蹤兩起女童凶殺案件。遭到謀害的女童被發現時牙齒都被拔光,一個被刮掉腿毛,另一個塗上口紅。兇手殘忍的手段,讓整個小鎮陷入極端的恐慌,居民們個個人心惶惶。
就在卡蜜兒一步步深入探究凶殺案件的真相時,卻也不小心挖掘出埋藏在自己家中的駭人祕密……
《暗處》
★ 入選2009《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年度推薦書單
★ 《今天週末》(Weekend TODAY)推薦「最佳夏日讀物」
★ 2009《紐約客》(The New Yorker)書評首選
★ 2009《芝加哥論壇報》(The Chicago Tribune)嚴選小說
《利器》
★ 史上第一本同時獲得兩座英國匕首獎的作品
★ 入圍「艾倫坡小說獎」最後決選名單
★ 獲得獲得年度英國犯罪寫作協會的「年度新人獎」以及「佛萊明鋼匕首獎」
★ 美國文壇暢銷作家史蒂芬‧金兩度為其著作背書,讚賞有加
★ 作家哈藍‧科本、薇兒‧麥克德米、歐各司坦‧柏洛斯、凱特‧艾金森大力推薦
★ 電影版權已經售出,由作者本人擔任劇本改編
作者簡介:
吉莉安‧弗琳(Gillian Flynn)
出生於密蘇里州堪薩斯市,父母皆是社區大學教授。在雙親的影響下,她從小就在書籍和電影的浸潤中成長。堪薩斯大學畢業後她進入加州的雜誌媒體,之後移居至芝加哥,在西北大學取得新聞學碩士學位,進入《娛樂週刊》(Entertainment Weekly)工作,曾經在世界各地的拍片現場採訪。
她於2006年推出首部小說作品《利器》,立即得到史蒂芬‧金、哈藍‧科本、薇兒‧麥克德米等文壇巨匠的高度推薦,同時入圍艾倫坡小說獎決選。接著,《利器》創下了史上首度同時獲得兩座英國匕首獎的罕見記錄:年度新人獎及佛萊明鋼匕首獎。全球各主要國家紛紛出版該書,目前已在20餘國發行,而電影版權售出後作者本人更獲邀擔任此片的劇本改編工作。
吉莉安‧弗琳目前已出版《利器》和《暗處》兩部小說,兩書均受到推理文壇與媒體的好評,史蒂芬‧金、哈藍‧科本、薇兒‧麥克德米都稱讚她高明的書寫功力。目前她正在創作第三部小說。
譯者簡介:
張思婷
台大外文系、師大翻譯所畢業。熱愛翻譯。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光用『恐怖』兩字,根本不足以形容這部小說處女作……在剩下差不多三十頁左右我就不敢再繼續往下看了,但是手指頭卻又不聽使喚地繼續翻著書頁。在我關上燈後,故事內容不斷縈繞腦海,不斷發出細微的嘶嘶聲,擾動著我,彷彿一條洞穴裡的蛇。一部令人驚嘆同時感到不舒服的小說,藉由作者深刻的筆鋒、以及更為深刻的洞見獲得了提升。」──史蒂芬‧金(美國著名暢銷作家)
*《利器》是我好一陣子以來看到最令人耳目一新的驚悚小說處女作。這本書扣人心弦、不落俗套而且文筆優美。書中飽受心理問題困擾的人物極為寫實,為這個故事大大增色。至於我原本以為我預想得到的結局,實則出人意料之外。《利器》這本書真的相當有殺傷力。──歐各司坦‧柏洛斯(紐約著名廣告創意人,《一刀未剪的童年》作者)
*「吉莉安.弗琳就是那麼會寫!讀過她的作品之後,大概就不用再去讀其他犯罪小說了。」──凱特.艾金森(英國惠布瑞特好書獎得主)
*「《暗處》從你翻開書的那一刻就緊緊抓著你,不到最後一頁絕不放手。」──凱琳.史勞特(暢銷犯罪小說家,著有《盲視》、《蘿莉的秘密》)
*吉莉安.弗琳儼然是二十一世紀的約翰.厄文,而且其怪誕恐怖更勝前人。她一手拿著手術的解剖刀,一手拿著生鏽的輪刀,準備好要劃開美國中西部美麗的地表。——加州《聖荷西搶鮮報》(San Jose Mercury News)
名人推薦:「光用『恐怖』兩字,根本不足以形容這部小說處女作……在剩下差不多三十頁左右我就不敢再繼續往下看了,但是手指頭卻又不聽使喚地繼續翻著書頁。在我關上燈後,故事內容不斷縈繞腦海,不斷發出細微的嘶嘶聲,擾動著我,彷彿一條洞穴裡的蛇。一部令人驚嘆同時感到不舒服的小說,藉由作者深刻的筆鋒、以及更為深刻的洞見獲得了提升。」──史蒂芬‧金(美國著名暢銷作家)
*《利器》是我好一陣子以來看到最令人耳目一新的驚悚小說處女作。這本書扣人心弦、不落俗套而且文筆優美。書中飽受心理問題困擾的人物極為寫實,為這個故事大...
章節試閱
暗處
卑鄙像器官,實實在在地長在我的身體裡;把我的肚子剖開,它會掉出來滑到地板上,多肉且黝黑,讓你盡情地踩。它在天家的血液裡。天家的血統大有問題。我從小就不乖,在那件凶殺案後更是愈來愈愛使壞。小小年紀就成了孤兒的我,被爸媽的親友丟來丟去,一下住表姊家,一下住姑婆家,一下住爸爸的朋友的朋友家;我在堪薩斯州四處為家,在各種活動式房屋、鄉間平房裡長大,長成陰沉又沒骨氣的個性。我穿著死去的姊姊的舊衣服上學校,襯衫的腋下都泛黃成芥黃色,長褲後面過寬以至於臀部鬆垮,用一條有裂痕的皮帶扣住最後一孔扣。照片裡的我,頭髮總是亂成一團,髮夾歪歪地卡在糾結的髮絲中間,好像頭上沾到髒東西;而且眼睛下總有眼袋,像酒鬼一樣泡泡腫腫;原本應該上揚的嘴角,也似乎總是不滿的下垂著。一副很哀怨的樣子。
我從小就不得寵,長大後更是沒人愛。如果要畫我的靈魂,大概會是一張滿是獠牙的塗鴉。
□
淒慘的三月,天氣陰溼到骨子裡,我躺在床鋪上,一心想著要自殺。我的嗜好是在午後的白日夢裡縱情徜徉:獵槍,我的嘴巴,砰,頭顛一下,兩下,血飛濺到牆壁上,涮,涮。大家七嘴八舌:「她要土葬還是火葬?應該請誰來參加葬禮?」沒人知道答案。前來觀禮的人(天知道有誰會來),一個個盯著彼此的鞋尖,或者死命地看著對方的肩膀。禮畢,一切歸於沉默,有人煮水,泡咖啡,動作輕快,器皿乒乒乓乓地碰撞。咖啡跟猝死真是絕配。
我從棉被底下伸出一隻腳,卻沒辦法把腳踩到地板上。我猜我有憂鬱症。我想,這二十四年來,我每天都為憂鬱症所苦。我覺得在我這發育不良的幼小身體裡還藏著另外一個善良的麗比,她可能躲在肝臟後面,或是脾臟底下,她要我站起來,做點事,她要走出陰影,快快長大。但最後還是卑鄙占上風。七歲那年,大哥屠殺了我們全家。砰砰。剁剁。掐掐。媽媽死了,兩個姊姊走了。從此以後,我也不用努力,反正沒人指望我會有任何成就。
十八歲那年,我繼承了美金三十二萬一千三百七十四元,這是各地善心人士多年來的捐款,這些大善人讀了我的報導,得知我悲慘的境遇,對我感到由衷地同情。每次我聽到這句話(我還滿常聽到的),我就會想像一顆顆大大的愛心,中間畫著花俏圖案,兩邊是小鳥的翅膀,拍拍拍飛往我童年住過的各個破屋;小小的我倚在窗邊,揮著手,抓住一顆顆鮮豔的愛心,花花綠綠的鈔票從天上灑下來,謝謝,謝謝,感激不盡!我小的時候,大人幫我把捐款存在戶頭裡,只要每過三四年哪個雜誌或電視台報導我的近況,戶頭裡的數字就會暴增。譬如這樣報導:「小麗比嶄新的一天:堪薩斯大屠殺的生還者出落成青澀甜美的十歲少女。」(照片上的我梳著兩條分岔的辮子,站在黛安阿姨的拖車屋前面,四周是散發著負鼠尿騷味的草坪。黛安阿姨難得穿裙子,站在我後面,一雙象腿紮根在黃色草堆裡,跟我一起入鏡)。或者這樣寫:「勇敢的麗比‧天,甜美的十六歲!」(生日蠟燭照亮我的臉龐,我的個頭仍然嬌小,但上衣胸前鼓脹,豐滿的D罩杯讓我就像漫畫裡的美少女:滑稽而色情。)
這十三年來,我都靠著這筆財產過活,但也花得差不多了。我下午要見一個人,以確定我還有多少錢可以花用。多年來有個總瞪大眼睛、氣色紅潤、名叫吉姆‧傑佛瑞的銀行員,專門負責管理我的帳戶,而且每年都堅持要請我吃一頓午餐,說是「例行察看」;我們通常都吃二十美元左右的餐點,邊吃邊聊近況。他可是從這麼高的時候,就一直認識我到現在,至於我,我對吉姆‧傑佛瑞一無所知,我從來不問他任何問題,一直還是用小時候的眼光看待我和他之間的約會。我叫自己要有禮貌(但通常事與願違),快點吃完快點了事。我都只用一個字回答他的問題,或是不耐煩地嘆氣(我只對吉姆‧傑佛瑞的一件事感興趣,那就是我猜他是基督徒,而且很虔誠,他很有耐心,又很樂觀,因為他相信「上帝正在看著」。)雖然「例行察看」是八、九個月後的事,但吉姆‧傑佛瑞一直來電嘮叨,還留了好多語音訊息,用正經八百的口氣壓低嗓子說他已經盡量妥善利用「帳戶裡的存款」,但是時候進入「下一階段」了。
說到這裡,我卑鄙的一面又露出來了:我想起另一個也常常上報的小女孩,叫什麼婕咪的,也是在一九八五年成了孤兒。她爸那時放了一把火,燒死她們全家,害得她局部毀容。每次我按提款機的時候都會想起這個叫婕咪的女孩,想當年要不是她搶了我的風頭,我的存款一定比現在多一倍。臭婕咪現在一定拿著我的錢在百貨公司裡血拼珠寶和名牌包,順便買化妝品遮蓋臉上的燒傷。有這種想法實在很可怕,至少我還明白這一點。
終於,終於,終於,我呻吟了一聲,讓自己從床鋪上爬起,慢吞吞地踱到房子前面。我住的是平房磚塊屋,左鄰右舍也都是;這一整排平房磚塊屋整齊劃一地蹲踞在一塊峭壁上,俯瞰底下的堪薩斯市,以前這整片都是廣袤的放牧場。我說的堪薩斯市,是指密蘇里州的堪薩斯市,不是堪薩斯州的堪薩斯市。這兩者不一樣。
我住在一個被人遺忘的角落,連個地名也沒有,路人都說「就是那邊再過去」。這裡是個詭異的次級城區,充滿死巷子和狗大便。一堆上了年紀的老人家挨挨擠擠地住在其他平房磚頭屋裡,他們在磚頭屋完工的那一年入住至今。老年人坐在紗窗後面,灰撲撲的,如布丁一般待著,一雙眼睛整天往外面看。有時,他們會蹣跚地踩著小碎步,小心翼翼走到車子旁邊,這讓我過意不去,總覺得好像該扶他們一把才對,但他們偏偏又不要人家扶。這些老人家一點也不和藹可親,個個癟著嘴,滿臉不高興,不歡迎我當他們的鄰居,嫌棄我這個新來的。整個社區流傳著對我不以為然的耳語,有那幫老人家的輕蔑,加上隔兩戶的那條狗會狂吠,那條狗瘦巴巴的,一身紅色毛皮,早上汪汪叫,晚上常哀嚎,這不變的叫聲吵到你快瘋掉了才停止,但好景不長,又馬上開始鬼吼鬼叫。社區裡唯一令人歡喜的聲音,是一大早我在睡夢中聽到的咿咿呀呀:一群臉蛋圓滾滾的幼童,身上裹得密不透風,搖搖擺擺走過我屋子後面。他們要穿過比老鼠窩還要髒亂的街道去上托兒所,大家排成一路縱隊,手上拉著繩索,跟著最前面的大人。每天早上,他們都像企鵝似的左搖右晃經過,但我從沒看過他們折返。我想他們應該是環遊世界一圈後,隔天早上同一時間回來,剛好又從我窗戶外面經過。不要想太多,總之,我很喜歡這些小朋友。有三個小女生和一個小男生,他們四個人都很喜歡穿紅色外套。如果我早上睡過頭,沒有看到他們經過,我的心情就會很「藍」。比平常還「藍」。我媽不喜歡憂鬱這麼嚴肅的字眼,她喜歡說「心情有點藍」。我的心情已經「藍」了二十四年了。
我換上襯衫,套上裙子,準備赴約;仕女服飾對我來說總是太大,穿在身上感覺好像小矮人。我身高號稱一五○,實際上只有一四六,但,四捨五入嘛。去告我啊。我今年三十一歲,但大家總愛用娃娃音跟我講話,當我是手上沾滿顏料的小朋友。
我走下屋前荒草遍地的斜坡,鄰居的狗又多管閒事狂吠起來。我走到車子旁,地上有兩具被車輾過的雛鳥骨骸,鳥嘴和翅膀都被壓扁了,看起來倒像是爬蟲類的屍體。這兩隻幼鳥已經橫屍在這裡一年了。我每次上車前都會忍不住瞥一眼,希望哪天淹大水,把這兩具屍體沖走。
對街有兩個老太婆站在屋前台階上聊天,我感覺她們故意不往我這邊看。我不知道那兩個老太婆叫什麼,要是哪天其中一個死了,我才不會假惺惺地說:「查林斯太太過世了,好可憐喔。」我一定會說:「對面那個老潑婦終於嗝屁了。」
我覺得自己像個小幽靈,悠悠坐上我那台雜牌車;不論怎麼看,這部車都像是塑膠做的。我一直等著哪天車商跑過來,開門見山地說:「這真是個笑話。妳根本不能開這車。在開玩笑吧!」我出神地開著我的玩具車,到市中心與吉姆‧傑佛瑞碰面。十分鐘後,我駛進一家牛排館的停車場,整整遲到了二十分鐘,我知道吉姆只會慷慨一笑,對我的遲到不予置評。
本來我到了以後應該撥手機給他,讓他急衝出來護送我進餐廳去。這家老式牛排館的周遭環繞著人去樓空的建築,他擔心這些空屋裡彷彿有一票強暴犯長年蹲踞著正等待我上門。吉姆‧傑佛瑞誓死保護麗比‧天,不讓她受到任何傷害。麗比‧天好勇敢,這個紅頭髮藍眼睛的七歲小女孩逃過了堪薩斯瘋狂殺人事件(又稱牧場大屠殺、魔鬼活人祭),孤苦伶仃活了下來。我媽和兩個姊姊都慘遭班恩毒手,只有我逃過一劫,跳出來指認元凶。大家都說我是乖寶寶,將我那崇拜魔鬼的哥哥繩之以法。我那時候紅得不得了,照片曾經登上《國家詢問報》的頭版,標題寫著「天使的臉孔」。
我瞥了一眼後視鏡,鏡子裡反射出我兒時的輪廓,雀斑淡了,牙齒也矯正過了,但我的鼻子還是很塌,眼睛也還是跟貓咪一樣圓。我把頭髮染成白金色,但根部的紅髮已經長出來,在夕陽餘暉的照耀下,我的頭皮好像在流血。挺嚇人的。我點了一根菸。我好幾個月沒抽菸了,但這時突然覺得:我需要菸。我就是這樣,一點恆心也沒有。
我大聲說:「走了,寶貝天。」每當我厭惡自己,我就會這麼叫自己。
我下了車,往牛排館走去;我右手拿菸,省得費心去看我殘廢的左手。天快黑了,浮雲像水牛,成群結隊飄過天空,夕陽西斜,將萬物灑上一層粉紅。往河邊望去,在千迴百轉的交流道中間,荒廢舊穀倉外牆的升降機顯得黑壓壓、大而無當。
我獨自走過停車場,腳下的碎玻璃跟天上星斗一樣閃閃發光。我沒有遭受任何攻擊。畢竟現在才五點出頭。吉姆‧傑佛瑞晚餐吃得很早,而且為此感到驕傲。
我走進牛排館時,他不出我所料正坐在吧台喝汽水,而且一看到我就馬上把手機從外套口袋裡掏出來,盯著螢幕猛看,好像疑心手機壞了。
「妳有打給我嗎?」他眉頭深鎖。
「沒有,我忘了。」我騙他。
他笑一笑:「那,好吧。人來了就好。準備好要談正事了嗎?」
他大手一蓋,把兩塊錢留在吧檯上,然後帶我走進一間包廂,裡頭的紅色真皮座椅下,黃色海綿從破損處炸出來。我坐進去,剛好坐在裂口上,破裂的表皮擦刮我的大腿後側,椅墊飄出陳年的菸臭味。
吉姆‧傑佛瑞從不在我面前喝酒,也不會問我要不要來一杯,不過侍者來點餐的時候,我故意點了一杯紅酒,然後瞟了他一眼,看他有沒有強裝鎮定、失望透頂、或是有任何不像他會有的反應。侍者追問:哪一種紅酒?我對酒沒有概念,真的!我向來記不住那些紅酒白酒的名字,而且永遠搞不清楚那些簡稱,所以我叫了一杯店酒。他點了牛排,我點了雙餡焗烤馬鈴薯,然後侍者帶著菜單離開,他便像醫生似地嘆了一口氣說:「呃,麗比,我們要一起邁向嶄新的人生階段了。」
「所以到底還剩多少?」我一邊問,心裡一邊默念一萬一萬一萬。
「妳看了我寄給妳的財報嗎?」
「有時候會看。」我又撒了謊。我喜歡收信,不喜歡讀信。那疊財報應該是堆在我家的某個角落。
「妳有聽我的留言嗎?」
「我覺得你的手機好像怪怪的,訊號時斷時續。」我聽是聽了,但一聽到有麻煩三個字就立刻掛掉電話,通常他一講完那千篇一律的開頭我就按掉了:我是吉姆‧傑佛瑞,麗比……
吉姆‧傑佛瑞不滿地噘著嘴,左手指尖與右手指尖對碰,又彈開,再回碰,彈開。「餘額只剩九百八十二元又一毛二。我跟妳說過了,如果妳肯找份正職工作,定期存款,可能還撐得下去,可是……」他雙手一攤,扮了個鬼臉。「看來事情沒有想像中順利。」
「那本書呢?那本書不是……」
「麗比,對不起,那本書一點幫助也沒有。我每年都這樣跟妳講。這不是妳的錯,但那本書就是……沒用。唉,算了。」
前幾年,我滿二十五歲時,有家出版社想藉機大撈一筆,寫信來問我願不願意出書,談一談我如何克服「往日的陰霾」。雖然我根本沒擺脫任何陰霾,但我還是一口答應,反正有個在紐澤西的女人會幫我捉刀,我只要透過電話口頭敘述。書在二○○二年聖誕節出版,封面上的我頂著一頭據說是充滿動感的隨興短髮,但看起來跟鳥窩沒兩樣。書名叫:《嶄新的麗比‧天!她不只克服了兒時創傷,甚至超越了自己,開創新生活!》書裡有我和我家人的合照,還有兩百多頁瑣碎的垃圾話叫讀者們正向思考。出版社付給我八千美金的酬勞,之後陸續有一些生還者互助會邀我去演講。我曾經飛去俄亥俄州的托利多市,聽眾跟我一樣從小就是孤兒。我還飛去奧克拉荷馬州土耳沙市,台下來參加聚會的青少年都很特殊,他們的媽媽都是死在自己的爸爸手下。我幫一群嘴巴開開的笨小孩簽書,他們問的問題都讓人心頭一緊,譬如我媽會不會烤蘋果派。我幫一群銀髮老先生簽書,他們的目光從老花眼鏡後面射出來,嘴巴張開就可以聞到胃酸和咖啡焦掉的味道。我簽上「開創美麗的一天!」或是「美麗的明天近在眼前!」我很慶幸我的姓可以有各種變化。我的書迷都神色憔悴,一副走投無路的樣子,個個裹足不前,零零落落圍在我身邊。來聽演講的觀眾很少。後來我發現演講沒有酬勞可以領,就再也不肯出席演講了。反正書的銷路那麼差。
我嘀咕道:「出書應該很賺錢才對啊。」我真的很希望那本書可以幫我大賺一筆,我跟小孩子一樣死腦筋,以為只要我天天禱告,上天就會實現我的願望。上帝應該要實現我的願望啊!
「我知道。」吉姆‧傑佛瑞苦口婆心勸了我六年,勸到現在已經無話可說了。他靜靜看著我喝酒。「不過,麗比,換著角度想,這個時間點很妙,正好提供妳步入下一階段的契機。也就是說,妳現在長大了,有沒有想要做什麼?」
我知道他是一番好意,但一談到工作我心裡就有氣,因為他媽的我就是什麼也不想做。
「真的都沒有錢了嗎?」
吉姆‧傑佛瑞哀傷地搖搖頭,拿起鹽巴往剛送上來的牛排上灑,紅色的肉躺在血泊裡,跟櫻桃汁一樣紅豔。
「會不會有新的捐款呢?二十五週年紀念日就快到了。」我再次感到怒火中燒,氣他為什麼要逼我把心裡的盤算說出來。一九八五年一月三號凌晨兩點,班恩噬血狂歡,這是我們一家慘遭屠殺的日子,而我卻期待這一天到來。誰會像我這麼沒良心?為什麼戶頭裡面連五千塊美金都沒有?
他再次搖頭。「不會再有人捐款了,麗比。妳都幾歲了?三十?妳已經是熟女了,誰還理妳。大家還要幫助其他小女孩,誰想幫……」
「我。」
「事實恐怕就是如此。」
「沒人要理我了,這是真的嗎?」我覺得自己遭人遺棄,好像小時候被某阿姨、某表姊丟到某某阿姨、某某表姊家。我受夠了,換妳照顧她。新接手的阿姨或表姊一開始都對我很好,卯足全力想討好頑劣的我,但是過了一個禮拜就……老實說,都是我的錯。真的都是我的錯,不是我在自責。我曾在某某表姊家的客廳到處噴髮膠,然後再放一把火燒掉。黛安阿姨是我媽的姊姊,她是我的監護人,也是我在世界上最喜歡的人。她把我接過去住,再送走;又接回去,再送走,來來回回不下六、七次,最後再也不准我踏進她家大門。這都要怪我對她實在太過分。
「麗比,在這個世界上,恐怕每天都有新的謀殺案發生。」吉姆‧傑佛瑞又開始說教:「人的注意力很短暫。妳看看現在大家有多瘋那個莉賽‧史蒂芬。」
莉賽‧史蒂芬是個漂亮的二十五歲漂亮褐髮女孩,在與家人吃完感恩節大餐的回家路上失蹤了。整個堪薩斯市,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全部動員起來協尋她;只要打開電視,就會看到她的照片衝著你笑。今年二月初,她的新聞更是鬧到全國家喻戶曉,但這一個月來案情沒有突破,想也知道莉賽‧史蒂芬已經死了,但沒有人肯放棄尋找。
吉姆‧傑佛瑞繼續說:「不過,我想大家都希望妳有很好的發展。」
「喔。」
「要不要考個大學?」他咬了一大口牛排。
「不要。」
「還是安排妳到公司打雜,例如整理文件?」
「不要。」我把自己防衛起來,餐點一口也沒動,只顧著散發怨氣。這也是我媽會說的話:怨氣,用來表示心情藍到不能再藍,藍到旁人生氣,藍到傷人於無形。
「嗯,不然給妳一個禮拜的時間,妳回去好好考慮看看?」他狼吞虎嚥地吃著牛排,叉子在嘴巴和盤子之間迅速移動。吉姆‧傑佛瑞想離開了。吉姆‧傑佛瑞受夠了。
他離開前交給我三封信,還露齒笑了笑,以示要我樂觀。那三封信怎麼看都是垃圾。以前吉姆‧傑佛瑞給我的信都是用鞋盒裝著的一整箱,每封信裡幾乎都有支票。我把支票簽好交給他,然後捐款人就會收到一張謝條,上面印著我方方正正的大字:「感謝您的捐款。因為有您,我才能期待光明的未來。麗比‧天僅緘。」我真的把「謹緘」寫成「僅緘」,吉姆‧傑佛瑞認為:故意寫錯字,大家看了會更心疼。
收到整箱捐款的歲月已經過去了,我手裡只剩三封信以及一個不知如何打發的夜晚。我開車回家,看到對面來車刺眼的大燈時,才赫然想起自己沒開車燈。堪薩斯市的天際線在東邊閃爍,一棟一棟不起眼的企業大樓,一座一座高聳入天的廣播電塔。我想像自己工作賺錢,從事各種大人的工作;戴著護士帽,手拿溫度計;穿著貼身的女警制服,護送小朋友過馬路;穿著花圍裙,戴著美美的珍珠項鍊,在廚房準備晚餐等老公回來吃。我心想:看看妳有多不長進,對成人世界的看法還停留在圖畫書階段。雖然我腦子裡這樣責怪自己,心裡的畫面是我拿著粉筆,正在黑板上教導眼睛明亮的國小一年級學生寫ABC。
我逼自己想像一些實際的工作,跟電腦相關的,例如資料輸入員,這也算是一種工作吧?或是去當客服人員?我記得我看過一部電影,女主角以遛狗為生,她每天穿著毛衣和連身褲,手裡捧著花,牽著一群流口水的可愛小狗。不過我不喜歡狗,狗好可怕。最後,我終於想到了:對了,我可以種田!我們家世代都以務農為生,到我媽那一代都還是種田的,只不過班恩把媽的頭砍了。農地後來也賣掉了。
賣掉就算了,反正我也不會種田,我只記得一些農忙時節的回憶:班恩翻動冰冷的春泥,一邊鞭打擋路的牛犢。媽媽粗糙的手伸進櫻桃紅的彈丸裡,這些彈丸以後會結出高粱。穀倉裡傳出蜜雪和黛碧的尖叫聲,她們在一捆一捆的乾草堆裡跳上跳下。「癢死了!」黛碧每次都這麼抱怨,抱怨完卻又繼續跳。我不敢沉醉在這些回憶裡太久,我把這些記憶列為危險禁區,是深埋在心底的闃黑之地。我媽急中生智修復咖啡機的身影;蜜雪穿著針織睡衣,中筒襪拉到膝蓋上,在一旁樂得手舞足蹈;想著想著,一不留神,我的心靈就被吸進闃黑之地:鮮血嘩啦嘩啦地在暗夜裡瘋狂潑濺;規律、如單調節奏的斧鑿聲不免又在耳畔響起,有如劈柴般,隨之而起的是走廊上的槍響,還有我媽松鴉般的驚惶尖叫,她的腦袋被轟掉了一半,卻依然誓死護著孩子。
行政助理要做什麼工作?我暗自揣想。
我把車停在家門口,跨出車門,踩上人行道,剛好踏到一塊有刻字的水泥磚:「吉米愛蒂娜」,應該是好幾十年前刻的吧!我腦海裡有時會閃過這對情侶的下場:男的在小聯盟打棒球,女的在匹茲堡持家兼抗癌;男的是離過婚的消防隊員,女的是律師,去年在墨西哥灣溺斃;女的執教鞭,男的死於動脈瘤,得年二十歲。這種腦力激盪很不錯,只是很殘忍。我總是把他們其中一個殺掉。
我看著我租來的屋子,心想屋頂是不是一邊高一邊低?不過就算屋子垮了,我也什麼損失。我身邊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只有一隻叫美金的老貓忍受我這個主人。屋前的木頭台階潮溼凹陷,我拾級而上,聽見美金在屋內憤憤不平地喵嗚喵嗚,這才想起今天還沒有餵牠吃東西。我打開大門,老貓緩慢地跛著腳蹭過來,像一輛爆胎的老爺車。家裡的貓食吃完了,我寫在條子上提醒自己要買,但過了一星期還是沒買;我走向冰箱,拿出幾片瑞士起士打發美金,便兀自坐下來拆信。我的手好臭,都是餿奶味。
我看完第一封就沒再讀其他信了。
親愛的天小姐,
妳好像沒有架設個人網站,但願這封信能順利到達妳手上。我已經追蹤妳的新聞好幾年了,我想知道妳的近況,也想了解妳接下來有什麼打算。妳願意在公開場合亮相嗎?只要妳答應,我們社團願意付妳五百美元的出場費。歡迎妳隨時跟我聯絡,我很樂意提供妳更多資訊。
賴爾‧沃斯敬上
附註:此係合法的工作
要我露點?還是拍A片?幾年前出版的那本書裡有一節是「麗比‧天的成長過程」,刊登了我從小到大的照片,其中最顯眼的是我十七歲那張,我穿著俗氣的白色繞頸小可愛,幾乎包不住我顛動的成熟雙峰。有好幾家雜牌色情雜誌徵詢我有沒有意願上鏡頭,不過他們出價太低,我想都沒想就直接拒絕。就算是現在,五百塊就要我全裸入鏡,好像還是太低了。但說不定(凡事多往好處想,乖寶寶!)說不定這真的是一份合法的工作,對方是某某失親會的成員,他要去我露個面,拋磚引玉,讓大家說出各自的心路歷程。五百美元換我幾個小時的同情,可以考慮。
信的內容是用電腦打字的,只有最下面一行的電話號碼是手寫字,字體強勁有力。我按照上面的號碼撥過去,內心祈禱能直接轉進語音信箱,沒想到,在一段洞穴般的空寂過後,電話接通了,只是沒人開口。我覺得很尷尬,好像朋友開派對沒有邀請我,我卻在大家玩得正嗨時打過去。
三秒後,電話另一頭響起男人的嗓音:「哈囉?」
「嗨,請問是賴爾‧沃斯嗎?」美金的鼻子在我腳邊磨蹭,急著索討食物。
「是誰?」電話那端是一片巨大的空無,他彷彿置身在礦坑底部。
「我是麗比‧天。你之前寫信給我。」
「喔喔喔……不會吧!真的假的?麗比‧天。呃,妳現在人在哪裡?妳在市區嗎?」
「哪個市?」
電話另一端的男人(或許是男孩,他聲音聽起來很年輕)不知回頭跟誰嚷了什麼,好像是「我早就做好了」之類的,接著便回來對著話筒說。
「妳在堪薩斯市嗎?妳住在堪薩斯市,對吧,麗比?」
我正想掛電話,但那小子開始「哈—啊—囉?哈—啊—囉?」地喊了起來,好像在叫喚上課心不在焉的我。我說我的確住在堪薩斯市,然後就問他到底想要幹嘛。他嘿嘿嘿地笑,好像在說妳一定不敢相信世界上居然會有這種事。
「這個嘛,我說過啦,就是想請妳亮個相之類的。」
「亮相?」
「呃,我們這個俱樂部很特別……我們這禮拜剛好有個特別的聚會,然後……」
「什麼俱樂部?」
「呃,我們跟別人不太一樣,有點類似地下組織……」
我沒接話,讓他繼續瞎掰。我聽他一開始講得頭頭是道,現在竟然支吾起來。很好。
「嘖,這用電話講根本講不清楚嘛。我能不能,呃,請妳喝杯咖啡?」
「現在喝咖啡太晚了。」說完後我才想到,說不定他根本沒有意思要請我今天晚上喝咖啡,而是想從這個禮拜另外找時間,我心想那我接下來五個小時要怎麼打發才好。
他問:「那喝啤酒呢?還是要喝紅酒?」
「什麼時候?」
頓了一下。「今晚?」
頓了一下。
「好。」
賴爾‧沃斯的外表很像殺人魔,這表示他大概不是殺人魔。一個人如果分屍妓女、到處揩油,會想把自己裝扮得盡可能像正常人。賴爾‧沃斯坐在燒烤店正中央,桌面非常骯髒。克拉克燒烤店是一家低級酒吧,附設在跳蚤市場裡,向來以烤肉聞名,店面經過整修,店裡常客是白髮老頭和頭髮垂下蓋到眼睛身穿緊身牛仔褲的瘦巴巴型男,整體畫面並不協調。但賴爾‧沃斯不是老頭也不是型男。他大概二十出頭,一頭褐色的自然捲髮,他可能想撫平自然捲而抹了大量髮膠,只可惜抹錯地方,以至於油亮的太油亮,毛躁的還是毛燥。他戴著無框眼鏡,穿著會員專屬的緊身風衣,配上一條緊身牛仔褲,不過就只是很緊而已,並不是帥氣的感覺。他的五官很精緻,但男人要粗獷才有魅力。男人的嘴唇像花苞是一種罪過。
我走向他,他跟我對了一眼,上下打量我,一副「沒看過的妞」的樣子,沒有認出我;等到我走近他桌子旁,他才把照片跟我本人拼湊起來:雀斑,小鳥似的骨架,愈看愈扁的鼻子……
「麗比!」他喊了出來,喊完後似乎覺得太過親暱,所以又補上我的姓:「天!」他站起來,為我拉開摺疊椅,拉完後似乎後悔自己太過殷勤,默默又坐了回去。「妳染了金髮。」
「嗯。」我說。我討厭別人一開口就聊一些既定事實,這是要我怎麼回?對啊,今天真的好熱。嗯,就是說啊。我看看四周,想找服務生來點酒。一個女服務生用她美麗的背影對著我們,她穿著窄身迷你裙,豐盈的黑髮起伏如波浪。我用手指頭敲擊桌子,她轉過身,一張少說也有七十歲的面孔對,臉上濃妝豔抹,脂粉全卡在皺紋裡,紫色的微血管爬滿她手背。她彎腰幫我點餐,不知哪裡的關節「喀啦」了一聲,我說我只要一杯藍帶啤酒,她就用鼻孔出氣。
賴爾說:「這裡的肋排很好吃。」不過他自己沒點菜,只是一個勁兒吸著奶昔的殘渣。
我不吃肉,真的不吃,自從看到我家人遭到開腸剖肚後就不吃了。我還在努力忘掉吉姆‧傑佛瑞中午大啖牛肉的模樣。我聳聳肩,表示不用,接著便耐心等待我的啤酒,像觀光客一樣左看右看。賴爾的指甲很髒,這是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服務生阿婆的假髮歪了,露出底下汗溼的白髮,一綹一綹黏在頸背上。阿婆把白髮塞回去,再從加熱燈底下拿了一包酥脆的薯條。我們隔壁桌坐了個胖子,他一面啃著牛肋排,一面檢視他從跳蚤市場買來的戰利品。那是一支俗氣的舊花瓶,瓶身畫著一條美人魚。他用油膩的手指玷汙了美人魚的胸部。
阿婆一聲不響把啤酒放在我正前方,然後轉頭去招呼隔壁桌的胖子,嬌聲叫了他一聲「帥哥」。
「所以你們社團是做什麼的?」我主動發問。
賴爾滿臉通紅,開始在桌子底下抖腳。
「呃,妳知道有些男生喜歡蒐集棒球卡,或是組夢幻足球隊?」我點點頭。「有些女人喜歡看八卦雜誌,八卦到對明星的大小事情全部都如數家珍,連他小孩叫什麼、老家在哪裡都知道?」
我頭斜向一邊,警覺地點了一下,要自己提高警覺。
「呃,我們社團差不多就像這樣,只是,呃,我們的名字比較特別,叫殺手俱樂部。」
我灌了一大口啤酒,鼻子上冒出汗珠。
「聽起來很怪,但其實還好。」
「聽起來真的是他媽的怪。」
「妳知道有人就是喜歡解不開的謎,有人就是沉迷於犯罪紀實的部落格。我們社團有很多這種人,每個人都有自己著迷的案子,像萊西‧彼得森(Laci Peterson)、傑佛瑞‧麥唐諾(Jeffrey MacDonald)、莉茲‧波頓……妳和妳們全家。妳和妳們家在我們社團超紅的。真的很紅。比選美小皇后蓉貝涅還紅。」他看到我的臉皺了一下,趕緊補了一句:「悲劇,這一切都是悲劇。還有妳哥,他被關了……多久?二十五年有吧?」
「不用同情班恩。他殺了我們全家。」
「嗯。沒錯。」他含著一顆奶昔冰塊。「所以,妳跟妳哥聊過這件事嗎?」
我突然起了戒心。有一群局外人堅稱班恩是無辜的。他們會把班恩的報導剪下來寄給我,但我從來沒讀過,一看到他的照片就直接扔進垃圾桶。記得照片裡的他紅髮披肩,跟耶穌的髮型一樣,剛好搭配他容光煥發的安詳臉龐。他快四十歲了。這些年來我從來沒去探過他的監。他關在我老家堪薩斯州金納吉市的郊外,就是當年兇案發生的地方,我去探監也方便。但我畢竟不是戀舊的人。
班恩的擁護者大多是女性,耳朵很大,牙齒很長,頭髮燙捲,穿著褲裝,一個個抿緊了嘴,一副要慷慨赴義的堅毅模樣。她們偶爾會出現在我家門口,眼神裡閃著光芒。她們說我的證詞有誤,說我那時候腦筋糊塗了,我才七歲,一定是受人強迫才會出賣我哥,竟然一口咬定他就是凶手。她們通常會口沫橫飛,對我吼叫,有幾個甚至呼我巴掌。她們的舉止更顯得她們不可靠:滿臉通紅外加歇斯底里,這種女人很容易遭人輕視。而我無時無刻不在抓人家小辮子,逮到輕視的人機會絕不放過。
如果她們對我好一點,搞不好我還會說實話。
「沒有,我跟班恩沒有聯絡。如果你們找我是為了這個,那我沒有興趣。」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這樣的。妳只要人來就好,這有點類似我們的社團聚會,妳只要讓我們發問就好。妳真的都不會去想那天晚上發生的事?」
闃黑之地。
「不會。」
「那妳可能會聽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我們社團裡有一些粉絲……嗯……專家,他們比警探更了解這件案子,不過這也沒多難就是了。」
「所以你們社團裡有一堆人想說服我說班恩是無辜的。」
「呃……大概吧。不過妳也可以說服他們班恩有罪。」我覺得他的口氣有點臭屁。他湊近我,聳著肩,很興奮的樣子。
「我要一千元。」
「我可以給妳七百。」
我掃視室內一圈,沒有說出我真正的想法。其實不管賴爾開價多少我都會收,不然我很快就得找事做了。我一點都不想工作。我沒把握可以一個禮拜連上五天班。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我連要連續五天下床都有困難。連續五天固定吃三餐也很不簡單。要我每天都到辦公室報到,一坐就是八個小時(一天待在外面整整八個小時!),我做不到。
「七百就七百吧!」我說。
「太好了。到時候會有很多收藏家,所以多帶一些紀念品……呃……多帶一點妳小時候的東西來賣。包妳輕輕鬆鬆就賺到兩千塊。有信的話帶信最好,內容愈私人愈好,接近案發日期更好。一九八五年一月三號嘛。」他很熟練地說:「或是任何妳媽的東西也好。大家都對妳媽……很感興趣。」
大家都對我媽很感興趣。大家都想知道,怎樣的媽媽會遭親生兒子殺害吧?
暗處
卑鄙像器官,實實在在地長在我的身體裡;把我的肚子剖開,它會掉出來滑到地板上,多肉且黝黑,讓你盡情地踩。它在天家的血液裡。天家的血統大有問題。我從小就不乖,在那件凶殺案後更是愈來愈愛使壞。小小年紀就成了孤兒的我,被爸媽的親友丟來丟去,一下住表姊家,一下住姑婆家,一下住爸爸的朋友的朋友家;我在堪薩斯州四處為家,在各種活動式房屋、鄉間平房裡長大,長成陰沉又沒骨氣的個性。我穿著死去的姊姊的舊衣服上學校,襯衫的腋下都泛黃成芥黃色,長褲後面過寬以至於臀部鬆垮,用一條有裂痕的皮帶扣住最後一孔扣。照片裡...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