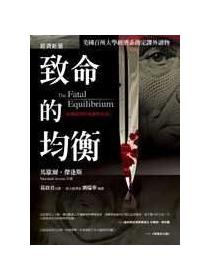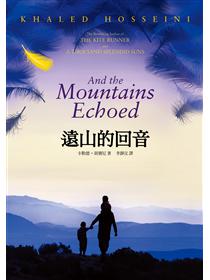名人推薦:
髙村薰是現代日本的杜斯妥也夫斯基。這次,看了她為文庫版重新改寫的《照柿》,更強化了我這種感覺。
——沼野充義(日本知名斯拉夫文學研究者)
推薦序
沼野充義(日本知名斯拉夫文學研究者)
高村薰是現代日本的杜斯妥也夫斯基。這次,看了她為文庫版重新改寫的《照柿》,更強化了我這種感覺。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毋需在此多做介紹,眾所周知是描寫某個「熱得要命」的夏日,認定自己有權逾越社會法規是個「天才」的青年拉斯柯爾尼科夫,拿斧頭砍死了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及其妹妹。《照柿》也一樣,是描寫「發狂似的」的酷暑盛夏(但這邊的舞台是東京與大阪)發生的殺人及殺人未遂案。驅使眾人抓狂殺人、宛如某種象徵貫穿全書的,是照柿,換言之,是夕陽映照下的熟柿色,這個顏色加上酷熱,決定了作品異樣凝重狂亂的氛圍。或許可以容我在此補充:射入屋內的西斜日光,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某些作品中同樣具有決定性意義。
《照柿》的主要人物,是警視廳派往八王子警署辦案的合田雄一郎警部補,以及任職羽村工廠的野田達夫。這兩人是兒時玩伴,隨著小說的進展,他們因緣匪淺的過去也漸漸揭曉。故事交錯從這兩人的觀點描述,他們為了美保子這個女人,在驚人的妒意驅使下發生衝突,最後迎來悲劇的結局。活到三十五歲、一直勉強不讓自己脫離社會正軌的兩個男人,這時候,彷彿因異樣的酷暑而中邪,在精神上出現變化,就此走岔了路。
本書開頭引用但丁《神曲》的一節,「行至人生半途/逸出正道的我/醒來已在幽暗森林之中」,想必正是暗示這樣的情節吧!《照柿》一方面描述工廠嚴苛的肉體勞動、流氓聚賭及可怕的凶殺案這種世界;另一方面也意外地大量出現繪畫與文學,達夫雖是工廠工人,嗜好卻是雕刻,甚至為此特地租了一間公寓當作工作室;他的父親則是畫作素來乏人問津、棄家業不顧的畫家。雄一郎雖然現在從早到晚四處奔走查緝犯罪,但過去也曾在大舅子加納祐介的推薦下,與妻子一同閱讀但丁。而且,至今仍會從祐介的書架自行取來拉辛的劇本《勃里塔尼古斯》,在電車上閱讀。調查殺人命案的現代東京警察與法國古典戲劇,感覺上或許是有點不可思議的組合。不過,拉辛的作品,描寫主角尼祿在嫉妒之下,毒殺與自己心上人相愛的皇子勃里塔尼古斯的悲劇,對《照柿》倒是頗具象徵意義。因為他描寫出男人為了女人燃起妒火,曝露原本苦苦壓抑的醜陋本性的過程。
高村薰是如何熟稔世界文學古典作品,只要看《晴子情歌》女主角涉獵的書籍便一目瞭然,不過我們恐怕也不能忘記,她之前描寫犯罪的小說也同樣在一開始就展現文學色彩。以《照柿》為例,那不僅限於但丁和拉辛。全書更濃厚洋溢的,恐怕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及俄國文學的影子。這是作品發表當初就被強調過的,當時的責編林勇造氏,日後回想他向作家要求,「能否寫一部類似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那種作品?」結果寫成的就是《照柿》(出自《別冊寶島 高村薰的書》)。同樣以合田為主角的前作《馬克斯之山》,其中一名警察綽號波菲里,不消說,自然也是因為想到了《罪與罰》。波菲里是《罪與罰》中的預審法官,一再執拗逼問殺人兇手拉斯柯爾尼科夫。
不過,足以聯想的不只是《罪與罰》。評論家野崎六助氏在《高村薰的世界》(情報中心出版局)指出,構成《照柿》故事的人際關係基本構造,比起《罪與罰》毋寧更像《白痴》。因為《白痴》描述的是拉戈欽與梅什金公爵這兩個男人,追求娜塔莎˙菲利波瓦那這個「宿命之女」的過程,最後以悲劇收場。不過,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中,拉戈欽是個渾身充滿陰暗情欲的男人,相較之下被稱為「白痴」的梅什金公爵則宛如基督是個絕對美好的人。《照柿》說來等於缺少梅什金,是兩個拉戈欽的故事。
不,若抱著這種心態搜尋,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影子除此之外也隨處可見。個性隨和的工廠工人岡村源太因氣性壞疽猝死後,在他家中舉行守靈時的雜亂感,令人想起《罪與罰》中,被馬車壓死的小公務員馬梅拉德夫的未亡人打理的追思禮拜;看到佐野美保子娘家的小工廠以前曾發生疑似縱火的火災,患有風濕行動不便的父親因此葬身火海這一段時,《惡靈》的讀者想必會當下想起不良於行的瑪利亞˙雷畢亞特奇娜這個登場人物吧!雷畢亞特奇娜是史塔布羅金在法律上的妻子,不幸遭人殺害,生前住的小屋也被人縱火。
真要找起來簡直沒完沒了,我不知道作者是否刻意想將杜斯妥也夫斯基換骨奪胎。但是,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世界雖是描寫將近一個半世紀前的俄國,卻預言式將現代日本的社會風貌詭異地搶先道出,因此高村薰在描寫人性晦暗情念這方面,堪稱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優秀接班人。《照柿》中在妒火驅使下掐住雄一郎脖子的達夫,感到彷彿漲滿「水太深踩不到底的浴池」的「以感情為名的滾水」正在沸騰,這種描寫之驚心動魄可以說早已超越了杜斯妥也夫斯基。
然而,令高村文學異樣「強悍」的(她的文章也被評為「如同硬質鋼鐵」),不僅是情念的激烈。毋寧,做為小說基礎的,是堪稱超級寫實主義、徹底寫實的描寫。如果少了這個,小說就變成只有觀念的捏造了。以《照柿》為例,作家這種罕有的資質,顯現在達夫任職的軸承工廠熱處理工程的細緻描寫。這裡我刻意不引用原文,但是看著工廠的描寫,讀者想必會覺得自己也被丟進那種異樣酷熱嚴苛的環境中,感到某種緊迫感吧!世人稱為「純文學」的小說中,沒有仔細調查社會上的種種職業和現實、只憑想像就隨意撰寫的作品並不少,而高村薰收集資料之徹底堪稱出類拔萃,如果追蹤作家之後的發展,從《Lady joker》出現的大田區小工廠及《晴子情歌》北海道的捕鯡魚便可看出,這種超級寫實主義一貫支撐高村文學,也一直是她的強大武器。即便放眼世界文學,也少有作家描寫得如此徹底。
不過,高村薰的筆,不只是針對工廠勞動的艱苛,也兼具緻密感,精確無比地捕捉到日常生活的瑣碎尋常表情。若要從《照柿》找出最佳範例,我想舉小說開頭,在發生跳軌自殺事件的車站,合田雄一郎初次邂逅宿命之女美保子的那一幕為例,「……女人緩緩移動腦袋,轉過來面對他。那是一張和小腿同樣白皙、同樣帶有豔光的臉龐。(中略)盯著眼前的兩個大黑洞目不轉睛,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正看得出神,身體驀然又是一陣燥熱。」這是令人預期今後的故事發展非常高明的提示。在這裡,我忍不住想起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同樣是文章開頭,佛倫斯基初次遇見安娜時奇蹟般的描寫。這才想起,《安娜˙卡列尼娜》和《照柿》一樣,被列車輾斃都是非常重要的主題。
剛才我提到超寫實主義,但光是那樣其實還無法說明高村文學的異樣「強悍」。因為如果單只是逼真地描寫現實,和照片一樣,還不算是藝術。這話聽起來好像很矛盾,但是帶入瓦解寫實的不合理,才令高村文學得到真正的強悍,得以形成值得驚嘆的小宇宙。在《照柿》中,說到常識無法說明的「不合理」,比方說,一眼就愛上美保子、陷入宿命戀情的雄一郎的「妄執」,以及驅使另一名主角做出毀滅性殺人之舉的動機的不合理。為了驚鴻一瞥的美保子,雄一郎之後採取的一連串行動,除了妄執無以名之。那麼,關於殺人又如何呢?無論在文學上或現實中,人都可能基於各種理由殺人。拉斯柯爾尼科夫說穿了是基於思想上的理由殺死高利貸老婦。卡繆的《異鄉人》主角「因為太陽照耀」殺死阿拉伯人。但是,釀成《照柿》高潮的殺人,雖然不合理(換言之欠缺了一般定義的動機構成的合理說明),卻具有異樣說服力。這點說穿了,是因為作者雖讓被逼到不惜行凶的人,墜至情念的深淵,同時卻又描寫得緻密精細才辦得到。極盡寫實之能事後,出現驚人的怪物──那就是高村薰描寫的人物,那超越照片的寫實感直接逼近讀者的心。
高村薰趁著已出版過單行本的作品發行文庫版,總會大幅改寫(有時甚至變成截然不同的作品),這點廣為人知。這大概就是不計現實得失、嚴格對待自己作品的作家魂吧!無論是《神之火》或《馬克斯之山》,都經過大幅改寫與添筆,作品給人的印象大不相同,到了《拿起手槍》,更已超越改寫之域,改頭換面變成另一部作品《李歐》。《照柿》亦然,自單行本於一九九四年出版已過了十二年。歷經《晴子情歌》和《新李爾王》益形成熟後,作家傾力投注現在的力量,可以說已經脫胎換骨。單行本版與這個文庫版若要做比較,是應該另外進行的大工程,所以我想留待下次機會,但若容我指出當下注意到的一點,那就是故事情節基本上雖沒變,但多餘的──通俗的,或者帶有傷感情調的──說明與對話被大量刪除,作品整體看來要比以前更緊湊。結果,突然墜入情網和殺人動機的不合理因此變得更加明顯,比以前更加費解的同時,作品本身的力道也增強了。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比較一下兩個版本,例如雄一郎與美保子在電影院交談的對話。在分量上,據我個人計算,大約減少了百分之十五(過去通常是改寫後會大幅增加分量,這點在根本上大不相同)。
高村文學,現在,已超越純文學或推理小說、犯罪小說這些標籤,被視為優秀文學屹立不搖。早在一九九三年,換言之也就是《照柿》尚未發表時,高村薰便曾在某次訪談中表示,「我至今不認為自己在寫推理小說。我只是一直在寫小說,只不過那湊巧不是戀愛小說或純文學或私小說。(中略)簡而言之,書就是書。小說就是小說。」(摘自《海燕》一九九三年十月號)對,基於這種意味,《照柿》的確不需要多餘的形容,簡而言之,就是小說。而且是描繪人性的妄執與感情漩渦──這已經無法光用優秀來形容,所以我寧可稱為「強悍」──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