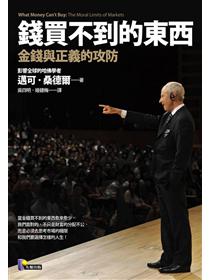「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所獲致的成功確實是第三波民主化之中最令人動容與振奮人心的故事之一。」──中研院副研究員,吳叡人
認識轉型正義的必讀經典
在嚴懲與縱放之間 面對歷史傷痕的第三條路
將宗教理念落實到政治的完美典範
一九九五年,南非總統曼德拉就職剛滿一年,面對過去種族隔離時代的政治迫害,他決定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並指定屠圖主教為首任主席。委員會的最大特色,就是不以「復仇」為宗旨,只要當年的加害者願意坦承罪行,就可以獲得大赦。
這個看似爭議的作法,是為了避免產生「紐倫堡大審判」的後果。當時新南非剛建國,若隨即追究白人刑責,恐會造成社會分裂,黑人將陷入復仇情緒,白人則陷入恐懼。但又不可能如智利的皮諾契特與軍政府一樣,在政權移轉的過程中全身而退。所以,為了兼顧追尋真相與彌補傷痕,和解委員會的任務便是讓受害者與加害者在全國性的聽證會中陳述個人經驗,讓當事人放下重擔,也讓政府得以記錄、還原過去的歷史。
正如屠圖主教在書中所說:
我們任何人都無權說「讓過去的事過去吧」,然後揮手間一切就真的過去了。我們的共同經驗恰好相反——過去的一切並未消失、沉寂。除非我們能徹底地解決一切,堅定地直視它的核心,否則它就會不斷回過頭來糾纏我們,甚至挾持我們;因為這正是它奇特的本質。
作者簡介:
戴斯蒙‧屠圖,一九三一年生,前南非聖公會大主教。早年曾為中學教師,一九五三年,南非政府強制執行種族隔離教育,此後他便積極投入反抗運動。一九六二年,他負笈英國,於國王學院研究神學,四年後回國任教並成為教會的重要領導人。一九八四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一九九五年總統曼德拉提名他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完成和解委員會的任務後,近年來他成立基金會,致力於愛滋病的研究與預防,並照顧愛滋感染病童,協助他們解決教育與謀生問題。
屠圖主教最重要的成就,在於教導世人如何將宗教理念落實於政治重建工作。全球舉凡經歷過政治迫害的國家,無不借重南非經驗來重建社會,彌補裂痕。二○○七年,屠圖主教訪問台灣,與各界分享實現轉型正義的經驗,對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台灣,帶來深遠的啟發。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中研院研究員吳叡人、玉山神學院陳南州牧師
名人推薦:中研院研究員吳叡人、玉山神學院陳南州牧師
章節試閱
導論
論道德的政治基礎:《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的逆向閱讀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
彌賽亞只在已經不再需要他的時候到來;他將在他已到達的第二天來到;他將到來,但不是在末日,而是在末日的第二天。──卡夫卡(Franz Kafka)
屠圖主教這本《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已經成為當代轉型正義研究的經典之一。它不僅是一位直接參與、主導南非著名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ttee, TRC)的政治行動者對一場當代最艱鉅的政治大和解的歷史見證,同時更是一位積極入世的宗教家對這段歷史最動人的道德見證。藉由雄辯而有感染力的宗教語言,對政治提出道德的見證,揭示政治的道德基礎、救贖與希望──這就是本書奇特而強大魅力的來源。
然而我們不能忘記,和解的政治終究是一種政治,在這個特殊場域之中,政治受人的道德意識所驅動、制約,但政治同時也在型塑、制約道德意識。換言之,所有轉型正義故事的道德劇背後都平行存在著一個爭奪物質與象徵權力,爭奪地位、意義與價值的殘酷劇場。對於所有這些敘述,我們因此都必須進行道德與政治的雙重閱讀。屠圖主教所講述的這個南非大和解的故事當然也不例外。首先我們可以順著他的筆觸閱讀,讀故事裡的宗教與道德啟示,讀人性的惡如何被自身的善所救贖,而我們會被感動,啟發,然後我們闔上書本,靜靜等待時光的流逝與情緒的平復,接著我們重新打開書頁,但是這回我們要倒著讀,讀自私、卑劣、衝突、對決,以及被壓抑與掩蓋的,無法救贖的怨恨、分裂與復仇慾望。第一次我們讀屠圖主教的表層敘事,也就是政治的道德基礎,第二次我們讀深層敘事,也就是道德的政治基礎。當我們完成這個雙重閱讀,我們才會理解道德與政治如何互為表裡,善與惡如何彼此糾結,救贖與背叛如何共存,而撼動人心的歷史如何必須在一個脈絡之中發生。
二
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創造了在紐倫堡大審對納粹的「報復」與西班牙在上一世紀末期對佛朗哥獨裁的「遺忘」之外,處理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一個社會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對於威權體制下所發生的國家暴力與人權侵害事件進行清算處理的政治工程──的第三條路,也就是以正義交換真相(加害者承認犯行以換取有條件赦免),以真相誘導被害者寬恕,進而促使社會和解的模式。這是一種高難度的衝突解決模式,然而南非TRC確實獲致了一定的成功。對於這個成功,屠圖主教在本書中提出了一個宗教(主要是基督教)─道德式的解釋:人同時具有為惡與向善的能力,前者導致加害與衝突的悲劇,後者則激發出懺悔與寬恕,最終克服了前者,帶來了和解。這個說法動人卻難以驗證,因為宗教的論證涉及了信仰。作為非信徒,我們不得不在神學教義之外,尋找某種比較世俗的(secular)理解方式:我們不得不將上帝的還給上帝,然後專注探究屬於凱撒的美德與惡行──也就是政治。
三
在甚麼意義下,南非的TRC模式是一種政治?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思考。
首先,TRC是一種推動轉型正義的模式,而轉型正義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它是民主轉型(democratic transition)的一環,目的在處理權力重分配與憲政制度安排之外,涉及價值與規範面的問題。更具體而言,轉型正義是一種依民主、人權原則清算過去的國家作為,以確立政治領域是非對錯標準的政治,因此涉及了「意義」的爭奪──誰來決定是非對錯,又該怎麼處理錯誤的行為,以及如何記憶這段歷史等等。在這種意義的政治中,道德論述確實不可或缺,然而更根本的決定性因素依然是實力的對決。
其次,南非與拉丁美洲、東亞臺、韓各國的民主轉型類似,都屬於「談判轉型」(negotiated transition)的類型。所謂談判轉型的共同特色是,舊政權菁英仍然掌握相當實力,民主派的力量不足以徹底擊敗、清算舊政權,因此被迫與舊政權菁英談判,以不追究過去罪責換取其下台。阿根廷、智利的民主化過程中,民主派被迫簽訂不起訴協約就是最有名的例子。南非的TRC模式中,以赦免換取真相以及對非洲民族大會(ANC)和國民黨雙方的人權侵害事件同時進行對稱性調查等作為,其實是一種政治妥協,源於ANC實力的限制。民主轉型前夜的南非,儘管ANC獲得了佔人口絕大多數的黑人民眾與國際支持,但白人仍掌握政治與軍警特務大權,以及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ANC如斷然採取激烈清算作為,非常容易引起白人的反彈、杯葛與抵抗,甚至導致政變或內戰。民主與獨裁兩派實力的對比,深刻制約了轉型正義實現的幅度與範圍。TRC能夠有效說服許多犯下重大罪行的警察出面認罪協商,乃至最終迫使前總理波塔接受審判,說明了ANC確實擁有不可輕忽的實力,然而TRC至始至終無法獲得另一個主要加害群體──軍方的合作,卻也同時反映了ANC實力的限制。
第三,我們常常忘了一個重要的事實:轉型正義不只是民主轉型的規範性面向而已,它同時還具有國家整合與民族建構(nation-building)的性質。構成轉型正義理念的諸核心價值如真相、問責、療癒、對話、和解與共同記憶等,正好體現了某種進步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的計畫。為什麼轉型正義會連結「民主」與「民族」呢?因為穩定的獨裁統治往往建立在社會分裂的基礎之上,而涉及權力重分配的民主化則極易誘發,乃至激化分裂雙方或各方的對立衝突,嚴重者甚至可能陷入內戰,導致國家解體。因此,經歷民主轉型的國家在進行權力重分配、建立新制度與新價值等由「破」到「立」的工程之同時,經常也必須處理社會整合的難題。轉型正義所揭櫫的兩個看似不相容的理念──清算與和解,反映的不是民主派菁英的邏輯混亂,而是民主化過程向他們同時提出的兩個困難的現實要求:轉型與整合。
幾乎所有從八○年代以來出現的轉型正義個案都具有國家整合意涵,南非的TRC模式則是其中一個重要典範,因為它幾乎展現了一個民主的公民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patriotism)的所有重要元素。在這齣共同體的道德劇中,有曼德拉扮演大立法者萊克爾葛斯(Lycurgus),有屠圖主教扮演先知,有白種義人伯萊恩(Alex Boraine),有獻祭的受害羔羊,也有皤然悔悟的兇手。更重要的是,彩虹南非的建國者們巧妙地交互運用神學教義的權威與「本土」民間信仰(所謂「吾布恩度」〔ubuntu〕)的正當性,通過全社會規模的象徵與儀式性行為──公開審訊、傾訴、認錯、寬恕、和解,展演了一場動人的民族靈魂自省(national soul-searching),確立了「真相與和解」論述的霸權地位。而TRC透過真相調查報告書創造一個加害與被害雙方之「共同記憶」的嘗試,則讓人想起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所說的,所有民族主義歷史敘事「選擇性記憶」的邏輯。借用安德森的語言來說,TRC的共同記憶論述必須「再次保證」(reassure)過去那段種族隔離制的歷史是同族的「手足相殘」(fratricide),而非異族的殖民壓迫。毫無疑問,以TRC為中心展開的南非轉型正義是一次令人嘆為觀止的國/族整合的政治工程。它誘發了如此驚人的熱情與能量,以致於南非憲法法院大法官奧比.薩克斯(Albert Sachs)會如此忘情地高呼說,TRC的工作「就是在創造一個民族(it is the creation of a nation)!」因此,我們必須穿透道德語言的表象,在這個公民民族主義政治(politics of civic nationalism )的層次上,重新理解與評估TRC的成敗。
四
南非TRC模式的轉型正義本質上是一種建立在民主與進步價值上的自由的民族主義計畫(a project of liberal nationalism),然而不管多麼進步,任何民族主義都不得不創造一個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來進行整合,而不管如何開放與多元,任何試圖整合的大敘事都難以避免壓抑與排除異質元素。TRC所受到的種種批判,幾乎都共同指向這一點:為了民族國家最終的和解(整合)的最高目標而犧牲了完整的真相與正義。我們可以列舉幾種批評的例證。
TRC的最主要目的是社會和解,其政治形式是民族國家的整合與形成,而其報告書的敘事形式,則是以民族國家之終極與必然之整合為目標的目的論敘事(teleological narrative)。哥倫比亞籍人類學家卡斯蒂耶-庫耶利(Castilleo-Cuéllary)指出,為了生產這個和解敘事,TRC以「加害者vs被害者」二元對立關係構圖為敘事前提,將人權侵害個人化,在調查時凸顯特定類型個案(具有明顯可見之加害被害關係者)與證據,忽視種族隔離制對普遍不特定對象所施加之結構性與系統性日常性暴力。在報告的敘事中,則刻意凸顯和解,忽視或壓抑拒絕和解或報復的聲音。其結果是,被害者的主要類型變成直接與體制鬥爭的少數反抗行動者與烈士,而非受在每日生活中受到體制壓迫的絕大多數一般民眾。
歷史學家費歐娜.羅斯(Fiona Ross)指出,在TRC選擇的個案中,如果受害者是女性,則往往凸顯其作為性侵受害者的面向,壓抑女性作為抵抗者的行動主體性。
人類學家理查.威爾森(Richard Wilson)關於約翰尼斯堡地區民間文化的民族誌研究證明,國家層次的主流「和解」論述其實壓抑或掩蓋了普遍存在於地方層次對報復性正義的強烈渴求。他更直接點出這個事實:TRC所謂「真相與和解」論述,其實只維繫了國家層次政治菁英之間的脆弱同盟,並未在人民中形成一個真正的共識。
也有論者提醒我們,在國際、國家與地方這三個層次,對於轉型正義原本就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態度與需求。國際層次的轉型正義工作,如負責起訴戰犯的國際刑事法庭(ICC),比較強調人權的保護,而國家層次的轉型正義則往往重視和平、和解與政治穩定,但是地方社會卻非常重視報復性正義。這三種需求非常難以同時滿足。
儘管有著種種缺點與限制,TRC確實達成了幾個重大的目標:
(一)它成功地創造了「真相與和解」的霸權論述(政治妥協的道德性基礎,國家歷史大論述的重構,以及修復式正義的優位性),協助維繫了民主轉型期的政治菁英共識,最終促成和平轉型與(至少在菁英層次的)國家整合。
(二)實現了普通司法體系難以達成的,一定程度的真相與正義。
(三)推動了一次廣泛的全社會性人權與民主教育,有助於民主鞏固。
(四)透過有效的宣傳,使TRC成為國際實踐轉型正義的一種典範與選項。
作為一種民主轉型與國家整合的政治,南非TRC所獲致的成功確實是第三波民主化之中最令人動容與振奮人心的故事之一。
五
和南非一樣,臺灣也是經由談判協商而達成民主轉型的個案,然而南非TRC模式的轉型正義卻難以在臺灣複製,因為即使同為談判轉型的國家,臺灣與南非之間仍然有許多重大差異。讓我們逐一檢視這些差異:
轉型模式:臺灣民主轉型的最重要特徵是,談判過程由舊政權內部的改良主義者(李登輝)主導,民主派的民進黨因為實力不足,只能扮演年輕合夥人(junior partner)的角色,成為李登輝用來向國民黨內強大保守派施壓的工具。這個高度不對等的談判模式決定了臺灣初期轉型正義工程的保守、妥協性格:非但沒有起訴任何加害者,連在有限的真相究明行動(行政院的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中都沒有指名任何加害者,從頭到尾只提被害者與被害者補償。換言之,即使將李登輝包含在內,整個臺灣的泛民主派根本連向國民黨保守派提出「用真相換取和解」的實力門檻都沒達到。臺灣民主派的脆弱與ANC的強大實力適成對比。
壓迫模式與受害類型:國民黨政權在臺灣的獨裁統治,早期仰賴大規模的國家暴力,後期則在國家暴力逐漸日常化、官僚化之後,開始依賴與本地菁英的利益交換,也就是政治學者吳乃德所謂的「威權侍從體系」。藉由這個交換體系,國民黨收編大量本地菁英,形成廣泛的本土獨裁共犯結構,也分裂了本土社會。因為大規模國家暴力發生在領臺初期,所以臺灣社會對轉型正義的熱情集中於早期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之上,對於國民黨後期威權統治的態度,則有著明顯的分歧。
領導者的政治判斷與政治意志:臺灣民主化初期的兩位總統──「虎口下的總統」李登輝,以及始終難以贏得執政多數的陳水扁──都基於自身實力不足的判斷,捨正義而取穩定,因此缺乏追究真相的政治意志。陳水扁在二○○六年政權危機之後才開始積極處理轉型正義,但此時已喪失正當性與社會熱情,因此注定以失敗告終。其結果是,轉型正義議題為舊政權出身的人物馬英九所收編。
知識界與公民社會:南非的TRC模式並非源於政界,而是由學界首先倡議,公民社會繼而積極推動,形成強大共識,最終才成為政治的選項。遺憾的是,臺灣的學界與公民社會沒有在民主轉型之初,社會熱情最強的時機,提出有效而系統性的轉型正義構想(不一定是TRC),對社會進行即時的教育與動員,從而對政治菁英構成壓力。九○年代民主化時期臺灣社會的訴求主要集中於二二八等特定歷史事件,缺乏遠見與系統性論述,得以將轉型正義、民主化與國家整合連結起來。
意識形態:臺灣是世俗導向極強的社會,民間宗教的世俗性也很強,基督教式超越性信仰的基礎較為薄弱,因此難以立即襲用屠圖主教或者拉丁美洲式的宗教性論述。另外,除長老教會等少數例外,臺灣宗教界沒有積極介入政治或公民社會事務的傳統,各種宗教教義中的公民意識元素尚待發展。也因此,轉型正義在臺灣仍然主要是一種世俗的事物,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臺灣也沒有發展出一個足以動員公民熱情的,強大的非宗教性轉型正義論述。
民主派缺乏實力,領導者缺乏意志,社會菁英被國家收編為共犯,知識界缺乏遠見與歷史洞見,公民社會尚未成熟,以及強大論述的付之闕如──這一切臺灣在地的脈絡與歷史特性,這一切作為臺灣人的「共業」,決定了我們難以強求複製TRC模式,必須另尋出路的命運。
六
出路在哪裡?歷史其實已經告訴我們,我們只剩下一條佈滿荊棘的道路,那就是回到民間,回到公民社會,從頭做起,由下而上,從根紮起。
所以我們組織了一個小小的「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TaiwanTRC, http://www.taiwantrc.org/),沒有法律授權,沒有國家資源,沒有宗教加持,沒有社會熱情,也不再能夠召喚任何選票,轉型正義在臺灣如今變成一種純然世俗,純然民間的志業,一種社會運動。我們必須完全仰賴志工,將極度匱乏的資源集中在幾種基礎的工作之上:調查、教育、監督政府與推動立法。我們以單薄的人力,南北奔波,勉力進行極為有限的真相訪查,一點一滴拼湊那段黑暗歷史的圖像。我們在大學開設課程,在綠島和景美的國家暴力現場協助舉辦營隊以教育年輕世代,促成健在的受難者前輩與青年的世代交流,試圖達成一點初步的療癒與傳承目標。我們緊盯著收編了轉型正義論述、如今重返執政的舊政權口惠而實不至,甚或扭曲人權精神與歷史正義的粗糙施政,以一篇一篇文章,一場一場公聽會,一次一次溝通,事半功倍、徒勞無功地緊盯這個對人權沒有信念,對民主沒有熱情的舊政權,但卻依然堅信滴水會穿石,真相會逐步揭露,正義會漸漸彰顯。因為歷史的制約,因為政治的失敗,因為知識的無能,臺灣的轉型正義如今回到了它的原始型態──在先人埋冤(tai-oan)之地,面向過去安魂與召喚,面對未來夢想與意志。
然而如果沒有彌賽亞,希望的根據在哪裡?二○○七年四月屠圖主教和TRC副主席伯萊恩博士受臺灣民主基金會邀請訪臺並參與「轉型正義與國族融合研討會」,筆者也參與了這場由一個正在傾倒中的民主政權所舉辦的遲來的研討會,並且對臺灣政局、社會的世俗性格以及轉型正義前景作了極度悲觀的發言。聽完我悲觀的話語,在臺下旁聽的屠圖主教立即起身發言,以他充滿魅力的言語和笑容,溫暖地慰撫這個不可知論者,要我對臺灣保持信心。此時和筆者同場發言的伯萊恩博士轉身笑著對我說:
當潘朵拉打開盒子時,最後飛出來的是什麼呢?
我只得苦笑回答說:「hope!」然而如果沒有彌賽亞,希望的根據在哪裡?數度展讀屠圖主教這冊《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我突然領悟到,其實希望不一定必須是一種信仰或信念,希望可以是一種意志,一種分別善惡,厭棄惡,朝向善的意志,而我們必須仰賴理性去維繫這個意志──不是工具理性,而是漢娜‧鄂蘭所說的,面對善惡的問題,必須負起身為一個人的「思考」與「判斷」責任的實踐理性:
最大的為惡者是那些不記憶的人,因為他們從未思考,而沒有了記憶,他們就肆無忌憚了。對於人類而言,思考過去的事務意味著向深層境界移動,意味著紮根,讓自己穩定下來,使他們不致於被任何可能發生的事物席捲而去,不管那是所謂時代精神、大歷史,或者就只是單純的誘惑。最大的惡不是根本的惡,它沒有根,而正因它無根,它就沒有任何限制,所以它可以走向難以想像的極端,橫掃整個世界。(’Some Questions of Moral Philosophy’, 1965-66)
第二章 紐倫堡還是全民遺忘?──第三條道路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的選舉日,是南非的轉捩點。它代表新南非的誕生,如競選口號所說的,民主的、無種族主義、無性別歧視的南非。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殘酷壓迫和極端不公的種族隔離制度走入歷史。在新的時代,我們很快就發現到,沒有人會承認自己曾是種族隔離的支持者。某些新現象在四月二十七日出現了。受傷的人不會再被遺棄在路邊;在過去,救護車風馳電掣奔向出事地點,專為救治另一種族的人。再不會有人被迫離開家園,然後像垃圾一樣被拋進貧困的班圖黑人家園。上帝的子孫再不會受到侮辱。種族分類局(Race Classification Boards)把南非人像牲口一樣分類。(同一個家庭的成員經常被劃分成不同的種族,膚色稍深的被歸入較低級的一類。有些人寧肯自殺,也不接受這種荒唐專橫的分類。)孩子們再不用接受稀薄而無內涵的教育,它實際上是要讓黑人兒童接受永遠的奴役,順從至高無上的白人主子。這一教育制度的始作俑者維爾華德博士(Dr. Hendrik Verwoerd)是種族隔離制度的倡導者,後來還擔任首相。他曾大言不慚地說︰
學校必須教導班圖人(Bantu)符合社會經濟層面的需求……教班圖孩子數學又有什麼用,他們實際上又用不到……教學內容與培訓課程必須依據人們的發發展機會而有所不同……。
我相信,這些事「再也不會發生了」。在新南非,我們再也不可能制定死板的法條,將無數人的生活從塵世打入地獄,因為新南非的至高權力不在議會,而是我們的新憲法,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世界上最自由、最以人權為本的憲法。立法不能僅憑議會的喜好,而是要得到我們的最高法院——憲法法院──的批准。誕生時間還不長的憲法法院已經表明,它將打擊一切悖於憲法宗旨和條款的行為。憲法不是一紙空文,而是所有南非人透過其所選出的代表所達成的莊嚴契約。
新的治理帶來許多新事物,但許多舊的面向也徘徊不去,如同灰暗而陰沉的黑雲,威脅我們嶄新的光明日。但是誰也沒有魔杖,新制度的設計者無法只是揮揮手,嘴裡叨念著「嘿!快變」,就在一夜之間把南非變成到處流著奶和蜜的天國。種族隔離制度持續了半世紀之久,又以殘酷的手段被落實,其餘毒難以抹除,還會在今後漫長的歲月中影響著我們。
種族隔離制度本質上有系統且強力地摧殘各種人權,正如五位資深法官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證詞所述:「種族隔離制度本身以及實施該制度的方式……就是對人權的粗暴傷害。」許多南非人都忘不了過去政府所犯下的惡行,比如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的沙佩維爾(Sharpeville)大屠殺。當時人們上街和平抗議通行證法(Pass Laws,編按:有色人種離家或到指定的地點都要攜帶通行證),但警察驚慌失措,向人群開火,六十九人倒地身亡,其中許多人是在逃跑時被擊中了背部。
人們也忘不了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六日的索韋托抗議事件。手無寸鐵的學生走上街頭,反對政府將斐語(Afrikaans)定為授課語文,但許多人在抗議遊行中被射殺。斐語被視為壓迫者和種族隔離制度執行者的語言。南非國民黨(National Party)自一九四八年起實行種族隔離制度,他們絕大部分人都操斐語。
南非人還記得那些在警方拘留室神祕死亡的人。當局稱這些人自殺了,用皮帶上吊了,洗澡時踩在肥皂上摔死了,還有的則從牢房或審訊室跳窗自殺。大部分的白人也許會相信這些話,但黑人是絕對不接受的。我們還被告知有的人是自殘而死。黑人自覺運動(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的年輕學生領導人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就是其中之一。據說一九七七年九月,他在和審訊者發生莫名且無理的爭吵時,以頭撞牆。史蒂夫赤身裸體,警方用卡車開了一千五百公里把他送到普利托里亞,說是要接受治療,可是到達不久他就死了。誰也沒有解釋,為什麼不能在他被監禁的伊麗莎白港進行急救,又為什麼讓他毫無尊嚴,昏迷中赤裸著被送往普利托里亞。
人們記得一九八五年在夸祖魯—納塔爾省阿曼奇姆多蒂(Amanzimtoti)的爆炸事件。放置在一家購物中心外垃圾桶中的爆破彈,在忙著聖誕節採購的人群中爆炸,五人死亡,六十人受傷。
還有一九八六年的瑪古酒吧(Margoo’s Bar)爆炸事件。羅伯特.麥克布萊德(Robert McBride)和兩個同伙在附近安放了汽車炸彈,三人死亡,六十九人受傷。據說這是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首領下達的命令。民族之矛是非洲民族議會的武裝派別,以鄰國波札那(Botswana)為根據地。
許多南非人看到殘忍的「項鍊」酷刑將人處死時,無不感到噁心。施刑者將灌滿汽油的輪胎套在受害者的脖子上,然後點火。城裡支持非洲民族議會的「同志」用這種可怕的處決方法來懲治「叛徒」,即被懷疑和政府合作的那些人;也用在自相殘殺上。非洲民族議會被禁後,許多同情者組成聯合民主陣線(United Democratic Front, UDF)。史蒂夫.比科發起黑人覺醒運動後,擁護者支持其理念而成立阿扎尼亞人民組織(Azanian People’s Organization, AZAPO)。但這些解放組織卻彼此交戰。令我們無比驚恐的是,人們(當中還有小孩子)居然能在痛苦掙扎的受害者周圍起舞。種族隔離制度既剝奪了執行者的人性,也剝奪了受害者的人性。在這一點上,種族隔離制度真是太成功了。所有人都會記得,這一切就是我們過往的一部分,我們歷史的一部分。
讓人驚恐的,還有一九八三年五月普利托里亞教堂街上的慘案。巨型炸彈在南非空軍總部外爆炸,造成二十一人死亡,兩百多人受傷。非洲民族議會宣布對此次爆炸負責。
接著就是一九九三年七月開普敦聖詹姆斯教堂的大屠殺。在那次襲擊中,泛非洲人大會(Pan Africanist Congress, PAC,一九五九年脫離非洲民族大會的解放組織)兩名成員衝進星期天的禮拜儀式,用機關槍殺死了十一名教徒,造成五十六人受傷。在這場城市游擊戰中,再神聖的事物也不被放在眼裡。
這些類似的暴行充斥於我們的歷史,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應該認真對待這段歷史、這段過去。我們不能裝作這一切並未發生,許多事情人們還記憶猶新。
實際上,在政權轉移時,是否應該妥善處理既往歷史的問題,眾人間並不存在異議。但問題不在於「是否應該」,而在於「應該如何」處理仍歷歷在目的過去。
有些人希望借鑒紐倫堡的模式,將所有嚴重違反人權的罪犯都捉拿歸案,讓他們經受正常司法程序的煎熬。結果他們發現這條路根本行不通,也幸好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盟軍徹底打敗納粹及軸心國,因此得以實施所謂「勝利者的正義」。被告一方毫無發言權,坐在審判席上的卻是人權的嚴重違反者(例如蘇聯官員,他們的罪行在史達林期間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整個審判過程讓不少德國人耿耿於懷。紐倫堡審判五十年後,我參加英國廣播公司的專題節目,地點在紐倫堡當年的審判廳,當時我還是感到這一切都不對勁。德國人接受了紐倫堡,因為他們一敗塗地,勝利者可以在被打翻在地的敗軍身上再踏上一隻腳。在南非,任何一方都無權實施勝利者的正義,各方勢均力敵,沒有一方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可以擁有這種權力。因此,為了讓南非轉型成民主、法制和尊重人權的國家,相關人士在進行繁複的討論後,否決了紐倫堡方案。
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如果種族隔離政權的軍警單位發現自己將以迫害者的身分面臨法律嚴懲,他們就不會支持這一和談方案,但它讓可是我們得以實現和平政權轉移,從高壓過渡到民主,宛如奇蹟一般。當時多少人做了可怕的預測,認為會發生大規模流血事件,災難將全面來襲。他們仍掌握著槍桿子,仍然有能力顛覆大局。
有些南非人,還有一些國際人士都在抱怨,我們為何不將所有罪犯繩之以法。這些人士都是和平轉移的既得利益者,都在新的民主政體佔有一席之地,當然可輕鬆地批評。我們都很健忘,忘了一九九四年之前我們如何焦慮不安。一場全面的災難如在弦之箭,一觸即發。由於上帝的慈悲,我們得以倖免。那些在新政權中享有位子的人過早地忘記了這一切原本多麼脆弱、多麼渺茫,忘記了整個世界仍然以驚奇的眼光注視著這一奇蹟的發展。奇蹟是談判的結果。如果我們堅持將所有迫害者送上法庭,談判就不會有結果,也不會有民主的新南非。紐倫堡後盟軍可以打起鋪蓋回家,我們南非人可是要朝夕相處的!
導論
論道德的政治基礎:《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的逆向閱讀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
彌賽亞只在已經不再需要他的時候到來;他將在他已到達的第二天來到;他將到來,但不是在末日,而是在末日的第二天。──卡夫卡(Franz Kafka)
屠圖主教這本《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已經成為當代轉型正義研究的經典之一。它不僅是一位直接參與、主導南非著名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ttee, TRC)的政治行動者對一場當代最艱鉅的政治大和解的歷史見證,同時...
目錄
導讀 論政治的道德基礎 吳叡人
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之評介與省思 陳南州
第一章 序幕
第二章 紐倫堡或是全民遺忘?第三條道路
第三章 及至時候滿足
第四章 什麼是正義?
第五章 開始行動
第六章 受難者聽證會
第七章 我們真的想寬恕,但不知寬恕誰
第八章 那是我兄弟,我認得那雙鞋
第九章 我為什麼做這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第十章 我們原先並不知道
第十一章 沒有寬恕,真的沒有未來
後記
致謝
導讀 論政治的道德基礎 吳叡人
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之評介與省思 陳南州
第一章 序幕
第二章 紐倫堡或是全民遺忘?第三條道路
第三章 及至時候滿足
第四章 什麼是正義?
第五章 開始行動
第六章 受難者聽證會
第七章 我們真的想寬恕,但不知寬恕誰
第八章 那是我兄弟,我認得那雙鞋
第九章 我為什麼做這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第十章 我們原先並不知道
第十一章 沒有寬恕,真的沒有未來
後記
致謝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24收藏
24收藏

 36二手徵求有驚喜
36二手徵求有驚喜




 24收藏
24收藏

 36二手徵求有驚喜
36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