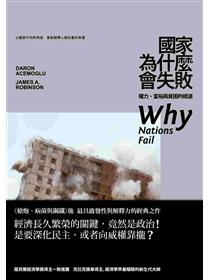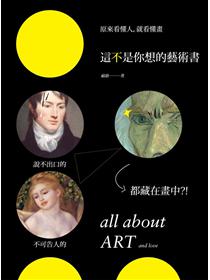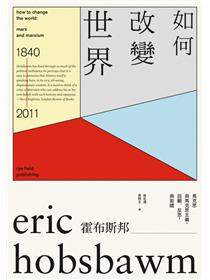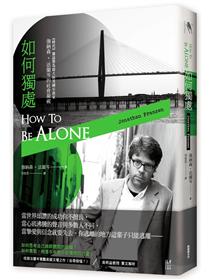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翰‧史坦貝克
20世紀最具傳奇色彩戰地攝影師Robert Capa
攜手創作精彩紀實作品
俄羅斯,一個人人被教育要絕對相信政府的國家,
相對於外面世界,她,樣板而失焦;
但透過約翰‧史坦貝克的眼睛與卡帕的鏡頭,
我們看到俄羅斯最接近”真實”的一面,
處處斷壁殘垣的景況下,百姓們展現了無窮活力和樂觀的笑容……
一九四七年,東歐降下鐵幕之際,世界知名作家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翰‧史坦貝克,與二十世紀最具傳奇色彩的戰地攝影師羅伯‧卡帕,兩人聯手合作,親自造訪俄羅斯境內各城市,諸如莫斯科、基輔、烏克蘭、史達林格勒,以及烏克蘭、高加索等地,決意將歷經二次大戰後重建期的蘇聯最真實的面貌呈現世人眼前。
俄羅斯人是怎麼生活的?鐵幕外所見的報導有多少是真實的?
為了報導真相,史坦貝克與羅伯‧卡帕決定要「更靠近」鐵幕下的俄羅斯;他們只記錄眼見的事實,而且不加以批判、論斷;因之,他們希望做到的是「俄羅斯紀事」,而非書寫「俄羅斯故事」。
在這趟詳實記錄俄羅斯的真相之旅中,史坦貝克與羅伯‧卡帕見到極權國家底下的「樣版城市」,以及訪問過程中官方說是陪同招待實則監視、令兩人哭笑不得的諸多滑稽景況。而另一方面,在深入市井小民的生活圈,雖然眼見的是殘破簡陋的景象,但這些百姓置身戰後的復甦重建,髒污的臉上卻一派開朗與樂觀,讓他們動容。而這些正是他們希望報導的“偉大的一面”之外的真相。
此書融合了兩位大師的熱情與幽默,透過信實的文字、震撼力十足的照片,將一路上接觸到的官僚政客、官方嚮導、商人、農人、學生、孩童、酒徒等等,彷如影像般一幕幕展現眼前,讀之令人莞爾!
作者簡介:
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
一九O二年出生於加州沙林納斯,成長於距太平洋岸二十五哩之遙的農地沃谷;河谷海岸均是他傑出小說的場景。一九一九年,他進入史丹佛大學就讀,斷斷續續選讀文學與寫作。一九二五年輟學離校,往後五年在紐約市當工人和記者維生,同時創作首部小說《金杯》。婚後遷居太平洋叢林市(Pacific Grove),出版兩本以加州為主題的短篇小說《天堂牧場》(1932)和《大地的象徵》(1938),另有數篇篇小說集結成的小說《長谷》(1938)。一九三五年問世、描述蒙特利(Monterey)鄉野鄙人的《薄餅坪》讓他功成名就,經濟無虞。
史坦貝克寫作勇於實驗。他在一九三O年末著有三本書寫加州勞動階級的作品《相持》(1936)、《人鼠之間》(1937),以及經典作品《憤怒的葡萄》(1939)。一九四O年初葉,史坦貝克以《被人遺忘的鄉村》一書成為製片人。到了一九四一年的《柯提茲海》(1941)又搖身一變成為嚴肅的海洋生物學研究者。此外,他也為戰爭效力,寫下《投弹了》和引人議論的劇本小說《月亮下去了》。繼《製罐巷》(1945)、《前進的客車》(1947)、《滄海淚珠》(1947)、《史坦貝克俄羅斯紀行》(1948)、實驗劇《熾熱的光》(1950)和《柯提茲海航海記》之後,融合雄渾的沙林納斯河谷傳奇與家族史於一爐的劃時代巨著《伊甸園之東》(1952)問世。
他後半生與第三任妻子住在紐約市和沙格港(Sag Harbor)。後期作品包括《甜蜜的星期四》、《比竇四世瞬息王朝》、《烽火一度》、《查理與我:史坦貝克攜犬橫越美國》、《美國與美國人》……等書。
攝影者簡介
羅伯‧卡帕Robert Capa
二十世紀最具傳奇色彩的知名戰地攝影師者羅伯‧卡帕,本名安德雷‧厄諾‧弗烈曼〈Endre Erno Friedmann),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生於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從十七歲離家,截至一九五四年在中南半島誤觸地雷喪生,其間周遊世界各地拍攝戰爭場面。他偕同摯愛伴侶姬妲‧塔柔〈Gerda Taro,波蘭籍未婚妻,死於一九三七年),初逢於西班牙內戰,拍下無數凸顯人類苦痛扣人心弦的照片,自此聲名大噪享譽國際。
一九三八年他前往中國,見證日本侵華行為;實地報導二次世界大戰;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時,他就置身現場。一九五四年,轉往中南半島。
一生出版過的攝影文集有:《死亡醞釀》(Death in the Making,卡帕與姬妲‧塔柔攝影,1938)、《滑鐵盧之路戰役》(The Battle of Waterloo Road,黛安娜‧傅畢斯-羅伯森撰文,卡帕攝影,1941) 、《失焦》(Slightly out of Focus,1947)、《史坦貝克俄羅斯紀行》(A Russian Journal,約翰‧史坦貝克撰文/卡帕攝影,1948) 、《報導以色列》(Report on Israel,鄂文‧蕭撰文/卡帕攝影)等。
譯者簡介:
杜默
資深文字工作者。曾任職雜誌主編、執行副總編輯,自立和中國時報資深編譯。譯作有《聖經密碼》、《玄奘絲路行》、《獨自一人》、《印度:受傷的文明》、《金錢書》、《美食與毒菌》等書。
章節試閱
【第1章】
緣起
這則故事和這趟行程的發端和用意,有必要先說個明白。三月底,我——向約翰.君特○1特別情商才能使用這個代名詞——坐在東四十街貝福特旅館酒吧內。改了四遍的戲本已銷毀,從指間流逝,我坐在吧檯凳子上,沉吟著下一步要做什麼。這時,羅伯.卡帕有點落寞的走進酒吧。打了幾個月的牌局終於收場,書也送進印刷廠,他驀地發現自己無所事事。向來善體人意的酒保威利,建議來一杯天下無雙的「瑞士」酒。我們悶悶不樂,倒不是新聞因素使然,而是處理新聞的方式所致。因為,新聞已不再是新聞,起碼在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已是如此。新聞已經變成碩儒俊彥的事。高踞華府或紐約案頭的人看看電報,配合自己的心態重做編排,再簽上文末署名。我們常看的新聞已經不是新聞,而是寥寥可數的學究對新聞意義的看法。
威利把兩杯淺綠色的瑞士酒放在我們面前,我們開始談論到,在這樣的世道裡,誠直開明的人還能有什麼作為。報紙上,有關俄國的消息每天不下數千言。史達林的想法、俄國參謀總部的計畫、軍隊素質、原子武器和導向飛彈實驗等,全都是由不在當地的人所寫,他們的資料來源絕不是無可非議。我們於是想到,有些跟俄國相關的事還沒人寫,而這些事正是我們最感興趣的。那裡的人穿什麼?餐會中上的是什麼菜?有什麼食物?他們怎麼做愛,怎麼處理死亡?他們談什麼?他們也跳舞、唱歌和演戲嗎?小孩子是否要上學?我們覺得,去探探這些事、拍拍他們、寫寫他們,不失為好事一樁。俄國政治誠然跟我們的政治一樣重要,但那裡想必也一樣還有重要的另一面,想必也有我們無法看到的俄國民眾的私生活,因為從來沒人寫過,也沒人拍過。
威利又調了杯瑞士酒,他附和我們的看法,說他對這種事也有興趣,想看的正是這種東西。於是,我們決定一試——純粹報導,輔以照片。我們要合作。我們要避開政治和較重大的問題。我們要避開克里姆林宮、軍人和軍事計畫,盡量接近俄國民眾。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並不知道是否可行,反而是一跟朋友提起,他們倒是很篤定我們辦不到。
我們的盤算是這樣子:若是能辦到,很好,可以有篇很好的報導;若是辦不到,我們也會有篇報導,談談怎麼力有不逮。打定主意之後,我們打電話到《前鋒論壇報》邀喬治.柯尼希〈George Cornish〉聚餐,告訴他我們的計畫。他同意這是件好事,答應盡力協助我們。
我們共同敲定幾件事:我們不應該是去挑釁,應該盡量避免批判或示好。我們要盡量據實報導,寫下所見所聞,不加論述評斷,不對自己不充分了解的事妄下結論,也不為行政官僚延誤生氣。我們知道,我們一定會碰到很多不了解、不喜歡和不自在的事。這雖是外國實情,但我們決意即使要批評,也應該是事後,不是未曾眼見就批評。
簽證申請在適當時間送往莫斯科之後,我的簽證在合理時間內就獲得批准。我前往紐約蘇聯領事館,總領事說道,「我們同意這是件好事,但你為什麼非得帶攝影師同行不可?我們蘇聯有很多攝影師。」
我答道,「但你們沒有卡帕。既然要做,就得合作,把事情做得圓滿。」
蘇聯有點不情願讓攝影師入境,對我倒是沒有不情願,在我們看來,這倒是很奇怪,因為檢查管得了軟片,卻管不了觀察者的心。我們在蘇聯之行全程中發現一件真實不虛的事,有必要在這裡稍加說明。相機是最可怕的現代武器之一,對那些曾經歷戰火、挨過轟炸和砲彈的人而言尤其如此,因為在一陣轟炸之後必然是攝影;殘破的城鎮和工廠背後,通常是利用相機做空中製圖或偵測製圖。因此,相機是令人畏懼的器材,攜帶相機的人到哪裡都受到懷疑和監視。你要是不信,不妨帶著「布朗尼四號」〈Brownie No. 4〉柯達相機到橡樹嶺○2、巴拿馬運河或全國上百個實驗區附近便知分曉。今天,在很多人心目中,相機不啻是毀滅的前兆,引人疑竇可謂其來有自。
我不認為我跟卡帕真的以為可以如願去做這件事,是以我們也跟別人一樣大感意外。簽證下來時我們吃了一驚,於是跟威利在酒吧後頭稍微慶祝一下。這當兒,我發生意外摔斷了腿,躺了二個月,卡帕倒是四處蒐羅器材。
多年來一直沒有美國人攝影報導蘇聯,所以,卡帕不但張羅最好的攝影器材,還各自準備一份備用以防失落。當然,他除了攝帶戰時所使用的 Contax 和 Rolleiflex 相機之外,也額外多帶相機。他帶的額外相機、底片和閃光燈實在太多了,國外航班超重費用就付了三百美元左右。
我們要前往蘇聯的消息一傳開,各式的忠告、告誡和警告紛至沓來,值得一提的是,泰半來自不曾到過那兒的人。
有位老婦人以驚恐的口吻告訴我們,「哎呀,你們準會失蹤,你們一過邊界就會失蹤!」
我們以精確報導的興味答道,「妳知道有人失蹤?」
「不,」她說,「我個人雖不知道,但確實有很多人失蹤。」
我們說道,「這話也許不假,我們也拿不準,妳是否可以給我們一個失蹤者的名字?妳可知道有誰知道有人失蹤?」
她答道,「有好幾千人失蹤了。」
有位男士別有深意的聳聳眉,滿臉狐疑地對我們說,「你們想必跟克里姆林宮很有交情,否則他們不會准你們入境。一定是他們買收了你們。」此人其實就是二年前在「史托克俱樂部」○3發表侵攻諾曼地總戰鬥計畫那位仁兄。
我們說道,「不,據我們所知,他們沒有收買我們。我們只是想做點報導的工作而已。」
他抬眼瞅著我們。他一認定便自以為是,二年前知道艾森豪心思,現在也了徹史達林的想法。
有位老紳士朝著我們一頷首,說道,「他們會拷問你們,這是他們的做法;他們會索性把你們關進黑牢再行拷問。他們會扭轉你們的胳臂,讓你們餓肚子,直到你們乖乖依從,說他們要你說的話。」
我們問道,「為什麼?所為何來?有什麼目的?」
「他們對誰都是這樣,」他說,「我前幾天剛看過一本書說⋯⋯」
有位相當有分量的商人對我們說,「去莫斯科,嗯?帶幾顆炸彈去炸炸紅小子。」
各式忠告逼得我們透不過氣來。有人告訴我們該帶食物去,否則準會餓死;什麼通信線路該保持暢通;偷運資料出境的方法。世上最難說得清的是,我們只是想報導一下俄國人的模樣、穿著打扮和言行舉止,農人聊些什麼與如何重建殘破國家。這最難解釋。 我們發現,好幾千人都患了莫斯科病,也就聽信荒誕意見和排除事實的狀態。當然,我們也發現俄國人同樣也患了華盛頓病的毛病。我們發現,我們醜化俄國人之際,俄國人也在醜化我們。
有位計程車司機說道,「他們俄國人呀,洗澡時男女共浴,不穿衣服。」
「真的?」
「當然是真的,」他說,「這是不道德的。」
追問結果原來是他看過一篇芬蘭蒸氣浴的記事,卻把氣出在俄國人頭上。
聽了這些情報之後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約翰.曼德威爾爵士〈Sir John Mandeville〉遊記中的世界絕未消失,雙頭人和飛蛇的世界依舊○4。的確,我們出國期間所出現的飛碟,並沒有推翻我們的命題。在我們看來,當今世上最危險的趨勢便是,寧願相信流言,不追究事實。
我們前往蘇聯時所攜帶的最佳裝備是,匯聚在一個地方的所有流言,而我們在本文中所堅持的是:一旦我們記下流言,就可稱為十足的流言。
我們在貝福特酒吧跟威利喝了最後一杯瑞士酒。威利已成為我們這個計畫的專任合夥人,瑞士酒也越調越出色。他給我們的建言中,不乏最好的忠告。威利很想跟我們同行。他若能成行倒不失為美事一樁。他給我們調了杯上好的瑞士酒,自己也呷了一杯之後,我們終於準備動身。
威利說道,「你們在吧檯後學到了多聽少說。」
往後幾個月,我們常想起威利和他的瑞士酒。
事情就這麼開頭。卡帕帶回大約四千張負片,我也帶回幾百頁札記。我們一直在沉吟如何把此行做個了結,幾經討論後決定依照日程、經歷和見聞不加區別地如實寫下來。我們要寫下所見所聞。我知道這種做法跟大部分的現代新聞報導背道而馳,但唯其如此本文也不失為一種調劑。
這只是我們的經歷。它不是俄羅斯故事,而是一則單純的俄羅斯報導。
【第2章】
抵達蘇聯
我們從斯德哥爾摩打電報給《前鋒論壇報》莫斯科支局長約瑟夫.紐曼〈Joseph Newman〉,告知預計抵達時間後便安心地認為他會派車接我們,並代我們安排旅館。我們的路線是從斯德哥爾摩到赫爾辛基,再到史達林格勒轉飛莫斯科。由於沒有外國飛機飛莫斯科,我們不得不在赫爾辛基改塔俄國班機。光鮮、亮麗、無瑕的瑞士班機載著我們飛過波羅的海,由芬蘭灣上空進入赫爾辛基。標緻的瑞士空姐送來精緻的瑞士小點心。
一段平順舒適的航程之後,飛機降落赫爾辛基新機場,但見新近完成的大樓甚是宏偉。 我們在機場餐廳裡等候俄國飛機。約莫二個小時之後,一架老舊的C—47慢慢地飛進來。機身上褐色戰鬥漆還在,觸地時尾輪爆開,好像蚱蜢般在跑道彈跳。這是我們此行所見唯一一宗意外,但事已至此再強提信心已於事無補。她刮痕斑駁的油漆和邋邋遢遢的整體外觀,無法跟光鮮的芬蘭和瑞士航空班機相提並論。
飛機跌跌撞撞地開上停機線,熱鍋似的飛機上下來一批剛從俄羅斯拍賣會回來的美國皮貨採購商。這一票人神色萎靡,沉默寡言,自稱這架飛機從莫斯科這一路上,飛行不超過地面一百公尺。有位俄羅斯機員下得飛機來,踹了爆胎的尾輪一腳,悠悠然地朝航站走去。不多時,有人告訴我們下午不飛,我們只得在赫爾辛基過夜。
卡帕整理一下十大箱行李,好像母雞帶小雞似的把它們送進行李間,再三提醒機場官員必須派守衛看守。他只要一離開行李,一刻都不能放心。卡帕平常為人樂天爽快,但一扯上相機就會變得很專橫和愛操心。
在我們看來,赫爾辛基雖然沒有受到嚴重轟炸但久經戰亂,是個陰鬱和沒有歡樂的城市。旅館淒淒清清,餐廳鴉雀無聲,廣場上樂隊演奏的不是歡樂的音樂。街頭上,土兵都好像是小男生,太年輕了,而且面容蒼白,帶有鄉土氣息。我們的印象是,這是個沒有生氣,缺少歡愉的地方,彷彿是赫爾辛基經歷二次大戰和多年抗爭與奮鬥之餘,著實已無法東山再起。我們不知道它是否真的無法重建經濟,但這的確是它給人的印象。
我們進城找艾伍德〈Atwood〉和奚爾〈Hill〉,也就是專門研究所謂鐵幕後國家社會與經濟的《前鋒論壇報》小組。他們一起住在旅館,房間裡到處是報告、小冊子、調查和照片,此外,他們還留了絕無僅有的一瓶蘇格蘭威士忌,以備有預期外的慶祝時之用。這就是我們了。一瓶威士忌其實也撐不了多久。卡帕玩了會兒寒傖又無利可圖的金羅美〈gin rummy〉牌戲,不多時我們便上床就寢。
飛向莫斯科
往後二個月,我們經常搭乘的俄國運輸機,彼此間有許多雷同之處,所以,這架飛機堪稱是箇中代表。漆著褐色選鬥漆的C—47都是租借的存品。機場上有些比較新的運輸機,配備一個三輪著陸裝置,但我們沒搭過。C—47的裝潢和舖毯有點破舊,但引擎保養不錯,駕駛似乎也不賴。它們的機員比我們搭的飛機多,但我們沒進過控制室,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室門一開,只見裡面好像一直維持著六、七個人的規模,其中一位是空姐。我們也不知道空姐在幹什麼。她彷彿跟乘客無關似的。機上沒有為乘客準備食物,乘客自行攜帶大量食物彌補缺失。
我們搭乘的飛機,通氣口總是故障,一直沒有新鮮空氣進來,要是碰到機內瀰漫食物和偶爾嘔吐的氣味便無法可施。聽說這些美製的老飛機要一直用到由較新式的俄製飛機汰換為止。
對習慣於本國航空公司的美國人而言,有些習慣是有點奇怪。譬如,沒有安全帶;飛行中不准抽菸,但一著陸人人都點起香菸;沒有夜間飛行,要是你搭的飛機趕不及在日落前進站,就得枯坐等到次日早上。除了碰到暴風雨,飛行高度都比我們的飛機低。由於俄國大部分地形近乎完全平坦,隨處可以找到迫降機場,所以這種做法相對而言甚是安全。
此外,在我們看來,俄國飛機的承載方式也很特別。乘客坐定之後,行李就堆在走道上。
我覺得,第一天最讓我們擔心的是,這飛機的外觀刮痕累累,看來就像是個長相不佳的老怪物。不過,引擎狀況倒是極佳,飛得也很棒,其實沒什麼好擔心的。而且,我也覺得,亮晶晶的金屬其實也沒有讓我國的飛機飛得更好。我認識一個人,他老婆就說過洗刷過後的車子跑得比較好。也許,很多事情都讓人有這種感覺。飛機好壞的第一原則是,可以待在空中飛,可以飛到目的地。俄國飛機在這方面不比別人遜色。
這架莫斯科班機上乘客不多。一位親切的冰島外交官和他的妻小、一位提著郵袋的法國大使館信差,以及四位沉默不語,一直沒開過口的身分不明男子。我們不曉得他們是何許人物。
卡帕精通各國語言,就是不會俄語,現在可是無用武之地了。他說的每一種語言都帶著另一種腔調,例如說西班牙語帶匈牙利腔、法語帶西班牙腔、德語帶法國腔、英語帶不知名的腔調。他不會說俄語,一個月後記了幾個單字,竟也常常被認為帶有烏茲別克腔。
十一點,飛機起飛,前往列寧格勒。飛機一升空,地面上長年戰爭的痕跡便顯而易見。戰壕、地洞和彈坑逐漸長滿雜草。越是接近列寧格勒,傷痕越深,壕溝也越見頻繁。舉目但見焚毀的農舍猶有焦黑的牆面兀立,有些發生激戰的地區坑洞和傷疤宛然,有如月球表面。一靠近列寧格勒,戰壕、據點和機槍槍垛隱約可見。
飛行途中,我們不免對列寧格勒通關感到憂心忡忡。我們心想,這十三件行李、幾千個閃光燈泡、幾百捲軟片、大量攝影器材和糾結的閃光燈電線,可能得花上好幾天才會放行。此外,我們也認為,我們可能由於這些新器材而受到嚴密審查。
飛機終於飛過列寧格勒上空。郊區殘破,城內似乎沒有受到太大損壞。飛機輕巧地降落機場草坪,滑進停機線。機場只有維修大樓,沒有航站大樓。兩名配備大步槍和亮晃晃刺刀的年輕士兵上前,站在我們飛機附近,接著,海關官員登機。主官是一位笑容可掬、禮數周到、鋼牙閃閃發亮的小個子。他懂一個英文字Yes,我們知道一個俄文da,於是他一說yes,我們就回聲da,如此周而復始。檢查過我們的護照和錢之後,輪到行李問題。行李必須在走道上打開,不得帶出機外。關員很有禮貌、很親切,但也查得極為徹底。我們打開所有皮箱,他則檢查所有東西。不過,在他檢查之間,我們恍悟他只是興味津津,並不是刻意要查什麼。他翻轉我們光鮮的器材,愛不忍釋地摩挲,每一捲軟片都拿起來瞧瞧,但既沒有動作也沒問話,好像只是對外國東西特別感興趣而已。此外,他的檢查時間似是毫無限制。最後,他跟我們道聲謝,至少,我們認為他是在道謝。
接著,在我們的證件上蓋章又出現新問題。他從上衣口袋掏出一個用報紙裹著的小包包,再取一枚橡皮章。他只帶章,沒帶印泥。不過,從他精心設計的手法來看,顯然他根本就沒有印泥。他從另一個口袋拿出一枝鉛筆,舔了舔橡皮章之後,用鉛筆在橡皮章上摩擦,在我們的證件上試了一下。毫無動靜。他又試一遍,還是毫無動靜。橡皮章連個印痕的跡象也沒留下。為了幫他個忙,我們拿出漏水的自來水筆,手指沾著墨水抹在橡皮章上。他終於蓋出個漂亮的印記。他把橡皮章用報紙包好收回口袋裡,熱烈地跟我們握握手後下機。我們再收拾好行李,堆在座椅上。
一輛卡車倒車到機門前,車上堆滿箱子,裝的是一百五十具新的顯微鏡。有位女工頭登機——此女身形瘦削,肌肉結實,一張波羅的海人士的寬臉,堪稱是我這輩子所見力氣最大的女子。她扛著沉重的包裹直趨駕駛艙,艙內堆滿後再把顯微鏡堆在走道上。她身穿帆布鞋和藍色連身工作服,綁著頭巾,雙臂肌肉隆起,而且跟那位關員一樣,一口熠熠生光的不鏽鋼牙,使得人類的嘴巴看來像極了機械器物。
我覺得,我們原本預期會有不快遭遇;反正,所有海關都是莫名其妙地侵害隱私,都會令人不快。也許是我們多少聽信那些沒到過這裡的「顧問」所言使然,以為多少總會碰到侮辱或苛待。結果啥事也沒發生。
裝滿行李的飛機終於再度升空,飛過一望無際的平地、森林和開墾的農地、樸實的小村莊和鮮黃色的草堆,直往莫斯科而去。飛機一直飛得很低,到雲層下降才不得不升到雲層上,不多時傾盆大雨便打在機窗上。
高頭大馬、金髮豐胸、長得像老媽子似的空姐,唯一的工作好像就是把幾瓶粉紅色的蘇打水遞過堆得高高的顯微鏡傳給駕駛艙裡的男人。她還送過一回黑麵包給他們。
我們沒吃早餐,已開始覺得饑腸轆轆,而這會兒似乎仍沒有再進食的可能。要是我們會說俄語,我們早就開口求她賞片麵包了。可惜我們連這一點也做不到。
沒人來接機
四點鐘左右,飛機降到雨雲下方,我們看到左方就是不規則向外擴張、龐大的莫斯科市,莫斯科河貫穿其間。機場本身很大,有些地面已鋪設,有些還是長長的草地跑道,四周停放著幾百架飛機,有些是老舊的C—47,也有很多是配備三輪著陸裝置和光面鋁漆的俄製新飛機。
飛機開向堂皇的新航站大樓時,我們不禁望出窗外,看看是否有熟識的面孔,是否有人在等我們。機外下著雨。我們下了飛機,在雨中整理行李,孤寂感陡然襲來。沒有人來接我們。看不到熟悉的面孔,我們連問路也不會,身上又沒有俄幣,根本不曉得該往哪裡走。
我們已在赫爾辛基打電報給紐曼,說我們會晚一天抵達。紐曼沒來,也沒人來接我們。幾位粗壯的搬運員把我的行李扛到機場前,期待似地等著我們付錢,我們卻沒錢可付。巴士一輛輛過去,我們赫然警覺到,我們連車行目的地也看不懂,何況班班車都擠滿了人,有些人甚至掛在車外,根本不可能把十三件行李弄上車。那幾位搬運員,挺粗壯的搬運員,還在等我們給錢。我們渾身濕答答,又驚又怒,覺得自己完全被人拋棄了。
就在這時候,法國大使館信差拎著郵袋走了出來,不但借我們錢付搬運員,還讓我們的行李搬上前來接他的車子。他是大好人,在我們差點就要自殺的時候救了我們的性命。若是他能看到本書的話,我們要再次謝謝他。他送我們到紐曼原本投宿的「都會大飯店」〈Hotel Metropole〉。
我搞不懂為什麼機場總是跟它們要服務的城市隔得老遠,但事實就是這樣,莫斯科也不例外。機場離市區好遠好遠,道路穿過松林、農莊和沒完沒了的馬鈴薯與包心菜園,時而崎嶇,時而平順。法國信差胸有成竹,早就打發司機去買點午餐,所以到莫斯科這一路上我們才有餡餅、小肉丸和火腿吃。車抵都會大飯店時,我們已覺得好多了。
都會大飯店有大理石扶梯和紅地毯,還有部偶爾能動的華麗電梯,算是相當豪華。櫃檯後有位女士懂英語。我們向她查問房間,她卻說沒聽過我們的名字。我們沒房間住。
這時幸虧有《芝加哥太陽報》〈Chicago Sun〉的亞歷山大.坎德瑞克〈Alexander Kendrick〉搭救。我們問他,紐曼到哪兒去了?
「哦,小約呀!他到列寧格勒皮草拍賣會,已經走了一個禮拜。」
他沒收到我們的電報,啥也沒準備,我們沒房間。沒有預約就想要房間,太荒唐了。我們原以為紐曼會聯絡俄羅斯的主管機關,但他既然沒聯繫,也沒收到電報,俄國人自然不知道我們要來。幸好坎德瑞克帶我們到他房間,請我們吃燻鮭魚和伏特加酒聊表歡迎。
過了一會兒,我們不再感到孤單迷失之後,決定住進紐曼的房間,讓他嘗嘗苦頭。我們用他的毛巾、肥皂和衛生紙,喝他的威士忌,睡他的沙發和床。我們覺得,為了補償我們所受的折騰,這是他起碼該做的。我們認為,他不能推說不知道我們要來,理當加以處罰。於是,我們喝了他兩瓶蘇格蘭威士忌。我們必須承認,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這是何等的罪過。派駐莫斯科的美國新聞人員固然有人相當不老實和矇混,但論程度都還比不上我們——沒有人偷喝別人的威士忌。
【第1章】
緣起
這則故事和這趟行程的發端和用意,有必要先說個明白。三月底,我——向約翰.君特○1特別情商才能使用這個代名詞——坐在東四十街貝福特旅館酒吧內。改了四遍的戲本已銷毀,從指間流逝,我坐在吧檯凳子上,沉吟著下一步要做什麼。這時,羅伯.卡帕有點落寞的走進酒吧。打了幾個月的牌局終於收場,書也送進印刷廠,他驀地發現自己無所事事。向來善體人意的酒保威利,建議來一杯天下無雙的「瑞士」酒。我們悶悶不樂,倒不是新聞因素使然,而是處理新聞的方式所致。因為,新聞已不再是新聞,起碼在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已是...
目錄
前言 蘇珊.席林格羅
第一章 緣起
第二章 抵達蘇聯
第三章 莫斯科生活
第四章 基輔
第五章 烏克蘭見聞
第六章 史達林格勒
抗辯書/ 羅伯.卡帕
第七章 喬治亞
第八章 弟弗利司
第九章 旅行結束之前
附錄一 史坦貝克年表
附錄二 史坦貝克重要著作年表
前言 蘇珊.席林格羅
第一章 緣起
第二章 抵達蘇聯
第三章 莫斯科生活
第四章 基輔
第五章 烏克蘭見聞
第六章 史達林格勒
抗辯書/ 羅伯.卡帕
第七章 喬治亞
第八章 弟弗利司
第九章 旅行結束之前
附錄一 史坦貝克年表
附錄二 史坦貝克重要著作年表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9收藏
19收藏

 31二手徵求有驚喜
31二手徵求有驚喜




 19收藏
19收藏

 31二手徵求有驚喜
31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