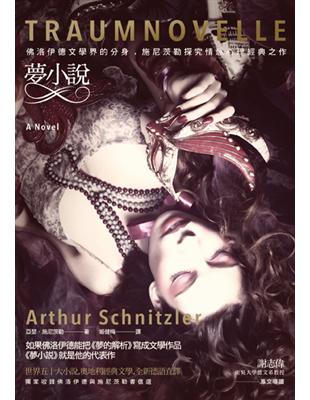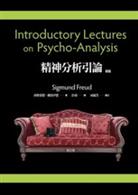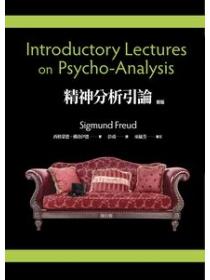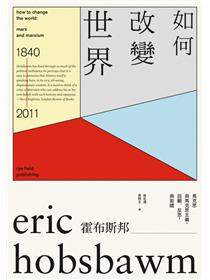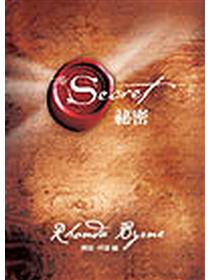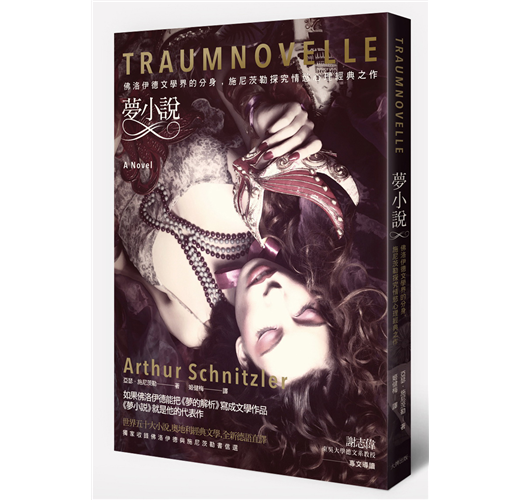如果佛洛伊德能把《夢的解析》寫成文學作品
《夢小說》就是他的代表作
★世界五十大小說,奧地利經典文學,全新德語直譯
★佛洛伊德文學界分身──心理分析作家施尼茨勒代表作
★獨家收錄佛洛伊德與施尼茨勒書信選
★導演史丹利.庫柏力克最後一部電影《大開眼戒》原著小說
施尼茨勒瓦解了文化傳統的可靠性,思想緊緊依附著愛與死的對立,
這一切都以一種駭人的熟悉感動了我。──佛洛伊德
對施尼茨勒甚為推崇的佛洛伊德,在一封寫給施尼茨勒的信裡聲稱,他視施氏為其分身,原因之一是,他注意到,「性愛與死亡本能」在施氏作品裡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佛洛伊德在這封信裡,幾乎是帶著醋味地指出,施尼茨勒顯然是僅靠著本能──敏銳的觀察力──就能洞悉他辛勤研究才能得到的結論。
夢是什麼?夢是人被壓抑的願望的變形實現
生活的秩序若是如此明確、不可動搖,它便會向你挑戰
展現你對於自由、冒險、危險事物的真正想法
那會發生在如夢的現實?或者只在夢裡?
「我成為你妻子的時候還是處女,原因並不在於我……」
「一把劍在我們之間……我們像死敵一樣躺在彼此身邊。」
無法任意滿足情慾渴望的夫妻,婚姻陷入危機。直到他們各自從無害的冒險與夢境中實現自己的慾望,才能再次靠近彼此。施尼茨勒用卓越的筆法將佛洛伊德的深層心理學帶進文學裡,描寫潛意識中的壓抑如何伺機而動,變形成一場春夢、一個出軌念頭,它放大誘惑,逼我們正視幽微心靈中不為人知的部分。
作者簡介:
亞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 (1862-1931)
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奧地利作家之一,以短篇作品及戲劇見長,多抨擊奧匈帝國社會的腐敗與虛偽,描寫人心的幽閉與神祕,為維也納現代派重要推動者。出生於猶太醫生世家,於維也納大學醫學系畢業後成為醫生。當時心理分析研究正掀起一股浪潮,他的醫學背景與寫作功力,成就了他在作品中對人物心理狀態描寫的能力,也成為他作品的一大特色。
施尼茨勒是二十世紀初作品最常被搬上舞台的作家,作品受到藝文界高度推崇,卻因多探討性與死亡,飽受社會輿論撻伐。 1901年中篇小說《古斯特爾少尉》(Leutnant Gustl),因為抨擊奧地利軍隊,施尼茨勒失去預備役主治醫師的頭銜; 1921年,他的劇作《輪舞》(das Reigen)首演,為歐洲第一部將性愛場景搬上舞台的劇作,因而引起眾怒,施尼茨勒被起訴,法院禁演他的戲劇作品。
愛情、婚姻、變態心理、夢境、意識流、死亡、性這些都是施尼茨勒擅長的主題,他宛如世紀末的繪圖師,描繪維也納市民階級的靈魂,剖析頹廢氣氛下人們的壓抑與命運。《夢小說》便是他對於性、死亡與夢主題思考的總結。
譯者簡介:
姬健梅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德國科隆大學德語文學碩士,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中英文組。從事翻譯多年,文學類譯作包括:《變形記》、《審判》、《城堡》、《美麗的賽登曼太太》、《一個戀愛中的男人》、《魂斷威尼斯》、《七年》、《基列系列 II:家園》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這部小說散發著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市民社會之道德規範的不耐,對婚姻關係的穩定性之挑釁,其實充滿著「憂鬱與無力」的本質,更是文學對「人」之彷如迷宮般的心理狀態做GPS定位的企圖。
──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 謝志偉
《夢小說》是一場現實與想像的精巧遊戲。
──德國《明鏡週刊》
施尼茨勒帶著一種非感傷的諷刺,成為描寫夢境與複雜心理的大師。
──《紐約客》
施尼茨勒筆下的角色躲在日常例行公事裡,這些瑣事如同裝飾,掩蓋了沒解決、不確定的問題,為這對靈魂上是雙胞胎的夫妻肖像增添色彩。
──《出版人雜誌》
施尼茨勒的作品檢驗了婚姻忠誠的本質,以及伴隨而來的誘惑、謊言、嫉妒。
──《紐約時報》
輔大德文系張善禮教授 好評推薦
名人推薦:這部小說散發著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市民社會之道德規範的不耐,對婚姻關係的穩定性之挑釁,其實充滿著「憂鬱與無力」的本質,更是文學對「人」之彷如迷宮般的心理狀態做GPS定位的企圖。
──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 謝志偉
《夢小說》是一場現實與想像的精巧遊戲。
──德國《明鏡週刊》
施尼茨勒帶著一種非感傷的諷刺,成為描寫夢境與複雜心理的大師。
──《紐約客》
施尼茨勒筆下的角色躲在日常例行公事裡,這些瑣事如同裝飾,掩蓋了沒解決、不確定的問題,為這對靈魂上是雙胞胎的夫妻肖像增添色彩。
──《出版...
章節試閱
當他走上通往寓所的樓梯,時間是凌晨四點。他先到他的看診室去,把那套化裝服仔細地鎖進櫥櫃裡,由於他不想吵醒阿貝婷娜,他走進臥室之前,先脫掉鞋子和衣服。他小心翼翼地打開床頭燈昏暗的燈光。阿貝婷娜平靜地躺著,手臂繞過後頸,嘴唇半張,痛苦的陰影在唇邊抽動;這是弗里多林不識得的面容。他俯身在她額頭上,她的額頭立刻皺了起來,像是被觸碰了一般,表情異樣扭曲;突然,仍舊在睡眠中,她尖聲笑了,把弗里多林嚇了一跳。他不由得喊出她的名字。她又笑了,像是在回答,以一種全然陌生、幾近陰森可怕的方式。弗里多林又更大聲地喊了她一次。這時她睜開眼睛,緩慢而吃力,眼睛瞪得大大的,愣愣地凝視著他,彷彿沒有認出他來。
「阿貝婷娜!」他喊了第三次。這時她才似乎醒過來。一種抗拒、畏懼、甚至是驚駭的表情在她臉上浮現。她把雙臂向上伸出,沒有目的,似乎感到絕望,嘴巴仍舊張著。
「妳怎麼了?」弗里多林屏住呼吸問道。由於她仍舊帶著驚駭凝視著他,他像要使她安心似地又加了一句:「阿貝婷娜,是我。」她深深吸了一口氣,試著微笑,讓雙臂落在被子上,宛如從遙遙的遠方問道:「已經是早上了嗎?」
「快了,」弗里多林回答。「四點剛過。我剛剛才回到家。」她沉默不語。他繼續說:「宮廷顧問死了。我到的時候他已經臨終,我當然不能──馬上把他的家屬單獨扔下。」
她點點頭,卻彷彿幾乎沒有聽見他所說的話,或是無法理解,眼神似是從他身上穿過,凝視著空無;而他覺得她似乎看透他這一夜的經歷,雖然在同一瞬間這個念頭令他感到荒謬。他朝她俯身,撫摸她的額頭。她微微戰慄。
「妳怎麼了?」他又問了一次。
她只是緩緩搖頭。他撫摸她的頭髮。「阿貝婷娜,妳怎麼了?」
「我做了夢。」她悠悠地說。
「妳夢到什麼?」他溫和地問。
「喔,很多,我記不清了。」
「說不定妳還記得。」
「那很混亂—──且我累了。你一定也累了吧?」
「一點也不,阿貝婷娜,我不想再睡了。妳知道的,當我這麼晚才回家,最明智的做法其實是立刻坐在書桌前──尤其是在這種清晨時分──」他中斷了自己的話。「不過,妳還是把妳的夢告訴我比較好吧?」他有點勉強地擠出微笑。
她回答:「你還是應該稍微躺一下。」
他猶豫了一會兒,然後照著她的希望做了,在她身旁伸展四肢躺下,但是留神不去碰到她。一把劍在我們之間,他憶起一句相同性質、半開玩笑的話語,有一次在類似的場合由他口中說出。他們兩個都沉默不語,睜著眼睛躺著,感覺到對方的接近、對方的遙遠。過了一會兒,他用手臂撐著頭,久久打量著她,彷彿他除了她臉部的輪廓,能夠看出更多。
「妳的夢!」他突然又說了一次,而她似乎只是在等待這個要求。她朝他伸出一隻手;他握住她的手,按照習慣,緊緊抓住她修長的手指,與其說是溫柔,不如說是心不在焉。而她開口:
「你還記得沃爾特湖那棟小別墅的房間嗎?在我們訂婚的那個夏天,我和父母親住在那兒。」
他點點頭。
「那個夢就是從我走進那個房間開始,我不知道我從哪裡來──就像個演員走上舞台。我只知道父母親出門旅行,把我獨自留下。這令我訝異,因為明天就該是我們的婚禮。可是新娘禮服還沒送來。還是說也許是我弄錯了?我打開衣櫥查看,那裡沒有掛著新娘禮服,卻掛著許多別種衣服,其實是戲服,像在歌劇中穿的,十分華麗,東方風格。婚禮上我該穿哪一件才好呢?我心想。這時衣櫥突然關上,或是消失,我記不得了。房間十分明亮,可是窗前是漆黑的夜……驀地,你站在窗前,櫓艦的奴隸划著槳把你帶來,我看見他們剛剛消失在黑暗中。(中略)
「一個奇怪的夢,」他說。「它已經結束了嗎?」由於她否認,他便說:「那就繼續說下去吧。」
「這並不容易,」她又開口。「這些事其實幾乎無法用言語來表達。嗯,我覺得自己彷彿經歷了無數個晝夜,時間與空間都不再存在,我也不再置身於被樹林和岩石圍繞的那片林間空地,而是在一片無盡延伸、花團錦簇的寬闊廣場上,那地方朝著四面八方沒入地平線。我也早已經──說『早已經』真是奇怪!──不再是獨自和這個男子在草地上。彷彿除了我以外,還有三對、十對、千對男女在那兒,我是否看見了他們,是否只屬於那一個男子,還是也屬於其他人,我說不上來。
「可是,一如先前那種驚駭羞慚的感受遠遠超出在清醒時所能想像的一切,在我們有意識的生活中肯定沒有什麼及得上我在這場夢中所感受到的輕鬆、自由和幸福。而我沒有一刻停止知道你的情況。是的,我看見你,看見你如何被捉住,我想是被士兵捉住,那當中也有神職人員;某個非常高大的人綁住了你的雙手,而我知道,你將會被處死。我知道,但不帶同情,沒有戰慄,完全是從遙遙的遠處觀望。他們把你帶進一個院子,像是城堡內院。你就站在那兒,赤身裸體,雙手被綁在背後。一如我看見你,雖然我在別處,你也看見了我,也看見摟著我的那個男子,還有其他那些雙雙對對的男女,這股無盡的赤裸人流,冒著白沫在我周圍湧動,我和擁住我的那個男子彷彿就只是其中的一道波浪。
「當你站在城堡內院一扇高高的拱窗邊,在紅色窗簾之間,出現了一名年輕女子,她頭戴冠冕,身穿紫色披風,是這個國家的女王。她向下看著你,帶著嚴厲詢問的目光。你獨自站著,其他許多人都待在旁邊,倚著圍牆,我聽見一陣低聲嘟噥和竊竊私語,陰森而預示著危險。這時,女王俯身在欄杆上。四下一片寂靜,女王給了你一個信號,像是在命令你上樓到她那兒去,而我知道,她決定要赦免你。可是你沒有注意到她的目光,或是不想去注意。突然之間,你站在她面前,雙手仍舊被綁著,可是身上裹著一件黑色斗蓬,並非在一個房間裡,而不知怎地是在戶外,彷彿飄浮著。
「她拿著一張羊皮紙,是你的死刑判決,上面也記載著你的罪過和判決的理由。她問你──我沒有聽見她說的話,但我知道──是否願意成為她的情人,在這種情況下,你就能免除死刑。你搖頭表示拒絕。我並不訝異,因為那完全合理,非如此不可,你必須永遠對我保持忠誠,不管碰上任何危險。這時女王聳聳肩膀,向空中把手一揮,你便頓時置身於一個地窖裡,鞭子嗖嗖地朝你揮下,我卻沒有看見揮動鞭子的人。血從你身上流下,像汩汩的溪水,我看見那血在流,意識到我的殘忍,卻對我的殘忍並不感到訝異。
「這時女王走向你。她的頭髮鬆開了,流瀉下來裹住她赤裸的身體,她捧著那頂王冠遞給你──而我知道她就是丹麥海灘上的那個女孩,有一天早晨你在一間浴場小屋的露台上見過赤裸的她。她一句話也沒說,可是她之所以在此出現,之所以沉默,是要問你是否願意成為她的夫婿,成為這個國家的國王。由於你再度拒絕,她突然消失了,我卻同時看見,有人替你豎起了一座十字架──不是在山下的城堡內院,是在遍地花朵的無盡草地上,在其他所有的情侶當中,我在情人的懷裡歇息。
「而我看見你,看見你獨自穿過古代風格的街巷,完全無人看守,但我知道,你走的路已經事先劃定,不可能逃走。你走在上坡的林間小徑。我緊張地等候你,卻不帶任何同情。你身上布滿鞭痕,但已不再流血。你爬得愈來愈高,小徑變寬了,樹林朝兩邊後退,這時你站在草地邊緣,在十分遙遠的地方,遠得不可思議。但你用雙眼微笑地向我打招呼,像是向我表明,你實現了我的願望,替我帶來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衣裳、鞋子和首飾。我卻覺得你的行為愚蠢至極而且沒有意義,我想要嘲笑你,當著你的面大笑──而且原因正在於你出於對我的忠誠而拒絕了女王的求婚,忍受拷打,此刻步履蹣跚地爬上這裡,將面臨可怕的死亡。
「我朝你跑過去,你也加快了步伐──我開始飄浮,而你也飄浮在空中;可是突然之間我們在彼此面前消失,而我知道:我們從彼此身旁飛過去了。這時候我希望當別人把你釘上十字架的時候,你至少能聽見我的笑聲。於是我大笑一聲,盡我所能地笑得又尖銳、又大聲。就是這陣笑聲,弗里多林,我就是在這陣笑聲中醒來。」
她沉默下來,仍然一動也不動。他也沒有動彈,同樣一言不發。任何話語在這一刻都會顯得無力,像個謊言,而且怯懦。在她的敘述中她愈說到後面,他自己的經歷,以它們到目前為止的發展,就顯得愈發可笑而且微不足道,而他立誓要把它們全都經歷到終了,再如實告訴她,以這種方式來向這個女人報復,她在夢中揭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不忠、殘忍而且背叛了他,在這一刻,他認為他恨她的程度勝過他曾經愛她的程度。(中略)
然而,不管在這一刻他的情況如何,也不管他在接下來幾個鐘頭裡會做出什麼樣的決定,此刻他迫切需要的是至少躲入睡眠和遺忘中一會兒。在他母親去世之後的那一夜,他也睡了,睡得很沉,而且無夢,難道他在今夜不能如此嗎?於是他在阿貝婷娜身旁伸展四肢躺下,她似乎已經朦朧入睡。一把劍在我們之間,他又想到。接著又想:我們像死敵一樣躺在彼此身邊。但那只是一句話罷了。
當他走上通往寓所的樓梯,時間是凌晨四點。他先到他的看診室去,把那套化裝服仔細地鎖進櫥櫃裡,由於他不想吵醒阿貝婷娜,他走進臥室之前,先脫掉鞋子和衣服。他小心翼翼地打開床頭燈昏暗的燈光。阿貝婷娜平靜地躺著,手臂繞過後頸,嘴唇半張,痛苦的陰影在唇邊抽動;這是弗里多林不識得的面容。他俯身在她額頭上,她的額頭立刻皺了起來,像是被觸碰了一般,表情異樣扭曲;突然,仍舊在睡眠中,她尖聲笑了,把弗里多林嚇了一跳。他不由得喊出她的名字。她又笑了,像是在回答,以一種全然陌生、幾近陰森可怕的方式。弗里多林又更大聲地喊了...
推薦序
導讀
「夢」外還有「遊」──《夢小說》裡「性」與「死亡」的迷宮
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 謝志偉
小說一開始是個二十世紀初歐洲傳統市民階級的家庭場景,一個小女孩自己在睡前讀著一篇出自《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譚)的故事:「二十四個棕色皮膚的奴隸划著華麗的櫓艦,將阿吉亞德王子載往哈里發的宮殿……」一旁的父母親告訴她,該睡了。這對年輕夫婦就是本書的男女主角弗里多林(Fridolin)和阿貝婷娜(Albertine)。有意思的是,之後,太太在告訴先生她做的一個夢時,是這麼說的:「驀地,你站在窗前,櫓艦的奴隸划著槳把你帶來……」女兒閱讀的虛構故事(fiction)跨界進入父母現實生活裡的夢境,如此,「現實」、「虛構」與「夢幻」三者交織成一座迷宮,吾人當即意識到作者的精心巧思,書名《夢小說》有其道理。之後,讀者得知,小女孩六歲。六歲?為什麼剛好是「六」歲而不是「五」歲或「七」歲?因為德文的「六」(sechs)和「性」(Sex)是一樣的發音(雖然有些地區例外)!無獨有偶,阿貝婷娜在接著和弗里多林的談話裡也強調,他們兩訂婚的時候,她「十六歲剛過」,然後再補上一句「我成為你妻子的時候還是處女,原因並不在於我」。原來,就在前一夜,夫婦兩去參加了一個相當詭異的化裝舞會,分別都強烈地感受到異性的誘惑而瀕臨「劈腿」的邊緣。劈腿無緣後,他們坐下來喝香檳,還吃了「生蠔」,「彷彿他們才初相識」。在這樣一種另類劈腿的氣氛下,兩人回到家裡,許久不曾有過的激情翻上心頭,當即熱烈相擁,一夜被翻紅浪,就不在話下。仔細看來,作者其實在小說的第一章就已在暗示,「性」在兩人的婚姻關係中面臨了淡化無味而需借重「背叛」的「面具」來刺激。這點作者在安排《一千零一夜》這部阿拉伯世界(源於伊朗/印度?)的小說時就已經預埋伏筆了:《一千零一夜》故事的緣起不正是皇后給國王戴綠帽而引發的!而「阿拉伯」數字「24」加起來也是「6」!
隔天,身為醫生的弗里多林一早就得到病人身邊,而身兼主婦和人母的阿貝婷娜也得起床,於是,「前一夜逐漸褪色,開端與結束均然」,這意味著前晚的作為只是治標而治不了本。現在,忙了一天,小孩終於睡了,兩人拾起化裝舞會的話頭,開始互相探索雙方是否曾經背叛過對方而互述夢境,企圖引起對方嫉妒,好透過出軌疑雲來刺激假性姦情的氣氛──也是一種面具。而其實弗里多林腦袋裡還真的沒忘掉前晚化裝舞會裡的那兩位令他神魂顛倒的神祕女子。亦即,一邊在和太太探索心靈幽暗的角落,一邊,弗里多林的心已經偷偷地翻牆出門了。忽然,女僕來報,某宮廷顧問(Hofrat)心臟病發,要弗里多林立即趕過去。弗里多林趕到時,病人已往生,唯一的女兒瑪莉安娜在床邊守著大體。瑪莉安娜已經訂婚,卻突然抱住弗里多林向他告白,已經暗戀他甚久,此刻,弗里多林腦海裡竟然浮現一本小說裡的情節:「一個年輕男子,幾乎還是個男孩,在母親臨終的床邊被她的女性友人引誘,其實是被她強暴」。「性愛」與「死亡」聯手出現的母題,這正是佛洛伊德視施尼茨勒為其「分身」(Doppelgänger)的原因之一。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四日,對施尼茨勒甚為推崇的佛洛伊德,在一封寫給施氏的信裡聲稱(本書末附有該信之中譯本),他視施氏為其分身, 原因之一是,他注意到,「性愛與死亡本能」在施氏作品裡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佛洛伊德在這封信裡,幾乎是帶著醋味地指出,施氏顯然是僅靠著本能(Intuition)──敏銳的觀察力──就能洞悉他辛勤研究才能得到的結論。三年後,一九二五年,彷彿為了印證佛氏所言「分身」的確不虛,施氏有部小說於柏林的時尚雜誌《仕女》(Die Dame)連載,並於隔年集結成書出版,該書即為《夢小說》,遙遙呼應著佛氏於一九○○年出版的《夢的解析》。
在這部小說裡,「夢」的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吾人若只關注這部分,恐怕施氏就只能屈就佛洛伊德的分身了。佛洛伊德看重施氏的藝術才情不是沒道理的。拿書中角色命名來說,就大有文章。弗里多林的德文是「Fridolin」,這個字源自「Friedrich」,與「宮廷顧問」的德文「Hofrat」,兩頭一接正是「Friedhof」,「墳場」的德文是也!其實,這部小說裡有「夢」也有「遊」,做夢的多是阿貝婷娜,正意味著,她壓抑較多──其名「Albertine」之前三字母「Alb」,依我之見,實乃隱指德文的「Alptraum 」,「惡夢/夢魘」之意也,「Alb」與「Alp」讀音一樣,而「Alp」就是「阿爾卑斯山」,咱們是「鬼壓床」,他們是「山灌頂」也;「出遊」的是弗里多林──正意味著,他壓抑不住。後者從半夜出門應診後,完事還不回家──書中多次強調,他不想回家──就在城裡城外逛迷宮似地遊蕩,尋找刺激到就差沒撿屍的程度。他經歷了許多誘惑,除了蒙面轟趴外,還被街上妓女帶回家,但卻因種種因素而沒交易,之後也撞見疑似在家接客的少女,後者似乎還與男人私交而被父親咒罵,正是應了一句「家妓無忘告乃翁」!而出門應診的那條街就叫「Schreyvogelgasse」,譯者譯為「鳴禽巷」,但是「Schreyvogelgasse」這字卻暗指「巷裡叫春的鳥兒」(「Gasse」這字在奧地利德語其實也可以是「街」),對照著像個無頭蒼蠅到處找一夜情的弗里多林,簡直擺明就是隻「被悶在褲襠裡的叫春鳥」。後來果真也碰到兩隻鳥:鋼琴師拿赫提加(Nachtigall,夜鶯)和病理(解剖)師阿德勒(Adler,老鷹)。至於他在阿德勒那裡對一具女屍做出幾乎忘情、近乎變態的十指緊扣的動作,再度呈現了「性愛」與「死亡」聯手的母題。有意思者,兩次看到「屍體」時,弗里林多都不由想到「腐爛和分解的過程已經展開」,而若照佛洛伊德的說法,「夢」之成因之一就是「慾求之不滿足或被禁」的結果,那此處「從死亡完成的那一剎那起,屍體即進入腐爛分解的過程」,在本小說裡,就有「從婚姻完成的那一剎那起,性愛即進入淡化無味的過程」之解讀的空間。「腐爛」證實「曾經生鮮」,「分解意味「彼時一體」,於是,從「對美好過往的懸念」通往「不顧腐爛分解的戀屍癖」就只差最後一哩路了。
總之,「夢」在本小說中的確扮演重要的角色,有多層解讀空間,篇幅所限,不及多顧,讀者可自行索義,但吾人更應關注到與「夢」一樣,面具、性與死亡,都是「跨界」或「挪移界碑」的概念。也因此,當我們注意到,阿貝婷娜對弗里多林告白「去年夏天」險險背叛丈夫時,其事發地點是「丹麥」海濱,等到後來弗里多林跟醫學院老同學拿赫提加夜赴維也納郊區某豪宅參加神祕轟趴時,拿赫提加告訴他的通關密語是「丹麥」,弗很驚訝並回說:「去年夏天我湊巧去了丹麥海邊」,我們不得不問:既是北歐,為何不是瑞典或挪威?要海邊,這兩國不會少啊。我的解讀是,德文「丹麥」(Dänemark)的構詞第二個部分「Mark」就是「邊界」的意思,而「Dänemark」以奧地利德語讀來,與「DeineMark」(= 你的Mark)十分雷同。是以,就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維也納現代派來看,所謂的Eros(性之愛/生之慾)與Thantatos (死亡),並非文學所獨有,在繪畫裡,尤其是維也納掌象徵派大旗的克林姆(GustavKlimt)之畫作亦是以諸此母題聞名,顯見其時「世紀末」(Finde siècle)氣氛之濃厚。惟本人以為,這種迷宮般的自我存在(生命)與迷離的人際關係(婚姻)身份之「臨界感」,在施尼茨勒的筆下別具心理分析引人之處。
整體來說,這部小說散發著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市民社會之道德規範的不耐(面具脫來戴去),對婚姻關係的穩定性之挑釁,其實充滿著「憂鬱與無力」(轟趴一事無成)的本質,更是文學對「人」之彷如迷宮般的心理狀態(夜遊維也納城裡城外)做GPS 定位的企圖。所須注意者,男女有別也,阿貝婷娜也有她的夢,但是弗里多林有「鳥」她嗎?文末,小說以「隨著隔壁傳來一陣清脆的孩童笑聲,新的一天展開了」結尾,似乎在無情地提醒著大人世界:一旦脫離孩童的清脆,從此就只剩大人的夢碎了。新的一天,舊的訊息──誰說,有夢最美,除了小說?
導讀
「夢」外還有「遊」──《夢小說》裡「性」與「死亡」的迷宮
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 謝志偉
小說一開始是個二十世紀初歐洲傳統市民階級的家庭場景,一個小女孩自己在睡前讀著一篇出自《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譚)的故事:「二十四個棕色皮膚的奴隸划著華麗的櫓艦,將阿吉亞德王子載往哈里發的宮殿……」一旁的父母親告訴她,該睡了。這對年輕夫婦就是本書的男女主角弗里多林(Fridolin)和阿貝婷娜(Albertine)。有意思的是,之後,太太在告訴先生她做的一個夢時,是這麼說的:「驀地,你站在窗前,櫓艦的奴隸划著槳把你帶來……...
目錄
導讀 「夢」外還有「遊」──《夢小說》裡「性」與「死亡」的迷宮
夢小說
談心理分析
心理學文學
附錄 佛洛伊德與施尼茨勒書信選
導讀 「夢」外還有「遊」──《夢小說》裡「性」與「死亡」的迷宮
夢小說
談心理分析
心理學文學
附錄 佛洛伊德與施尼茨勒書信選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