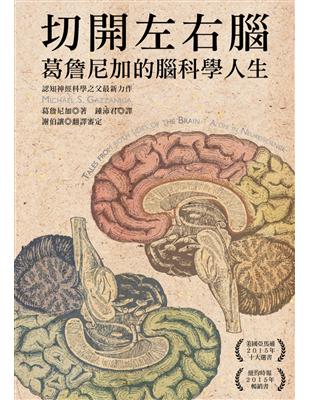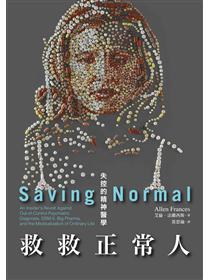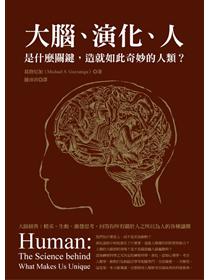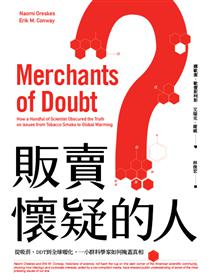《切開左右腦》既幽默又感人,
利用關於人類意識本質的超群發現,
講了一個如何做科學的迷人故事。
以認知神經科學之父葛詹尼加的一生為軸,見證偉大的腦科學的誕生!◎《大腦、演化、人》、《我們真的有自由意志嗎?》暢銷作家葛詹尼加最新力作
◎美國亞馬遜2015年十大選書
◎紐約時報2015年度暢銷書
◎腦神經科學家、暢銷作家《都是大腦搞的鬼》謝伯讓教授翻譯審定
◎書封精緻牛皮卡紙,搭配典雅金屬銀印刷及古典亮黑燙金,盡展葛詹尼加豐厚且精彩的科學人生。(金屬銀印刷為特殊設計,顯現科學家的低調與精緻)
葛詹尼加切開左右腦後,大腦的研究才劃開了一個里程碑
於二十世紀中,葛詹尼加發現將連結左右腦的胼胝體切開後,於一連串的實驗中發現,人類的左右腦可以各自產生不同的心智運動,並且獨自判斷,此一系列的研究即稱為裂腦研究。左右腦各自有心智的發現震驚腦神經科學界,也展開對人類大腦探索的新次元:心智從何產生,腦內如何溝通。葛詹尼加也至此被譽稱為「認知神經科學之父」。
葛詹尼加為恩師斯佩里打下奪得諾貝爾醫學獎的實驗基礎
於《切開左右腦》此書中,葛詹尼加回顧了他在腦神經科學領域中充滿熱情且持續探索的一生,尤其是他在學術界中每一步的累積,用了幾乎半世紀的時光去理解被分開來的兩個半腦如何互相溝通及交互作用。從他還是一個充滿野心,仍住在芝加哥達茅斯學院的「動物之家」瘋狂宿舍開始,之後前往加州理工學院跟隨大腦科學大師斯佩里開始進行左右腦研究,獨自發展出切斷胼胝體方法,並且實際受試於第一個癲癇患者身上,其研究成果奪得諾貝爾獎的契機,也開展了葛詹尼加自主獨立,離開斯佩理的研究之路……
費曼先生、斯佩里、量子化學創始人鮑林……
葛詹尼加的科學人生就是一段偉大的科學史
本書為葛詹尼加親筆撰寫,有別於以往他的科普書籍專門討論一個問題,這本書即以他個人自傳的方式,呈現他開啟裂腦研究這門領域的種種過程,處在頂尖的環境中,身邊無時無刻不環繞著有趣的人事物,暨是在進行科學研究,更多的是在享受這個人生。書中,你可以看到費曼拜訪他的派對,主動大方承諾可以讓葛詹尼加切開他的左右腦,前提是不可以影響到他做物理研究;你可以看到他與知名喜劇演員艾倫一時興起在體育館主辦公開的政治辯論;你還可以看到他與多位當代科學名家(諾貝爾獎座在書中數也數不完)交互激盪的過程……這不僅是他一生的紀錄,也是大腦研究科學史的見證。
作者簡介:
葛詹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
全球著名的腦科學家,被譽為「認知神經科學之父」。
一九八二年,葛詹尼加創建了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並創辦《認知神經科學期刊》,現為該期刊的名譽總編輯。一九九三年,他創建了認知神經科學學會。一九九七年,葛詹尼加當選美國國家藝術與科學院院士,二○○六年入選國家醫學研究院院士。此外,葛詹尼加還是Sigma Xi的成員,APA、APS及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的會士。
葛詹尼加目前擔任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聖吉(SAGE)心智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不僅是知名的臨床及基礎科學研究者,也出版了許多大眾科普書籍,如《大腦、演化、人》、《社交大腦》(The Social Brain)、《心智問題》(Mind Matters)、《自然界的心智》(Nature 's Mind)、《倫理的腦》(The Ethical Brain)、《我們真的有自由意志嗎?》等書,紐約時報評論說:「對腦科學研究來說,葛詹尼加所做的研究堪比史蒂芬.霍金的研究之於宇宙論。」
相關著作
《我們真的有自由意志嗎?——意識、抉擇與背後的大腦科學》
譯者簡介:
鍾沛君
台大外文系、輔大翻譯研究所畢業,專職中英同/逐步口譯、書籍文件筆譯,譯有《大腦、演化、人》、《魚翅與花椒》、《與神共餐》、《我們真的有自由意志嗎?》。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2015美國亞馬遜十大選書
2015紐約時報暢銷書
名人推薦:
學界聯合推薦
◎李宏鎰/《遇見「過動兒」,請轉個彎》作者、台灣應用心理學會理事長、
◎李嗣涔/台大前校長
◎徐百川/博士、中研院生醫所研究員
◎高閬仙/陽明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兼副校長
◎謝淑蘭/國立成功大學心理學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國際媒體一致讚譽
「這是關於科學研究如何和這位傑出科學家的生活密切交織的故事。科學家葛詹尼加不只創造出一個新的探索領域,而且還剛好住在過達特茅斯學院聲名遠播的那間『狂歡動物屋』。本書以優美的文筆,描述一場精彩刺激的冒險。」
—《迷戀音樂的腦》(This Is Your Brain on Music)與《有組織的大腦》(The Organized Mind)作者列維廷
「這是關於一個天才的個人故事。他在裂腦症這種至今依舊無邊無際、令人費解的人腦未知領域當中做出了少見的重大發現,並因此聲名大噪。」
—《刺激的吸毒考驗》(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與《太空英雄》(The Right Stuff)作者沃爾夫
「我這輩子都想知道大腦如何運作,以及為什麼有時該動腦筋時就不動。《切開左右腦》是一個有趣、平易近人的故事,不只告訴你左右腦怎麼運作,也是關於一群絕頂聰明又怪得很可愛的神經科學家怎麼想辦法找出答案的故事。」
—《康納脫口秀》主持人歐布萊恩
「葛詹尼加講述如何發現人類的左右腦會互相合作的精彩故事,內容相當引人入勝,這本書會讓你對『思考』三思。兩個腦袋絕對比一個好,而我們大多數人一個頭裡都有兩個。」
—知名演員艾達
「一般人想像的『科學進步』,常常是靠一群被我們當成跟『大腦皮質』沒兩樣的科學家,持續不懈、不帶感情地篩選理論,追尋真相所達成。葛詹尼加本人是神經科學界的先驅,他幫我們矯正了這個看法。透過親身的經驗,他揭露了自我、政治、嫉妒、羨慕、慾望以及其他所有在人類知識進步過程中的滔天大罪。如果你關心科學、歷史、人腦,以及人心,那你就不能錯過這本書。」
—《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共同製作人暨編劇卡普蘭
「這是一本敘事優美的作品。葛詹尼加梳理自己的科學成就,讓我們看見他的重要性:一個受啟發的教育者,一手建立了認知神經科學的領域。這本作品帶有深沈的哲學涵意,他生命旅程中的種種刺激欣喜,在在顯示他因為科學而變得豐富,因家庭、朋友、歡樂與幽默而變得更好。」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醫學博士暨哲學博士比茲
得獎紀錄:2015美國亞馬遜十大選書
2015紐約時報暢銷書名人推薦:學界聯合推薦
◎李宏鎰/《遇見「過動兒」,請轉個彎》作者、台灣應用心理學會理事長、
◎李嗣涔/台大前校長
◎徐百川/博士、中研院生醫所研究員
◎高閬仙/陽明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兼副校長
◎謝淑蘭/國立成功大學心理學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國際媒體一致讚譽
「這是關於科學研究如何和這位傑出科學家的生活密切交織的故事。科學家葛詹尼加不只創造出一個新的探索領域,而且還剛好住在過達特茅斯學院聲名遠播的那間『狂歡動物屋』。本書以優美的文筆,描述一場...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深入科學
物理學就像性:當然,它也許會造成某些實際的結果,但我們不是為了那結果才做的。—費曼
一九六○年時,大部分的大學都還不是男女合校,我在鳥不生蛋的新罕布夏州的漢諾威,和幾百個男人一起念達特茅斯學院。當夏天來臨,我心裡只有一個念頭。我申請了加州理工學院的實習計畫,因為我希望這個夏天能和在冬天認識的麻州衛斯理學院的女生接近一點。於是我在生物學與重大發現的傳說之地,加州理工學院,度過了一個燦爛的夏天。之後,她對別的事更有興趣,我卻對科學開始著迷。我常想,我當初去那裡真的是因為對科學求知若渴嗎?或者只是因為對住附近的那個女孩有興趣?誰知道年輕人千變萬化的腦袋裡在想什麼呢?想法有時候確實能找到空隙,鑽進被賀爾蒙填滿的心智裡。
對我來說,鑽進我心裡的其中一個想法就是:「大腦是怎麼讓一切運作的?」我去加州理工學院的另外一個理由,是因為我在《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上看見一篇斯佩里的文章,1內容是在神經迴路生長過程中,神經如何建立從A點到B點的特定連結的相關研究。很多,其實應該說大部分的神經生物學,都卡在這個簡單的問題。斯佩里是當時的王者,而我想了解更多這方面的研究。除此之外,我剛剛說過了,我女朋友就住在加州聖馬利諾的那條街上。
直到我在多年後聽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傑出的物理學家阿瓦雷茲的說法時,我才知道自己內心疑問背後的衝動,不是只有好奇心那麼簡單。阿瓦雷茲說,科學家做的事並不是因為出於他們的好奇心,而是因為他們本能上覺得,事情運作的原理並不如別人說的那樣。2他們實驗性的心智推動了齒輪,讓他們想到另外一種也許可行的方法。他們雖然會對一項發現或發明感到驚嘆,但也會出於本能自發性地開始思考別的方法或解釋。
以我為例,我總是在思考如何從不同的觀點來面對一個問題。部分原因在於我的量化技巧非常貧乏。數學對我來說並不簡單,我通常會躲開任何高度技術性的討論。而我發現在很多情況下,用日常生活的語彙來思考看來很複雜的問題是很容易的。這是真的,因為世界就是這個樣子。畢竟,你不需要了解撞球的原子組成和量子物理也可以打一局撞球;只要簡單、可靠的古典物理就很夠用了。
我們人類一直都在進行抽象思考,也就是從一個具體的事實發展出更大的理論與理解。因此我們會一直提出新的、更簡單的一層描述,讓大腦有限的能力更容易理解。以我的卡車為例 。「卡車」是一種新的描述詞:它描述了一種擁有開放空間裝載東西的車輛,並且由六汽缸引擎、散熱氣與冷卻系統、底盤等等組合而成。現在因為我有了這個新的描述詞,每次我在思考或是提到我的「卡車」時,我就不需要在我的心裡重新喚起它的所有部分並重新組裝一次。我完全不需要去想這些零件(除非有個零件壞了)。我們無法在每次提到一樣東西時,就處理一次為了理解該物品機制而存在的各種複雜原理,這對我們的心智處理過程來說負擔太大了。所以我們會分割,給這個機制一個名字——「卡車」,藉此把這東西帶給我們的成千上萬的負擔縮減到一個字詞。一旦我們對本來非常繁瑣的主題建立起抽象的觀點,我們對這個主題或運作原理,就會有超級清楚的新思考方式。有了新的關鍵字與指涉對象,我們的心智就彷彿被解放,獲得再次思考的新能量。在大自然裡,這樣的層級似乎無所不在。
我會在本書後面會回頭討論我所謂對世界的「分層」觀點,這個想法來自於試著了解細胞、電腦網絡、細菌與大腦等複雜系統的科學。分層的概念幾乎能應用在任何複雜系統上,連我們的社交世界,也就是我們的私生活領域,也不例外。發揮良好功能的一層,會以其獨特的獎勵系統驅動我們。然後突然間,我們可能會碰到適用其他規則的另一層。對當時的我來說,加州理工學院是新的一層。我在當時看到與做的一切都是「第一次」,而我在那裡有很多「第一次」。
總之,我在即將從達特茅斯學院大三升大四的暑假到了那裡。我緊張地走進加州理工學院,為接下來許多的初體驗開了頭:去斯佩里在柯克赫夫廳的辦公室見他。原來他是個說話溫柔、認真的人,不太會喋喋不休。我後來聽說,在我和他見面前幾週,有一隻猴子從動物室裡逃脫,溜進他的辦公室,還爬到他的書桌上。於是他抬起頭對當時的訪客說:「我們可能去隔壁比較好,那邊應該比較安靜。」
加州理工學院自有一種令人暈頭轉向的氛圍。每個人都絕頂聰明。3辦公室的門後坐著許多在各自領域內表現傑出的科學家。雖然所有的大學都如此自誇(特別是現在,在他們那些語氣雀躍的網頁上),總是沾沾自喜地強調他們多麼「跨學科」。但現實經常是相反的。可是在加州理工學院,不論是當時或現在,這都是鐵一般的事實:這些科學的引擎總是在運作,而且朝著彼此前去。這個地方的特質可以用一句老話來概括,「我知道他發明了火,不過他最近做了什麼?」在一個會推著你以不熟悉的方式來思考的團體裡工作,會讓人快速往前衝。要跟上這個步調也是一種挑戰,而這還是保守的說法。整間加州理工學院都是這樣,在斯佩里的實驗室更是如此。
身為一個菜鳥,我愛死這個環境了。回過頭來看,也許沒人能知道在一個人的故事裡,到底哪些部份是他走上某條道路的原因,或者哪些部分真的能解釋他後來的際遇。當然囉,偶然的意外與重大的事件,都會讓我們在新的情況與環境中找到自我。同樣神奇的是,我們幾乎能立刻融入新的環境,跟上這不同的節奏與不同的知識基礎。很快地,我們便埋頭往新的目標努力。
除了原本吸引我過來的神經生長迴路研究之外,這間實驗室顯然很快有了新的研究焦點:裂腦研究。他們想知道左右腦是不是能各自獨立學習。許多博士後研究生在這裡研究被手術切斷左右腦連結的猴子和貓的行為,到處都鬧哄哄的。我該從何開始呢?
我很快想到了做出「暫時分裂的腦」這個主意。我想利用所謂「擴散抑制」(spreading depression)的方法來研究老鼠:把一小塊紗網或是明膠海綿泡在鉀裡面,用它蓋住半邊的腦,使這邊的腦暫時休眠或停止活動,而另外半邊處於清醒、可以學習的狀態。4擴散抑制現象的世界權威之一馮哈瑞芬的辦公室就在斯佩里的隔壁,所以向他請教會很方便。他人很好又很優雅,非常平易近人,在跟科學有關的事方面更是如此。可惜那個實驗從來沒有實現過,可能是因為我真的很怕老鼠!
所以我改用兔子。同樣的,我的想法也很簡單:為什麼不在左側或右側的內部頸動脈注射麻醉呢?因為左右邊的頸動脈分別輸送血液到左腦或右腦,注射麻醉就能讓一邊的腦睡著,留下清醒、可以學習的另一邊。真的會這樣嗎?在當時的科學界,尤其是加州理工學院,唯一會阻止你的想法或實驗的,就是你的活力與能力。那時候沒有科學研究與倫理審查委員會的問題,也不會缺少經費,沒有人會對你潑冷水,也沒有落落長的規定,你大可以放手去做。
我必須有辦法測量神經活動,確保處理過的半邊腦真的睡著了,而另一邊確實是清醒的。所以我的第一步就是弄一台腦波儀(簡稱EEG)。接著我得搞懂怎麼教兔子學習一件事,後來我們決定教會兔子聽到某個聲音就眨眼。我完成了這個後,還必須學會怎麼把記錄用的電極貼在小兔子的頭骨上,以記錄腦波活動。這我也莫名其妙地學會了。最後,我還要能把麻醉藥注射到左邊或右邊的內部頸動脈(從心臟通往腦的主動脈),並且確認麻藥只停留在半邊的腦,沒有流到另外半邊,害另一邊也睡著。我在圖書館裡花了很長的時間研究位在腦部底側的動脈構造威利環(又稱動脈環)的解剖學,最後判斷這個實驗在兔子身上應該行得通。雖然從兩邊動脈供應的血液似乎會在威利環混合,但有一些研究顯示,特殊的血液動力學會避免這種事發生。於是我打算放膽嘗試,深信血液動力學會是我的救星,並且希望其中一條頸動脈裡的麻醉藥留在半邊腦的時間夠久,好讓這個實驗可以成功。我終於做好大幹一場的準備了。
我進行這整個實驗的空間是斯佩里實驗室外的走廊。那裡很狹窄,有很多博士後研究生走來走去忙著自己的研究。有一天我準備開始做測試實驗,所有東西都就位了:兔子、記錄神經活動並且能將結果畫在紙上的腦波儀,還有八根在紙上來來回回的墨針,此時鮑林經過我旁邊。每個人都知道鮑林是什麼人,尤其是我們這棟樓的,因為他的辦公室就在化學大樓的轉角那邊。他是量子化學與分子生物學的創始人之一,被尊為二十世紀數一數二重要的科學家,他的肖像在二○○○年登上美國郵票。鮑林停下腳步,問我在做什麼。我簡單說明過後,他說:「其實你『記錄』下來的那些曲線,可能會跟測量裝在碗裡的果凍狀物質出現的簡單物理結果沒什麼兩樣。你最好先試試看。」
他繼續往走廊另一頭走去,而我全身發熱。他告訴我的很簡單:年輕人,不要有成見,什麼都要測試。不管你去哪裡,都會有人挑戰你、質疑你、挑釁你,但又鼓勵你,並且確實支持事情可能有另外一種發展的觀念,激勵年輕的科學家繼續往前,這太令人陶醉了。當時我並不知道,鮑林在幾年後贏得第二座諾貝爾獎後,居然會控告之後成為我畢生摯友的小巴克利誹謗!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大約一年多後測試了最早的裂腦患者。我想了解因醫療目的接受裂腦手術的人的情況:他們的左右腦不再相連。這本書是關於這個特殊的真實醫學現象,說明這是怎麼回事,具有什麼意義,以及教導了我們什麼。故事中提及許多直接或間接參與裂腦症研究的科學家。雖然他們的生平細節在過去幾乎純粹只有科學敘述的文獻中都被刪除了,但是我在回顧自己的研究內容時發現,在許多看似無關,但最終匯流聚集,建立起人生樣貌的經驗當中,抓住至少一個故事是很重要的;而在這個例子裡,這些經驗最終建立的是我的科學人生。不過這些是後話了。
在那個時光飛逝的夏天,我準備好了進行實驗的兔子。實驗室裡總是有人會七嘴八舌,但我選擇的工作是我要做的。光是想到我可能會發現某事運作的一點點原理,就讓我沈迷並興奮不已,我完全被吸引了。當時我就知道,我得回去和我父親談一談。他的夢想就是我可以跟著他和我哥哥的腳步,進入醫學院就讀。我父親非常強勢。要打破老大的計畫需要好好談一談。
起源
我父親丹堤‧阿基里斯‧葛詹尼加於一九○五年出生在麻薩諸塞州的馬爾波羅。他在新罕布夏州曼徹斯特的聖安瑟倫學院畢業後,打算和從義大利移居到美國的祖父一樣,在家附近的靴子工廠工作。但當初幫忙他進聖安瑟倫讀書的當地神父,插手阻止了他的選擇。他告訴我父親,如果他在夏天自修化學和物理,他就能幫忙安排他去遙遠的芝加哥羅耀拉大學念醫學院。那時候的生活真是簡單又直接啊。你只要學習,就能走到下一步。他照做了,於是在一九二八年去了芝加哥,帶著他媽媽存的錢,打算自己買一架顯微鏡。可惜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恐慌,讓銀行裡的那筆錢化為泡影。
他在芝加哥住的地方,就在黑道老大卡彭主使的恐怖情人節大屠殺的地點附近,他甚至還聽過克拉克街上的槍聲。我父親有時候會在發生槍戰的巷子口那間便宜小酒館買蛤蜊巧達湯,偷偷把配湯吃的小圓蘇打餅乾帶出來,當時這就是他的主食。他又高又壯,所以加入半職業的橄欖球隊,藉此養活自己並且付學費;此外他還會駕駛起重機,並且在起重機裡完成他大部分的功課。總之他完成了一切。我曾經想過我們的經歷有多麼的不同,因為我是在加州富裕奢華的帕沙第納拿研究生獎學金做研究的。
在芝加哥念了四年書之後,他前往火車站,心裡的盤算是坐上第一輛前往陽光普照的地方的火車。他成功達成目標,在洛杉磯下了車。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他在當地著名的郡立醫院擔任實習醫生。一九三三年的元旦,當他從醫院正門階梯小跑步出來,準備和他的哥兒們去看美國大學橄欖球的玫瑰盃比賽時,第一次看見正準備去上班的我母親。三個半月後,他們就結婚了。我母親的一生非常活躍,她曾一度擔任過著名的女性佈道家麥艾美的秘書。麥艾美創立了四方福音會,而她在自建的安吉利斯主教堂的佈道,讓洛杉磯人著迷不已。但也可能是我母親出名的父親,葛瑞芬斯博士,為她在那個重視媒體的鎮上安排了這份工作。我外公除了是洛杉磯第一位整形醫師,還是一位才華洋溢的成功物理學家。他的患者不乏好萊塢明星,除了女星畢克馥和黛薇絲之外,還有卓別林及牛仔影星米克斯。
雖然我從來沒見過我外公,但他在當地的圈子裡以高超的棋藝出名(大師級),而且還是《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西洋棋專欄長期作家史坦納的好朋友。在一九三七年一場西洋棋比賽結束後,兩人在回好萊塢的路上被一個酒醉的駕駛迎面撞上,我母親看了報紙才發現自己的父親死於車禍。我最近才第一次看見我外公的一張照片,發現我們的臉有些相似之處,不過他的西洋棋基因卻沒遺傳到我身上(我弟弟艾爾就有)。
在洛杉磯的生活步調很快,多采多姿。但當時畢竟還是經濟大蕭條時期,工作機會很少,連醫師都面臨困境。因為在洛杉磯找不到工作,我父親便為建造科羅拉多河大圳的那些工人看病。那是一個龐大的計畫,引科羅拉多河的水,經亞利桑納州直達加州。儘管如此,我父親在沙漠中閒暇之餘還進行了另一項計畫。他在各地探勘,並提出挖掘權申請。不過幾年後,因為他志願從軍加入二戰軍力,便把挖掘權全數讓給政府。我父親總是能同時從事好幾項活動,而且都能勤奮進行。他的小孩也都繼承了這個特質。
我父親有一個在麻薩諸塞州北亞當斯當醫生的堂兄弟溺水身亡,於是家族要求他搬回故鄉。因此在一九三四年的夏天,他開著我們家的德索托轎車,戴著我母親以及剛出生的寶寶,我大哥唐諾,回到了北亞當斯。家族安排他們住在城外的一間房子裡。在大雪紛飛的暴風裡,我父親被困在城裡,原本是加州女孩的我母親,只能孤伶伶地坐在燒著柴火的壁爐前,盡量幫寶寶取暖。此時,我父親卻跟哥兒們在城裡玩牌取樂。這樣的日子撐不了多久。隔年二月,在麻薩諸塞州西部嚴苛的寒冬裡,我母親的表親寄給她一枝來自溫暖加州的橙花,讓她徹底崩潰。我父親也不喜歡這種天氣,於是他們在大約九個月後搬回加州。他和當時才剛起步的魯斯羅斯醫療集團牽上了線,成為他們的創始伙伴之一。這個醫療集團後來成為美國史上第一個健康維護組織,也是現在龐大的凱薩醫療機構效法的模範。
顯然我父親很有勇氣,而且有一點叛逆。他繞了一圈,終於回到專業領域上取得成功,雖然從我的客觀角度來看是再明白不過了。但他自己也這麼想嗎?我不知道當我跟他宣布我的新計畫時,他會有什麼反應。「爸,我想去念加州理工學院而不是醫學院。」就這樣,我清清楚楚地這麼說。我爸用一種醫學權威的表情看著我說:「麥克,如果你都可以當一個博士的老闆了,你為什麼要自己去念博士?」他真的很不能理解。我父親就像某些人一樣,為醫療投入心力,全心為病患服務。我們被取消或縮短的度假次數,遠多過於那些開心度過的假期,因為病患總是優先。
儘管如此,過了一會兒後,我爸微笑著祝我好運。畢竟還有一件小事要處理:讓加州理工學院接受我入學。加州理工學院會接受的學生特質,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剛剛說過了,這個地方到處都是絕頂聰明的天才,而且大部分都遙遙領先我好大一段距離。然而,我已經知道,有很多學生是因為另外一個原因成功入學:他們以某種方式向他們未來的導師證明,他們知道怎麼做事,通常都是靠著我才剛完成的暑期研究計畫證明的,而這也是我進去的唯一希望了。
大學生涯
斯佩里來和我討論,因為他對我的兔子實驗以及我整體的活力印象深刻。於是隔年春天,也就是我在達特茅斯學院的第四年,加州理工大學生物學系有條件地接受我進入研究所。顯然我一定要在第一年就做點成績出來。
我在達特茅斯學院的四年充滿挑戰。不過我當時根本不知道,就因為我加入了聲名狼籍的「狂歡動物屋」(圖三),我的社交生活居然會比我在學術界的任何成就都更值得大書特書。在這些惡名昭彰的動物當中,我這個科學怪胎以「長頸鹿」的身份度日。我是兄弟會裡的書呆子,寧願待在心理學家史密斯的實驗室裡,也不想在兄弟會的地下室喝酒。
史密斯很有研究熱忱。他在麥克納特大樓的頂樓蓋了一間小實驗室,我們在那裡開發測量眼球移動的方法。我們會一起研究到半夜。做研究對我來說是全新的、很刺激的事,而第一次一窺大自然謎團之一的研究帶來的誘惑,讓我立刻上了癮。可是當時,在加州理工學院那個值得紀念的夏天之前,這彷彿只是為了上醫學院而做的事情之一。我在「狂歡動物屋」確實交到了一些好朋友,那裡的氣氛也激勵我要好好享受人生!
因此,隨著達特茅斯學院的日子對我的吸引力日漸下滑,我對加州理工學院的興趣日益濃厚,我在大四的時候一心想知道:「胼胝體被切斷的人會怎麼樣?」(「切斷」指的是用手術將腦中最大的神經束切開。)度過了在加州理工學院做兔子大腦實驗,以及大力強調基礎研究的那個夏天過後,我很清楚這就是我要走的兩個方向。當時還無法想像人類的左右腦切斷連結後,會那樣表現出與動物手術後相同強烈的後果。沒有人真的想過,當你在一個人的左手放一個物體,他居然無法用右手找到相符合的物體。當時這聽起來根本是瘋了。
用培根的傳統演繹法來說,這就是觀察馬嘴裡的牙齒數量的時候了。這個故事可能是虛構的,但確實捕捉了科學的本質:
在西元一四三二年,一群教友對於馬的嘴巴裡到底有多少牙齒,發生了嚴重的爭論。這場爭執延續了十三天都沒有平息的跡象。所有人翻遍古代書籍與編年史,提出這個領域裡前所未聞的精彩或冗長的論述。在第十四天早上,一個外表討喜的年輕修士向前輩請求發言的許可。接著,他直接了當地哀求那些聰明到讓他難以理解的爭論者,站起身來,採行一種粗魯而且前所未聞的方法:直接看看一匹馬張大的嘴巴,就能找到問題的答案了。這讓他們的尊嚴受到嚴重的打擊,於是他們惱羞成怒,在一陣狂暴的衝突中衝向年輕修士,痛毆他的臀部與大腿,然後立刻把他趕走。他們說,這個大膽的新修士一定是被撒旦引誘才會提出這麼不神聖、史無前例的方法來尋找真相,和所有神父的教誨都背道而馳。經過許多天更激烈的爭辯後,和平鴿降臨了集會:有一人宣布,因為極度缺乏相關的歷史與神學證據,這個問題會是永遠的謎團,並命令應如此記載此事。
對我來說,馬的牙齒就是在洛契斯特大學,接受與加州理工學院的動物相似手術的人類病患。這一批著名病患在一九四○年代初接受胼胝體切開手術,將他們的癲癇大發作限制在一側的腦內,同時也切斷了左右腦的連結。
手術由神經外科醫師韋哲執刀。他曾觀察到一名罹患癲癇的患者在胼胝體長出腫瘤後,癲癇發作的情形反而減少,於是他懷疑,切斷胼胝體也許能阻止引發癲癇的電脈衝從腦的一側傳到另一側,因而切斷了二十六位有無法控制的嚴重癲癇大發作的患者的胼胝體。才華洋溢的年輕神經學家阿克雷提斯當時似乎詳細檢查過這些病患,發現他們所經歷的癲癇發作確實大幅減少,手術後也沒有任何重大的行為或認知改變。左右半腦失去連結,而且好像什麼都沒有變!皆大歡喜啊。十年來,文獻中記載的就是這樣的結果。當時一流的實驗心理學家,同時也是斯佩里研究所的指導教授賴胥利,緊抓著這項發現,推廣他對大腦皮質的質量作用(mass action)與「等潛原則」(equipotentiality)的想法。他表示,腦中分離的迴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皮質總量。他引述阿克雷提斯的研究,下了這樣的結論:切斷連結左右腦的大量神經束,對於左右半腦間傳遞資訊並沒有任何影響。他還笑稱胼胝體的作用只有把左右腦連在一起,以免它們下垂而已。
這些患者之後被稱為阿克雷提斯患者。他們似乎是最適合確認,或推翻斯佩里和他的研究生梅耶斯在加州理工學院做的動物研究,到底是否適用於人類的患者。根據當時的動物研究,切斷左右腦的連結後,猴子的左手並不知道右手在做什麼。人類有可能也是這樣嗎?雖然這似乎很瘋狂,但我確信一定是如此。我想要重新測試洛契斯特的那些患者。
我找到了可能認識那些洛契斯特患者的人,打電話給他,結果透過在一九四○年代初期的手術當時擔任住院醫師,並為這些病患動手術的司密斯博士辦公室的聯繫,我成功獲得拜訪這些患者的許可,前提是要找得到他們。
我設計了很多和阿克雷提斯不一樣的實驗,和斯佩里用信件討論了很多想法與計畫。我向達特茅斯醫學院的瑪莉希區卡克基金會申請,得到一小筆兩百美元的獎學金,支付租車和在洛契斯特住宿的費用。於是我開車前往洛契斯特,直接前往司密斯的辦公室。我翻遍他的檔案,想找到可能有用的名字與電話號碼。此時他打電話來,告訴我他改變心意了,基本上就是叫我馬上滾蛋。儘管我的車子裡裝滿了借來的速讀訓練器、電腦時代之前的各種用來在螢幕上顯示影像一段時間的儀器,還有從達特茅斯心理學系借來的一堆器材,我還是照著他要求的離開了。想要揭曉人類胼胝體切開後的影響,只能之後再努力實現。
然而,幾個月後,我又回到了這條路。這次我並不失望,而是興奮不已。我要去帕沙第納。在接下來五年的燦爛時光裡,加州理工學院就是我的家。
發現加州理工學院
從「狂歡動物屋」搬到以詩人艾略特的著作為名的「普魯弗洛克之屋」,對我是一大挑戰。這間房子就在加州理工學院生物學大樓的對街上(圖四)。幫我安頓的是當時斯佩里的一個資深研究生,漢密爾頓。他很快成為我在那裡最好的朋友,一直慫恿我住在普魯弗洛克之屋。我到的時候,那裡就以有天才、有派對,基本上就是什麼都有而聞名。漢密爾頓的室友是泰明和梅舍生,他們已經讓這棟兩層樓的出租公寓蓬篳生輝:泰明後來因為在病毒方面的突破性研究獲頒諾貝爾獎;梅舍生則和史塔爾共同完成了分子生物學史上最出名的實驗。*我搬進去的時候,理論物理學家科爾曼和多姆貝也住在那裡:科爾曼和諾貝爾獎得主,同時也是著名推廣科學的學者費曼一起作研究;多姆貝則是和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創造「夸克」這個詞的蓋爾曼一起作研究。科爾曼後來在哈佛成就非凡,成為「物理學家中的物理學家」。
普魯弗洛克之屋在週末辦的派對和狂歡動物屋的派對水準完全不同。有一次,費曼也來參加派對,他離開之前跟我說,「只要你保證我可以繼續研究物理,我可以讓你切斷我的左右腦連結。」我大笑了,回答:「我保證。」費曼立刻以電光火石的速度把他的左手和右手都伸出來,和我握手,表示一言為定!
*他們的研究支持了DNA複製是一個半保守過程的假設:複製時僅使用原本DNA螺旋的其中一股,和在複製過程中新完成的一股。M. Meselson and F. W. Stahl, “The Replication of DNA in Escherichia coli,” PNAS<$> 44 (1958): 671–82.
第一章 深入科學
物理學就像性:當然,它也許會造成某些實際的結果,但我們不是為了那結果才做的。—費曼
一九六○年時,大部分的大學都還不是男女合校,我在鳥不生蛋的新罕布夏州的漢諾威,和幾百個男人一起念達特茅斯學院。當夏天來臨,我心裡只有一個念頭。我申請了加州理工學院的實習計畫,因為我希望這個夏天能和在冬天認識的麻州衛斯理學院的女生接近一點。於是我在生物學與重大發現的傳說之地,加州理工學院,度過了一個燦爛的夏天。之後,她對別的事更有興趣,我卻對科學開始著迷。我常想,我當初去那裡真的是因為對科學求...
推薦序
推薦序 謝伯讓(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暢銷書《都是大腦搞的鬼》作者)
2003年,一封來自美國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的博士班入學許可通知書,把我捲入了認知神經科學的歷史發展洪流之中。當時,正值本書作者葛詹尼加(Michael Gazzaniga)在達特茅斯執掌認知神經科學研究中心的期間。一心想要研究人類意識現象的我,正是因為葛詹尼加的大名,才申請了這一所位於冰天雪地中的美國常春藤盟校,而這一封入學許可通知書,也徹底改變了我的一生。
1961年,葛詹尼加畢業於達特茅斯學院的大學部。隨後前往加州理工學院追隨斯佩里(Roger Sperry,1981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研究裂腦病患。1985年,他第一次回到達特茅斯任教,之後又搬到加州。1999年,因為發現裂腦病患似乎擁有兩個不同心靈而名滿天下的葛詹尼加再度回鍋達特茅斯,並為學校帶來前所未見的資金譯注,他當時所取得的研究經費,超過了全校總研究經費的一半以上。在他刮起的「認知神經科學」熱門旋風的影響之下,達特茅斯成立了全美國第一個認知神經科學中心、以及全美第一個擁有功能性磁振造影機器的心理系研究大樓。
在這段風起雲湧的時期,許多對認知神經科學有興趣的頂尖研究生、博士後研究員以及年輕學者都蜂擁聚集在達特茅斯。只可惜,在我入學時,葛詹尼加正忙於行政與管理工作,並且在我入學兩年後便離開達特茅斯前往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因此我並沒有機會直接和他共事學習。
不過在葛詹尼加離開達特茅斯之後,我仍有機會結識書中第八章所提到的許多關鍵人物,例如心理物理學高手芬卓奇(Bob Fendrich),幾乎沒有預測錯誤過的心理統計學教授沃福特(George Wolford)、精力充沛的精神醫學科學家格萊弗頓(Scott Grafton)、青少年大腦的專家蓓爾德(Abigail Baird)、以及聰明過人的牛津大學教授布萊克摩爾(Colin Blackmore)等人。至於書中提到的那家催生出神經影像共享資料庫的「髒牛仔咖啡店」,更是我在學生時代光顧不下百次的熟悉老地方。
葛詹尼加在這本書中,以裂腦症的研究貫穿了他豐富宏大的一生。如果你對大腦和裂腦有興趣,那你應該閱讀這本書,因為你可以在書中看到關於裂腦研究的第一手資料。如果你對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方法有興趣,你也應該閱讀這本書,因為葛詹尼加為了研究大腦,無所不用其極地使用了各種可得的研究方法,並且對它們作出了最佳示範和描述。如果你對科學假說的演進有興趣,你也應該閱讀這本書,因為葛詹尼加清楚的展現出如何針對一個現象提出假說並進行驗證的科學活動過程。如果你對科學家之間的社會互動有興趣,你更應該讀這一本書,因為你可以從這本書中看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想法衝擊如何改變一個科學領域的走向。
如果你是想要進入這個領域的學生,那你應該好好「熟讀」這本書,因為你可以透過這本書知道其中各個相關研究主題的靈魂人物到底是誰。如果你已經是這個領域的研究者,那你更應該「偷讀」這本書,因為你可以看到諸多名人、師長、同事和朋友的軼聞趣事與八卦。如果你是科學領域中的領導者與管理者,那你更應該「搶讀」這本書,因為你將可以從中學到一個新科學領域的開創與領導先鋒如何展現其華麗的政治與管理手腕。
在葛詹尼加等身的諸多科普書籍當中,如果你想選擇一本起手、或者暫時只有時間閱讀其中一本,那就先從這本精彩絕倫的科學家自傳開始吧!
推薦序 謝伯讓(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暢銷書《都是大腦搞的鬼》作者)
2003年,一封來自美國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的博士班入學許可通知書,把我捲入了認知神經科學的歷史發展洪流之中。當時,正值本書作者葛詹尼加(Michael Gazzaniga)在達特茅斯執掌認知神經科學研究中心的期間。一心想要研究人類意識現象的我,正是因為葛詹尼加的大名,才申請了這一所位於冰天雪地中的美國常春藤盟校,而這一封入學許可通知書,也徹底改變了我的一生。
1961年,葛詹尼加畢業於達特茅斯學院的大學部。隨後前往加州理工學院追隨斯佩里(...
目錄
前言:來自著名心理學家平克
序
第一部分:發現大腦
第一章 深入科學
第二章 發現分裂的心智
第三章 尋找大腦的摩斯密碼
第二部分:分分合合的左右腦
第四章 揭露更多模組
第五章 腦部造影確認裂腦手術
第六章 依舊分裂
第三部分:演化與整合
第七章 右腦有話要說
第八章 安穩生活,受徵召貢獻一己之力
第四部份:大腦層級
第九章 層級與動態:尋找新觀點後記
前言:來自著名心理學家平克
序
第一部分:發現大腦
第一章 深入科學
第二章 發現分裂的心智
第三章 尋找大腦的摩斯密碼
第二部分:分分合合的左右腦
第四章 揭露更多模組
第五章 腦部造影確認裂腦手術
第六章 依舊分裂
第三部分:演化與整合
第七章 右腦有話要說
第八章 安穩生活,受徵召貢獻一己之力
第四部份:大腦層級
第九章 層級與動態:尋找新觀點後記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