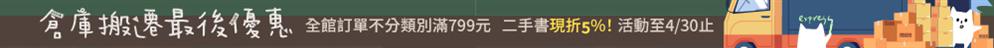被殺死的原來不只是妳,
還有那年夏天,我們的青春……
入圍IMPAC都柏林國際文學獎!
入選德國年度最佳犯罪小說!
十五歲的我們不知道,
有些事件就像有去無回的入口,通往新的生命階段,
有時更美好,但通常更殘酷……
一九八一年的那個夏日清晨,十五歲的少年站在沙丘上凝望著海浪中的十七歲少女,曬成蜜色的纖腰、翹臀、長腿……他看傻了眼,過了好一會兒才意識到,自己注視的其實是命案現場。
乳品店女兒露西年輕生命的隕落,奇異地吸引住海口小鎮上的一群少年。少年們憑著一股天真的正義感開始尋找兇手,露西在他們互相拼湊的記憶中越來越完美,他們所窺見的成人世界,卻越來越晦暗不明。隨著小鎮的氣氛在內憂外患下日益緊張,少年們從小聽慣的浪濤聲,也在不知不覺之間變成了鼓動情欲與血性的脈搏。
多年以後,已不再年少的他們仍掙扎著回頭,想穿過烈日、海霧和暴雨,看清自己當年的純真如何在一連串失控中亂葬,十五歲那年的漫長酷暑,彷彿從來不曾結束……
作者簡介:
卡爾‧尼克森 Carl Nixon
專業小說家與劇作家,也是紐西蘭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他曾在1997、1999年兩度贏得週日明星時報短篇小說獎,並在2007年榮獲紐西蘭最頂尖的短篇小說獎項──紐西蘭銀行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獎。2006年,他以處女作《炸魚薯條店之歌故事集》榮登紐西蘭暢銷小說榜首,並入圍大英國協作家獎東南亞暨南太平洋區最佳處女作獎。2013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處女與鯨魚》則獲選《紐西蘭聽眾》雜誌年度百大好書,以及紐西蘭自治領郵報與基督城報年度最佳紐西蘭小說前五名,並由南太平洋電視公司買下影視改編權。
2006年,尼克森應娥蘇拉.貝索創意紐西蘭基金會之邀,在康特柏里大學擔任駐校作家期間創作了《夏日死亡紀事》,本書隨後入圍IMPAC都柏林國際文學獎,並入選德國年度最佳犯罪小說。
譯者簡介:
趙丕慧
一九六四年生,輔仁大學英文碩士。譯有《杜鵑的呼喚》、《臨時空缺》、《少年Pi的奇幻漂流》、《易經》、《雷峯塔》、《穿條紋衣的男孩》、《不能說的名字》等書。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看似輕薄短小,卻承載了複雜而厚實的情感和憂傷。──圖書版權經紀人譚光磊
這是一本幻象之書,是由魔術師鍛造的傑作,它巧妙地將你的心思與最初的故事漸漸錯開,直到你驀然驚覺,之前讀過的所有事件忽然都有了新的意義……充滿豐富的細節與感染力。──基督城報
尼克森寫青少年語氣時充滿角色性格,他完全掌握了青春期那種火爆的情緒和探查未知的癡迷……若不把這本書列入全國高中英文課必讀,那可真是罪過!──尼爾森新聞網
尼克森懂得精算犯罪小說中的每一分情緒,讓懸疑盤旋,然後俯衝襲擊,在一個人身上堆積焦慮,然後把威脅感傳染給其他人。他是一個真正有天賦的作家!──週日明星時報
尼克森生動的書寫喚醒了彼時彼地,二十七年前的紐西蘭。那是青少年主角們生命的轉捩點,也是紐西蘭這個國家的分水嶺。這本書勾動了我們潛意識底下的懷念,渴望回歸那個一切都看起來比較簡單和有秩序的純真年代。──懷卡托時報
尼克森的寫作優美動人,完美演繹青少年的風格與音色,發揚了他在《炸魚薯條店之歌故事集》中展現的潛力。──南與北雜誌
《夏日死亡紀事》召喚出1980年代紐西蘭的氛圍:酪農業、夏季、沙灘、青少年的百無聊賴與性渴望,也抓住了男人中心的陽剛文化、悲傷,以及悲傷的難以言說。──紐西蘭自治領郵報
卡爾.尼克森技巧精湛地重建了1980年代的紐西蘭鄉下……真希望尼克森趕緊多寫幾本小說。──週日先鋒報
尋找真兇只佔了本書強大閱讀魅力的一小部分。 ──澳洲女性周刊
名人推薦:看似輕薄短小,卻承載了複雜而厚實的情感和憂傷。──圖書版權經紀人譚光磊
這是一本幻象之書,是由魔術師鍛造的傑作,它巧妙地將你的心思與最初的故事漸漸錯開,直到你驀然驚覺,之前讀過的所有事件忽然都有了新的意義……充滿豐富的細節與感染力。──基督城報
尼克森寫青少年語氣時充滿角色性格,他完全掌握了青春期那種火爆的情緒和探查未知的癡迷……若不把這本書列入全國高中英文課必讀,那可真是罪過!──尼爾森新聞網
尼克森懂得精算犯罪小說中的每一分情緒,讓懸疑盤旋,然後俯衝襲擊,在一個人身上堆積焦慮...
章節試閱
是彼特.馬歇爾在海邊發現了露西赤裸的身體,就在木馬街的盡頭附近。此後,將近三十年過去了,二十世紀也即將告終,可是我們還是能把露西躺的位置分毫不差地指出來。她的身體就在沙丘腳下,被滿潮送了上來,很靠近警告牌。警告牌上提醒民眾有激流,不要在河口銜接大海,也就是沙嘴盡頭的深水道中游泳。打從一開始,實事就明擺在眼前,殺死露西.阿舍的不是這些庸俗平常的危險。
那是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週日,再四天就是聖誕節。清晨七點半。今年夏季已經儼然有創下最高溫的趨勢。天空清朗,沙子已觸手溫熱。每年的這一天總是酷熱難當。
沙丘上闢建的小徑以及遊客踩出來的小路棋盤交錯,但是彼特什麼路也不管,只抄最快的路線回到馬路上。他的腳陷入沙丘的棱線,躍過凹洞,衝過羽扇豆叢,最後他喘得跟狗一樣,來到了傑斯.哈畢吉的門前。傑斯的爸叫比爾,是高級警官;幾分鐘後他就會快跑在彼特後面,穿著褪色的短褲,鞋帶鞭打著腳踝,隨手從曬衣繩上拽下來披上的白襯衫隨風翻飛。
「像一隻白色大信天翁。」這是多年後彼特的形容。「我記得他一躍而過最後一個沙丘,我還以為他要飛上天了。我當時可能嚇傻了。」
我們經常談論前天晚上浪有多大。倒不是暴風雨的關係,只是大潮,浪頭比平常要高上許多。黑暗中從南太平洋翻翻滾滾而來,一波一波湧上高峰,再一波一波撲上沙灘,每一道波浪都有猛烈的東風為之助長聲勢。回顧起來,倒是容易看出當時看不出的重大意涵。不過在發現露西屍體的隨後幾天內,我們有好幾個人的回憶中那一夜只是躺在床上聽著海浪拍岸。我們想像著海濤逐漸侵蝕沙丘,我們的家及大海之間的唯一屏障。浪濤聲是我們生活中的環境音樂,單調宏亮,從小聽慣了,只是仍沒能完全聽而不覺。坐在教室中聽老師講課會夾雜著浪濤聲,坐在南布萊頓中學沙質的校園裡吃午餐也有海濤聲;坐在自家廚房吃飯,兄弟姐妹吱吱喳喳,也掩不住洶湧的濤聲。這是我們青澀青春期的配樂。但我們不止一個覺得露西.阿舍遇害的那天晚上躺在自己房間裡,海濤聲似乎更深沉,而且帶著哀悼。黑暗中一列無止無盡的火車駛過,受了詛咒,永遠在奔馳,卻不會有通過的一天。
彼特站在哈畢吉家門口,跟比爾.哈畢吉說早上七點半他到海邊去遛狗。他的說法不太靠得住──不說別的,彼特家並沒有養狗。稍後到警局做筆錄,彼特的說詞又變了。不過也沒人注意。沒人當彼特是嫌疑犯。我們有警方的筆錄影本,記錄上彼特宣稱他是到海邊慢跑,為橄欖球賽季鍛練身體。至少他修改過的版本經得起審查。彼特的確是十六歲以下少年組的校隊隊員,不過沒有人會選年底的時候就開始鍛練,即使是國家代表隊「黑衫軍」只怕都不會在聖誕節前四天清晨七點半到沙灘去跑步。
幾天之後彼特跟我們承認了,他到沙丘去其實是要拿回他從他哥哥那裡偷來的《閣樓》雜誌。他哥哥東尼再過幾個月就要去當海軍,從沙嘴以及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彼特把雜誌藏在一個金屬工具盒裡,埋在一處天然的階梯形沙丘下。此外他還藏了一條從露西家的乳品店偷來的牛奶巧克力和一些防曬油。那地方四周長滿了高大的羽扇豆,不熟地形的人幾乎找不到,除非是誤打誤撞。我們有些人會用那裡當集合地點,不過那天早上只有彼特一個人。
那他又為什麼爬到沙丘頂上呢?我們問了彼特,他說他也不知道,他就是想看看。看海浪?看朝陽?看一大早就來衝浪的人像黑色海豹划著衝浪板趕上浪頭?他聳聳肩。顯然就只是看看。
反正情況就是這樣:十五歲的彼特滿腦子是不著邊際的幻想,爬到了沙丘頂,跋涉過草叢和羽扇豆,眺望著荒涼的沙灘。大潮改變了沙子的位置,和以前一樣,所以彼特看到的風景跟他上一次看到的微微不同。
「你當時是以為她在做什麼?」(底下摘自警方的筆錄。)
「我以為她是在做日光浴。」
「早晨七點半?」
然後彼特跟警察說了一句至理名言,恐怕大多數人都想不到他會說出這麼有智慧的話。「你如果十五歲,看到一個光溜溜的女生躺在沙灘上,你的腦袋就會變成漿糊。我真的以為她在做日光浴。」
露西微微側躺,頭轉向另一邊,彼特看不到她的臉,所以才沒認出她來。她的右肩右臂半埋在沙裡,但彼特一開始沒看出來。她的頭就在大潮線下,那裡的沙浸了水,比較暗,和覆著草叢及蕪蔓的羽扇豆的沙丘相接。她的手腳微微向外伸張──隔天早晨的報紙頭版上有記者以「箕張如海星」來形容她(並不正確)。兩條腿裡有一條更朝下伸展,彷彿她是要用腳趾去點海水,測試水溫,動作卻永遠靜止了。
彼特從制高點能看見她日曬過的雙腿,圓翹的臀部,然後曲線急轉直下,收束到她的纖腰。對,沒錯,她的臀溝和飽滿的臀。在此之前,彼特壓根不可能在活生生的女人身上看過(嚴格來說,至今也不曾見過)。還有她的背。露西會游泳,也是救生員,她的背很寬,微微有雀斑,但是彼特認不出露西的背部。彼特到現在仍不知道他看見的是誰。
好,我們暫時不管筆錄和警方的報告,就憑臆測好了。對彼特而言,沙灘上的女人必定像是他的夢中情人下凡。無名無姓,一絲不掛躺在雪亮的晨光下;簡直是他哥哥的雜誌上的美女活了過來,只為了滿足他的欲望。這種想法應該跟彼特腦袋裡轉的念頭相差無幾(別忘了他十五歲);或者,他想像的也可能是更香艷的畫面。就算在心蕩神馳的頭幾分鐘裡,彼特.馬歇爾想到的是美人魚,或是亞特蘭提斯遭放逐的女兒,他也沒說出來。當然不會跟警察說,連我們他都瞞住了。
彼特一直到小心翼翼接近才看見女人的左臂斑駁的奇怪。再靠近幾步,他發覺她的皮膚似乎鬆垮垮的,跟她游泳選手似的寬肩不太搭。她的頭髮亂七八糟,夾纏著一根指骨似的泛白漂流木。根據驗屍官的記錄(證物五),露西.阿舍在被海水沖上岸之前落水約五小時。從屍體上可判斷她的身體被壓在波浪下,不斷撞擊海床。彼特跟警察說他再走近幾步,就看出她的頭躺在沙灘上的角度「怪怪的」。
警方的攝影師拍了一張照片(證物七),可以看見沙上有一枚腳印差不多碰到露西伸長的手。那隻手掌心朝上,手指微曲,好似握著一個球,只是不知在晚上的何時被海洋掰走了。腳印是匡威球鞋留下的,是那種帆布籃球鞋,腳踝的位置會有藍色或紅色的星。那些日子我們大家都穿。不過彼特只說他靠得夠近,看出了女人是露西.阿舍。她的頸子上有一圈瘀血,是那個在晚上強暴她又勒死她,再把她的屍體拋入深海的人留下的印記。
那時彼特「嚇得剉賽」,轉身就跑,奔過沙丘,去找傑斯.哈畢吉的老爸,而老哈畢吉很快就像隻大白鳥飛掠過沙地。
沙嘴從新布萊頓郊區的沙灘向海中延伸,走到沙嘴上一路向南直到弄濕雙腳,就算遇到它的邊界了。這是一條乾燥的帶狀沙地,最寬的地方也不過一公里。走到中間,木馬街就像一條暗色的血管穿過。沙嘴的一邊是幾千公里的冰冷南太平洋,另一邊是亞芳河與希斯叩特河沖積而出的河口;三面環水,一天有兩次潮汐,沙子也時時在變動。
其實新布萊頓整個被水隔離開來。亞芳河順著海岸流淌,最後匯入河口,類似護城河。新布萊頓彷彿遺世獨立,像另一個市鎮。那何必在這裡定居?這是一般人的想法。城裡有比沙嘴交通更發達、景色更優美的地方可以居住,還有許多地方不會忽視聖經的教誨,把自家的房子蓋在沙子上。總是有人喃喃預言只要智利發生大地震,一定會有海嘯淹沒這裡。同樣一批人也老是說海岸線侵蝕嚴重,不出半年,沙丘就會消失殆盡。他們說遲早我們所有人的家都會被沖進大海裡。
不錯,在我們這邊土壤只是薄薄的一層粉飾。草叢、朱蕉、耐寒的亞麻實在不算園藝植物,可是花園裡只有這些種得活。而且還有東風。這也是大部分人不喜歡沙嘴的原因。大部分的日子裡東風在早晨剛過一半就會吹起來,吹來海上的寒氣。東風把鹽粒吹撒在我們的房屋上,就算是新車也不出幾年就會生鏽。窗戶一年到頭都結著霜。風勢大作的話,沙灘上的沙子會積到足踝深,打痛了我們的腿,把沙丘噴成軟軟的形狀。當地人都管這種風叫「懶骨頭風」。我們這裡流傳一個笑話:東風實在太懶得到處吹了,所以就直接從你身上穿過去。
新布萊頓是工人階級聚集的地區,大家都把汽車殘骸和做了一半的船放在屋子前面,一放就是幾年,像是隨時都要翻修。我們的爸爸不是黑手就是建築工,不是屠夫就是市府的雇工,要不就是在碼頭當裝卸工人。他們是開垃圾車或造馬路的人。這些腳踏實地的人工作時把收音機開得震天響,夏天聽現場轉播的板球,到了冬天就皈依橄欖球。
我們的爸爸大多是土生土長的新布萊頓人,也和我們一樣,對於沙土在家中地毯上堆積、堵塞住吸塵器、累聚在鋁窗軌道上,都習以為常。他們甚至也聽不見棲息在屋外曬衣繩上的海鷗憤怒地吼叫,看不到海鳥在他們妻子辛苦洗好的床單上拉了一條條的白色糞便。他們不是娶布萊頓長大的女孩,就是娶願意嫁雞隨雞的女人。
那些日子裡沙嘴變成了動人的不動產,許多房屋之間出現了新的建築。許多大的地段會在側面鋪一條車道,在後面蓋一兩棟樓房。不過在一九八○年木馬街的兩側大概還只是一排的老房子,每一棟屋子都有一塊相當大的院子。靠海這邊的房子大多沒有後院籬笆,所以沙丘和後院的界線完全是隨你說了算。空地也不少,雜草叢生,偶爾會長出一株松樹,而半流浪的家貓則讓野兔的數量不致失控。
露西.阿舍也跟我們一樣念南布萊頓中學,不過她是高年級的,十七歲了,而且在她死前三週已經畢業了。她父母開的乳品店就在木馬街的前四分之三段上,阿舍一家就住在店鋪的後面。阿舍家有兩個女兒,露西還有一個妹妹凱若琳,比我們低一個年級,以前叫四年級,不過凱若琳既不漂亮又不會運動,所以在我們眼裡跟隱形人差不多。
露西總是在放學後和週末到店裡幫忙,我們也常幫爸媽跑腿,去買個牛奶麵包報紙什麼的。我們自己則買白色小袋子裝的牛奶瓶形狀的QQ糖,佳發蛋糕,八角味車輪糖和棒棒糖。我們用吸管吸果汁粉泡的果汁,夏天就買甜筒冰淇淋,阿舍太太有八種口味供我們挑選。我們用瓶裝可樂把東西沖下肚,如果想要健康一點,就喝調味乳。我們差不多每天都會看到露西.阿舍,不過我們對她並不會多加注意,就像我們不會去注意父母臉上的紋路增加了,或是我們出生長大的房屋是何種顏色一樣。後來我們才學到往往要等到失去了,你才會看見。
在露西的屍體被發現之後,報紙大幅報導。記者就跟流浪狗一樣在海灘來來去去,在馬路上攔下我們,問我們是否認識露西,她是哪一種女生。偶爾我們能在報上讀到我們被歸為「好友」或是「被害人的同學」。隨口說的話變成白紙黑字看來怪怪的,很少會跟我們認為我們說的話一樣。當然那些描述露西的話跟我們每天在學校或是乳品店裡看到的露西連邊都沾不上。
有一張相片是《媒體報》和《晚星報》最愛用的。是夏天拍的,露西仍然是六年級的學生。照片中的露西站在衝浪俱樂部外,舉著小小的獎杯,她剛贏得了全省沙灘競跑的冠軍。她穿著一套紅色泳裝,左肩上沾了一塊濕沙。照片只拍到她的腰部以上。她的膚色深褐,面帶笑容,兩手捧著銀色獎杯伸向攝影機,彷彿是要送給攝影師。她的頭髮是淺棕色的,曬了太多陽光,所以比冬天顯得更淡一些(後來我們才知道她每晚就寢前會擠檸檬汁到頭髮上,想讓髮色變淡)。她有棕色的眼眸,嘴巴很寬,幾乎像美國人。雖然長得不錯,露西卻不是什麼大美女,除非是你跟她混熟了,了解她的內在美。
獎杯還在,只可惜那一年弄壞了,一直沒送修。露西死後一個月,獎杯丟進了阿舍家的垃圾裡,就丟在最上層,被塔格.嘉迪納發現了,他是送報生,阿舍家也在他的路線上。獎杯是為鼓勵運動而製作的,不過無論是誰買的都一定認為也很適合拿來當作十七歲以下女子沙灘競跑的獎品,因為基座上的雕像是一個銀色女生跑到終點,低頭向前,雙臂向後甩,胸前披著終點線的繩子。顯然這個獎杯還沒有重要到把露西的名字鐫上去,可是除了她沒有別人了──當然也因為獎杯和照片裡的那個一模一樣。
整體來看,露西的這張相片拍得很棒。我們寧願這麼想:換作別的情況,露西會很樂意看到相片刊登在那麼多報紙上。
那年夏天,天氣從進十一月就一直炎熱。等到露西.阿舍被殺害,已經沒有人再談什麼完美的夏天了;人人都在哀嘆乾旱。學期尚未結束,沙嘴僅有的一點點草皮也變黃枯萎了,乾死的草葉最後被東風吹散,飄落在河口的水面上。只有朱蕉似乎仍欣欣向榮,而且在十月底開出茂盛的白花,預測了漫長又炎熱的日子。除此之外,萬物差不多都被太陽吸乾了生命。
但是海桐草例外地繁盛。也不知是高溫讓河口的淺水水溫升高,或是排放到河口西邊的氧化池(我們叫它大便池)裡的水,反正那一年海桐草一發不可收拾。萊姆綠,皺折邊,像滑溜溜的薯片,覆滿了河口退潮以後的幾畝泥巴地。就連最深的水道都可能會被海桐草堵塞,水裡的氧氣也被吸光了。水面能見到死亡的比目魚和鯡魚。新的警告牌立了起來,告誡大家不要吃甲殼類海產。
有人投書到報紙,痛責議會對河口開發不當,對於海桐草蔓延,各式各樣的論點也出爐了,但我們只知道臭氣熏天。在晝夜都炎熱的時候,臭味低懸在沙嘴上方。那年夏天河口退潮後的悶濁空氣迷漫,是腐敗的海桐草混上了泥巴,死魚,以及晚上螃蟹大軍你搶我奪的屍體的味道。我們躺在床上想著露西,臭味鑽進了我們的鼻孔。有些晚上實在太臭了,連嘴巴裡都有味道,害我們食不下嚥,晚上也睡不安穩。
我們有的會在晚上在鼻孔下擦薄荷膏。我們被包圍在幼年生病的氣味中入睡,又回到了我們的母親把我們緊緊塞在被窩裡,喃喃念著安慰的咒語,祈求我們的高燒消退的時光。那段時光,十五歲的我們還能夠清楚記憶,只是沒能全然了解它已經一去不復回。
一個少女的死,讓一群少年開始探索成人世界的陰暗面,他們發現有一種自己不能理解的暴力和殘酷,來自遙遠的陌生人、親近的父執輩、甚至是自己內心深處。然而,那時候他們還不知道,自己即將失去人生中最珍貴的東西……
是彼特.馬歇爾在海邊發現了露西赤裸的身體,就在木馬街的盡頭附近。此後,將近三十年過去了,二十世紀也即將告終,可是我們還是能把露西躺的位置分毫不差地指出來。她的身體就在沙丘腳下,被滿潮送了上來,很靠近警告牌。警告牌上提醒民眾有激流,不要在河口銜接大海,也就是沙嘴盡頭的深水道中游泳。打從一開始,實事就明擺在眼前,殺死露西.阿舍的不是這些庸俗平常的危險。
那是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週日,再四天就是聖誕節。清晨七點半。今年夏季已經儼然有創下最高溫的趨勢。天空清朗,沙子已觸手溫熱。每年的這一天總是酷熱難...
推薦序
從世界彼端飛行而來的美麗巧合
──中文版《夏日死亡紀事》的身世
圖書版權經紀人/譚光磊
二○一三年五月,我受邀參加奧克蘭作家節的國際交流活動,搭機飛往紐西蘭。這個活動有個很好聽的名字,叫做 Flying Friends(當然後面一定要加上毛利語版的 Te Manu Ka Tau)。確實,對紐西蘭這個遺世獨立的國度來說,任何來訪的朋友,恐怕都得千里迢迢、飛度重洋,才能來到這個美麗之地。
在當天的歡迎晚宴上,我得知這次受邀參加活動的一共有四人,除了我和愛米粒出版的莊靜君,還有一對德國老夫婦,史蒂芬.維朵和他的妻子芭芭拉,兩人共同經營一間小而美的「維朵出版社」(Weidle Verlag),是,而他們之所以受邀來奧克蘭,是因為出版了卡爾.尼克森的小說《夏日死亡紀事》德文版。
聊著聊著,話題當然不免轉到卡爾.尼克森這位紐西蘭作家身上。史蒂芬娓娓道來他是如何審慎評估之後簽下版權,自己動手翻譯,趕在二○一二 年法蘭克福書展之前推出。那年紐西蘭正好是主題國,他們還特別請尼克森去德國宣傳,這次到紐西蘭,夫妻倆還提早到南島的基督城去找他,再北上參加作家節。
史蒂芬原本是把《夏日死亡紀事》當成文學小說出版,沒想到幾位犯罪推理小說的部落客讀了以後非常喜歡,口碑不脛而走,結果在犯罪小說圈裡引起轟動,後來還有大出版社用高價買下平裝版權。一本文學小說居然被當成推理小說讀,也真是夠神奇的了。
在奧克蘭最後一天,我沒有任何特定行程,搭的又是晚班機,便獨自在市區晃蕩。我找了家海邊的咖啡館,坐在白得刺眼的天光下,一邊吃新鮮的炸魚薯條配葡萄柚汁,一邊翻開了《夏日死亡紀事》。我從白天看到晚上,換了兩間咖啡館,等計程車來接的時候坐在旅館大廳裡看,等登機的時候坐在貴賓室裡看,就這樣一口氣在午夜之前讀完了這本書。
這本二百四十頁的小說看似輕薄短小,卻承載了複雜厚實的情感和憂傷。故事設定在一九八○年代的紐西蘭小鎮,一個炎熱的夏天,美麗少女露西被人發現陳屍沙灘上,她的死亡使得小鎮的生活從此不再平靜。
這是一個懷舊的故事,也是一群少年的成長故事,更是一個未解謀殺謎團的推理故事。最讓人耳目一新的是,卡爾.尼克森竟採用了第一人稱複數的敘事口吻,這個「我們」是一群十來歲的少年,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但都曾經為露西著迷,為她的死亡哀嘆而且抱屈,發誓要找出兇手。他們歷經了一九八一年炎熱的耶誕節(是的,我們別忘了紐西蘭位於南半球,所以他們的「夏天」是我們的冬天),小鎮上因為露西死亡而呼之欲出的種種祕密,還有透過電視機和廣播傳來的、外在世界的種種災荒或動盪。
幾十年過去,這群男孩早已長大而且老去,有人成家立業,有人依然獨身,但他們彷彿一個歃血為盟的秘密組織,仍然利用每一次假期的空檔齊聚一堂,耙梳他們日積月累的剪報與「證物」,反覆檢視一個又一個的假設與嫌犯。他們或許永遠不會知道誰殺死露西,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無人記得露西死亡之前的事情。他們的記憶始於她生命的終結,一個年輕美好生命的殞落,形塑了一整個世代的共同記憶與人生。
《夏日死亡紀事》讓我想起《神祕森林》和澳洲作家的戴朗.威廉斯(Darren Williams)的《天使岩》(Angel Rock),某種程度上,你甚至可說這是紐西蘭推理版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在這個版本的泛黃回憶中女神不再,但年輕的男孩依舊燃燒著青春的烈火,為她前仆後繼,哪怕只是將關於她的片段銘刻於記憶,用一輩子來溫存……。
回到台灣之後,我馬上給紐西蘭出版社寫信,說我非常喜歡這本書,想要代理中文版權,奈何他們的版權皆交給澳洲藍燈書屋處理,我完全使不上力。
想不到半年後的法蘭克福書展,我和維朵夫婦又相約到紐西蘭的攤位聚首,在拿取自助式早餐的人群之中,我遇見了卡爾.尼克森。更不可思議的是,他告訴我自己正在跟一位經紀人談代理事宜,而那位經紀人正是我前幾天初次見面的新客戶,西班牙Pontas經紀公司的瑪麗娜.沛瓦納(Marina Penalva)。又是半年過去。瑪麗娜正式發來《夏日死亡紀事》資料,將中文版權託付到我手上。距離我飛往奧克蘭、首次聽說卡爾.尼克森這個名字,差不多正好一年。這並不算是太漫長的等待,卻是充滿驚喜的巧合。現在,這本精彩的小說終於要與中文讀者見面了。
從世界彼端飛行而來的美麗巧合
──中文版《夏日死亡紀事》的身世
圖書版權經紀人/譚光磊
二○一三年五月,我受邀參加奧克蘭作家節的國際交流活動,搭機飛往紐西蘭。這個活動有個很好聽的名字,叫做 Flying Friends(當然後面一定要加上毛利語版的 Te Manu Ka Tau)。確實,對紐西蘭這個遺世獨立的國度來說,任何來訪的朋友,恐怕都得千里迢迢、飛度重洋,才能來到這個美麗之地。
在當天的歡迎晚宴上,我得知這次受邀參加活動的一共有四人,除了我和愛米粒出版的莊靜君,還有一對德國老夫婦,史蒂芬.維朵和他的妻子芭芭拉,兩人共...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