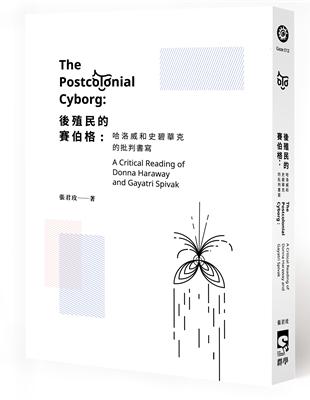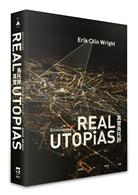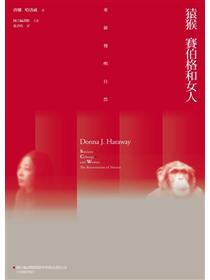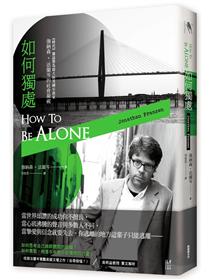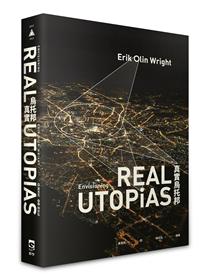身為後殖民的賽伯格,
島嶼破碎的主體性需要不斷的跨越與重構。本書從界線、批判、抵抗這三條交互纏繞的向度去貫穿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思想,分別就知識的基礎、倫理的可能以及行動的方向,去釐清共同生活的多重意義。
導論勾勒了本書的問題意識與具體計劃。第二章檢視兩位學者的批判意象,每一個批判意象都同時是行動的意向,涉及了界線協商、衝突、呈現與體現的多重權力鬥爭。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別深入檢視兩位思想家的批判方法論,及其深層的世界圖像與行動意義。第五章結論則指出,在兩位思想家看似各有領域的思考軸線中,可以找到共通的實踐取向分別展現在她們差異的發言位置。
這個共同基礎是蘊藏在她們批判方法論中的對於強權與現狀的抵抗。這樣的抵抗表現在很多層面,其中必然也涉及對界線的重新思考、跨越與打造,此為兩位思想家共同指出的當代倫理責任。同時,她們之間的差異所在依然重要,尤其是各自迥異的發言位置所揭示的故事、隱喻和矛盾。此外,在所有的閱讀計畫中,我們都必須去尋找並建構自己賴以生存、思考與行動的語言。
英文簡介:
This book discusses Donna Haraway’s and Gayatri Spivak’s theories from three interweaving dimensions of boundary, critique and resistance, and explores the meaning of living together in terms of the basis of knowledges, the possibility of ethics and the future of actions.
The introduction provides an outline of the book as a whole. The second chapter examines the critical images in Haraway’s and Spivak’s works. These images imply particular intentions of action and the relevant power struggles about boundary negotiations, conflicts, representations and embodiments. Chapter 3 and 4 investigate respectively Haraway’s and Spivak’s methodologies of critique, and the underlying world images and their agential significance. The conclusion chapter points out that these two thinkers share some common orientations based respectively on their different positions of enunciation.
Their common ground is the resistance to strong powers. The resistance is multifarious and inherent in their methodologies of critique, and involves rethinking, and reconstitution of boundaries. Their works point to the same ethical responsibility we face in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world. However, their differences are as important as their common goals. Each in her own particular existential position of enunciation reveals unique stories, metaphors and contradictions. Meanwhile, we have to construct our own discourses in every reading project. It is only through these discourses we can begin to understand our own worldly existence, and to think and act for ourselves.
作者簡介:
張君玫
張君玫,相信思考是一種行動,書寫是演化的另一條道路。研究領域包括社會學理論、後殖民論述、女性主義思想、生態理論、動物研究等,目前任職於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推薦序
理解「我們」的島嶼經驗/成令方
你/妳說你/妳是台灣人,你/妳愛台灣。你/妳理解「台灣人」嗎?我想你/妳若理解得越深刻,就越知道可以如何「愛」台灣了。
我來自中國移民家庭的背景,作為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承受全球爆炸的商品資本主義資訊,參與凝聚台灣的認同,隨手使用多樣科技的日常生活,我的島嶼經驗是複數、混搭、矛盾、流動、位移、五味雜陳。我常自問,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生存者,我該如何在繽紛多彩的誘惑迷霧中,看到邊緣殘酷的現實與困境?做為社會人文的教師,我又如何與探索、渴求的青春心靈激盪出迴響,讓我們能跨越世代/性別/階級/族群的彼此看見?作為社會的改革者,我如何辭嚴色厲地批判,卻還能唱出悲憫疼惜的曲調?作為女性主義者,我如何洞視父權嚴密結構的限制,卻還能運用流動的權力在細縫中找到抵抗的能量與活水?這些問題不斷地在我的心中反覆思索,這應該是很多島嶼上生活的人們的共同經驗吧!
翻譯高手的君玫把史碧華克的後殖民文化批判理論巨作《後殖民理性批判》(2005)和哈洛威的後人類科技批判巨作《猿猴,賽伯格和女人》(2010)引介到華文世界,讓華文讀者可以一窺其深具啟發奧妙的論證。吸納融會了這二位學術巨靈的思想養分,君玫以台灣島嶼女人的立場,思考身為後殖民的主體,也是科技科學的主體,在這兩個並存的樣態與處境中來回對話思索,完成這本《後殖民的賽伯格》。
君玫討論史碧華克和哈洛威的思想,讓我特喜歡的是著重在她們批判與實踐的意義:「對我而言,這並非單純的所謂『理論應用』。實際上,我始終主張理論的動態思考並不是關於拿一個理論來應用到現實,而在於回歸到活生生的生存處境:誰在思考,在哪裡思考,如何思考,如何生活,如何在生活中思考,並在思考中改變生活。」君玫的書寫,讓我有故知新解茅塞頓開的喜悅。原來就是這樣,人可以生猛地活在分裂混雜的矛盾中,而且可以藉由不斷思考我們身處的界線/戒限,來批判,來抵抗,逐漸地我們生活在改變中。
這本書沿著三條交織的主軸「界線、批判、抵抗」帶領我們理解,耙梳史碧華克和哈洛威的思想。我認為跨界是重要的能力,可以讓我們看見彼此的差異,是實踐批判與抵抗的基礎,我想以生活中的例子來說明。
二〇一六年五二〇那天小英總統就職典禮,總統府外慶祝大會,最後全體觀禮者與蔡英文總統和陳建仁副總統合唱當年被政府視為宣揚台獨理念而被禁唱的《美麗島》。「原住民族青年陣線」則在臉書上吐槽,批評《美麗島》歌詞中仍展現漢民族中心主義:「從國民黨『大中國史觀』到民進黨『台灣人史觀』,原住民族跟著你們『篳路藍縷』,我們就『顛沛流離』;你說這是美麗島,啟的都是我們的山林」。
這首歌曾經凝聚了部份「台灣漢人」的認同,挑戰了「嚴懲台獨」的界線/戒限,但輕忽了「原住民主體認同」。換言之,島嶼人民在凝聚「認同」的過程形成了界線/戒限與界線/戒限之間的衝突與矛盾。日常生活中,我們可能接受某些主流的論述,而邊緣論述也呼喚著我們的邊緣生活經驗。史碧華克認為這些邊緣論述彼此是「不可化約的」,例如:「獨立建國」的論述不能凌駕於「多元成家」、「環保」或「動物權」論述之上,而是彼此同時並存彼此競逐。「不可化約的邊緣」,可以讓參與其中的個人認識其他身為邊緣、他者、從屬者、被壓迫者、被殖民者的處境。這樣可以擺脫容易造成分裂的「本質論」,理解認同的界線是可以隨著社會改變而轉移的,也因為有踏實的生活經驗為基礎,個人不會落入虛無主義。當每一個人看見彼此的生活處境,他/她就能培養出文化解釋的能力,也培養出對社會權力批判的能力。
要能夠看見,就需要有觀看的位置,觀看的人站在特定的物質位置上,採用特定的儀器、工具、組裝,透過具體的感知中介,例如:身體、概念、價值、影象,才得以完成(這裡就帶出哈洛威的「賽伯格」的意象)。例如:作為女人,女性主義論述經由視覺化的科技,書本、電影,號召出我的一些女性在父權體制壓迫下的經驗,讓我認知到父權的宰制與壓迫,也經由視覺化的科技,例如:紀錄片、書籍、電子郵件、臉書貼文,認識了勞動女性與慰安婦,讓我得以我的身體去想像勞動者的困境,體認日本殖民時代作為性奴隸的處境。逐漸地我理解作為中產女性與勞動女性生活經驗的界線/戒限,也對日本殖民體制有更深刻的理解。作為人文社會的教師,我在課堂中也不斷以此方式引導同學,去跨越世代、性別、族群與階級去看見其他的弱勢者。
這樣的知識用哈洛威的說法,是具有部分客觀性的處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s)。藉由處境知識的獲得,我們看到自己和他人都擁有多重認同與生活經驗,也理解多重認同彼此的界線/戒限,有了理解與體認,內在的謙虛逐漸發酵,就不會以某一論述去霸凌或化約另一論述。哈洛威建議,弱勢的團體可以透過彼此的親近性(affinity),而非認同來結盟。於是島嶼上邊緣弱勢的處境,逐漸成為部份的「我們」共同理解的處境。
要在島嶼上互相看見「我們」,除了上述的路徑外,哈洛威提出的賽伯格意象,可以讓我們更加意識到「我們」作為科技島的特色。哈洛威認為「賽伯格是我們的存有論」。戰後的台灣積極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政府投入大量的金錢與土地協助台塑發展石化工業,以及後來的電子科學園區。石化產品是每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都會使用的,電子科技成為島嶼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加上近二十多年來人們常用的生物科技產品(例如:健康食品、醫療輔具、各類藥品),這是我們存在的客觀事實。我們就是賽伯格。然而,島嶼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製造河川、土壤與空氣的污染之上,是建立在砍伐森林、改變河床、剝削自然之上,是建立在壓榨工程師、勞工的健康之上,是建立在過度醫療化之上。二十世紀中期逐漸沸騰的動物權論述指出,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完全否定動物生命的價值,這是最殘忍的事實。哈洛威批判獨尊人類的思想,指出一個改變的方向:人類的存在需要轉向理解人與非人(科技與動物)的關係。換言之,科技島嶼的住民需要思考科技發展與大自然的關係,放下以人獨尊的觀看位置,重新思索、批判,尋找永續生息之路,讓科技發展減少污染,無須過度破壞自然也無須過度壓榨參與的勞工。在過程中,每一個「我」逐漸改變,於是「我們」在改變中,這島嶼也逐漸在改變中。
當每一個台灣人能夠跨界看見其他生活在這島嶼上的弱勢者、動物、科技與我們的關係,當思想轉變成行動,這行動中必然產生一些批判與抵抗,於是在這轉動的能量中,我們每個人混搭的生活經驗與認同也擴展、越界、舊的矛盾消失在新的矛盾中。作為島嶼住民的「我們」,可以珍惜島嶼上的住民和多重行動者(包括人與動物、科技的關係)共構的世界,「我們」就更認識「台灣人」,更會愛台灣了。
作者現為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推薦序
富裕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貧窮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林明仁
托爾斯泰在鉅著《安娜‧卡列尼娜》的開場白說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讓我借用文豪的邏輯,將其改寫為:「富裕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貧窮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本書兩位作者 Banerjee 與 Duflo 過去二十年來致力瞭解窮人如何落至如此不幸的境地,以及有哪些可能的解決政策。更重要的是,他們發展出一套以隨機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為主軸的評估方法,更讓我們對貧窮的瞭解,從理論層次進步到有可以與理論對話的實證基礎。這本《窮人的經濟學》,就是他們研究結果的非技術介紹(non-technical summary),也是貧窮研究的必讀入門書。
如何定義窮人?對台灣的讀者來說,我們可能會覺得月薪 22K,付完房租、 餐費跟其他必要開支後,只剩下幾千元,應該就屬於吃土魯蛇一族了。但如果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這還算是中等收入:二○一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ngus Deaton 從購買力平價的角度出發,計算出貧窮線應為每日支出低於 1 塊美金(房租除外)!這筆大約一個御飯糰的錢,在印度大概可以買 15 根小香蕉。而在這麼低的標準下,全世界仍然有超過 10% 的人每日生活費是低於這個數目!因此本書主要聚焦的,不是每日生活費仍有 20 塊美金的已開發國家低所得工作者,而是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在生存邊緣掙扎,真正窮苦的人們。
有人類以來就有窮人。考古遺址中有許多精緻飾品陪葬的,就是當時的富人,只有少許器物的家境較差。而最窮的人,恐怕早就因為被草草埋葬而無法在現代被挖掘出來了。由於缺乏資源與權力,窮人在歷史的記載中一向不受重視(通常是以飢民的型態出現),所以文學作品就成了我們對貧窮者生命歷程的重要來源。然而,不論是關漢卿筆下說出:「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的竇娥,或者是在雨果的《悲慘世界》因偷竊一塊麵包而被判刑十九年的尚萬強,雖然讓我們感動、同情,且因自己無力對他們作些什麼而感到自責,但也容易讓我們選擇了一個簡單的看法與解方:將貧窮怪罪於財團的貪婪、政府的無能、以及資本主義的弊病。彷彿只要打倒惡魔黨,美麗新世界就會來臨。另一個極端,則是認為窮人之所以淪落到這步田地,都是因為他們懶惰、不投資自己的人力資本、愛冒風險所以生意容易失敗、個性不愛與人交際、當街友反而更自由自在的緣故。因此一切都是他們咎由自取,與社會結構無關。
隨著這些簡化的誤解與歸因而來的,是簡化的解答。而兩位作者認為,這其實就是人類社會在對抗貧窮上面遲遲無法取得進展的最主要原因。窮人雖然擁有的東西不多,但這並不代表他們的生活不複雜有趣;事實可能正好相反:就是因為手頭拮据,所以窮人們必需更像個斤斤計較的經濟學家才能生存下來。許多在一般人眼裡微不足道的制度調整、社會改變,或自己所犯的錯誤,都會對窮人造成很大的影響。從這個角度切入,每一個選擇對窮人來說都是關鍵。
因此,對抗貧窮的政策比起其他領域的公共政策來說,更需要跨領域的討論、審慎的評估與精確的測量。Banerjee 與 Duflo 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可說是無人能出其右。兩人全面的瞭解窮人在家庭、經濟與政治生活上所面臨的各種挑戰(經濟學家稱此為制度性細節〔institutional details〕),以及使用經濟學與其他學科如心理學等的概念來建構理論,收集可以衡量這些因果關係的變數資料(是的,沒有測量,就沒有科學),並且有系統的使用科學方法(主要使用的是 RCT 及其他應用個體經濟學常用的分析工具,如工具變數、差異中的差異、以及回歸不連續)等,作者兩人在以上各層面都有非常大的貢獻。而他們將所有制度細節、理論、資料、計量方法、以及面訪所得的結果加以消化並整合出一個體系的功力,在這十幾年來累積的研究成果與對政策的影響力上展露無遺,堪稱經濟學家入世的最佳典範。
我在此就以第七章〈來自喀布爾的男人與印度太監:窮人貸款的簡單(不簡單)經濟學〉為例,介紹他們的分析手法。在印度,窮人們作小生意的生財器具都是租來的,可是只要把每天的租金存下來,幾個禮拜就可以買到好幾台推車!但為什麼沒人這樣做?這些人的回答是:「除了高利貸業者,沒人願意借錢給我!」為了幫助這些人,經濟學家 Yunus 創建了孟加拉鄉村銀行,以微型信貸給因貧窮而無法獲得傳統銀行貸款的創業者,以改善他們因流動性限制(liquidity constraint)而無法翻身的問題,他也因此獲得二○○六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不過這個有理想有熱情的經濟學者入世拯救窮人的感人故事背後,存在一個巨大的問題:微型信貸到底有沒有用?當二○○二年 Banerjee 與 Duflo 對這些微型信貸機構提出這個問題時,這些人的第一個反應是:「為什麼我們要像賣水果的攤販一樣接受評估?」接著他們提出一些經由微型信貸翻身的窮人當作例子,並且提到人們也會一直來借錢就是最好的證據。最後再很熱血的說:「我們是熱心奉獻的非營利組織,而且堅信小額信貸是幫助窮人最好的方式!」可是這些人忘了,微型信貸接受了非常多的政策補貼,而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果微型信貸沒用,那麼政府的補貼不是就該移到別處嗎?
兩位作者最後終於說服了其中一家最賺錢的微型信貸,讓他們以前述的 RCT 作實驗,結果如下:在隨機設立據點的社區中,人們創業的比例的確增加了,但只是從 5% 增加到 7% 而已。兩位作者認為雖然效果不大,但小額信貸應該已經站上正確的位置。不過必須注意的是:此一政策的重點,不在於借到錢的機率是否增加,而是較容易借到錢之後,對這些窮人的生活產生了什麼樣的改變。接下來就有非常多的學者使用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地區評估微型信貸的影響。
Duflo 主編的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在二○一五年第一期就刊出了地區涵蓋波士尼亞、衣索比亞、印度、墨西哥、摩洛哥以及蒙古,時間從二○○三到二○一二年的研究成果。這幾篇研究基本上都指向相同的結論:微型信貸的確增加借到錢的機率(take up rate),但是效果普通(modest〔大約 20% 左右〕),這些家庭參與的商業活動也增加了(這表示借到的錢有投入在生意上)。但是比較麻煩的是,即便可以借到錢作生意,然而這六篇研究都無法找到微型信貸可以提高窮人家庭所得的證據!不過幾個研究倒是發現微型信貸儘管增加了商業所得,卻減少了家庭的薪資所得(整體所得效果相互抵銷)。所以 Banerjee 把這些結果詮釋成:「至少讓人們獲得更多在職業上選擇的自由(it does afford people more freedom in their choices e.g., of occupation)」, 但是家庭消費沒有增加,而長期投資也沒有改善(例如小孩教育、健康、女性自主權等)。因此作者的結論是:微型信貸的確有些許的直接效果(指借到錢的機率增加),但是借到錢之後的生活並未有太大不同(modestly positive but not transformative effect)。
讀者或許會覺得訝異。這不是諾貝爾獎等級的努力嗎?怎麼會跟在報章雜誌看到有許多窮人靠著微型信貸翻身的報導大不相同?應該是學者專家找到了好的方法,打倒了放高利貸的壞蛋,從此窮人們就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才對呀?藉由討論借錢給窮人的風險,作者在第七章花了很大篇幅來解決這個疑惑。其實最主要的問題來自於資訊不對稱:對無法提供擔保品的窮人來說,事前評估還款可能與事後經常追討的成本實在太大了(所以才需要靠可怕又殘忍的喀布爾男人, 還有露下體給你看,讓你一輩子倒楣的印度太監來恐嚇你要還款)。與可收到的利息相較,實在不成比例。微型信貸的創意在於利用透過團體互保,對其他人的借款負責來減低交易成本,但結果卻是有限(我的看法是,如果借錢給窮人真有那麼大的後續利益,市場一定會找出一個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本書其他討論營養、健康、教育等章節,閱讀起來也跟微型信貸這章有相同的感覺:作者指出一些貧窮理論,觀察某些依照這些理論所提出的作法其效果如何,結果卻是離全面根除貧窮還有一段距離,烏雲後的光(silver lining)似乎是對此一情況最好的描述。就如同 Banerjee 對上述六個研究所做的評論:「這些研究提供了微型信貸並非貧窮疾病萬能藥的初步證據(which is a prima facie case against microcredit being a panacea〔a cure-all〕in the literal sense),但是也的確產生了微小的效果。」
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作者討論了他們看待貧窮的方法,以及其所提出的解方與其他學者的異同。在發展經濟學的領域裡,許多人強調大制度的重要:如紐約大學的 William Easterly 就認為,只要釐清政治過程,好的政策自然到位。Acemoglu 跟 Robinson 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也論證廣義的良好制度(他們稱之為廣納型〔inclusive〕),才是國家發展的主要原因。Easterly 對於發放蚊帳這種政策相當不以為然,他甚至認為 RCT「無法處理廣泛的制度或總體政策的效果。尤有甚者,它也讓發展經濟學者降低了自己的抱負!」二○一五年諾貝爾獎得主 Angus Deaton,也從方法論上批評 RCT。認為它能釐清的只是在特定脈絡下的因果關係,無法推論到其他更一般的樣本;而現在學界也過度放大 RCT 的好處而忽略了它的缺點。這些批評,平心而論也並非沒有道理,只是改變大制度的困難度太高,雖然以管窺天是 RCT 的問題(有些批評者認為,不是打一個漆彈到牆上,就可以畫出房子的全貌),但是至少提供了檢測各種不同假設的機會。目前文獻上與 RCT 相抗衡的結構估計法(Structure method),或者是 Deaton 提倡的憤怒鳥從錯中學(Angry Bird try and error)的方法,其優缺點剛好與 RCT 相反。我想對以解貧民於倒懸之中為志向的發展經濟學家來說,我們的確不應該放棄遠大的志向與高層次的問題,但我們也不應該忽略小思考、小變革的長期影響。由下而上,有時也會帶來意外的驚喜。舉例來說與我曾經合作過的耶魯大學的錢楠筠(Nancy Qian)教授就發現,雖然中國整體民主發展水平還是很低,但是農村選舉的確讓村長更能夠不執行受地方反對的中央政策,公共支出也會更重視地方的需求!不執著於特定的方法,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以有理論基礎跟經過實證評估的作法當作改革的藍圖,一點一滴的改變現狀,說不定是改變的最有效路徑。
在 MIT 經濟系訪問時,我經常有機會在每週三的教師午餐與 Banerjee 還有 Duflo 討論研究。Banerjee 溫文儒雅,即便是面對針對自己論點的批評,也總是不疾不徐的詳細說明對立說法的異同與優缺點。Duflo 較為年輕,因此對於她認為不好的論點,總是直言不諱。當我在 MIT labor seminar 報告時,就曾被她直接批評:「你這篇論文中與醫學相關的文獻回顧已經太落伍了。」(不過她是對的!)這本書的寫作風格,其實是跟兩位作者的氣質相符的:一方面好整以暇的告訴讀者面對棘手問題時該如何思考,並且娓娓道來目前研究成果(不論是自己或是其他人的)正反意見的解釋(pros and cons),另一方面對於邏輯的推論是否嚴謹,理論與實證證據的連結是否正確,則是追根究底,毫不手軟。人書合一,其實是我最喜歡這本書的地方。閱讀這本書需要一些耐心,他不會給你 magic bullet 或快速的解決之道,而是讓你反覆思索各種方法的利弊得失,瞭解到改變不是一蹴可幾。而大部分的方法即使有用,效果也不可能太大。但是如果能從小思考著手,各個面向都能往前進步一點,加總起來的效果就會非常可觀!
林明仁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二○一二教育部頂尖大學計畫 MIT 訪問學者
名人推薦:推薦序
理解「我們」的島嶼經驗/成令方
你/妳說你/妳是台灣人,你/妳愛台灣。你/妳理解「台灣人」嗎?我想你/妳若理解得越深刻,就越知道可以如何「愛」台灣了。
我來自中國移民家庭的背景,作為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承受全球爆炸的商品資本主義資訊,參與凝聚台灣的認同,隨手使用多樣科技的日常生活,我的島嶼經驗是複數、混搭、矛盾、流動、位移、五味雜陳。我常自問,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生存者,我該如何在繽紛多彩的誘惑迷霧中,看到邊緣殘酷的現實與困境?做為社會人文的教師,我又如何與探索、渴求的青春心...
章節試閱
第三章 哈洛威:跨界的抵抗辯證
來了,來了
來了一個詞,來了
穿過黑夜而來,
想照亮,想照亮。
(策蘭,「密接和應」,孟明譯 2011: 255)
一、轉換隱喻:對呈現邏輯的批判
圖像是展演的意象,可以棲居其中。無論是言說或影像,圖像都可以是關於可爭議世界的凝縮地圖。所有的語言,包括數學語言,都是圖像的,也就是喻說所做成的,由很多突起所構成,致使我們偏離字面的理解。我強調圖像,是為了彰顯所有物質─記號的過程都無可避免具有喻說的性質,尤其在科技科學中。
─哈洛威(Haraway 1997a: 11)
本書第二章討論了史碧華克和哈洛威的批判意象與意向,以及其中所涉及的呈現與權力議題。關於怎樣的呈現(或替現、代表)才算是真正讓「從屬者」、「弱勢」、「邊緣」或「自然」得以被看見、被聽見,從來就不是抱著良善的意圖就足夠的,甚至也不是靜態客觀的認知所能確保。在肯定被壓迫者的能動力的同時,必然會影響我們正視她們所身受的壓迫或剝削嗎?其中的緊張拉鋸,是無可避免的嗎?抑或這是某種發言位置的效應?也可能是特定批判方法所造成的作用?因為,很顯然,受壓迫或被剝削,並不一定表示就沒有能動力可言,儘管行動的空間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與壓縮。同樣的,在那些優勢的生存處境中,也常有能動力乏善可陳或受到高度限縮的個體與群體。此外,能動力的展現並無法確保不會形成與體制之間的共謀關係,進而有利於維持不公不義的社會現實。更重要的是,能動力,或行動力,從來就不是「有」或「無」的存有論問題,甚至也不是如何知道誰有能動力的知識論問題,而是特定個體「如何可能」展現出能動力的政治問題,以及在怎樣的條件底下或情境之中,這樣的能動力展現可以被認為是「有效」(可以發揮某種程度與層面的影響力)的倫理問題。然而,從一個更深的層次來說,我們必須留心不要落入某種領域論的陷阱,誤認存有、知識、政治、倫理等不同分析層次的問題乃是在實質上各自不相干的。實際上正好相反,它們之間的關係是複雜曖昧且界線交錯的。但在某個意義上,我們仍然可以也必須在分析上加以區分,方能思考行動與介入的可能。同樣重要的是,在商榷或重構政治、倫理的相關問題時,我們也必然重新構造知識和存有的問題。
在史碧華克備受爭議的「從屬者不能發言」的陳述,以及哈洛威關於「實驗室動物參與勞動」的說法中,我們所看到的是,能動力,包括行動和發言,所具有的社會或政治效力並不是沒有條件的。簡言之,行動的物質條件乃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如何可能做出這些條件,很可能是一種最根本的社會改造實踐。換言之,更重要的可能不是想像中的「忠實呈現」或「如實代表」,而是展演與行動。
在這些思考中,我們必須盡量避免單純的選邊站,或僅止於浪漫化任何明顯的「弱勢」立場。在本書接下去的討論中,透過從批判意象/意向到批判方法論的探討,我想凸顯的是,我們身為文化解釋與批判者所運用的隱喻不僅是我們藉以思考的概念,也不僅是建立在我們對於社會現實的特定觀察與取用,甚至也不僅是具有研究或探討的引導力。我們的隱喻是一個種子,包裹著世界的圖像,以及我們的未來。種子需要適當的時機、土壤、氣候與其他條件,才能夠發芽成長轉化。這個生態學的比喻,對我來說是當代思想的豐饒所在,是連結我們思考和生活的有機橋樑。哈洛威的賽伯格、怪物、同伴物種,史碧華克的從屬者、土著報導人、行星性,都像是這樣的種子,提供了我們特定的世界圖像與問題意識。這些種子並不是固定或靜態的,在思考未來的方向與可能時,我們有必要去追蹤這些批判意象或隱喻角色的軌跡,才能更深刻瞭解其中的潛力與偏誤。
基本上,這兩位女性主義理論家都充份認知到隱喻的重要性。哈洛威求學階段的主修是生物學。她一直在關心科學做了什麼,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隱喻,其實是一個做思考的過程,有時候像美麗的萬花筒,有時候則像恐怖的俄羅斯輪盤。她在70年代研究胚胎學的論述建構時,就已經開始投入日後持續對科學的文化批判,或更精確地來說,對科學文化的批判,把科技科學當成一種知識敘事生產的過程來加以剖析。到最後,她真正挑戰的,乃是科技和文化之間的僵化界線,指出其中流動的權力操弄。她在博士論文《水晶、纖維,以及場域。二十世紀發展生物學的有機比喻》( Crystals, Fabrics, and Fields: Metaphors of Organicism in Twentieth-Century Developmental Biology [Embryo])中指出,「隱喻具有一種預測性的價值」,足以引導生物學家的研究往哪裡走去,因此也對「典範」具有指導方向的作用。「一個具有解釋力的隱喻乃是一個典範的生命精神」(a metaphor with explanatory power is the vital spirit of a paradigm)(Haraway 1976: 9)。她討論了二十世紀初主要的胚胎學理論,藉此探討文化裡的隱喻與相關期待,包括像是〔血液〕循環的視覺圖象,如何影響了當時的生物學研究計劃。那時候,她已經開始思考有機的界線如何維持,以及有機和機器之間如何區分。1984年出版的《泰迪熊父權體制》(Teddy Bear Patriarchy: Taxidermy in the Garden of Eden, New York City, 1908-36)討論了美國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的透視圖設計人卡爾.艾克里(Carl Akeley)如何運用槍枝、攝影機、剝製標本術等相互交纏的科技,從而建構出一種特定的現實主義敘事風格,並用肉眼觀察的立即視覺圖象去建立資料的科學權威。哈洛威指出,在科技科學的實踐與論述中,隱喻和敘事佔有核心的運作地位。換言之,它們在論述中發揮了非常具體的作用,主動引導了論述的進行,而不僅是被運用。
文學比較出身的史碧華克則特別強調很多人文學科或文化批判論述中的關鍵概念其實都是一種隱喻,或「一個文本裡的概念隱喻」。比如馬克思理論中的「價值」(Spivak 1988: 171),和女性主義裡的「女人」、「性別」等。所有的概念隱喻同時都是一種化約,相當程度簡約了原本必然是多重決定的現象,片面強調單一的因果面向。此外,這些概念隱喻往往也是一種「詞語誤用」(catachresis)或是舊名新用(paleonymy)。任何一個既定的「名」必然有特定用法的歷史,承載了許多的意象與涵義。所謂的「舊名新用」,並非單純指涉舊有命名的延用,而是一種刻意的「詞語誤用」,同時也是一種「舊名新用的邏輯」(logic of paleonymy),一種策略的必然性。也就是說,在號稱「新的」的論述策略中,往往必須保存或借用「舊的」名稱(Derrida 1982: 307-330)。在這些分析中,史碧華克標舉出書寫的策略性,就像哈洛威所強調的存活權力,亦即活下去的力量。
對我來說,在我們如何共同生活的相關思考中,最核心的概念隱喻可能就是土地,土地不僅是真實的孕育,也是觀念的聯繫,情感的牽絆。而「土地」作為一個隱喻,其實正是信念之所以能夠生根發芽的社會與物質基礎。這也是我在本書最後一章將回返的主題。
本章要探討哈洛威的社會批判理論,同時也是她對於生命與生存的看法。對哈洛威來說,生存始終是凡俗的、入世的、此生的。在她的學術實踐中,經歷了幾次很關鍵隱喻轉換,每一次轉換都代表了一種批判當時社會歷史處境的意象與視角。隱喻,是一種批判社會的方法,也是一種如何共同生活的方法。在1985年的〈賽伯格宣言〉中她的口號是「為了凡俗生存的賽伯格!」(Cyborgsforearthly survival!),到了2004年的《同伴物種宣言》(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她的口號變成「快快跑;用力咬!」(Run fast;bite hard!),然後,在2008年的《當物種相遇》(When Species Meet)以後,她告訴我們「不要逃避麻煩!」(Stay with the trouble)。無論是不帶純淨幻夢的、充滿褻瀆與歡慶、但也堅持負起重構界線責任的賽伯格凡俗生存,或是身心相繫、彼此建構、共同演化的同伴物種的跑跳咬,或是勇敢承擔多重主體混雜相處、矛盾衝突、痛苦受難的糾結關係,都是關於如何面對「我們」如何共同生活的難題。
關於「我們如何共同生活」的倫理學問題,除了顯然有政治面向之外,必然同時涉及了存有論和知識論的提問。這樣的宣稱看似簡單,尤其在大家逐漸熟悉這類交織性的詞彙之後,其實非常的複雜,並且充滿了難解的內在矛盾。但是,有矛盾並不等同於不真實或錯誤。相反的,面對與處理內在矛盾很可能正是最關鍵的任務。我們存在著、消失著,認識著、迷惑著,活著、死著,愛著、吃著,彼此。簡單來說,我們互相依賴,又彼此切割。
在當前充滿剝削、宰制、支配的全球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生命處境中,批判社會與共同生活必然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哈洛威對於「剝削」與「壓迫」有不一樣的反省。在碎裂的處境中,她傾向於強調受剝削者和被壓迫者本身的行動力,甚至因此會被批判忽略了對壓迫者的譴責,以及對優勢者行動的檢驗。她的出發點之一是對於代言政治的質疑,但更重要的是傳統「呈現」或「代表」在概念與操作上的批判。在此,我將稱之為對於「呈現邏輯」(logic of representation)的批判。哈洛威主張,我們必須留心呈現的可能陷阱,並練習更曲折的看見。
基本上,哈洛威的隱喻可以分為兩種類型,而此二者在運作上的交織也凸顯了知識和存在的密不可分。第一類是關於批判的意象,可以作為批判領航員的獨特存在物,怪物、賽伯格、同伴物種。第二種是關於批判的方法論,關於科學如何可能,以及更廣義來說,如何認識世界的途徑,衍射、內爆、花繩。意象,同時也是意向,並藉此連結了方法,從而進入世界,並和世界一起演化。換言之,批判的意象和方法並非二分,必須互相支援。哈洛威的隱喻都有一個共同點,界線的開放、混雜、拆解、重組。在談界線的問題時,開放、混雜、拆解、重組是四個必須同時並重的向度,若只有前三項,而少了持續進行的重組,也就等於放棄了最重要的基本責任:重新打造界限,也就是重新去釐清關係(relations, relationships)。而關係,正是哈洛威所說的「最小分析單位」(Haraway 2003: 24),稍後更改為「最小的可能分析模式」(the smallest patterns for analysis),因為她認為「單位」一詞會產生實體化的誤導,尤其是她始終極力在概念上排斥的自生系統論(autopoiesis)或其他有機形式的想像(Haraway 2008: 26, 313n. 31)。儘管我們可以商榷,這和她在談論同伴物種時所強調的物種特定能力(species-specific capacity)與成就(Haraway 2003: 53)之間是否造成某種抵觸。其實,哈洛威對「有機」概念的排斥是有其特定歷史意義的,主要因應美國從1950年代開始在社會學與生物學界同時崛起的結構功能論(Haraway 1991)。在當時,有機整體論所連結的政治傾向往往是保守與拒絕徹底改革的。然而,這樣的知識情況已逐漸改變。事實上,有機的界線開放乃是生物學近年來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在此我要強調的是,「有機」概念的開放與封界,如此持續不斷地辯證運動,正是哈洛威理論中的張力。這份張力不會總是均衡的,但在某些關鍵議題上,甚至會出現嚴重的失衡,比如當她的論述觸角更深入到活生生的具體動物生活時,往往忽略了有界線的生命。如何對待動物,關乎批判理論的未來。本書上一章觸及了這個議題,本章將更充分討論哈洛威的理論面貌與動向,以期藉此更深刻領會其中的兩難處境與倫理要務。
上一章探討了第一類關於批判意象的隱喻。基本上,那都在引領批判的意向時指出一個重要事實:過往的呈現邏輯已經不足以因應當代複雜的政治倫理佈局,我們必須在此之外提出更有效的發聲模式,以利社會改革的發生。當代政治倫理佈局最大的特性在於外在與內在界線的日趨模糊,但權力的支配與壓迫並未因此稍減,而以更細緻的方式深入日常生活的理路。發言位置的物質條件當然是很重要的,但在界線混雜的處境中,物質條件的釐清也變得更困難。史碧華克會用共謀來形容這樣的狀況,儘管這不必然是悲觀的,而可能召喚出更具反思性更加負起說明責任的行動能力。面對這個歷史處境,哈洛威的因應方式則是更強調「共享」。從「同伴物種」的隱喻轉向上,我們已經看到這點。無論在行動力、勞動、苦難、責任,乃至於知識建構和政治倫理的可能性上,哈洛威都主張以關係為最小的分析模式與理解脈絡。換言之,不僅必須跨越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知識論界線,也要體認到存在及其界線的浮現,乃是發生在複雜的關係與元素過程中。
這樣的知識立場,當然並不容易理解。畢竟我們大多已經習慣了啓蒙以降的知識論姿態,以一個相對來說固定位置的認識主體去掌握世界。哈洛威並沒有徹底揚棄這點,她最大的貢獻是要去釐清「位置」的物質性與複雜性,尤其在當代的科學科技政權中,或是她所說的「支配的訊息學」,以及種種重要學科界線的內爆,包括科學家用以形塑世界觀的生物學和化學,以及生物學和資訊學等等。
在1989年出版的《靈長類視線:現代科學世界中的性別、種族和自然》(The Primate Vision: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導論一開始,哈洛威引用了南非博物學家尤金.馬雷(Eugene Marais)的話指出,「因為所有事物都必須以一個愛的行動為開端。」(For thus all things must begin with an act of love.)(Haraway 1989: 1)愛、權力和科學,交織在文化對於自然的建構過程中。哈洛威後來針對1996年知名的「索卡惡作劇」(Sokal hoax)指出,索可對於「社會建構論」的批判其實是基於誤解,他認為所謂的建構論者不相信現實的存在,這並不是真的。哈洛威再度引用馬雷,強調對科學的愛是知識生產過程中的重要因素,而這適用於「科學家及其研究對象之間,還有研究科學的人及其主題之間的關係」(Haraway 1997c: 124)。她並沒有直接回應索卡等科學家對於建構論或解構的抨擊,她直言這其中有很多的情緒,報復、憤恨與惡意,在多年的「科學戰爭」(Science Wars)裡,有很多說法都像是惡作劇,很難讓人當真,雖然這樣的戰爭是很真實的(Haraway 1997c: 123)。哈洛威以自己同時身為生物學家和科學史研究者的雙重經驗出發,去回應這些所謂的科學戰爭。她指出,無論是科學,或是以科學為研究對象的探討,都是持續「製造意義」的實作,這樣的實作同時必然是歷史的,涉及到許多有著特定社會、文化、物質處境的行動者,包括人與非人的行動者,諸如「機器、有機體、人、土地、制度、金錢、分子,以及很多其他類型的事物」(Haraway 1997c: 124)。她強調,在科學知識中一直都有很多的故事,若是硬要把這些故事除去,那將是一種「知識論的避孕或科學的自虐」(epistemological contraception or scientific self-abuse)(Haraway 1997c: 126)。不僅故事重要,故事的故事更重要。換言之,故事如何被生產出來,這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社會存有論與知識論問題。就像哈洛威在〈同伴物種宣言〉中所說的,她要說的是「關於故事的故事」(Haraway 2003: 21),科學和文學在喻說中不斷流通運輸的正是故事。比如,metaplasm這個詞,在修辭學上是「詞形變化」,指的是一個字透過發音、音節和字母的增減或換位而產生改變;在生物學上則是「後生質」或「後成質」,指的是細胞裡面不屬於原生質(protoplasm)的、沒有生命的物質,因此也有譯成「副漿」。哈洛威很喜歡這類字詞的意象與隱喻,跨越學科分界,也跨越意義的限域,貌似錯誤,猶如新生。「後生質」代表「錯誤」,也就是一個轉折,而英文喻說(trope)的原意,一個關乎肉身的差異(Haraway 2003: 20-21)。
換言之,科學作為有系統的知識(此為科學一詞的原意),並不是僅止於忠實地呈現事實,而是一個不斷在進行敘事的過程,不斷透過隱喻在說故事。但這並不表示沒有「現實」存在。而只是說現實的顯露不可能是沒有中介的。另一個很重要的點是政治倫理的參與。哈洛威提到自己的教學經驗,在反越戰的年代中,他們在對非本科系學生傳授生物學相關的知識時,乃是抱著一種公民教育的使命感。這並不是說科學才是啓蒙的唯一道路,反而必須指出,科學的實作本身早已透露出知識、技術、符號、政治、物質等層面都是連結交錯的。我們所認知的世界正是如此製造得出。
生物學是一個政治論述,我們在其中必須致力於實作的每一個層次,包括技術上的、記號上的、道德上的、經濟上的、制度上的實作。除此之外,生物學也帶來了強烈的歡樂,包括知識的、情緒的、社會的和肉體上的歡樂。任何像這樣的東西,都不應該被輕易放棄,也不應該片面加以譴責或讚頌。(Haraway 1997c: 127)
第三章 哈洛威:跨界的抵抗辯證
來了,來了
來了一個詞,來了
穿過黑夜而來,
想照亮,想照亮。
(策蘭,「密接和應」,孟明譯 2011: 255)
一、轉換隱喻:對呈現邏輯的批判
圖像是展演的意象,可以棲居其中。無論是言說或影像,圖像都可以是關於可爭議世界的凝縮地圖。所有的語言,包括數學語言,都是圖像的,也就是喻說所做成的,由很多突起所構成,致使我們偏離字面的理解。我強調圖像,是為了彰顯所有物質─記號的過程都無可避免具有喻說的性質,尤其在科技科學中。
─哈洛威(Haraway 1997a: 11)
本書第二章討論...
目錄
序 理解「我們」的島嶼經驗 成令方
序 穿過詞語的黑暗去照亮 印卡
致謝辭
第一章 導論:島嶼書寫的一段理論旅程
第二章 界線/戒限:批判的意象與意向
第三章 哈洛威:跨界的抵抗辯證
第四章 史碧華克:解構的雙面受縛
第五章 結論:後殖民的賽伯格
參考書目
序 理解「我們」的島嶼經驗 成令方
序 穿過詞語的黑暗去照亮 印卡
致謝辭
第一章 導論:島嶼書寫的一段理論旅程
第二章 界線/戒限:批判的意象與意向
第三章 哈洛威:跨界的抵抗辯證
第四章 史碧華克:解構的雙面受縛
第五章 結論:後殖民的賽伯格
參考書目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