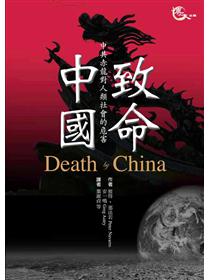生命本不是一場滯留。旅遊不僅是一場儀式。
一個街區有五間不同國家菜的餐館,
商店售賣多國產品、網上的資訊每天徑自跑進眼球。
如果說旅遊是一場內在的穿越,
看電影、讀小說、一場好好的對話、一場冥想,也能達至心靈穿越之效,
穿透力有時比起實地旅遊還要來得強烈。
那麼為何我們還要讓自己舟車勞頓,
在機場中原因不明地等待,在異地的火車站月台惶惑,
提著行李時指頭發痛?為甚麼我們還要去旅行?
當我們說去旅行,到底我們是在幹甚麼?
對我來說,旅遊是離開秩序,甚至是創造混亂。在手足無措的當兒,以及在新秩序還未被建立之前,切切實實地感到自己活著,不被安全感所麻木,腦袋變得敏感,目光變得敏銳:這是一個麵包。這是一張車票。這是今天的地圖。這是今天所迷失的路。所有東西都是一回事,懷著重量,變得真實。陌生感是我們的朋友,熟悉感也是,我們需要這兩位朋友,缺一不可;人最好別只得一位朋友。
有人說,離開是為了回來,說到像陌生感只為熟悉感而效勞一樣,並非如此,事實上,兩種感覺既獨立,也共生,出走不是為了回去,因為我們沒有回去,而是變成嶄新的自己,繼續在路上前進。
作者簡介:
卓韻芝,香港著名跨媒體創作人,暢銷作家。
她以13歲之齡參與商業電台主持工作,其後主持的個人節目,打破電台冷門時段的宿命,收聽率之高史無前例。所創作的《芝See菇Bi Family》廣播劇,亦極受年輕人歡迎。先後成為電影導演、編劇、演員及電視節目主持人,並為香港史上首位於大型場地演出棟篤笑之女藝人。曾於倫敦大學金匠學院修讀美術,現居香港。
卓韻芝寫作題材廣泛,涵蓋社會文化、旅遊、生活、愛情,理性分析與感性分享兼而有之,作品暢銷,《蘋果的中文是什麼?》(2010)、《你的心不是公廁》(2010)及《今日阿婆金句》(2012)更獲選為年度中學生十大好書。近年出版《導演的13個寓言》、《今日阿婆金句II》、《N-girl 養成術》、《宿墨傷筆》。
其電影創作亦屢獲提名及嘉許,包括香港影評人協會最佳編劇(《初戀嗱喳麵》2001)、台北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提名(《初戀嗱喳麵》2001)、金紫荊獎最佳編劇提名(《出埃及記》2007)及IFVA公開組銀獎(《打錯》2012)。編導電影《失戀急讓》(2014)。
章節試閱
三維局限
我一度喜歡跟不同的人討論:為甚麼掃墓?
我的意思是,為啥要身體力行,勞師動眾,登上山頭去懷念先人?我對亡母的思念,長存於心,想跟她說話時,只需閉上眼細語。事實上我經常向她說話。我深愛她,但我的問題是「為甚麼掃墓」。安放她的骨灰之地點,對她、我或整個家族而言毫無紀念意義──家母有生之年甚至沒曾踏足那山坡。我不認為掃墓才能反映孝義,更不認為後輩必須千里迢迢到達墳前才能與祖先溝通,莫非媽媽的靈魂就一直躲在那個由機構隨機抽樣安排的石碑後面?這聽來在任何我所認識的宗教裡都說不過去。親愛的,為甚麼掃墓?外面陽光多毒烈,蚊蟲多活躍。當然當然,掃墓不為了死者,而是為了生者,身體力行讓生者明白自己在死後不會被遺忘,但我們可以憑藉更多具意義的活動去讓生者明白這一點。好了,除了那纏腳的倫理問題、習俗問題,請問:為甚麼掃墓?
參觀波蘭克拉科夫(Kraków)維利奇卡地底鹽礦(Wieliczka Salt Mine Underground),必須走下三百七十八級木製樓梯直達地底。下樓梯時,我向身後的朋友說:「多幸福,我們多幸福,在矯健時來了該來的地方,時、地、人,所有東西都對了。」不出數分鐘,奇妙的鹽洞讓我把剛才思緒拋諸腦後。龐大猶如地底城市的地洞並非天然,而是人類於十三世紀開採礦物遺下的地底網絡,半小時後,一個壯麗到幾乎像異景的畫面出現眼前:地底教堂St Kinga’s Chape1,我問既然當時工人們不住在礦洞中,為何建築教堂和精緻的鹽雕?導遊的回答很妙:「無論如何,人總得相信一些甚麼。」忽地,一個念頭跑進腦海──別問我這念頭經由甚麼引發,反正它跟信仰或鹽或地洞沒有直接關係,實情是:當時我沒有特意思考,無論如何,這是瞬間閃現心坎的思緒──
因為我們跳不出三維。
因為我們是人。
也許這就是答案。
飛機再快,我們還是飛不出三維。當人身處一個地方,就沒可能同時身處另一地點。如果要到另一地點,必須將自己的身體移動到那裡(無論用甚麼方式,用雙腿走、坐在輪椅上,或乘坐戰機也好)──這是人人平等的,財富和健康只能節省移動的時間,而不能超越定律。所謂「科技發達,距離不復存在」是比擬而已。跳不出維度就是人類的限制。有人說,在四維裡,能夠穿越時空,但那都是理論,實情是憑著人類的意識,根本沒法感受三維以外的事,就像螞蟻絕無法設想跳起的感覺。
是以,我們必須通過軀殼的切實移動,才能感受空間、體驗距離、反省速度。透過移動,我們具體地理解一己的局限,同時感受自己的可能性。這並非憑藉段暫的移動(例如五分鐘步程)能夠輕易獲取的體驗,人類需要透過一段較長的時間裡所作出的移動──歷程,才得以累積對時間和空間的敬意,了解生為人的限制,透過歷程,我們過濾、沉澱、整頓、發覺感受。
為甚麼掃墓?
的確,它沒有必要,但甚麼謂之必要?莫非純粹應付生存才算必要?那麼不必要但極為重要的事,例如愛,怎麼計?在「必然性」的範圍內兜轉是徒然的。旅行和掃墓,是通過一段較長的時間裡所作出的一種移動,以獲取體驗,通過較長時間的身體移動來感受。某程度上,掃墓就是你走出去,移動你整副軀殼,憑藉一個有點把握的原因,為了回應一個虛幻的念去獲取一段真實的歷程。至於歷程的得失,在起行前,當事人是無法預知的。就像我怎麼也無法預想某次掃墓啟發我在棟篤舞台上足二十分鐘的講稿。就像我至今也猜不透為何在地底鹽礦閃現「三維局限」的小領悟。閣下儘管透過電腦程式,在鍵盤上按一下「拜祭」,就當作掃墓完畢,但那鍵盤最好還是經過迂迴曲折的路程才能按到。「旅遊」跟「掃墓」有著異曲同工。用程式拜祭跟收看旅遊節目,同樣能得到某種成效,然而惟通過肉體移動,我們才能獲得「惟有透過肉體移動才能達到」的體驗。
為甚麼旅遊?
因為我們跨不過維度,因為我們的意識範圍極為有限。我們需要距離,需要實地。惟有實地,才能感受實地。實地的聲音、氣溫、濕度、氣味、明暗的變化、各事物出現的次序等等,組織成一種歷程,造就感悟。我們擁有知識,但敵不過宿命的感受性缺陷;幾乎每個人都知道世界很大,卻難以真正明白世界之大。知道跟明白,是兩碼子事。將高度、體積、距離化成數字,對人類的感受而言,是欠缺實際意義的,惟切身會悟距離,才能透徹地領略世界之大,曉悟感受的邊際。惟有山巒出現眼前,才能真正感悟高峰之高,體會嶽與嶽、峭與峭之間的闊度。惟有在場,才能收集經由自我選擇所得的資訊,當他人被查理大橋的美麗所震撼,你或發現在聖像頭頂打轉的蒼蠅更具啟發性。惟有在場,才能承認言語的缺失,無論文人將弗朗西斯科哥雅(Francisco Goya)的畫作描寫得多麼淋漓盡致,無論拷貝何等高清,惟有置身普拉多博物館(Museo Del Prado)的房間裡,才能細味畫作讓不同背景的訪者頓變沉默的詭異力量。
對,外面陽光多毒烈,蚊蟲多活躍,但我還是選擇上路,找尋生命中的奇遇,或說,等待奇遇發生。旅遊時,我必須屈服於生為人的局限,向定律臣服,以便參透自然的力量,瞭悟人類在局限中保持的創造性,同時咀嚼自己的可能性。透過舟車勞頓,成就衝擊性的境況,在步伐中重新感受迷失和清晰,守候與驟降,失望與傾慕,拒絕與接納,意志的力量和冥冥中的注定。
生命本不是一場滯留。
旅遊不僅是一場儀式。
旅遊不是什麼
旅遊就像信仰一般抽象,對於旅遊的理解,不關乎一個人去了甚麼地方,而是他認為旅遊是甚麼,就像信仰一樣,信者各取所需,不信者認為一切徒勞無功。
每個人對於旅遊的詮釋盡不同。對於鄧小姐來說,旅遊就是吃、吃、吃。對於莎莉而言,旅遊就是跟男朋友一起度假。阿米認為去哪裡都沒所謂,只要逃離工作的困惑便可以。他們三位都是我的朋友,但我發現自己難以跟他們討論旅遊。
理解旅遊的方式反映人生觀,旅遊形式的選擇,不僅透露人們的處境,更以實踐的形式揭示人們追求怎樣的生活、為自己鋪陳的道路如何,又渴望在人生裡獲取甚麼。這一切合成人生意義的基調,處世的核心價值觀。我一直覺得,細聽別人談論旅遊,是切實地認識一個人的方法。
旅遊雜誌上刊登搶眼的題目:「大慳家旅遊哲學」。長達十頁的專題特刊,詳盡報導首爾哪處可以購得(相比起香港)便宜的貨品,還附有數學算式,合計如果將東西全部買下,共可節省多少塊錢。這讓我想起自己在柏林公園遇上的塗鴉作品:
FUCK RYANAIR SPEND & SAVE
Ryanair是德國廉價航空公司,口號是「Spend & Safe」(花得越多,節省越多)。這口號似乎觸動塗鴉藝術家的神經,以至毋須再加以詮釋地作為鏗鏘有力的警世語句;在塗鴉藝術家眼內,「購物能夠省錢」是資本主義下的荒誕歪理。閱讀那首爾購物特輯時,我遐想它的「哲學」到底是甚麼──除了標題以外,「哲學」在內文再沒出現──這個特刊之所以存在,因為有為數眾多的人們認為旅遊是購物,是擁有更多物質生活的手段。他們不但飢餓於擁有物質,更渴望在消費的同時,讓自己顯得聰明和深思熟慮。在消費的同時想著節省,為了改變個人對一己的看法:好使自己認為一切說得過去。
對於一些人來說,旅遊是一種慰藉,行使個人權利,讓自己的生活說得過去。
另一種旅遊,關於照片,甚至不關乎攝影,而是純粹的「獲取照片」。
我在旅遊網站看到這詞彙:Instagram-able。那是介紹曼谷咖啡店的報導,幾乎沒花筆墨評論咖啡的質素,編輯了解讀者急於知道哪家咖啡室的裝潢或食物的排場能夠獲取最佳照片。
發稿至旅遊雜誌前,編輯通常首先詢問「有沒有照片」,並會因為照片不足而將刊登頁數縮減。某次,他們看中了我的一張相片,反過來問我有沒有甚麼可以就它寫寫;那僅為公路旁的小丘,沒啥值得寫,然而編輯部意決以之作為跨頁照。他們的決定是可以理解的,在那幀照片中,我以瑜伽式子佇立野餐桌上,後方山巒起伏,感覺舒泰,正合雜誌讀者的心意。只是,那照片的內容跟我毫無情感牽繫可言,它投射出的氛圍亦非我在該趟旅程中對紐西蘭的印象。讓我難以忘懷的噴水洞(Blowhole)、鯨魚、螢火蟲洞(Glowworn Cave),由於種種因素──例如天氣、拍攝位置、隨行器材──而缺乏「成功的」照片,編輯決定將它們縮至小框中。此刻遙憶,我仍舊深深記得噴水洞的爆炸力,或在絕對漆黑的蟲洞中,螢火蟲的微光浮現的剎那。後來多番接觸專業攝影師們的噴水洞或螢火蟲洞作品,明白沒一幀照片足以表達實地感受到的能量。
在好些情況下,旅遊的原點始於照片:梁小姐看見櫻花樹的照片,就此決意到日本大阪旅行。也許她曾經遇上無數同類櫻花照,更詩意的大有所在,然而不知怎地,大概因為天時地利人和,她因為那張照片,篤定下一個旅遊目的地•這種例子俯拾皆是。許多人在計劃旅遊時,腦海就單靠一個影像作為依歸。某程度上,誘發人們出走的,是影像──一張照片,一段錄像,或電影中的一個鏡頭,造就所有幻想。當事人幻想自己成為該照片的主角,置身其中,拍下相似的照片。這是為甚麼許多人只想去一個地點──我的意思是切實的一個地點。梁小姐並不在乎那趟日本旅程的整體,還不是走走吃吃,不外如是,但對於到大阪毛馬櫻之宮公園的那一天,她顯得相當緊張,還打探酒店有沒有熨斗,因為她特意攜帶了和服,好去複製那張照片,旅遊僅止取得照片的手段。旅程的原點起於照片,也就讓旅程終結於照片。
我檢閱梁小姐的櫻花照,心裡納悶,也許很多人是為了得到婚紗照而結婚,縱使他們絕不承認。他們會說,一切是為了回憶。旅遊,為了用相機俘虜一切,以便製造回憶──
──且慢,當真是為了回憶?
到底多少人為了印證和重塑回憶而拍照?多少人真的會翻閱在途中拍下的,海量一般多的照片?
攝下整個世界的欲望本身,並不為要恢復或創造記憶,它是一種確認經驗可被表現出來的需求──如果它不可被理解的話;同時它也是創造一種庇護靈光的需求。
美國街頭攝影師格瑞溫諾葛蘭(Garry Winogrand)這番話比較接近事實。人們提起相機的舉動,來自一種自身經驗能夠被呈現的欲望,渴望透過照片把凌浮空中的體驗具體呈現,就像我們試著透過言語解釋複雜的心情,或透過故事來表述意味深長的意象。人們拍照,企圖複製自身感受,讓自己感到一切能夠定性和詮釋,這份欲望是原始的。我想起小時候,只要同學忽然開始跑,我就會立即起跑去捉住他,完全不為了甚麼。
自從互聯網的表演舞台確立以後,拍攝的企圖變得更為複雜。出門遠行,相機是基本裝備,跟護照和現金同樣舉足輕重。在這個年代,「獲取照片」跟「上載展示」幾乎劃成等號。社交網絡有所謂「打卡」(上載照片以示到此一遊),「展示」(Display)是旅遊的重要部份;不拍照便會死。互聯網舞台造就各種攝影產品,廣角、超廣角、超微距、全景、長時間曝光、連環快拍……可別忘記還有無數的照片後期科技。展示的欲望蠶食旅途中所有時刻,猶如癌細胞:成功得到稱心的照片,才算是去了一趟成功的旅行。我們經常聽到人說「最糟糕是拍不到(美麗的)照片!」,不能獲取照片的挫敗成為遺憾,污染回憶。沒人問這些照片能夠讓他們得到甚麼,如果是換取社交網中的「讚」,那些「讚」又讓他們得到甚麼。
人們渴望展示,然而展示的企圖並不簡單:在選擇哪張照片被公開而哪張被刪除之間,人們試著建構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希望他人運用自己認可的方式去了解、認知自己,照片是有力的手段,誘導他人運用自己渴望的方式去認同自己。
人類用著各式各樣的方式爭取認可,排解孤獨。
旅遊也為了博得自我認同。
普遍都市人恐懼閒逸,對於假期既期盼亦害怕;空閒可以是件惱人的事。人們怪罪於自己「啥也不幹」,批判自己「浪費時間」,歌頌爭分奪秒,藐視感受分秒。誇張點說,我懷疑都市人花了五成時間去設想自己「可以做甚麼和應該做甚麼」,換句話說,用一半時間埋怨自己沒有做甚麼。美國棟篤笑表演者Louis CK所言:「你需要擁有一種能耐才可以『不幹任何事』。這就是手機掠奪人們的東西:光坐著啥也不幹的能力;純粹當一個人的能力。」「不幹任何事」可謂假期的噩夢,人們要求自己必須做出一點甚麼,就像上班時我們被要求一樣,旅遊成為輕易可取的解決良方,一種較具把握的,容易獲得自我認可的填充空閒的方法。
近年,旅遊工業迅速改變,由販賣書是蛻變成販賣冒險精神,旅遊節目不再使用字眼「travel」,改用「wanderlust」(源自德文,意謂「流浪的渴望」),旅遊宣傳摒棄使用「遊客」,改用「旅人」或「浪人」,參加旅行團不如自由行,到東京購物不如去格陵蘭尋找冰山,透過旅遊擴闊視野,這都很好,然而經過市場推廣部的手以後,卻驟變恐嚇,目標客戶是渴望取得自我認可者。旅遊指南裡被調色的照片和擠滿感歎號的文章,既製造威迫,亦暗懷輕藐:「還住飯店?何不自己紮營!」「懂爬的,當然爬這個山!」「只有親手採過的蜂蜜才是甜的」「死前必須到訪的地方」……在死前,你越來越多事需要幹了,親愛的,最好別早死,然而若果晚一點死,或發現更多「死前必須到訪的地方」也不定,有時我感到,人們帶著恐懼去旅行。
相比起許多亞洲國家,香港人出國旅遊的年齡非常早,出國的次數亦算得上頻密。許多港人二十來歲已經跟朋友走遍上海、台北、東京、首爾、曼谷。一來由於我們的生活指數較高,到異地消費也就顯得便宜,而且香港真的很小。去旅行是港人生活的一部分,每當有連續四天假期,我們首先想到的,是離開。
香港的旅遊文化存在一種普遍心態:關卡式(Checkpoint Style)。以效率作為旅遊的成功指標,用走馬看花的形式,「極速」將「景點」逐一「擊破」,充滿暴力和侵略性意味。這種旅遊者的確對自己相當暴力,他們不介意操勞──如果同行者賴床,多半會惹來紛爭──他們依循計劃早起,「發誓」要「攻陷」行程上的每一處。這種心態並非香港專有,只是在這裡尤為普遍,在香港「自己找自己吃的」稅制下,有薪假期少之又少,普遍人並不曾嘗過三個月旅行的滋味;一個月假期,在工作者內可算天大事件。
有人認為,去三個月旅行,因為你富裕,「誰不想一個月只去一個國家?就是因為窮,假期短,才拚命計算旅遊的性價比。」我拒絕運用這種想法認知,在我眼內,貧窮不等於放棄深度。莫先生每月薪俸一萬五千──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月薪一萬五千是捉襟見肘的數字──為了讓假期沒有差池,他用上一季時間計劃。他準備用兩周時間到訪老撾、柬埔寨及越南,回來時,他告訴我,他只去了東埔寨,我問發生了甚麼事,他表示沒事發生,只因為「柬埔寨太值得逗留」。往後,他讀了三本關於東埔寨的書籍,計劃五年後重遊一趙。莫先生是德國人,在德國長大,但成年以後,再沒居留德國,他居留香港已經七年,並準備繼續定居;他是香港人。閣下或許會想:「原來如此,外國人才會這樣!」但為甚麼呢?
在西方社會裡,有所謂的Gap Year(在畢業以後,投身社會以前,出走一年)──Gap Year中人,多數身無分文,胸前的盾牌是青春,所有的「錯」都在一年內犯齊,人生路向盡可能在同一年辨清。可惜,我們沒有Gap Year的習慣,大學畢業生沒有,中五輟學生更沒機會擁有。就此,我們缺乏因為年少輕狂而別有一番風味的體驗:在異地放肆買醉、在寒冷的營地中生火失敗、到只認識半天的「朋友」家借宿、提著背包在公路旁呆等三小時便車……窮遊的體驗是重要的,它奠定一個人認知旅遊的方式。
在港人的印象裡,旅遊是必須透過辛勞工作才能獲得的權利──我們經常說:「沒錢怎去旅行?」旅遊首先讓我們想到的,是金錢。既然如此,人們更希望用最短的時間、到訪最多的地方,這意味著用最少的價錢求得最多,順理成章地,關卡式旅遊成為普遍心態。追求速度,不求深度,因為沒有時間,也就缺乏細味的空間。有時人們忘記了自己經已下班。
關卡式旅遊是一種假豐盛,換來奴性的活動,追求效率心態,沒有在旅遊中退去,忘記旅遊的真義,忘記回憶由甚麼構成。關卡式旅遊,出自遺忘。
我們都很懂得取笑稚嫩的旅遊方式,知道旅遊不該是甚麼,但旅遊是甚麼?
三維局限
我一度喜歡跟不同的人討論:為甚麼掃墓?
我的意思是,為啥要身體力行,勞師動眾,登上山頭去懷念先人?我對亡母的思念,長存於心,想跟她說話時,只需閉上眼細語。事實上我經常向她說話。我深愛她,但我的問題是「為甚麼掃墓」。安放她的骨灰之地點,對她、我或整個家族而言毫無紀念意義──家母有生之年甚至沒曾踏足那山坡。我不認為掃墓才能反映孝義,更不認為後輩必須千里迢迢到達墳前才能與祖先溝通,莫非媽媽的靈魂就一直躲在那個由機構隨機抽樣安排的石碑後面?這聽來在任何我所認識的宗教裡都說不過去。親愛的,為甚麼...
作者序
沒必要去旅行
當時我身處一家印度餐廳,老闆是印度人,侍應則是土耳其女人,身後一桌食客合共七人,簡中夾雜亞洲人和白人面孔,他們以濃烈倫敦腔的英語對談,話題環繞席中一名十來歲的女孩到美國長島探訪朋友的事(「我差點便躍進水裡,幸好沒撞上石頭。」),從口音和說話的方式聽來,她是英籍華人。那女孩擁有一張「BBC表妹臉」,我的意思是,曾經有幾位朋友向我介紹他們在英國土生土長的華裔表妹或堂表妹,她們的氛圍跟這女孩有點相似。
靠牆的雙人桌坐著兩位操廣東話的中年女士,我難以猜透她倆的關係,也許是親戚,也許是朋友,卻不像是要好的朋友。較年輕的一位說話方式非常進取,活像那種經常衝口而出的女子──「怎麼你不把單位賣掉?至少也該裝修!」較年長的那位回以含混的咕噥。年輕的女士識趣,或是出於沉悶,隨即轉換話題:
「我沒去過印度,也想去一趙。你想去印度嗎?」
「不……(含混)旅行。」
「甚麼?」
「沒‧必‧要‧去‧旅‧行。」
事實上,是這話讓我回頭去打量說者──一位短髮,架著眼鏡,看來蠻富修養的女士。諷刺的是──若果編劇寫出如此劇情來,定會被認為過份鋪陳──當時我正在閱讀秘魯的旅遊書籍。
吃完籃子中的nan(印度麵包),往窗外眺望熟悉的街道──香港天后區。時値下午,判街的日式蛋包飯小店門外掛有一張寫著「オムライス」的海報,它跟鄰旁的韓式烤肉店一樣格外冷清,可能由於天氣過於寒冷;當天香港只得三度,比起同日巴黎的氣溫還要低。
我閤上書。
往後數天,我將發現自己被這句話纏繞。
沒必要去旅行。
這是要吃甚麼就能吃到甚麼、幾乎沒有產品買不到的都會,為甚麼要去旅行?這裡是種族混合的香港,城裡滿是歐洲人、南亞人、中東人、BBC、ABK,如果對異地文化感興趣,大可以去跟他們聊聊,為甚麼要去旅行?我們正身處要看甚麼就能看到甚麼的時代,Google Earth和成千上萬的旅遊網站,何不在屏幕前安心探索作罷?上載於Prado博物館網站的那幅Francisco Goya Saturn,比起在現場用肉眼觀看還要高清。我們根本毋須移動,因為身邊的世界正在為我們移動。一個街區裡有五間不同國家菜的餐館(而且提供的菜做得蠻正宗),商店售賣多國產品(並且越來越專門),網上的資訊每天巡自跑進眼球,為甚麼要去旅行?
在這個年代,沒人能像鄭和下西洋一樣發現好望角,或如Captain Cook一樣在太平洋裡為後世繪畫地圖,地球上幾乎沒有地方不曾被探索、紀錄、解釋,「世外桃源」僅止旅行社的推銷字眼,旅遊僅止代表「在安全情況下移動」,「往外走」不再象徵冒險的決心,跟真正的探索已經扯不上關係。如果說旅遊是一場內在的穿越,看電影、讀小說、一場好好的對話、一場冥想,也能達至心靈穿越之效,穿透力有時比起實地旅遊還要來得強烈。也許,外遊的確沒有必要。
連續一周,我反覆質問自己:該如何回應那位女士?事實上,為何我們要讓自己舟車勞頓,在機場中原因不明地等待,在異地的火車站月台惶惑,提著行李時指頭發痛?為甚麼我們還要去旅行?
為了回應她,我嘗試去寫這本書,心裡懷著一份深刻的盼望,渴望自己在街角重遇她,然後送上這書。
卓韻芝
2016年1月
沒必要去旅行
當時我身處一家印度餐廳,老闆是印度人,侍應則是土耳其女人,身後一桌食客合共七人,簡中夾雜亞洲人和白人面孔,他們以濃烈倫敦腔的英語對談,話題環繞席中一名十來歲的女孩到美國長島探訪朋友的事(「我差點便躍進水裡,幸好沒撞上石頭。」),從口音和說話的方式聽來,她是英籍華人。那女孩擁有一張「BBC表妹臉」,我的意思是,曾經有幾位朋友向我介紹他們在英國土生土長的華裔表妹或堂表妹,她們的氛圍跟這女孩有點相似。
靠牆的雙人桌坐著兩位操廣東話的中年女士,我難以猜透她倆的關係,也許是親戚,也許是朋友...
目錄
序──沒必要去旅行
CHAPTER I
自然之禮讚──新西蘭
三維局限
旅遊不是什麼
CHAPTER II
緩慢與河居──荷蘭
CHAPTER III
必要的沉思──東歐三國
大膽據點
旅遊的剪接
移動中的移動
懷別人的舊
CHAPTER IV
隨興的遠足──意大利
CHAPTER V
內儉的藝術──日本直島
執拾行李
跳火車
寂靜的聲音
去旅行,是為了不知道
序──沒必要去旅行
CHAPTER I
自然之禮讚──新西蘭
三維局限
旅遊不是什麼
CHAPTER II
緩慢與河居──荷蘭
CHAPTER III
必要的沉思──東歐三國
大膽據點
旅遊的剪接
移動中的移動
懷別人的舊
CHAPTER IV
隨興的遠足──意大利
CHAPTER V
內儉的藝術──日本直島
執拾行李
跳火車
寂靜的聲音
去旅行,是為了不知道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6收藏
6收藏

 4二手徵求有驚喜
4二手徵求有驚喜




 6收藏
6收藏

 4二手徵求有驚喜
4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