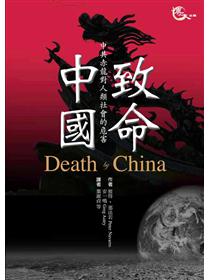“中英相遇”不僅僅發生在兩個大國之間。這兩個國家的貿易往來還發生在大英帝國和英聯邦這些更宏大的背景之下。本書根據作者在劍橋大學所作的演講修改而成。
這部探討中英關係的作品文筆優美、思想雋永,作者圍繞着「戰爭」、「貿易」、「科學」及「治理」這四個詞彙,闡述了中國和英語民族複雜、多采、動態的交往關係,既審視兩者交往的可能,同時又洞悉其限制,為讀者展示了一幅既深遠壯闊又細緻入微的中西文明之間相遇融合的歷史畫卷。
本書特色:
1. 坊間一直缺乏平實易懂但又冷靜客觀的普及歷史讀物,去分析中英兩國近百年來相遇互動、相交衝突以至相知合作。本書深入淺出,適合不同年齡層人士閱讀。
2. 本書分成軍事、商業、信仰和管理四個大主題,透過不同主題,可反映中英兩國近百年來的相遇相識,從互不了解到文化交流的歷史發展過程。
作者簡介:
王賡武,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席、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主席,獲頒大英帝國司令勳章(CBE),當選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外籍名譽院士、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院士,榮膺國際學術獎、福岡亞洲文化獎。歷任馬來亞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1957-1968),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遠東歷史系主任、太平洋研究院院長(1968-1986),香港大學校長(1986-1995),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1997-2007)。
研究方向為中國歷史、海外華人、民族主義、移民研究等,涉及歷史學、文化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近年作品有《中國與東南亞:神話、威脅和文化》(1999)、《海外華人:從土地束縛到爭取自治》(2000)、《1800年以來的中英相遇:戰爭、貿易、科學及治理》(2003)、《更新中國:國家與新全球史》(2013)、《另一個中國周期:致力於改革》(2014)等。
推薦序
一 導論
受邀做史穆茲英聯邦演講,我深感榮幸。我在馬來西亞西北部的霹靂州首府怡保市長大。歷史上,霹靂州曾接受英國的保護。我在當地一所公立學校(安德遜學校)修讀英帝國和英聯邦史,獲頒劍橋證書,這所學校以前總督約翰‧安德遜(John Anderson, 1858-1918)爵士的名字命名。我在新加坡新建的馬來亞大學就讀時,簡‧克利斯蒂安‧史穆茲(Jan Christianan Smuts, 1870-1950)爵士依然健在。我感興趣的是,為何這位負笈劍橋的殖民地居民一度痛恨大英帝國,卻又離奇轉身成為英聯邦的忠誠擁躉。1968年,我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見到史學家基思‧漢考克(Keith Hancock, 1898-1988),當時他剛完成《史穆茲傳》(第二卷),我對史穆茲的研究興趣油然而生。我樂於閱讀這位布林人青年時代的故事和他在第二次布林戰爭(1899-1902年)期間建立的功勳。他人生的最後階段,也就是1933年之後的經歷,更讓我關注。他為何變得對英聯邦如此忠誠?在我這個華人看來,有兩個原因甚為突出。一個原因,他是歐裔基督徒,認同英國歷史文化,同時是世界名牌大學培養的英美法系律師。另一個原因,他是殖民地居民,深愛祖先的南非土地,渴望他的民族在那個多民族大陸上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文明國度。因此,他大力宣傳鞏固英聯邦制度,使他的國家奉行自由和博愛,成為世界大家庭的一員。
在我身上都找不到這兩種動因,難怪我有機會走近英聯邦歷史,卻沒有從事這項研究。我出生在遵奉帝制的中國文人家庭。辛亥革命改變了這種家庭的生活。我的父親放棄了對傳統儒家經典的研究,考入現代大學。畢業後,他發現必須離開中國去尋找他樂意從事的職業,遂僑居英屬馬來亞,以教書為生。父親之後回國結婚,夫妻一同前往荷屬東印度羣島。我生在印尼蘇臘巴亞市。父親時任一所中文中學的校長。在我年幼時,他離開爪哇,在馬來西亞霹靂州英國管轄的教育部擔任漢語學校督學。父親在中國大學學過英語,極推崇英語文學,但他從沒把我培養成大英帝國的順民。不過,通過學校工作,父親開始了解大英帝國管理多元社會的舉措,他便自認他的工作目標是讓中國孩子接受良好的現代教育,使華人社區將中國文化力所能及地傳播給感興趣的民眾。我的母親中文很好,但一點也不懂英文,我們在家只能說中文。對於父母來說,馬來亞不是真正的家,他們內心最深的渴望便是回到祖國的懷抱。他們向我這個獨子宣揚要愛中國及中國的東西。
那麼,我為甚麼有資格談英聯邦?一個原因是,除了短暫的三年,我這一生一直生活在前英屬殖民地或現英聯邦國家。我過去的歲月是在以下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城鎮中度過的:馬來亞、馬來西亞、英國、澳大利亞和香港,最後是獨立的新加坡。另一個原因包含多種因素。儘管學術寫作圍繞中國歷史和海外華人,我的歷史可是從大學裏的英國老師和同事那裏學來的。我的研究、教學和寫作都在英聯邦體制下的大學和環境中進行,這使我有足夠的機會思考中英關係,不管是在英聯邦國家之內,還是在英聯邦以外。於是,我時常納悶,各種各樣的中國人同英國人打交道時的際遇怎樣,從與各式英國人的交往和英國人在亞洲各地區的活動中,中國又得到了甚麼。
因此,這些講稿都圍繞這個角度來寫作。內容上不可能面面俱到,涵蓋英國與中國、中國人關係的各個方面,而是從中英兩國的周邊加以旁敲側擊,試圖將關乎兩國人民的中心問題與看似無關緊要的問題相提並論。我使用“相遇”(encounter)一詞,沒有吉莉恩•比爾(Gillian Beer)定義的“有力的、危險的、誘人的、基本的”這些屬性,但是我希望這個詞正如她所提到的,“能充分探討未經省察的假設,允許一般解釋者而不總是政要們去挖掘未經表達的動機”。我選擇的研究視角有時比較棘手,提供的場景撲朔迷離,始終不夠全面,不過,我的核心觀點是:在關乎深層價值觀的最重大問題上,中英兩國人民仍存在極大分歧。
我從中英兩國一開始就動盪不安的關係說起。兩國人民之間能對上眼的東西本就不夠多,以至於無法增進相互了解。箇中原因是複雜的。有些源於政治經濟上的直接衝突,但大部分是出於歷史文化上的千差萬別。這一點本來就不足為怪。英國深受西方文明的薰陶,而中國有着自身創造出來的獨特的文化傳承,雙方可謂大相徑庭。另外,在跟中國相遇之前,英國人已和其他偉大的文明國家打過交道。事實上,與中國人的聯繫相比,英國人跟西亞的穆斯林國家、南亞的印度這兩大文明的交往更加深入。英國跟上述兩者的關係也好不到哪裏去。英國人的帝國疆域越來越大,始終苦於寡不敵眾。他們覺得自身勢力橫豎不穩固,便建立起防護欄,並擴展到社會和文化關係。外族環峙,令英國人根本應對不及;人手不夠,也實在做不到減少防禦工事。
儘管如此,中英關係的發展卻豐富多彩,卓有成效,儘管兩國差異懸殊,但漢語世界的人與英語民族在許多場合中過往甚密,有些交往甚至對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中國對英國海軍的強大耿耿於懷,但更羨慕一個現代的民族主權國家造就了這種實力。中國不斷地評估自身的國防和國家安全,但是國家為應對那種實力所須作出的洗心革面卻姍姍來遲;同時,中國的官僚階層對海外商企能夠創造的巨大財富感到震驚。這最終使他們重新審視中國商人的地位,重新定義在中國復興過程中商人的角色;此外,不同的中國羣體對於英國傳教文化的反應也是不同的,最終,英國的科技進步贏得了最多的信徒。其結果是,對於中國各民族而言,科學思想成為衡量現代文明的方式,並決定了現代教育的意義;最後一點,大多數中國人對英國人的遵紀守法、市民自律和行事高效感到驚訝,儘管他們並不總是理解如何培養起對法律的這種尊重,要理解這個法治社會的管理體系是如何分級建構的,也不是一樁易事。但無疑,兩國範圍廣泛的交往日積月累所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
我將擷取中英交往的歷史,分析和思考其在當下和未來的意義。第二、三章探討中國對戰爭和海外創業戰略的態度。第四、五章講述中國科學史的重新發現和中國對於現代治國方略的回應,包括對政黨制的試驗。然後我將對這些思想進行整合,以提供對英中現象的一個長遠的眼光。
一旦比較英國對中印兩國產生的影響,我總是震驚於19世紀印度穆斯林詩人米沙‧迦利布(Mirza Ghalib, 1797-1869)的兩行詩。當時,他正向印度阿里格爾穆斯林大學創始人賽義德‧艾哈邁德‧汗(Sayyid Ahmad Khan, 1817-1898)提議,希望後者不要過度關注莫臥兒人的過去。他這樣寫道:
睜開眼睛,審視英國人,
觀看他們的作風、風俗、貿易和藝術。
同時代的中國官員是不能夠聽從這一建議的。為甚麼會這樣?背後有重要的文化因素。這也能衡量印度人(包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與中國人世界觀的不同起點。在迦利布希望賽義德‧艾哈邁德‧汗審視的四個品質中,只有英國人的“貿易”才可能吸引中國的沿海商人,但另一方面,清朝官員要控制的也正是貿易。他們絕不會鼓勵中國商人學習英國的經商之道。對英國人的“作風”和“風俗”更是如此,清朝官員一般會積極找茬。一些中國人可能覺得英國人的“藝術”有趣,尤其是其實用設計藝術、工藝美術,以及材料使用上的創新。但在大多數時間,中國人所景仰的還是英國人的強國之道。
那麼中國人的關注點是甚麼?我注意到英國漢學家亞瑟‧韋利(Arthur Waley, 1889-1966)在《我們欠中國的情義債》一文中卓有高論。文章寫於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期,兩年後,該文在蕭乾(1910-1999)的《千弦琴》中再版,韋利談到在20世紀首20年,“我們與中國的關係的偉大轉捩點到來了”,當時英國的有閒之士、詩人、教授和思想家,接替以往的士兵、水手、傳教士、商人和官員,開始到訪中國。韋利竟吸引大家留意這種轉變,有點令人驚訝。伊萬‧莫里斯(Ivan Morris)這樣寫道:
最奇怪的是韋利從沒到過中國和日本。我問起原因,他始終沒有直接答覆。雷蒙德‧莫蒂默說,“韋利癡迷唐朝時期的中國和平安時代的日本,他不能一邊直視現代的醜陋,一邊在荒蕪中尋找許多保存完好的美跡”,他這麼說自有一番道理。韋利心中早存有中日兩國的風光景致,他不希望旅行沖淡這種美好感覺。
韋利揭開中國詩歌的神秘面紗,將中國詩歌領入英語世界,他自己就屬於“偉大的轉捩點”。他獨闢蹊徑,與中國人進行深層次的心靈和審美的交流。遺憾的是,能意識到這份情感如何對中國的思想、語言和藝術產生咒語般魔力的中國人,實在寥寥無幾。
亞瑟‧韋利在文中提到幾個人,他們“不是去傳教(convert)、貿易(trade)、統治(rule)或打仗(fight),而僅僅是為了交友和學習”。他認為這些訪客本該為中國帶去英國人的嶄新形象。他提到的高斯華夫‧路斯‧狄堅遜(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 1862-1932)和羅拔‧特里維廉(Robert Trevelyan, 1872-1951)沒有產生影響。只有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給中國留下了印象,但像他這樣有影響力的學者屈指可數,且訪華時大多為時已晚,沒能結交多少朋友。事實上,韋利前面提到的這四個詞比他期望的更正確。當然,我們不能怪他沒有預見到在接替英國的更強大的國家身上,用這四個詞同樣適用。我指的是非正式的美帝國,已經不知不覺地進入中國人、東亞人和東南亞人的視線,取英帝國而代之。不管正式與否,美國榮登帝位,加入中英交往的第二階段,使更加寬廣的歷史畫卷無縫連接,直至當下。所以,我建議依然將這四個詞作為故事展開的關鍵字。“傳教、貿易、統治或打仗”描述了中國和英語民族關係史的核心內容。
這四個詞暫不按順序來講。我先說“打仗”,中國對這詞的關注度最高。1842年,中國初嘗鴉片戰爭失敗的屈辱,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厄運的開端。也許,中英人民之間從此沒法把關係理順的原因正在於此。我再說“貿易”。“貿易”起步很早,但只有當戰爭的硝煙散盡,貿易的影響方能彰顯。中國人遠較英國人了解對方,隨着雙邊合夥貿易的深入,彼此評價較少發生偏差。“傳教”則是單方面的,中國傳統上較少關注勸人皈依的工作,但當該詞延伸到涵蓋宗教和世俗兩方面的教育,雙方就有了充分的探討空間,結果是,沒有甚麼對上眼,但中國人還是設法從接觸中獲得了很多其所需要的東西。“統治”更是單方面的,但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勢必是不完全的體驗,如果不是邊緣化的經歷的話。在打開中國沿海地區之前,英國不得不統治印度,但對於中國,卻並無統治的興趣。英國最後還是統管了零碎的行政權,管轄範圍包括中國通商口岸、中國海關,轄區涵蓋中國大陸之外的華人社區,主要是香港、馬來亞和婆羅洲(東南亞加里曼丹島的舊稱)的北部地方。中國人對此反應不一。但這可能加深他們對現代治理本質特徵的理解,值得關注。
鑒於我將暢談中國,跟史穆茲紀念演講由以得名的英聯邦相關的問題暫且放在一邊。我希望各位接受我的一個觀點,即儘管創建英聯邦的政治家自有動機,但英聯邦背後的理想卻超越了一個由有着共同過去的成員國組成的溫馨俱樂部。他們取之於一個大膽嘗試的理想,要將一個多文化、多種族的世界中各個國家的獨特經驗予以歸納總結,並梳理這些經驗供他國學習,乃至效仿。中國自身不直接屬於那個世界,並仍堅持一己之願景,以便在定義那個世界的未來中依然能扮演重要角色。但目前,有千百萬海外華人生活在不同的社會經濟體制下,其中的大多數人生活在由美國非正式領導的說英語的帝國裏。他們成為溝通中國和全球化了的那個世界的有用紐帶。
簡‧克利斯蒂安‧史穆茲會理解20世紀前後半葉世人觀點之嬗變。他是同齡人中最國際化的布林人。他敬仰溫斯頓‧邱吉爾的世界觀,惋惜美國的孤立主義,畏懼蘇俄的崛起,認識到印度獨立的必然性。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他於1937年9月帶着不詳的預感,寫下這樣的評論文字:
完全釋放之後,這個巨人將做甚麼?我擔心日本所為不僅自毀前程,而且日後可能威脅到西方國家幾代人,這種破壞將超過東方國家歷史上的任何歷史事件。中國的英雄主義或將震撼世界。
引用史穆茲的原話,他的悲劇是“擔心淹沒在黑非洲⋯⋯造物主犯了一個錯,造成了不同膚色,我們有甚麼辦法?”因此,英國沒有管好南非,史穆茲沒有加以責備。回想起來,英國人錯在跟布林人打仗。英國勝得並不輕鬆,儘管最後是贏家。他們終究未能阻止世界上最醜惡的政權在英聯邦誕生。但英國在經貿方面幹得不錯。南非確實成為非洲大陸上最富有的國家。至於勸人皈依基督教理念,功勞當屬英國國教,培養了像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這樣的基督徒。照中國人的話來說,曼德拉就像蓮花“出淤泥而不染”。這朵美麗的蓮花定會得到中國文人雅士的敬仰。
更有甚者,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不經意地誕生了另一位傑出人物,那就是印度國大黨領袖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1948)。他先前在南非擔任律師,與史穆茲是同代人。韋利用在旅華的英國人身上的四個詞──打仗、貿易、傳教和統治,如果用到印度身上,甘地會拒絕接受。甘地反對一切戰爭,因為印度人和英國人造成了太多的殺戮,他看不見在印度這片戰場上戰而勝之的曙光。甘地欣賞基督教的精神力量,但反對基督教會。他在公開場合引用基督教中那些能夠使他堅持本來信念的信條。他更加強烈反對英國統治,但在尋求民族獨立的道路上,他對遇到的每個問題都堅持非暴力解決,這難住了頑固不化的大英帝國當局。他還反對基於大規模生產的貿易方式,英國人借此壟斷了印度市場,削弱了印度的傳統農業經濟和文化。
與甘地的四個拒斥相比,中國缺乏如此徹底革命、不屈不撓的政治領導人。中國宣導徹底改革和革命的領導者,如康有為(1858-1927)、孫中山(1866-1925)、激進的民族主義者蔣介石(1887-1975)和青年毛澤東(1893-1976),對大家看到的以英國為代表的現代化和世俗化的反應,比甘地來得更加迅急。跟許多實幹的中國人一樣,這些領導人樂於以西歐模式為學習榜樣,而不單單向英國看齊。那麼,為甚麼在今天看來印英交往結出的碩果貌似多過中英交往?為甚麼英國對印度的影響甚至大過整個西方世界對中國產生的影響?我將不去回答這個問題。但我希望通過我對中英交往的述說,幫助其他人揭開這一看上去引人入勝的謎題。
一 導論
受邀做史穆茲英聯邦演講,我深感榮幸。我在馬來西亞西北部的霹靂州首府怡保市長大。歷史上,霹靂州曾接受英國的保護。我在當地一所公立學校(安德遜學校)修讀英帝國和英聯邦史,獲頒劍橋證書,這所學校以前總督約翰‧安德遜(John Anderson, 1858-1918)爵士的名字命名。我在新加坡新建的馬來亞大學就讀時,簡‧克利斯蒂安‧史穆茲(Jan Christianan Smuts, 1870-1950)爵士依然健在。我感興趣的是,為何這位負笈劍橋的殖民地居民一度痛恨大英帝國,卻又離奇轉身成為英聯邦的忠誠擁躉。1968年,我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見到史學家基思...
目錄
鳴謝
一 導論
二 “去打仗”
三 “去貿易”
四 “去傳教”
五 “去統治”
六 餘論
鳴謝
一 導論
二 “去打仗”
三 “去貿易”
四 “去傳教”
五 “去統治”
六 餘論
 2收藏
2收藏

 5二手徵求有驚喜
5二手徵求有驚喜



 2收藏
2收藏

 5二手徵求有驚喜
5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