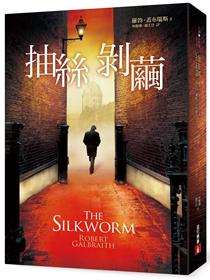一切都將終結於「冒險」——
一個死刑的詛咒、一個逃家造成的婚姻,被命運層層疊疊出魔法師的陰謀,「外來者」欲破門而入,先知咒符黃金已然鏽蝕,所有已知與未知交錯,他們必須冒最後一次險……
命運對我露出諷刺的微笑。
「我希望能收到尊敬的羅偃先生,他那本寫著所有魔法師幾百年來的歷史的書——的副本當作嫁妝……據我所知,裡面也應該記載著我祖先的名字……」
史上最偉大的大魔法師達米爾的後代——雷坦納爾‧雷寇塔斯,因假稅吏意外事件被鬼魂法官的詛咒判決判了死刑,緩刑一年,為尋求解除方法,踏上漫長旅途。赫赫有名的貴族英雄上校獨生女——艾拉娜‧梭爾,為逃脫家人掌控離家出走,淪落到四處漂泊賣藝的喜劇團。在當今僅存的最厲害魔法師有計畫性的安排下,兩人的命運開始交錯一起……
而魔法師最終的目的,是藉由一本《法師史》的書籍要到造化之門尋找擁有「先知咒符」的人,進而成為整個世界的主宰,統治世界。
魔法師、傷痕者、繼任者、守門者、流浪者、門外的第三元力……最後都集結在最後一位先知的地方決定世界的命運……
「心理系」奇幻大師夫妻檔——賽爾基&瑪麗娜.狄亞錢科,文筆獨特優美,人物描寫細膩,筆法與英語系作家完全不同,特殊的敘事腔調,以及帶有俄羅斯童話色彩的奇幻氛圍,有如魔法版《罪與罰》在語言形式和人物內心的探究上,均承繼了優良的俄國文學傳統。
作者簡介:
賽爾基&瑪麗娜.狄亞錢科Sergey and Marina Dyachenko
這對烏克蘭夫妻檔作家賽爾基和瑪麗娜.狄亞錢科文壇佳偶,其小說和短篇作品已獲得眾多文學獎座的肯定,並榮獲2005年歐洲Eurocon最佳科幻小說作者大獎,目前兩人定居於基輔。發表於 1997 年的奇幻小說《傷痕者The Scar》,是狄亞錢科夫婦「流浪者系列」(Wanderers Series)四部曲的第一集,與前傳《守門者The Gate-Keeper》幾乎拿遍俄國所有的奇幻文學大獎,也奠定了他們「心理系」奇幻大師的地位。
譯者簡介:
伊凡尤命
泰雅族,政大斯語系畢業,自由譯者、蕎麥飯愛好者,曾於俄羅斯聖彼得堡、莫斯科、切爾克斯克、烏克蘭基輔等地留學及工作。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作者獲獎記錄:
◎2005年歐洲科幻大會年度最佳作家
EFSF’s (European Science Fiction Society)Best Writers of Europe in Eurocon 2005.
(2003年為《夜巡者》作者謝爾蓋‧盧基揚年科Sergey Lukyanenko獲得同獎項)
◎《傷痕者The Scar》獲選「文化部第37次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本系列前傳《守門者The Gate-Keeper》獲得1994年俄國「水晶桌獎」最佳處女作。
◎《傷痕者The Scar》獲1997年「石中劍獎」最佳科幻小說肯定!
《傷痕者The Scar》在俄國賣座超過100萬冊!
名人推薦:
蔡曉玲(逢甲、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作者最擅長心理學領域的奇幻小說,獲得眾多文學獎座的肯定。」
「非常精彩的作品,故事饒富趣味,細節豐富細膩,優點多不勝數、卻幾乎挑不出毛病,我很肯定地給予五顆星評價。」——from GoodReads reader’s review
「多年來狄亞錢科夫妻書寫著人類靈魂在混沌與秩序、自由與體制之間模糊地帶所經歷的奇異蛻變。」—— Knizhnik-review
「這對作者搭檔不容小覷,他們並不專注於故事的驚險刺激,而以普遍人性為根本,筆下角色脆弱平凡、並非能夠殺人於無形的世外高人,但卻總面對殘酷的抉擇,擺脫不了生命的重擔──抉擇不僅是權利,更是責任。」—— Knizhny Klub Magazine (The Book Club)
「兩位作者創造了令人訝異的另一個世界,時而冷酷無情、時而美麗炫目。或許正因為他們無論年紀、性情與之前投身的行業(瑪麗娜之前是女演員,而賽爾基則是精神科醫師)都差異如此之大,才使讀者得以見證奇蹟。」—— The Viva Magazine
「狄亞錢科夫妻寫作成功的秘訣除了精緻的筆觸以外,也在於寫實的風格底下會摻入一點幻想元素。每部作品之中都只有少許奇幻成分,但卻因此得以觸及純寫實小說迄今(或許永遠)無法碰觸的人性複雜之處。」—— Znamya Magaizne
「賽爾基與瑪麗娜.狄亞錢科的寫作策略沒有破綻:他們將最不可思議的前提放在最樸實但又細緻的脈絡中,並以最普通平凡的角色包圍最為殊異的主要人物。這樣的對比擦出的非凡火花更加耀眼明亮,也使讀者更容易看清人類面對的心理與社會問題。」—— Realnost’ Fantastiki Magazine (The Reality of Fantastic)
「狄亞錢科夫婦出色不僅在於身為優秀的作家(當然他們的才華足以傲視群雄),也在於他們特殊的創作模式:兩個人先以個人的想像各自構思,然後才將想像融合,成果自然層次豐富、規模宏大……」—— Mir Fantastiki Magazine (The World of Fantastic)
「在這鬥爭劇烈、道德淪喪的年代,賽爾基與瑪麗娜.狄亞錢科卻願意堅持自己創造的世界,那個世界仍有良知運作,勝者也必須受到批判。」—— Novosti Stolitsy daily newspaper (News of the Capital)
「賽爾基與瑪麗娜.狄亞錢科帶領我們看見書中世界,甚至超越了書本的形式,如同看一部精心製作的電影──那是賽爾基的劇本寫作功力加上瑪麗娜的演員生涯相輔相成後的結果。」——Perekrestok Mirov (The Crossroad of the Worlds)
媒體推薦:
「豐美而生動的文字,紮實卻又出人意料的劇情,還有超凡的人物刻畫,可與最優秀的俄國文學媲美。這是一部真正令人心醉神迷的作品,即便是對老套英美奇幻小說感到厭煩的讀者,肯定也會愛不釋手。」—— 柯克斯書評(Kirkus)
「賽爾基&瑪麗娜.狄亞錢科的作品不是島嶼、更不是大陸,而是整個銀河!」——《烏克蘭雜誌》(The Ukranian Magazine)
「豐美而生動的文字,紮實卻又出人意料的劇情,還有超凡的人物刻畫,可與最優秀的俄國文學媲美。這是一部真正令人心醉神迷的作品,即便是對老套英美奇幻小說感到厭煩的讀者,肯定也會愛不釋手。」——柯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 starred review)
「賽爾基和瑪麗娜.狄亞錢科的《傷痕者》結合寓言故事的單純與俄文小說的複雜和豐富。」——圖書館學刊(Library Journal)
「……一個非正統的故事以魔法、愛情、祕密社團,以及時間盡頭為邊界在述說。」——書目(Booklist)
「賽爾基與瑪麗娜.狄亞錢科充滿創意,筆下故事難以預料發展,而且面向多元,難以一言道盡他們作品的奧妙,更不適合強套上科幻或奇幻底下的特定類型。他們的作品不是島嶼、更不是大陸,而是整個銀河!」——《烏克蘭雜誌》(The Ukranian Magazine)
得獎紀錄:作者獲獎記錄:
◎2005年歐洲科幻大會年度最佳作家
EFSF’s (European Science Fiction Society)Best Writers of Europe in Eurocon 2005.
(2003年為《夜巡者》作者謝爾蓋‧盧基揚年科Sergey Lukyanenko獲得同獎項)
◎《傷痕者The Scar》獲選「文化部第37次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本系列前傳《守門者The Gate-Keeper》獲得1994年俄國「水晶桌獎」最佳處女作。
◎《傷痕者The Scar》獲1997年「石中劍獎」最佳科幻小說肯定!
《傷痕者The Scar》在俄國賣座超過100萬冊!名人推薦:蔡曉玲(逢甲、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章節試閱
牆壁聞起來像是腐爛的抹布,獄卒手上的火炬在高處閃爍著。他 – 我是指獄卒不是火炬,自以為莊重的宣布:
「無罪之人阿,安心吧,因為法官會還你們清白的!有罪之人阿,委…畏、畏懼吧,因為法官會幹… 看、看清你們內心最深的陰謀並毫不留情地懲罰你們!」
說的內容是背得爛熟,但聲音卻是枯乾嘶啞,尤其這兒是監獄的最底部,讓我有種混酒的味道是從地底的喉嚨裡所散發出來的錯覺。
「沒錯,正義將得以伸張!」獄卒意有所指的高喊。他站了一會兒,觀賞著我們仰天的臉,然後門栓發出鏗鏘聲、絞盤機也嘎吱作響 – 砰的一聲關上了審判室的鐵頂蓋。就像蓋上湯鍋似的。
「光明的老天啊,救命阿,保佑阿」小偷兒在黑暗中呻吟了起來。「噢、我再也不會動任何一根手指了,我再也不拿任何一毛錢,只求祢的寬恕阿,噢…」
其他人都安靜不語。
好幾個月前在森林裡被逮捕、且等待審判之夜近半年的獨眼強盜沉默著。就算拿糖灑滿他全身看起來也會彬彬有禮的老人沉默著,順帶一提,他被指控強姦並殺害了一個女童工。而審判室裡唯一的女性也沉默著 – 是說我也不知道她是犯了什麼罪而被丟來地牢。
「救命阿,光明的老天… 我再也不敢了…」小偷兒啜泣著…
眼睛慢慢適應了黑暗。老人像是啄木鳥般敲著自己的燧石,嘗試敲出一點火花。強盜從鼻孔哧了口氣出來。
審判室裡的空氣變得濃稠,像是樹脂靜置在桶子裡,沒有微風吹動,也沒有通風口。我想我很快就會溺死在這些香氛中 – 潮溼又腐爛的抹布味、強盜身上散發出的臭味、從女人那也傳來一半沒洗澡一半甜香水的異味…
所有的味道混在一起,瀰漫在石頭的地板上。我用手沿著牆壁摸索,找到了遠方的小角落,還沒決定要不要坐下,身體已靠上濕答答的牆壁。
「這裡有蠟燭!」老頭開心地告知。「黏在角落… 先生請看一下,那邊的角落是否也有蠟燭?」
「先生?」- 很明顯地,是對我說的。
「他們驕傲的很」女人冷冷地說。「不會跟我們這些賤民說話的… 等法官來,看他怎麼好好地鞭他們一頓!」
小偷兒的呻吟變得更大聲了。有人 – 似乎是強盜 – 像是背負著任務般地朝小偷兒的肋骨揍了一拳。呻吟聲立刻消失了。
「管好妳的小舌頭吧,」強盜幽幽地向女人建議。「怎麼,妳覺得妳就不會被鞭?」
「我是清白的,」女囚鄭重地聲明。「我、我什麼都不怕…」
「我在市集裡偷了個錢包,」小偷兒低聲淒慘地承認。「在那個星期裡還偷了隻鵝… 偷了… 然後賣了…還有條項鍊… 是從大肚男那偷來的…」
兩支蠟燭先後燃燒了起來。不知怎麼地變得有點擠,好像溼漉漉的石牆往前踏了一步。而鐵製的天花板 – 湯鍋蓋 – 打算落在我們頭上似的。
「假如妳是清白的,」強盜瞇起他黑色的獨眼,「那妳又怎麼會落在這裡呢?」
「這些畜生就只會亂抓人,」原來女人是個中年的妓女,她傲慢地聳了肩。「法官會查明清楚的。」
「會查清楚的,」強盜邪惡地笑道。小偷兒哭了起來,繼續數算著自己的罪行:「還有去年… 從馬車上… 偷了兩袋… 還有在市集裡… 一樣是錢包… 商人的… 大嬸的…」
小偷兒的身材乾瘦還有個尖鼻子,看起來年約十六歲,一又開始懺悔就停不下來。他的回憶越陷越深,已經深到了童年時期 – 再過不久他就會想起五歲時從妹妹那裡偷來的那顆水果糖…
「各位先生,」老頭咳了一聲。「我,也許不是時候,但說實在的…司法正義非 鬼魅之事。實際上,法官大人也可能…」
「閉嘴吧,」強盜的聲音中清楚地透露出絕望。「就是碰上了阿!」 - 大家都沉默了。
老頭子倔強地把毫無血色雙唇一癟:「各位先生,我和衛兵隊聊過…只要找到對的方法,跟最粗魯的鄉巴佬也能聊開… 獄卒們最後說實話了… 最近二十年… 都沒發生過類似的事情。以前任何一個晚上走進這囚禁室的人,隔天早上都還能活蹦亂跳地走出去。只有一次,在五年前吧,有一個人因為太懼怕而心臟病發 – 所以說,各位先生,心臟病在哪裡都可能發生的,特別是對膽小的人來說…」
「那你就在這兒享盡天年吧,」女人譴責地嘆道,「住到頭髮全白,卻不知道法官…」
她頓住了。我一開始以為是強盜用眼神讓她閉嘴 – 但不,強盜的視線正盯著地板。儘管如此,女人還是不作聲,像是東西卡在喉嚨裡似的。就連她香水的甜都好像失去了自信一樣,味道變得越來越淡。還是只是我自己的錯覺…? 命運多舛啊!該不會這老頭子真的掐死人了?
「年輕的男士,」老頭抓住了我的視線,緊握著拳頭靠近心臟的方向靠去,「像您這樣體面,不用懷疑,也有教養的人… 您覺得鬼魅究竟能干涉人的事情到什麼程度?也就是說,當然,他們是能說預言或是其他的,但說到司法,在我看來,怎麼說都是人類自己的事啊…」
「那你到底有沒有幹掉那個少女?」強盜陰沈卻興致勃勃地問。「如果沒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但如果有…」
老頭憤怒地揚起眉毛,但他似乎覺得不夠,又將十指交纏放在頭上,一副 ''這是多麼愚蠢又毫無根據的控告''的樣子。
女人森森的冷笑著:「如果你是清白的… 你幹嘛坐立不安?」
「我不跟你們說了,」老頭忿怒道。
他以為我會跟他聊天。真是白費力氣 – 因為我一點都不想跟他說話。
我好累。先前牢房裡有發臭的褥墊,我連碰都不想碰,所以決定睡在什麼都沒有的長板凳上,牢友們在牢房裡沒有其他的樂子,就抓起了跳蚤來並往我的襯衫底下塞。他們覺得我怕跳蚤的樣子很滑稽…
就這樣過了一個星期。我後來想想,如果我是兩個月前就被抓來這,可能就像強盜一樣坐在牢房裡兩個月,或三個月,或四個月,一直在這等著審判之夜,甚至還可能跟跳蚤們變成好朋友,反正牠們都也已經在我的手掌裡跳了好幾圈的輪舞。
還好,審判室裡沒有這些褥墊。但要從塔裡逃脫,如同他們所說的,是不可能的。因為吊橋在二十四小時都有衛兵隊嚴格的監視下根本不可能放下,他們又在環著塔的壕溝裡養了一隻極兇惡的生物,說什麼我也不會想要用游的游過壕溝… 多舛的命運啊…
「年輕的男士,」老頭子會心一笑。「體面的人應該會感到非常鬱悶才是… 就像我一樣,潮溼、惡臭就讓我很苦惱… 但事實上我們可是空前的走運。明天我們就會像鳥兒一樣自由。」
小偷兒嗚咽地說:「那法官呢?」
老頭輕輕地微笑。這是一種當一個人知道的比別人多的時候就會出現的特別的微笑。
「一清早就會放了我們。」老人瘦乾的手像父親般放在小偷兒的後腦杓。「別再哭哭啼啼的了,小伙子。這裡已經夠溼了。」
女人嗤之以鼻。強盜默不作聲。
整座塔沉寂了起來; 想必就連衛兵們都穿著纏著抹布的靴子,還踮著腳尖走在牆壁間裡吧。橋上的執勤員們互使眼色,用手掌遮住燈籠: 「嘖… 審判之夜…」
我還是忍不住地朝冰冷的地板倒去。身體緊貼著雙腳坐了下來。背靠著牆。
快點吧。不管結果什麼都好,讓這過程快點結束吧…
當然,如果在這大半夜的從牆壁裡會打開一條暗道,然後從那裡走出衛兵隊扁扁的鬼魅長官… 滑稽地令人難以相信。但事情又不是這麼簡單。
審判室裡變得更冷了。安靜下來的小偷兒緊偎著老人,另一邊女人雖然已經表示自己是冤枉的,卻也發抖的越來越嚴重,不單單是打寒顫而已。強盜靜靠在另一面 – 但他卻變得越來越陰沈,而且不時地環視著審判室,直到我跟他對上了眼。
強盜不相信老人善意的保證。強盜知道自己過去的作為 – 而且有些事情哪怕是不用法官,連最無所謂的鄉長都能直接把他送上絞刑台。
「最好是直接吊死。」他的聲音讓我倒吸了一口氣。看起來,我們想的一模一樣。
「最好是直接吊死,」強盜的眼神掠過我並固執地重複。「要判… 應該要判已經知道的罪行啊… 」「哪像這樣…直接全部定罪…」
他嘆了口氣; 這氣讓蠟燭的火搖曳了起來。小偷兒又啜泣了起來,女人緊閉著雙唇,老人的眼中閃過一絲絲的不安卻又立即消失,耐著性子冷笑道:「沒有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做過什麼事… 你呢?怎麼不去審判呢?你不是還活著嗎?」
我攥緊著手指頭們。石室裡好冷。非常冷。非常。
我叫做雷坦納爾˙雷寇塔斯。一個星期前我當著逮捕我的人們面前說出了這個名字。然後又說了一次 – 在狹窄的裁判室裡。我想這樣就夠了 – 所以其餘的時間我都不發一語。不開口多說一句話 – 這是身為雷寇塔斯家族後裔的我,僅存的自尊心。
這些匹夫們對我的名字沒有任何印象。一點也沒有; 他們平淡地讀著我的檔案,而且每一次,當他們骯髒的手指頭碰到諭狀時,我感覺就好像他們摸到我的身體一樣。什麼?偉大的魔法師達米爾是光榮的雷寇塔斯家族的祖先?什麼?赫美策斯男爵?要知道,我的這些獄卒們好不容易才看懂老舊紙張上潦草的字跡啊。
我用沉默回應這些荒謬的指控。當他們把我送進滿是跳蚤流氓的牢房裡時,我還是不發一語。當被送進法庭時,我依然保持緘默…
而現在,在這寒冷等待中的夜晚 – 我認為,若是我的舌頭再不鬆開,話語可能會自己找別的出路。用爬的,最好的情況是,從耳朵爬出去。
「那麼,」我用著好像是別人的嘶啞聲問道,「法官向誰宣布判決?向被判刑的人們?好讓他們認為自己應該跑向劊子手然後在他耳邊重複一次判決的內容這樣?」
沒有人對我這突如其來的多嘴感到驚訝。強盜把頭縮進脖子裡,這種雞才會有的動作與他的獨眼、黑色大鬍子、和魁梧的身材非常違和。
「法官,他自己也就是劊子手,」女人緊張地環顧四周,就像強盜之前一樣。「他怎麼判 – 判決結果就會如何,這是可想而知的…」 「他們誣告我毒死了那個商人。可是我沒有毒死他,是他自己心臟病發作,我也只是拿走錢零而已…」
她緊咬著嘴唇然後重複了強盜的動作 – 把頭縮進脖子裡。怎麼搞的連我都想把頭縮起來。
「那您呢,年輕的男士,被指控了什麼罪呢?」好一個簡單又富善意的問題。還沒聽完他的話,我就突然驕傲地抬起了下巴。老頭子慌了起來:「不、不… 我不是有意讓您…」
「法官很快就會知道我是無辜的」女人快速地回答。「他的死跟我無關, 無關, 無…」
「別說了,」老頭子輕輕地建議。「難道有證據可以證明是妳毒死他的?他們有從妳身上找到毒藥嗎?還是在死者的肚子裡找到毒藥?還是有誰看到妳毒死他的?啊?」
女人搖頭。
「證據啊!」老頭子一根細長的手指向上,「如果沒有任何證據…」
「笨蛋!」強盜沙啞低聲說。
「法官… 他…」女人開了口,想要說些什麼 – 但沒繼續說下去。大家都沉默了,像被人下令似的; 審判室裡再次被死寂所籠罩,蠟燭的火變得尖銳且不再搖曳,我的皮膚像是被寒氣撕裂開來。
上頭的絞盤機似乎動了起來。是獄卒嗎?
鐵頂蓋笨重地躺著,呼吸變得越來越困難了,他們要整死我們,就像整死老鼠一樣,或許,這就是審判夜的公義所在?
「安靜,」強盜低聲道,就算大家都已經屏息不語。「安靜… 安靜…」
我臉旁的濕石上頭爬著一隻有著透明腹部的銀白色潮生蟲。
蠟燭的火舌晃了一下。擺動了一下,但不明顯,像是有風吹過,從容不迫地,虛弱地,像海底裡的海藻。我發現,強盜的表情變了,小偷兒骯髒的臉沉了下來,女人舉起了雙手,像是要閃避飛向自己臉的石頭; 他們三人都不再裝了,全跑向老人尋求幫助及支援,剩下我一個人坐著,背陷在石頭裡,非常冷的石頭,非常,冷的像是我自己的墓碑似的。
蠟燭熄滅了。但其實,也不需要蠟燭了。
他就站在審判室的正中央; 在那瞬間我以為,他並非血肉之軀,透過他衣服的皺褶看得見對面的牆,而且他的短腳並沒有碰到地板。
可能,那個瞬間真的是這樣 – 可是一秒後,他穿著粗糙農民鞋的腳露了出來,真實且具體地站著,就像我,就像強盜,就像小頭兒,就像牆上的潮生蟲一樣。
我驚恐地用眼睛尋找暗門。乳白色的光讓審判室更像石製的擠乳桶,牆壁變得模糊又遙不可及。沒有一絲絲細縫,沒有一丁點兒孔,出現在這裡的鬼魅是從哪裡插入鬼鑰匙的…
難不成,他真是鬼魂?
他看起來並不老。小小的頭上戴著厚重的灰白色假髮,孱弱的身體隱沒在多皺摺的法官大禮袍中。厚重的鞋子看起來像是法碼,像是錨,緊緊地嵌入那如同蜘蛛腳般纖細穿著長黑襪的腳中。他看起來也不可怕 – 一點也不,也不高傲,反而像個鄉長去法院似的,嘗試讓自己看起來比平常更有威嚴、更聰明…
「各位,你們好。」
這聲音讓我冷汗直流。
我討厭鐵片刮玻璃的聲音。我討厭蜘蛛網被撕裂所發出輕微的啪聲; 法官的聲音都包含了這些聲音,不是真的包含,但卻已經足夠讓我想把耳朵捂住。
小偷開始在石頭地板上抽搐,用盡全身的力氣雙手按在肚子上。
女人打了個噎。老頭子坐著不動,平和的坐著,就好像坐在自己家裡面一樣,獨眼的強盜卻卷縮在老頭子的膝蓋旁,一伙人看得傻眼!傻眼地就好似看著一幅畫著隱士生活的木版畫…
「那麼,」法官四面張望像是在找個舒適的地方,然後走向牆,兩手交叉放在胸前,肩膀靠上牆壁「嗯。這樣我才看得見你們大家…」
他的小黑臉上有著光滑的下巴,細細的鷹勾鼻; 一小撮的灰白色假髮雜亂地垂在額頭上,但在那撮假髮下的眼睛卻像兩根黑色的大頭針似的,微微地發亮著。
「各位,你們每一位會被帶來這裡都是因為一些特別不幸的事情… 那麼,我們開始吧。」
「請聽我說!」女人語無倫次地說著。「我會解釋… 我… 請聽,我沒…」
「我不聽。」
法官針似的目光讓女囚的舌頭順利地黏在上顎。她像是尋求幫助般,緊緊地抓住也變得肅穆的老頭子的衣服 – 老頭子面無血色,在乳白色的光中,隨著法官的每一個動作,慘白的程度就越來越像張白紙。
我想用背把牆壁弄暖 – 但怎麼也弄不暖。就好一塊巨冰在我肩後,在我完全失溫前,盡可能地吸取我的體溫。身為真正雷寇塔斯家族的後裔,我高傲孤獨地等待自己的命運,但怎麼我竟也感覺到寂寞在這個時刻是如此難受。
「我們開始吧」- 如此不悅耳的話。
「我們開始吧」手中拿著箝子要拔牙的 理髮師會這樣說。「我們開始吧」醫生豎起手術刀時會這樣說。「我們開始吧」從桶子裡拿出籐條的教師會這樣說… 「我們開始吧」法官也這樣說。
我叫雷坦納爾˙雷寇塔斯。在我的家族裡都是高官和魔法師。被我放在小旅箱的諭狀,是我達官顯貴的曾曾外祖父頒給我曾祖父的感謝狀,因為他救了當地居民殺了惡龍,赫美策斯男爵能得救,也是託大魔法師達米爾的福。而那時後的拉特˙雷吉爾還只是他的僕人而已…
小時候我為了要看見靜脈裡的血液,就割了自己的手。
現在我卻在這濕臭的審判室角落裡坐著,某個法官從牆壁裡冒出來,打算來定我的罪。或許特別是後者的關係吧 – 不枉費城裡的衛兵們發狂似地在大馬路上追我,把我從馬車上抓了下來拖進這該死的牢房裡…
「我不打算聽,」法官緩緩地重複說道。「不用再多說什麼了,因為你們說的,做的,說實在的,已經夠多了… 至於妳,女人,妳被指控謀殺的罪是沒有依據的。一個月前死在妳床上的那個人不是妳殺的。」
在審判室裡的所有人 – 除了法官以外 – 都倒吸了一口氣。然後老人開始咳起嗽來,小偷兒發出一聲驚叫,強盜從齒間也發出嘶嘶聲,而女人就站在那 –
一直吸氣直到肺爆滿了空氣,圓的像個氣泡似的,紅色的眼睛裡透出難以置信的幸福感。她不發一語,臉卻越來越紅,像在決定要不要吐氣似的。
「但其他的,」法官刺耳的聲音像是在取笑人,「妳的罪行多不可數,妳偷了死人的東西,妳用身體賺錢… 從今夜起,任何一個男人的擁抱都會變成妳痛苦的來源。想繼續重操舊業 – 就繼續吧,妳的工作將變成妳的懲罰。妳聽見我說的話了,人稱床墊女的蒂莎。判決已定。」
女人,似乎忘了怎麼吐氣。她的臉由紅逐漸變紫,最後變成了青藍色; 沒人想到要去拍她的背,去把卡在她喉嚨裡的判決書給拍出來。
甚至沒有人看他一眼。大家只想著自己,連我也是。
法官換了個姿勢 – 可以聽見他笨重的鞋碰到石頭的悶聲。法官長袍的皺褶裡一瞬間露出了一條寬大的金色鎖鍊,而下一秒鐘已被絲絨蓋住不見了。
「下一個要聽誰的?」法官毫不遮掩地冷笑,他的小頭晃了一下,假髮落到了眼睛。法官調整好自己的帽子,就如同修正自己失態的樣子。「要不就你吧,克利維˙梅尼丘諾克?」
小偷兒抖了一下。跳了起來,又馬上咚地一聲跪了下來,在石地板上爬向法官的鞋子,悲情地唱了起來:「我-我… 濕…窩… 說… 頭…」
真是個有天份的小夥子。早應該要用聲帶來工作阿。
「偷竊,」法官冷冷地說。「有朝一日你會因偷竊而被判絞刑… 還是算了。從現在開始,別人的錢會如火般灼傷你!而如果你真的被吊起來的話,一定是因為別的事… 你聽見我說的話了,克利維。判決已定。」
整個審判室再次變得安靜。我用餘光尋找潮生蟲 – 牠卻消失了。
「現在輪到你了,」法官再次把重心換到另一隻腳上,他的目光停在強盜身上。曾景何時,一個強壯且凶殘的男子漢、森林裡的殺人兇手,現在竟然就像個孤兒院裡的少女似的 – 害怕地抽搐著…
法官沉默了。看著臉部已嚴重變形的強盜,沉默了很久,然後打破沉思: 「你真是個奇怪的人,人稱蛙人的阿赫爾,你的每一個罪行都有三個可以減經的情..況… 但你殺了不少人,只好判你死刑…」
審判室裡充斥著逼瘋人的空氣。「但因為你求而受難,」法官沉思地連白假髮都低到黑色的肩膀。「你求饒了.. 所以一個月後再執行死刑。你聽見我說的話了,蛙人,判決已定。」
強盜不由自主地舉起手朝向繃帶 – 就是曾經是眼睛的位置。他仍然坐著 – 像是被強光照到的姿勢坐著。
法官又調整了假髮一次 – 儘管一點必要性都沒有。沈重的鞋尖蹭了一下石地板,大聲地嘆了口氣,然後他大頭針似的雙眼定睛在我的身上。
我當時為什麼沒有閉嘴 –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法官的小黑臉蹙起,像是吃到了酸的東西,他半張開嘴,準備要說些什麼 – 但就在這個時刻 – 彬彬有禮的老頭子就像是癲癇發作似的猛然抽動了一下,然後法官的目光就像隻笨重的蟲子,慢慢地從我身上爬開。爬過了整個審判室,爬到了 – 不久前被迫互相擠在一塊的室友們那裡。現在他們都分開了 – 女人仍在試著要把肺部裡多餘的空氣擠出來,小偷兒淚汪汪莫名其妙地望著,真不知道,究竟是開心還是在哭。強盜縮坐在另一邊,手遮住空空的眼窩,像是擋住乳-白色的光,擋住這漫長的 – 審判夜。老頭獨自一人 – 他的臉甚至比法官蓬鬆的假髮還白。
「是不是鬼魅都可以隨意地干涉人類的事務?」看來,這位彬彬有禮的老人是真的想知道答案。
因為法官忘了我 – 他的黑臉變得更沉了。薄薄的嘴唇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條刻薄的細縫。
「你,寇賀,別騙自己了。別騙自己可以逃過一劫。你逃不過的,寇賀,別奢望。」
「誣告,」老頭的聲音小到幾乎聽不見。「誣告,密告,沒有任何的證據… 她很愛到處遊盪,而且也生病了,誣告…」
法官抬起了尖銳的下巴。這一刻馬上就看清楚,在白色假髮下的瘦小身影投射在四個面,而我們都在著陰影下坐著,似乎,假髮上灰白色的頭髮正塞住我目瞪口呆的口,讓我無法呼吸…
我猛咳了起來。毫無預警地。法官他蜘蛛腳般纖細穿著長黑襪的雙腳,仍然靠著牆站立著,而審判室裡不祥的沉默 – 被我不禮貌的咳嗽聲給打斷了。
已經多少次了,我總是在最不恰當的時刻被嗆到。
「你,寇賀,你很快就要付出極大的代價。你的心已經腐爛了,二十四小時之內你就會像張發霉的硬紙板死去。你聽見我說的話了,珠寶商。判決已定。」
「誣告,」老頭子固執地重複道。女人用手掌遮住了嘴,偷偷地嗚咽著。小偷兒連滾帶爬地從老人旁離開,跑向遠處的角落裡待著。
法官的目光再次爬過整個審判室 – 爬回原來的方向。我知道它要爬去哪,而當兩根黑色的大頭針停在我身上時,我又猛咳了起來。
法官很客氣地等我咳完。他依然站立著,小小的頭顱在巨大的假髮下晃動,讓我覺得,他就像是從黑暗中、在地下室潮溼的牆壁縫裡長出來的菌類。
「雷坦納爾˙雷寇塔斯…」
我打了個哆嗦。我家族的姓氏從這邪惡的羊肚蕈嘴冒出,聽起來真詭異。
就好像,法官罵人不帶髒字似的。
「你的道路將通往泥沼, 雷坦諾。你的腰帶已被鮮血弄髒… 稅吏被吊在城門口,有人說是他活該,但你卻要為他的死負責,雷坦諾。你跟強盜一樣 – 但森林裡的殺人犯只是割喉,而你卻想出如此殘酷的領帶。你有一年的時間,一年後執行死刑… 你聽見我說的話了。雷坦納爾˙雷寇塔斯。判決已定。」
牆壁聞起來像是腐爛的抹布,獄卒手上的火炬在高處閃爍著。他 – 我是指獄卒不是火炬,自以為莊重的宣布:
「無罪之人阿,安心吧,因為法官會還你們清白的!有罪之人阿,委…畏、畏懼吧,因為法官會幹… 看、看清你們內心最深的陰謀並毫不留情地懲罰你們!」
說的內容是背得爛熟,但聲音卻是枯乾嘶啞,尤其這兒是監獄的最底部,讓我有種混酒的味道是從地底的喉嚨裡所散發出來的錯覺。
「沒錯,正義將得以伸張!」獄卒意有所指的高喊。他站了一會兒,觀賞著我們仰天的臉,然後門栓發出鏗鏘聲、絞盤機也嘎吱作響 – 砰的一聲關上了審判室的...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