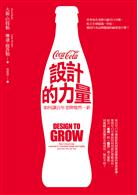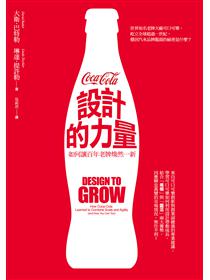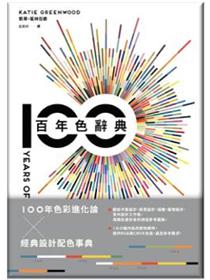衣飾忘憂:相體裁衣
看《我和Dior的華麗邂逅》(Dior and I, 2015)總覺得主角不是徘徊在Dior atelier裡的Christian Dior本尊幽靈,也不是新入主,面對完全陌生的高級訂製服行業,正徨徨不安的Raf Simons,而是在atelier裡那數十名裁縫。當中尤以女性為主,她們很多已屆中年,這套Dior and I將這些多年來被創意總監光暈遮掩的女裁縫師帶到世人眼前。
總說時尚是男設計師的世界,從十九世紀中後期起,固然有Madeleine
Chéruit、Jeanne Paquin、Jeanne Lanvin、Coco Chanel、Elsa Schiaparelli這些懂裁衣也會設計的女子,但業界內仍是以男性為主。來到二○一六年春夏之間,英國倫敦Savile Row終於有了第一名首席女裁縫Kathryn Sargent在這兒開業,這可是裁縫街二百年來首名自立門戶的女裁縫。不禁叫人思索女裁縫的故事是怎樣的?
裁、縫:掩蓋與掀露
裁縫是相體裁衣的職業,由是經由手藝,裁縫為一個特定的身體裁出最適合它的衣裝。當中必然包括一些直覺:怎樣去感知一個身體,怎樣以各式觸感、溫度的布料,去或掩藏或顯露這個身體的一些面向。二○一五年的電影The Dressmaker(港譯《華麗轉身》,二○一六年上映),正是關於一個女裁縫怎樣以她的裁縫技巧報復虛偽的世界。電影改編自澳洲作家Rosalie Ham同名暢銷小說,講述五○年代,一位才華洋溢的服裝設計師Tilly,她在巴黎為Madeleine Vionnet工作,後者輾轉將她推薦給Cristóbal Balenciaga。本來前途一片光明,卻執著於自己小時候背負殺死小男孩的罪嫌被趕出小鎮,為了找出真相,毅然帶著縫紉機從巴黎返回澳洲小鎮。
故事背景設在小鎮,幾將封閉社會裡的偏見與病態都呈現了——鎮長、老師、士多老闆、警長、醫生、被歧視的寡婦,每人都長久地扮演各自的角色,沒有流動的改變。而從外界回來的女主角,帶回了各式時尚新裝,故事就此展開。將時裝與小鎮並置本身已是十分有趣的設定:你怎能在閉塞的社會中了解時間的流逝呢?猶是死去兒子的女人仍沉浸在二十多年前的悲傷中,Tilly的母親仍背負著女兒是殺人犯的屈辱。但縱是如此,走在時代前端的新裝,依然在這如死水的小鎮裡施展魔力。
Tilly一回到小鎮,她的New Look裙子就引起易服癖警長的留意,也引發小鎮女子妒忌。流言四起,她當然仍是二十多年前懸而未決的殺人犯,但憑藉一身華服,男子對她刮目相看,女子亦知道她能為她們改頭換面──擁有製作華服的技巧就是擁有操控他人慾念的能力。一如她時而失智時而清醒的母親說:「You can create. You can transform people. That’s very powerful. Use it. Use it to against them.」
於是她利用巴黎、倫敦等地運來的最新布料,跟警長交換當年的口供;利用為鎮上女子設計新裝,用禮服交換真相,一件衣服換一個情報,製作當年的真相拼圖。她的華服使死氣沉沉的人都活過來了,這還真有點悖論:時裝本是重重掩飾身體的缺點,但真相卻因此被掀露。原來當年的事情,每一個人都在共業中,有害怕自己背上罪名而推指Tilly殺人,有不想牽涉其內,有害怕別人不信自己而不敢說出真相。大半鎮上的人都犯了各種邪惡,如嫉妒、壓榨、欺騙、利用等等。
為甚麼說擁有製作華服的技巧就是擁有操控他人慾念的能力?難忘電影中有一段,連當年憎恨她、一心認為她殺死自己兒子的鎮長夫人Mrs. Pettyman也來求助於她。細心留意,會聽到背景在播的音樂是電影South Pacific的「Bali Ha'i」。當鎮長夫人跟Tilly說:「I want to look better than everybody else!」女聲在唱:「Most people live on a lonely island, lost in the middle of a foggy sea. Most people long for another island, one where they know they will like to be.」或許換一身衣裝就足以令人誤以為可以離開孤島,到達想去的他山。
但事實呢?這套黑色喜劇,訴說的是外在到底能改變內在多少?或許醜惡的始終難以華衣掩飾,最後當Tilly得悉她無法改變小鎮的邪惡時,她一把火燒掉所有,並用一匹吸滿火水的紅布料將火焰引到各家各戶裡去。
十七世紀:從女裁縫到女設計師
華衣、慾念、邪惡、掩蓋與掀露……說得沉重了。不如說些輕鬆的,比如說,英國倫敦的Savile Row終於有了第一名女裁縫Kathryn Sargent開業,那麼歷史上是從何時起,女裁縫開始變得重要?
手上有《法式韻味》一書,翻開第二章〈時尚女王──高級訂製服的誕生〉,說到一六七○年的巴黎是現代時尚產業的起源。把時間往前推二十年,在一六五○年「衣服要選用何種款式是非常私人的事;裁縫到客戶家中幫忙試衣,這個過程嚴重阻礙了創新和變革。有多少新衣服或新配飾能被四處炫耀?如果一次只有一個顧客,那怎麼能夠向她灌輸擁有其他衣服的觀念呢?」
但到了十七世紀末,購物變成公眾活動,「貴族婦女首先邁出家門,前往那些創立聖日耳曼集市的商人所開設的高級時裝店購物;這些商店大多聚集在勝利廣場(place des Victoires)附近」。而因著這些轉變,原本只做些小修小補的女裁縫開始爭取設計和製作服裝的權利,到了一六七五年,讓這些女裁縫擁有正式資格的同業公會成立了,「couturice──女服裝師」這個詞語亦因此出現,認證了女性在將時裝改變為時尚產業上扮演著關鍵角色。當時第一批知名女服裝師,包括「商店位於勝利廣場的維倫紐夫人(Madame Villeneuve);商店全部開在佩蒂香街的雷蒙德夫人(Madame Remond)和普雷瓦特夫人(Madame Prevot);在蒙托古路(rue Montorgueil)開店的夏邦堤耶夫人(Madame Charpentier)。
世人都知道歐洲時尚出自宮廷,但那遠非流動的時尚,直至這些女服裝師在大街上開起了商店,婦女們爭先鬥艷,時尚才因為更流動於各階層而成為影響日深的行業。
《法式韻味》為十七世紀這批先行者正名:「十七世紀末的巴黎時裝界與現代設計師經常回顧汲取靈感、位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裝蓬勃發展年代有許多共同點,時裝在當時有了完全的重新定義。主宰這兩個時期的都是女性設計師,女設計師深諳女性顧客的需要:無論十七世紀還是二十世紀,出自女性設計師之手的時裝都頗具革命性,因為這些衣服比起之前的女裝都更為舒適,也更具體形意識。」
也更具體形意識,就是相體裁衣之意了。使一個身體因此掙脫束縛、因此而更自由,這可真是transform people,亦transform times。時代與人皆因衣之轉變而有所改變,最老土的說法,當然是愈舒適的女裝使女性能參與到更多的社會與經濟活動裡去。
二十世紀:女設計師大爆發
要談時代與女裁縫的故事,就不能跳過二十世紀初那一大堆特立獨行的女性。《法式韻味》說兩次大戰之間由女性設計師主導,此話不差。一六七五年,讓女裁縫擁有正式資格的同業公會成立,促進女性更方便地投入到事業裡去。而三百多年後,一九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美國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通過婦女獲得投票權,女性地位受到承認,無怪乎這段時期先後出現了多位重要的女裁縫/女設計師,她們的手藝與設計皆對女性的新形象起了重大作用。
世人都知道Jeanne Paquin是最早舉辦fashion show的女設計師,她讓模特兒穿著自己設計服裝在歌劇或是賽馬比賽開始前走台,一九一四年,她更在倫敦的宮殿劇院舉辦了第一個正式的時裝表演。但世人或許忘了她早於一九○六年推出了Empire-line系列,打破了當時S形的裙子廓形。Jeanne Lanvin於一九一六年推出「robe de style」裙子,它影響了上世紀二○年代早期的女裝輪廓。而Madeleine Vionnet的斜裁裙子一樣幫助女性擺脫了束腰,而且借助斜紋本身的張力,衣服緊貼人體卻不拘束,真正做到為身體的需要而裁衣。至於Coco Chanel的影響,就真的不用再詳述了,其打破的不止是女裝的藩籬,也是高級低級、正式休閒之間的界線了。
這些女性以創作改變他人,或許就以Raf Simons的話作結吧,他在Dior and I裡這樣描述那些在Dior atelier裡工作的裁縫:「就像流動的元神,創意的精神現今在屋裡蔓延,它延伸到了學徒和裁縫師那裡,他們的手指碾過那些樣品衣,他們的手指刺著針,或者在縫隙上停留,他們的手指正在創造,明天的時尚。」
爵士時代的女子
《筆羈天才》(Genius, 2016)是一套男人戲,不止因為兩個主角都是男人──傳奇編輯麥斯柏金斯(Max Perkins)與他一手捧紅的作者湯瑪士沃爾夫(Thomas Wolfe),講的也是一個年輕人尋找父親角色的故事,對沃爾夫這個從南方來到紐約的作者而言,麥斯不止在寫作路上引導他,亦如一個父親般使離家日遠的他在精神上有所依賴,他的第二本書《時光與河流》(Of Time and the River)就是寫父親的故事,他獻給了麥斯。但在這套男人戲裡,更吸引我的,倒是三個女角色:麥斯的妻子露易絲(Louise Saunders),沃爾夫的情人愛蓮伯恩斯坦(Aline Bernstein)及出場次數只有一兩次的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太太賽爾妲(Zelda Fitzgerald)。在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美國紐約,當麥斯與沃爾夫思考文字對捱餓的人有甚麼意義時,這些女人一樣掙扎著活出她們獨特的人生,縱使當中有犧牲、有隱忍、有悲哀。
Aline Bernstein:創立服裝博物館
時值二○年代末期的紐約,麥斯與沃爾夫是一組對照,前者努力發掘天才作家,一直克制自己對書寫的慾望,以數年時間刪減沃爾夫長達數千頁的文稿;沃爾夫則放縱自己的才情,日寫五千字,只懂放不懂收,小說總結不了尾。他們身邊的女人也是這樣的對照,露易絲想當劇場演員,卻不為丈夫支持,她也寫劇本,卻於飯桌上為沃爾夫所輕視;而愛蓮則不理世俗定規,拋夫棄子與年輕自己二十載的作家相戀,以舞台設計師與戲劇服裝設計師的身份養活自己。
在電影裡,這兩個女子圍繞男性而活,有一幕戲是這樣的:她們於劇院相遇,露易絲正看著一張劇場海報,恰好是愛蓮的劇,她們相遇後,兩個喜歡劇場的女子本該有太多話題可以聊,但在電影裡,當然安排她們找家餐廳,坐下來談身邊兩個男子的事情。
但事實上除了這兩個男性,她們一樣有自己的煩惱,這些男子女子的慾望其實都沒有分別,都是想找出自己是誰──那是二○與三○年代的故事,別忘記咆哮的二○年代(Roaring Twenties)其實也是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這些經歷過一戰的人,無論在歌舞昇平的二○年代,還是大蕭條的三○年代,一樣有他們對世界的懷疑與迷惘,一樣在理想與生活中拉扯,露易絲的選擇是將家庭置於首位,愛蓮則更追求個人的慾望,並成就一番事業。真要談談Aline Bernstein,現代時裝史不能錯過這一筆。生於一八八○年年尾,比Coco Chanel早三年出生,活到一九五五年,二十二歲時嫁給華爾街經紀,後來成了Neighborhood Playhouse的舞台設計師與戲劇服裝設計師。她也寫過書,除了回憶錄,她寫的大多亦與衣飾相關,比如一九三三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三套藍色西裝》(Three Blue Suits)以及身後出版的Masterpieces of Women's Costume of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她更與愛蓮路易松(Irene Lewisohn)於一九三七年共同創立服裝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Costume Art),其後併入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成為其服裝研究館部(The Costume Institute)。可以說沒有愛蓮路易松,我們現在還真的沒有每年的時裝熱話Met Gala晚宴。
Zelda Fitzgerald:美國第一摩登女子
電影裡麥斯遇上沃爾夫時已是二○年代尾,後者是無名作者,前者早已是金牌編輯,已於早些年發掘了費茲傑羅及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為他們推出大受歡迎的作品,此中有一九二五年費茲傑羅的《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記下的就是美國人戰後歌舞狂歡的日子,當中的享樂卻總有虛無如魅隨形。
在《筆羈天才》裡,費茲傑羅伉儷出場時已是三○年代,與美好的二○年代不同,賽爾妲神經脆弱,費茲傑羅為了醫療費用和生活費不停寫短篇小說賺錢,終致寫不出任何東西來。賽爾妲是在一九三○年四月精神崩潰的,恰如一九二九年爆發的經濟大蕭條,給二○年代劃下一個句號。一個時代的消逝、一個女子的崩潰、一場經濟的崩坍,竟環環相扣。電影裡,賽爾妲剛從療養院出來,她與丈夫出席麥斯家的晚餐聚會,沃爾夫醉酒後大放厥辭又狂吼,嚇得她雙眼蓄淚,這時的她,不再像前十年般風華絕代。
有一張賽爾妲的經典照片是這樣的:身穿H-Line低腰裙子,一頭fingerwaves短Bob髮,細長眉毛,煙燻妝,還有大紅嘴唇旁的黑痣,全是當時的流行造型。她手持香煙遞到唇邊,雙眸望著鏡頭在攝觀看者的魄。
這是經典的Flapper形象,無怪費茲傑羅曾戲稱她為「美國第一摩登女子」(the first American Flapper)。Flapper於巴黎的同義詞是「女男孩」(La Garçonne),取自一九二一年的流行小說《女男孩》,評論家更將Coco Chanel的風格稱為「Garçonne Look」。這「女男孩」之詞,卻無關乎去性別,當這些女子穿著輪廓簡潔、不再強調凹凸有致的寬鬆裙裝時,她們更自由的追求享樂,那些塗滿深色眼影的眼窩,開啟與閉上間全有關慾望──不願平庸的慾望。
賽爾妲寫過一篇〈摩登女子悼詞〉(「Eulogy on the Flapper」),第一句就是:「摩登女子已死。」所謂悼詞其實更是讚詞,已死之意,是賽爾妲想突出摩登女子是因其成就而活而非單為了追求摩登(I am assuming that the Flapper will live by her accomplishments and not by her Flapping.)她寫到:「摩登女子從貴族名媛主義的沉鬱中醒覺過來,蓄短髮、襯上等耳環與華麗妝容赴戰。因為好玩她與男人調情,因為擁有美好身形她穿藍色一件頭泳衣,她很明白她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她一直想做的。媽媽們都打從心裡不贊同她們的兒子攜摩登女子去跳舞、去喝茶、去游泳。」
賽爾妲就是這樣的摩登女子。要談論摩登女子,必離不開時代。二○年代是美國的「爵士時代」(Jazz Age,名字正來自費茲傑羅一九二二年的小說《爵士時代的故事》),年輕人剛從一戰的創傷中復甦過來,嚮往浪漫奢侈的生活,而戰時經濟向和平時期經濟轉型,帶來爆發性增長,新式消費品湧入市場造就經濟繁榮。工業量產的普及,使得汽車成本大降,人人買得起福特汽車,可以到處參加派對。這是為甚麼當一九二六年Coco Chanel推出小黑裙時,小黑裙被稱為時尚界的福特汽車,因為兩者一樣訴說了時代在變遷,階層分野更為模糊的故事。
費茲傑羅本人也是這樣的故事,一九一八年他遇上十八歲的富家之女賽爾妲,兩人相戀並且訂婚,但費茲傑羅的家世實難維持賽爾妲的揮霍生活,女方有意退婚,終因費茲傑羅的小說《塵世樂園》(This Side of Paradise)大賣,證明了他有賺錢能力,而娶得美人歸。二○一一年電影《午夜巴黎》裡就有費茲傑羅夫婦一晚走多場派對的場面,費茲傑羅的《大亨小傳》裡的蓋茨比與黛西或多或少也有他與妻子的影子。
《大亨小傳》由旁支人物尼克敘述整個故事,他來美國中西部,一如當時其他有為青年,都衝到華爾街一爭長短,因為一九二二年夏季的紐約,股市升到歷史高點,派對愈開愈大,滿街的汽車、華燈與廣告牌,道德益趨淪亡,早兩年頒布的禁酒令完全無效。尼克搬到紐約長島的西卵,這是新貴豪宅區,而他的表親黛西與其丈夫則住在對岸的舊權貴豪宅區,故事就在新舊權貴在紐約互相對峙的情況下展開。
在這樣的時代,那些眼窩塗滿深色眼影的Flappers,穿梭城中大小派對,尋歡作樂。但在此前不久,她們蓄長髮,穿更長的裙子,對自身的所感所欲未全面覺醒。費茲傑羅在一九二○就寫有〈柏妮絲剪髮記〉(「Bernice Bobs Her Hair」),描述了轉變中的女性。柏妮絲去表姐瑪喬莉家短住一個月,之前她受的都是女孩要有美德的教育,而大受男人歡迎的瑪喬莉讓她明白,世界早已改變,女子要懂得怎樣迷惑男子。瑪喬莉還教柏妮絲跟男孩們說自己要去剪短髮,以此成為焦點,最後柏妮絲在表姐起哄下,真的剪走長髮──故事倒峰迴路轉,男孩們都對短髮的柏妮絲失去興趣,她才知悉這是表姐設下的陷阱,最後她乘表姐睡著時剪去她的長髮報復。
故事寫的是兩個女孩的妒忌心理,但同樣顯示了當時大眾開始對短髮女子感到好奇,但又未願意接受短髮為美的心態。而不過兩年,《大亨小傳》故事所設定的一九二二年,蓋茨比大宅舉辦的豪華派對裡,觸目所及全是短髮Flappers。從二○一三年上映的電影《大亨小傳》裡,我們看見蓋茨比回憶五年前在黛絲家初遇佳人,那場舞會中所有女孩都蓄長髮。女性衣著在上世紀初二十年間的改變,比過去二百年還要多。
迷失的世代
自上世紀初起,女裝與女性的角色都在經歷翻天覆地的改革,在一切急速發展的二○年代,女子放肆地跳舞、自由地追尋自己是誰,她們確是在二○年代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但更多是在外表衣著、男女關係之中,這股解放女性的力量與消費文化結合,指向沉溺與歡愉,多於政治與社會權利。
比如說一九二九年的復活節,女人手持香煙,參與一場在紐約第五大道舉行的遊行,煙圈吞吐間,爭取的是女性自主和公共參與。雖然後來世人知道這是一場推廣香煙的宣傳活動,但Flappers正是此一結合經濟增長、工業發達、大眾宣傳而成的魅力形象,因此才得以經由名人生活將新的生活方式極速傳揚開去。自此,賽爾妲那手持香煙的經典形象不止在派對中出現,也成為大街內的日常風景。要知道不過在一九○四年,還有女子因為在第五大道點燃香煙而遭到拘捕。
但快樂的日子總不會長久,同年十月二十九日華爾街崩盤,後來再有這樣充滿魅力的女性解放形象,要到同樣迷失的六○年代了,但那是一個更有反思的時代。
《筆羈天才》電影開始時已接近二○年代尾,《時光與河流》於一九三五年出版後,歐遊歸來的沃爾夫,望著紐約到處排隊領物資的人,告訴麥斯這些經歷大蕭條的人都不會讀他的小說,他寫這些小說對這些人有甚麼用處?
大蕭條終止了爵士年代,迷失的卻不只是那些追夢的男人。賽爾妲與費茲傑羅關係一直緊張,兩個互有天分的人,都不滿對方在自己的作品中寫進他們的真實人生。賽爾妲一直精神起伏很大,《午夜巴黎》裡就有一場,她認為費茲傑羅不再愛她而上映的跳河記。
賽爾妲寫小說、寫詩,就是在一九三○年被送進療養院後,她亦在裡邊完成了半自傳體小說《為我留下那首華爾茲》(Save Me the Waltz),並於一九三二年出版,後來於一九四八年死於醫院的火災中,而費茲傑羅則在早八年死於心臟病發。
有人說她阻礙了費茲傑羅的發展,又有人說她是男權下的受害者。但或許沒有這樣的華麗人生與相隨而至的折磨,兩人都寫不出那些故事。與迷失、崩潰相隨的狂歡,正是大蕭條前的糖衣,這些各有風采的人就是糖衣的表象。難怪費茲傑羅如有靈感,在《大亨小傳》的結尾中這樣寫:於是我們繼續往前掙扎,像逆流中的扁舟,被湧浪不斷地向後推。他原來早在二○年代中期,預言了此一時代終會成為過去。
而《筆羈天才》裡,麥斯是這樣回答沃爾夫有關寫作之用的問題:在古老的過去,人類始祖躲在山洞裡,外邊有狼嚎,他們就是靠說故事來擊退恐懼。而費茲傑羅所寫的虛無與華麗相隨的故事,與這些二、三○年代女子的人生並讀,叫世人更明白璀璨時代的陰翳面向,叫人洞悉怎樣越過符號與慾望,追尋真正的自由。
縱使這種自由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