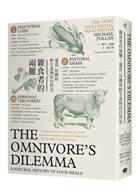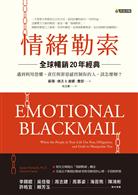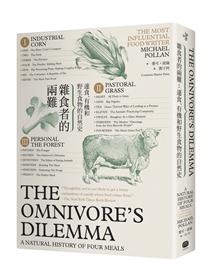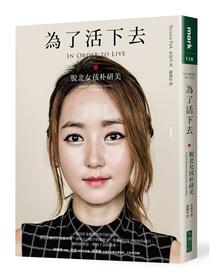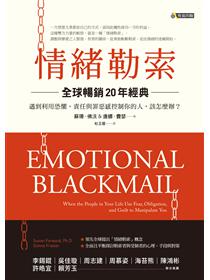綜觀一直以來心理學探討的核心議題,不外乎是:「我」在哪裡
「我」何所始?又何所止?「他者」又始於何處?★生態心理學經典之作
★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雷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專文推薦
一個人要與「自己深層的自我」調和,需要的不僅是一趟探索內在的旅程,也需要和外在世界的環境和諧共存。 ──詹姆斯‧希爾曼
九〇年代,本書編者西奧多.羅斯札克在美國倡導「生態心理學」,號召生態學界與心理學界相互對話與合作,共同面對人類與環境逐漸崩壞的關係。應運而生的這本經典文集,揭開一連串蝴蝶效應。
書中揭露,擁有健康的關係不只與個人心靈有關,更牽涉到地球上眾多生命的存亡。當我們開始在意環境、並同時回顧自己在關係中的模式,就可以發現荼毒著我們親密關係的控制、否認、虐待與投射等互動模式,和我們對大自然的不珍惜,背後的態度與形式,其實如出一轍。
在收錄的二十多篇不同領域的省思與實踐中,涵蓋從心理學觀點、兒童發展、女性主義、科技成癮等多種角度切入分析環境危機的論述,與包含生態式覺知技巧、完型治療或棲地復育的實務分享,以及薩滿式諮商和荒野治療等前衛方法等,讓這部旁徵博引又筆調犀利的著作,充滿自我的覺察與對大自然的關懷。
透過這本文集,在環境保護日益重要的當今,希望重新喚醒人類與大地母親最初的聯繫,從心靈角度發現愛護環境和愛護自己,其實是同一件事情。
我們為了要使用「我是」二字而產生獨立分隔的錯覺,是現代世界的問題之一。一直以來,我們在全球宏大模式中根植的程度,遠比我們膽小的自我所敢知道的還更深遠──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一個供我們體驗自己的靈魂,也體驗地球靈魂的場域。──華特.克里斯堤(緬因州立醫學中心精神科的副主任)
什麼地方,人的精神被踐踏了,生態環境便蒙災難;
什麼地方,人感到無力時,生態環境便蒙災難;
什麼地方,人活著感受不出生命的意義和目的時,生態環境便蒙災難。
換句話說,人蒙受痛苦時,生態環境便蒙受痛苦。──高爾(美國前副總統)
本書特色★生態心理學經典之作
★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雷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專文推薦
作者簡介:
西奧多.羅斯札克Theodore Roszak(1933-2011)
西奧多在九O年代的美國舉起「生態心理學」(Ecopsychology)旗誌,號召生態學界與心理學界的對話與合作。應運而生的這本書,猶如佛洛伊德《歇斯底里症研究》之於精神分析,或是瑞秋.卡森的《寂靜的春天》之於環境運動,揭開了一連串蝴蝶效應。
西奧多是歷史學教授,也是加州州立大學海沃德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Hayward)生態心理學研究所的所長,發表過許多作品,其中有嚴肅的文化論述,也有推理小說。在1992年的《傾聽地球的聲音》(The Voice of the Earth)一書中,他延展榮格的集體無意識和佛洛伊德的本我,從中得到合理的結論,認為這些術語所指向的就是「世界」,是為生態心理學的萌芽,隨後在1995年彙編本書。
瑪麗.鞏姆絲 Mary E. Gomes
鞏姆絲是加州北部的索諾瑪大學(Sonoma State University)的生態心理學助理教授。為舊金山灣區生態心理學團體(Bay Area Ecopsychology Group)的成員,生態心理學機構(Ecopsychology Institute)的共同主持人,以及《生態心理學通訊》(Ecopsychology Newsletter)的編輯委員。
艾倫.肯納 Allen D. Kanner
肯納是在加州門洛公園市(Menlo Park)和柏克萊私人執業的臨床心理師,也教授生態心理學,並在史丹佛大學醫學院的精神醫學與行為科學系擔任臨床教職。為舊金山灣區生態心理學團體(Bay Area Ecopsychology Group)的成員,生態心理學機構(Ecopsychology Institute)的共同主持人,以及《生態心理學通訊》(Ecopsychology Newsletter)的編輯委員。
審閱者簡介
陳俊霖
荒野保護協會常務監事、臺灣心理治療學會常務理事、亞東紀念醫院心理健康中心主任。
譯者簡介:
荒野保護協會志工群
荒野成立於1995年,致力以全民參與方式,透過自然教育、棲地保育與守護行動,推動台灣及全球荒野保護工作。成立理念為保存台灣天然物種、讓野地能自然演替、推廣自然生態保育、提供相關教育環境與機會、協助政府保育水土及維護自然資源、培訓保育人才。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James Hillman(榮格分析師、原型心理學創始者)
Lester R. Brown(聯合國環境獎得主、看守世界研究中心所長)
王浩威(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
李偉文(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作家、牙醫師)
陳玉峯(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山林書院創辦人)
陳瑞賓(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秘書長)
蔡怡佳(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
【原書推薦序——心理篇】
以地球為度的心靈
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榮格分析師、原型心理學創始者
所有心理學探討的核心議題只有一個:「我」在哪裡?「我」何所始?又何所止?「他者」又始於何處?
在其大部份的發展歷程中,心理學理所當然地認為,有一個具有意向性的主體,亦即自傳式的「我」(biographical “me”),負責職掌及承受一切的作為。大部份的心理學史便把這個「我」定位在個人之內,而所謂的人也不過是用肉體的皮囊和其直接的行為來界定。這個主體充其量不過就是「軀殼裏,以及與其他主體間種種關係中的我」。「自我」(ego)這個術語常被用來涵蓋這整套哲學系統,而自我所承載的一切則稱為「經驗」。
過去二十年來,與此主題相關的一切都曾被詳細檢視、拆解,甚至摒棄。後現代主義解構了連續性(continuity)、自我(self)、意向性(intention)、認同、中心性(centrality)、性別及個體性(individuality)。建立一套傳記式連續體(biographicalcontinuity)所需的記憶完整性,已受到挑戰。「自我」的一致性在多重人格(multiple personalities)的衝擊下,也顯得分崩離析。在所謂「投射性認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機制運作的片刻,可以將遠處的客體也緊附在「我」的心中,讓自己深信如果沒有這些客體,自己也活不下去;反之,即便是我個人身體的某些部位,有時也可能變得非常疏離,以致於自我殘破的身體形象甚至視那些部位為獨立個體,無法感受這些部位,儼然猶如「他者」。「他者」距離的遠近該如何界定?這是否就是「全然的他者」(Wholly Other),猶如魯道夫.奧圖(Rudolf Otto)深信的「上帝」一般?或者,這個「非我」天生就是與我相關的他者,如馬丁.布柏(Martin Buber)所謂的「禰(Thou)」?倘若我們再也無法確定自己就是記憶中的自己,那麼我們該在何處劃下「我」與「非我」之間的界線呢?
只要我們一天無法確定「我」的邊界觸及多遠(是在我的皮囊中?在我的行止間?或在我個人送往迎來所形成的影響與軌跡之間?),我們又如何能界定心理學的範圍?既然心理學的首要任務是要探討並描繪主體性(subjectivity),當今的我們又如何能清楚定義心理學的範疇?但,這卻是一個必須要做的工作。
在此,「心理學」(psychology)一詞就如字面所示,是研究心靈(psyche)邏輯之學(logos)。這意味著所有心理學在定義上來說,都是深層心理學(depth psychology),一是因為它預設行為背後還有內在的祕意(情緒、反思、幻想、感受、思想),二則是因為從兩千五百年前的赫拉克利圖斯(Heraclitus)開始,人們即已認為靈魂深不可測且無法捉摸。因此我認為所有心理學派在定義上,終極而言都是一種又一種的治療,因為它們都涉及對靈魂的探討。
心理學的歷史中,有個例子可以清楚說明「我」與「非我」之間的切割是多麼武斷。法國理性主義式的心理學,繼笛卡兒(Descartes)、馬利布杭雪(Malebranche)和拉.美特希(LaMettrie)之後,宣稱動物沒有任何意識(consciousness),甚至沒有痛的感覺。這是個使動物截然有別於人類的極端劃分方法。後來這個分界逐漸模糊,康德(Kant)同意動物擁有感覺,但沒有理性。達爾文對表情的研究,見證了人與動物之間深厚的相似性。隨後,當本能與天生釋放機制(inborn release mechanism)學說賦予動物有限的推理能力時,動物與人的距離就更近了。如今從動物身上耙梳出越來越多如「人類」般 的特質,有些特質甚至更超越人類的意識,致使人與動物分界的本身也開始受到質疑。
為心靈和心理學劃定界限的爭論,因為無意識(unconscious)概念的出現而變得更加複雜。我們無從為人類的認同感劃定界限,因為它從我們清晰的醒覺狀態,延伸隱沒到幽暗的夢境、斑駁的記憶、本能和不知從何而來的自發情緒裏。自從「發現無意識」以來,各種關於人格的複雜理論,都必須承認無論我所謂的「我」是什麼,它都有部分根源自並非我所能主宰和覺察的領域。這些無意識的根源,或許埋藏在任何所謂「我的」以外的領域,反而比較像榮格所謂的「類心靈體」(psychoid),半物質半心靈,猶如心靈與物質的融合體。這個類心靈體的源頭指的是生命的物質基礎。比如鈣在分類上屬於無機物,但存在於骨骼時,便能在生命體中受到生命活動所驅動。從物質的觀點來看,這些類心靈物質具有反應;而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這些效應則可被視為意向(intentions)。人們用來改變心理狀態的各種合法或非法的藥物,更對原本無法接受這種理論的成千上萬平民百姓,證實了類心靈物質學說中的物質意向性,或物質的「生命性」(liveliness)。所以,同樣的問題又來了,心與物的分野究竟在何處?對運用心理學做為療癒方式的先賢而言,心靈的最深處與生物軀殼(佛洛伊德)以及世界中的物質(榮格)是相融為一體的。
我在這裏回顧這些眾所週知的心理學理論基礎,是為了說明人類始終存在於更宏觀的自然世界裏。既然組成人類的物質和世界相同,這件事也就理所當然,怎麼會有別的可能?然而心理學的實務往往漠視這些事實的重要性。
西奧多.羅斯札克在探索生態心理學的《傾聽地球的聲音》(The Voice of the Earth)一書中,的確正視了這些事實。他延展了榮格的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和佛洛伊德的原我(id),從中得到合理的結論,認為這些術語所指的就是「世界」。
要使深層自我適應於集體無意識和原我,就等於是適應於有機與無機的自然世界。更進一步來說,一個人要與「自己深層的自我」調和,需要的不僅是一趟探索內在的旅程,也需要和外在世界的環境和諧共存。我們無法將最深層的自我限制成「在裏面」,因為我們並不確知它是否同時也,甚至完全是「在外面」!如果相信羅斯札克、佛洛伊德和榮格的說法,那麼,最深層的集體和無意識的自我就是自然的物質世界。
自我與自然世界的分界既然是人為的,我們可以將此分界線定成肉身的皮囊,或順著你的心定到多遠都行,甚至遠及蔚藍的大海和遙遠的星子。但分界本身的重要性,遠不如覺察到劃分界線的動作本身具有不確定性一事來得重要。這個不確定性使心智再度充滿好奇,使新思維得以進入心理治療的世界。或許處理我的感受,並不比處理附近環境的空氣品質來得更「主觀」。或許在我家院子用化學藥品除草,和我內心對待自己的童年回憶,代表著同樣程度的潛抑(repressive)作用。或許我深層內在自我中無意識承受的虐待(abuses),比起我周遭生態環境時時刻刻遭受的濫用(abuses)還相形見絀,而我也是這些破壞傷害的共謀或參與者。察覺自己是個受害者,可能要比承認自己是個加害人容易多了。
然而我們必須要了解,自我與世界之間的分野固然是人為武斷所訂,卻有其必要。實務上我們習慣為某一領域界定範疇,在此即是心理學領域。領域有了範疇後,才能基於其範疇內發生的事情,發展出自己的思想典範。但這張所謂「心理學」的地圖,只是不確定性疆域中的一小部份;事實上,這張地圖可能只是某個小區塊被過度放大後的放大圖。因此,對當前世界所承受的鉅大災難來說,心理學徒然鼓勵我們不成比例地過度重視人類的情緒、關係、願望、與憤懣。
心理學所造成主觀主義的過度膨脹,已使之自食惡果,因為回到治療室來的各種病症,正是這些心理學理論所引發的,諸如:人格本身就是無法遵循心理學所劃設的種種規定的邊緣性障礙(borderline disorders);耽溺在自己主觀的情緒中,所謂的「成癮」(addictions)與「復原」(recovery);無法將外在世界納入個人的知覺範圍的,被稱為「注意力缺損障礙」(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s)或「自戀」(narcissism);以及因為再怎麼努力也無法解決要在現實世界中達成個人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這種過度期待,所帶來的淡淡的憂鬱枯竭感。
我們可以指控治療式心理學吹捧了個人的內在世界,誇大其重要性,且有系統地漠視了外在的世界,這種誇大是心理學理論在拒絕涵括並抵禦真正宏觀世界時,所出現的補償作用。
簡言之,如果心理學是研究主體的學問,而主體的界限又無法確定,那麼不論情願與否,心理學將與生態學融為一體。
對深層心理學而言,這個融合過程暗示著,改變「外在」的世界,可能和改變我自己的主觀感覺一樣具有治療性。我身在「其中」的「惡劣」處境,指的可能不只是憂鬱的心情或焦慮的心智狀態,也可能是我白天辦公的密閉巨塔,夜間寢身的市郊特區,或者我用以往返這兩地之間壅塞的快速道路。
環境醫學和環境精神醫學已經開始研究真實的場所和物件,如地毯和窗簾等物,對人類各種精神障礙的影響。某些假設認為有些癌症會在近期產生失落感的人身上發病,失落的是什麼?僅指個人的失落嗎?或者個人的失落感使人有機會發現更龐大,卻更少被意識到的失落,即自然世界的緩慢消逝,一種整個文明共有的流行性失落?若真是如此,那麼深層心理學和生態學的結合意味著,要想了解今日靈魂的病症,得從了解外在世界的病症開始,了解世界所承受的苦難。……(節錄)
【中文版推薦序──環境篇】
尋找環境運動的曙光
李偉文╱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作家、牙醫師
2017 年元月,全世界關心環境的朋友,內心應該都五味雜陳,甚至是忐忑不安。
因為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即將上任,從他競選時對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的證據嗤之以鼻,當選後又任命素來對環境保護非常不友善的大商人擔任部會首長,這幾個月的國際情勢除了讓全球的有識之士驚愕得說不出話來之餘,不禁讓人反省,環境運動與環境教育數十年來,對全世界的發展究竟有沒有發揮作用?為何在人類文明面對抉擇的十字路口時,會有這麼令人不解的頓挫?而且這些完全違反多年來環運人士理念的競選言論,儼然成為社會主流?不然川普怎麼會當選?
這世界究竟出了什麼事?
我想一方面來自於恐懼,因為全球化競爭與社會典範轉移,許多人面對失業的恐懼與物質生活匱乏的擔心,使得人們無心思考數十年後的問題。
另一方面是人的慣性思考,認為環境問題是假議題,環保人士喊了那麼多年狼來了,可是什麼事也沒發生,至今每個人不是活得好好的。
其實,時代的變化,通常是漸漸的,漸漸的,一些微小的,片段的,零碎的改變,可是,突然之間,一切都不一樣了,原先似乎龐大堅固的結構就土崩瓦解,然後再也回不到過去了。
真實世界的進展,往往不是線性的,而是曲線,存在所謂臨界點或崩潰點,這對我們習於「昨天是如此,今天還好,所以明天也應該還可以」的線性思維,是很難理解的。
環境問題,往往是非線性的複雜系統,尤其是大氣和海洋生態,都是非常複雜的系統,也是「非線性」的系統。所謂非線性就是你對這個系統施以某一程度的改變時,它的反應不會和你的施加的力量成比例地反應,換句話說,有時候只有一點點改變卻產生很大反應,有時給它非常大的力量,它反而沒有多少反應,甚至會和原先預期的方向相反。
這種非線性的系統,是因為有太多正回饋與負回饋互相的干擾消長,很不容易去預測,因此,在全球暖化的研究與觀察中,可以看到許多矛盾的數據或現象,因此也會落入「數據會說話沒錯,但是一個聰明的科學家會讓數據說他想要說的話」這樣的陷阱。
對於「懷疑論者」而言,我想重提在一九八○年代歐洲因環境議題論戰所發展的觀念「預防原則」。
所謂預防原則就是指面對環境議題時,即使科學證據還沒有得到百分之百肯定的因果關係,就應該採取行動。因為歷史告訴我們,對於環境危機,一旦發展到十分肯定「就是這個罪魁禍首」時,往往情況已糟糕到無法挽救的地步。
再以通俗一點的方式來講,我們搭飛機買保險,顯然不是因為「確定它一定會失事」,所以我才花錢買保險,而是只要有會發生的可能風險,就會付出一定的代價來預防吧!
另外一個因素,也就是人類內心的恐懼與不安,1992 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地球高峯會議中,美國前副總統高爾(當時他擔任參議員)曾經說了一段話:
什麼地方,人的精神被踐踏了,生態環境便蒙災難;
什麼地方,人感到無力時,生態環境便蒙災難;
什麼地方,人活著感受不出生命的意義和目的時,生態環境便蒙災難。
換句話說,人蒙受痛苦時,生態環境便蒙受痛苦。
的確是如此,人若是身心靈都健康了,環境就會健康。
因此,要說服民眾,願意正視環境問題,願意為了將來而改變現在的生活習慣,我想,一定要從解決人心裏的不安來著手。
尤其近代物質文明的高度發展,阻隔了人與自然生命的互動,甚至人與人的互動也在電子訊息虛擬世界中變質,這種與真實世界的疏離沒有改善的話,很難真正改變自己,進而採取對週遭環境友善的行動。
從川普的當選,以及美國廣大民眾不承認氣候變遷的事實,更突顯了生態心理學的重要,因為只有療癒了人類的心靈,才會為復育地球採取長久且有效的行動。
生態心理學第一版是2010 年由荒野保護協會翻譯出版,提供帶領民眾接近大自然的志工作為進修與學習之用,現在很開心能夠與心靈工坊出版社合作,修訂改版,讓關心環境的廣大民眾有機會看到這本非常重要的著作,這本書或許是環境運動遭遇迷霧中,前方的一線曙光,也盼望大家閱讀之餘,能起身接近大自然,療癒自己,也復育萬物眾生。
【中文版推薦序——心理篇】
讓心向自然學習
王浩威╱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
人,可能單獨存在嗎?至少,這個觀念經常是被質疑的。
日本榮格心理學大師河合隼雄在和村上春樹對話時,提到他卅多年來的臨床經驗,很難在日本人的心智中體會到西方文明所說的「個體性/不可分割之最小單位」(individuality)的存在。
在西方的文明發展裡,從文藝復興運動後,以人為中心的人文精神或人本主義(humanism),代表著各層的意義,其中一層重要的意義是強調人的獨立存在,如瑪麗.雪萊(Mary Shelly)筆下的科學怪人,連生命也可以是經由人而產生,不必經由神鬼/自然。
雖然這觀念屢屢遭到挑戰,包括後現代思潮巨人之一傅科(M. Foucault)就提出反人本主義(anti-humanism)的看法,但是,這想法卻始終根深蒂固而屹立不搖,特別是在心理學和心理治療。
西方的心理學和心理治療,所有理論的提出,都假設了一個獨立人格的優先性,是唯一健康或正常的標準。如果我們有機會檢驗一下佛洛伊德的著作,他的豐富理論,便可以發覺這一信仰的徹底程度了。
但是,臨床上真的是這樣嗎?
A 是我多年的個案,一位經濟不錯,從小在美國長大的單身女性。我和她每週見面一次,她總是固定三五個主題重複不去,包括她和她經濟上所支持的父母如何持續衝突著。最早些年,我們討論著如何邁向成熟,包括結束和原生家庭的關係,包括獨處的能力。多年過去,她的痛苦始終如一。我是不耐煩了,她也感受到而生氣了:「可是醫生,人為什麼要獨立才可以呢?」這句話,確實是大哉問,反而開始讓我懷疑這多年來的治療。
更早以前,我還在花蓮行醫時,曾經遇到一位布農族的年輕人。他原本考上陸軍士校,後來政府開始招收職業女軍人,校園駐紮了一群女生。每次他坐在教室裡,即便操場是寬闊而遙遠,但是當這些女子部隊行進間的答數或口號聲音細微傳來,他都坐立不安,最後還恐慌、崩潰而退訓。回花蓮山上休養數個月後,他基於生計,到平地鎮上的加油站打工。可是,每當摩托車或汽車駛來,他的心臟又失控一般地亂跳。
臨床上這是一個簡單的案例:社交焦慮症。不過,在門診的過程中,最教我著迷的是他用腔調十足的國語,十分不自然地講起休養這半年來,每天和祖父去山上打獵的經驗。他說,空氣中的每一股氣味或地上的每一堆落葉,都充滿著豐富的訊息,而且是清晰地排列著。我忍不問他,這樣的訊息會不會太豐富,以致於讓他又慌亂了?他不太能回答我的話,只是描述著當清晨的風拂過樹林,或臨晚的飛鼠滑過林間時,他不必去分析,便清楚地和這一塊土地與森林知道了一切。然而,在小鎮上,他覺得所有的訊息都是混亂而不可預測的,以致於自己永遠都要處於備戰狀態。他描述的那個鎮我經常路過,不過是花東縱谷裡,在花蓮市和玉里鎮之間的一個極其安靜的小鎮,連觀光產業都沒發展的。
人,真的可以從家庭分化出來嗎?人,真的可以從大自然中切割出來嗎?還是,這原本就是另一種「異化」?
心理治療中的家族治療,部分的理論是最挑戰這觀念的。奧地利生物學家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將四○年代當時流行於泛物理、數理與工程的系統論思考,和生物學結合,提出大自然是普遍系統的理論(General System Theory),也就是人心到地表一切,都是連為一體的。人類學出身的貝特森(Gregory Bateson),也是家族治療在五○年代誕生的重要人士之一,在1971 年出版《邁向心智生態學》(Stepstoan Ecology of Mind)和1979 年《心智與自然》(Mind and Nature)兩書中,更強烈地影響著家族治療者。家族治療一直視家庭/家族為一個系統,雖然沒強調與大自然的關係,但也不再落入「個人至上」的人本想法了。
心理治療的發展,嚴格說起來是到了一個瓶頸的階段,許久沒有新的典範出現了。這一本《生態心理學》裡,許多文章揭示出大自然也許開始成為一種可能性。這些想法或許還不夠成熟,但也夠教人興奮了。
名人推薦:James Hillman(榮格分析師、原型心理學創始者)
Lester R. Brown(聯合國環境獎得主、看守世界研究中心所長)
王浩威(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
李偉文(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作家、牙醫師)
陳玉峯(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山林書院創辦人)
陳瑞賓(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秘書長)
蔡怡佳(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
【原書推薦序——心理篇】
以地球為度的心靈
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榮格分析師、原型心理學創始者
所有心理學探討的核心議題只有一個:「...
章節試閱
引言
當賽琪遇上蓋婭[1]
西奧多.羅斯札克(Theodore Roszak)
個人與全球
提到環境主義,我們想到的是個大規模的全球性運動,要處理的是龐大難以想像的複雜社經議題。環境運動是有史以來,人類所進行過最浩大的政治理想,它含括了每個人,因為也不能錯失任何一個人。它關照的範圍甚至擴展到人類以外的物種,及於所有的動植物,乃至山川大地。每當我談到環境議題的時候,都能強烈感受到其他非人眾生的目光也正在注視著我,我們的萬物同胞們正在仰望,期待這個令其不解的人類表親能看到自己錯誤的作為。
另一方面,當我們提到心理治療時,想到的卻是最小、最個人尺度的人際關係,亦即一對一,或是親密的團體關係。治療是很個人而且很內省的;治療處理的是生命中隱藏的一面,那些深埋得甚至連自己都不知道的恐懼、慾望、自責等秘密。
這兩個層級的文化活動能有什麼共同之處呢?在個人和地球之間能有怎樣的連結呢?
我們立即想到的是,環境運動與心理治療想要解決的規模,都和只想守成不變的政治思維大相逕庭。生態保育和心理治療的問題,就算能解決,也無法期待能在國家、區域自由貿易、軍事同盟和跨國企業所護衛的疆域中完成。前者的規模遠超過這些拼湊而成的詭異人為結構,後者也非這些遲鈍的體制所能掌握。或許這件事本身即存在著一項最重要的生態事實:我們活在一個地球和人類兩者,都乞求政治思維能有大幅調整的時代。從這個觀點來看,人類和地球有沒有可能都在追尋永續的經濟和情感生活所需的某種新基石,也就是能使親密情感和廣大生物圈結盟,且懷有能善待環境之公民精神的社會呢?
直到數年前,環境主義者和心理治療師們可能都還未能察覺到這種可能性。環境運動持續執行組織、教育和激發民眾的工作,卻很少注意到他們想要贏得的大眾,具有脆弱而複雜的心理。環境主義者對自然棲地複雜性的了解非常深刻,但心中看待人類行為的引導意像卻是極端簡化。他們憑藉有限的策略和動機行事,包括災害風險的統計數字,和恐懼及罪惡感等強制性的情緒力量。做為一個環保作家與演說者,我知道要淪溺於採用恐嚇和斥責的技巧是多麼容易的事;這些方法便於著手。畢竟,我們的環境習慣確有許多令人害怕及羞慚之處。雖然許多環境主義者是本於對壯麗野趣的真心喜樂而付諸行動,但是除了攝影家、電影工作者、山水畫家和詩人等藝術家以外,幾乎沒有人由衷相信人類能以這個活生生地球子孫的身份,做出合宜的舉止。
至於心理學家和治療師們對人類心理健康的理解,往往也不超過都市的界線。現代的心理治療乃是都市智能的產物,也只意圖用以平撫都市的焦慮,因而不曾被認為適用於家庭和社會以外的世界,去面對非人類棲居之地,然而這個領域卻大規模包圍了佛洛伊德所說「文明及其不滿」的微小心靈孤島。舉例來說,在《診斷及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這本由美國精神醫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頒布,讓保險公司付錢,讓法院認可其權威性,記載各種精神官能症的標準疾病名錄裏,大自然僅以單一種型態出現,「自然」只躲藏在「季節性情感障礙」(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這種因陰鬱的天氣所引起的憂鬱背後,而且還得排除此種憂鬱是否因季節性的失業所引起。經濟的因素被看得比自然的現象更為重要。[2]
如今跡象顯示,這兩個領域都已開始改變。新世代的心理治療師正在尋求管道,試圖讓專業的心理學在當代環境危機中插手相助。這項改變的指標之一就是這本書。你將發現具有環境意識的心理治療師們的思考範例,及其創新技巧的報告,都呈現在這冊由全國最頂尖的環境出版單位[3]銜命編纂的書頁之中。在此,你也將發現某些環境運動者的作品,這些人對永續心理學的需求展現出健康的好奇心,期待這種心理學能吸引正向動機與對自然的愛。這樣的觀照來得正是時候,因為我們亟須面對環境運動中可見的憤怒、消極與情感的枯竭。最近澳洲雨林運動人士約翰.席德(John Seed)在私人信件中這麼說道:
我很清楚我們無法透過一次救一片森林來拯救所有森林,也無法透過一次處理一項議題來拯救地球,如果人類的意識沒有更深沉的改革,所有森林很快就會消失。有心為地球效力的心理學家的加入,協助生態學家學習深入理解該如何促使人類心靈產生深沉改變,在此看來正是關鍵。
同樣地,美國執牛耳的「生態戰士」(ecowarriors)戴夫.佛緬(Dave Foreman),反對只用罪責與羞辱的方式帶動沉重的負面情緒,他睿智地提醒環保同志們,大家現行事業的更高目標,是要「開啟我們的靈魂去愛這顆亮麗璀燦、生機蓬勃的星球」。他提出警告,如果忘記這個目標,就是「在殘害個人的心理健康。」
親生命性與生態心理學
還有一個更有意義的改變趨勢也值得一提。生物學家們已開始注意到人類心理層面的演化。哈佛大學的動物學家威爾森(E.O. Wilson)在晚近的著作中,提出人類可能具有所謂「親生命性」(biophilia)的能力,亦即「人類天生對其他生命體的情感親近性」[4] ,並視此為挽救地球岌岌可危的生物多樣性的一股重要力量。只需簡單環顧民間故事與神話傳說,再看看原民部族的宗教生活,必然可以找到許多素材來支持這個理論。威爾森的同事當時很快指出,親生命性的影響力在某種程度上,可能被另一種同樣天生的「懼生命性」(biophobia)所抵消。但從心理學家的觀點看來,我們對自然的愛與懼都是情緒,兩者都值得研究。這兩種情緒雖然也可能化身為奉獻的熱誠、尊重、關切或敬畏,但都可以用來重建我們和自然環境的情感連結。那些因身處於環境日受破壞的工業都會而感到困頓的人,需要找到一切能得的協助,以克服我們與人類以外世界的疏離,那個我們每一口呼吸都必須仰賴的世界。確實,連我們可在精神上與這個世界保持和諧都只能是個「假說」,還有什麼比這更能說明我們的疏離感?然則,即便是假說的型態,親生命性概念至少激發了某些通過學術檢視,且可做為科學證據的行為研究。就某種意義而言,生態心理學可以視為心理學家與心理治療師們的承諾,以努力使親生命性假說獲得驗證,並成為理想中心靈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生態心理學」是最常用來稱呼這個心理(在此同時涵蓋心理治療與精神醫療)與生態相融合的新興領域的名稱。此外,下列幾個名稱也曾有人提出:心理生態學(psychoecology)、生態療法(ecotherapy)、全球療法(global therapy)、綠色療法(green therapy)、地球中心療法(Earth-centered therapy)、再地球化(reearthing)、以自然為基礎之心理治療(nature-based psychotherapy)、薩滿式諮商(shamanic counseling),乃至森林療法(sylvan therapy)。這些新名詞聽來似乎並不順耳;但若就此而論,「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在當年亦復如是。不論是用哪一個名稱,背後的設論都一樣:生態學需要心理學,心理學需要生態學。在我們這個時代,用以定義精神健全的脈絡已然達到全球性的尺度。
一如所有心理學的分支,生態心理學也關注人類天性與行為的基礎。不像其他主流心理學派自行侷限於內在的心理機轉,或偏窄到甚至不超越家庭層次的社會面向,生態心理學本著人類心靈最深處仍和化育我們的地球同心相繫的假設,持續發展。生態心理學認為我們可以將人類與自然環境的互動,即我們使用與濫用地球的方式,解讀為無意識需求與慾望的投射,就好比我們透過解讀夢境與幻覺,理解我們深層的動機、恐懼與憤恨。事實上,我們一廂情願且任性的在自然環境上印出的戳記,或許比我們明知為幻且一醒即忘的夢境,更能顯示出我們集體的靈魂狀態。我們每天在現實世界中,以鋼筋水泥、血肉身軀和剝自地球的物質資源,瘋狂製造「現實」的夢想,所造成的影響其實更為深遠。正因為我們學會將自己的意志加諸於環境之上,地球便成了一塊神經質的無意識用以投射幻想的空白螢幕。如果我們願意傾聽,所有毒性廢棄物、資源耗竭、對相伴物種的殘害行為等問題,都能讓我們看到自己最深處的自我。因此,詹姆斯.希爾曼曾敦促我們要將「石棉和食品添加劑、酸雨和衛生棉條、殺蟲劑與藥品、汽車廢氣與人工甘味劑、電視與離子」都帶入分析和治療的國度。「心理學總是靠著我們心中潛藏的焦慮,靠著將被揭露的真相予以病理化,來擴展整個學門的意識。我們的生態恐懼所顯露的,是當下靈魂的心理注意力所關注事物之所在。
向石器時代精神醫學借鑑
我一向說生態心理學是「新的」,但事實上它的起源卻可遠溯到原始民族。所有的心理學都曾經是「生態心理學」,根本不需要另用特殊新詞。世界上最古老的治療師,也就是那群一度被社會稱為「巫醫」的人,正好只是遵循環境互惠的脈絡來進行治療,別無他巧。有些人敏銳地看出,我們對引導傳統社會的神聖生態與日俱增的讚頌中,存在著多愁善感與浪漫情懷的成份。這實在是個誤解。這些事根本不像我們對字面的理解那樣「神祕」或「超越」。人類倚賴動植物和山川天地提供生命所需與生活的指引,因此必須與之處於互相尊重、互相授受的狀態,這本是日常生活常識。一位科尤康族(Koyukon)[4] 的老人曾經警告說:「大地心裏有數。」他說:「如果你對它做了錯事,整個大地都會知道。它感覺得到所有發生在它身上的事情。我想萬物在地底下有著某種串連的管道。」
當我們輕蔑地謔稱精神科醫師為「shrink」[5] ,其實就默認了他們和古代心理治療模式間仍遙相連接。我們承認這門似應已經歷科學啟蒙的精神醫學裏,實仍夾雜著一大堆不知所云的胡言亂語。反之,在乍看如迷信的巫醫行為中,是否存在著有價值的發現呢?人類學家馬歇爾.沙林斯(Marshall Sahlins)曾經研究當代尚存的狩獵採集文化,試圖重新建構「石器時代的經濟學」。基於類似的發想邏輯,是否也有一種「石器時代的精神醫學」(Stone Age Psychiatry)等待發掘呢?
我提出這個觀點的同時,也清楚知道有些新時代運動(New Age)的熱衷者,已經蒐羅並自行借引古老原住民文化的遺緒,但鮮少加以細究或給予應有的準備。在本書中我們試圖交代清楚一件事,即生態心理學家深切了解,要為世上倖存且往往極為脆弱的邊緣原始文化,與主流社會之間搭起溝通的橋樑,有著極大的困難。在歸納現代世界的正常與瘋狂之後,生態心理學家才學會用最究極的區辨能力來使用「我們」二字。他們認知到主宰工業世界的「我們」,和在雨林、蠻荒內地、原民保留區裏仍舊堅用的「我們」,兩者間疏遠的距離當以光年計。而用來測量此距離的刻度是財富、資產、蠻力、新聞媒體、管理控制等權力。
即使撇開公平正義的問題,要使傳統與現代得以對話,兩者間仍存有一項直接的心理障礙。這項阻礙與工業社會心理治療及傳統巫醫之間迥異的世界觀有關。傳統巫醫中秉持著一種泛靈式的世界觀,而這是猶太─基督宗教教條與科學客觀性皆予摒棄的感受能力。在我們的文化裏,去聆聽地球的聲音,彷彿非人眾生也能感受、聆聽、發言,這對大多數人而言就是精神異常的病症。心理治療是否有可能正藉由主張維護這種瘋狂的概念,在護衛著人類最深沉的壓抑—亦即這種認為大地是沒有生命、沒有感覺、記憶和意念而供人奴役之物的假設,而這也是讓工業文明進展最關鍵的心理殘害?基於現代科學的全然權威,正統的精神健康觀念也就將石器時代精神醫療排除在治療模式之外。那些認為透過類似在發汗小屋(sweat lodge)[6] 坐上幾個小時就能輕易修正這個情況的人,事實上對他們自己真正的疏離程度並不了解。
然而,那面映照著我們無止盡的慾求與渴望的歷史明鏡,自有其根深蒂固的道統。即便在最優越、最狂妄的文化中,宗教和科學仍得接受現今所謂典範轉移這類重大轉變的操控。在當代的主流基督教會中,也有支持環保的神職人員在推動教友們積極討論「地球管家」(planetary stewardship)[7] 和「受造界靈性」(creation spirituality)[8] 等觀念;有些人還試圖消除長期以來對「異教」(pagan)文化與觀念的歧視。新的地球與靈性運動(Earth and Spirit)正在探索以宗教為基礎的親生命性理論的可能性。
在此同時,至少在現代科學的邊緣,我們看到新宇宙觀正在誕生,這種宇宙觀的基礎,是個期望地球和宇宙整體保有有序複雜性的深化願景。科學家們或許仍難以明言這個逐漸浮現的世界觀中所隱含的革命性哲學思想,但這個新宇宙的輪廓卻越來越清晰:從科學觀點看來,我們再也不需要視自己為「處在那個我們並未創造的世界裏,滿心恐懼的陌生人」。現在我們知道元素週期表,由輕到重、由簡而繁的排序,正是我們的集體演化傳記。演化本身就是一部創生的歷史。如同某位天文學家所說,氫是「一種輕巧無味的氣體,給它足夠的時間,化身成為人。」……(節錄)
22
魔法之生態學
大衛.亞伯蘭(David Abram)
「魔法」在當代社會裏,主要是以喜慶表演或兒童文學的型態殘存著。但就像大衛.亞伯蘭發現的,在傳統社會中,魔法師同時也具有生態學家的功能。亞伯蘭身為生態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業餘的戲法表演家,他發現自己對峇里島(Bali)薩滿巫師的研究,強烈地改變了他和「人類以外」世界之間的關係,直到他又回到所謂的「文明」裏面。他在這篇文章中提醒我們,生態心理學可以從古代泛靈式的感受能力中學到許多事情,只要我們願意帶著耐心與尊重去探索它。
★ ★ ★
……我是藉著研究補助到印尼去研習魔法——更確切的說法是去研究魔法與醫療之間的關係,一開始先是找「督坤」(dukun),也就是印尼群島上傳統的魔法師,之後則是找「江克里斯」(djankris),也就是尼泊爾的傳統薩滿師。這次考察補助有一項特別之處,我並非以人類學家或學術研究者的身份進入亞洲的鄉村旅行,而是憑自己身為巡迴魔術師的身份前往,希望能更直接地與當地的魔法師接觸。我曾經擔任過五年專業的戲法魔術師,在新英格蘭各地的俱樂部和餐廳中表演,賺取學費以完成大學學業。我也曾經中斷認知心理學的學業,休學一年,旅行歐洲各地在街頭表演魔術,整個旅程即將結束前,我在倫敦停留了幾個月,和連恩(R. D. Laing)[2]及他的同仁們共事了一陣子,探討將魔術技法運用於心理治療的可能性,看看如果臨床療癒者遇到難以走近其心靈的困頓患者時,魔術是否有機會做為一種溝通的方式。這份工作使我對西方世界多已遺忘的民俗醫療與魔術之間的關係產生興趣。
這份興趣最後促成了前面提到的這趟補助訪遊,使我在亞洲鄉間以魔術師的身份逗留了一段時間。在此地,我的魔術技法大大地引發了當地薩滿的好奇心。魔術師與魔法師,不管是當代做節目娛樂者也好,或是傳統部落的法師(sorcerers)也好,都會運用知覺可塑性的特質。當地的法師瞥見我起碼有些能改變一般知覺領域的粗淺技巧後,便邀我到家中,和他們分享魔術中的秘密,最後還鼓勵我,甚至是敦促我去參加各種儀式與祭典。
但我研究的重點逐漸從原來關切魔術技巧在醫藥及儀式性治療中的應用,轉而更深入探索傳統中魔法和自然世界之間的關係。這個更宏觀的問題似乎也握有解開前一問題的關鍵。我在印尼小島上結識的諸多法師,以及我住在尼泊爾時追隨的薩滿師中,沒有任何一位把他們療癒儀式的工作視為自己在社區中的主要身份或功能。他們之中大部份的人當然是村子和鄰近地區主要的療癒者或「醫師」,這些村子裏的居民通常也這樣稱呼他們。但有些時候,這些村民尤其會在私密的對話中壓低音調,稱他們為巫師(witch,峇里語為「雷加克斯」〔lejaks〕),意指「黑暗的魔法師」,認為他們到了晚上,可能會施展逆向的療癒咒語,使人們得到白天他們要予以治癒的那個疾病。我自己從來不曾意識到我所結識的任何魔法師或薩滿在鑽研害人的魔法,也沒看過任何具說服力的證據,顯示他們曾做過這種事。然而讓我驚訝的是,他們也從不出面做或說些什麼,來澄清這些煩人的謠言和懷疑,就這樣任其暗中流傳在自己生活的地區。慢慢地我才體會到,正是藉由這樣的謠言,以及這些謠言所產生的模糊恐懼,法師才得以維護自己最基本的隱私。容許這些難以避免的懷疑與恐懼自由流傳,法師們反而得以確保只有真正迫切需要其法術幫忙的人,才敢來找他們求助。這樣的隱密性,繼而讓魔法師得以浸淫在他們主要的技法與職責裏。
這項職責的跡象之一,可以從魔法師很少住在村落中心而略見端倪,他們的居所反而常常位於寬廣的社區邊陲,或許在稻田中央,或許在森林邊緣,或在巨石之間。於是魔法師的智慧與理解力也就不侷限在社會之中,它屬於邊緣地帶,他們在人類社群及其賴以維生、汲取養分的更廣大社群之間,冥想沉思。這個更大的社群除了人類以外,還包括許許多多構成當地地形地貌的非人實體,從居住於此或遷徙而過的無數動植物,到形塑當地地理的特殊風向、氣候,再加上森林、河流、洞穴、山脈等,各式各樣為週圍天地貢獻出其特有風華的地景。
我慢慢覺察到,傳統的魔法師通常扮演媒介的角色,以確保養分能在人類整體以及廣大的生態場域間適當流動,不只從週圍的土地流入人類棲所,也從人類社群回流到週遭的大地中。透過他們的儀式、出神、狂喜以及「神遊」等作為,魔法師確保人類社會與廣大的萬有社會能維持平衡而互惠的關係,確認村落絕不從活生生的大地中取走多於回歸大地的——不單指物質層面,而是包括禱告、酬贖、崇神等等。部落群體總是要與所居住的自然世界,協商收穫與獵捕的數量。某種程度上,社區中的每個成年人都參與這種過程,調整頻率以傾聽存在於週遭,且影響日常生活的其他存在。而巫醫或法師則是模範旅人,穿梭於人類與非人世界間的中介國度,他們也是和他界(Others)打交道時主要的策略家與談判者。
於是,只有當傳統魔法師們不斷投注精力於僅存在於人類部落以外的生命力量後,才能消解部落裏面許多人發生的疾病。在很多這類型的文化中,疾病被認為是病人體內失去平衡,或是邪靈、惡靈侵入病人體內引起的。有時候,村子裏存在著邪惡的力量,干擾著部落中較為脆弱的個體,因而破壞了這些人的身體健康和情緒穩定。然而人類群體中這些破壞性的力量,通常可以回溯到人類群體和其所處的更大力場間的不平衡。只有那些在每天的工作中,監測和調節人類村莊和外在眾生環境之間關係的人,才有能力恰當地診斷、治療,最後解除產生在村莊中的各種疾厄與病症。不管是哪一個治療師,如果沒有同時關注到人類社會與更大的人外場域之間複雜的關聯性,可能只會將疾病從一個人身上排出,又讓同樣的問題(或許以不同的樣貌)在村子裏的另一個地方冒出來。所以,傳統魔法師或「巫醫」(medicine person)主要是擔任人類與非人世界間的中介,其次才是扮演療癒者。對當地文化與自然環境間的相對平衡與失衡,若無法保有不斷調節的覺察力,並具備調整這種基本關係的必要技能,任何的「療癒者」(healer)都是沒有價值的——事實上,他根本就不能算療癒者了。所以,巫醫的主要任務不在於人類部落,而在於包圍部落的大地關係之網上,而巫醫正是由此中獲得解除人類病痛的力量。
對西方學者而言,非人社會對魔法師的重要性,以及他們與大地萬物關係間的核心性,未必顯而易見。無數的人類學家在長篇大論地記載薩滿與「超自然」(supernatural)力量間的糾結時,錯失了薩滿法術中的生態面向。我們可以將這項疏忽歸因於現代文明隱含的預設,亦即認為自然世界大部份是固定的、機械性的,所有超越一般人體驗的怪力亂神經驗,勢必屬於某些超越自然而存在的非實體領域,是謂「超自然」。然而,我覺得,原始口傳文化型態所強烈地敬畏與歎服的,應該也不外乎我們稱之為自然的本身。薩滿靈交的深層神秘力量和存在,其實就是花草、鳥獸、森林和風等自然之物,這些在有文化修養的「文明」歐洲人眼中,只是在人類的煩憂之外,一幅令人愉快的風景背景而已。
可肯定的是,即使是敏銳的觀察者,也未必能在初學乍見時,就看出薩滿師扮演著人類社會與自然大地中介角色的生態功能。我們看到薩滿被請去治療生病族人的失眠問題,或只是去尋找失物;目睹他進入出神狀態,將意識傳送到另外一個空間,以求得覺見或助力。但我們未必願意就此稱之為「超自然」空間,或認為這完全是作法者個人心理的「內在」領域。因為西方心理學經驗中的「內在世界」(inner world),一如基督宗教信仰中的超自然天堂,很可能是源自於人類先祖與活生生的大地互惠互通這項能力的喪失。當這些在數百萬年來和我們一同演化的眾靈,忽然被貶抑得比人類更低鄙、無意義,當養育我們的豐饒大地被視為不具靈魂、沒有感受覺知能力的有限物體時,那些始終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野生異客只得遷徙,或許轉移到自然世界以外的超凡天國,或許轉入人類本身的頭腦裏,因為這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允許幻不可測、諱不可言的事物容身的避難所。
然而,在真正的口傳部落文化中,這個感官世界本身仍然是眾神寓身之處,祂們具有足以保佑也可以消滅人類生命的神聖力量。薩滿們並非將自己的意識送出自然世界外,也不是進入到自己心靈內的旅程,去接觸守護生命與健康的神靈;而是將他的意識向側面推展,同時在感官和精神層次上向外推至大地深處,形成一個栩栩如生的夢境,一個我們與翱翔的老鷹、蜘蛛以及幽幽冒出地衣的崢嶸石塊共享的夢。
和大眾對薩滿學是一項個人超越工具的普遍認知一樣,流傳於美國非主流文化圈中對「魔法」最精微的定義是:「能隨心所欲地轉變個人意識的能力或力量。」當中對為何要轉換個人意識狀態,並未提及任何理由。在部落文化中,我們所謂的「魔法」所隱含的意義乃基於一項事實,即在原民口傳的文化脈絡中,人們體驗到自己的智能只是多種覺識型態中的一種。傳統的魔法師培養出能從平常的意識狀態中脫出的能力,就是為了要以其他物種本身的方式與之接觸。薩滿只有在暫時卸去文化中既定的知覺邏輯時,才能與賦予當地地景生命能量的諸多非人感應力產生連結。也可以說薩滿的定義是:一項為了接觸大地中的其他力量並向之學習,而可隨時跳出其特定文化知覺界限的能力,這些界限在社會規範、文化禁忌,尤其在日常對談或語言中受到強化。薩滿的魔法正是他所擁有的超高接受力,用以接收週遭廣大的非人世界中,充滿意義的歌聲、鳴唱與姿態等引領訊息。
在我前往印尼研究魔法在醫療上的運用當時,魔法師與非人自然世界的關係其實並不是我立意探討的目標,我是後來才漸漸察覺到當地魔法師的技能中這個較細膩的面向。我第一次改變成見,是發生在峇里島內陸一位年輕巴里安(balian),也就是魔法修習者,的家中留宿數日時。他們從家族屋群(峇里島上大部份的住宅是在一塊圈圍起來的土地上,由幾間分立的小屋一起組成)給我一間只有一個房間的獨立住所,裏頭只有一張簡潔的床鋪。每天早上,那位巴里安法師的妻子會過來給我一盤美味的水果,我則獨自靜靜地坐在屋外的地上用餐,背靠著我住的屋子,看著太陽慢慢地從婆娑的棕櫚葉隙間昇起。
我注意到這位女主人給我水果的時候,同時還端了一個大托盤,裏頭還有好幾個船型的綠色小淺碟,每個都是用一段新鮮的棕櫚葉巧編而成。這些小碟子大概有兩、三英吋長,每一碟裏頭盛著一小坨白米飯。女主人給我早餐後,就托著盤子消失在其他屋後,幾分鐘後,她回來收我空盤時,她的托盤裏也是空的。
第二天早上,當我看到那排盛飯的小碟子時,我問女主人它們的用途。她很有耐心地向我解釋,這些是準備給家中神靈的供品。當我細問峇里語中她說的那些「神靈」時,她重複地用印尼語向我解釋,說明這些是準備給家族屋群中神靈的禮物,我想我對她的意思的理解應該正確。她給了我一盤切好的木瓜和芒果後,又走到屋子轉角處離開。我思考了一會兒,放下碗,走到我小屋側邊,在樹縫間探視。我看到她在另一間房子的角落旁彎身下去,小心翼翼地擺放著我想應該就是供品的東西。然後她起身端起托盤,走回另一個屋角,又擺上另一份供品。我則回去把我早餐碗裏的水果吃完。
那天下午,當大家各自忙著其他家事時,我走到屋子後面看到她擺放供品的地方。在屋子後頭那兩個屋角,確實安穩地擺著綠色的小碟子。但裏頭的白米飯卻已經不見了。
第二天早上我吃完切好的水果,等女主人過來把我的空碗收走後,我便靜靜地走到房子後頭去。兩個棕櫚葉小碟盛著的供品,就放在前幾天其他供品擺放的位置上。碟子裏盛著米飯。我正在注意其中一個碗時忽然嚇了一跳,發現裏頭的米粒正在移動。直到我跪下來靠近看清楚,才看出有一小列黑色的螞蟻正在土壤中蜿蜒地朝這片棕櫚葉走去。再更靠近點看,我看到兩隻螞蟻已經爬到供品上頭,正用力要搬走最上層的那粒米飯;我看到其中一隻將一粒米飯拖下棕櫚葉,沿著原先螞蟻部隊的路線搬回家。第二隻螞蟻搬走另一粒米,爬下飯堆,又拖又推的,結果摔到葉子外頭去;第三隻螞蟻又跟著爬上供品。這一整列螞蟻是從附近一株棕櫚樹旁濃密的草叢中爬出來的。我走到另一份供品處,發現另一排小螞蟻也正在搬動米粒。在我屋子後面的地上還有另一份供品,同樣有一排近乎一模一樣的螞蟻隊伍。我走回自己的房間咯咯竊笑。那位巴里安和他的妻子每天大費周章準備用來安祭居家神靈的供禮,徒然被那些細小的六腳小賊給偷光光了。多麼浪費啊!但,突然間,有個奇怪的念頭在我內心湧現。如果這些螞蟻本身就是供品所要供養的居家神靈呢?
這個想法我越想越不奇怪。這個家族屋群就和其他位在這個熱帶島嶼上的屋群一樣,蓋在好幾個螞蟻窩之間。既然家中眾多的烹調工作都在屋子裏進行,又有精心為各種儀式慶典準備的食物供品,這塊地和這些房子很容易就會被螞蟻侵入築巢。這種入侵可能小從偶發性的騷擾,到定期性的出沒,大至持續性的圍攻都有可能。每天用棕櫚葉提供的供品,很顯然是在排除這些環繞著(或潛藏於)家族土地的自然力量的攻擊。每天用白米做為供禮讓螞蟻群有事可做,想必也讓牠們感到滿足。這些供品每天規律地放在屋群各處不同屋角的同樣位置,似乎在人類和螞蟻社群間建立了固定的邊界;人類透過祭禮來尊顯邊界,顯然希望勸服這些昆蟲也尊重邊界的設定,不要進入建築物中。
但我仍對女主人宣稱這些供禮是「給神靈的」感到困惑。很明確的是我們西方對「神靈」(通常是相對於物質的或「有血有肉」之物)的概念,和部落或原民文化中敬重的神秘存在之間,總是有著某種程度的混淆。早期西方學習各種語言風俗的學者們,有許多是基督教傳教士,他們習慣在部落居民只是單純對當地的風表示敬重時,將之視為神秘無形的鬼怪。對西方人而言,「神靈」的概念大多具有人形化或與人有關的聯想,我遇到這些螞蟻的經驗是我第一次發現,原民文化中的「神靈」主要是指不具人形的智能或覺知型態,爾後仍有許多次經驗提醒我這一點。
身為人類,我們非常熟悉於人體的需求和能耐——我們活在自己的身體中,因而打從內在深深地知道我們這種生命型態的可能性。我們無法以相同的熟悉度和親密感,知道一尾草蛇或一隻鱷龜(snapping turtle)的生命經驗,也無法親身體會一隻蜂鳥從花中吸出花蜜時的確切感受,或是一株橡膠樹如何享受日光。我們的經驗可能是其他種種感受模式的變形之一;然而,因為身為人類,我們無法全然地感受另一種生命型態的生命感覺。我們並不能清楚地知道他們的慾望或動機,也就是說我們無法知道,或者永遠沒辦法確定我們知道,他們究竟知道些什麼。鹿有感官知覺,牠擁有天生秉賦,知道如何在大地找到方向,在何處找食物,怎樣保護幼子,也很清楚如何在森林中生存,而不需要人類所倚賴的工具,這些對人類來說都很明顯。芒果樹有能力結實纍纍,耆草(yarrow plant)能讓小孩子退燒,這些也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對人類來說,這些他者都是奧秘的承載者,秉賦著我們所缺乏的智能,也正是這些他者告知我們天氣不合時節的變化,或警告我們即將發生的火山爆發與地震。當我們在採食時,告訴我們哪裏有最好的食物,哪一條是回家最好的路線。我們從它們身上獲得了無數的食物、燃料、庇所和衣服等禮物。但對我們而言,它們仍然保持著他者的角色,過著它們自己的生活文化,進行著它們自己的儀式,從來無法被完全探知。最後,能對口傳文化的意識以神靈形式開口傳言的,並不止於西方文明認為「活著的」存在,也不止於動物或植物,還包括動物喝水的蜿蜒河流,傾盆而下的季風雨,以及盈握大小的石頭。
峇里島固然未盡屬於原始部落文化;其廟宇建築之精妙,灌溉系統之複雜,慶典與工藝的多彩多姿、金碧輝煌,在在都顯示出多種不同文化的交互影響,其中以印度的印度教文化為最。然而在峇里島上,這麼多種文化源流又和印尼諸島原住民族的泛靈觀念交織在一起;印度教的男女諸神都依其原本的職務,由當地更具火山特色的神靈所取代。
然而就像太平洋上其他許多島嶼一樣,印尼泛靈文化的背後,瀰漫著人類學家通常稱為「祖靈崇拜」(ancestor worship)的信仰。有些人可能會想爭論,認為對過世已久的先人所做的崇拜儀式,以及先人對現代生活影響的假設,能輕易否定了我的主張,亦即我所提出在原初民族的口耳傳述間穿梭的各種「力量」或「神靈」,最後是與此封閉島域上非人(但仍有意識)力量有關的論點。
他們這項辯駁運用了基督宗教文明中隱含的幾個觀念,比方假設死者的「靈」必然存留著人的形體,或說這些靈完全超離到感官所及物質世界以外的另一國度。但是,許多原始部落民族在自然大地之外,並無另一個非物質世界作為退路。對大部份的口傳民族來說,這個懷抱著我們而且有感有知的地球,從來就同時是生者與死者的棲身之所。他們還沒把人類或他者「身體」視為機械性物體。身體是個神奇的存在,是心靈感官層面的產物,而死亡後身體化作春泥、蟲蟻與塵土的腐化過程,顯現的只是長輩與先人逐漸融入活生生的大地中,而萬物也會再從大地中誕生。
每個原始文化都用自己的方式,加入所處特定區域的不同線索,詳細闡述對此形態變化過程的體會。使這眼前世界充滿生氣的無形氣場,也就是在我們及萬物間流動的幽微存在,往往含納了亡者的靈或氣息,直到這股氣息再度進入並活化另一隻鳥、另一頭鹿或一片野生稻麥等可見的形體為止。有些文化火化屍體,期望亡者能完全化為裊裊的煙霧回歸到流動的空氣中,化為火焰以歸於日月星辰,存餘為灰燼以歸於塵土大地。另外有些文化,像是某些喜馬拉雅山中的部族,會肢解屍體,將某些部位留在禿鷹、豹子或者狼可見、可食之處,藉此加速亡靈返回大地中特定動物境域的轉世過程。這些例子只是告訴我們,死亡在部落文化中表示另一種形態變化的開始,在此中人的存在並不從這個可感知的世界「消失」(還能去哪裏呢?),而是在廣大的地域中以具生命力的能量存在,它可能存在於無影無形的風中,或存在於具象可見的鳥獸中,或在火山那需索無盡安撫的爆發性怒火之中。所以,形貌多樣的「祖靈崇拜」,窮其究極,實為關注非人類自然世界的另一種模式;其重點並不在於對人類力量的敬畏與尊崇,而是在我們熟悉的人體死亡腐敗後,化成廣闊宇宙的一部份時,敬拜這個脫離人類型式後所呈現的意識。
這個人類在大千世界中生死循環的過程,確保我們所經歷的各種物體,不論是螞蟻、柳樹或白雲,永遠不與我們絕然疏離。撇開外觀、能力以及存在的形態等等外顯的差異,至少它們仍令人隱隱感到熟悉,甚或親如家人。矛盾的是,這份對親緣遠近的認知,反而使我們察覺到的差別感或他者感更顯突出。[10]
和這些魔法師與占卜師們接觸的經驗逐漸轉化了我的知覺,使我越來越容易感受到人類以外事物的懇請。當某個魔法師提到某種力量或「存在」在他的屋角逗留時,我會試著去注意穿過牆隙的一道日光,照亮了一股飄移的灰塵,進而體會到這道光就是一股力量,用它的熱能影響著氣流,事實上也就影響著整個房間的氣氛;雖然我之前未曾有意識地觀察過那道光的力量,它卻早已在組構我的經驗。我的耳朵開始用新的方式去傾聽鳥兒的歌唱,那些歌聲不再只是人類話語背景中的律唱,其本身就是有意義的言談,回應著、評論著地球週遭發生的事物。我開始學習覺察細微的差異:微風如何而能只翻動樹上的一片葉子,而其他的葉子卻仍能靜止不動(這片葉子難道不是正被魔法所拂?);又或者陽光的熱度如何精確地展現在蟋蟀的鳴叫節奏上。走在泥土路上,我學會放慢自己的腳步以感受一座山丘與另一座山丘間的不同,或者當當地的魔法師「督坤」告訴我某處具有特殊力量,會提供獨特的禮物時,我會在一天中的特定時刻去品嚐那片田野的氣息。透過樹影在那一刻投射的方式,透過滯留在草地上未被風吹散的氣味,透過在佇足和傾聽多日後才慢慢分離出來的元素,我的感官接收到了那股力量。
而後,其他的動物們慢慢地開始在我漫步時出現,彷彿我的姿勢或呼吸的節奏解除了他們的戒心。我開始和獼猴面對面接觸,並遇到一些我即使開口說話時也不會溜走,反而好奇趨前的大蜥蜴。在爪哇島(Java)鄉下,我常看到獼猴在頂上的樹枝伴我而行,烏鴉在路上啞啞叫地朝著我走來。在爪哇島南部海岸凸出的半島上,有一個名叫巴干達蘭(Pangandaran)的自然保留區(附近一位漁民跟我說「這是一個充滿神靈的地方」),我在那裏曾有一次從樹叢裏走出來,發現自己正和一頭當地獨有的美麗稀有的野牛正面相迎。我們凝視著彼此,牠噴氣的時候,我也以噴氣回應,當牠移動肩腳時,我也移動步伐;而當我搖頭時,牠也搖頭以應。我發現自己進入和這個他者以非語言溝通的狀態,那是姿態的對唱,而我的反思性的覺識一點作用也沒有,我的身體彷彿忽然被某種比我的思考還古老的智慧所驅動,受到比言語更深沉的法則所定所動,這是一種他者的身軀、樹木、空氣以及我們所立足的礫石土地也能言說的法則。
我興奮地回到北美,因為現在我擁有這份在心中激盪的新感受力,亦即我對人外世界,對大地能量的威力,尤其是對和我們的生活與文化緊密交融的大小動物們的銳敏巧思,新獲得的覺察能力。有些鄰居會被我嚇到,因為我會跟溜下樹幹和我嬉玩的松鼠聊天,或者一連花上好幾個小時待在附近的河口看鷺鷥捕魚,或者看著海鷗在沙灘上用石頭砸蚌殼。
可是非常緩慢地,我開始失去對動物本身知覺的感受能力。海鷗砸蚌殼的技巧開始變得像是機器的自動化動作,我不再能輕易感覺到海鷗必須凝聚在每個新蚌殼上的心神。也許從頭到尾每一個貝殼都一樣,並不需要任何自發的注意力。
我發現自己現在是從鷺鷥的外在世界觀察鷺鷥,雖然興味盎然注視牠小心翼翼地抬腳走路,又突如其然地將長喙射入水中,但我的肌肉已不再能感受牠那緊繃卻又泰然自若的警覺力。奇怪的是,郊區的松鼠們也不再回應我的呼喚。雖然我希望能繼續像前幾週那樣輕易地投入牠們世界中,但卻已經沒有辦法做到,因為我的注意力很快地就轉移到各種內在世界的語言思緒中,一種完全在內在進行的自我對話。松鼠們當然無法參與其中。
從書本文章和許多人的討論中,越來越顯見的是,其他的動物並不像我原本預期的那樣清醒而覺知,牠們缺乏任何真正的語言,因此也沒有思考的可能,牠們對外界那種看似自發性的反應,大部份也都是「設定好的」行為,在科學家們正在解讀的遺傳物質上早有「編碼」。我越來越了解,在人類無限的智能和其他動物有限的感覺之間,並沒有共同的基礎,我們和牠們中間並不存在任何媒介足以讓彼此溝通互動。
但就當這些蘊含豐富情感的自然美景,逐漸消失在我全心關注的人類議題之後,幾乎就要變成某種幻覺或幻想之時,特別是在我胸口和腹部,我開始有種我與滋養生命的源頭遭到切離的感受。
今天,在「已開發世界」中,許多尋求靈性上自我了解的人參加以「薩滿」方式來自我發掘、自我探索的工作坊和課程。在此同時,心理治療師和某些醫師也已開始專修「薩滿式治療技巧」。「薩滿學」於是成為一種另類治療型態;這些受歡迎的新薩滿治療者,強調的是個人的內省與治療。固然他們有著崇高的理想,但是我相信他們只是從原始薩滿的主要角色中,衍生及引用出來的次要功能,若缺乏長期且持續與荒野自然、其生命模式及其交替循環接觸的經驗,就無法充分扮演原始薩滿的角色。如果我的推測正確的話,不了解原始薩滿與自然荒野群聚的關係,貿然模仿他們的治療手法,只能把某些症狀轉變成另一些症狀,或者把不適從人類社會中的某一處轉移到另一處。畢竟壓力的根源乃是存在於人類社會和其所賴以維生的自然大地之間的互動關係中。
可悲的是,我們的文化和活生生的地球間的關係,絕非處於互惠平衡的狀態。每小時有數千公頃的原始森林就此消失,因為人類文明的無度擴張造成每個月有數百種同胞物種就此滅絕,你我也無須震驚於文化中如此之多的流行病,從日益增多的嚴重免疫失調、癌症,到廣泛遍佈的心理困擾、憂鬱和與日俱增的自殺事件,乃至平常看似正常的人忽然沒來由地殺人的案件,也在逐漸增多。
從泛靈的觀點來看,這些身體上與心理上的問題最明顯的根源,都是在於我們的文明濫加在地球生態上的無謂暴行;唯有拯救後者,才能治好前者。這乍聽起來或許像是個單純的信仰口號,但當我們認知到自己完全依賴於和我們共同演化而來的無數有機生命體時,這個道理就非常清楚了。因為陷溺在一團抽象事物中,我們的注意力也被這些只能反照出人類自己的人造科技所催眠,我們太容易忘記自己的肉身傳承,乃源自於非人世界中的知覺與感受力所形成的母體。我們的身體乃是在這個生機地球中,在各種層次的觸感、聲音和形狀精巧的交互作用中形成;我們的眼睛是在與其他眼睛的細膩互動中演化而來,而我們耳朵的結構則是因應著狼嚎與野雁的鳴叫調適而成。將自己阻隔於這些聲音之外,執著我們的生活方式,摒棄其他這些感受能力,使之終因漠視而滅絕,其實就是在劫奪自己感官的完整性,也是在剝削我們心靈的統合性。我們唯有與非人相互接觸、相互和樂之下,始真正是為人。唯有在與所謂他者互動時,我們才開始療癒自己。
註解
[1] 譯註:「賽琪」(Psyche)為希臘神話中一位好奇的公主,後引申為「心靈」之字源。「蓋婭」(Gaia)為希臘主掌大地的女神,後為生態界引用為視地球為一生命整體的環境觀念。
[2] 原註:《診斷與統計手冊》早期的版本中還包括另一個涉及人類以外世界之處:戀獸癖(zoophilia),亦即和動物發生性行為。較古老而典雅的說法是用「bestiality」,但用強暴動物之類的字眼來說可能更貼切。因為太怪異了,所以「戀獸癖」這個字也就排除了愛上動物的「正常」狀態的可能性。
[3] 譯按:原書為美國最負盛名的環境保護團體Sierra Club所編製印行。
[4] 譯註:科尤康族(Koyukon)為北美阿拉斯加(Alaska)一個地區的名稱,也是阿拉斯加最大一支原住民語言的名稱。
[5] 譯註:英語中對心理治療師的俚稱。
[6] 譯註:發汗小屋(sweat lodge)係印第安人所採用一種似三溫暖般之高溫小屋,參加者進入其中思考自我,以提昇自我。
[7] 譯註:地球管家(planetary stewardship)係基督宗教中對人類應珍惜環境的論述之一,比喻人類如同地球的管家,有責任在上帝出門的這段時間,管好地球這顆行星,所以不應該濫用資源、殘虐其他的生物。
[8] 譯註:受造界靈性(creation spirituality)係指一種以創造為中心的靈修方式,目的是要使基督徒的靈修達到均衡,也就是從過去所強調的救贖、成聖層面的靈修,轉變成一種包括人性各個層面的靈修,乃涉至生態危機、技術工業化等問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於1979 年欽定熱愛自然的受造界靈性先賢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i,1181 年生於義大利)為生態學者的總主保。
[9] 譯註:連恩(R. D. Laing,1927-1989):英國著名之精神醫學家,對當時主流精神醫學思想多所檢討與批判,常與湯瑪斯.薩茲(Thomas Szasz)等人被合歸於「反精神醫學」(anti-psychiatry)一類的學者。
[10] 原註:這樣一種宇宙觀和日漸勃興的當代生態學觀點有許多相類似之處。提出蓋婭假說(Gaia hypothesis)大氣地理學家James Lovelock 主張地理環境本身乃是由有機的生命體和有機代謝的產物所共同構成。用他的話來說的話,我們住在「一個由我們的祖先與骨骼化身而成的世界」。見"Gaia: The World as Living Organism," New Scientist (December 18, 1986), 25-28。
引言
當賽琪遇上蓋婭[1]
西奧多.羅斯札克(Theodore Roszak)
個人與全球
提到環境主義,我們想到的是個大規模的全球性運動,要處理的是龐大難以想像的複雜社經議題。環境運動是有史以來,人類所進行過最浩大的政治理想,它含括了每個人,因為也不能錯失任何一個人。它關照的範圍甚至擴展到人類以外的物種,及於所有的動植物,乃至山川大地。每當我談到環境議題的時候,都能強烈感受到其他非人眾生的目光也正在注視著我,我們的萬物同胞們正在仰望,期待這個令其不解的人類表親能看到自己錯誤的作為。
另一方面,當我們提到心理治...
推薦序
【譯序代導讀】
生態與心理的融合與轉化
陳俊霖╱荒野保護協會常務監事、臺灣心理治療學會常務理事
緣起
「生態學」和「心理學」躋身學術領域,各自有著百年以上的歷史,對當代民眾而言,早已耳熟能詳。1990 年代,原以研究「非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著稱的美國歷史學者西奧多.羅斯札克開始提倡他定名為「生態心理學」(ecopsychology)的新領域,號召生態學與心理學攜手同行,前有1992 年他個人著作的《傾聽地球的聲音》(The Voice of the Earth),後則為1995 年由他出面召集主編的《生態心理學》,亦即本書,為時至今日我們所看到生態心理學的發展,吹響起床號。
當初出版此書的,卻不是心理領域的專業機構,而是由美國最重要的環保團體山岳協會(Sierra Club)所出版。恰好與此書同年,遠在臺灣的荒野保護協會也在此1995 年誕生。就在荒野成立後不久,初得此書,志工們曾斷斷續續試譯過部份文章刊載在當時的《荒野快報》上。2007 年荒野與山岳協會之間有些交流,繼而在2009 年正式簽訂本書的中文版權。
2010 年4 月,地球日40週年之際,荒野出版《生態心理學:復育地球;療癒心靈》中文版,並發起「生態心理季」一系列相關活動,應該算是臺灣正式引進生態心理學的濫觴。全書完成的過程原本很符合荒野志工共事合作的行事風格,由諸多志工們分頭發譯後再彙整出版。
爾後這幾年,陸續有生態心理學圈的前輩,如澳洲的約翰.席德(John Seed),英國的瑪莉- 珍.羅斯特(Mary-Jayne Rust)訪臺,示範帶領本書中提及的眾生大會(Council of All Beings)工作坊,以及身為專業諮商心理師如何將自然運用在心理衛生工作上。荒野保護協會也基於本書的理念,著手招訓生態心理志工團隊,從環運的角度發展相關的實作。心靈工坊出版社亦協助翻譯出版另一本生態心理學文集,由英國的瑪莉- 珍.羅斯特和尼可.托頓(Nick Totton)主編的《失靈的大地:生態心理學的反思與實踐》。大約與此同時期,另一系列將自然元素和心理衛生工作結合的綠色照護(Green Care)領域,例如推動園藝治療的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發展冒險治療及荒野治療的亞洲體驗教育學會臺灣冒險治療專業領域工作者社群,以及動物輔助治療、森林益康、生態療癒⋯⋯等概念紛紛在臺興起,生態心理學及其相關的實務工作,的確逐漸萌芽茁壯。
然而因為荒野保護協會與山岳協會的合約到期,山岳協會亦已將原書的版權委由出版社代理。因此,荒野首版兩刷有著墨綠及橄欖綠封面,編排樸拙生澀的舊版《生態心理學》也成為絕響。
所幸在心靈工坊接洽新代理商後,重新取得中文版權,也因此得能讓這本學習生態心理學絕不可錯過的經典書籍,以更專業,更友善於讀者的版本在2017 年再度問世。
新的版本由荒野保護協會與心靈工坊合作出版,由荒野提供舊有的譯文,重新校正修訂,整合多處譯名,加上較多的譯註,再加上全新的設計與排版,相信可以帶給讀者更好的閱讀品質。惟憾原書最末還有一篇由歐卡納岡族(Okanagan)印第安原住民珍妮特.阿姆斯壯(Jeannette Armstrong)所撰,名為〈地球守護者〉(Keepers of the Earth)的文章,再度議約時仍未能收錄。
走進生態心理學
然則生態心理學究竟在探討哪些融合生態學與心理學識見的思維呢?以西奧多.羅斯札克(Theodore Roszak)對其進一步的開展為骨架,以及用此書的內容為例的話,生態心理學大致繼續發展出:
1. 生態學與心理學的逐漸融合
生態心理學包括走向生態的心理學,也包括貼近心理的生態學。本書由得過聯合國環境獎的雷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賜序〈生態心理學與環境革命〉,探討傳統的環境運動路線應該要多關切環境運動對民眾心理層面的影響,以及如何向心理學的知識尋求理論與實務上的資源;繼而由榮格心理學重要大師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為文〈以地球為度的心靈〉,評述心理學在科學化的過程中掉入二元論的典範後,該如何喚醒自己,打開生態尺度的視野。而主編羅斯札克的〈當賽琪遇上蓋婭〉一文,更接著具體勾畫出兩個領域交會的大地圖,一方面讓環境主義工作者從早年的「悲情綠人」,有機會變成慈悲的新角色,使環運人士成為心靈療癒者;另一方面,也讓心理學圈擴大關切的範圍,進行「心理學綠化運動」,以期有朝一日建構出一套不只關心人類,而是「關照整個地球的心理學」。生態學和心理學兩個原本遙遠的領域,倏乎出現攜手合作的契機。
2. 在心理治療的實作中技術性地運用生態學的識見
後現代思想解放了許多傳統心理治療裏固有的框架,其中有許多思考即在檢視治療是否只能限制在小小的會談室中?是否在面對個案的情緒反應時除了用內在情結詮釋,也該認可其在真實世界中的意義?心理衛生的工作是否該與外在真實世界多些互動?是否可以引入與自然相關的元素進入心理治療的實務工作中?也因此,在心理治療或更廣義的心理衛生工作中,出現如書中所談到的荒野療法,引進原民文化的薩滿技術,此部份可參考〈荒野效應與生態心理學〉、〈荒野之道〉、〈薩滿式諮商與生態心理學〉等文。這或許對規範森嚴的心理治療圈而言還太過另類,但過去十餘年,國內的園藝治療、冒險治療、荒野治療、森林療癒等模式的確正一步步推動中,值得心理衛生圈期待其發展得更健全。而即使在既有的治療規範中,〈榮格心理學與世界無意識〉、〈垂死行星之治療〉、〈大地受傷,誰來回應〉、〈完形療法中的生態紮根性〉等文,仍值得治療師們玩味思考如何在現有的治療工作中,多些與生態思維的串連。
3. 研究人類對地球的情感聯結
在生態心理學的理念中,人與地球、人與自然萬物之間,有著與生俱來,或者更溯源來說,從億萬年演化路程而配備進眾生之間的各種鍵結,當然也包括情感上的聯結。這可以參考〈當賽琪遇上蓋婭〉文中提及威爾森的「親生命性」,羅斯札克倡談的「生態無意識」、「生態自我」,以及〈榮格心理學與世界無意識〉中埃森史塔特結合到榮格學派「世界無意識」等概念,在在試圖讓我們相信人與世界間有著深植心靈深處的地下根系相連結,並可能成為後續環境運動值得倚靠的信念。即便沒有理論的闡述,〈哀悼生態〉文中提到諸多環境關懷者對各種生態浩劫的嗟嘆,其實關心環保的讀者們也一定在不同的場合真實地感受過人與自然的情感從來不曾斷離。
4. 尋求以環境為基礎的心理健康標準
套用主編的調侃,如果只以精神醫學的診斷系統為標準的話,人類如何濫用自然、破壞賴以維生生態體系的自傷傷人行為,都不足以構成心理異常的診斷。這固然不是精神醫學原本關注的定位,但若擴大當代心理衛生的概念,當家暴、性別平等、網路成癮等議題成為心理衛生工作人員隨著時代進展而應該新增的研習時,一種有可能毀滅生態體系的文明型態卻不用接受心理面向的檢視,就變成房間裏一隻坐在電動按摩椅上的大象了。〈我們快樂了嗎?〉、〈一心消費的自我〉對當代西方消費文明提出心理層面的檢討,〈人與自然關係之精神病理學〉裏對人類演化成如此自毀的生活方式,提出好幾種精神病理學上的解釋。莎拉.康恩在〈大地受傷,誰來回應?〉文中提到的「物慾障礙」,〈生態式知覺的技巧〉引用大衛.亞伯蘭「集體近視」的概念為開端,也可能是看待人類問題行為的診斷答案。或者近年另一個流行的非正式診斷「大自然缺失症」(nature deficit disorder),也值得我們自省一番。人類原原本本應有的心理健康狀態中,到底該和大自然之間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呢?
5. 在顧及整個世界的條件下重新定義「精神健全」的意義
循著將環境列入心理健康標準的考量,生態心理學描繪更寬闊的精神健康意義,大致上是從一個只在乎個人或自身物種利益,自戀自大自我封閉的個體,轉變成對週遭環境更敏銳、更同理,對週圍非人訊息也更具有通透性,放下自我的宰制與控制慾,從「嗜分隔的自我」轉化為「關係中的自我」,成為真正與世界萬物相互連結,扮演好相互依存網絡中的一份子。這在〈兒童發展之生態心理學〉、〈井神之辱──女性主義心理學與環境危機〉、〈女神之心〉等多篇文章中漸漸浮現出來。或許我們仍難定義精神健全的規則來供人遵守奉行,但「尋求與自然和諧相處之道」多多少少成為一種正向的標竿,促成「綠活」、「慢活」等制衡競逐式生活型態的替代選項,也復興了「天人合一」的心靈向量。
回顧與省思
然則在生態心理學問世二、三十年後的今天,身處臺灣,這個看似美妙,兼有理論與技術,甚至帶有幾分生命哲學意味的學門,能帶給我們什麼省思呢?
自從生態健全被經濟發展綁架之後,生態心理學想幫自然生態償付的贖金,原本奠立在若能提高心理的價值,應該就能降低以金錢衡量價格的比重。這個想法的確有些進展。隨著不丹國王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提倡以「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來衡量國家發展,人們對傳統GDP(國民生產總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式的經濟量度的確產生反省。「世界快樂地圖」、「世界快樂報告」等研究的問世,的確讓心理價值稍稍受到重視。
同時在個人層次上,似乎每個時代總有一定比例注重性靈發展的人,拋下世俗的物慾,尋求某種自足圓融的生活模式,除了宗教的修行之外,也可能像陶淵明,也許像嬉皮,也或許是近年媒體愛報導放下光環工作返鄉「半農半X」的新世代。生態心理學提供了某種詮釋,讓這一條道路成為可理解的、合理的選擇。做為理論和教案的支援,生態心理學也因而滋養了不少實務工作的誕生或轉化,從生態旅遊、環境教育、自然體驗內容的豐富化,到園藝治療、冒險治療、森林療癒的萌生,環保團體亦引進眾生大會或心靈風自然體驗等新工作模式,原本就常運用自然山水的靈修團體也可在此中找到現代化的依據。
這些都算是具體的貢獻,但這所激起的波瀾,相較於全族群的人口數,似乎滄海一粟,只迴盪在一個令環境工作者擔心的極低比例,恐怕比任何一型新手機的使用者還要少得多。許多人不免擔心生態心理學中浪漫地倡導人與自然的心靈相連,只是又一次中產階級酒足飯飽後的風花雪月,對於還得汲汲營生的黑手小老百姓而言固然缺乏說服力,對於竊國者侯的大黑手們更缺乏勸阻力。
這或許是心理學的宿命,借用政府改造後的架構為量尺的話,這個社會秤了心理衛生工作的斤兩,也不過給了半個司的砝碼;環境資源才剛能升級為部;如果立部最久的經濟面向不能更積極地看到生態及心理做為社會資本的重要性,心理思維的加入,只是在軟資產上再加上軟資產,不容易吸引看慣硬資產的現代人。
同時,這或許也是心理學的本質,做為一種陰性的力量,雖然在檯面上總是不及陽性的政治、經濟那樣搶眼,但其實不論任何時空,心理力量在社會中的翻攪,卻也隨時擾動著政治與經濟原有的步調。君不見自古諸多天災,以及後續在社會上激起的心理漣漪,常常成為經濟崩解、政權輪替,甚至宗教改革的序曲。只是連心理學家也很難以在當下說得明白,想來也就不需要低估心理軟力量對硬體制隨時散發出的影響力。
也許一門思潮,幾本書,幾場演講或活動,丟進人類大社會之後就像砂糖入海一樣地溶化。讓我們借用心理學的信念,相信這些一路累積下來看不到、講不清的思緒,沉積成為一個社會的集體無意識後,即使還是看不到、講不清,終將成為另一道命運在未來改變我們全體。
【譯序代導讀】
生態與心理的融合與轉化
陳俊霖╱荒野保護協會常務監事、臺灣心理治療學會常務理事
緣起
「生態學」和「心理學」躋身學術領域,各自有著百年以上的歷史,對當代民眾而言,早已耳熟能詳。1990 年代,原以研究「非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著稱的美國歷史學者西奧多.羅斯札克開始提倡他定名為「生態心理學」(ecopsychology)的新領域,號召生態學與心理學攜手同行,前有1992 年他個人著作的《傾聽地球的聲音》(The Voice of the Earth),後則為1995 年由他出面召集主編的《生態心理學》,亦即本書,為時至今日...
目錄
【譯序代導讀】生態與心理的融合與轉化——陳俊霖
【中文版推薦序-環境篇】尋找環境運動的曙光——李偉文
【中文版推薦序-心理篇】讓心向自然學習——王浩威
【原書推薦序-環境篇】生態心理學與環境革命——雷斯特.布朗
【原書推薦序-心理篇】以地球為度的心靈——詹姆斯.希爾曼
引言 當賽琪遇上蓋婭/西奧多.羅斯札克
第一部 理論觀點
1 自然與瘋狂/保羅.雪帕
2 科技、創傷、與荒野/闕莉絲.葛蘭汀寧
3 人與自然關係之精神病理學/若夫.梅茲納
4 我們快樂了嗎?/艾蘭.都爾寧
5 一心消費的自我/艾倫.肯納、瑪麗.鞏姆絲
6 榮格心理學與世界無意識/史帝芬.埃森史塔特
7 兒童發展之生態心理學/安妮塔.芭若絲
8 井神之辱—女性主義心理學與環境危機/瑪麗.鞏姆絲、艾倫.肯納
9 荒野效應與生態心理學/羅柏特.葛林威
10 哀悼生態/菲莉絲.文德
第二部 生態心理學之實務應用
11 垂死行星之治療/泰倫斯.歐康納
12 大地受傷,誰來回應?/莎拉.康恩
13 薩滿式諮商與生態心理學/潘蜜拉.絲隆專訪蕾絲莉.葛瑞
14 荒野之道/史蒂文.哈伯
15 生態式知覺的技巧/蘿拉.希渥
16 完形療法中的生態紮根性/威廉.卡哈朗
17 復育棲地,復育社區,復育心靈/艾朗.夏比洛
18 修通環運悲情/喬安娜.梅西
第三部 文化多樣性與政治參與
19 生態心理學與純白迷思/西奧多.羅斯札克訪談 卡爾.安東尼
20 人種自慢的政治學/約翰.麥克
21 女神之心/貝蒂.羅斯札克
22 魔法之生態學/大衛.亞伯蘭
編輯與作者群簡介
致謝詞
【附錄一】參考書目
【附錄二】專有名詞對照表
【附錄三】文獻對照表
【譯序代導讀】生態與心理的融合與轉化——陳俊霖
【中文版推薦序-環境篇】尋找環境運動的曙光——李偉文
【中文版推薦序-心理篇】讓心向自然學習——王浩威
【原書推薦序-環境篇】生態心理學與環境革命——雷斯特.布朗
【原書推薦序-心理篇】以地球為度的心靈——詹姆斯.希爾曼
引言 當賽琪遇上蓋婭/西奧多.羅斯札克
第一部 理論觀點
1 自然與瘋狂/保羅.雪帕
2 科技、創傷、與荒野/闕莉絲.葛蘭汀寧
3 人與自然關係之精神病理學/若夫.梅茲納
4 我們快樂了嗎?/艾蘭.都爾寧
5 一心消費的自我/艾倫.肯納、...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