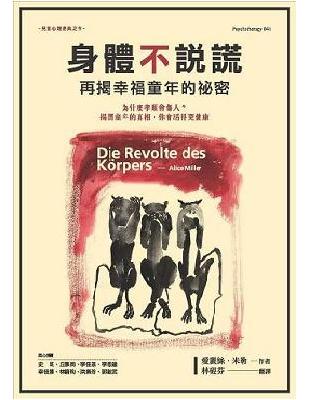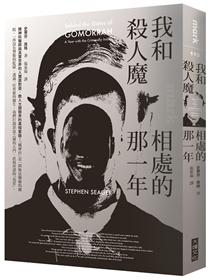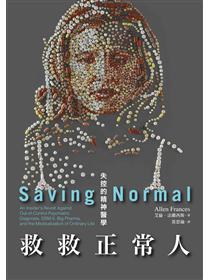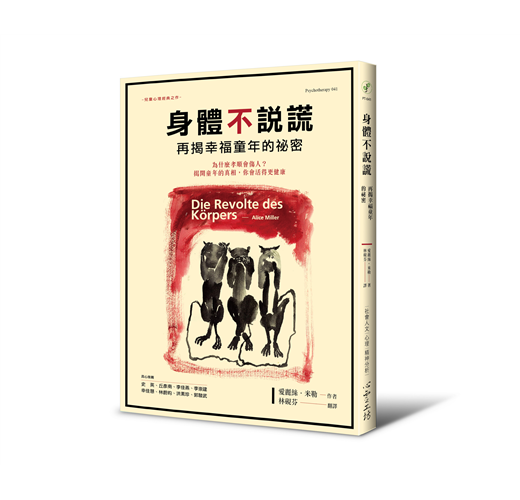名人推薦:
真心推薦 (按照姓氏筆畫排序)
史 英 (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丘彥南 (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
李佳燕 (家庭醫學科醫師、還孩子做自己聯盟發起人)
李崇建 (作家、教育工作者、千樹成林創意作文班創辦人)
幸佳慧 (兒少文學作家)
林蔚昀 (專欄作家、波蘭文學譯者)
洪素珍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郭駿武 (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秘書長)
人們已因「以暴養暴」的理解而反對體罰教養;然而對於世界源源不斷的病痛與衝突,不管是身體或心理的,米勒綜合自身、臨床、文學作家的多方經驗與研究,仍給出一個驚人的解釋觀點。那是更挑戰社會禁忌,直接向「孝敬父母」此一天條戒律的控訴。這本書,對深陷苦痛的人們不僅給出一道出口,對我們紛亂的社會,也有解咒之效。——幸佳慧(兒少文學作家)
童年不會只有一次,因為它一直和我們共處至今!——郭駿武(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秘書長)
愛麗絲‧米勒揭露了只有極少數人肯承認的事實:那些在育兒慣例的偽裝之下,加諸於兒童身上的異常痛苦與心理傷害。——莫里士‧桑塔克(Maurice Sendak,繪本《野獸國》作者)
【推薦序一】
哀悼與理解的交錯
洪素珍(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對古典精神分析學派的理論而言,影響人一生最大的,無非就是童年創傷經驗的反覆,對精神疾病追本溯源,總是可以找到童年期發生的病根。以研究童年早期心理創傷的成因及其之後影響而著稱的原波蘭籍心理學家愛麗絲•米勒(Alice Miller)更認為,早期創傷,尤其是嚴重的身體與精神虐待,不僅影響日後的心理發展,與生理的健康也息息相關。她的《身體不說謊》舉出很多歷史名人幼時受虐,造成日後身心苦痛,甚至英年早逝的例子來支持與論證其觀點,頗具說服力。
米勒曾接受精神分析訓練,並擔任精神分析師。她童年有過受虐經驗,長期關注兒童受虐議題,發現當父母對孩子造成身心虐待,由於社會文化道德的壓力,受虐的孩子會選擇壓抑,從小到大、日積月累,終於積怨成疾,持續對自己也對他人造成傷害。
有趣的是,在從事二十年的精神分析工作後,米勒選擇了放棄這個發掘潛意識的治療工具,因為她認為,精神分析理論和實踐無法讓受虐者認識到父母的錯誤,而且傳統文化道德、宗教倫理要求人們「敬愛父母」,更讓問題失焦,或許這唯一的好處是讓施虐的成人變老後,像買了保險一樣,享受「養兒防老」的保險受益。但這卻讓受虐的孩子帶著創傷成長,他們也許又會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複所經過的那些虐待,以紓解壓力;他們的身體也可能反應出創傷的後遺症,身心受苦。
人類做為一個有感知覺受,且具長期記憶的有機體,無法不受過往經驗的影響。米勒在本書中對「敬愛父母」的道德律提出嚴厲批判,並對於精神分析不正面處理傳統道德障礙、因而影響到治療效果感到不耐,她主張直指父母造成傷害的事實核心,讓受虐的孩子不再替施虐父母背負責任。依照她的實務經驗,此舉確實有效幫助了許多人解決長久困擾的身心舊創。
米勒點出了我們很難敢於檢討和挑戰傳統道德的盲點;然而,當我們成功地把錯誤責任還給犯錯的父母、勇敢對於自己是個絕對獨立自主的個體產生自覺,逃離了內在父母的監控,不再依賴父母之愛的幻想……以後,就能夠從此過著自由幸福的日子嗎?
米勒在書中舉出日本名作家三島由紀夫的自殺,可能是童年時期對於祖母與父母的教養不滿,憤怒無從發洩,因而造成悲劇的例子,以作為敬愛父母的道德律可能殺人的說明,但我想,這並非否認父母之愛的重要性。對此,我以另一位日本天才作家的悲慘生命故事作為對照,加以說明。
從一九六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九年四月的半年之間,日本東京、京都、函館、名古屋連續發生四件槍擊死亡事件。在一次企圖槍殺警察的行動失敗後,被逮捕的十九歲男子永山則夫,自承犯下前述的四次案件。
永山則夫出生於北海道,家徒四壁,在八個手足中排行第七。他父親是個嗜賭的酒鬼,倒斃路旁;母親後來帶著四個小孩離家,留下四個小孩獨活,包括會對弟妹施暴的二哥、有精神疾病的大姐、則夫以及最小的妹妹。四個小孩居無定所,以拾撿菜市場的棄菜爛葉裹腹為生。有暴怒的哥哥為榜樣,永山也會虐待妹妹。永山則夫失去父母的愛,也沒能好好上學,幾乎與文盲無異。他國中時被問到將來的志願時,他的答案是:「自殺!」
國中畢業後,永山則夫到東京謀生,他遭受到嚴重的歧視與排斥,沒有一個崗位能夠久待。他自殺過無數次,但沒一次成功。有一天他闖進美軍基地,想像可以被亂槍打死。不過他竟成功潛入基地,不僅沒被發覺,還偷到一把手槍。於是他決定以這把槍隨機殺人,以發洩對人生的不滿。
雖然永山犯案時未滿二十歲,可被視為不能被判死刑的未成年犯,心理鑑定也將他的殺人認定為「因為心理嚴重受創」的結果;但都無法改變法官認定他不可教化、應與世永隔的裁決,永山因此被判死刑。
永山的心理鑑定雖不被採認,然而不可思議的是,當時與他談話的心理醫師石川卻打開了他的心門。在晤談中,他了悟自己的錯誤,感到愧疚、後悔,嚎啕大哭,然後在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走到人生終點的黑暗中開始重新整理自己。他開始讀書識字,甚至寫作。
從一個幾乎目不識丁的殺人犯,入獄不到兩年,一九七一年,永山出版了第一本書《無知之淚》,敘述自己的內心痛苦,因無知、貧窮而犯下滔天大罪,並真誠地道歉與懺悔。書出版後,感動日本人心無數,並一躍為暢銷書。之後他繼續出版《無知之淚續集》一樣大受歡迎,甚至得到文學界的注意。一九八三年出版小說《木橋》,得到日本文學界的桂冠、第十九屆日本文學獎,依慣例,得獎者將被推薦進入「日本文藝作家協會」為會員。在極大爭議中,永山則夫被接受為會員,有些反對者則退掉會籍以示抗議。
永山的懺悔與文學傳奇並沒有改變他死刑犯的身分,雖經多次上訴,也有機會改判,但他終於放棄上訴,在一九九○年死刑確定,一九九七年被執行。
承認「父母的愛」可能是會殺人的道德律,或許可以拯救三島由紀夫;但是,如果曾經擁有父母的愛,是不是也可以拯救永山則夫呢?這中間應該還有很多更細緻的糾結值得探討。
三島與永山所失落的,不管是對痛苦的自覺,還是愛,都因為缺少了佛洛伊德所說的「哀悼歷程」(mourning process),而走入絕境。以精神分析理論的觀點來看,哀悼雖然痛苦,但卻是復原的必經之道。米勒雖未使用「哀悼」字眼,但她跳脫道德桎梏的枷鎖、呼籲世人面對內在真實的痛苦,其實就是要經歷哀悼的過程;正如同更細緻地操作精神分析,因而突顯了本書的價值。
【推薦序二】
當自己內在小孩的媽媽
林蔚昀(專欄作家、波蘭文學譯者)
愛麗絲‧米勒的《身體不說謊》,我是在眼淚中讀完的。而且不是普通的流淚,而是無法抑止的無助嚎啕。
身體會感到痛、會哭泣,我想是因為這本書激起了我體內那個小女孩──雖然在現實生活中,我已經是一個四歲半小男孩的母親──她內心的無助、被不斷拋棄與拒斥的絕望,於是,我三十二歲的身體也感受到她的痛苦而慟哭了。
我和作者來自完全不同的背景、活在完全不同的時空,現實中唯一的連結是我目前住在波蘭,和她出生長大、後來逃離的國家是同一個;但是我十分能理解她所說的受虐兒的心理,以及他們對童年苦痛的否定。因為,我也是受虐兒,而且我是花了許多年的時間、付出極為痛苦的代價,才有勇氣承認、面對這件事。
國小六年和國中三年,我都有被學校老師體罰或以語言羞辱的經驗。打我最兇的是我小一的導師,她打我只是因為我幼稚園沒學過ㄅㄆㄇㄈ、剛開始上學時國文考不好,還有常常在學校哭著想媽媽。除了考試成績沒有達到標準、不守秩序會被打,這位老師也會因為莫名其妙的理由打學生,比如說被打時手沒有伸直、忘了說謝謝、或者被打沒有哭反而笑;她還會對我們進行情感勒索,比如罵我們「只會和父母告狀、不懂得感謝老師付出的心血、讓老師背黑鍋」等。
即使是在今天看來那麼明顯、不可思議的暴行,我也是直到最近兩三年,才能以「虐待」來稱呼那發生在我身上的可怕事件。很小的時候,我會認為我被打是應該的、對我有好處的、需要被感謝的,原因也許就像是匈牙利作家因惹‧卡爾特斯(Imre Kertész)在他著名的小說《非關命運》中所說的:如果不把在集中營中遇見的所有費解而殘忍的事情解釋為正面的,他會因死亡的恐懼而崩潰(引自《身體不說謊》內文)。
米勒在《身體不說謊》中提到,我們的社會時時刻刻都在提醒我們「要尊敬父母」。在西方世界中,這個信仰是依靠基督教精神來鞏固(米勒提出了摩西十誡中的第四誡,稱它為「老人的人壽保險」),而在儒家文化圈,包括台灣,尊敬父母的思想更是得到了廣泛的延伸,隨時隨地透過孝道、五倫、尊師重道、敬老尊賢……等教條來約束我們,要我們善待包括父母在內的所有老人,不管他們曾經對我們造成多大的傷害。
於是,我被迫去為自己憤怒的情感負責,去「體諒」、「寬恕」、「理解」那些其實一點都不負責任的大人。我的父母雖然沒有對我的痛苦袖手旁觀,但是他們也無力改變老師的暴行,只能叫我不要在意。這些壓力、矛盾衝突、敵意和失望一直在我體內膨脹、沸騰,終於,在我十四歲的某一天,它透過讓我用美工刀切開自己的身體,撕裂了我。
照愛麗絲‧米勒的說法,我的身體說話了。那話語是如此的誠實、血淋淋,以至於當時的我和身邊的人都沒辦法面對它,也沒有人能理解這種語言,於是我身體的尖叫只好以沉默的姿態繼續存在。許多年後,當我的自殘行為轉變成對丈夫的語言及肢體攻擊,當我身體的尖叫終於被我自己和他人聽到,當我有了覺悟認真去做心理治療、不再因為痛苦而中斷……我才慢慢聽到、也聽懂了我身體的話語。
「救我。」這就是我的身體、我身體裡那個小女孩從我七歲起就不斷對我發出的訊息。而我一直等到有了自己的孩子,因為不想讓我過去受到的傷害成為孩子的負擔,才有勇氣、意願和能力,去成為我內在小孩的母親,去照顧、擁抱和保護她,對她說:「妳有權利感覺到妳所感覺到的,世界上沒有任何人能夠剝奪妳的感覺。妳不必為妳的感覺感到罪惡,妳值得別人對妳好。」
「妳值得別人對妳好。」當我能夠對自己的內在小孩說出這句話,我也用行動向她證明了:她值得我對她好,我可以對她好。我成了愛麗絲‧米勒口中那個可以滿足孩子對愛的需求的人。同時,因為當母親的經驗,我明白自己的侷限,明白我偶爾也是無法給予的、也會感到疲倦或厭煩,無法滿足內在小孩的所有需求。
但是沒有關係。就像我不必在我的孩子面前扮演一個完美的母親,我也不必在我的內在小孩面前扮演一個完美的「知情見證者」。我慢慢學會,不要因為有時候無法愛自己而感到罪惡,因為那只會讓我陷入無止盡的怪罪漩渦。我只要像英國兒童心理學家溫尼考特(D. W. Winnicott)說的,夠好就好了。因為夠好,我可以允許自己像波蘭兒童教育家柯札克(Janusz Korczak)一樣,針對「如何愛孩子」的問題坦白地回答:「我不知道。」
我感覺自己正站在一艘帆船上,即將航向一趟未知的旅程。我知道在那旅程中我會遇到自己的小孩以及我的內在小孩,甚至是我父母及丈夫的內在小孩。我即將和他們產生一些關係,但我還不知道那會是什麼樣的關係,也不知道要怎麼去接近他們。我只知道風已經起了,而那風,有一部分是愛麗絲‧米勒的書所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