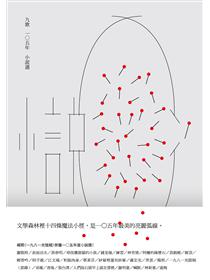說書人的專長是
復活,詞的復活
讓石頭
更像石頭
讓花更花
‧
如果在西夏,你走進了那間旅館
盜夢者與女神剛剛離開
桌上還留有一抹烙著光影的字痕
記憶無法存取,彷彿正在消散
趕不上了嗎?不,故事永遠準備開始
幸運的話,那個說書人還在
一開口啊,幾千億光年的繁華在眼前展開
那是一個銀杏葉漫天紛飛的世界
33篇深入閱讀核心的珍藏書語,當代文學不可錯過的夢幻書單:宛如死亡百科全書的馬奎斯《百年孤寂》;卡爾維諾《命運交織的城堡》的永劫回歸;無限接近那傷害、暴力、恐怖景觀的第一現場的黃錦樹之南方書寫;將真實時間液化、不斷重返的邱妙津《蒙馬特遺書》;看透籠中少女的暗慘心思的張愛玲《雷峰塔》;直闖神話森林不可思議意象的大江健三郎《個人的體驗》;企圖贖回最初依偎時光的童偉格《西北雨》;仿若整個地獄輝煌燃燒的陳雪《附魔者》;盤旋險峻通往無光所在的天梯的房慧真《單向街》;直視未來驚駭想像的韋勒貝克《無愛繁殖》等。
每一次閱讀,都是一次時空輪迴之旅,解構記憶,延展夢境。
在那裡,人生永遠有機會,重新開始。
是這樣靜謐的獨自時光(也不是獨白或獨語),而是獨自感受著星光、流風、時間、大海、暴雨臨襲前的風雲變化,無害但存在於老屋或這座島各處的鬼魂。一個完滿的宇宙。——駱以軍
【胡人閱覽室】推薦書單
童偉格《西北雨》
房慧真《單向街》
黃錦樹《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猶見扶餘》、《雨》
朱天心《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
蘇偉貞《魔術時刻》
陳雪《附魔者》
李渝《九重葛與美少年》
木心《木心作品集》
大江健三郎《個人的體驗》
莫言《蛙》、《生死疲勞》、《檀香刑》
楊澤《新詩十九首》
楊凱麟《祖父的六抽小櫃》
張怡微《哀眠》
徐譽誠《紫花》
蔡俊傑《世界早被靜悄悄換掉了》
黃宜君《流離》
埃蒙德.巴恪思《太后與我》
邱妙津《蒙馬特遺書》
陳綺貞《不在他方》
金宇澄《繁花》
卡爾維諾《命運交織的城堡》
馬奎斯《百年孤寂》
伊恩.班克斯《捕蜂器》
羅貝托‧波拉尼奧《2666》
張愛玲《雷峰塔》、《易經》
奈波爾《米格爾大街》
赫拉巴爾《沒能準時離站的列車》
安娜.普露《惡土》
艾莉絲‧孟若《太多幸福》
安潔拉‧卡特《焚舟紀》
喬伊斯.卡洛.奧茲《狂野的夜》
韋勒貝克《無愛繁殖》
賀景濱《速度的故事》
余華《我能否相信自己》
作者簡介:
駱以軍
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研究所畢業。曾獲第三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首獎、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推薦獎、台北文學獎等。著有《肥瘦對寫》(與董啟章合著)、 《讓我們歡樂長留》、《女兒》、《小兒子》、《棄的故事》、《臉之書》、《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夢遊街》、《西夏旅館》、《我愛羅》、《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降生十二星座》、《我們》、《遠方》、《遣悲懷》、《月球姓氏》、《第三個舞者》、《妻夢狗》、《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紅字團》等。
章節試閱
贖回最初依偎時光
克蒂斯能描述各種自己從未見過的事物:世界是詞藻的海洋,是沼澤、是沙漠,瞬息萬變地環繞他所站立的方寸之地。魯恩總看著朋友,七手八腳為眼前所見的事實塗上一層又一層厚重的油彩,直到一切黝黑而可疑,不再是原來的樣子。……「朋友,」每一場戰役後,魯恩總對克蒂斯說:「您知道的,我但求公平一戰。」「我的朋友,」克蒂斯總是聳聳肩,一手敲著拐杖,一手扶起魯恩,對魯恩說:「只有讓他們在我的言語前,成為需要嚮導的盲人時,我們才平等。對此,我深感抱歉。」我深感抱歉;幾乎每則歷險,都結束在這句話上頭。事後想起,這亦是整個童年時代,白紙黑字浮現在我腦中的最後一句話。
我讀童偉格,視覺上那翻動著空曠的場景如此像年輕時看的塔可夫斯基。但流動的詩意卻讓我想到以色列小說家奧茲,或較好時的石黑一雄。
等待,一個被遺棄的孩子。「時間本身,單純地讓每個人終成鰥寡。」一種時間的洞悉同時放棄。一種靜默的瘋狂,一種焦灼、緩阻,目視著學習老人們(後來你知道那其實是死人亡靈)如何無聲在這殘酷的荒原和時間中,慢速地活著,不,展演他們儀式般慎重以對,像某些要素被吃掉被隱蔽的記憶,「最好的時光」(但難以言喻的古怪)。
小說是這樣靜謐的獨自時光(也不是獨白或獨語),而是獨自感受著星光、流風、時間、大海、暴雨臨襲前的風雲變化,無害但存在於老屋或這座島各處的鬼魂。一個完滿的宇宙。
空間上它是一座島(或有兩個不同名字:狗山和光武島的不同兩座島)。這個島,也許譬似艾可的《昨日之島》,似乎泅泳過去便穿過換日線到被時間沒收的另一端;但卻又歷歷如照明燈下近在眼前栩栩如生的遊樂場。「我好像必須花上淺薄生命裡的數十個年頭,才敢向自己確認,也許,它將永遠如此靜靜的瘋癲,像宇宙中最稱職的療養院。」這個霧中小島有神話時期的父親,有史前時代的軍隊,有王爺府,有火車、鐵路,有校園、村落、家庭、鄰里親人……在這些地貌場所上活動並進行著什麼的人際關係。小說的大半本以上這個小說像在翻印著一具你找不到邏輯的視窗,一種村上春樹的末日之街,石黑一雄《別讓我走》那提供器官之複製人的寄宿學校,或瑪格麗特‧愛特伍的《末世男女》、韋勒貝克的《一座島嶼的可能》──是的,科幻小說,我們借著小說家的凝視,看著那一整片他描述出來的畫面風景,古怪又詩意,其實是童偉格將那「災難」的耳半規管從所有飛翔情節之鴿子的內裡摘除掉了,那變成一種「空望」。童偉格在晚近以單篇形式發表的一篇題名為〈將來〉,奇怪的是,「將來」除了作為這整個小說接近結尾部位的一個時間邏輯的給予,恰像是童偉格自《無傷時代》即發展出來的時光劇場,讓它們進入核爆過後的世界。計時失去了任何藉以形成描述人類存在之意義,與回憶相對應的是一個被永恆取消掉了的現在,那是一個死亡的時間,「已經」終結了,但無法在目蓮救母式的巨大悲願重建這一切枯荒無望之曠野的同時,「解決」那悖論的仍在前進的物理時間。
那讓人想起馬丁‧艾米斯的《時間箭》。一部小說如錄影帶倒帶,時間是顛倒進行的,我們眼中所見,竟不止是動作的倒轉:抓姦的丈夫變成把妻子送給姘頭的皮條客,劊子手贈予死屍完整的身體和生命,噁心的糞便從馬桶的水喉上升吸入人的肛門,之後從他口中吐出豪華豐盛的美筵……「當生命倒著走時,一切變得美好了」。在童偉格的這個「將來」的世界發生著什麼事呢?一種保護著──甚至如在碎成破片的倒影世界裡傻笑著,如失聰者,如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痴」──《無傷時代》的,以超荷於「小說所能贈與、贖償真實之空無」的願力──黏貼模型那樣「小小世界真奇妙」的一個空間化的「白銀時代」(借王小波的書名)。那是我所能想像小說家用不可能之死物與屍骸,用一「借來的時間」讓它們活在宛然畫面裡(一座被大海包圍的島)。
所以這個只要用願力泅泳過換日線的「昨日之島」,一切都變換成白銀熠熠的「將來」,在「我想起來了」的魔術啟動之前,它們恆只是漂浮靜止於巨大標本皿內的死物(殘缺的曠野),一種內向封印於族類的環節們失落的「故事」。這種刻意返祖,剝落掉寫實主義以降強大複刻「真實」的細節元素,使之類似神話(寓言)場景的「故事」,讓人想到巴加斯‧略薩的《敘事人》:「因為在馬奇根卡斯人中間有一個擔負著十分特殊任務的人,他既不是巫師,也不是巫醫,而是主要擔負著講述歷史的任務。這個人是講述事情的、說話的。不久前,馬奇根卡斯人還是分散的,孤立成一個小小的公社,有時是人數很少的家族團伙,因為他們居住的地區是非常貧瘠的……不能組成重要的社會集體。這樣他們便完全分散、孤立的生活。馬奇根卡斯人稱之為『敘事人』的人物是他們各團伙之間來往連繫的一種形式,有些像中世紀的行吟詩人,也有些像巴西東北地區尚存的流浪歌手,彈著六弦琴,走村串鎮,邊走邊唱。至於『敘事人』並不是唱歌而是講故事──既講他們在別的部落裡看到的事情,也講他們自己的經驗、公社裡過去的歷史故事、神話、傳說和個人編造的故事。」
這個在死者、祖先、昨日和將來間,傳遞故事(或夢境)的「我」,是一個退化症的畸人(譬如《鐵皮鼓》的侏儒奧斯卡,《最後一個摩爾人》裡的早衰症少年)。歷史在這個島因某種畫框外的重擊而擱淺了,所有人都停止在那故障的時刻裡,「一個人出生的地方,終於成了他們所能抵達的,最遙遠的地方。」停格,曝光,永遠重複。「我」的父親是個外國人(飛行員。飛機被擊落而被島民俘虜關在大狗籠裡),像瘋了時的老邦迪亞那樣以原人形象成為猿猴般的展示物。真到父親的國家戰勝,島民這一邊的國家戰敗了。「但是,『恥辱』哪裡去了?『仇恨』哪裡去了?還有,『憐憫』哪裡去了?」「我」構造著父親的感受,凝視、獨白、頓悟。由這個退化症的「我」,「無傷時代」的「我」,慢速,默片、黑白膠卷地投影那個父親孤自面對一島之人的屈辱、仇恨和憐憫。這樣篩沙也似流光從眼前傾落,一種偏執的觀照,想看清楚無辜的每一個在場者是在哪個關鍵遭受侮辱和損害。其實其證物泯滅之哀慟一如舞鶴之〈拾骨〉。只是童的「祖先遊戲」之抒情核心更在「寬諒」。寬諒什麼?「我」的罪如迷霧包裹,層層遮蔽(他的祖先們並無罪啊,有的只是被剝奪、被侵侮、被壓碎了)。因為「我」無法修補父祖們的壞毀?「我」故障了,這個僅能用如此艱難晦澀故事重建殘酷時光劇場之「我」讓想像中的父祖失望了?「當簡潔與溫暖,終於也像餘燼那樣將要消亡,對他們的每次猜想,於我就像傾巢的話語,去抵禦那個終將沉默的自己。」
所以這是一個「自己」之書。但那又是一個魯佛的《佩德羅‧巴拉莫》的世界,所有死去亡靈的追憶、懷念、遺憾,全部進駐這個唯一活人(甚至他發現自己也早已死去)的意識。「我」負載著這所有沉默無告的祖先們那麼巨大無垠的苦難,「自己」是遺忘的荒原最後一隻稻草人,最後一根鹽柱,但我難改自己血液基因裡那善於苦笑、沉默、原諒,和畏敬海天的天性,「我已經無話可說了」。「我」,假定是複製自他人生命的贗品;但同時對抗這種複製,形成了楊照所說的「廢人存有論」:不給人帶來困擾,不與這世界發生過多不可測的連繫。
「我」養著一隻「穿透了老王的心」的那隻小象;「我」在父親面前和看不見的貓玩把戲,這樣馬歇‧馬叟式的和不存在,已離去的失落之物(親愛者)玩「他們仍在場」的默劇,「我」像捧著將要迸散碎落的水,那樣小心翼翼,那樣預示著「將要」,必然的失手。那個慢速連笑話都失去了該有的痙攣,「沒關係,笑話會等人。」或「好好想,你時間多。」「他」(在後來的章節證明是「我」的祖父)在「我」的夢裡,時光運鏡不斷往前推:包括「他」總是被陌生人騙走的母親;「他」在軍中承受那一次靜默荒謬的暴力,薛西佛斯式的浪費;「他」的父親為了兒子的命運去找神乩打架,想收回海王之神諭,最後卻變成那麼悲哀、孤獨,那麼自由對羞辱的反轉冥想之死前時刻。當「自己的故事」退無可退成為「箱裡的造景」──「『他的』山村如何被封固在一個更為繁複的人造童年裡,和時間兩相遺忘,在地理中消失。他帶動一整幢病院,發現世界並沒有瘋」,只是變成一死者回返的霧中風景。「我全部想起來了。」從無言、失語而至這整個小說最後滔滔不絕的描述,「我」成為那個之前因舌頭賈禍的海王,喚起所有人的記憶,「我深感抱歉」。「我」睡著了,在夢中造鎮,又用小圓鍬鑿毀整個島活人與鬼魂的阻礙;「我」,一種贖回的意志;「我深感抱歉」,為著同時祭起這驚擾亡魂而融化已凍結的時光,讓不知自己已死的親愛之人們重演活著的時光。但那正是「我」和所謂界線外粗暴、快速、無感性的正常世界對決的「平等的話語幻術」。倒帶、透明,揹著快樂無害的他們在這片夢中荒原跑,從葬禮出逃,拉出這樣一幅浩瀚如星河,讓我們喟歎、悲不能抑、靈魂被塞滿巨大風景的「贖回最初依偎時光」的夢的卷軸。
-------------
逆旋的時光重力場
孟若收在《太多幸福》短篇集裡其中一篇,〈自由基〉的故事大致是這樣:
一個叫妮塔的女人(她六十二歲)的丈夫瑞奇(他八十一歲)剛過世(死於猝死)—小說的開頭便是這個初老婦人孤獨剛辦完那寂寥的葬禮。
孟若的所有故事,發生的地景,因為那典型加拿大小鎮地曠人稀之感,把人和人的距離在那攤平的空間拉遠些,所以使得一切猜疑、懷念、較長時光裡的耿耿恨意、曾發生過的某一次偷情祕密收藏了幾十年、在那些屋子裡一起生活的男女必然產生的,時光落葉堆的彼此厭煩……這一切似乎比其他人的小說,因為在一較空蕩蕩的運動場館裡,產生了恍如有回音的效果,每一種心思電子在那「孟若空間」裡跑動,要花更長一些時間,才會如撞球擊打到桌台上的另顆球。
這個故事,這個初喪偶的老婦妮塔,在一種靜默、孤寂,對生命乏味的持續狀態,「剩下我一個人活著了」,有一種輕微的錯愕或面對生命的荒謬不知作何表情的呆愣:即原本她(以及那老丈夫)預想是她會先走,他倆大概一年前就有了準備,那時醫生診斷她的癌症已到了最末期。
「我怎麼料得到,這會兒居然被他搶先一步?」她成了那個,必須疲憊辦理老伴喪事的,「收拾者」。主要是,了無生趣,活在死亡遮蔽所剩無多的餘光裡。這時孟若開始露了一手她的「巨蟹座時光落葉堆魔術」,女主角的內心獨白,回憶。原來這妮塔在很久很久以前,是這瑞奇和他前妻婚姻的闖入者,「鳩占鵲巢」,趕走了那個前妻,成為這屋子的新女主人:
最後的結局是貝蒂去了加州,後又搬到亞歷桑納州;妮塔則在教務主任的建議下辭了工作;瑞奇因此無法升為文學院院長。他選擇了提前退休,賣掉市區的房子。妮塔沒有接收貝蒂的木匠圍裙,卻在一片混亂中開開心心看她的書,用電熱爐作簡單的晚餐,不時散長長的步,探索周遭的一切,帶回長短不齊的虎百合和野胡蘿蔔花束,放進空油漆罐權充的花器。她和瑞奇安頓好之後,有時想起自己不知怎地一下子就成了那個年輕的新歡、得意的小三,活躍歡笑、蹦蹦跳跳的天真姑娘,不免有點汗顏。她個性其實一板一眼,是個笨手笨腳,在別人面前就不自在的女人。
好吧,我把敘事的轉速調快些,免得掉進「孟若的時光重力場」,那內心層層累聚的深井。總之,這被布置成「多出來的時光」,所有生命債務的相關人事終於在幾十年後都死去,那些愛情、後宮機謀的鮮豔毒汁,早變成老婦內心,無人想好奇探知的壞朽家具—一個靜態的、被時光之塵封印的靜物畫—卻在某個白天,一個青年上門說要「檢查保險絲箱」,當然他不是,他是個剛殺了自己的父母和坐輪椅的姊姊(覺得他們很煩)而逃亡的瘋子殺手(他告訴妮塔老婦,他是要他們坐在客廳拍全家福照時,拿出手槍砰砰砰,把他們全幹掉了,然後又拍了一張他們驚愕或垂頭死狀的照片),變成了很像這類電影(變態殺手和屋子的人質之間的對峙戲碼)。
不對稱的,完全無可商議的暴力,這個年輕人處在瘋狂和躁鬱的高亢情緒,他輕輕一捏就可以把這老婦像螞蟻捏死。事實上,在他眼中,她也已是必死之人(他怎麼可能在離開這屋子前不殺了她,讓她去報警,給他添亂),他賤蔑她,要她拿出屋裡的茶、紅酒、食物,砸碎她的餐盤、展示暴力關係裡,不讓被施暴者用話語中的道德規勸、動之以情、機智、心理戰順藤摸瓜的任何平等刷話位置。在這樣的二人封閉劇場中,施暴者和承受暴力者,皆無可救贖的掉進一「人失去人類形貌,所有文明的細微支架皆無效」,道德最黑暗的墮落深淵。因為我終將殺掉妳,此刻在這火柴盒裡,我對妳所做的一切醜惡、變態的展演,都不會有任何外面的人知道了。沒有任何關於禮貌、道德、輿論指責、別人的目光造成的羞恥、潛意識裡的宗教審判︙︙我可以盡情暢爽的在妳(一堆死肉)面前,演這唯一一個觀眾的獨角戲。
但這時,這個老婦妮塔,在孟若筆下,出現了一個三頁左右的魔術,她對這年輕人說:
「我知道那種感覺。我知道把傷害你的人幹掉,是什麼感覺。」
「是喔?」
「我也幹了跟你一樣的事。」
「少來。」
接下來她說了一段像變色玻璃隱形眼鏡片將光線變暗的故事:她告訴那殺人凶手,當初她如何用院子裡的「大黃葉子之葉脈中的毒」,如何精密計畫,不動聲色,瞞過眾人耳目,下毒在那要拐走她先生的賤女人的咖啡裡。這時連我們讀者都產生一種畫框裡的細節,在哪被揉捏一下,便偷天換日產生了「宇宙曲拗」的暈眩感。你可能要小說的更後面才意識到:啊?她把故事中的人物顛倒過來了。她變成那個當初被她搶走老公的,近乎沒有臉的妻子。而這個妻子進入「下毒時光」所毒殺的「賤女人」,正是多年前的她自己。也就是,她說了一個僭越進「當年被她奪走所愛」、理應那怨恨足以支撐一個巧布機關謀殺她的,那個妻子的內心。但其實一切都沒有發生。但在那個故事(此刻她的丈夫已死,她也罹癌似乎不久人世)裡,那「薛丁格的貓」把另一個鏡像宇宙裡該發生的像莎士比亞戲劇那血流五步、復仇夜梟之翼拍擊的情節,全發生了。
更弔詭的是,這個她「顛倒、錯置自己是那個真正生命受創者,所殺掉的死者」之故事,真的打動了這個年輕瘋狂殺人魔。他可能內心哪個祕密的插栓被拉開,視眼前這個脆弱無助的老婦為「自己人」,是和他一樣,「早被打入地獄之人」。他放過她,說了一些恫嚇她的話,開著她丈夫留下的老車子離開了。
這老女人在那倖活下來的發抖時刻,內心想著:
她應該寫信給貝蒂的。
親愛的貝蒂,瑞奇死了。我因為扮成妳,救了我自己一命。
在同一本書裡的另一個短篇〈虛構〉,則非常奇妙的,寫了一個「像那篇〈自由基〉的倒影,或鏡像」的故事。這一篇的女主角喬伊絲,恰是某個「被奪去所愛」的妻子,雖然兩篇在各自的人
名完全不同—當然這是兩篇在各自祕境按不同打孔的人心音樂盒簧片旋轉,各自孤立的小說—小說開頭先慢速(孟若轉速)微勘了丈夫離開她的時刻:驚惶、不解、女性自尊崩解(她那麼美、玉腿纖纖、金色長髮、智商全校第二——她丈夫是第一——她在學校教音樂;而那搶走她男人的贏家,只是個矮個、全是刺青、沒有女人味的蠢貨?)。
之後是——像許多美麗女人的一生,可以是別的人的幾輩子,傷害過她的往昔人事,或許只成為列車過站其中一個站名的月台,或是,祕境湖泊上划小船下望那清澈水底的一艘沉船——可能二十年過去了,喬伊絲已是另一個有錢男人的妻子(續弦的),她已在豪宅、好客丈夫的眾朋友們來家的餐會、葡萄酒、美食、管弦四重奏……的另一種生活中完美的成為,這種充滿活力、交際應酬、歡樂、菁英圈子的世界,稱職的美麗女主人。之前那個,年輕時和她一道流浪、經歷嬉皮歲月、智商和她匹敵而和社會主流那套格格不入、放棄高學歷文憑而安靜的在偏僻小鎮當個木匠的,那和她像一對「偕老同穴」、靈魂雙胞胎的男人—重要的是,遺棄她而和另一個怎麼看都比不上她的怪女人在一起—這對她都是很久遠,甚至記憶模糊的過去了。
但有一天,她意外買了一個年輕女孩的小說,非常奇幻(透過閱讀)的某種穿越,她發現那篇小說正是說著她的故事,只是敘事者是以一小學女生的眼光,充滿愛情的回憶著當年那位「小提琴課老師」,那個一頭長髮、個子高高、身上氣味是雪松碎片的味兒的女老師。但後來孩子的母親去師丈那邊上班,這孩子夾在大人錯綜複雜的關係與錯覺之間,一頭霧水。
……星期四有音樂課,是一週中最重要的一天。那一天的喜與憂,全取決於孩子表現得好不好,老師有沒有注意到。兩者都幾乎難以承受。老師的聲音可能很冷靜、溫和,有時講講笑話,掩飾聲音裡的疲憊與失望。孩子好傷心。但老師也可能突然變得輕鬆愉快起來。
於是這個許多年後的金髮高個美女喬伊絲,在這小說中比對、像疊放的幻燈片,重新冒出一個「當年沒意識到,躲在角落以小動物的愛慕,看著那個正在受創的自己」的新視覺,變成一種難以言喻的複式回憶。她既是那被奪去所愛、羞辱的妻子;卻又在這小女孩(而且是那篡奪者的女兒)眼中,充滿當時的她並不意識到的,全世界最輝煌幻光的美。她有沒有利用這小女孩對老師的崇拜,心不在焉的籠絡她,打探自己老公和她媽之間的私密細節呢?
透過那小說的閱讀,她想起早已遺忘的片段:她開車載這小女孩回家,帶小女孩去買冰淇淋,看船屋渡口,告訴她一些野花的名字,別有用心的唆使、探問孩子……如果說〈自由基〉是當年搶走別人老公的這個小三,許多年後(老公衰老死去),卻在一次意外危機中,以顛倒、虛構那個挫敗退場的妻子,在不存在的平行宇宙,下毒謀殺了那個自己。她靠這個顛倒、移形換位到「想必恨自己入骨」的老情敵,其實不存在的怨恨密鎖保險櫃,越俎代庖說出了這個「殺死自己」的故事,卻因此救了自己一命。而〈虛構〉這篇小說,卻像量子力學中的「粒子纏繞」—發生過纏繞的粒子,分開後,無論隔多遠,這個粒子發生旋轉,另一個粒子會像鬼魅的魔法,同步產生逆旋—孟若寫了另一個短篇,是以「被奪走丈夫的妻子」,那個受創者,很多年後,她卻是讀到那已與她生命無關的男人、女人,和當年那小女孩,長大後寫的小說,迴旋重臨那傷害現場。那多出來的觀測鏡片,折射出比原諒、遺忘更在時光中讓人低迴、品嚼的,對人類情感的味蕾細微繁複變化之慨:或是在當年的那巨創中,她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但小女孩像凶殺案現場呆站的目擊證人,她看見的是這個美麗的女人,在殺死,從那個悲慘的前身蛻殼,變化成另一個人,之前的,那麼短暫的換日線。
贖回最初依偎時光
克蒂斯能描述各種自己從未見過的事物:世界是詞藻的海洋,是沼澤、是沙漠,瞬息萬變地環繞他所站立的方寸之地。魯恩總看著朋友,七手八腳為眼前所見的事實塗上一層又一層厚重的油彩,直到一切黝黑而可疑,不再是原來的樣子。……「朋友,」每一場戰役後,魯恩總對克蒂斯說:「您知道的,我但求公平一戰。」「我的朋友,」克蒂斯總是聳聳肩,一手敲著拐杖,一手扶起魯恩,對魯恩說:「只有讓他們在我的言語前,成為需要嚮導的盲人時,我們才平等。對此,我深感抱歉。」我深感抱歉;幾乎每則歷險,都結束在這句話上頭。...
目錄
贖回最初依偎時光
底層的珍珠.微物之神
寫在南方
第二次
不確定的灰色地帶
鎮魂曲:不存在的女兒和她的瘋魔情人們
哥德大教堂與曼陀羅
他從自己褲袋掏出那枚錢幣,放上
靈魂深處祖母的敘述
從不斷累聚的陰影朝下望
在時間的影子裡玩耍,閑坐,喝茶
一種少年同伴的時光冒險邀請
那麼大的離散;那麼小的團圓
佇立地獄入口的文字神靈
真空管裡的獨角獸
別人的夢
讓人眼瞎目盲的愛之太虛幻境
時光踟躕
Un Momento
繁花
永劫回歸
死亡百科全書
妖異綻放的「惡之華」
宇宙黑洞裡蘊藏的能量
籠中少女的暗慘心思
真實世界的邊陲地帶
逆旋的時光重力場
如利刃般的想像
在大師的墓地上跳舞
華麗髑髏場
不只是處決了小說一次而已
百感交集的旅程
贖回最初依偎時光
底層的珍珠.微物之神
寫在南方
第二次
不確定的灰色地帶
鎮魂曲:不存在的女兒和她的瘋魔情人們
哥德大教堂與曼陀羅
他從自己褲袋掏出那枚錢幣,放上
靈魂深處祖母的敘述
從不斷累聚的陰影朝下望
在時間的影子裡玩耍,閑坐,喝茶
一種少年同伴的時光冒險邀請
那麼大的離散;那麼小的團圓
佇立地獄入口的文字神靈
真空管裡的獨角獸
別人的夢
讓人眼瞎目盲的愛之太虛幻境
時光踟躕
Un Momento
繁花
永劫回歸
死亡百科全書
妖異綻放的「惡之華」
宇宙黑洞裡蘊藏的能量
籠中少女的暗慘心思
真實世...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6收藏
16收藏

 22二手徵求有驚喜
22二手徵求有驚喜



 16收藏
16收藏

 22二手徵求有驚喜
22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