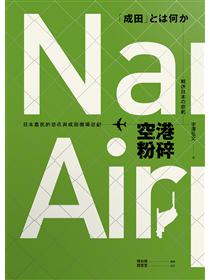我想找尋的是一種不同種類的烏托邦:其歷史是循著邊邊走,以環形行進,切分節奏,總是處於浮現中狀態,永不抵達。最起碼,這種兼納多樣性和反諷的曲徑讓我們有可能批判單音權威 ——不管那是支配性權力還是社會行動起義者所作的單一真理斷言。我們面對的與其說是一條清晰的歷史道路,不如說是一叢群的替代方案,一個由糾結關係構成的當代現實。
全球的權力安排正在我們腳底下發生變化。無論如何,「未來」都確實比二次大戰之後的任何時期都更具開放性,更加結局未定。在這個「未來」中,另類的發展模式、區域主義、文化特殊性、多樣化主權和原民主義—世界主義連接真有前景可言嗎?歷史正往一個以上的方向移動嗎?在這個結局未定的交接口,怎樣才算是「現實主義」?究竟怎樣的故事才算夠大的故事?今日的危機甚至「混亂」有理由讓我們感到恐懼還是懷抱希望?顯然兩者皆是……
作者簡介:
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目前為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意識歷史學系榮譽教授,並於2011年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為當代文化反思論述之最重要學者,其跨學科觀點與批判包含人類學與民族誌、田野調查工作、原住民研究、藝術、歷史,博物館學,與文學分析。著有《個人與神話》、《文化的困境》、《路徑》、《人類學邊緣》、《復返》等書,同時與喬治.馬庫斯(George Marcus)編輯有《書寫文化》。
譯者簡介:
林徐達,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學博士,目前為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教授。著有《詮釋人類學:民族誌閱讀與書寫的交互評註》(2015)。
梁永安,台灣大學人類學學士,東海大學哲學博士班肄業。譯有《李維史陀:實驗室裡的詩人》、《與珍雅各邊走邊聊城市經濟學》、《聖保羅:基督教史上極具爭議的革命者》等。
比恕依.西浪(Pisuy.Silan),台灣原住民泰雅族人,目前就讀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班。
章節試閱
「我們」將會消聲匿跡嗎? 作者:Pisuy.Silan
《復返》(Returns)一書是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繼《文化的困境》(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及《路徑》(Routes)三部曲系列的第三本重要著作。此系列作品的後作可視為前著的延伸與討論,《文化的困境》批判人類學知識與研究職權,反對單一且獨白的民族誌書寫,強調以複調的敘事方式再現。《路徑》則是反思過往人類學偏執於固著性與疆界的劃定,認為透過旅行與接觸,作為探討未竟現代性的關鍵所在。本文所要討論的《復返》,從探究邊界孔隙及流動的《路徑》出發,進一步以原住民為核心,討論其面臨現況所採取各種轉圜、折衝與策略方式,重新省思因族群身分所延伸出的各種多頻、複雜的議題。
原住民社會與傳統部落文化是否將如同悲觀的預測,在全球化及經濟發展的傾軋裡逐漸銷聲匿跡?克里弗德透過《復返》宣示,這絕對不是當代原住民唯一可行的路徑。很多族群的語言確實不斷消失;很多部落社會及文化漸漸瓦解,然而在種種危機的進逼之中,仍有為數不少的原住民族群挺住壓力,把遭受破壞的生活方式,從殘存的文化與傳統中重新編織,從底蘊中挑選具有適應力的傳統材料,在錯綜複雜的後現代性中新闢出不同的途徑。
克里弗德透過三個可以拆解且他自白聲調不一的學術「中篇故事」(novellas),引領讀者理解原住民文化的復興以及原民行動(indigenous agency):第一個單元介紹並分析歷史的轉化和政治能動性的理論:銜接(articulation)、表演和翻譯。第二個單元則以「突然現身」於現代世界的伊許為案例,被視為「美國最後一位野生的印地安人」(the last wild Indian in America)的伊許,他的出現與死亡標記著原住民的消失和覺醒。第三個單元則聚焦於阿拉斯加的科迪亞克島,透過博物館與原住民合作的「協作式展覽」以及當地博物館向法國借回自己族群面具的過程及展覽,討論原住民文化資產如何作為原住民文化復興的一環。
略過可議的策略性和表演性質,現今原住民絕少如同殖民時期裡的明信片,以恍如隔世的奇風異俗形象再現,有意識者能乘勢隨著全球化大展開,選擇以一種公共角色讓自己被看見及被聽見。這種具有原民自覺的再現,克里弗德稱之為「原民現身」(Présence indigene)。他援引半世紀以前轟動的「自豪非洲人」運動(Ne’gritide),創造了「自豪原住民」(Indig’enitude)一詞,形容自八〇年代起遍地開花的「原住民現身」運動,彰現了「再銜接」(rearticulation)的過程:原住民的傳統被恢復,並且與其殖民、後殖民及全球化的歷史有關聯。「自豪原住民」運動致力挑戰或重構民族國家以及跨國資本主義主導的現代化議程,並且運作於地方、國家、跨國活動或者種種不同文化價值如環境保護、身分認同等等的社會運動之中。
《復返》裡列舉的原住民現身的案例:一九七一年美國在原住民以及欲鋪設油管的石油公司壓力之下,通過了《阿拉斯加原住民土地權力處理法》(Alaska Native Claims Settlement Law),讓原住民有權經營公司的優勢;一九七五年在新克里多尼亞舉辦的「美拉尼西亞 2000」,原是彰顯卡納克人認同的節慶,卻連動引發涵括太平洋、南島的認同意涵,擴散連結成泛太平洋島民文化節慶;二〇〇〇年雪梨奧運,場內原住民為開幕表演歌舞,場外同時聚集抗議的原住民,不同舉措的原民面貌,同時間傳遞至全世界各地的新聞鏡頭。而原住民運動員凱茜.弗里曼(Kathy Freeman)優越成就在此亦獲得舉世注目。
如此顯著的原住民現身案例,卻反向暗示著並非所有的原民現身,皆能以這般耀眼的姿態被觀注。原住民日常生活中的傳統文化感,大部分以沈默平淡的姿態持續,卻隨時能被群體召喚、挪動、調整及運用,將過往與未來聯繫,讓族群調整生存的方向。這種原住民群體銜接的歷史與現實、過往與未來的能力,在克里弗德看來,不只是原住民族群存續的問題,也是一種原民生活在現代性的容身調適。這般開放的視野及寬敞的態度,扣連在《文化的困境》中反對人類學權威暨獨白的民族誌書寫,繼而提出複調、多頻與眾聲喧嘩之後,進一步探究原住民現身問題。克里弗德認為,研究者更需要的是再現的圓滑機制(representational tact),需要一種耐心、自省(self-reflexivity)的開放性。他引用詩人濟慈所說的「守虛能耐」(negative capability)形容這種態度:保持一種警覺性、不遽下結論的開放態度。除了意識到我們對他者的經驗只能局部企及,也必須追蹤阻礙模式和事件浮現的多元場址,有能耐將「大於地方」的模式串連。他強調現在人類學家已經不只是「照樣子說出來」而已,而是抱持一種聽尋歷史的守則去探究。這種態度被稱之「民族誌-歷史學現實主義」,即著眼於被決定程度較低的轉化過程,注意到新意(newness)是如何在實踐中銜接;差異和同一如何被翻譯、詮釋;以及如何向不同的群眾展演原住民群體。於是《復返》不只關注全球化及後現代之下,原住民如何被動的現身問題,也提醒原住民是向內、向自身文化挖掘,創造機會的能動者。
在此論述的過程中,克里弗德也並置研究者應該抱持的態度。在伊許現身的故事中,圍繞其身邊的人類學家克魯伯(Alfred Kroeber)、沃特曼(Thomas Waterman)、一起練弓、狩獵,同時是私人醫生的朋友波普(Saxton Pope),以及在伊許死後四十年透過克魯伯的口述資料撰寫《兩個世界裡的伊許》(Ishi in Two Worlds)的克魯伯夫人西奧朵拉(Theodora),混雜了科學研究、友誼、主從、虧欠等矛盾關係,勾勒出人類學者、白人與原住民延續超過一個世紀來的糾結情緒,並在紛紜的複調中有所批判;同時也透過美國加州原住民「伊許遺骸返還運動」的故事,佐證不同的原住民群體共享了伊許帶來的歷史(泛)原住民文化親緣性。
伊許帶出的種種變奏:《復返》第二部分及第三部分是各種不同面貌的原住民「現身」經驗。克里弗德著墨最多的是人稱「最後一位野生印地安人」伊許的故事。藉由伊許,作者提出關於恐怖與療癒的沉思,顛覆克魯伯夫人在《兩個世界》近乎獨白式的書寫;再者,透過伊許提出關於「歸鄉」(repatriation)與「復興」(renewal)的省思。族內最後一人的伊許,應該歸回誰的「故土」,哪個族群可以聲稱為其歸屬?他又如何成為整個加州原住民復興的契機?一九一一年 八月底伊許走出了他躲藏的地方米爾澗和鹿澗的深谷,在美國北加州小鎮奧羅維爾郊區的屠房被人發現。從「被發現」到罹患肺結核辭世的五年裡,他受聘於加州大學人類學博物館裡擔任管理員的工作,每個星期天為參訪博物館者演示雅希人(Yahi)的箭術以及造箭、做弓的技術。這個看似單純的故事,克里弗德卻能引導出許多精彩的討論:
首先他讚揚了西奧朵拉的《兩個世界》,如實書寫白人干擾加州田園生活的暴力和種族屠殺事件,明指白人的種族優越感,以及優越感賴以獲得支撐的歷史失憶症。克里弗德藉此提醒,康拉德在小說《黑暗之心》中所描寫的世界並非虛設,不過一百年前美國加州也發生屠殺事件,讓伊許失去所有親人。歷史失憶症其實不分地區、種族及年代。我身屬的泰雅族 Mncaq(大豹群,位於新北市三峽和桃園市復興區交界區域)、Msbtunux 及 Mgogan(大嵙崁前山群、後山群,位於桃園市復興區),自十八世紀起陸續面對清國及日本的殖民統治。Mncaq 群慘遭消滅,部落土地在日據時代被佔領,為財團三井合名株式會社所有,到了中華民國時代又搖身一變為國有地。被侵略的泰雅人領域 Msbtunux 及 Mkogan 的土地,直接被命名為「桃園市復興區」,殘酷的歷史遙遠嗎?其實並不怎麼遙遠。
克里弗德其次討論了博物館的角色。何以伊許不是投靠棲地北方,與他語言勉強溝通的原住民,或者選擇南邊稍有淵源的邁杜人(Maidu),而是在博物館工作?西奧朵拉天真地認為伊許是心甘情願地選擇博物館的工作,並與博物館朋友建立深刻、溫暖的跨文化友誼,亦以忠誠和配合研究做為回饋,克里弗德則從另一種角度,點出伊許的抉擇的複雜性:「克魯伯和沃特曼肯定是把伊許看成是純正印地安文化一個未受污染的珍貴樣本。他們有強烈的動機把他留在近旁,以便研究」,並指出「當時人類學家缺少想像替代方案的能力,以及讓伊許暴露在城市的疾病中和博物館公開角色的隱憂」。以博物館立場而言,伊許絕對為博物館提供身分正確的文化專業服務;然而卻無視伊許直接面對白人疾病無力抵抗,而讓他暴露在危險當中;初來乍到現代世界的伊許,在博物館裡「演出」過往純真的種種反省:至少有原住民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固執,以及博物館自恃為原住民純正性的見證及守望者。不僅如此,克里弗德亦從伊許的角度設想及觀望:有地方居住、可以自由行動,並能賺取費用,對於一個面臨生存危機的人看來,舒服的博物館環境總是比陌生的原住民部落更容易被決定。
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加州原住民的「伊許遺骸返還運動」讓伊許再次登上媒體版面。有別以往,這次伊許被加州原住民賦予了族群存續的高度期待。克里弗德指出,返還運動至少有三個重疊的論述一起運作:使者、狡猾生存者和療癒者。作者觀察到,人們賦予伊許使者般的冠冕。西奧朵拉在為學童所寫的故事書裡,形容伊許是雅希部落的最後一位英雄,並將雅希人包含勇氣、信念和強壯的生活之道帶給文明。二〇〇〇年九 月,慶祝伊許歸葬故土的慶典海報,象徵著伊許回到故土與祖先聯繫;也指涉加州原住民透過伊許與祖先再次達成連結。然而最特別的是聖羅莎(Santa Rose)加州印地安人博物館暨文化中心所舉辦的「伊許:一個有關尊嚴、希望和勇氣的故事」。其中一個展區的設計呈現伊許一張近照以及一項雅希人德目:「勇氣」、「慷慨」、「尊重」及「自重」,表示伊許勇敢充滿了這四項美德,並將其視為一位為原住民未來世代帶來美好信息及典範的使者。然而,並非所有人都同意伊許體現了美好的人性價值。克里弗德提醒我們從原住民族人對伊許的反諷評論不僅動搖了伊許本身所代表的「純正成分」,也彰顯了世界上並沒有單一的族群身分以及統一的原住民觀點。
作者舉出阿尼什納比族(Anishanaabe)的維森諾(Gerald Vizenor)為其學校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伊許園」啟用典禮致詞的說法:「部落姓名和部落故事的陰影持續著,而這陰影是我們的自然存活。」在維森諾用詞裡,「存活」(natural survivance)與堅守與延續傳統生活方式的「存續」(survival)並不相同:前者是一種為了生存而做的取捨,也是一種存活的技巧。克里弗德認為,當伊許從事博物館工作,便接受了「純正模擬」御前表演(command performance)的角色。他在表演雅希人的同時,正是將自己的一部份隱藏起來,藉此「存活」下去。維森諾的說法雖然中性,但也道出「存活」是部落姓名和部落故事的「陰影」。克里弗德則用狡猾者(tricker)來形容伊許,並非指稱伊許是口是心非配合他的博物館朋友,而是提醒我們,伊許如何在權力關係中建構一套生存模式。
來自族人的評論尚不止於此,克里弗德例舉了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原住民藝術家倫納(James Luna)的表演藝術《人工製品》。一九八七年,倫納讓自己光著身體,全身只有下半身蓋上一條毛巾地躺在博物館的地上,四周擺上了展品解說,說明躺在地上的人的姓名以及傷疤造成的原因。除了直接指涉伊許作為活展品的生存術,也銳利地指出博物館對原住民身分(identity)及本真性的渴求。從伊許開始,美國博物館開始有所謂的「純正印第安的表演」。原住民該是什麼形象呢?博物館再現的原住民,常常是凍結在前接觸的年代所謂「最純淨」的形象,是使用傳統弓箭狩獵而非霰彈槍;穿著丁字褲潛水下海射魚,而不是穿著潛水衣或使用機動船;使用水平背帶機在地上織布,而不是用電腦織布機的原住民吧。克里弗德認為,倫納這件作品諷刺了博物館進行的「搶救性搜集」的態度,一如作者在《書寫文化》(Writing Culture)中敘述的「搶救性人類學」(salvage anthropology)那尖銳視角一般,持續質問:「即將消失的文化傳統的紀錄者和詮釋者是某種本質的保管人,是本真性無可置疑的目擊者嗎?」那麼,博物館該呈現出甚麼樣的形象呢?從克里弗德述說複雜紛紜的伊許,或許可以給出一些答案:讓出空間,不只提供了本真性和身分的各種辯論,更帶出了族內聲音的參差、眾聲及異質性。
返還運動的第二種論述圍繞在伊許成為眾人的療癒者,並成為加州原住民的連結過往與現代的橋樑。邁杜族的藝術家戴伊(Frank Day)聲稱他與父親在伊許現身的前幾個月,看見伊許為同伴療傷,並以畫作《依許與同伴在拉明沼澤》畫下所見。他筆下的伊許,猶如具有神聖能力的巫醫。作者認為,戴伊描繪的伊許似乎與現況不符。畫作中的伊許面容莊嚴具有能力,與現身時形銷骨立的難民形象形成強烈對比。雖然這些疑問無法獲得確認,但確定的是畫作混合了部分真實、部分寓言(fictions),讓戴伊成功創造了關於伊許的邁杜族口傳故事。故事加強了邁杜族與雅希人的連結,後來更成為邁杜族主張伊許應該安葬族中的依據。
不只在邁杜族,在其他族群伊許也發揮了同樣的能力。伊許在加州的原住民群體被回憶、借用、轉化與詮釋。克里弗德提及一九七三年沙斯塔學院(Shasta College)的戲劇表演《伊許》。劇裡演出伊許祖母的黑爾斯通(Hailstone)是雷丁河的原住民,她說明了參與演出的理由:「我演這個的理由不只是因為伊許是雅希部落的最後一個族人。演出時心情沈重,因為他還是關於我的部落,有關所有部落—他們正處於垂死中。在美國兩百週年的今日,我希望我們可以攜手計畫未來,而不是由別人為我們計畫」。誰都不願意淪落至「族中最後一人」的困境,但誰都可以想像「自己是伊許」的認同;如此的想像足以讓自己時刻保持儆醒,並鞭策自己積極規劃族群未來。至此,伊許已經不只屬於他自己或者雅希部落而已,而轉化為攸關加州其他原住民部落生存與未來的故事。
伊許的故事說來單純,然而克里弗德卻追溯了殖民史觀崩塌的過程,並從故事裡騰出許多空間。族中最後一人的伊許該歸葬何處?是傳說中伊許母親的族群邁杜族?還是由與伊許所操雅希語(雅那語的一種方言)有關係的雷丁和皮特河的原住民(他們混有若干雅那人血統,但早已不操雅那語)?族群認屬的疆界模糊且充滿了彈性,無疑地挑動了人類學過往所認為族群存在的僵固區分,持續滋長的是更多的新興、複合、聯合及跨部落的事實。如克里弗德所說的「環繞在伊許這名字所產生的故事不斷滋生,打開眾多新的可能性,其他種類的『進步』因此變得可以想像:烏托邦也許本已存在,所以重點不是前進,而是轉向和回歸」。因而《復返》的第二部分以西奧朵拉為人類學家丈夫克魯伯譜寫的安魂曲為基礎,搭配一直以來克里弗德慣有對搶救式人類學方法的諷刺,以及對原住民回應現代種種向內復返又向前連結姿態,演奏出複調的變奏曲。
傳統作為創發性動力:《復返》另外重要的篇章是〈望向多邊〉以及〈第二生命:面具的復返〉。克里弗德透過阿拉斯加沿海的原住民阿魯提克人(Alutiiq,也稱為蘇格皮亞克人 [Sugpiaq])與當地阿魯提克博物館協作式的大型展覽「同時望向兩邊」(Looking Both Ways),藉此總結原住民遺產工作是一個由原住民選擇進入過去,開通一個未決定的未來的途徑。作者透過法國海布洛涅的城堡博物館「皮納爾面具蒐藏」返回阿拉斯加科迪亞克島的阿魯提克博物館,探討面具復返後對阿魯提克人乃至於當代阿拉斯加原住民所產生的意義。
克里弗德仔細鋪陳了對阿拉斯加原住民身分認同相當具有影響力的《阿拉斯加原住民土地聲索解決法》(The Alaska Native Claims Settlement Act; ANCSA)產生的背景。在一九七〇年日益強大的阿拉斯加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一個急欲興建一條橫跨阿拉斯加的輸油管的跨國公司,以及企圖終結失敗的「保留地政策」的政府三方協商之下,《解決法》在一九七一年通過。該法將四千四百萬畝土地和近十億美元撥給十三家區域性原民公司和二〇五家鄉村公司。同時也規範如果個人要成為股東,則必須至少具有四分之一的原住民血統。這些原住民公司以發展經濟為主,並也負擔起阿拉斯加原住民醫療、教育及文化更新。由此,克里弗德描繪出阿拉斯加原住民文化的振興,與資本主義經濟的連結。克里弗德提及,諸如由已開發為目的大型開發公司掌控了大部分的土地和基金(而非部落);雖然規定只能雇用阿拉斯加原住民,但實際執行狀況卻參差不齊;或者是原住民持股二十年內不能出售股權,但二十年之後則可以自由轉讓,讓本法原先希望土地永遠把持在原住民手中的目標以及自由主義私有化議程陷入矛盾;以經濟、個人主義進步願景為主的開發公司,多少與由擴大親屬關係、社群守望相助和自己自足維生方式所構成的傳統有所衝突等問題。即便《解決法》一直都是複雜、問題重重也是好壞參半,但是「解決法」更確實形塑了當代阿拉斯加原住民的身分政治。例如原住民身分突然變為具有經濟價值意涵;著眼追求經濟利益為主的公司,或以復振原住民文化為目標?這意味著原住民公司的內部,有著不同的發展取向。確實,一九八〇至九〇年代,部分原住民公司強調,原住民文化工作並不亞於原住民醫療、教育等議題。因而在此基礎下,對原住民來講遺產工作能夠爭取到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參與資本主義的現代性其實也攸關緊要。
二〇〇一年「望向兩邊」的展覽,承接著文化振興熱絡的年代,由史密森尼博物院與由當地原住民群體主持的阿魯提克博物館合作。展出的文物是由史密森尼博物院出借,由在地原住民決定展覽形式並出借展覽場地。克里弗德認為,這個展覽在一九九〇年代在科迪亞克島拉森灣(Larsen Bay)原住民社群向史密森尼博物院要求返還一九三〇年代被掠去的祖先遺骨和文物之後更顯得意義非凡。展覽開幕活動包含由一個四代同堂的原住民家庭主持剪綵活動,並混合著原住民傳統舞蹈表演、酒會和東正教祝福禮。該展覽展出阿魯提克史前文化、歷史文物,以及當代原住民生活的照片。克里弗德精闢地提出見解:
這個文物、文本和影像的混合體展示出一種複雜的阿魯提克人身分和遺產,它透過把古代、近代和當代文物的並置顯示出貫穿於變遷的文化連續性。展覽要傳達的信息直接分明,洋溢著歡慶情緒。其結果是對「阿魯提克人」身分一個融貫的表演和理想化。
確實,這個展覽清楚地把「阿魯提克」標界(boundary marking)出來(特別這個族群顛沛流離,曾經有過自以為是俄國人的身分認同),展覽一如一九八四年在卡魯克村(Karluk)的那一場考古挖掘一樣,宣示了其與鄰近族群如尤皮克人(Yupiit)、阿留申人(Aleut)的界線,並將這群人重新銜接為阿魯提克。另外,「望向兩邊」的展覽手冊更是「眾聲喧嘩」:列出五十一位參與展覽或籌備會議長老的名字,文章中各長老的話語遍佈了手冊各處,手冊中文字內容的作者多達四十個,讀者可以看見各種不同的聲音、修辭、影像、說法和故事。克里弗德主張,這個展覽是一個文化復興的時刻,將長達超過二十年的討論、奮鬥和通融遷就編織在一起。
克里弗德也提出了阿魯提克博物館另外一個重新銜接的案例—「面具返回」展覽及其過程。阿拉斯加原住民的面具舞原本是傳統生活的核心部分,但是就如同許多原住民在殖民政府及隨之進入的新宗教所面臨的一樣,被看作是不文明、落伍、邪惡、陰暗的而被禁止。面具不是被燒毀就是任其毀壞。八〇至九〇年代,隨著原住民文化的復興運動勃發,各項傳統工藝被學習及被復振。面具的製作也同樣被記憶和被練習。彼時阿魯提克博物館的館長哈坎森也輾轉得知法國城堡博物館藏有一批科迪亞克的面具,在幾次努力協調之下,面具返回仍是遙遙無期。法國的博物館擔心,若將面具借出展覽,這些得之不易又富特殊性的館藏可能將永遠返回阿拉斯加;但哈坎森運用的策略另人印象深刻。
二〇〇〇年哈坎森帶領九位蘇格皮亞克的藝術家造訪該博物館,這些藝術家同意將會雕刻一件「可以跳舞的面具」,並擔任博物館的鄉村教育課程老師,作為給阿魯提克博物館的回饋。克里弗德描述這些藝術家在法國看見自己祖先面具的激動情緒,立即感染了法國在場的行政官員及城市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而成為後續借展成功的因素。二〇〇七年由法國政府和城市博物館同意出借一半的皮納爾面具蒐藏抵達科迪亞克,阿魯提克博物館召集長老見證了開箱儀式,克里弗德形容「隨著古老的面具一一取出,面具彷彿夾帶著更新過的靈力,讓在場的人陷入極大的情緒激動」。而我相信,能夠引起阿魯提克藝術家的高漲情緒,除了過往阿魯提克運用了簡單的工具,卻創作驚人藝術性的面具之外,就是面具連結了阿魯提克藝術家和祖先的情感和精神。
二〇一五年,我所屬的基國派部落婦女開始熱衷地學習傳統織布技術,由部落女性長者教授年輕女性,其中大部分尚能記存編織方法僅存平織,而高級的織布技巧如挑花已經無法記憶。據傳日本天理大學存有一批我部落的傳統服飾,於是我在族人期待下前往日本天理大學參考館參觀,看看「祖先的衣服」樣貌、花紋、顏色。礙於館方規定,我無法前往館藏倉庫,所以先行閱讀了館藏目錄,由研究人員拿出幾件指定的服飾,當我在博物館研究員早坂文吉先生帶領下抵達館藏倉庫地下室,看見自己族群大嵙崁泰雅族的服飾,當早坂先生將泰雅族的男性肚兜和披肩攤開在自己眼前,彷如電流通過那樣,當下我淚流滿面情緒激動,頓時間深刻感應到祖靈正對我說話。
古老面具返回的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復返》探討面具復返之後銜接出嶄新的用途與意義。按照克里弗德的說法是,這些古老面具為阿拉斯加原住民帶來了「第二生命」。他認為這第二生命從幾個脈絡中清楚浮現:靠著圖騰文化清楚劃出有別其他群體原民的身分政治、正在滋生的原住民藝術世界、學校和博物館工作坊的雕刻課程、公共和私人場合被演出的面具舞蹈、在觀光場所被販賣的面具等等。如同我部落族人這幾年來,透過政府部分補助的小計畫學習傳統織布,同時開始學習製作傳統口簧琴,過程和成品都不斷地形塑及標誌出了「我們基國派部落」的身分認同。我們開始在各種文化活動場合中,代表部落「表演」融合織布和口簧琴的泰雅舞蹈。那些精熟製作技巧的族人們,部分成為國中小學「鄉土課程」的老師,傳授織布以及製作口簧琴的技巧。也在基督教的聚會場合裡面,販賣他們捐給教會當義賣品的布匹以及口簧琴,作為修繕教會設備的資金。這些義賣品主要販賣給來部落參加禮拜的人(大部分是漢人基督徒)。一如克里弗德提到阿魯提克∕蘇格皮亞克人一樣,我的部落族人正運用過去的傳統技藝,採取各種姿態以連結於當代世界,並以「基國派部落族人」向眾人顯現。
原住民面對未來,難道只能哀嘆過往已逝的美好,或者切斷傳統,熱切迎接進步的想像嗎?現代化真具有絕對的霸權,能將所有舊事物無情且無分化的吞噬嗎?我們只能哀傷地為族群的命運吟哦輓歌?或者是悲嘆族群的「本真性」逐漸消散?至少克里弗德並不這樣認為。作者否認塔姆斯.魯瓦令加(Tamusi Qumak Nuvalinga)視野裡,時間河流的目的地是一個有去無回、沒有差異的形式;也拒絕原住民面對世界並不像是李維史陀在《憂鬱的熱帶》所提及的「能趨疲」(entropy),世界歷史採取了瀑布形式將差異帶向同一的那樣,克里弗德的觀察和探究超越了非一即二的單調且大部分對立的論點。
《復返》舉出許多有關原住民「現身」的故事,透過這些故事,克里弗德仔細敘說種種環繞在原住民傳統、身分、主權社會文化運動,不斷展示「事情絕非這麼單純」,提醒我們避免落入一昧過早喊讚或過早批判的窘境,而是要為多重、複雜的事物騰出空間。那麼,原住民社會文化如何能夠在現代社會存在延續?拋開現代與傳統對立的情境,細緻思考與觀察原住民在特定社會、經濟和政治角力中,難道不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創造出「揀擇而得的傳統」嗎?「我們」不正是持續向內汲取並繼續往前,並且走在向你們顯現,有關文化銜接、表演、翻譯的路上嗎?「我們一直設法成為世界的一部分。」
「我們」將會消聲匿跡嗎? 作者:Pisuy.Silan
《復返》(Returns)一書是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繼《文化的困境》(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及《路徑》(Routes)三部曲系列的第三本重要著作。此系列作品的後作可視為前著的延伸與討論,《文化的困境》批判人類學知識與研究職權,反對單一且獨白的民族誌書寫,強調以複調的敘事方式再現。《路徑》則是反思過往人類學偏執於固著性與疆界的劃定,認為透過旅行與接觸,作為探討未竟現代性的關鍵所在。本文所要討論的《復返》,從探究邊界孔隙及流動的《路徑》出發,...
作者序
詹姆斯.克里弗德
《復返》是一個著作系列的第三冊,該系列以一九八八年的《文化的困境》(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和一九九七年的《路徑》(Routes)打響第一、二砲。就像先前兩冊,本書各篇章大略寫成於十年之間。每一冊揭櫫的觀念會在另一冊重新省思。所有重要問題都保持敞開。所以,《復返》並不是一個結論,不是一組三部曲的圓成。它是一系列持續反思的一部分,是對時代變遷的一些回應。站在現在回顧,這些變遷該如何理解?是哪些更大的歷史發展(哪些壓力和侷限的變換)形塑了這個思考和寫作的過程?
以有限的後見之明將自身的工作置於這些歷史變遷之中,是件具風險的事情。你原有的見解肯定會被證明是錯的,至少是被證明為落伍過時。重讀《文化的困境》的文字,我強烈感覺到它們的遙遠。它們屬於另一個世界。書中索引不見「全球化」一詞,也沒有「網際網絡」和「後殖民」的條目。尋找一套歷史敘事以理解變遷的過程中,我發現那是一種權力關係與漫談位置(discursive location)的深深轉換。簡言之,這個變遷就是西方的去中心化(decentering)。但必須馬上補充的是,所謂的「去中心化」並不意味原有的權力中心已經消失或旁落。它依然虎虎有力,但一個變遷(不平均和不完整的變遷)已經就道。大地已然移置。
這讓我想起一九七〇年代早期的一番交談。當時我還是博士班研究生,正在倫敦經濟學院研究馬凌諾斯基的手稿。一天下午,我在圖書館外頭與著名人類學家弗斯﹙Raymond Firth﹚不期而遇,聊起人類學的歷史。弗斯以研究蒂蔻皮亞島(Tikopia)知名,既是馬凌諾斯基的學生又是同事。他提到把跨文化研究與殖民勢力相提並論的趨勢,又特別是阿薩德(Talal Asad)所編的重要著作《人類學與殖民遭逢》﹙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他無意小覷這個趨勢,但認為人類學與帝國的關係比一些評論家主張的還要複雜。他搖搖頭,表情半是假困惑半是真困惑。這是怎麼回事?他說。不太久之前我們還是激進分子。我們自視為批判性知識分子、原民文化的擁護者和人民的捍衛者,但現在,一剎那之間,我們卻成了帝國的婢女!
是謂之體會到歷史滄桑。剎那之間,歐美自由派學者明白了殖民主義原來是可能有盡頭的一段時期。試問,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誰又會料得到法國和英國的大多數殖民地將會在十年內形式上獨立?體會到歷史滄桑就像是腳下的小地毯被抽走:那是一種完型(gestalt)的變換,一種立足點的突然改變,或是暴露在一些此前一直隱藏著的凝視之下。對歐美的人類學來說,經驗到自己被界定為一種「西方」科學,被界定為只是部分真理的提供者,固然是一個難接受和難處理的過程,但最終來說也是一個增益的過程。同一種挑戰和學習經驗亦把與我同輩的很多學者推向了性別、種族和性向的研究。顯然的是,過去五十年來,失去中心地方的並不是只有「西方」。
回顧之下,我把我的工作定位在一種政治轉換與文化轉換的後戰(postwar)論述之下。就像弗斯,我也開始體會到歷史滄桑。
我出生於一九四五年,先後在紐約市和弗蒙特州長大。那時的世界和平是一種戰勝國之間的和平,以冷戰對峙和一種由美國領導的持續經濟膨脹為特徵。我對現實的基本感知(即對什麼東西確實存在和可能存在的感知)是在物質繁榮和安全程度都前所未有的環境下形成。我的世代固然反覆經驗到核子滅絕的恐懼,但由於裁軍協議看似指日可待,我們也學會安然生活於「恐怖平衡」之中。在其他方面,世界看來穩定而不斷擴寬—至少對中產階級的美國白人是如此。我們從不匱乏什麼,戰爭總是在別處開打。地緣政治對抗的界線有清楚標示,而且大部分時間都是維持得住。
一九五〇年代的紐約市儼然是世界中心。北美的權力和影響力濃縮在曼哈頓的商業區。只要一趟地鐵就可以把你帶到華爾街、聯合國、現代藝術博物館和前衛的格林威治村。後戰時期的去殖民化運動姍姍來遲,表現為民權運動、反越戰和人們逐漸給予接受的另類文化。我的批判性思考受到激進藝術和多樣化政治(politics of diversity)的滋養,源頭是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跨文化人類學、音樂和大眾文化。新的歷史行動者﹙女性、受排斥的種族及受排斥的社會群體﹚正在發聲,要求得到公平對待和承認。
和同一輩很多人一樣,我認為學術工作不能迴避這些對社會規範(societal norm)和文化權威的挑戰。這些挑戰為知識、政治和文化生活打開一個新的開口。建制化的經典和制度結構於是受到挑戰。這些酵素同時產生出排他性身分政治(exclusivist identity politics)、享樂主義次文化和多元文化主義的多種經營形式。所以說,語言的多樣性有時是會遮蓋住頑強存在的不平等。大多數學術作品﹙包括我本人的著作在內﹚從不質疑為邊緣觀點「創造空間」的自由派特權。我們不應高估「六〇年代」所帶來的改變。很多表面上的成就(如反貧窮倡議、平權法案和女性權利)如今面臨四面楚歌或正在退卻。但一些重要的改變還是發生了—這些改變不平均和不完全,但仍然具有決定性。這裡只舉一個例子:站在現在回顧,一九五〇年代美國大學英語系的調調(強烈歐洲中心和由男性支配)猶如惡夢一場。
三十三歲那一年,我從北大西洋遷居到太平洋邊緣,從一個全球性海洋和世界中心遷居到另一個。最初,我自感是一個流落邊陲(「西岸」)的紐約客。但亞洲的身影、美洲北∕南移動的長遠歷史和文化豐富的「島嶼太平洋」(Island Pacific)𤩐1的影響力,卻一點一點讓人感受到。在一個去中心化和接觸頻盈的動態世界,「西方」的觀念﹙即把西方視為某種歷史大本營﹚不再站得住腳。
住在加州北部,一件事情很快變得明白︰我開始感受到的「去中心化」並不只是戰後去殖民化和「全球性六〇年代」眾聲喧譁的結果。這兩種力量固然帶來了改變,且至今仍在作用中,但「去中心化」還是一些新形式資本主義(充滿彈性和流動性的資本主義)的產物。自此,我對一個尚未完成的歷史雙重取向(由兩股既緊張又合作的後戰力量構成)深感興趣:去殖民化和全球化。
加州的聖塔克魯茲(Santa Cruz)—從一九七八年起便是我的家—縮影著這種雙重性。除了是一座大學城和六〇年代反文化願景家的一片飛地(enclave),聖塔克魯茲還是矽谷高科技新世界的臥室之一。這裡是大量資本流入、四小龍和勞工移民的「環太平洋」。我同時也是住在一個「前沿帶」(frontera)—一個把拉丁美洲連結於美國與加拿大的接壤區,它不受控制又不斷擴大。聖塔克魯茲縣的北半部座落著強烈認同於多元文化主義、女性主義、環保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一所大學和一個市政府。而在這個縣的南部,則是人口不斷增加的墨西哥∕拉美裔工人和勢力不斷坐大的農業綜合企業。我開始覺得,當前的歷史運動是一個矛盾和無可避免充滿曖昧的交接口(conjuncture),同時體現著後殖民和新殖民的色彩。
開車前往舊金山途經沿海的山嶺時,我有時會想起詩人奧森﹙Charles Olson﹚的詩句:「我們的大洲跑完於此。」我們?事實上,加州給人的印象愈來愈不像美國的「西岸」,更像是一個多元歷史的交叉口。《路徑》裡的文章反映著這種對位置(location)和流動性的複雜意識。全書的最後一篇文章〈羅斯堡沈思〉(Fort Ross Meditation)把我往北帶到阿拉斯加—一個不同的「前沿帶」。羅斯堡(今日重建於緊靠舊金山海岸邊)在十九世紀早期原是俄國毛皮貿易帝國的前哨站,住著許多不同族群,人數最多的是討海的阿拉斯加原住民(今日自稱為阿魯提克人 [Alutiiq] 或蘇格皮亞克人 [Sugpiaq]),他們在俄國人的強制下從事狩獵海獺的工作。在後續的研究中﹙見本書「第三部分」﹚,我追隨這些流動性原住民的步伐去到科迪亞克島﹙Kodiak Island﹚—在那裡,他們的後人正在更新已遭破壞的傳統文化。這個接觸地帶(contact zone)同時濃化了我對加州原住民的興趣,特別是對伊許(Ishi)的興趣。伊許是加州最知名的印地安人,但有關他的故事歷經了很大變化。這位「最後的野生印地安人」目前正以一世紀前無法想像的脈絡捲土重來。伊許故事的許多版本可在本書的「第二部分」找到—此單元是一個對「恐怖」與「療癒」的沈思,一個對「歸鄉」(repatriation)與「復興」(renewal)的沈思。
在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任教也打開了我接觸南亞和「島嶼太平洋」(Island Pacific)之門,因為該校的跨學科課程「意識史」有許多來自這兩地的研究生選讀。這些學術旅人把自己界定為「後殖民時代人」和∕或「原住民」。他們有些學成後會留在美國教書,有些會回返故鄉。這些年輕學者身在歐美的觀念與制度世界之內工作,眼界卻沒有停留於此,這讓我更強烈感受到自己是身處什麼東西的邊緣或末端。我意識到自己正在他們建構的歷史裡扮演一角。
《復返》裡面的文章就像它的前驅一樣,是根植於一九八〇和九〇年代。隨著「六〇年代」的式微和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站穩腳跟,革命的願景被「闖入」(transgression)和「批判」的文化與思想戰略所取代。及至一九八〇年代,正面去對抗一種流動性霸權看似已經不起作用。我們改而採取了葛蘭西式的「陣地戰」,即一系列小型的抵抗與顛覆。不可能被打敗的東西也許可以被動搖、闖入或打開。對許多在歐美權力中心工作的知識分子而言,這意味著在認識論和社會文化音域兩方面支持「多樣性」。我們相信,支配性權威和常識是可能被批判和從理論上被拆解。我在《文化的困境》裡許多文章(以它們對一言堂權威的否定,以它們致力於多樣化和實驗)可以由此獲得理解。《路徑》是同一種批判氛圍的產物,那怕它對新興形式(兼含「離散」形式和「原住」形式)的接受暗示著更多其他東西。《復返》雖仍帶有一九九〇年代的烙印,但卻開始記錄一種新的歷史氛圍。
西元二千年之後的發展不若「後六〇年代」那幾十年容易歸納。但有幾件事情看來是可以成立的:美國不再是無可爭辯的世界領袖。它在九一一之後表現的軍事實力被證明是不能持之以久的,只是一種對長期性和不可逆變遷的痙攣性反應。它無疑還會有進一步的冒險,但美國的全球霸權已不再是一個有可信度的方案。美國得面對新經濟強權的競爭,得面對伊斯蘭教(它還只是非西方全球性意識形態最顯眼的一支)的競爭,還得面對亞洲的威權式資本主義模式的競爭。系統性危機和過渡(transition)的徵兆無處不見:見於金融的不穩定和市場的不受控制,見於不平等和匱乏的升高,見於生態受到侷限和資源競爭的加深,也見於許多民族國家的內部分裂和財政危機。許多危機都看不見解決之道,許多過渡都看不見方向。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一九八〇年代說過一句名言:「TINA:沒有別的選項。」站在今日看,這種話是不通的。如今,每個人都知道有別的選項存在(這情形是好是壞是另一回事)。
從新世紀(new millennium)的高枝回望,我明白到過去半世紀的變化是兩股相扣歷史能量的互動結果:一是去殖民化,一是全球化。兩個過程都不是線性,也不保證會貫徹到底。兩者都無法包納對方。兩者都包含著矛盾和未定結局。另外,兩者都是致力於去掉西方的中心地位—借恰克拉巴帝﹙Dipesh Chakrabarty﹚的話說便是「將歐洲予以外部化」﹙provincialize Europe﹚。這是個未完成但卻不可逆的方案。
「全球化」並不是﹙或不單純是﹚「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它當然是資本主義性質,但又多於此。「全球化」就我們所知是一個關於開展中多連結的世界,但卻無法充分表述之。它是一個「過繁複」(excess)的表徵。這當然不是一九九〇年代的版本:「歷史的終結」,「地球是平的」。它也不是我們熟悉的敵人:不是博韋(Jose Bové)對抗麥當勞3,不是「西雅圖戰爭」
全球化是一個多方向和不可表象的物質和文化關係總和,它把距離遠近的人和地點全連結在一起。它也不只是(如一些左翼評論家常常指稱的)帝國的延續,是想用別的(更彈性的)方法以遂繼續宰制的目的。沒有「發自下層的帝國主義」這回事,但卻有「發自下層」或「發自邊緣」的全球化。「全球化」是一項「指稱物」(placeholder),是一個「切入點」(in medias res)。《復返》是要嘗試描述這個銜接性的多中心總體。它是一種多元的時代精神(Zeitgeists),一團糾結的歷史(histories)。
類似地,「去殖民化」也是一個未完成和過複雜的歷史過程。不像一九五〇和六〇年代的民族解放(這些解放先是取得成功後又被原殖民者收編),去殖民性指的是一種反覆出現的能動性(agency),一種被堵塞、引偏和持續再創造的歷史力量。它曾一度被捆紮於「第三世界」或「民族解放」這些詞語裡,但其能量仍然與我們同在。它們以出人意表的形式重新出現在出人意表的地方:體現在「原民性」(indigeneity)(所有一度被認為注定消失的人),體現在「阿拉伯之春」(不管最後結果為何),甚至體現在舉世公敵—「恐怖分子」。
歷史突然變得可被想像為「結局未定」當然讓人興奮。至少對我們其中一些人來說,看到我們一直抵抗的支配系統失靈讓我們備受鼓舞。新自由主義之無力包納替代方案和把所有人一網打盡讓我們更容易想像新的身分、社會鬥爭和歡宴形式(forms of conviviality)。但這種歷史可能性帶來的興奮感又離不開(至少對我本人來說是這樣)另一種二十五年前沒有經驗到感覺:害怕,因意識到一個既有世界可能會突然消失而害怕。體驗到滄桑:大地移位了。
我們孫子輩的未來一下子變成了一個迫切問題。這種不安全感無疑是與政治經濟衰頹的循環過程有關,但它也受到了一個不再能駕馭或輸出的長期生態威脅所加強。那是一種不同規模的歷史性,關乎的是整個人類物種,是一整個地球的過去和未來,以及它維持永續生命的能力。當人口增長到達極限,當物質供給耗竭,當資源戰爭變得迫在眉睫,會有什麼樣的事情發生?這些不穩定性極其深遠,足以改變世界。當然,暴露在危險之中的感受是大部分世人早有深刻體會。
當初生活在一個泡泡中的確定性,即「第一世界」的安全感已不復存在。向這一切說再見吧。但接下來呢?
《復返》只跟進其中一個新興趨勢:在一九八〇和九〇年代變得廣泛可見的原住民復興現象。長久以來,部落社會或原住民社會都被認為注定會在西方文化和經濟發展的暴力進逼下消失。大部分有見識的人都一度認定,這個歷史任務將會由「種族屠殺」和「涵化」(acculturation)完成。但到了二十世紀之末,事情的發展卻顯然是另一個樣子。很多原住民確實被殺死,很多語言確實消失,很多社會確實瓦解。然而,仍然有為數不少的原住民挺住壓力,把橫遭破壞的生活方式的殘餘給改編和重組起來。他們往根深而有適應力的傳統取材,在一種錯綜複雜的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中闢出新的途徑。文化同一是一個變化(becoming)的過程。
我在《復返》裡探索了這個變化過程,觀察它是如何用實用主義方式與全球化勢力、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和特定的國家霸權周旋。我又重探了文化整全性和歷史連續性的問題—它們在《文化的困境》末章「馬什皮(Mashpee)的身分認同」曾被提起。事隔二十五年後的今日,這些問題所暗示的原民持續與復振(revival)過程不再只是鬆開西方範疇的契機。在現今這個充滿系統性危機和不確定過渡的時代,我把它們看成真正的替代性出路。
我在《復返》中持一種民族誌和歷史學現實主義立場,主張歷史和真實(the real)的各種觀念當前正在角力,並在權力高張的場域(從進行土地權訴訟的法院到博物館和大學)受到有創意的翻譯。所有這些事件的結合都是偶發性(contingent)和由意見不盡一致的諸造構成。所以,一種充分的現實主義必須並置(即既連結又保持分開)相因而生的部分故事。我處理了三種活躍於過去半世紀的敘事:去殖民化、全球化和原民生成(indigenous becoming)。它們代表不同的歷史能量、行動規模和可能性政治(politics of the possible)。它們不能被化約到一個單一的決定性結構或歷史。它們也不能被彼此分開太久。這三段歷史建構彼此、加強彼此又困擾彼此。有必要把這一類「大小恰好」(big-enough)的歷史維持在辯證張力中,讓它們在同時(simultaneous)但非同步(synchronous)的存在。因此,《復返》提供的是一種凹凸不平的逼真(verisimilitude),政治力量、經濟力量、社會力量和文化力量在其中彼此貫穿,但沒有構成一個整體。如果說本書無法以簡馭繁,那這個失敗乃是有意為之,是決心要貫徹現實主義立場的結果。
《復返》由三個關係不緊湊的單元構成。
「第一部分」屬於通論和理論性質。它探索今日用於理解原住民的不同方法,主張歷史命定(historical destiny)和發展時間(developing time)的觀念必須修正,因為非如此將解釋不了種種原民文化復興和社會運動。它介紹了分析歷史轉化和政治能動性(political agency)的工具:銜接(articulation)、表演與翻譯。它把源自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霍爾(Stuart Hall)和吉爾羅伊(Paul Gilroy)的文化唯物主義理論、霸權理論和離散理論連接於源自文化人類學的民族誌-歷史學方法。「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始於想像一個移置的、「後西方」的觀點,以之作為一個翻譯地點(place of translations)去理解原民能動性(indigenous agency)。後續的討論用具體的當代脈絡來發展這些觀念。
「第二部分」追溯了一則先是標誌原住民消失後又變成標誌原民復興的故事。一九一一年,伊許出現在加州一個屯墾者城鎮,從此變得廣為人知,被視為「美國最後一個野生印地安人」。一九六〇後,因著克魯伯夫人(Theodora Kroeber)為他寫的傳記成了暢銷書,伊許再次廣為人知。二〇〇〇年前後,伊許再次登上報端,因為加州印地安人最終決定把他的遺骸遷葬,並在這過程中重新掀開一段屯墾者∕殖民者的暴力史。我滿懷興趣地跟進了這趟「歸鄉」過程,參加了公開聚會,又與與會者多所攀談。一度是加州原住民消失的象徵,伊許至此變成了他們存續下來的象徵。他的經驗謎樣而豐饒,而他的生與死都在很多不同方面對很多不同的人充滿意義。伊許的故事傳達了殖民暴力的持續遺產、人類學的歷史、後殖民何解的前景等議題。
「第三部分」在對「島嶼太平洋」進行過比較性一瞥後,把焦點放在阿拉斯加中部,又特別是放在科迪亞克群島。我對阿魯提克人(又稱蘇格皮亞克人)文化復興的討論是奠基於過去十年的研究(這種研究可稱之為「學術性探訪」或「帶有理論特徵的記者採訪」)。其成果是兩篇互相環扣的文章。第一篇討論協作式的文化遺產工作,特別是一次大型展覽和一本多人合寫的書籍《同時望向兩邊》(Looking Both Ways, 2001)。第二篇文章集中在阿魯提克博物館—科迪亞克群島上一家由原主民自主管理的文化中心。文章描述了十九世紀面具的復返(從它們現今位於法國的家借回來),以及這些祖先文物在一個變遷中世界能喚起的新意義。這些面具翻譯過來的「第二生命」開展在地方歷史的糾結脈絡、跨國原民性,以及跨國公司式多元文化主義(corporate multiculturalism)的國家政策中。
若說「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構思是以現實主義為主導原則,那「第二部分」就是以一種不同的分析與想像風格展開。它追溯了屯墾者∕殖民者史觀的坍塌經過,但沒企圖用一套更充分的新敘事取而代之。代之以,它採取一種反諷、「後設」(meta)觀點,為複數、矛盾和烏托邦的結果留下空間。環繞「伊許」這名字所產生的故事不斷滋生,打開了眾多新的可能性。其他種類的進步(progress)因此變得可想像:烏托邦也許本已存在,所以,重點不是前進而是轉向和回歸。挑戰是去想像歷史中的不同方向和運動,想像彼此並行又分離的發展。為此,《復返》把語言給用罄。
本書的結構需要一些解釋。就像同一系列的前兩冊,《復返》是一部文章的拼貼(collage),每篇文章寫成於不同時候,用的是不同的風格或聲音。我並沒有去熨平篇章間的高低落差。修辭上的多樣性讓形塑本書的脈絡和聽眾保持能見。它要展現的是過程而非最終成品。熟悉的文類(專著和論文集等)目前正處於匯流局面。自《文化的困境》在二十五年前出版之後,人們的閱讀習慣已經發生改變。現在更少人會一氣呵成,把一本書從頭讀到尾。他們會複製、掃描和下載書本的某些部分。《文化的困境》和《路徑》在以「書本」的形式存在一段時間之後,都是以影印本和 PDF 檔案的方式獲得了第二生命。這一類「出版品」有些理會版權法,有些不理會。以這種方式傳輸知識不是法律所能(或所應該)遏阻。明顯不過的是,以實體書形式存在的學術著作並不會流通太廣。經過拆解和模件化之後,文本反而可以去到更多人手裡。
《復返》的編排是考慮到這些新的流通方式。雖然它的全體要大於部分的總和,但三大單元卻是可拆開的。每個單元都自成一篇長篇文章,可以單獨閱讀,且先讀哪個單元皆無不可。在沒有更好名稱存在的情況下,我權稱它們為學術「中篇故事」(novellas)—一種可維持複雜性和發展性又不犧牲可讀性的中間書寫形式。我猜想,把三個單元拆為三本小書出版,供人在不同時間和不同心緒閱讀,大概會提供更大閱讀樂趣。另外,三大單元的每一章一樣是可獨立看待的文章。
如此編排的一部書必然包含不少重覆冗贅。一些重要的脈絡需要一提再提,基本觀念亦復如是。《復返》並不是以直線方式展開:它的「論證」呈圈形運動,周而復始。不過,我已經設法把一些明白多餘的重覆減到最低,又給每章引入一個新的脈絡以探索本書的中心關懷。應該指出的是,書中有些用語並不一貫。例如在阿拉斯加的脈絡,我按照當地的習俗把 Native 和 Elder 的第一個字母大寫,但在其他脈絡卻沒這麼做。
最後要一提的是稱謂的問題。許多原住民社會都把殖民時代的稱謂廢除,恢復舊稱謂(有時是另創新稱謂)。這是去殖民過程的基本一環。因此,我們看到瓜求圖族(Kwakiutl)被夸夸嘉夸族(Kwakwak’awakw)取代,帕帕戈族(Papago)被圖霍諾奧哈姆族(Tohono O’odham)取代,愛斯基摩人被因紐特人(Inuit)取代,紐西蘭被奧特亞羅瓦(Aotearoa)取代。本書尊重這些更易,予以採用。不過,在有需要的地方,我也會把殖民時代與後殖民時代的稱謂並陳。這樣做也許是因為新稱謂並未穩定,也許是為了在歷史脈絡避免時代錯亂,或是考慮到有些讀者對新稱謂毫無所知。
我的核心關懷對象缺乏一個可讓所有人滿意的稱呼,光是英語裡便有以下各種用字:「原住民」(indigenous)、「土著」(native)、「原初住民」(aboriginal)、「部落住民」(tribal)、「印地安人」、「美洲原住民」,「第一民族」(Frist Nation)等不同用字。我會採取哪個字眼,是視乎我的所在場合和聽眾性質而定,但這當然有可能會得罪某些人,或顯得張冠李戴。
詹姆斯.克里弗德
《復返》是一個著作系列的第三冊,該系列以一九八八年的《文化的困境》(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和一九九七年的《路徑》(Routes)打響第一、二砲。就像先前兩冊,本書各篇章大略寫成於十年之間。每一冊揭櫫的觀念會在另一冊重新省思。所有重要問題都保持敞開。所以,《復返》並不是一個結論,不是一組三部曲的圓成。它是一系列持續反思的一部分,是對時代變遷的一些回應。站在現在回顧,這些變遷該如何理解?是哪些更大的歷史發展(哪些壓力和侷限的變換)形塑了這個思考和寫作的過程?
以有限的後見之明將...
目錄
出版序
導論
原序
第一部分
第一章 諸歷史之間
「自豪原住民」
另類史觀(一)
解銜接後現代性
另類史觀(二)
民族誌現實主義
另類史觀(三)
銜接、表演與翻譯
第二章 原民銜接
第三章 形形色色的原民經驗
第二部分
第四章 伊許的故事
恐怖與療癒
被帶回家的伊許
伊許的各種變奏
烏托邦
第三部分
第五章 郝歐法的盼望
第六章 望向多邊
身分的政治經濟學
同時望向兩邊
前驅
互動:阿拉斯加原住民遺產中心
浮現與銜接
遺產關係:變遷中的氣候
協作視域
第七章 第二生命:面具的復返
復返之路
第二生命(準理論的間奏)
面具返回
三本展覽目錄
在翻譯中迷失與尋獲
「召喚」和∕或「銜接」(理論的間奏)
糾葛的主動性
連結
跋
參考書目
各章來源
致謝
索引
人名對照表
出版序
導論
原序
第一部分
第一章 諸歷史之間
「自豪原住民」
另類史觀(一)
解銜接後現代性
另類史觀(二)
民族誌現實主義
另類史觀(三)
銜接、表演與翻譯
第二章 原民銜接
第三章 形形色色的原民經驗
第二部分
第四章 伊許的故事
恐怖與療癒
被帶回家的伊許
伊許的各種變奏
烏托邦
第三部分
第五章 郝歐法的盼望
第六章 望向多邊
身分的政治經濟學
同時望向兩邊
前驅
互動:阿拉斯加原住民遺產中心
浮現與銜接
遺產關係:變遷中的氣候
協作視域
第七章 第二生命:面具的...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6收藏
6收藏

 110二手徵求有驚喜
110二手徵求有驚喜




 6收藏
6收藏

 110二手徵求有驚喜
110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