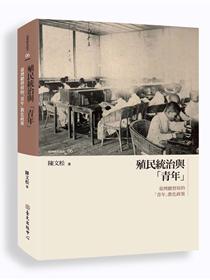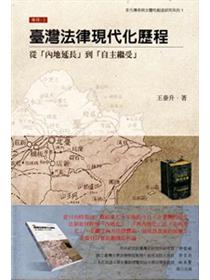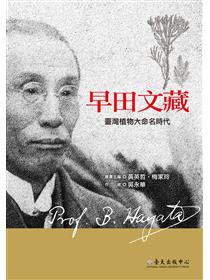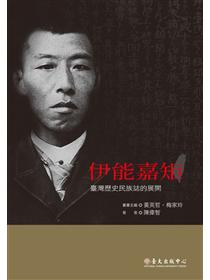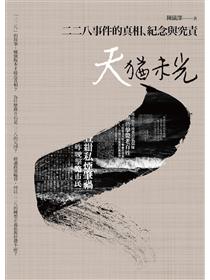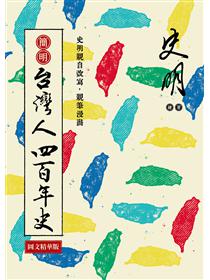作為統治核心的專業法律人,對殖民地台灣留下了什麼刻痕?
本書是一本正統的法思想史學術著作,運用嚴謹、專業的比較思想史的方法,加入法社會學的觀點,追溯日本在臺殖民法律人──法學者、法官、檢察官與律師──思想的根源、特質,歸納其類型,並且深入地評價其影響。
在〈導論〉之後,第一章分析及評價殖民統治初期,日本法學者岡松參太郎如何嘗試將台灣的慣習法體系,改造成近代德國法體系的事蹟及其法思想。第二章則以私法學的角度,檢討台灣的慣習法中與台灣人自我認同關係最深的「祭祀公業」制度的法律性質,以及祭祀公業之沒落,如何改變了台灣人民族認同的形式與内涵。
第三章以台灣進入現代法體系之後首次發生的政治裁判──治警事件的裁判過程為背景,探討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如何運用法庭抗爭與殖民者進行對抗的戰術及其極限。第四章則透過顯密二教兩種類型的法學家的介紹與比較,說明「凡庸之善」姉歯松平與「凡庸之惡」増田福太郎,在知識與意識形態成反比例消長的歷史情境下如何自處,從而改變了殖民地台灣對於現代法的信念。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吳叡人——專文導讀
王泰升(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臺大講座教授)
吳密察(國史館館長)
李茂生(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若林正丈(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
許玉秀(前大法官)
黃文雄(台灣人權促進會前會長)
黃丞儀(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聯合推薦(依姓氏筆劃排列)
這本書告訴我:看起來掙脱於被殖民之外,卻又受困於被殖民之中;看起來致力於追求價值之中,卻同時置身於價值之外;看起來努力邁向現代化,卻更像處處背離現代化。是前進,是後退?衝突與矛盾的化解之道?一反省!——前大法官許玉秀
關心人權(human rights)的人都不能不同時關心「人枉」(human wrongs),不論後者——來自節制不足的國家權力、規約不足的市場經濟、還是帝國與殖民,法律都是一個重要的介面和機制。本書從透視現代性的視野,俯瞰日本把從德國繼受的法學和法制應用到殖民地台灣的「辯證」過程。因為所用的不是「通史」而是比較少見的多觀點、跨觀點的「問題史」取徑,讓非法律人的讀者如我,反而在增加了對法律史的瞭解之外,不但對這段台灣史的掌握在其他面相上得到不少啟發,也對作者已立下「書」狀將處理戰後時期的下一冊,充滿期待。——台灣人權促進會前會長 黃文雄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至少有三個世代的日本法律人投入殖民地的經營。過去對於日治時期的法律史研究較為側重法律規範與司法裁判,偶見以台灣法律人為對象的研究。本書當屬第一本全面針對日本法學家、法曹和律師在台灣的嘗試與業績,進行長時段、跨地域的比較與批判。從初期的舊慣調查事業、中期受到大正民主影響的內地延長和政治審判,到末期極富法西斯風格的皇道法學思想,本書縱橫捭闔,汪洋閎肆,深入探究殖民者的內在理路,見人所未見。作者對於殖民地法學者的批判,不僅再次凸顯了日本近代國家的曖昧困境,也展現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共同經歷的探險,更反身指涉國族建構與階級宰制在當代台灣的臨水照鏡。本書不只是台灣法律史所結出的奇花異卉,更是關心台灣法律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人,不得不讀之書。——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黃丞儀
作者簡介:
吳豪人
1964年生於台北。日本國立京都大學法學博士,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研究領域為基礎法學與人權思想。除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外,編有《大正十三年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豫審記錄》(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出版)。
最常說的一句話是:「我不懂實體法。」天生自由人,遭際冷硬派。非自願型人權工作者。滴酒不沾,痛恨西裝,不會打領帶,會打撐人結。不喜奔競,避官如避禍。曾口占二句以明志:「我是佛門鴦堀子,不學人間富貴禪。」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岡松參太郎的法學烏托邦(摘錄)
岡松參太郎(1871-1922),是日本明治維新/法學近代化之後的第三代民法學家,而且是最傑出的一位。他不但擺脫第一代第二代法學前輩(如穂積陳重等)只能被動繼受歐陸法學的困境,開始思索如何建立合於國情卻不抱殘守缺的日本民法學,而且在方法論上已經突破法律釋義學的侷限,自覺地或不自覺地進入了法律史學及法律社會學的層次,對於其後的第四代及第五代日本民法學家(末弘嚴太郎、我妻榮等人)影響至深。
岡松參太郎同時也是最難理解的近代日本法學家。但這不是因為他的學術成就難以理解,而是因為他參與了─同時也深深影響了日本對於台灣(以及日後的滿洲國)所進行的殖民統治。這個殖民法學家的身分,讓他在戰後背負了一種污名,除了少數的學者之外,岡松的所有研究成果與事蹟均被刻意遺忘,乃至於幾乎無人(意欲)知曉。對於台灣的研究者而言,岡松同樣也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儘管台灣法制近代化的最初三十年,其走向幾乎完全被籠罩在岡松的思想中而成形。我們大致知道:他是後藤新平最重要的智囊,決定了「舊慣立法/漸進統治台灣」的路線。他在台灣進行了大規模的法社會學/法人類學的實證調查與研究,出版了卷帙浩大的成果報告書:《臺灣私法》(臺灣舊慣調查報告書)、《清國行政法》、《臺灣番族慣習調查報告》,而且還翻譯成英文,回饋歐陸學界。他致力將台灣的舊慣——一種被視為「前近代」的法律,改編入西歐的市民法體系。甚且日後因為後藤擔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總裁,岡松將在台灣的經驗帶到滿洲如法炮製。但他英年早逝,因此在滿洲的調查成果遠不如台灣。另外,他之所以在台灣進行大規模的舊慣調查,目的並不純粹在滿足後藤新平或殖民者的殖民需求,他還有一個祕密的目的:藉由創制實際可行且非生吞活剝盲目繼受的《臺灣民法》,以回頭修改(生吞活剝盲目繼受的)日本民法典。
大致上,我們對於岡松參太郎這麼重要的法學家的了解,就只是這麼片段。除了戰後初期福島正夫的幾篇回顧性論文、1980年代春山明哲和1990年代後期吳豪人的研究,以及2009年西英昭的專書《『臺灣私法』の成立過程》之外,基本上關於岡松的研究非常稀少。近年來最重要的當然就是,早稻田大學研究班底致力於整理岡松文書並加以出版的成果。但是真正使用這些文書資料而發表的學術論文也非常有限。即使早大的研究成果報告書裡的幾篇論文(淺古弘、岡本真希子、岡松曉子,2003年),甚至西洋法制史的大家石部雅亮的論文(2002年),也止於提出一個大致的研究可能方向而已。唯一的例外是千葉商科大學的藤野奈津子教授的論文〈岡松參太郎與羅馬法研究〉,才真正檢視了岡松文書中岡松構思計畫撰寫而未果的西洋法律史手稿,並且從他的學術訓練(例如拉丁語能力)推斷岡松的撰寫計畫與可能內容。同時,北海道大學法學部的田口正樹教授,也正在調查岡松於赴歐留學期間的軌跡,雖然尚未有論文問世。總而言之,在有限的研究社群裡,大家都在汪洋閎肆而又晦澀難解的資料大海裡,從不同的方向摸索著前進。
不過,筆者要特別提醒的一點是:日本學者對於岡松的關心大致上分成兩種。第一種是「平反岡松」,強調他在民法學以及帝國的學知上的傑出表現以及所受到的不當漠視,以彌補日本近代法律史的缺口。第二種是藉由岡松豐富的學術背景(特別是歐陸背景),試圖在日本法律史與西洋法律史之間建立跨學際的研究。但是這兩種研究取向,都不是以台灣觀點為出發點。換句話說,這都只是日本本國史,或者是日本/世界史。更直接的說法,就是殖民者的子孫如何評價他們的前人。但是岡松所有研究與政治實踐的起點與終點都在台灣而非日本。如果在一百年之後台灣仍是研究客體而非研究主體,則殖民仍未結束。因此,由被殖民者的後裔觀點出發的岡松研究,便更具有在地/跨國/全球化的三重準確度。唯一的問題是我們做得到做不到,想不想做,以及國家的學術資源是否願意花費在這個看似冷門的研究上面而已(筆者的個人經驗是:國家不願意)。
國內目前關於跨地域法律史(包含思想史與社會史)之研究者及研究論文數量尚屬有限,對於曾深刻影響台灣法制走向的歐洲法學以及繼受中介者的日本殖民地法律家,三者之間的思想連鎖關係也尚未完全釐清。同時,關心同時代的比較殖民法律史的研究者也很少見。本章內容正是藉由以岡松的法學思想系譜研究為起點,重新檢視岡松參太郎所處時代的殖民法制的世界史,提出來自曾為研究客體的台灣的主體性答案。因此,本章將從十九世紀德國人種法學(乃至於比較法學)與德國殖民法學的系譜,追溯岡松所受到的影響;尋索岡松的法學師承(包括日本本國與歐陸諸國),試圖釐清他的法學思想;同時也試圖將岡松與同一時代的荷蘭殖民地法學家C. van Vollenhoven作一對比,以凸顯岡松對於現代性的認識程度,以及因此產生的,對於台灣(印尼)殖民法制走向的影響。但是,這是一場迷宮似的思想漫遊,大概也是本書最不容易理解的一章。此岸過了,自入佳境。
第一節 德國人種法學之系譜
一、歷史法學派
十九世紀德語圈的知識狀況,大約可以用「歷史主義」一詞以蔽之。有關法學的領域裡,薩維尼(C. F. von Savigny, 1779-1861)所率領的歷史法學派,亦揭示「法之歷史性」的綱領,風靡一時。
在1815年創刊的《歷史法學雜誌》創刊號中,薩維尼指出「法律是民族的共通確信」,並說明「法的歷史性」指的是「所謂法的素材,係來自於國民的全歷史。法律,產生自國民本身最內奧的本質及其歷史。」就像歷史絕對沒有停滯的一瞬一樣,所謂「全歷史」,也沒有所謂絕對的停止的瞬間。換言之,薩維尼將法律的進化與民族歷史的進化視為同義語。在這篇綱領論文被提出來的時候,正好是普魯士和奧地利對抗拿破崙,在戰爭中取得勝利,德語圈民族意識最高昂的時期。因此,歷史法學立刻席捲了整個德國法學界。然而,薩維尼雖然提倡「法的歷史性」,但真正關心的對象並不是日耳曼古代部族各種傳統法律的探求,而是「羅馬法的現代適用」(usus modernus Pandectarum)。另一方面,他的大弟子格林(Jacob Grimm, 1785-1863)卻忠實地遵守綱領論文,頑固地拒絕進行羅馬法的研究。尤有甚者,薩維尼因為擔心所謂絕對王權以「立法者的恣意」來進行立法,因而力陳所謂「法的二重生活」之重要性。他指出:在「民族的幼年期」,「民族」(Volks 民眾)的確是法律的承擔者;但是,隨著法律高度的進展,進入到「民族的成年期」之後,承擔法律活動的人,不再是「無教養的民眾」,而是所謂的「學識法曹」(gelehrte Juristen)。也就是說,薩維尼將法和民族生活的關係視為是「政治的要素」,而把法律學問性的生活視為是「技術性的要素」,將兩者做嚴格區分。而其結論就是「學識法曹,作為民族精神的代表人,不得不獨占所有的法技術」。格林則對此種迂迴曲折的理論完全不表關心,而是一心一意地研究「自古傳承的,神聖的」日耳曼民眾法、慣習、詩歌、寓言等等。最後格林終於開創一個嶄新的學問,亦即歷史學、法學、言語學(詩歌)等「三位一體」的學問。格林的研究命題是:歷史學、法學的主題,並非個人(例如政治家、軍人、君主、王朝、冒險家等等有名人士)的豐功偉業,而是共同體的生活方式。很明顯地,格林的命題當然受到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很深的影響,甚至還可追溯到維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 1668-1774)的理論。因此,格林和專注於羅馬法現代適用的薩維尼,愈發地道不同不相為謀。甚至,他雖然身為一個法學者,卻對以服務王權為目的的國家制訂法不屑一顧。其心態,亦非難以解釋,日後他捲入哥丁根七君子事件,被專制王權整肅,毋乃必然。
薩維尼和格林之間學術風格的對立,在不久後發展成政治性的對立,歷史法學派遂因而分裂。這是目前西洋法律史學者間的通說。薩維尼的追隨者被稱之為羅馬主義者,而格林的追隨者則被稱之為日耳曼主義者。兩者的對立,一直到二十世紀的前半仍未解消。羅馬主義者可稱之為概念法學之祖,到了十九世紀以後,在德國的法學界居於主流位置;相反地,日耳曼主義者則開創如古代法、法社會學、法人類學、比較法學等嶄新的學問。雖然始終被視為異端,但仍舊不斷地推陳出新。
當然,這兩派雖然有競爭的關係,但日耳曼主義者並非頑固地拒絕學習實用法學。在下一個世代的法學者裡,同被視為異端的艾利希(Eugen Ehrlich, 1862-1922),就冷靜地指出:「沒有任何的理論是不能成為技術的出發點的。即使是法律學
也不例外。」德國法學者柯恩(Bernd-Rüdiger Kern)如此說明:「法史學和法釋義學,兩者間並非毫無媒介地平行並存。法史學的存在,只不過是為了能顯豁對現行法的認識,以及使現行法之法釋義學更加洗鍊。」日耳曼主義者與羅馬主義者兩者的立場,即使有可能二者擇一,但是對於這些開創嶄新法學領域的大家而言,實用法學的成果在現實上畢竟仍是非常重要的。後面將要提到的巴浩芬(J. J. Bachaofen, 1815-1887)、坡斯特(A. H. Post, 1839-1895)或柯勒(Josef Kohler, 1849-1919)等等法學巨匠,率皆精通實用法學,之後才又開創嶄新的學問領域。因此,我們所能見到的,格林「法古事學」對於始源性的憧憬,可說沒有直接的繼承人。然而,如果不侷限於「日耳曼」,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古代社會」法先驅之大著《母權論》(Das Mutterrecht, 1861)的作者巴浩芬,以及開創研究原始法(亦即「未開」民族之法律諸慣行)和人種法學的坡斯特。此二人毫無疑問地繼承了格林的─或至少是歷史法學綱領論文的法乳。甚至,將比較法學確立成為嶄新學術領域的柯勒也在同樣的影響之下。柯勒後來為岡松參太郎所私淑,因此,德國的人種法學的法乳,就這麼飄洋過海,來到日本,甚至來到了台灣。
二、達爾文主義
歷史法學雖然賦予德國人種法學根源性的影響,但並非是唯一的影響。格林「三位一體」的手法,已經宣示了一個嶄新的、學際整合時代的來臨。當時盛行於西歐的自然、社會科學等新興學說,皆被人種法學納入其方法論範疇中,此即為人種法學的特徵。而若是沒有法史學、法哲學、語言學、人種學、民族學、社會學,以及更重要的、統括這些新興學問的達爾文主義,甚至是史賓賽(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社會進化論,我們可以說,人種法學是無法被樹立的。達爾文主義,對於十九世紀後期西歐知識社會的影響,可說是無遠弗屆。但是,此一影響,並非只是單線進行的。西村稔曾經如此指出:「一般而言,1890年代以前,達爾文主義對社會的適用,主要是以《發展說》為媒介,以理性主義、自然科學之啟蒙為目的。此即所謂的前期達爾文主義。到了1890年代以後,達爾文主義之《淘汰說》則變成是為了正當化特定的政治、社會意識形態而存在、而被利用。如同阿蒙(Otto Ammon)的人種人類學(Rassenanthropologie)或是普勒茲(Alfred Ploetz)的人種衛生學(Rassenhygiene)等等,均屬於後期達爾文主義的產物。」
此外,根據茲瑪爾茲力克(Hans- Günter Zmarzlik)的說法,則達爾文主義影響層面所以如此複雜,是因為引用者各執一詞,並堅決相信自己掌握了其真髓:「有時我們會看到,一些倫理的擁護者宣稱其主張乃依據達爾文主義;另一方面,野蠻的統治者或道德家,也同樣基於達爾文主義而宣揚其理念。自由主義的進步思想應用達爾文主義,而粗野的歷史宿命論也同樣利用達爾文主義。社會主義之平等理念的先行者們引用達爾文主義為其思想武裝,而相對地提倡人種主義者亦是如此。」達爾文主義因此擁有繁瑣而多樣的面向。然而,若是我們將發展說與淘汰說還原成兩個基本型態,則我們可看出當時的達爾文主義,一方面作為一種進化思想,另一方面則是作為一種淘汰原理。各路人馬,各取所需。
在德國,乃至其後日本的人種法學可見的達爾文主義的刻痕,究為前期的進化思想,抑或是後期的淘汰原理呢?此問題對於我們了解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調查事業的本質而言,非常重要。更具體來說,亦即作為殖民地政治家的後藤新平,與作為殖民法制創造者、法學者的岡松參太郎,應得到如何的歷史評價?了解達爾文主義的兩種型態,對於回答此問題甚有助益。
附帶一題,達爾文的進化論(《物種源始》)付梓於1859年,所以原本和薩維尼的民族有機體論毫無關係;只不過,到了十九世紀後期,達爾文主義以一種溯及的型態,為薩維尼的學說背書而已。然而,對於巴浩芬等苟全學術性命於學院邊陲的學者,當時的歐洲知識社會並未抱持著善意。巴浩芬雖然發現了與羅馬、日耳曼父系制度全然不同的家族制度,但是其於《母權論》中,主要也只是在處理古代的民族,幾乎沒有對於所謂現存之未開民族作任何討論。因此,巴浩芬對於坡斯特的影響可說是間接性的,進化論才具有關鍵性影響。
關於巴浩芬學說的詳細說明,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內,留待日後再行討論。在此,首先須做處理的是用語及與其相關的問題。
所謂「人種法學」的用語,最早是被坡斯特所使用。此用語在現今已變成了死語,無人使用,故需要略加說明。戰前,「ethnologische Jurisprudenz」被日本人翻譯為「人種學的法學」,不過,到了戰後,一般學界則改譯為「民族學的法學」(民族法學)。大概是由於反省戰前用語——「人種」這個字眼帶有後期達爾文主義之色彩,具歧視的意味,才加以改譯。此種對於戰前的反省,及清算學術用語的例子,可說是不勝枚舉。而在1970年代以後,或許也是人類學界本身自我反省的結果,近年來「民族」或是「民族學」等用語,都被學者極端地厭惡,取而代之的是日文的「エスニック」——一種曖昧的片假名修辭。不過,因為考慮到戰前時代的侷限,也為了能更接近岡松參太郎的學術本質,本章仍沿用「人種學的法學」此種舊式的用語。
戰後,德國對於人種法學的研究,在質和量兩方面,相較於美、英、法三國的民族法學(法人類學)的奔軼絕塵,只有「瞠乎其後」四個字可以形容。特別是在戰前本已有坡斯特、柯勒、亞當(Leonard Adam)等人所累積之大量研究業績,可是到戰後並沒有多少學者繼承這些戰前的研究,甚且進行檢討、考察。因此,筆者在整理所能掌握的文獻中發現,最能幫助我們檢證戰前德國人種法學之理論與實踐的現代著作,大概就是蕭特(R. Schott)一系列的論文。而其論文中與本章處理之問題關係最深、且內容最為明快的,就是「德國人種法學與法人類學之主要趨向」。
在蕭特此篇論文中,他一方面意識到英語圈的學者們對於學術歷史的認識,另一方面也全盤回顧了戰前德國人種法學的全盛時期,甚至對於戰後人種(民族)法學的不振,有許多的反省。蕭特解釋,戰後此種學問之所以一蹶不振,其原因和戰後德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衰退有關。易言之,和敗戰國德國之反納粹的心理結構,或先前所提及人類學者的反省有關。此一觀點非常重要,因為本書所引用的,日本學者有關後藤新平與岡松參太郎的傑出先行研究成果,其所使用的資料幾乎都是戰前的日文記述或翻譯,或是本於日本本位之邏輯所展開的討論,因此,往往有將此二人視為悲劇英雄、過度「神入」的結論。姑且不論此一結論是否近乎真實,不過,對於被殖民者而言,說服力似嫌不足。因為日本學者重視的,是想藉由研究殖民地台灣的法律史來補足日本近代法制史的空白部分;而台灣的學者卻是以建構台灣的近代法制史之立場,來對後藤新平、岡松參太郎等人進行歷史評價。二者在本質上有無法相容之處。儘管如此,也許我們可以超越此兩國本國史的範疇,進入世界史的視野。亦即,將後殖民的論述導入殖民時代的研究。就此而言,蕭特如此謙遜地嘗試超越德國戰前思想的論文,對於日本或台灣的研究者而言,可說有著相當的啟示性。
第一章 岡松參太郎的法學烏托邦(摘錄)
岡松參太郎(1871-1922),是日本明治維新/法學近代化之後的第三代民法學家,而且是最傑出的一位。他不但擺脫第一代第二代法學前輩(如穂積陳重等)只能被動繼受歐陸法學的困境,開始思索如何建立合於國情卻不抱殘守缺的日本民法學,而且在方法論上已經突破法律釋義學的侷限,自覺地或不自覺地進入了法律史學及法律社會學的層次,對於其後的第四代及第五代日本民法學家(末弘嚴太郎、我妻榮等人)影響至深。
岡松參太郎同時也是最難理解的近代日本法學家。但這不是因為他的學術成就難以理解,...
推薦序
導讀:立法者之書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Das war kein wahres Paradies—
Es gab dort verbotene Bäume.
(那不是真正的樂園―
那裡有生長著禁果之樹。)
—— Heinrich Heine, Adam der Erste
一、法思想史與後殖民批判
這是一本不易閱讀,也不易掌握作者真意的書。用作者吳豪人京都大學時代的業師河上倫逸教授慣用的調侃話語來說,這本書「對讀者不太友善」。在表層意義上,正如書名《殖民地的法學者》所示,這是一本正統的法思想史學術著作,運用嚴謹、專業的比較思想史的方法,加入法社會學的觀點,細緻(有時甚至繁瑣)地追溯日本在台殖民法律人─法學者、法官、檢察官與律師─思想的根源、特質,歸納其類型,並且深入地評價其影響。但是進一步細讀之後,我們又會發現書中有很多「溢出」思想史範疇的東西,如隨處可見的機鋒、反諷、自嘲,乃至當代觀點的評論,以及鮮明的政治立場等,因此似乎顯得「不夠專業」或「非歷史」。然而這些「溢出」─或者冒瀆了─傳統學術專業框架的東西正好說明了,本書不只是一本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法思想史的專業著作,而且還是一本日治時期台灣法思想史的後殖民批判(a postcolonial critique of the history of legal thoughts of colonial Taiwan)。正如同蘇格拉底慣用的反諷一般,作者在本書中看似肆意揮灑的「機鋒、反諷與自嘲」,其實是一種表現台灣史上連續與多重殖民經驗所造成的道德複雜性(moral complexity)的方法,而那些「非歷史的」當代觀點評論與「不夠客觀的」台灣主體立場,則是進行任何有效的後殖民批判的必要尺度。
掌握了本書兼具法思想史與法思想史的後殖民批判的雙重或重層特性,我們因此可以對它進行某種雙重的,或者重層的閱讀。作為一冊法思想史著作,本書從戰前日本國家意識形態內所謂「顯」(國體論)、「密」(現代君主立憲論)兩教並存的曖昧本質此一大脈絡或前提出發,觀察作為密教現代性先鋒的殖民法律人的特質、行動,以及他們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作者遵循法思想史的研究取徑,從這些法律人的思想內在理路中解釋他們的行動─特別是他們在前現代的顯教教義與帝國主義國策強大制約下,在殖民地台灣追求法律現代性的成就與限制。
做為一篇法思想史的後殖民批判文本,本書隱含另一個深層論證:戰前日本深深受困於西方現代性論述,它對台灣的統治,包含其成就與限制,都清楚反映了此種受困,而書中論及的這批殖民法律人則是日本受困物語的例證,他們也同樣都是西方現代性意識形態的囚徒。另一方面,作為日本殖民統治的臣民,台灣人可以說是雙重受困者。我們必須從這個認識出發,超越戰前日本所構築的知識與道德霸權之壁,對日本殖民統治及其遺產進行批判性的檢視,才能真正理解那些來統治我們的人到底是誰,他們做了甚麼事,又在我們的身體與靈魂中留下了甚麼痕跡。然後,我們才知道我們接著要往哪裡走。
第一層次的論證是實證的、歷史的,第二層次的論證則是政治的、當代的。前者為後者的分析提供經驗基礎,後者則是前者的規範性演繹,兩者相互呼應,共同構成了一次台灣思想史上少見的對日本殖民統治之法思想面向的知識/道德考掘。
在嘗試釐清作者的意圖,以及勾勒出本書兩個層次論證的輪廓之後,讓我們接著對這個論證進行比較細部、深入的討論。由於本書的論證涉及到許多法學以外的專業概念與問題,例如帝國、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等,所以這篇導讀以下的討論,主要是為本書關於法思想史與後殖民批判的論證提供比較政治、政治史與政治思想史的補充詮釋。首先,筆者會簡單探討戰前日本帝國與殖民主義的結構特質與思想特徵。其次,筆者會在這個日本帝國整體的脈絡之中,觀察作者在本書所建構的殖民地法律人的面貌與特質。最後,筆者將重建日本殖民統治下不同位置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群體的結盟型態。
二、日本帝國的特異性:顯密兩教並存的結構性起源
本書論證的前提,也就是戰前日本國家意識形態中「顯密」兩教並存的說法,是日本近代思想史的著名典故。顯密兩教之說最初是哲學家久野收與鶴見俊輔在1956年的共同著作《日本の思想》所提出的。他們主張,當初伊藤博文在制定明治憲法時,刻意設計了兩套對天皇制的解釋系統:教育一般庶民大眾時使用國體論,日本被視為「神國」,天皇被視為絕對主權者,是為「顯教」,也就是天皇主權說;教育菁英層則使用現代憲法思想,日本是現代君主立憲國,天皇權力受到憲法限制,是為「密教」,也就是天皇機關說。這種二元設計,日後成為政治衝突的根源。大正、昭和前期的日本政治史的變遷,體現了這兩種國家觀的對立消長:所謂「大正民主」就是密教對顯教的「征伐」,但是昭和期法西斯主義的抬頭則代表了顯教的反擊與勝利。久野收這個說法影響深遠,幾乎與丸山真男的「無責任體系」並列,成為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最著名的定說之一。京大法學部出身的本書作者,顯然就是在這個日本知識脈絡中發言的。
日本戰前國家意識形態中的二元性或折衷性是一個重要的事實,然而用「顯密兩教」來解釋此種二元性,似乎誇大了明治開國者的能動性與日本的特殊性。另一種比較合理的解釋方式是,這是日本在戰前世界體系與地緣政治結構位置的思想上反映。印度後殖民理論家Partha Chatterjee指出,殖民處境中的民族主義者的思想結構經常表現出一種折衷的特質,也就是想要同時保有民族認同與追求現代性(national modernity)。中國的中體西用論,印度的「東方精神、西方科學」論,以及幕末佐久間象山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論均是例證。明治中期,日本依然處在西方列強殖民壓力下,受不平等條約桎梏,伊藤博文兼採顯密兩教,試圖調和本土與外來、傳統與現代,以及象徵與現實權力的明治憲法,也可以看成是這種追求「民族的現代性」的一個例證。這種折衷主義具有內在不穩定性,常常誘發內部傳統、西化兩種不同路線的爭鬥,甚至導致整個國家方向劇烈擺盪。戰前日本顯教(傳統主義)與密教(現代主義)的鬥爭,乃至整個國家由明治前期熱烈學習西化的「脫亞入歐」,一轉為昭和時期的「脫歐返亞」,就是戰前日本民族主義思想的折衷性或曖昧性的表現。處於相同結構位置的印度與中國的民族主義也具有類似思想特徵,這類意識形態具有結構性根源,不能化約成偉大開國者的政治設計。
戰前日本不同於印度與中國之處在於,它擺脫了殖民或半殖民的處境,同時還進一步發展成一個殖民帝國。不過戰前日本帝國是一種向同文同種的鄰接地域擴張的領土連續帝國(contiguous empire),與統治遠隔重洋的亞非異文化殖民地的歐洲海外帝國適成對比。從比較政治角度觀之,這是民族國家擴張與初期帝國形成相互重疊的個案,類似於英格蘭向凱爾特邊陲(Celtic fringe)的擴張模式。基於國防與地理、文化近接性的理由,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即試圖將擁有完整主權的新領土如沖繩、北海道、台灣、樺太與朝鮮,透過「差序式吸收」(differential incorporation)的模式,經由漸進的制度整合與文化同化,逐步整編、吸收到日本民族國家之內。因此,日本在這幾個地域的統治同時具有殖民統治(差別)與民族建構(同化吸收)的雙重性質,可稱之為一種「民族化的殖民主義」(nationalizing colonialism)或者「殖民的民族建構」(colonial nation-building),這也與古典的歐洲殖民主義非常不同。
在地緣政治與世界體系結構中,戰前日本帝國處於西方的邊陲,而沖繩、台灣、朝鮮等地則處於日本的邊陲。處於半邊陲位置的日本,一邊以折衷主義的反殖民民族主義論述抵抗西方中心,一方面又把這個論述轉化為支配邊陲領土的殖民意識形態。與被殖民者同文同種(特別是共享儒教與漢字文化)的事實使日本的統治具有合理性,但日本成功吸收西方現代文明的事實又使他們在當地的統治具有「文明開化」(現代性)的正當性。這種基於「同中之異」的曖昧統治與西方殖民主義純粹基於差異性的統治(rule of difference)有本質的差異,筆者將此種日本式的殖民主義稱之為「東方式殖民主義」(oriental colonialism)。在東方式殖民統治下,同文同種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會出現複雜的協力與對抗的景致。
前面簡單勾勒的戰前日本帝國與殖民統治模式的圖像,目的在為理解本書所處理的殖民地法律人提供一個大的政治與意識形態脈絡,因為他們基本上都是在這個極為特殊的脈絡中活動的歷史行動者。他們並非完全沒有自主性,但他們確實深深受到這個歷史脈絡的塑造與制約。從這個脈絡中觀察,有助於我們掌握他們的思想與行動,成就與限制。
三、殖民地法學者與法曹:自由帝國主義者與平庸的辯證
本書所討論的殖民地法律人,包含法學者(岡松參太郎、増田福太郎)與實務法曹如法官(堀田真猿、姉歯松平)、檢察官(三好一八、上內恆三郎)與律師(如治警事件辯護律師群)。對於這些人物的特質,作者在書中做出了複雜、深刻而辛辣的觀察:
(一) 他們雖有自由、保守之別,但基本上都是前述母國國家體制與國策(帝國擴張、殖民統治、漸進整合與同化主義)的支持者,偶而會與殖民政府齟齬,但絕不抵抗國家,更不敢觸及天皇與國體顯教。法官與檢察官則根本屬於現地殖民官僚系統的一環,自然遵行殖民政府政策。
(二) 除了増田福太郎這個較為複雜的特例外,他們都是法律現代性的真誠信仰者。我們可以觀察到幾種法律現代性的表現方式:
(1) 初期以岡松參太郎為代表,從法多元主義(legal pluralism)立場支持後藤新平的特別統治主義路線,不過他的目的並非證成後藤的政治現實主義,而是想建構一部「臺灣民法」,追尋台灣特有的法現代性形式。岡松的思想源於德國人種法學,但也受英國式殖民主義尊重舊慣的思考,特別是同時代英國殖民法律人為印度舊慣建構成文法典事業的影響。
(2) 中期以後的殖民地法律人多信仰法的一元論,主張內地與台灣屬同一國家,故應法律一體,並由此角度支持內地延長主義和同化政策。實務法曹主張廢除祭祀公業,全面適用日本民法即是此一立場的例證。
(3) 至少到1937年為止,他們基本上都信仰法治國家原則,治警事件一審判決無罪是最有名的例證。
(三) 這些法律人大多懷抱使命感而來,視殖民地(新領土)為推動其法律現代性理念的「樂園」——此處所謂「樂園」,指的是可以讓這些擁有巨大權力的殖民官僚與法曹自由形塑當地的法律與社會,實現其現代性理念的場域。然而他們所信仰的法的現代性,終究是承襲自西方的事物,並非自己的原創,因此他們所想像可以任意揮灑、自由塑造的「樂園」也終究不是真正原創的樂園,而是一個仿造的遊樂場而已。
(四) 除了岡松參太郎以外,這群殖民地法律人─特別是以姉歯松平為首的務實法曹─多是日本社會的第二線人物,並非出身菁英階層,然而這個凡庸的特質產生了一個有趣的辯證:因為凡庸,他們並未真正理解模仿自西方的法律現代性,只是對這個外來事物抱持堅定的信念,於是凡庸加上過剩的信念,再加上現地實務法曹擁有的權力與優勢,使他們在台灣積極推動法的普遍性,最終產生了將原被排除的被殖民者納入日本法秩序的不預期效果。作者如此生動地總結:
被殖民者原本是殖民法制中權利的被排除者,只有對西歐法的價值信心堅定的「敗者」,才會致力於法╱權利的自我增殖。雖然這種增殖純屬自我建構與自我完成,無關殖民統治之善惡。(頁206)
最終,在台灣的現代化之路留下痕跡的,是這些堅定信仰法的現代性的實務法曹,而非大法學家。這是一個複雜的圖像。整體而言,這群涉入台灣統治事務的日本法律人是日本國家兩面性意識型態之中的「密教」,也就是現代性的信仰者與尖兵;他們來到台灣並非為了掠奪,而是為了在這個新領土推行與實現自身的法律理念。就這個意義而言,這群懷抱文明開化使命感(以及優越感),自許將為台灣帶來法律現代性的法律人,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馬考萊式(Macaulayian)的「自由的帝國主義者」(liberal imperialists)集團。然而,這群自由帝國主義者的文明化計畫必須被加上括號,因為那是二手的,而且他們凡庸到無法真正理解西方原創的精神,以至於只能比西方人更加倍熱情地,更忠實,更徹底地在人工的樂園推動二手的現代性計畫。一個弔詭的結果是,熟知現代性的西方人不願在他們的殖民地徹底推動現代性計畫,而西方手下敗者的日本法律人卻因忠實、徹底地在殖民地推動模仿自西方的現代性計畫,反而在那裡留下了比較深刻的痕跡。徹底實行的二手計畫,反而比不願實施的原創計畫達到更大的成果,這就是作者所提出的日本式殖民現代性之辯證。
對於這個精采複雜的論證,筆者在此只想補充兩點。第一,如同前述,日本統治台灣的最終目的是要將台灣吸收到日本國家之中,因此其治理模式遠較任何歐洲殖民帝國(包括宣稱同化主義的法國與葡萄牙)更重視同化與整合。殖民地法曹固然因為真誠信仰西歐法現代性而勤奮地推動法律一體化,但日本逐步吸收台灣的統治方針也為他們的行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條件。
第二,殖民文官(包含法務官僚)的凡庸其實是現代帝國的常態。除了大英帝國統治下印度的文官體系(Indian Civil Service, ICS)是完全由英國統治階級與劍橋、牛津等大學畢業生甄拔形成的超級菁英集團(elite corps)之外,幾乎其他所有歐洲帝國的殖民文官,都是經由一個特別的殖民文官養成體系培育而成,如法蘭西帝國的Ēcole Coloniale,而且學生大多資質凡庸。十九世紀歐洲殖民帝國得以成立的真正權力基礎,其實不是高素質的殖民官僚,而是殖民母國的綜合國力,包含了能有效凝聚與動員國民忠誠的政治組織型態(民族國家)、科技(軍事)、經濟(資本主義),以及關於所謂文明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的意識形態霸權。換言之,歐洲殖民帝國的崛起背後,其實就是經濟史家Douglas North所想解釋的「西方世界的興起」的問題。從比較殖民主義角度觀之,日本雖是後進帝國,但其殖民官僚素質介於英國的印度高級文官與其他歐洲帝國殖民官僚之間,雖然不是全由帝大出身的第一線菁英組成,但仍具有一定水準。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確實是有效率的,但這只需要忠誠、勤奮而負責的官僚、警察與軍隊即可實現,然而支撐日本有效的台灣統治的是日本帝國的綜合國力─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科技與資本主義發展,以及一整套帝國的意識形態。討論至此,於是我們會發現,本書作者精彩的「殖民現代性的辯證」論證的原型,其實是母國日本,因為最初的仿冒,第一個二手計畫,就是明治民族國家的建構,以及日本對西方列強的急起直追。當我們質問台灣殖民現代性的辯證法,其實就是在質問日本民族國家形成的辯證法,然而這已經超出本論的範圍了。
四、日本東方式殖民統治下的抵抗與協力
如前所述,日本的東方式殖民主義不是典型歐洲殖民主義的「差異的統治」,而是異同並用的「曖昧的統治」。它的意識形態結構不是「西方/現代」對「東方/傳統」單純二元對立圖式,而是「東方+西方/傳統+現代」對「東方/傳統」的區隔。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分享共同的東方傳統(儒教與漢字傳統),這正當化了領有權與同化的可能,但殖民者又擁有被殖民者沒有的西方現代性優勢,這點則正當化其支配權。
對於日台共享的文化傳統以外的在地特殊性,日本殖民統治者採取漸進的文化同化與制度整合的政策:先進行語言與部分慣習的同化(如斷髮、放足等),其次進行制度整合(地方制度改正、共學等),民俗信仰與宗教同化則放在最後。這個局部的「漸化」(第三任台灣總督乃木希典語)政策導致了一段相當長的「舊慣溫存」時期,在這段期間,殖民政府甚且積極支持本地民俗信仰(如建醮),以攏絡民心。
在戰前的世界體系結構中,日本處於西方的邊陲,而受日本支配的殖民地則成為日本的邊陲。在這種「雙重邊陲」情境中「遠交近攻」成為主要的邊陲抵抗策略,也就是直接與核心部位(西方)進行現代性的論述結盟,批判日本統治現代性的不徹底。孕生自雙重邊陲情境的反殖民民族主義論述,因此往往帶有較鮮明的親西方、現代取向。被殖民者或者直接援引西方現代性論述,或者透過與日本內部的西方現代性論者結盟,批判日本意識形態的折衷與封建。戰前台灣與朝鮮的民族主義者直接與基督教結盟,或者與大正民主派知識人結盟,均是例證。
在東方式殖民主義下,反殖民民族主義者同時也是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者。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共享許多文化傳統(特別是儒教式封建主義)的狀況下,他們批判殖民者的封建性,必然同時也會批判自身(儒教)傳統的封建性。此外,他們也批判殖民者刻意溫存的舊慣風俗信仰(如迎神、建醮、歌仔戲)。成為被批判對象的本地文化保守主義者或傳統主義者則向共享封建價值,並且寬容他們舊慣風俗信仰的新殖民者靠攏,成為協力者。
東方式殖民主義下,以現代/傳統之對立為主軸,形成一種外來、本土交錯的結盟關係。最主要的敵我區隔,是由殖民地民族主義者與母國自由派知識人的「反殖民的現代性同盟」與由殖民政府與殖民地傳統主義者的「殖民主義同盟」相對峙。作者在本書中提到,在廢止祭祀公業(家族制度)問題上,形成殖民者與反殖民者結盟的奇妙關係,也就是民族主義者與現代派殖民法曹聯手對抗本土傳統主義者。筆者認為這是東方式殖民主義促成的一種有限度的議題性結盟,雖然短暫跨越了殖民與被殖民的界線,但並未導致結盟雙方根本政治立場(殖民/同化 vs 反殖民/民族自決)的變化。
廢止祭祀公業問題涉及殖民地傳統家族制度,家族制度則是本地文化認同的核心要素,容易引發保守主義或傳統主義者的反彈,因此殖民政府理性,或者機會主義地採取除外例,以迴避正面衝突。不過殖民地台灣的傳統家族制度具有強烈封建性格(家父長主義),反封建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自然會選擇支持殖民政府廢除該制度,於是形成反殖民主義與殖民主義在非直接涉及政治的現代性問題上的議題性結盟。
事實上,整個二○年代的反殖民台灣民族主義論述均帶有強烈反傳統主義色彩,所謂「本土現代性」或「民族現代性」的思考與運動,要在三○年代前半的一波文化民族主義中才開始出現,而且集中在與語言、文字相關的領域,如台語文字化、民間傳說採集、歌謠創作,以及本土語言學、文學、哲學等。在二○年代的祭祀公業論爭過程中,台灣民族主義者從未發展出將祭祀公業─亦即本地家族制度─當成民族認同素材並加以現代化的思考。作者提到法學者戴炎輝在三○年代中期開始暗示這個方向,但這個時點台灣民族運動已經瓦解,而祭祀公業的沒落也大勢已定,在缺乏政治奧援與社會基礎的情況下,戴氏也並未繼續環繞這個議題發展出本土或民族法律現代性的論述。或許我們可以說,戴炎輝是一個遲來的民族主義者(belated nationalist),或者早夭的「台灣格勞秀斯(Grotius)」,而他想將祭祀公業轉化為民族認同基礎的思想嘗試,則是一種「沒有民族主義的民族法學」,注定徒勞無功。
五、結論:朝向未來的「台灣法史」
在他京都大學的博士論文〈『台湾法史』の可能性:法社会史的・法思想史的試論〉的終章,吳豪人提出一個意味深長的反省:由於台灣法史乃是由連續外來政權之「統治者的恣意」所形塑,從未體現台灣人的集體意志,與德國歷史法學派主張法是全民族的「共同財產」與「共同確信」完全相反,因此台灣人如果想通過法律獲得自己的民族認同,就必須逆用歷史學派的論證,把「法是民族的共同財產與共同確信」這樣的說法,由客觀事實轉化為主觀願望。換句話說,一部外來者書寫的台灣法史告訴我們,在台灣所謂「法是民族的體現」尚未成為客觀事實,只能是未來的願景,而為實現這個願景,為了在未來創造真正體現民族意志的法,必須對這個由連續的「統治者的恣意」所構成的台灣法史進行清算。
這篇博士論文和本書的內容有部分重疊,然而吳豪人卻整個拿掉了足以「明志」的博論終章,讓這本書的顯得更為迂迴、隱晦。上面這段自省,使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確認他整個「台灣法史」研究計畫的反殖民、後殖民,以及追尋主體建構三個環環相扣的目標。起源、成長於日本殖民支配,並且在戰後國民黨的移民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下獲得新生的台灣法史,必須經過一次或反覆的後殖民批判審視,才能化為真正屬於台灣人自己的精神遺產,也才能在這個基礎上構思、醞釀與書寫真正體現台灣人民族認同的法。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傳統中,所謂「立法者」(the lawgivers)在政治共同體的形成過程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在思想史家區別的三種立法者類型中,英雄般的創建者(herofounder)從外部以非常手段與過去決裂,締造新的共同體,而制憲者(constitution-maker)與法典制定者(codier)則在內部賦予這個新生的共同體穩定的政治與法律秩序,使其得以綿延久遠。放在這個思想脈絡中理解,吳豪人的《殖民地的法學者》可謂一冊探討立法者與台灣政治共同體的奇妙著作─更精確地說,這是一冊立法者之書的序論,因為它是為一個尚未降生的台灣政治共同體,以及未來世代的台灣立法者們而寫的。它具有創建者的決裂意圖,但它主要的工作是在為未來的制憲者與法典制定者們清理、清算日本法律人在殖民統治時代所留下的足跡與遺產,協助他們辨識我們的先人曾經驗過的黑暗、光明與複雜曖昧的黃昏景致,並且鼓舞他們為我們這個將要降生卻遲遲未降生的、難產中的台灣政治共同體,描繪出一個全新的政治與法秩序的願景。
導讀:立法者之書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Das war kein wahres Paradies—
Es gab dort verbotene Bäume.
(那不是真正的樂園―
那裡有生長著禁果之樹。)
—— Heinrich Heine, Adam der Erste
一、法思想史與後殖民批判
這是一本不易閱讀,也不易掌握作者真意的書。用作者吳豪人京都大學時代的業師河上倫逸教授慣用的調侃話語來說,這本書「對讀者不太友善」。在表層意義上,正如書名《殖民地的法學者》所示,這是一本正統的法思想史學術著作,運用嚴謹、專業的比較思想史的方法,加入法社會學的觀點...
作者序
事實上,本書既是,也不是筆者的博士論文。博士論文只不過是取得文憑的終點,但卻是思想推求的起點。從2000年取得日本國立京都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至今,筆者不斷推敲自己在這篇博士論文裡所提出的問題,也不斷地修改能夠說服自己的答案,所以從不急於出版。況且回到台灣不久,就發現台灣法律史的研究領域,並非異端如筆者所能廁身其中者,因此將自己的研究範圍,轉移至廣義的人權思想與實務。從此,「出書」更是不亟之務了。儘管如此,夢倒是愈做愈大。
構想中,《殖民地的法學者》至少得寫成兩本書,第一本談日本殖民台灣時代的日本法學家,第二本談中華民國殖民台灣原住民族時代的「白浪」殖民法學家——包括筆者自己在內。這個構想的前提是:假設戰後的台灣只有原住民族仍然處於被殖民狀態(為什麼不假設「整個台灣都仍然處於被殖民狀態」呢?理由很簡單。法律上「我是不是人」並不是「我之所以為人的要件是否滿足」的問題,而是「我」要不要出於自由意志公開宣示「我是人」的問題。是否為獨立國家,或者尚在被殖民狀態的判斷亦然)。
在這個構想的前提之下,第一本書中探討他者─日本殖民(法學)者的本質,盡量不及於台灣的近代法律人。目的是要凸顯一個問題的重要性:「作為殖民者的日本人,和荷蘭人、鄭成功或大清帝國究竟什麼地方不一樣?」或者,「日本的殖民為什麼徹底改變了台灣?」當然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一定是互動、互相形塑的,不過在「知識等於規訓或權力」的現代性命題被台灣人參破之前,「形塑殖民者」的力量相較於「被殖民者型塑」的力量便顯得微弱。因此討論台灣的近代法律人,就不妨委諸於下一本專書。若就已經成書的第一本,與構想(夢想)中的第二本作對比,那麼第一本出現的「殖民地的法學者」全數都是現代性理念的傀儡,而第二本出現的,卻將是能夠自由出入、從而「超克」現代性理念的「新種」。也就是能夠充分體會日裔美籍學者Masao Miyoshi於Off Center: Power and Cultur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s的以下這段話的新種法律人,乃至於「新種台灣人」:
中心╱邊陲的圖式,並不在於鼓勵邊陲打敗中心而另成一個新中心,並將舊中心打入邊陲。邊陲本身並無法求得倫理的優越性。被壓迫、被欺詐、被殖民等受害者經驗與記憶本身,並無任何倫理上的價值。只有當這些特定的民族苦難記憶,轉化為強烈保護其他民族不受相同苦難欺凌的動機與實踐之際,才真正出現倫理上的價值。上述的弔詭才得以避免,中心╱邊陲的循環論證,才得以終止。
如此深刻的體認,當然不可能一步到位。第二本的出現,必須等待第一本的完成。如今,算是繳卷了。
是為序。
事實上,本書既是,也不是筆者的博士論文。博士論文只不過是取得文憑的終點,但卻是思想推求的起點。從2000年取得日本國立京都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至今,筆者不斷推敲自己在這篇博士論文裡所提出的問題,也不斷地修改能夠說服自己的答案,所以從不急於出版。況且回到台灣不久,就發現台灣法律史的研究領域,並非異端如筆者所能廁身其中者,因此將自己的研究範圍,轉移至廣義的人權思想與實務。從此,「出書」更是不亟之務了。儘管如此,夢倒是愈做愈大。
構想中,《殖民地的法學者》至少得寫成兩本書,第一本談日本殖民台灣時代的日本法...
目錄
圖輯
「臺灣研究先行者」序言╱黃英哲、梅家玲
導讀:立法者之書╱吳叡人
自序
導論
第一章 岡松參太郎的法學烏托邦
第一節 德國人種法學之系譜
一、歷史法學派
二、達爾文主義
第二節 德國人種法學之理論與實踐
一、A. H.坡斯特之人種法學
二、J.柯勒之比較法學
第三節 德國人種法學對於台灣舊慣調查事業之影響
一、背景
二、岡松參太郎之台灣舊慣調查事業
三、小結
第四節 從歐陸殖民法學尋找線索
一、貌合神離:柯勒的問卷與德國殖民政策
二、岡松參太郎的對照組:C. van Vollenhoven的Adat Law研究與荷蘭殖民政策抗爭
第五節 結論
第二章 臣民與帝國之間的「絕緣體」:祭祀公業的興廢
第一節 序論
第二節 前史:1923年以前
一、日本領台前的祭祀公業
二、祭祀公業之種類及其內容
第三節 內地延長主義時期的祭祀公業
一、於台灣適用民商法的問題與祭祀公業的廢止論爭
二、祭祀公業之法律性質
三、祭祀公業大解體:日治法院檔案(台中地方法院)中的線索
四、「絕緣體」的最終抵抗:1937年之後的祭祀公業
第四節 結論
第三章 大正民主與治警事件
第一節 先行研究與本章檢證範圍的設定
一、先行研究
二、本章檢證範圍的設定
第二節 大正民主時期對日本法律人的影響
一、大正民主時期
二、大正法學與法律人
第三節 治警事件的法律爭點
一、政治裁判的定義
二、治警事件以前的台灣刑事法概要
三、治安警察法的成立與其在日本國內的爭議
第四節 治警事件中關於治警法的爭點
一、治警事件發生的過程
二、第8條第2款
第五節 日籍檢察官與辯護律師的備忘錄
一、判決
二、日籍辯護律師的備忘錄
三、日籍檢察官、法官備忘錄
四、小結
第六節 結論
第四章 敗者的精神史:「凡庸之善」姉歯松平與「凡庸之惡」増田福太郎
第一節 法學「大老」退場後的台灣殖民法學界
第二節 「法/權利的自我增殖者」姉歯松平
一、姉歯松平的出身背景與學術業績
二、姉歯松平的政治立場:長男的回憶與「朱諾號事件」
三、小結
第三節 凡庸之惡:「法」學者筧克彦與増田福太郎
一、筧克彦的「皇道神(法)學」
二、筧克彦學說對増田福太郎的影響
三、増田福太郎與「日本法理研究會」
第四節 結論
終章
註解
附錄一 研究德國殖民地所謂自然民族(Naturvölker)法律關係之問卷/柯勒(J. Kohler)
附錄二 筧克彦的日本法理圖
參考書目
圖輯
「臺灣研究先行者」序言╱黃英哲、梅家玲
導讀:立法者之書╱吳叡人
自序
導論
第一章 岡松參太郎的法學烏托邦
第一節 德國人種法學之系譜
一、歷史法學派
二、達爾文主義
第二節 德國人種法學之理論與實踐
一、A. H.坡斯特之人種法學
二、J.柯勒之比較法學
第三節 德國人種法學對於台灣舊慣調查事業之影響
一、背景
二、岡松參太郎之台灣舊慣調查事業
三、小結
第四節 從歐陸殖民法學尋找線索
一、貌合神離:柯勒的問卷與德國殖民政策
二、岡松參太郎的對照組:C. van Vollenhoven的Adat Law研究與荷蘭殖民...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4收藏
4收藏

 21二手徵求有驚喜
21二手徵求有驚喜




 4收藏
4收藏

 21二手徵求有驚喜
21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