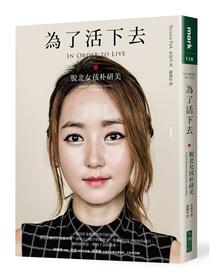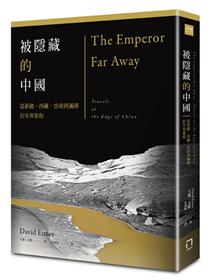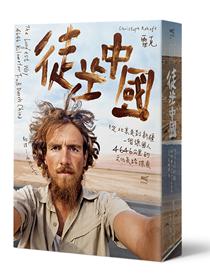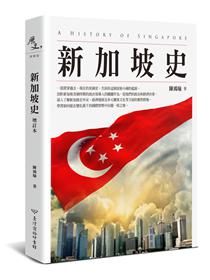{縝密的在地考察、犀利的旅人之眼、雕刻刀般的文筆}
天下並無必看不可的風景,只有你想不想去的地方。
「不同於長居某處,旅行要義在於流動。
這個流動過程,讓你不斷遇到人和事。
它們難免浮淺,但是好比一幅拼圖,
讓你慢慢看到整體。」
第11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提名散文集《考工記》作者──
【周成林】最新南亞人文旅行散記
◆「跟著火車跳了一夜,暈頭轉向,我還在輕微打顫。
也許,為了追尋歐威爾及其《緬甸歲月》,這不算什麼;
比起長年含辛茹苦的緬甸人,更不應該大驚小怪。
可我還是好奇,歐威爾時代,火車也是這樣跳舞?」
「不只一次,我告訴這趟旅行遇到的諸多西方旅伴:前幾年來緬甸或許太早,過幾年又怕太遲,現在來,或許正是時候。」
──周成林(獨立作家、譯者、旅行者)
◆作者把所見所聞訴諸生動精細的文字,就像一幅講究細節而又趣味盎然的拼圖,小中見大,堪稱華文世界旅行文學的精品。
◆作者周成林為《愛與希望的小街》作者,毛姆《客廳裡的紳士》、《時光中的時光:塔可夫斯基日記》、《奈波爾傳》譯者
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仰光學生反抗軍人獨裁的示威遭到殘酷鎮壓。隨後一個月,緬甸各地成千上萬民眾上街要求民主自由,當局出動軍隊,三千多名學生、僧人和平民死在軍人政權的槍下。這是緬甸現代歷史最慘痛的記憶,但是它讓世人知道美麗而無畏的翁山蘇姬,也為二十多年後的「緬甸之春」播下無數種子。
《跟緬甸火車一起跳舞》,是中國獨立作家和旅行者周成林這幾年兩度前往緬甸旅行數月的詳實記錄,但非追趕時效的新聞報導,亦非枯燥乏味的政經解析,而是對「緬甸之春」的冷靜觀察和切身體會。從威權統治步向民主自由,與世隔絕將近半個世紀,古老佛國緬甸正在慢慢轉變。作者把所見所聞訴諸生動精細的文字,就像一幅講究細節而又趣味盎然的拼圖,讓您小中見大,堪稱華文世界旅行文學的精品。
本書並收錄作者近年在印度和柬埔寨等國的旅行文字,多從歷史與現實的交織點切入,以寬廣視角和敏銳眼光,觀照這些國度的諸多變遷與現狀,譬如尋訪赤柬領袖波爾布特在柬、泰邊境最後藏身的叢林小屋和焚化地,感受鼓吹民族主義的印度總理穆迪上台後的面子工程,親歷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達蘭薩拉的法會……每一篇章,從內容到文字,值得讀者細細體會。
作者簡介:
周成林
獨立作家、譯者、旅行者。一九六六年出生於四川成都。早年做過工人、眼鏡店驗光師、省政府賓館客房服務生和培訓幹事。後在澳門和深圳工作和居住十年。
二○○一年開始寫作和翻譯,作品發表於《萬象》、《南方都市報》、《財新週刊》、《民主中國》、《騰訊大家》等海內外報刊或網路媒體。著有非虛構文集《考工記》、《愛與希望的小街》、《就當童話讀吧》,譯作有毛姆《客廳裡的紳士》、《時光中的時光:塔可夫斯基日記》和《奈波爾傳》等。
二○一三年,因為《考工記》一書,周成林入選《南方都市報》主辦的第十一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散文家」五人提名(其他入選者為:劉亮程、李娟、梁鴻、野夫),提名理由為:「《考工記》是周成林第一部結集出版的散文……篇幅不長,卻帶給人一種真實的沉重,這是上世紀八○年代普通人生命中的沉重,充滿了家庭關係的殘酷、瑣屑生活的不堪和受命運擺布的無奈,就是看不到一個光明的結局。作者冷峻的筆調讓人很難帶著輕鬆愉快的心態來閱讀本書,但這種沉重亦會讓人安心,即使天地不仁,也要在這世間求生。」
章節試閱
這個緬甸
開場白
緬甸在變。在仰光三十七街小小的蒲甘書店(Bagan Book House),你幾乎找得到所有關於緬甸的英文書,從撣邦歷史孟邦(Mon State)歷史到英國人廢黜的熱寶王朝,從蒲甘的興衰到極其怪異的新首都內比都,從翁山蘇姬到不受歡迎的丹瑞將軍,從西方人寫的緬甸遊記到緬甸女作家用英文寫的緬甸遊記……「沒錯,影印本占多數,但誰在乎。」我告訴店內偶遇的一位六十開外的美國攝影師;我們聊起書架上幾本讀過的傳記、遊記和地緣政治論著,如逢知己。
蒲甘書店的老闆是位矮胖的中年人,和善,卻又不乏生意人的精明。五天前初次光顧,我買了兩本影印的英文書,議價時,他一臉苦相:「Don’t make my cry.」這一次,我指著幾本從前的禁書對老闆說:「三年前,這些都不可能。」「兩年前。」他糾正我。「從前只能藏起來。」最後一次光顧,我買了英國人喬治.史考特(George Scott)寫的The Burman: His Life and Notions(《緬甸人的生活與觀念》);作者是十九世紀典型的帝國主義者,化名Shway Yoe(緬甸人名),撰成這本至今流傳的小範圍經典。見我選了這本書,美國攝影師恍然大悟:他讀過我正在讀的那本關於史考特的書:「哈,Shway Yoe 原來就是Scott。」一下賣出兩冊,書店老闆給了我們折扣:每本便宜一千緬幣。「謝謝。」老闆接過錢,像幾乎所有緬甸平民一樣客氣。
在仰光郊外髒亂昏暗的昂敏加拉爾(Aung Mingalar)汽車站,我坐在露天茶室,喝著一罐越南產的可口可樂,等著開往曼德勒的夜車。鄰桌坐了幾個緬甸年輕人和一個嬉皮裝扮的美國黑人。其中一位緬甸後生英語講得流利。他說美國黑人是他姻親。我說外國人從陸路進入緬甸依舊困難而且昂貴。「會變的。我們現在有了民主。會變的。」緬甸後生信心滿滿,我忍著沒說這個民主還不是真正民主,路還很長,哪怕現有改變是個良好開端,就像今年一月最後一期英文版《緬甸時報》(The Myanmar Times)的頭條新聞,講到新聞審查取消後自由記者面臨的挑戰:報導政府軍和少數族裔的武裝衝突不再犯禁,記者也不再因此受到當局恐嚇,但是難在從各類傳聞之中找出真相。同一期報紙的文化版還有一篇報導,導演U Anthony 要拍一部電影,主人公是一名十六歲的高中女生Ma Win MawOo,一九八八年的民主運動之中死在軍政府的槍下。二十多年來,當局不斷恐嚇死者父母,甚至在死者祭日阻止僧人到家中接受布施。而今,父母終於可以公開紀念女兒,這部四月開拍、九月十九日(死者忌日)上映的電影,也將以家人的紀念作為最後一幕。
不是所有人都信心滿滿。在撣邦南部的格勞,一位退休的印裔老者告訴我,他做過政府部門打字員,每月退休金只有四千緬幣(不足五美元)。「夠什麼?」老頭歎道。他現在幫NGO(非政府組織)做項目掙外快,兒子則在香港做事。我說我喜歡格勞遍山松林、清新安寧。他撇撇嘴,有些不屑:「從前更好。現在滿街中國摩托車。很吵。一輛只要三、四百美金。材料廉價。」在曼德勒山腳的露天茶室,一位印裔計程車司機,黑瘦,五十來歲,坐著在喝可樂。「緬甸人現在很懶。他們不想做事,只想享樂。」計程車司機有些忿然。在蒲甘,一座荒蕪小廟近旁的洋槐樹下,十三歲的莫莫(Momo),領我去看小廟後面她的家:祖孫三代八人同居的竹棚。莫莫告訴我,她十七歲的姐姐不時要去鄰村幫人洗衣,一天只賺五百緬幣(權作對比:一瓶純淨水在緬甸通常要賣三百緬幣)。
等我第三次回到仰光,載我到仰光機場的司機也開了一輛廉價的中國車。仰光郊外綠蔭宜人。車過大學路,我脫口而出:「翁山蘇姬就住這條路。」「對。就往左。你去看過?」「沒。又進不去。現在也沒集會。」沉默片刻,年輕計程車司機說:「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一夜之間,全世界,尤其富裕國家的遊客和旅行者,似乎都湧來緬甸。不只一次,我告訴這趟旅行遇到的諸多西方旅伴:前幾年來緬甸或許太早,過幾年又怕太遲,現在來,或許正是時候。
一
飛機晚點了。我到仰光已是薄暮。機窗下,不再是一片雲南的紅褐,綠色叢林點綴著金色佛塔和瓦楞鐵屋頂的平房,大小不等的水塘與河湖,泛著雲影的稻田,豬腸一樣細窄的公路,火柴盒一樣的零星車輛。「這個國家看上去很多農田嘛!怎麼會窮呢?」坐在後排的中國鄉下人用西南口音告訴同伴,滿腦袋當代中國式的不解。
仰光機場就像昆明機場一樣現代,男廁的小便池放著防臭的綠色衛生丸,足以讓你產生幻覺,以為自己來到一個中等發達的國家。帶著不容置疑的堅決,一美元也不退讓,我告訴中年印裔計程車司機要去市中心獨立紀念碑附近某家旅店。仰光沒我想像的熱,或許我在靠近熱帶的澳門住過多年,回到南國反而令我興奮。「你從哪來?」計程車司機問。這個問題就像日常問候,我隨後天天都會遇到,也很快因為自己的國籍和提問者的沉默而尷尬,不得不隨機改變自己的身分。但是初來乍到,報上國籍,我還察覺不出計程車司機的不置可否。
我要投宿的旅店只剩二十四美元一晚的雙人房。無暇細看仰光鬧市滿街小販遍地吃喝,我在獨立紀念碑和蘇萊塔附近找到棲所:三美元一夜的地鋪,最後一個空位。客棧位於衰敗的殖民時代磚樓第三層,地鋪則在閣樓,四人同居,鄰鋪都是白人男女,兩台電扇一高一低吹著熱風,窗外則是車水馬龍的摩訶班都拉大街(Mahabandoola Road),殘破的仰光巴士,日本淘汰的舊車,車尾的發動機蓋掀起,賽車一般呼嘯而過。一名豐滿的金髮妹跟我一樣剛到,也跟我一樣,總算找到廉價住處。「三美元。還想怎樣?況且我帶了耳塞。」「我也帶了。」她笑道。下到逼仄前台,客棧兩名小廝,來自仰光附近的勃固(Pegu),纏著紗籠,臉上塗著清涼的特納卡(Thanakha),正跟一名上身赤裸圍著浴巾的印度住客講笑。「這是什麼?」中年印度人板起臉,指著小廝臉上的特納卡,自問自答。「你就像非洲人!」
「你是日本人?」一名小廝問我。我笑著搖頭,但他認定我是日本人。兩個小廝跟我講起歪歪扭扭的日語:空巴哇。阿裡嘎多歌紮依馬西達。哦哈喲……
客棧隔壁就是一家啤酒屋,臨著小街,斜對蘇萊塔。這類啤酒屋,通常只有男人光顧,__緬式英語叫作Beer Station,聽來堂皇,實則酒吧的替代物(你在緬甸很少見到真正的酒吧),除了酒,還賣佐酒小食和簡單飯菜。我坐在啤酒屋,喝著一杯緬甸生啤,鄰桌的中年男子在喝一小瓶緬甸威士忌,不時對我微笑,露出檳榔汁染紅的牙齒。身後,一台液晶電視懸在半空,播著一場官式慶典:體育場內,軍樂隊走著隊列奏著軍樂,看台上的男女衣冠楚楚。鏡頭單調,只在軍樂隊和觀眾之間緩慢切換。
「內比都?」我問鄰桌(內比都是緬甸的新首都)。
「內比都。」他點點頭,幾乎講不了英語。他長得不好看,甚至有點「樣衰」,讓你想到書中讀到的官方密探,幾年前遍布該國茶室與啤酒屋,偷聽食客閒談,舉報「不軌」言論。對當局的任何公開不滿都會引來麻煩,哪怕幾句調侃。上個世紀九○年代,一位著名的緬甸喜劇演員講了一個笑話,說自己買了一台彩色電視,搬回家發現彩色電視只有兩種顏色:綠色和橙色(綠色是軍人,橙色是僧人)。他諷刺電視裡將軍向僧人捐贈財物積累功德的「善舉」沒完沒了。表演結束,這名演員被捕,在仰光北郊的永盛監獄待了五年。
「嗯!」「密探」一臉通紅,啞巴一樣發聲,把一小碟炒蠶豆遞到我面前,要我嘗嘗。斜對一桌來了幾個印裔緬甸人,說著,笑著,其中一人,厚厚一疊緬幣用橡皮筋捆紮,通貨膨脹一般,別在圍著紗籠的腰間。見你張望,對方也會回望,微笑,點頭,哈囉,沒有我來的國度那些國民的目光躲閃表情僵硬。等我吃完一碗湯麵,灌完三杯生啤,「密探」也搖搖晃晃,徑直買單走人,沒有道別,彷彿真的是個趕著回去交差的密探。
不到九點,仰光已經打著呵欠。蘇萊塔旁的摩訶班都拉大街路燈昏暗,商店十門九閉,街邊發電機轟鳴。殘破的大小巴士猛然煞到路旁,車上負責收錢的男子,長臂猿一般,半身懸出門外,高聲兜著最後的生意。然而人未散盡,每條窄巷的巷口,都是印度人的露天食檔、檳榔攤和菸攤(我的住處靠近印度人社區)。廢墟一樣的街道,凹凸不平,危機四伏。
我在街邊一處還算明亮的冷飲攤坐下,喝著雪糕、草莓和小粒果凍混合的泡露達,研究電子版的旅行指南。冷飲攤的主人,一位將近六十的瘦小男子,突然湊近,友好、怯生,指著Kindle 用英語問我:「這是什麼?」
「這是電子書。」
「這是什麼?」他指向我放在桌上包裝精巧的小包紙巾,來自另一世界。
「這是紙巾。」內心惻然,我翻出電子書中翁山蘇姬最新傳記的封面照片給他看。他咧著嘴笑,像個憨厚的老農。
(待續)
這個緬甸
開場白
緬甸在變。在仰光三十七街小小的蒲甘書店(Bagan Book House),你幾乎找得到所有關於緬甸的英文書,從撣邦歷史孟邦(Mon State)歷史到英國人廢黜的熱寶王朝,從蒲甘的興衰到極其怪異的新首都內比都,從翁山蘇姬到不受歡迎的丹瑞將軍,從西方人寫的緬甸遊記到緬甸女作家用英文寫的緬甸遊記……「沒錯,影印本占多數,但誰在乎。」我告訴店內偶遇的一位六十開外的美國攝影師;我們聊起書架上幾本讀過的傳記、遊記和地緣政治論著,如逢知己。
蒲甘書店的老闆是位矮胖的中年人,和善,卻又不乏生意人的精明。五天前初次光顧...
作者序
一
二○一五年八月,即將第二次去緬甸,我為本書〈這個緬甸〉一文的後記加了一段註腳:
時至二○一五年,緬甸的絕大部分政治犯早已出獄,但是該國的改革進程又有新的倒退。當局仍然不時騷擾、恐嚇和檢控非官方傳媒的從業者。緬甸的穆斯林少數族裔羅興亞人(Rohingya)繼續受到歧視和迫害,基本權利不得保障。二○一五年十一月八日,緬甸將要舉行全國大選,正式結束持續將近五十年的軍人統治。然而,根據之前軍方支持的國會制定的憲法(這一憲法的修訂,也為軍方控制的國會否決),因為兩個兒子持有英國護照,翁山蘇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NLD)即使大獲全勝,她也不可能就任下一屆緬甸總統。出於政治和大選考量,翁山蘇姬也不復舊我,從英勇無畏的民主英雄變成深思熟慮的政壇精英。她對羅興亞穆斯林命運的沉默不語,她對國內激進佛教徒諸多偏執言行的沉默不語,她訪問北京時,公開場合絕口不提中國當局關押的另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都讓不少人困惑,以至失望。
半年多以後,等我第二次離開緬甸,上面這段話跟現實的出入不是太大。翁山蘇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NLD)的確不負眾望大獲全勝。因為憲法掣肘,她沒當成緬甸總統,而是出任特意為她設立的新職位「國事顧問」(State Counsellor);如她所願,實權「超越總統」(above the President)。NLD主導的新政府上台,繼續推行各項改革,西方資本也不斷進入。仰光到處建築樓盤,蘇萊塔附近新開了高聳入雲的蘇萊香格里拉酒店,緬甸有了第一家KFC炸雞店,人頭攢動的翁山市場一旁,外資的百盛(Parkson)購物中心向為數不多的本土中產階級敞開消費主義的懷抱……根據國際傳媒報導,仰光的寫字樓和公寓租金,已經超越相對富裕的曼谷等亞洲大都會。
然而,這只是部分現實。除了軍方要員及其附庸,多數緬甸國民依舊艱難謀生,並未真正得益。離開投資熱點仰光,無論基礎建設還是城鄉風貌,緬甸仍是東南亞乃至全球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意氣風發的翁山蘇姬和新政府任重道遠,因為國事顧問雖然「超越總統」,退居幕後的緬甸軍方依然不可撼動。不管是旨在結束政府軍和少數族裔武裝衝突的和解談判,還是最終建立三權分立文官治理的民主政體,翁山蘇姬都得顧及軍方的反應和利益。再有,舉世矚目的「緬甸之春」,既讓廣大民眾有了初步的言論自由和其他自由,也讓一度沉寂的民族主義情緒肆意滋長。近幾年,國內的佛教極端主義者不斷發表敵視穆斯林等少數族裔的蠱惑言論,族群衝突或流血事件時有發生。
瀏覽國際傳媒關於緬甸的近期報導,你會發現一個特點:「緬甸之春」不再居於首位,更多則是前幾年世人鮮知的穆斯林少數族裔羅興亞人的遭遇。為數大約一百萬,羅興亞人世代居住在緬甸的若開邦西部,但是長期不被當局視為國民。二○一二年若開邦爆發的族群衝突,更讓十萬多人流離失所。二○一六年十月,緬甸當局開始「清剿」羅興亞武裝分子以來,軍警強姦燒殺的消息卻不斷傳出,迄今已有七萬多羅興亞人逃往相鄰的孟加拉。面對國際社會的指責,包括同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圖圖主教等人的呼籲,翁山蘇姬保持罕有的沉默,當局也不讓國際媒體前往若開邦調查真相。儘管國事顧問和新政府對軍方的影響力有限,這一姿態,尤其是執政黨全國民主聯盟的發言人新近指責虐殺報導誇大,認為事件屬於「內政」,卻讓緬甸當局漸趨開明的國際形象再度打了折扣。
遺憾的是,身為獨立旅行者,資費和行程安排常常捉襟見肘,兩次到緬甸,我都沒能去成偏遠的若開邦,因為來回得坐飛機,加之當局以安全等理由限制外國人前往「敏感」地區(包括仍為少數族裔武裝割據的諸多邊境地帶)。二○一六年重訪,我在撣邦南部的格勞(Kalaw)遇到兩位年輕的西方旅人,他們很想去若開邦探訪穆斯林難民營,也因路途遙遠,而且擔心當局限制,不敢貿然成行。
儘管羅興亞人這一族群名稱也不為緬甸官方認可(當局稱之為Bengali,即孟加拉人),在緬甸旅行,羅興亞人一詞,還是不時闖入你的耳膜。在南部的孟眉(Moulmein),薩爾溫江大橋旁塵土飛揚的路邊奶茶鋪,幾個扮相很酷的年輕人跟我搭訕,我問一位黝黑後生是哪個民族,其他幾個擠眉弄眼道:「他是羅興亞人!」顯然,這不是恭維。在更南的土瓦(Dawei),靠近馬來半島,坐在一家中檔餐廳的草坪飯桌旁,我和兩位偶遇的緬甸人聊到夜深。一個是緬族畫家兼導遊,一個是克倫族小商人。說起羅興亞人,念過大學的克倫族激烈否認他們是緬甸人;畫家兼導遊比較溫和,只說Daw Suu(緬甸人對翁山蘇姬的尊稱)很為難,夾在軍方和反穆斯林的激進佛教徒之間,要給她時間。
第二次去緬甸,我的另一個遺憾,則是沒能見到上過《時代週刊》封面人物的那位曼德勒(Mandalay)中年僧人維拉圖(Wirathu),聽他發表針對相較平和的緬甸穆斯林的敵視言論。間隔不過一個月,兩次騎單車去到維拉圖駐錫的曼德勒遠郊寺院,我都失望而歸。第一次,我在寬廣寺院閒逛,端詳那尊酷似倫敦大笨鐘的怪異鐘樓,審視維拉圖居處門外那幅看板,圖文並茂,緬英雙語,展示ISIS 等回教極端主義組織的恐怖暴行(擺在一座佛寺,比那尊鐘樓還要怪異)。第二次,我登堂入室說明來意,卻因沒請翻譯不獲接見,因為他的隨從用極為基本的英語告訴我,維拉圖不會英語,身邊也沒懂英語的人。也許,這就是一個獨立作家兼獨立旅行者的尷尬,不僅財力和「背景」有限,還需更多歷練。
二
旅行是本書一大主題,作者寫到的,當然不單限於緬甸,也包括近幾年走過的印度、尼泊爾和柬埔寨等國。但我無意也無能為讀者諸君奉上觀光線路和名勝攻略(個人以為,天下並無必看不可的風景,只有你想不想去的地方,譬如在印度旅行,我就一直避開可看可不看的泰姬瑪哈陵,反而去了門可羅雀的尼赫魯故居和世象奇異的回教蘇菲派某位聖徒之墓),而是欲借旅行這一主軸,盡可能從歷史與現實的交織點切入,觀照所到國度的社會變遷與諸多現狀:這也是我現在旅行的首要目的。__
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你不可能通諳所到每一國度的語言,也不可能有四通八達的各類「資源」讓你很快熟知當地(尤其對於不依附大牌媒體機構的獨立旅行者)。反過來講,個人的眼光,卻是我心目中的旅行之最佳「配置」,因為你要的,不是追趕時效的新聞報導或枯燥乏味的政經解析,也不是給扶老攜幼歡喜出遊的大型觀光購物團做前期踩點。身為作家,旅行途中,你的所見所聞所思,都是天然絕妙的寫作素材;把旅行和寫作結合在一起,更是我長久以來一大夢想。
但我並非遊歷豐富經驗老到的旅行家。旅行於我,仍是學藝。多年前,我在葡萄牙管治的澳門居留五年,也去過日本等地,後來又在雲南大理住過兩年,但是本書第一篇長文〈這個緬甸〉,才是我在中國以外第一次真正旅行的結晶。在這之前,我寫過一些在中國旅行的文字,它們可謂本書的「熱身」。得益於這些年我讀過的西方旅行作家(包括寫到旅行的作家),從較早的福樓拜、毛姆、諾曼.劉易斯(Norman Lewis)、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彼得.梅恩(Peter Mayne)到當代的布魯斯.查特文(BruceChatwin)、保羅. 索魯(Paul Theroux)、奈波爾(V. S. Naipaul)、威廉. 達爾林普(William Dalrymple)、派屈克.佛蘭區(Patrick French)等等,我想讓自己筆下的旅行向這些同行看齊,因為他們的眼光,不論所見或大或小,正是前面我說到的個人眼光,或者,說得更專業,有著寬廣視野的作家之獨立眼光。
然而,對於普通人,除了商務一類出差,旅行(包括旅遊)的確也有不同或交叉類別:度假、覽勝、購物、探險、野營、蜜月、消遣,乃至拿著失業救濟金的先進國家公民滿世界晃蕩,所謂global trotter(環球旅行者)。我的旅行已如上述,更多是為寫作。出於個人興趣或偏執,我對常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問題或「落後」國度的興趣,遠遠大於多數人趨之若鶩的瑕不掩瑜之先進國度,因為前者給你更多精彩獨到的素材,所謂報憂不報喜,也正是這個意思。這麼說,並非等於把旅行和寫作的樂趣建基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英文的確也有slumming 一字),而是問題和「落後」更需關注乃至關懷,自己也更擅長從中尋覓題材。如果我能自由選擇,前往旅行和寫作都能挑戰極限的地方,阿富汗和厄立垂亞這類國家,可能會是我的首選。
只是,且不說旅行所需的物資儲備,對於一個第三世界專制國度的窮作家(中國即使步入「盛世」,諸多民生指標仍屬發展中國家,中國護照的簽證自由度更是國際排名居後),既不投靠官方機構,也不依附官商合謀的各類文化團體,旅行卻有更多限制,不比開放社會的自由公民一本護照暢行天下。我的旅行,只能像苦心經營的小本買賣人,做一單生意,算一單生意。
即使如此,你也可以因地制宜,哪怕來自第三世界,去的地方多半也屬第三世界,同樣可以給你文化衝擊,讓你有所對比(譬如,我就覺得緬甸的VIP長途巴士比中國的同類汽車舒適人道;一度同屬獨裁體制,篤信佛教更加貧窮的緬甸民眾,普遍也比相對富足的中國民眾樂於助人);尤其是在全球化和氣候變遷的今天,所謂落後國度經歷的劇烈震盪前所未有,很有可能,過些年重訪,我寫到的仰光就會面目全非,就像過去一百年,巴黎依然是巴黎,但北京早已不是北京。
旅行也有諸多局限,我在本書〈這個緬甸〉的後記中寫道:「不同於長居某處,旅行要義在於流動。這個流動過程,讓你不斷遇到人和事。它們難免浮淺,但是好比一幅拼圖,讓你慢慢看到整體。旅行也是暫時忘掉自我的最佳方式……旅行也有悖論:做外國人總是比做本國人容易。不論動身之前讀過多少相關論著,你看到的另一個國度,總是隔了一層玻璃。」
但是經驗稍多,我已不再滿足於躁動症一般不停流動的旅行,也不安於做一個旁觀的外國人。今後不管去哪裡,我更希望自己能像已故的英國作家彼得.梅恩那般:上個世紀中葉,印、巴分治後,他辭去巴基斯坦政府的職位,移居北非的摩洛哥,住進普通民居,學習阿拉伯語,跟本地人打成一片。梅恩後來在《馬拉喀什一年》(A Year in Marrakesh)中寫道,自己騎著單車,頂著烈日在舊城兜圈,乃是為了吸收它的形狀、聲音和氣味,「這要好多個月,然後我會突然擁有這個地方。它會成為我的—或者,不管怎樣,我會成為它的一部分,兩者沒有區別」。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一
二○一五年八月,即將第二次去緬甸,我為本書〈這個緬甸〉一文的後記加了一段註腳:
時至二○一五年,緬甸的絕大部分政治犯早已出獄,但是該國的改革進程又有新的倒退。當局仍然不時騷擾、恐嚇和檢控非官方傳媒的從業者。緬甸的穆斯林少數族裔羅興亞人(Rohingya)繼續受到歧視和迫害,基本權利不得保障。二○一五年十一月八日,緬甸將要舉行全國大選,正式結束持續將近五十年的軍人統治。然而,根據之前軍方支持的國會制定的憲法(這一憲法的修訂,也為軍方控制的國會否決),因為兩個兒子持有英國護照,翁山蘇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
目錄
自序
這個緬甸
波爾布特的叢林小屋
S-21,金邊
杜克同志二三事
高棉人的快樂指數
金邊的示威
柬埔寨會讓你心碎
跟緬甸火車一起跳舞
歐威爾那段緬甸歲月
格勞的小酒館
孟眉的金覺先生
加爾各答
清潔印度
洛迪花園的情侶
你買不了幸福,但你可以買書
印度好人
另一個西藏
自序
這個緬甸
波爾布特的叢林小屋
S-21,金邊
杜克同志二三事
高棉人的快樂指數
金邊的示威
柬埔寨會讓你心碎
跟緬甸火車一起跳舞
歐威爾那段緬甸歲月
格勞的小酒館
孟眉的金覺先生
加爾各答
清潔印度
洛迪花園的情侶
你買不了幸福,但你可以買書
印度好人
另一個西藏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9收藏
9收藏

 11二手徵求有驚喜
11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