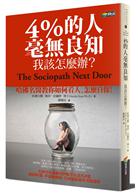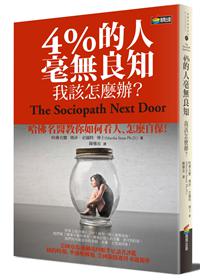◇人生就是不斷的失去。記錄失去摯愛之人如何面對人生的故事。
◇關於愛的禱詞,描繪愛情的不同形式,質疑愛是否有終止之日,展現愛之中對過去與未來的包容、接納、坦然。
◇養育男孩的男人講述男人對女人的施加的暴力,以及暴力留下的傷痕。
活著的人承受傷痕。
摯愛離開他兩次:分手、死亡。
十三年生死契闊,今夜他要向幽魂好好道別。
2016法國花神文學獎入圍‧凝視傷痛,深情告白
塞繆有兩個生日:脫離母體那日、遇見瑪麗那日。她是塞繆愛過的第一個女人,是他的妻子,是兒子的母親。他失去瑪麗兩次:她愛上了別人、她死於那個別人的拳下。
那個男人以愛之名施加在女人身上的暴力,由這個深愛她的男人來承擔苦果。眾聲喧囂中,塞繆帶著稚子面對死亡、輿論、譏諷、羞辱。他也像是個失親的孩子,在一瞬間長大,又即刻老去。
十三年後這一夜,瑪麗來到塞繆床邊。他帶著她在巴黎漫步,走過那些見證兩人愛情與心碎的場所。從夜晚到清晨,他向亡妻傾訴,回顧同享的歡樂與傷痛,細數她出走後父子倆的生活。如夢如禱詞的語句一步步逼近心底那道傷,觸及瑪麗離世的那天,訴說丟失摯愛後的人生……
愛情逝去後能否還有愛?關於愛的不同樣貌,關於愛攙雜的苦痛,關於過去,關於失去,關於死亡,關於生命的故事。
「不要想著再也見不到的事物,想想那些還在身邊的,例如愛還有痛楚。剝去死亡,剩下的部分才是人生。」
「我愛著,而對妳的愛不間斷。」
作者簡介:
塞繆‧本榭特里特Samuel Benchetrit
法國作家、劇作家、導演、演員,一九七三年出生於巴黎郊區城鎮馬恩河畔尚皮尼(Champigny-sur-Marne),十五歲便結束學業展開職業生涯,做過攝影助理、電影院領位員等各種工作。一九九五年開始編導電影,二○○○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說。
曾編導《珍妮絲與約翰》(Janis et John)、《黑道快餐店》(J’ai toujours rêvé d’être un gangster)、《吉諾》(Chez Gino)、《旅行》(Un voyage)、《寂寞心房客》(Asphalte)等片;出版過《閒人手記》(Récit d’un branleur)、《瀝青年代記》(Chroniques de l’asphalte)、《誠心在外》(Le Cœur en dehors)、《狗》(Chien)等小說,以及舞台劇劇本《月台上的喜劇》(Comédie sur un quai de gare)、《負二》(Moins deux)。
二○○八年推出的電影《黑道快餐店》曾獲日舞影展與盧米埃獎最佳劇本獎肯定,《誠心在外》則在二○○九年獲得大眾小說大獎 Prix Eugène-Dabit du roman populiste。
本書封面圖由作者親繪。
譯者簡介:
陳思潔
台北人,譯有《泰芮絲的寂愛人生》。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塞繆‧本榭特里特成功地逗笑我們、軟化我們的心、帶領我們進入故事之中;儘管這故事實際上充滿暴力與傷悲,最後在讀者心中卻留下了華美的泡沫。……這是對已逝之人致獻的崇高敬意。──ELLE
出色的一本書,精準呈現塞繆‧本榭特里特的好脾性、價值觀與這一路的苦行修練。美妙的一本書,毫不虛偽造作,極為謹慎自制。……將單一悲劇提升至普世層次,墨色之血不只承載不幸,而是流進人心深處,感動眾人。──《費加洛報》
本書是篇強而有力的證詞,也是生命力旺盛的文學作品,帶著如夢的語調。《與亡妻共度的夜晚》是挑戰死亡的愛情宣言。──L’EXPRESS
這無疑是最揪心的情書,寫給亡者的情書,筆尖的墨水沾染著憤怒,也帶著無法被時間稀釋的傷感麻木。──le Parisien
名人推薦:塞繆‧本榭特里特成功地逗笑我們、軟化我們的心、帶領我們進入故事之中;儘管這故事實際上充滿暴力與傷悲,最後在讀者心中卻留下了華美的泡沫。……這是對已逝之人致獻的崇高敬意。──ELLE
出色的一本書,精準呈現塞繆‧本榭特里特的好脾性、價值觀與這一路的苦行修練。美妙的一本書,毫不虛偽造作,極為謹慎自制。……將單一悲劇提升至普世層次,墨色之血不只承載不幸,而是流進人心深處,感動眾人。──《費加洛報》
本書是篇強而有力的證詞,也是生命力旺盛的文學作品,帶著如夢的語調。《與亡妻共度的夜晚》是挑戰死亡...
章節試閱
她叫作瑪麗,四十一歲,膚色如潔淨的衣物般白皙,披落著一頭黑髮。深夜的某些時刻,她會戴著夏葉與藍紫色小花編的細花冠。她總是穿著那件洋裝,寬鬆,長袖,布料是綠色的天鵝絨,那是件帶著印度風情的洋裝(一款印度女子會穿著的洋裝──印度製造)。她會赤裸著雙足,吸菸。她不需現身,她就在那邊,在我雙腳旁的床沿,雙眼始終凝視著我。她不需要移動,便逕自顯影在每一個我眼神觸及的角落。她認得,她認得白晝,但僅於夜深時分前來,在清晨將臨時離開。她會認得時間、季節。她會歌唱,在一片寂靜裡,低喃旋律。她不再記得那些歌詞,大部分人的名字,城市以及旅行。她會珍視眼前的一切、每一位無可取代的人、每一分喟嘆與輕息。她會微笑。
夜
妳來了嗎?我沒有真的睡著,但我想我做了夢。我在找我的氣息,尋找我曾丟失的空氣,妳知道那些空氣去哪了嗎?我呼吸別人的呼吸,移植空氣。但妳知道那不一樣,來自他人的氣息不會那樣純淨、清新。在那之後我的身體像缺了水般燥熱,在哪之後?妳走了之後嗎?不,妳是空的存在,即使妳會在深夜時分到來。在一片蔭滿枝枒的樹影下,妳曾說過我是對的,人並不善良。我們自生下本就無愛,妳相信嗎?愛是擁有還是落空?愛真的存在嗎?我愛著一個女孩,因為如此妳出現在這嗎?其實,我正想起身晃晃。城市。氣喘。妳來跟我作伴吧。總之我只是想路人看著我走在街上喃喃自語。妳知道,我習慣回望人群。那些尿漬宛如雲朵,形似某些事物。尿液自人行道上消散會成為什麼?雲嗎?尿就是尿。而雲朵,只是一攤水。我遲早會殺死某個傢伙,為他們實在醜惡的面容。我不會殺掉那個殺了妳的人。爛命一條。但我很想痛扁他一頓。就像上回和R走在路上,以為那個坐在該死的蒙馬特該死的露天座椅上的是他,我像瘋子一樣地跑過去,死命地喘,胡亂地抓了一把破椅,想劈開他那顆掛著耳環的該死的腦袋。但那不是他。整座城市遍布水井,地面濕滑。路人彼此相似,像雲朵像尿水的形狀。如果我能重置一張臉,我會請求長得狀似一朵花或是一泡尿。有時候,我為擁有鼻子、一張嘴以及一雙眼而感到羞恥。拳擊,被啃齧的指尖,在相互毀傷的舉止中充盈著愛。我凝視的不是那些扭腰擺臀的姿態或碧綠色的瞳孔,而是那切割的尖銳,劃開的傷口,皮膚上深邃的窟窿。
妳不是第一個來到我房間的女人。我不是指那些有著美麗瞳孔與臀部的女性軀體,而是魂魄。到底是誰說逝者比生者來得美好?得要像神父般的人才能說出這樣的話。大概只剩不死之人才能告訴我該做些什麼,確實存在永生之人,我遇過一位,那時他也不過活了一千多年。關於這件事,他要求我緘口保密,但我對妳說了,因為妳已死去而我在顫抖。總之那位活了千年的男人和我說了一些該做的事。不要背對風口。我想當孩子手上的一紙風箏。外頭下著雨,是妳正偕著雨水散步嗎?我不討厭下雨天,落雨穩重而且來自天空。此刻妳在哪裡生活?妳見過耶穌嗎?我見過一次,在夢中。夢見我們彼此牽手仰著身軀游過水面。隔天我去了泳池,獨自泅泳,哀傷難過。那些人都不友善,或者太過迷信。死掉的人會做夢嗎?對於生命,還存有遺憾嗎?會迅速遺忘生前記憶嗎?妳會感到飢餓嗎?而我,不再想出門。下著雨,那些人就不會看著我喃喃自語。雨滴,讓整座世界傾斜。陽光讓一切事物溫熱,但我不太喜歡。我會融化,會灼傷。我也不喜歡人們開心的模樣,我寧可他們痛苦、折磨。妳是來看我的嗎?我們的兒子睡在樓上。我跟他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他現在長得比妳疊在我肩上還高大。這些日子妳都在哪?妳還抽菸嗎?讓我看看妳雙腳的模樣吧,我知道,它們不再一如以往地美麗。反正,心靈困乏的人才需要美,尤其有雙美麗的腳最重要。何況,我們的兒子見過其他部分,他見過妳皮表下的內在。我從來不敢提及,怕他勾起回憶。妳是如此地美麗,以致整座世界在頃刻間顯得醜陋無比。妳的心是否仍舊跳動?若可以,我想錄下所有我愛的人的心跳。不是照片。影像。髮絲。而是心跳。聲音。腳步。孩子的笑。奇蹟在哪裡?我常常尋找妳,尤其在一開始,我尋找著妳,分分秒秒,透著玻璃窗,在飛馳之際,時速三百公里讓人看不清介乎尼姆與巴黎間的鄉村人群,讓人看見那些不存在的人影。我有顆寬闊包容的心,妳似乎這樣說過。還有一次深夜走在路上,走在杜果街頭,走過拉法葉百貨與巴黎以外的省區,妳就在我背後,我沒有轉過身去生怕妳就在那裡。以前都是我跟著妳,以前我們生活的時候,妳出門走走而我依附在後,我跟著我的妻子與藍色購物袋。妳想泡個澡嗎?活著的人牽掛死去的人比死去的人牽掛活著的人多。我們有鐘聲有慶典,而你們什麼也沒有為我們做。至少,我是這麼覺得。只有痛楚與佔據地下的幽晦。哀傷與痛苦之間有什麼分別?我喜歡感到痛苦,它讓我覺得靠妳很近,這是妳害的。我想撒尿。我現在要跟妳說些事,讓妳知道妳死後都發生了一些什麼。我先是成為了世界泰拳冠軍,我很想讓妳看看他們給的獎盃;但我因為非法販運鑽石被關進美墨邊境提華納的監獄,那時用它換了兩包KENT牌香菸。我在格陵蘭生活了五年,吃釣來的魚維生,我們的兒子搭雪橇去上課。我重新為瘖啞者發聲為盲人開電影院。對,我做了這些事。妳呢?妳都做了什麼?妳看了電影嗎?我看了幾部妳應該會喜歡的作品。妳知道伯格曼和費里尼曾宣布會合作拍片嗎?他們後來拍了嗎?內容在講什麼?還有繼續嗎?我的腳邊好熱,妳不願將壓在被毯上的身子挪開一些,是妳讓我感到窒息。妳是第一個在我身旁睡在這一側的女孩。我還維持這個習慣。不過我現在愛的女孩也睡在這一側。我們暫時睡在一起彼此交疊,有時候會太熱,但我們愛著對方。總有一天,我會滑下床,留給她我的位置。但我不會給她任何承諾。有些事似乎不要說出口,這是妳教會我的。
「我曾經隨時都對妳說我愛妳,隨時隨地。」
對,但它不具意義,重要的字眼都不具任何意涵。一塊麵包就有意義,我們切開然後吃掉。吸一根菸也是,點燃然後抽菸。但是愛就像新年,新年快樂然後呢?沒有意義。你們那裡過聖誕節嗎?妳離開後的第一年,兒子想要妳當作禮物。他收到一套蝙蝠俠裝和一台腳踏車,我教他怎麼騎。這,就具有一些意義。一台腳踏車,我們騎在上面然後奔馳。妳不具意義。如同愛情,妳不帶任何意思。如同時間。血。希望。空氣。夢。海。妳不具意義。愛情的痛苦具有意義,如同手錶的針指向時間,針筒的尖頭抽出血,二十二萬七千歐元附帶百分之七的利息分期二十年的房貸給人擁有這座房子的希望。冬天自孩童口中呼出結成冰的白霧,早晨洗去汗水的淋浴,七月海水浴後我們從皮膚上舔舐的鹽。我相信愛並且相信伴隨而來的痛苦,以及其他的愛與其他的痛苦。我只為痛苦為繼續感受妳而愛。我們曾經開拓過一片多麼美好的寬廣園地,我持續地澆灌,以穢物施肥,一切垂敗發臭的物質。我是這座莊園之主,受人尊重,在這裡,我很好。出了這裡,我假裝自己很好,我經常笑,我經常說:好的,好的……天氣真好,很舒服……人們的目光很重要……反對個人主義……謝謝您,女士,您人真好……你等下要一起喝杯東西嗎?我很開心見到你。對,我說開心。妳並沒有奪走我全部的感受。我也說:我愛你……我真的愛你……我很喜歡你們。我發誓這都是真心,我的心是滿的,在這裡,我不是存活,我是殘活。抄襲著別人的舉止。我的模仿天賦至少足以讓我去演電視劇。我仿擬的不是聲音,而是心。笑聲。失落。溫柔。熱情。先生不好意思您的牛肝味道如何。素食主義。集體主義。疾病。痊癒。哀悼。羞恥。積極傳教。勇氣與寬容。人們施加和承受的暴力。原諒。不,這個部分我要保留,原諒屬於我,它由我創造,充盈著我,自我內部蔓生,溢出潰流如河川淹沒水壩。我模仿剩下的,一切其他,這裡或那裡,此刻與昨日,最靠近以及最遠極端的人事。但我只複印複印機,一座疊一座,堆得比高塔還高的機器。在這片惡物荒園,廢棄砂礫堆疊成高聳顯著的山景,我日日傾注酸雨,在那些該死的深夜傾瀉。我一直走著,沒有停留。在這兩個世界,我們的與他們的,我行走著,以迴環反覆的方式,斂手低垂著頭。在我們的田園之外,我只在周邊徘徊,沿著曲折的圍欄,僅僅透過真實劃定邊界。
「讓我看看那座田園。」
只有悄悄依隨妳走在妳的街道,我才會直直前行,我那時曾掌握訣竅──重擊的經驗,一如成為拳擊手冠軍,並非由於出色的拳技,而是對疼痛的記憶。走在喧騰的街心,我相隔五或十公尺的距離跟隨妳,荒無人煙的空巷,二十到三十公尺的距離。廣場,則視人潮而定,四分之一、半圓或四分之三的弧度。我跟隨妳,在輕霧中聽著妳的步伐,在狹小街道間嗅著氣味,這是妳的味道嗎?我嗅不出來,死亡的氣息卻存在。而妳,帶著這個氣息,讓我心痛。心痛,為妳是我兒子的母親,為兒子對死亡一無所知被蒙在鼓裡。是否有人從未感受到死亡的氣息一如有些人嗅不出腳臭?不過,有味道沒關係的,對吧?殘酷的是我們無法擁有氣味。妳死後的某日,我去了絲芙蘭香水店,向店員要了一小瓶紀梵希的淡香水紳士。我的手埋在口袋中,握緊手心裡的瓶子。終於,我能聞見妳。只要我想,妳就在那,或許就在那百萬分之一秒,僅在開啟瓶口靠近鼻翼的瞬間,妳的身軀、黑髮、無限的笑靨全數湧現,迷失在百萬分之一的秒時微粒裡,於倏忽間轉瞬即逝。如此浮影生命的渴望,還會有誰在意?然而一天之中我也僅能讓妳浮現一或兩次,妳的一切最後都散逸在香氣盡頭。味道使人習慣,死亡亦然。妳只在不預期之際到來,在我不自覺地舉起手拂過鼻尖之時。冬天則凍結靜止──鼻塞。這一切只能在腦海中顯影,腦海底。愛、罪惡、灼傷、撞擊殘留下的一切,在腦海。插入黃色管子的妳破碎的臉龐,在腦海。就在今早包圍環抱著我的妳的聲音,在腦海。妳的笑聲,在腦海。不對,我曾錄下妳的笑聲。妳想聽聽妳生前如何綻放笑容嗎?
我的房裡有張書桌,我偶爾坐在那工作,右邊第二格抽屜為妳保留。
照片,我們的婚禮,戒指,一張從未寄出的南法卡西斯海灣的明信片,妳一九九八年的記事本,一只妳送給我的錶,妳送我的鋼筆,一些信,一支錄音筆。
聽,聽聽妳的笑聲,親愛的。或許時間早已斑駁了妳的聲線,但總聊勝於無。科技不就是這點用處,讓過去重活,製造一個能更深刻記憶痛苦的來日。物形如此哀傷,方程式僅只驗證了我們的悲惆,我們何以數學極差?出於恐懼?黑板晦暗,深夜裡殘舊的粉筆,正是我們的模樣。昔日潔白閃耀的純真,激昂的騷響,無所憂懼,無憂錯誤,無懼結束。所有我們曾構築的堅實信念,瓦解成灰,如滑石粉、骨灰、沙,海灘即是墓園。或許該讓妳長眠於此。抱歉,好抱歉,我早該想到。可妳讓我厭惡大海,我好久沒見過海,我一直迴避逃離。目視平地,海水退流,陸塊分離,浪濤是一種壓抑,潮汐褪去的陸面如此相似於我們憂傷的田園。 萬物於此敗亡,海灘癲癇般地口吐泡沫,潮濕的魚鱗,顫抖的眼珠,魚刺、骸骨、石頭的記憶,褪逝的色澤。那些是昔日海風吹拂後剩餘的事物,潮水為此撤退,展露它死亡的面容,宛如愛與隱藏於愛背後的痛苦。但我不在乎,我喜歡這麼說,這是妳父親教我的。我痛,痛將我狠狠燒灼。他說你只管麻木自己。字句箴言,是好解藥,但談何容易,而藥物用途不正是如此,讓人成功地自我麻痺。需要一種人生,麻木度日。或者歷經戰爭。死亡是否悲傷?是否始終持續?死了以後還會有什麼?後悔嗎?
在妳死後,我和兒子也出走,來到這個有著靠海露台的海邊小屋,小屋比露台還小。我只在深夜出門,在兒子熟睡之際。我知道海就在我前方蔓延,桅杆帆影掛著幾盞小燈,倒映的月光讓我想起海的遼闊,似一襲黑袍沒入我心海裡,靈魂之鏡。與兒子沙灘共度的白日,他挖著洞,戴著小小的帽子,帽緣壓得低低,一路垂到耳部。你在做什麼?我在找媽媽。我停格在他臉前,盡可能地貼近。特寫。讓其餘一切顯得模糊,沒有景深,這樣比較好。遠離人群,遠離住屋,遠離家庭、船隻、倒影、笑聲、生活。自眼前的事物重新開始,從面前一公分處開始,從簡單的字眼開始:早安、吃飯、抱抱、喝、睡覺覺。重來。早安、吃飯、抱抱、喝、睡覺覺……我們重新降生。夜裡,我鍛鍊背肌,為了能繼續背著他走。妳覺得我迷人嗎?如果妳是第一次見我,會不會喜歡我?妳在冥間有男人嗎?最後一夜,魔鬼曾來到屋裡,他是旅者也是航員,潛進我們兒子沉睡的房間,來到他的床沿,自他微啟的口中滲入搖晃他的肺。咳嗽轉成一場風暴,猛烈,憤怒──我始終無法讓他靜下來。破曉,他最後的幾滴眼淚已乾。重新降生,張口第一個字,媽媽,媽媽,媽媽。他之後沒再哭過,再也沒有。我很驕傲,也心碎。在這裡,驕傲與心碎是同樣意思。他是否還有叫過媽媽?也許那是我在做夢。不過,爸爸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字眼。當我在路上聽到這兩個字,依舊會回過頭來。我會在校門口徘徊,只為能夠聽見這兩個字。
爸爸爸爸,走吧走吧,我們出發。
我不相信噩夢,但我相信噩夢般的人生。死神要帶走妳的時刻,妳是否抵抗過?妳最後看到的影像是什麼?男人舉起手來的畫面?銳利堅硬的戒指?猩紅的雙眼?咆哮的嘴臉?最後聽到的字呢?婊子?賤貨?他媽的閉嘴?妳最後說出口的話?住手?不?兒子?塞繆?抱歉,我太自以為是了。痛過你們給的痛,世界帶給我的傷害相對無感。我抽光了所有妳沒抽完的香菸。妳我很清楚不是嗎?總有一天我們就不再相見──我們也只知道未來會這樣。即便如此,我依舊會在深夜輾轉反側無法成眠,想著總有一日我們就再也看不見彼此。而我常覺得那樣很美,我告訴兒子,記住這樣的念頭,不要想著再也見不到的事物,想想那些還在身邊的,例如愛還有痛楚。剝去死亡,剩下的部分才是人生,如同痛從來都不在表面,從不,始終在內心裡頭,就像刮在我們孩子喉嚨深處的暴雨狂風。
妳想吃點什麼嗎?妳喜歡這個房間嗎?這裡從來不是我們的臥房。妳離去後我才經常住在這。有什麼是妳還熟悉的事物?床嗎?不,這張床我三年前才買的,在一間清倉特賣的寢具店,床墊和彈簧床都半價出清。其實,那間店至今還貼著螢光黃的海報,宣傳折扣拍賣與營運困難。為了求財致富而佯裝潦倒窮愁,世道是否早已是這副模樣?我想抽菸,也想吃些東西,也有一些事情想問妳。很重要,真的。畢竟我們不是一天到頭都能遇見死人。看見妳在我面前抽菸,讓我聯想,在心中納悶:死人用的香菸盒上,有沒有寫著吸菸導致死亡?還有,那些肺癌死掉的人還繼續抽菸嗎?還有,如果咳嗽死不了人的話大家會繼續抽嗎?還有,這些日子以來妳都做什麼去了?告訴我,多久了?十二?還是十三年?妳不要跟我說這十三年來妳從沒想過來看我們?妳都去哪了?和誰在一塊?如果妳告訴我是和殺死妳的那個他,我就殺了妳。
她叫作瑪麗,四十一歲,膚色如潔淨的衣物般白皙,披落著一頭黑髮。深夜的某些時刻,她會戴著夏葉與藍紫色小花編的細花冠。她總是穿著那件洋裝,寬鬆,長袖,布料是綠色的天鵝絨,那是件帶著印度風情的洋裝(一款印度女子會穿著的洋裝──印度製造)。她會赤裸著雙足,吸菸。她不需現身,她就在那邊,在我雙腳旁的床沿,雙眼始終凝視著我。她不需要移動,便逕自顯影在每一個我眼神觸及的角落。她認得,她認得白晝,但僅於夜深時分前來,在清晨將臨時離開。她會認得時間、季節。她會歌唱,在一片寂靜裡,低喃旋律。她不再記得那些歌詞,大部...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