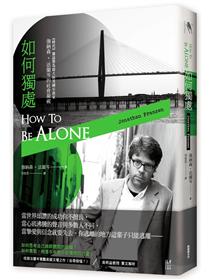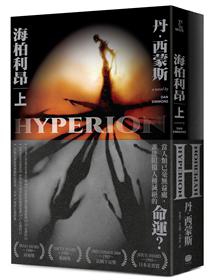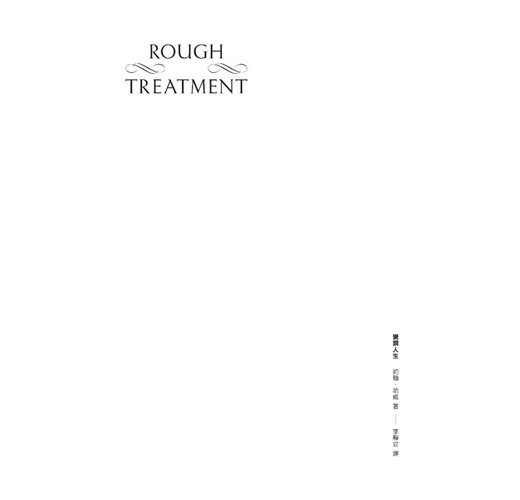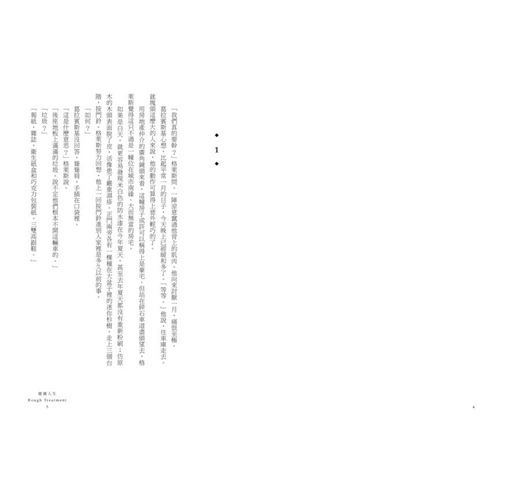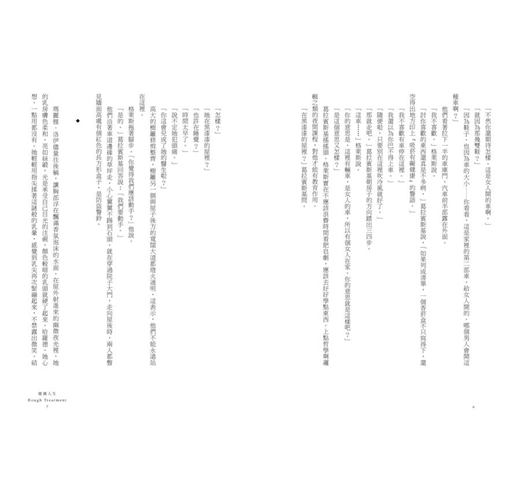"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CWA) 鑽石匕首獎
有史以來最出色的英國警探小說!「一瞬的回眸,人生就此走上不歸的路途。
倘若一切能重來,你還會有同樣的選擇嗎?」
英國犯罪小說天王約翰‧哈威
最知名系列作品「芮尼克探案」第二部
◆ 2005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銀匕首獎
◆ 2005美國《致命的快感》雜誌巴瑞獎
◆ 2007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鑽石匕首獎
在層疊交錯的人物與情感關係中,約翰‧哈威讓筆下警探脫離了絕對的正與邪。沒有人能代表善,也沒有誰全然等同於惡。自典型犯罪小說中,甩脫了正義剛直的一般準則,綻出一朵人性關懷之花。
【內容簡介】
葛拉賓斯基是專業竊賊,與搭檔格萊斯合作無間,手法乾淨俐落,從不留蛛絲馬跡。不工作的時候,葛拉賓斯基是個愛賞鳥、爬山,仗義勇為的好公民。然而,一公斤純古柯鹼的出現,和一場致命的邂逅,他的人生劇本自此改寫……
在這起竊案發生以前,一切看來日常且平和。但你我都曉得,確實有什麼在檯面之下,隱隱策動著暗幕的開端。而從竊案背後連根拔起的,竟是更為棘手的……?
諾丁罕督察芮尼克在平凡無奇的竊案裡嗅到微妙的異常氛圍,一腳踩進演劇圈的爾虞我詐、販毒集團的猖狂橫行、唐人街的家族恩怨裡。深諳人性幽微的芮尼克能不能從龐雜錯綜的零碎資訊裡抽絲剝繭,找出背後的真相?能不能以小惡為代價,揭櫫更為巨大的罪惡呢?
俠盜羅賓遜的故鄉諾丁罕,行俠仗義的故事持續上演……
作者簡介:
約翰‧哈威 John Harvey
1938年出生於倫敦,是小說家,也兼有詩人與劇作家身份。
在諾丁罕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後,曾在中學教授英文與戲劇,後轉而從事專職寫作。並於1980年代返回母校,教授電影與文學。作家生涯創作過百餘部作品,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犯罪推理系列。
尤其又以「查理‧芮尼克探案」系列小說最為膾炙人口。
第一部作品《寂寞芳心》,甫出版便廣受矚目,獲英國BBC改編為影集,並登上英國泰晤士報的二十世紀百大犯罪小說榜。第二部作品《變調人生》,亦入圍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金匕首獎。
2007年,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再度頒發表彰終生成就的鑽石匕首獎,推崇他為「犯罪作家中的犯罪作家」。
譯者簡介:
李靜宜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博士,美國史丹福大學訪問者。曾任職出版社與外交部。譯有《追風箏的孩子》、《燦爛千陽》、《遠山的回音》、《奇想之年》、《史邁利的人馬》、《完美的間諜》、《末日之旅》、《此生如鴿》、《那不勒斯故事》、《極北》、《寂寞芳心》等。
臉書交流頁:靜靜讀一本書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2005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銀匕首獎
◆2005美國《致命的快感》雜誌巴瑞獎
◆2007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鑽石匕首獎
名人推薦:
陳 浩(作家/資深媒體人)
張國立(作家)
黃宗潔(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蘭 萱(資深媒體人/中廣流行網主持人)
聯手推薦
《追風箏的孩子》資深譯者李靜宜翻譯
媒體推薦:
「哈威的警探小說堪稱經典,對人性脆弱面的深刻描繪直逼狄更斯。」──《科克斯書評》
「約翰‧哈威的芮尼克系列是有史以來最出色的英國警探小說。」──《GQ》雜誌
「約翰‧哈威不僅僅是犯罪小說家,更是極其出色的作家,風格獨具。」──約翰‧康納利
「約翰‧哈威以精彩作品證明他是領先群倫的佼佼者。」──麥可‧康納利
「『推理之王』的榮冠,約翰‧哈威當之無愧。」──《泰晤士報》
「若是有人能讓你同情殺人犯,那肯定非約翰.哈威莫屬。因為他總能深入刻劃罪大惡極之徒最為纖細可憫的一面。」──《紐約時報》
「哈威的小說結構嚴謹,人物刻劃生動,讀者除懸疑情節之外,也能讀到幽微人性,滿足閱讀樂趣。」──《文學評論》
得獎紀錄:◆2005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銀匕首獎
◆2005美國《致命的快感》雜誌巴瑞獎
◆2007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鑽石匕首獎名人推薦:陳 浩(作家/資深媒體人)
張國立(作家)
黃宗潔(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蘭 萱(資深媒體人/中廣流行網主持人)
聯手推薦
《追風箏的孩子》資深譯者李靜宜翻譯媒體推薦:「哈威的警探小說堪稱經典,對人性脆弱面的深刻描繪直逼狄更斯。」──《科克斯書評》
「約翰‧哈威的芮尼克系列是有史以來最出色的英國警探小說。」──《GQ》雜誌
「約翰‧哈威不僅僅是犯罪小說家,更是極...
章節試閱
1.
「我們真的要幹?」格萊斯問。一陣涼意竄過他背上的肌肉。他向來討厭一月,痛恨至極。
葛拉賓斯基心想,比起平常一月的日子,今天晚上已經暖和多了。「等等。」他說,往車庫走去。就塊頭這麼大的人來說,他的動作可算得上意外輕巧的了。
用房地產仲介的廣角鏡頭來看,這幢房子或許可以稱得上是豪宅。但站在碎石車道盡頭望去,格萊斯覺得這只不過是一幢位在城市南緣、大而無當的房宅。
如果是白天,就更容易發現米白色的防水漆在今年夏天,甚至去年夏天都沒有重新粉刷;仿原木的木頭表面脫了皮,活像患了嚴重濕疹。正門兩旁各有一棵在大盆子裡的迷你杉樹。走上三個台階,按門鈴。格萊斯努力回想,他上一回按門鈴進別人家裡是多久以前的事。
「如何?」
葛拉賓斯基沒回答,聳聳肩,手插在口袋裡。
「這是什麼意思?」格萊斯說。
「後座地板上滿滿的垃圾。說不定他們根本不開這輛車的。」
「垃圾?」
「報紙,雜誌,衛生紙盒和巧克力包裝紙。三雙高跟鞋。」
「不然你還期待怎樣。這是女人開的車啊。」
「就因為那幾雙鞋?」
「因為鞋子,也因為車的大小─你看看,這是家裡的第二部車,給女人開的。哪個男人會開這種車啊?」
他們看著拉下一半的車庫門,汽車前半部露在外面。
「我不喜歡。」格萊斯說。
「討你喜歡的東西還真是不多咧,」葛拉賓斯基說,「如果列成清單,一個香菸盒不只寫得下,還空得出地方印上『吸菸有礙健康』的警語。」
「我不喜歡有車停在這裡。」
「我還以為你巴不得上車。」
「隨便啦,只要別在這裡吹冷風就好了。」
「那就走吧。」葛拉賓斯基朝房子的方向踏出三四步。
「這車…」格萊斯說。
「你的意思是,這裡有輛車,是女人的車,所以有個女人在家。你的意思就是這樣吧?」
「是這個意思又怎樣?」
葛拉賓斯基搖搖頭。格萊斯實在不應該浪費時間看肥皂劇,應該去好好學點東西。上點哲學啊邏輯之類的夜間課程,對他才能有教育作用。
「在黑漆漆的屋裡?」葛拉賓斯基問。
「怎樣?」
「她在黑漆漆的屋裡?」
「也許在睡覺?」
「時間太早了。」
「說不定她犯頭痛。」
「你這會兒成了她的醫生啦?」
高大的樹籬修剪整齊,樹籬另一側與屋子後方的寬闊大道都燈火通明,這表示,他們不能永遠站在這裡。
格萊斯拖著腳步。「你覺得我們應該動手?」他說。
「是的。」葛拉賓斯基回答說:「我們要動手。」
他們沿著車道邊緣的草坪走,小心翼翼不踢到石頭。就在穿過院子大門,走向屋後時,兩人都瞥見牆面高處有個紅色的長方形盒子,是防盜警鈴。
瑪麗雅‧洛伊儘量往後躺,讓胸部浮在飄滿香氛泡沫的水面。在屋外射進來的幽微夜光裡,她的乳房膚色柔和,亮如絲緞,光是承受自己目光的注視,顏色較暗的乳頭就硬了起來。哈羅德,她心想。一點用都沒有。她輕輕用指尖揉著這謎般的乳暈,感覺到乳頭再次緊繃起來,不禁露出微笑。結婚都十一年了,每次都還是只在床上做愛,這算是什麼婚姻啊?況且,次數還不多。
「沒關係,」她對著自己的乳房輕聲說,「沒關係喔,我可憐的小東西。總會有人愛你的。」
她再次憐愛地用力捏了一次,才坐起來。
「沒關係喔,我可憐的小東西。」
「那是燈嗎?」葛拉賓斯基輕聲問。
「什麼地方?」
「那裡。看見沒?窗簾邊緣。」
「是百葉窗。那是百葉窗。」
「那是燈嗎?」
「不是啦。」
「有可能是蠟燭。」
格萊斯看著他。「說不定她在玩碟仙。」
他用塑膠片邊緣往左邊撥一公分,陽台門就敞開了。
「不然你以為我打電話給你幹嘛?」瑪麗雅對著電話說,「告訴你說我有多愛你?」
袍子底下的身體飄著爽身粉的香味,是紀梵希經典紳士香水的味道。嗯,哈羅德總也還是有優點的,對吧?
「不,哈羅德,」她打斷他的話,「我是打算飛去啊。此時此刻,就在我袍子底下,正有翅膀長出來呢。」
電話旁邊的圓桌上,有半杯葡萄酒,她用拇指和兩根手指端起來。這酒是昨天晚上喝剩的,再不然就是前天晚上,喝起來比以前酸。
「沒錯啊,我當然是自己動手試過了,可就是沒辦法啊。」
她轉頭,對著房間中央吐口煙,話筒雖然離臉遠遠的,但還是聽得見他的聲音,接連不斷。
「哈羅德…」
又一次。
「哈羅德…」
再一次。
「哈羅德,機器老是故障,時間碼總是不見,聲音永遠沒辦法同步。我不知道他們幹嘛把整個公司最蹩腳的配音間給你,可是他們就是這樣。永遠都這樣。是啊,也許他們是想傳達什麼訊息給你。我也想傳達一些訊息給你。我已經洗好澡,等我喝完我的酒─不,這不是什麼烈酒,就只是一杯葡萄酒,而且是劣酒─等我喝完,我就去換衣服,然後,既然我沒辦法把車開出車庫,而你也不會開車來接我,所以我要打電話給傑瑞和思黛拉,叫他們繞過來接我。」
她又吐了幾口煙,嘆嘆氣,聲音大得讓他知道,不管他們之前有過什麼共識,如今她都覺得痛苦不堪。她向來就喜歡清清楚楚讓他知道她的不滿。
「是啊,哈羅德,」她說,「我聽過『計程車』這個名詞。我也聽過『再見』這兩個字。」
她眼睛盯著話筒,掛掉電話,綻開微笑,兩人之間的連結如此輕易地瞬間斷裂,讓她很開心。一舉步,絲裙拂過她的腿輕輕擺動。她穿過廚房,把杯裡的酒倒進水槽,摁熄香菸,放下杯子,又拿起另一只杯子,走回客廳。一排酒瓶站衛兵似的站在電視機和擺放錄影帶、雜誌和平裝書的架子中間。她發現有兩三張邊緣捲起爛兮兮的手稿,從哈羅德用來充當書房的房間跑到這裡來了。她心想,一定要記得叫他拿回去收好。她扭開J&B特選威士忌的瓶蓋,給自己倒了一大杯。雖然有那個爛到爆的車庫,那輛爛到爆的車子,還有打給哈羅德那通爛到爆的電話,但泡過澡之後,她還是覺得舒服極了。
她嘗了一口威士忌,很大的一口,心裡正想著:「去死吧,哈羅德!」一轉頭,放下酒杯,就看見門邊一個男人。
「天哪!」
她左手掩住嘴巴,牙齒深深咬進拇指底端的皮膚裡,她很久沒這樣做了,打從告別童年之後就沒有過。
她整個胃壁有了很奇怪的反應,所有的血液彷彿全沖到頭部。她往後靠在架子上,覺得自己就要暈過去了。
那男人還在原來的地方沒動,彷彿靠在門框上,但其實沒有。他身材魁梧,身高起碼一八○,而且很壯碩,身穿深藍色雙排釦西裝,讓他看起來比實際的身材更胖。他什麼話都沒說,眼睛直勾勾盯著她看,眼裡的那個神色,嗯,這麼說吧,是正在好好欣賞眼前所見的尤物。
「噢,天哪。」瑪麗雅輕聲說,「噢,天哪。」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他一開口,她就嚇得跳起來,經過這一晌沉默之後,他的聲音讓她大吃一驚。她迎向他的目光,不知道─她這會兒肯定是不會暈倒了─她自己該怎麼做或怎麼說。如果她有任何反應,會比較好嗎?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瑪麗雅‧洛伊不知道究竟是他真的又重覆說了一遍,又或者只是這句話在她腦袋裡倒帶而已。
「我們不會……」─短暫停頓─「傷害你的。」
她的手指捏住酒杯,嘴巴好乾,舌頭彷彿黏住了。她知道她想抓住的關鍵字是「傷害」這兩個字,但是在她腦袋裡扎了根似的不肯擺脫的卻是「我們」。
我們。
她拼命制止自己,不轉開視線張望。她豎起耳朵聽,卻什麼都沒聽見。說不定他只是說說而已,為的是讓她更害怕;他很可能只有一個人。
瑪麗雅吸了一小口氣。
這樣會比較好嗎?如果他是隻身一人?
一抹微笑斜斜的掛在臉上,彷彿他真的知道她在想什麼。於是她知道,對他來說,這是家常便飯。他輕鬆自在,這自信來自於練習,練習,再練習。否則他幹嘛微笑?這時她聽見台階傳來的腳步聲,知道他說的「我們」並非謊言。
第二個出現的男子個頭小一些,但也不算矮。他身上的褐色西裝已經磨得有點禿亮了,腳上褐色的鞋很舊,但擦得很亮。這兩個男人年紀差不多,大約四十四、五歲,瑪麗雅猜。和她老公約略同齡,但並不怕表現出真實的年紀。他們不必像他那樣裝年輕,穿有鮮豔商標的拉鍊外套,腳踩價錢高達六十鎊的運動鞋來代替真皮皮鞋。
兩個男人互看一眼。第二名男子慢條斯理,簡直是悠悠晃晃地穿過房間,輕鬆坐在真皮長沙發上。
「地方不錯嘛,」他像是找她閒聊似的說,「給你自己搞了個很不賴的地方喔。」
瑪麗雅的目光來回梭巡,看著他們兩個,一個甩不開的念頭在心底盤旋:他們闖進了她家,這會兒竟然打算買下來,這兩個穿西裝和真皮皮鞋的男子。
瑪麗雅‧洛伊克制不了自己,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克制得了她,她頭往後一仰,哈哈大笑。
他們三人一起坐下。葛拉賓斯基坐在罩著自由百貨公司印花布的扶手椅裡。格萊斯背靠著長沙發另一端的椅背,一臉無聊地望著他們。瑪麗雅‧洛伊坐的是一張直背椅,面對他們兩人,是他們三人形成的三角型頂點。葛拉賓斯基眼裡還是微帶意興的神色,瑪麗雅知道他想循著她的腿往上看,儘量往她絲袍之間瞧去,想搞清楚她袍子底下究竟有沒有穿任何東西。
她驀然發現自己正在想,她剛才套上的是哪一條內褲。不知道,呃,是不是很乾淨。就像想像自己出意外時的情況一樣。她又喝了一口威士忌,免得自己笑得更厲害。她現在碰上的不就是意外嗎,不折不扣的意外。
「你還要再來一杯嗎?」葛拉賓斯基滿懷期待的問。
「她不想再喝一杯。」格萊斯說,再次翹起腿。
「你怎麼知道?」
「現在不是喝酒的時候。」
「這個嘛,我想來一杯。」葛拉賓斯基說,逕自站了起來。他外套的釦子沒扣,瑪麗雅看見衣服底下的身材,就這個年齡的男人來說,身材還真不賴,沒有緊緊束在皮帶底下的大肚腩。哈羅德一週運動三次,白癡也似的在腳踝上綁沙包,卻還是挺著個啤酒肚。
「沒有伏特加,」葛拉賓斯基在酒瓶裡搜尋一番之後,很失望地說。
「不好意思。」瑪麗雅道歉。
「天哪,」格萊斯忿忿說,「這是什麼狀況啊?」
「我們要喝杯酒啊。」葛拉賓斯基不慍不火地說。
「我們是要偷東西耶,這不是我們正在做的事嗎?」格萊斯說,一手的掌心底端用力壓在膝蓋上。
「前幾天有客人來,」瑪麗雅解釋說,「喝光了我們的伏特加,我們還沒去補貨。」她這是在幹嘛?還道歉?
「沒關係,」葛拉賓斯基說,撫慰似的傾身向前。「威士忌也很好。」他拿起瓶子,「特選威士忌。」
格萊斯嘟嚷一聲,葛拉賓斯基倒了三杯威士忌,他自己的杯裡只有一點點酒,不過他還是端到廚房裡去加了點水。到他回來,其餘兩人都還是動也不動。
「我們喝了酒還能幹嘛?」格萊斯開始發牢騷。
葛拉賓斯基給他酒,也把瑪麗雅的杯子遞給她,然後坐回椅子裡。「放輕鬆,」他說,「我們會搞定的。有什麼好急的?」
他真希望格萊斯去走走,逛逛這房子的其他地方,行行好,去偷點東西吧。他覺得這樣應該還不賴,對他自己和這個女人來說─她說她叫什麼來著,瑪麗雅?那雙腿修長得像沒個盡頭哪。他敢說,她袍子底下就算有穿,也肯定是一隻手掌就遮得住的小內褲。天哪!他都感覺到自己開始出汗了。聞到了。看看她,那雙眼睛竟然也盯著他看,想看透他的心思。他心裡在想:她知道他在想什麼。
瑪麗雅‧洛伊在想,電話隨時會響,不是傑瑞就是欣希亞,想知道她在哪裡,他們人在哪裡。再不然就是哈羅德,說不定就是大人物哈羅德本人,打來道歉,說他還是會回來接她,一起開車去。
只不過她想起來了,個子較小的那個傢伙,也就是手搓著膝蓋,活像犯風濕痛或關節炎什麼的那個男人,已經把電話線拔掉了。
「把酒喝完,」格萊斯對搭檔說,「我們該把工作搞定啦。」
葛拉賓斯基點點頭,喝一小口威士忌和水,站了起來。
「來吧,」他露出微笑說。
瑪麗雅知道他在看她。
「不行,」格萊斯說。他也站起來,朝門走去。
「讓她幫忙吧,」葛拉賓斯基說,「這樣可以節省時間,不必把所有的東西都翻過一遍。」
「你覺得她會幫我們?」
「當然,為什麼不幫呢?反正我們無論如何都會動手的。」
瑪麗雅再一次忖思,他們兩個是真的小偷嗎?說不定是某種慶祝活動的把戲,哈羅德朋友搞的:兩個失業的演員,提供逼真的表演,比會唱歌的電報更有噱頭。這在六○年代叫什麼來著?即興演出。嗯,演得也夠逼真的。她站起來,身上的絲袍下襬一度貼在大腿內側。葛拉賓斯基嘴巴微張,眼睛瞪得發直。她都已經記不得有多久,哈羅德沒對她有相同的反應了。
「這我不相信,」格萊斯站在門口說。
瑪麗雅‧洛伊喝完她的第二杯威士忌,把杯子擺在椅子上,「也許我應該帶路?」
她知道葛拉賓斯基緊緊跟在她背後,也知道爬上樓梯時,絲袍會多麼緊密地貼在身上。
「就只剩一件事了,」格萊斯說。珠寶、現金和信用卡已經裝進軟皮袋子裡了。這軟皮袋共兩只一組,是他們上一個夏天去維京群島旅行的時候買的。她的兩件皮草掛在葛拉賓斯基的左臂上。
「什麼?」瑪麗雅問,但是格萊斯的表情讓她明白,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們兩個人都知道,她感覺得出來。但他們怎麼會知道她家有保險箱呢?
她得先推開枕頭,跪在床上,拿下克林姆的複製畫,交給格萊斯,他把畫上下顛倒靠在床邊。她覺得自己真的想不起來密碼是什麼,但是一碰到號碼轉盤,手指就自動地轉出正確號碼。
保險箱門一打開,她就轉身。
「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來。」格萊斯對她說。
裡面有一個珠寶盒,是個如假包換的珠寶盒,裝有如假包換的珠寶。裡面的珠寶首飾有她媽媽在遺囑裡留給她的遺產,有哈羅德還為她神魂顛倒的時期買給她的。保險箱裡還有兩疊不計記名債券,用粗粗的橡皮圈束起來。兩份遺囑,他和她的。一卷哈羅德攝影師朋友拍的錄影帶,當時他們四個人在某個爛兮兮的希臘小島混了一個星期。勉強吞下口的每一顆橄欖都讓哈羅德反胃。攝影師老二很大,但他愛拍的卻是他女朋友舔瑪麗雅肚臍上的鹽巴。回到英國之後,瑪麗雅發現自己得了輕微的肝炎。
葛拉賓斯基對她伸出手,等著她把錄影帶交給他。
「沒別的了?」格萊斯問。
瑪麗雅點點頭。
「別擔心,」葛拉賓斯基說,「你可以申請保險理陪,把錢要回來的。」低頭對著手上的錄影帶咧嘴笑,「除了這個。」
「你確定?」格萊斯說。
「確定。」瑪麗雅說。她從床上起來,沒讓他們再多瞧見什麼。她現在只想儘快把他們送出門。
「過半個鐘頭再報警。」葛拉賓斯基說。他們朝房間外面走。「你不想惹麻煩的話,就想想看該怎麼對警察形容我們的長相,仔細想想喔。」
「兩個黑人,」跟在他們背後的格萊斯出點子。
「穿皮衣搭牛仔褲。」
「戴巴拉克法拉帽。」
「戴滑雪面具。」
「他們強迫你打開保險箱。」
「最好呢,」葛拉賓斯基說,「是說他們逼你說出密碼。」
「沒錯,」格萊斯說,「這樣說比較好。」
他轉身走回房間。
「你去哪裡?」葛拉賓斯基問。
「擦掉她留在保險箱上的指紋。」格萊斯回答說。
瑪麗雅看著他,覺得雙腿發軟。葛拉賓斯基站得離她好近,手指輕輕戳著她最好的那件皮草大衣。
格萊斯站在床上,貼近保險箱,瑪麗雅看著他用手套擦掉她留下的指紋,然後眼睜睜看著他伸手進保險箱裡。
「喔噢,」他說,轉身面對他們兩人,眼睛瞪著瑪麗雅,「你騙我們。」
1.
「我們真的要幹?」格萊斯問。一陣涼意竄過他背上的肌肉。他向來討厭一月,痛恨至極。
葛拉賓斯基心想,比起平常一月的日子,今天晚上已經暖和多了。「等等。」他說,往車庫走去。就塊頭這麼大的人來說,他的動作可算得上意外輕巧的了。
用房地產仲介的廣角鏡頭來看,這幢房子或許可以稱得上是豪宅。但站在碎石車道盡頭望去,格萊斯覺得這只不過是一幢位在城市南緣、大而無當的房宅。
如果是白天,就更容易發現米白色的防水漆在今年夏天,甚至去年夏天都沒有重新粉刷;仿原木的木頭表面脫了皮,活像患了嚴重濕疹。正門兩旁各有一...
作者序
譯後記/李靜宜
或許是朝陽如春晚風似冰的劇烈天氣變化,也或許是幾趟來去匆忙的差旅,在冬日腳步遲緩猶疑的年歲交替之際,竟被流感病毒狠狠擊垮了。好幾天的時間,只能躺在床上望著藍天浮雲,什麼也做不了。
「找本血腥又暴力的小說來提振精神吧。」好友說。
翻出一本早就買來卻沒時間看的推理小說,光看書名就血腥又暴力的那種。
「如何?有效吧?」好友又問。
不,沒效。以一具屍體揭開序幕的故事情節,手法殘暴,節奏飛快,一頁頁翻去,一個又一個得不到解答的「為什麼」,終於模糊了閱讀的樂趣。
於是,找出早前幾年朋友就推薦,卻始終找不出時間來看的美劇《警察世家》(Blue Bloods),名正言順追起劇來。
同樣有謀殺,同要有暴力,以一家三代四名警察為故事主軸的《警察世家》沒有高科技辦案工具,沒有動不動亮出的犯罪剖繪,有的只是警探辦案的老法子:抬起屁股去找證據。順著人性的脈絡與邏輯的推演,在雜亂無章的瑣碎細節裡,拼湊出可用的線索,抽絲剝繭找出事實的真相。更不要說這三代同堂的一家人,每到週日還要在家族聚餐的餐桌上,對著犯罪與執法的本質,來一段世代觀點差異的唇槍舌戰,每每讓人在關注案情推理之外,也省思起人性的種種。
或許就是這樣的省思,讓有些推理故事和其他的故事顯得如此之不同吧。混跡紐約街頭各匿名戒酒會的馬修‧史卡德是如此,在諾丁罕夜夜無眠的查理‧芮尼克也是如此。
警察是一種特殊的職業(或是一種特殊的人類?)站在執法的第一線,以肉身隔絕市民日常生活與犯罪活動。但是,黑白世界的分野向來就不是那麼涇渭分明,沒有一條具體鴻溝的切割,有的只是存乎一心的判斷。道德感不夠強烈,很可能就在惡魔的誘惑下墜入墮落深淵;道德感過於強烈,很可能就自許為正義的化身,無視於法律的規範。在這片灰色的地帶行走越久,累積的未必是更多的清晰辨別,有時候反而是更多的挫折,甚至是更多的憤慨不平。
警察作為執法的具體化身,往往讓人忘了在他們的職業與工作之前,他們其實先是一個「人」,一個如你我般有愛有恨,有沮喪有衝動的平凡人。鎮日與罪犯為伍,會讓他們更透澈瞭解人性,但不會因而失去了人之為人的喜怒哀樂與人性情理。於我而言,閱讀警探推理小說的樂趣與意義也在於此。並不是在於解開某個謀殺謎團的興奮刺激,而是在於隨著警探那雙見識過人世滄桑的眼睛,探索複雜幽微的人心。
這是我之所以喜愛約翰‧哈威筆下這位查理‧芮尼克的主要原因。失婚獨居的芮尼克,除卻警探的身份,就只是一個養貓、聽爵士樂、喝威士忌,偶爾看看足球的中年大叔。但是孤獨的生活,並沒有讓他沉溺於寂寞的自憐裡,卻只讓他更能以同理心,看待這世間的一切。同儕常笑他是靠直覺辦案,但他的直覺並非突如其來的靈光一閃,而是累積了許許多多的細微觀察之後,對於任何一絲風吹草動都難以逃過耳目的靈敏感受。也因此,橫跨二十年時光的芮尼克探案系列,儘管沒有高科技的辦案工具,欠缺今日生活中隨處可見的電子設備,但每個故事都還是能打動我們,因為,不管外在的世界如何變化,人性永遠不會改變,而對人心的掌握與解析,也正是閱讀推理小說最大的樂趣所在。
很喜歡小說裡的一段情節:長期失眠的芮尼克深夜來到廚房,他養的四隻貓裡最弱小的那隻巴德竄出來迎接他。巴德因為弱小,分配給牠的貓糧常被最強悍的迪吉給搶走。在這樣的夜深貓靜時分,芮尼克給巴德開了一罐罐頭,給自己一杯加了威士忌的咖啡,喃喃說失眠也是有好處的。讀到這段文字,那一貓一人共享寧靜深夜的畫面躍然眼前。突然覺得,有睡眠困擾的我說不定也該養隻貓,人貓依偎窗前,等待黎明到來,心,或許也就暖了。
這樣的時刻,這樣的時代,我們需要芮尼克。
譯後記/李靜宜
或許是朝陽如春晚風似冰的劇烈天氣變化,也或許是幾趟來去匆忙的差旅,在冬日腳步遲緩猶疑的年歲交替之際,竟被流感病毒狠狠擊垮了。好幾天的時間,只能躺在床上望著藍天浮雲,什麼也做不了。
「找本血腥又暴力的小說來提振精神吧。」好友說。
翻出一本早就買來卻沒時間看的推理小說,光看書名就血腥又暴力的那種。
「如何?有效吧?」好友又問。
不,沒效。以一具屍體揭開序幕的故事情節,手法殘暴,節奏飛快,一頁頁翻去,一個又一個得不到解答的「為什麼」,終於模糊了閱讀的樂趣。
於是,找出早前幾年朋友就...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