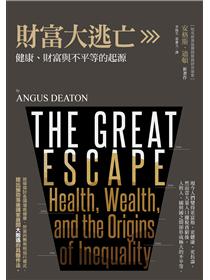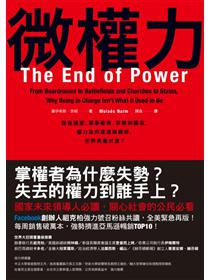1962年,中國與印度爆發邊境戰爭
2017年,中、印再度引發邊界對峙,緊張局勢看似一觸即發
《東方化:中國印度將主導全球》作者拉赫曼眼中的兩大新興世界強權
如何在五十年來解決不了的邊界爭議上,體現兩國的歷史與地緣政治角力脈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吳啟訥專文評介
1950年代,中國與印度分別成為亞洲兩大獨立國家,兩國間就此開展了五十年亞洲大陸地緣強權的勢力競逐。中國對於印度東北各邦少數民族獨立運動的支持,英國殖民政府劃下的麥克馬洪線中印邊界爭議,以及九十年後中國欲借道緬甸取得通往印度洋的策略通道。透過政治運作、軍事衝突、外交折衝,在世界屋脊的大喜馬拉雅山區掀起五十年的陰謀、動盪、煽動與暴力。
在《中國的印度戰爭》一書中,作者柏提爾.林納援引近年解禁的中印戰爭軍事情報資料,四十年間在印度東北、中國西南及緬甸北部少數民族部落區域訪問好幾代武裝勢力的第一手經驗,寫下大喜馬拉雅山區中印鬥爭,以及各族群在動盪陰謀中求生存的掙扎。
1962年的中印戰爭對印度是場重大挫敗,不只是折損軍力,國家尊嚴受到重大挑戰,同時全世界也認定印度為挑釁者,中國僅是「防衛自家領土完整」。半世紀後,本書作者林納透過爬梳更多機密文件、史料與訪談紀錄後,將當時被認定是「邊界爭議」的軍事衝突,重新放置在兩大亞洲強權的歷史與地緣政治角力脈絡。
本書不只重新定位1962年中印戰爭的基調,柏提爾.林納更認為中印戰爭始終不單純是一段邊界爭議,當時在大喜馬拉雅山區掀起的國際角力,今日仍舊在緬甸北部、中印交界及印度洋區域持續演進。未來,中國與印度這兩大亞洲新興強權勢必爭奪亞洲甚至世界的發言權。
作者簡介:
柏提爾.林納 Bertil Lintner
瑞典記者、作家與緬甸問題專家,專研亞洲局勢近四十年。曾任《遠東經濟評論》緬甸特派員,目前為《瑞典日報》及丹麥Politiken雜誌亞洲特派員。他是緬甸、印度東北區、中國及北韓關係的專家,大量作品刊登於三十多國媒體。林納是第一位披露緬甸與北韓策略合作關係的記者。2004年柏提爾.林納關於北韓的傑出報導,獲得亞洲出版人協會獎。他在緬甸、印度東北、寮國及中國雲南區域耕耘近四十年,以深入蹲點報導,爬梳區域安全、政治叛亂、族群衝突與組織犯罪之間盤根錯節的脈絡。報導與分析作品常見於《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及《亞洲時報》網路版。
譯者簡介:
林玉菁
紐約市立大學政治學博士班,劍橋大學印度研究碩士,政大新聞系。曾任職IFRC國際紅十字與紅星月會聯合會美洲辦公室,雲門基金會,北藝大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及國內外NGO組織。現為專職口譯、筆譯。譯有《業的盡頭》、《榮耀之城伊斯坦堡》、《印度:南亞文化的霸權》等書。
章節試閱
前言與誌謝
我對喜馬拉雅邊界爭議的興趣始於一九六七年。當時我是個十四歲的瑞典少年,手寫一封信寄到斯德哥爾摩的印度大使館,詢問爭議的相關訊息;年紀輕輕就已經對國際事務深感興趣。我十分好奇,究竟邊界爭議是如何導致一九六二年那場短促卻傷亡慘重的戰爭呢?
我收到一箱回覆,箱內有整疊的白皮書,其中包含了新德里與北京信件和正式聲明的複本,以及詳細的折疊式地圖,描繪出印度與中國各自主張的領土區域。我開始對區域地理有些了解,並從印度觀點建立了對衝突的基本認識:中國對喜馬拉雅地區發動了大型攻擊,印度是中國侵略的受害者。
戰爭結果以印度大敗收場。然而出乎許多人意料的是,中國並未持續占有東部的占領區。中國將印度軍隊逐出多數爭議區域後,便沿著喜馬拉雅山脊,撤退到舊的實質控制線(Line of Actual Control)之後。儘管今日的中國官方地圖仍標示此地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印度的行政管理與軍事人員卻可以重回這些區域,僅有在西邊的拉達克(Ladakh),實質控制線的微調傾向中國的利益。
數年後,我在一九七○年代中期讀到一本書《印度對華之戰》(India’s China War),作者是澳洲英文記者奈維爾.馬克斯韋爾(Neville Maxwell),他針對這衝突呈現完全不同的觀點。馬克斯韋爾認為,雖然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是由中國發動攻擊,戰爭卻是因印度挑釁所起。印度獨立後的首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提出「前進政策」(Forward Policy)後,印度便沿著實質控制線建立一連串軍事據點,甚至越過控制線。
馬克斯韋爾的論點基於一份外洩的印度機密報告,這份《亨德森.布魯克斯─巴格特報告》(Henderson Brooks-Bhagat Report),是由兩位資深印度軍官亨德森.布魯克斯中將(T.B. Henderson Brooks)和普里敏德拉.辛格.巴格特准將(Premindra Singh Bhagat)撰寫。報告內容當然支持馬克斯韋爾的論點,亦即這場戰爭是由印度所挑起,中國僅是反擊並重申中印邊界的領土主權。中國主要是尼赫魯敵意政策下的無辜受害者。
同時,根據馬克斯韋爾的說法,印度對實質爭議區域並無主張之權利。這些區域只印在一九三○年代英屬印度政府單方面發行的部分(但非全部)地圖中,並於一九四七年後,全面印在獨立印度政府發行的地圖裡。在此之前的正式地圖中,英屬印度的北方邊界與中國地圖上所展現的邊界並無二致,兩者同樣位於阿薩姆平原的喜馬拉雅山腳丘陵。
英國、西藏與中國代表於一九一三與一九一四年,曾在可俯瞰北印平原的高地上,時為英屬印度政府夏都的西姆拉(Shimla)召開會議,欲解決西藏地位及邊界問題。然而馬克斯韋爾、阿拉斯泰爾.蘭姆(Alastair Lamb)及其他西方學者皆主張,這幾次會議並沒有共識,因為中國拒絕接受英國與西藏的提案。
我當時認為馬克斯韋爾的書十分具有說服力;不僅文筆流暢、充滿細節,同時提供了詳盡的注釋。當我對此議題涉獵得愈深入,也發現這本書對許多的西方及亞洲學者、決策者影響深遠。
毫不意外地,中國領導人對馬克斯韋爾的著作讚譽有加。在一九七一年北京的正式宴會中,中國總理周恩來與巴基斯坦總理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由主桌一同起立,前往外國記者座位區。當時馬克斯韋爾也在那兒,周恩來上前向他致意,周恩來透過翻譯說:「馬克斯韋爾先生,你的書講出了真相,令中國受益。」
就連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也印象深刻,在他的著作《論中國》(On China)一書中,表明對印度的前進政策不予認同。馬克斯韋爾在二○一四年的訪問中表示,一九七一年《印度對華之戰》在美國上市時,季辛吉曾讀過此書。
它改變了他(季辛吉)對中國的想法,並將書推薦給尼克森(總統),這些現在都記載在尼克森―季辛吉―毛澤東談話紀錄中(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季辛吉訪問北京時,周恩來傳給我私人訊息,說季辛吉告訴他:「這本書讓我知道可以跟你們打交道。」
但進而廣泛閱讀中印衝突的相關資料後,我開始了解到,馬克斯韋爾對一九六二年戰爭一連串的因果事件描述,完全禁不起嚴格審視。首先,尼赫魯的前進政策是為穩定整條中印邊界,西起拉達克,東至東北邊境特區(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過去為阿薩姆邦政府下的行政機構,現在屬於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此政策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日新德里的會議中決定,此時離戰爭爆發不到一年。這會議由尼赫魯主持,與會者包含國防部長梅農(Vengalil Krishnan Krishna Menon)、情報局長穆立克(Bhola Nath Mullik)、外交部長迪賽(M.J. Desai)以及新任陸軍總司令塔帕(Pran Nath Thapar)。
這顯然是場最高層級的重要會議。然而,會後下達軍隊的指令並非侵略性,而是「(在拉達克阿克賽欽[Aksai Chin]區域)盡可能由現有據點向前巡邏。此舉意圖建立防止中國持續前進的據點,同時掌握對方可能已於我國領土建立的任何據點」。而西段阿薩姆平原上已建立的新據點,僅駐有相對小型且裝備不足的軍力,並且多數來自準軍事組織「阿薩姆步槍隊」(Assam Rifles)。
因此與其說是印度挑釁中國,更可主張為新中國的共產黨領袖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後的侵略行為。一九五○年,中國派出數萬軍隊入侵當時仍為事實獨立的國家:西藏。此後,印度與中國兩大文明之間不再有西藏扮演緩衝角色,雙方領土在歷史上首度直接接壤。
一九五○年代,中國在阿克賽欽區域修築了一條公路。雖然中、印兩國皆宣稱擁有這塊領土,但此區明顯由中國管控,因為印度是在將近一年後,才發現了這條穿越阿克賽欽最高點、連接中國新疆到西藏的新藏公路。由於阿克賽欽除了氂牛游牧民外,並無任何定居人口,因此中國得以在不受注意的情況下建造公路。
但西藏卻不同,其平民遭屠殺,佛寺僧院被毀壞。中國在西藏的鎮壓引發了一九五九年三月的拉薩起義,最後中國人民解放軍鎮壓了抗爭行為,殺害數百名僧侶與平民,並導致上萬難民穿越喜馬拉雅山脈,前往印度尋求庇護。其中包含西藏的精神領袖:神王達賴喇嘛。
中國在西藏起義前(特別是起義後)於西藏各地建立軍事據點,其中包含鄰近印度領土的區域。中國建造通往印度東方的新路,直達東北邊境特區的中印邊界上,這很難不令人認為,中國版「前進政策」(雖然並非如此稱呼)比印度版更加積極且具侵略性。
馬克斯韋爾認為,中國決定攻擊的可能日期是「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因為印度在多拉(Dhola)建立哨所,激化邊界東段的緊張局勢。在此之前一切仍舊『平靜』」。根據某些地圖,多拉位於印度與西藏邊界的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以北,此邊界是一九一四年英屬印度與西藏政府代表在西姆拉會議中同意的。當時中國代表只簽下開頭字母,但未正式簽署協定,因為中國並不承認西藏是獨立國家。此議題後續未獲解決,也影響邊界情勢發展的正常化。
一九五九年拉薩起義後,中國開始在麥克馬洪線對側與沿線進行各種動作,我不清楚馬克斯韋爾對此是否蓄意無視或一無所知。沒有任何嚴肅的軍事分析師會認為,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中國對印度的大規模戰爭(或開戰前數日發生的戰鬥),會是在人民解放軍跨越邊界(東段的麥克馬洪線及三千公里外西段拉達克實質控制線),前一週或數週所做的決策。
中國對這場戰爭的準備明顯遠早於一九六二年十月,甚至比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尼赫魯提出前進政策的會議更早。即使當地已有新建道路與軍事基地,仍需要運輸數萬名人民解放軍及許多噸補給,包含軍事重裝備,進入世界上最崎嶇難行的地理區域。毛澤東總共派出八萬名人民解放軍進入拉達克及喜馬拉雅山東側,發動對印度的攻擊,因此必須建立且穩固通往西藏後方基地的補給線。
而跨過邊界後,中國軍隊明顯熟稔印度軍隊駐紮地的地形與地勢,並清楚如何發動攻勢。由於當時中國還無法獲取衛星影像或以偵察機得到空中影像,完全得倚靠在地潛伏的特務蒐集情報,在這種地勢崎嶇且缺乏道路的東北邊境特區,必定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不過中國特務潛伏對象主要是藏語社群,幾乎無法進入以非藏語部落為主的東北邊境特區大部分地方。
因此,中國發動攻擊的區域有經過仔細選擇,而且實際上相當侷限,這與包含印度在內的多數研究認定不同。一般常誤解,人民解放軍穿越了東北邊境特區多數區域,並直抵巴魯克旁(Bhalukpong)低地,此地為現今阿魯納恰爾邦與阿薩姆邦的交界。巴魯克旁遭到棄守,人民解放軍與印度軍的最後交火,是在魯巴(Rupa)以南、靠近邦迪拉(Bomdila)的查庫(Chakhu)。在東部的人民解放軍並未超過瓦弄(Walong)太多;從中央區域入侵蘇班西里(Subansiri)與桑朗(Siang)的武力相對較弱。
這些區域都有一個共同點,在地人口主要是藏語族群或使用藏語相關方言,是戰前得以進行人際情報收集的地區。當解放軍進入東北邊境特區,透過藏人翻譯,可與這些留在當地的居民溝通。雖然印度軍隊由東北山區的所有據點撤出,但解放軍並未進入由密什米人(Mishmis)、阿帕塔尼人(Apatanis)、尼伊希人(Nyishis)及其他非藏語部落為主的區域。由於戰爭開始前的謹慎計畫並未得到此地情資,這些部落可能被認定為具潛在敵意的敵方。
中國在一九六二年十月發動攻擊前,還採取了其他準備措施。印度軍隊的約翰.達爾維准將(John Dalvi)與部分軍隊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遭俘虜成為戰犯,直到一九六三年五月才獲釋。他的著作《喜馬拉雅失策:印度最毀滅性軍事災難背後的憤怒事實》(Himalayan Blunder: The Angry Truth about India’s Most Crushing Military Disaster)記載了整段經歷。達爾維被俘送往另一側之後,得以觀察中國如何謹慎準備對印度的閃電攻擊。他發現中國已經建立可容納三千人的戰犯營,同時印度所有主要語言的翻譯員也於一九六二年三至五月間送往拉薩。遠在攻擊發生前,不僅有上萬名軍隊事先遣入區域熟悉邊界山脈高度,還招募數千名藏人挑夫,並沿著邊界建立臨時軍火供應站。更明顯的是,達爾維發現中國興建了一條可承重七噸貨車的道路,直上麥克馬洪線附近的馬曼(Marmang)。綜合種種觀察,達爾維最後寫下:「並非意外,更絕非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之後才決定。這是中國冷酷算計的謀劃之舉。」
雖然做成最終決定的時間點,確實可能是在解放軍行動的前一週(從軍事策略角度思考的確說得通),但重要的是,印度軍隊在次大陸最偏遠角落建立哨站,實在與一九六二年戰爭毫無關聯。此事或許可視為託詞,即使如此也相當薄弱。毛澤東更在戰爭前後告訴尼泊爾與蘇聯代表團,重點從來不是麥克馬洪線或邊界爭議。中國認為印度對西藏有所圖謀,而後者在一九五○年代,正逐步納入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之中。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拉薩起義爆發後三週,達賴喇嘛正翻山越嶺前往印度,當時的中國政軍領袖鄧小平,明白在會議中表達了中國立場:「等時候到了,我們會跟他們(印度)清算總帳。」美國安全與南亞議題專家布魯斯.里德爾(Bruce Riedel)認為:「也許早在一九五九年,毛澤東就決定將對尼赫魯採取強硬行動。」
中國國家安全部的南亞分析師趙蔚文,曾在一九六二年戰後寫道:「印度熱切希望持續英國在西藏的事業。」而尼赫魯本人「則懷抱黑暗心理」。趙蔚文認為,這些因素導致尼赫魯在一九五九年表現出「游移不決的態度」。美中關係學者高龍江(John Garver)則引述他的話:「黑暗心理導致尼赫魯放任『反中勢力』不管,試圖在西藏煽動騷亂,以此『推翻中國中央政府的統治』。」
根據高龍江的研究,毛澤東本人也現身一九五九年三月的會議,並表示印度「在西藏做壞事」,因此需要有所處置。毛更進一步告訴在場的中國核心領導,中國此刻不應公開譴責印度。相反地,要給印度足以吊死自己的繩子,「多行不義必自斃」。中國等待處理印度的時機到來,但首先需要邊界另一側的精確情報。
中國情報行動專家尼可拉斯.艾夫第米亞迪斯(Nicholas Eftimiades)揭露,中國早在軍事侵略前兩年,已開始派遣特務進入東北邊境特區與其他區域。「透過潛伏在邊境公路盜匪、挑夫與馬隊中的特務,解放軍收集關於印度軍事作戰序列、地形地勢特徵,以及軍事戰略等情報。」艾夫第米亞迪斯指出,這些特務「隨後在攻擊行動中,引導人民解放軍穿越邊境區域 佯裝為藏人的低階軍官早已事先偵查行動區域」。
「軍事侵略前兩年」,表示至少是在尼赫魯提出「前進策略」的前一年,因此「印度的區域行動挑釁中國出兵」此一說法就更難站得住腳。此外,經過數年準備後的最終行動日期: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更是精挑細選。此日期與古巴飛彈危機同時發生,而中國透過與蘇聯領導人的關係早已事先知情。隨著蘇聯在古巴布置飛彈,可以肯定美國必然無力旁顧遠在喜馬拉雅山脈中發生的戰事。
由於當時中蘇關係逐漸惡化,蘇聯領袖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並未親自告知毛澤東,蘇聯正遣送飛彈前往古巴。如里德爾書中所寫:「直到開戰前兩天,毛才告知莫斯科,中國將與印度開戰。」然而,根據英國分析師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記載,當時中國駐莫斯科大使劉曉「提前告知北京赫魯雪夫的計畫,中國可能早已知曉,因為他們在古巴擁有極好的情報來源」。
中國在東北邊境特區的情報蒐集工作,可能早在一九五九年鄧小平指示將與印度「清算總帳」前就已展開。根據一九五二年的一份情資報告,當時一個反對達賴喇嘛的西藏異議教派,被送入印度擔任「間諜與煽動者」。報告指出這教派「在(一九五○年)占領西藏的行動中,擔任(中國的)第五縱隊」。
中國顯然正準備與印度進行一場長期衝突。然而,一九六二年之後卻轉成代理人戰爭,由印度境內的反抗勢力進行鬥爭。看似不可能的夥伴包含在印度極東山丘地帶的基督徒部落那迦人(Nagas)。那迦人在費佐(Angami Zapu Phizo)的領導下,高舉武器反抗新德里政府,並立即獲得印度頭號敵手,巴基斯坦的軍事援助。此外,那迦反抗軍也獲許在東巴基斯坦(今孟加拉)設立營地,由此向印度發動攻擊。費佐本人則由東巴基斯坦借道瑞士前往英國,在肯特郡的流亡寓所持續與那迦丘陵的指揮官保持聯繫。
一九六二年六月,那迦反抗軍指揮官之一的莫烏.格韋增(Mowu Gwizan)在前往倫敦與費佐會面的途中,停留喀拉蚩(Karachi),並在巴基斯坦接待的介紹下認識了「中國友人」,後者承諾給予那迦人援助與支持。18會議之後,那迦人集結一百三十二名兵力,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從那迦山區出發。他們在數個月的時間裡徒步跋涉,穿越緬甸北部叢林,於一九六七年一月抵達雲南,接著在當地接受政治與軍事訓練。一九六七年底,第一批受訓的那迦人帶著中國製突擊步槍、機關槍與火箭發射器返回印度。一九六七至一九七六年間,有超過七百名那迦反抗軍前往中國受訓,帶著大批武力回去對抗印度軍隊。繼那迦人之後,同樣來自東北邊境山區的米佐人(Mizo)反抗軍也跋涉前往中國;他們同樣接受軍事訓練,並帶著中國武器返回山區家園。一九七○年代,另一群來自曼尼普爾(Manipur)的反抗軍,則在西藏接受中國政治與軍事訓練。
一九六二年戰爭前,人民解放軍已獲取部分發動越境決定性攻擊的經驗。一九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一年二月,數千名中國軍隊跨過中緬邊界,追擊中國國民黨餘軍。這批軍隊在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內戰敗北後,便撤退到緬甸偏遠的東北山區,運用跨越中緬邊界的庇護,向中國境內發動襲擊。由於緬甸也希望驅逐這群入侵者,因此兩國軍隊合作發起攻擊行動,在緬甸代號為「湄公河戰役」(Mekong River Operation),中國則稱之為「中緬聯合勘界警衛作戰」(Burma Border Surveying and Security Operation)。
然而作戰結果僅有部分勝利,多數國民黨餘軍逃過一劫並退往泰國邊界,這也暴露出解放軍的弱點:難以在陌生地形環境中開展作戰。雖然參與聯合作戰的部隊與一九六二年攻擊印度的部隊不同,但可以合理推測,中國的戰略制定者從此役中獲取教訓,因此一年後得以在喜馬拉雅山區發動更為成功的作戰。
若是如此,《亨德森.布魯克斯─巴格特報告》又是怎麼回事呢?這份報告始終列為機密文件,不過我在二○一三年時從一名資深印度記者那裡取得了複本。一年後,馬克斯韋爾決定將之公諸大眾。他將報告的電子文件檔公布在網路上,香港報紙《南華早報》則以標題「奈維爾.馬克斯韋爾公布文件,顯示一九六二年邊界戰中,印度挑釁中國開戰」報導此事。報導甚至令人驚訝地宣稱:「(該)記者像史諾登(Edward Snowden)一樣,揭露了一九六二年戰爭的來龍去脈,強化了中國和平崛起的宣示。」
我認為一個人必須擁有強大的想像力,才能從《亨德森.布魯克斯─巴格特報告》導出,印度是一九六二年戰爭的侵略者,而中國是受害者的結論。「誰攻擊誰」或「誰該為戰爭負責」等問題,甚至不在這份報告討論的範疇裡。這份報告主要探究了戰爭的四個領域,以此了解印度為何挫敗,分別是:訓練軍備的可能缺失、指揮體系、軍隊體能、各階層指揮官影響下屬的能力。
基本上,除了「印度並未準備好面對戰爭,自然無法抵禦中國攻擊」外,《亨德森.布魯克斯─巴格特報告》內容並未延伸太多。它指出印度指揮架構的弱點,政府與軍隊間缺乏有效合作,但絕對沒說印度應該為戰爭負責,也未質疑整體前進政策。
馬克斯韋爾將報告公諸於世後,看起來顯然缺乏有趣內容,許多印度記者與研究者開始猜想,是否可能有第二份報告或第一份報告的附錄,以提供更多訊息。然而令許多人失望的是,這份報告內容確實不如馬克斯韋爾或其他人所宣稱。或者如《印度時代雜誌》(Times of India)前助理編輯維格斯(B.G. Verghese)在二○一二年所寫:「這份報告展現出政治與軍事上普遍的天真糊塗、矛盾對立,以及缺乏計畫與控制。《亨德森報告》中沒什麼需要保護的軍事機密,只有待隱藏的政軍自負及愚蠢。」當我開始審視《印度對華之戰》書中的注釋後,發現馬克斯韋爾所寫,與引用資料實際所說確實有出入。
讀過馬克斯韋爾後,我轉向閱讀英國學者阿拉斯泰爾.蘭姆的著作,他曾大量書寫中印與中巴邊界爭議。雖然蘭姆的書籍文章比馬克斯韋爾對邊界議題與一九六二年戰爭的書寫來得學術,仍有嚴重缺失及合理批評。一九六八年,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學教授李奧.羅斯(Leo E. Rose)對蘭姆的兩冊巨著《麥克馬洪線:中印涉藏關係史,一九○四至一九一四年》(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曾如此評論:「當議題涉及當今政治爭議時,學術客觀性與特別請願間的界線必然更為狹小,一如這篇研究所充分體現。」無疑地,羅斯對蘭姆的作品如此寫道:
在當今中印喜馬拉雅東段邊界爭議中,形成中國觀點的論述,這並非不受歡迎。中國確實有其道理,而比起北京政府,蘭姆先生以更清晰而有說服力的方式呈現此觀點。但不熟悉這片鮮為人知邊界的非專家讀者,必須明確意識到,作者在評估分析事件與結論時有其特別偏向。
對我來說,蘭姆對地圖細節及劃界等相關次要議題幾近癡迷,同時模糊了更大的地緣政治圖像。當我進一步研究相關議題時,更明晰了解到這其實遠超越邊界爭議;而中國從未意圖持有戰爭期間占領的區域,這塊他們宣稱是屬於中國的領土。
中國軍隊一九六二年從占領區域中撤軍,實際上令軍事史家及眾人感到不解,一般猜測可能是因為嚴冬即將到來,或是後方漫長的補給線中斷了軍事行動。即使有這些困難,中國事實上可以進一步往下推進,來到阿薩姆核心區及布拉馬普特拉河(Brahmaputra River)平原。在這個區域裡,氣候將不成問題,同時能擁有大量糧食。他們可以輕易掌握山脈以南的德茲普(Tezpur)小城,此地機場狀況良好,而印度軍隊及行政機關已棄城離去。
在一九五○年代韓戰之後,中國開始積極發展空軍,因此在對印戰爭時已擁有數千架飛機(包含運輸機)。這些飛機部分由蘇聯輸入,其他則是經過授權在中國製造。雖然並無跡象顯示一九六二年時中國曾派機進入西藏(當時西藏僅有五個可運作的機場),或許是人民解放軍缺乏空軍駕駛,但美國情報單位相信:「若中國空軍可從緬甸進行任務,或是掌握布拉馬普特拉河谷的機場,能力將大幅提升。」美國報告也指出,對印作戰時,亦可運用中國西南省分雲南與四川的機場。
然而中國意圖並非征服占有土地,這不是中國領導人決定攻擊印度時的本意,而是在地緣政治上發出重要一擊,這已足夠。尼赫魯這位一九五○年代不結盟運動的主要推動者遭到羞辱,再也不是亞非新興獨立國家的領頭羊;他從一九五五年印尼萬隆的歷史性會議後,一直扮演這個角色。經過一九六二年戰爭,中國取代印度成為第三世界的領袖。「第三世界」一詞也是由中國無所不能的毛澤東主席提出,以此取代舊有的不結盟概念。而第三世界的領袖,自然是毛澤東所帶領的中國。
中國領袖決定與印度「算帳」(引述鄧小平的話),並動用戰爭準備的時機點,必須放入當時中國內政問題的脈絡來理解。一九五八年,毛發動災難性的「大躍進」,意圖帶動中國現代化。一九六一年,約有一千七百萬至四千五百萬人死於毛的政策之下;大躍進帶來了饑荒,而非預期的任何快速工業化進程。
毛不但失去聲望,甚至面臨可能下台的處境,他深覺需要重掌權力,而最好的方式莫過於團結國家(特別是軍隊),共同對抗外侮。印度是個「軟」目標,它在一九五九年才剛提供因反中侵藏起義失敗而出逃的達賴喇嘛政治庇護,並允許西藏神王在北印度的麥克羅甘己(McLeodganj)建立流亡政府;此外還有中國不承認的邊界爭議。
馬若德在中國文化大革命起源的詳實歷史著作中寫道,中國的內政與外交政策間常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毛澤東的世界觀中,中國革命是一連串全球事件的一部分,並且有著雙向影響。然而馬若德也指出,中國軍事行動與內政的連結經常隱而不顯。根據其說法:「中國參與一九五○年爆發的韓戰,讓中國共產黨領袖得以發起愛國行動,團結身後的人民。」
韓戰爆發於一九五○年,正好是共產黨取得中國政權後一年,並持續至一九五三年。當時中國新統治者首要之務在於鞏固權力,並為尚未獲全民愛戴的政權贏得支持。因此數萬人上街頭舉行反美示威,同時估計在韓戰方興未艾的半年中,有七十一萬人被標籤為舊政權相關的反革命者,遭到處決或被迫自殺。
災難性大躍進後的情勢有些雷同。一場勝仗對毛及其支持者來說有如天賜大禮。雖然戰爭與毛重新掌權之間的直接關聯,仍有待中國內部文件證實,但毛確實在一九六二年戰後重新掌握了黨與國家的大權,部分敵人遭到清算,部分仍存活。因此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發起偉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一步將所有政治對手消滅,並在中國上升到接近神的地位。
考慮到中國的區域野心與當時的內政情勢,任何嚴肅的觀察家與分析師都很清楚,邊界爭議不過是發動一九六二年戰爭的藉口。然而同時我們也須謹記,中國的態度一向認定自己是對的,任何挑戰中國說法的企圖,都會被視為「挑釁」。不論出於任何原因,只要不為中國所喜的條約都視為「不平等」,因此也不會遵守。
身為專長亞洲區域安全議題的記者,不難察覺中印邊界爭議與南中國海主權爭議之間的相似性。今日的中國也許比一九六二年時更為開放,意識型態也比較不僵硬,不過它對待鄰居的方式仍然不變。
中國從未控制或統治印度東北任何區域,但今日卻如此宣稱,並在地圖這樣標記;這與南中國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島的情勢發展驚人相似。中國在地圖上以大U字型,宣稱將斯普拉特利群島幾乎全數納入領土;今日台灣、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與汶萊均宣稱擁有全部或部分島嶼。而根據北京說法,「挑釁」的是這些國家,而非中國。
中國發言人堅稱,根據十五至十六世紀的明代文件證實,中國統治整個南中國海地區。然而此說絕非事實。明朝皇帝對海洋事務並不上心,在十五世紀中國短暫的海權時期,探險家鄭和帶領艦隊航向南亞、東南亞、印度次大陸、阿拉伯半島,甚至遠及東非海岸。鄭和的助手馬歡留下詳細紀錄與地圖,羅列東南亞與印度洋超過七百個地名,包含安達曼(Andamans)、尼可巴(Nicobars)、馬爾地夫與拉克沙兌普(Lakshadweep)等島群中的偏遠小島嶼。
中國製圖家十分清楚斯普拉特利群島的存在與位置,馬歡也提到它們,但並不如紀錄中的其他地方詳細。原因十分簡單:斯普拉特利群島並非島嶼,而是捉摸不定的沙洲淺灘與暗礁,古代水軍必須繞行以避免沉船。然而,此一事實並無法阻止中國做出驚人宣言,最近同時更透過在淺灘暗礁建立人工島嶼,實質鞏固其主張。任何反對意見都將被視為干涉中國內政。
二○一六年七月,海牙的國際仲裁法院回應菲律賓提出的指控時,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發現中國對南中國海並無可信的「歷史權利」。法庭指出並無證據證明,中國曾行使此種專屬主權性質的權利。北京政府對此則憤怒回應,宣稱判決是場「鬧劇」,並宣布中國在海洋中的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不受判決影響。中國官媒《人民日報》刊出措辭嚴厲的社論,堅稱仲裁庭「忽略基本事實」,「踐踏」國際法,因此「中國政府與人民堅定(反對)判決,不承認也不接受」。
喜馬拉雅山區也許不會爆發另一場戰爭,但中國在南海的不妥協態度與行徑,極可能導向另一場區域衝突,而且比今日所見更加嚴重。此外,中國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水壩建造者。許多河流由西藏、雲南流往下游國家,中國常未先諮詢這些國家便建壩攔水,甚至有計畫將西藏的水大規模導向中國核心地帶。
西藏就如同西方非政府組織Maptia所指出:
是世界獨特的大量淡水提供者,透過河流進入中國與十幾個下游國家。西藏是亞洲河流的主要源頭,此外更透過支流注入其他河川(例如恆河),地球上找不到任何類似情況。我們只有一個西藏,沒有備援,也沒有第二次機會。
還有事實獨立的台灣,是否真如北京宣稱,是中國的一部分呢?再一次,在這些議題上,中國認為抱持其立場以外的意見,都是干涉內政。
由於今日地緣政治現實牽涉甚廣,我們更需要回頭研究喜馬拉雅山區衝突的緣起與發展。如今中印仍舊是強大的區域對手,而兩者之間的敵意,開始於半個世紀前的喜馬拉雅山區。
有關邊界爭議的研究使我前往阿魯納恰爾邦、錫金及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北部地區;也曾進入緬甸的克欽族領域、中國雲南省、尼泊爾與不丹。倫敦大英圖書館館藏的印度辦公室檔案(India Office Records)是資訊的寶地圖,試圖找出北京主張的背景與歷史紀錄。研究途中曾有許多人提供協助,由於人數眾多無法一一誌謝,而且因為議題敏感,多數要求保持匿名。
即使如此,我想感謝魯巴的多吉.堪卓.騰多(Dorjee Khandu Thongdok)。中國攻擊魯巴時,他逃出故鄉,後來也寫下這段故事。我在達旺(Tawang)遇到兩名還記得一九六二年中國占領他們家鄉的藏人。一位瓦弄村民與我分享戰爭期間發生的事。大吉嶺有名年長藏人,比我認識的任何人都還清楚邊界情況。還有錫金甘托克(Gangtok)的地方官員。在西孟加拉邦北部的西里古里(Siliguri),我遇見阿比吉.馬遵達(Abhijeet Mazumdar),他是已故拿撒爾人(Naxalite)運動領袖查魯.馬遵達(Charu Mazumdar)的兒子。過去我也無數次訪問印度東北地區的那迦、米佐與曼尼普爾反抗軍,他們曾經在一九六○與一九七○年代前往中國受訓。同時,我也有機會訪問了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United Liberation Front of Assam)反抗軍,包含最高領袖阿拉賓達.拉吉科瓦(Arabinda Rajkhowa)與派瑞許.巴魯亞(Paresh Barua)。在尼泊爾,我拜訪退休記者作家卡納克.馬尼.迪克西(Kanak Mani Dixit),以及其他當地媒體與研究區域暴力衝突的國際組織;同時也造訪了尼泊爾南部的難民營,此地從一九九○年代初期,就收容許多來自不丹的尼泊爾裔難民。在不丹,我有機會與數位政府官員討論中國相關議題,然而對方希望維持匿名。西藏專家朱利安.吉林(Julian Gearing)協助我探索錯綜複雜的西藏派系這困難任務;喜馬拉雅山區的佛教世界常令外來觀察者感到撲朔迷離。同時,我也想感謝阿拉斯泰爾.蘭姆。二○一六年一月我在大英圖書館進行研究時遇到蘭姆教授。雖然我不同意蘭姆的論點與結論,但他慷慨分享資訊,甚至送了我一些相關書籍。我從未試圖聯繫奈維爾.馬克斯韋爾,除了《印度對華之戰》,我還讀了他另一本較不為人所知的著作《中國邊界的解決與衝突》(China’s Borders: Settlements and Conflicts),以及過去數年發表在《經濟政治週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的文章。
當然,面對中印爭議如此炙手可熱的衝突性議題,充斥許多相互矛盾的歷史與當代紀錄,我們很難達到完全精確無誤。但我盡一己之力,在此呈現衝突的完整細緻樣貌:衝突為何及如何開始;衝突轉變後的樣貌;衝突在當今亞洲現實中所代表的意義。倘若有任何事實出入,那麼都是我的責任,與任何口述或書面資料來源無涉。
前言與誌謝
我對喜馬拉雅邊界爭議的興趣始於一九六七年。當時我是個十四歲的瑞典少年,手寫一封信寄到斯德哥爾摩的印度大使館,詢問爭議的相關訊息;年紀輕輕就已經對國際事務深感興趣。我十分好奇,究竟邊界爭議是如何導致一九六二年那場短促卻傷亡慘重的戰爭呢?
我收到一箱回覆,箱內有整疊的白皮書,其中包含了新德里與北京信件和正式聲明的複本,以及詳細的折疊式地圖,描繪出印度與中國各自主張的領土區域。我開始對區域地理有些了解,並從印度觀點建立了對衝突的基本認識:中國對喜馬拉雅地區發動了大型攻擊,印度是中國侵略的...
目錄
前言與誌謝
第一章 未必是邊界爭議
第二章 界線
第三章 入侵
第四章 戰爭結束時
第五章 著迷的,也是致命的邊界
第六章 國民幸福指數?
第七章 毛主義再現
第八章 邊疆與大洋
年表
注釋
延伸閱讀
前言與誌謝
第一章 未必是邊界爭議
第二章 界線
第三章 入侵
第四章 戰爭結束時
第五章 著迷的,也是致命的邊界
第六章 國民幸福指數?
第七章 毛主義再現
第八章 邊疆與大洋
年表
注釋
延伸閱讀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8收藏
8收藏

 28二手徵求有驚喜
28二手徵求有驚喜




 8收藏
8收藏

 28二手徵求有驚喜
28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