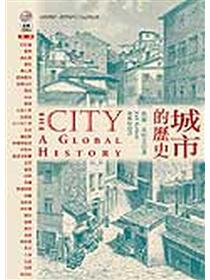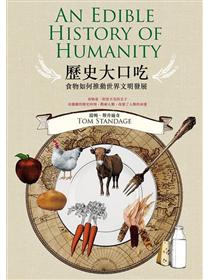它是馬修.史卡德的原點,也是進入史卡德的最佳選擇。 《蝙蝠俠的幫手》增訂新版,加碼收錄兩個短篇〈米基.巴魯瞪著空白螢光幕〉,揭露米基.巴魯人生中,最讓人訝異的轉折、〈葛洛根的最後一夜〉,描繪馬修、伊蓮、米基、克莉絲汀滿是離愁的相聚,以及編劇名家布萊恩.柯普曼的導讀和卜洛克的後記
愛倫坡終身大師獎得主、紐約犯罪風景的行吟詩人——卜洛克
廣受全球萬千書迷喜愛的馬修.史卡德系列全新修訂版
國際知名導演王家衛想拍卜洛克的電影
影帝梁朝偉當導演最想拍的也是偵探史卡德的故事
臥斧x郝譽翔x翁裕庭x張國立x陳雪x陳國偉x劉梓潔x譚光磊x顏忠賢x史蒂芬.金x麥可.康納利……
知名作家和推理評論家,齊聲推薦
推理評論人 冬陽 專文推薦窗外
給袋婦的一支蠟燭
黎明的第一道曙光
蝙蝠俠的幫手
慈悲的死亡天使
夜晚與音樂
尋找大衛
夢幻泡影
一時糊塗
米基.巴魯瞪著空白螢光幕
葛洛根的最後一夜
作者簡介:
勞倫斯.卜洛克 Lawrence Block
歐美當代冷硬派偵探小說書寫第一人
一九三八年出生於紐約水牛城。除了極少時間之外,卜洛克幾乎都定居於紐約市內,並以該城為主要背景,從事推理文學創作,成為全球知名推理小說家,因而獲得「紐約犯罪風景的行吟詩人」美譽。
卜洛克的推理寫作,從「冷硬派」出發而予人以人性溫暖;屬「類型書寫」卻不拘一格,常見出格筆路。他的文思敏捷又勤於筆耕,自一九五七年正式出道以來,已出版超過五十本小說,並寫出短篇小說逾百。遂將漢密特、錢徳勒所締建的美國犯罪小說傳統,推向另一個引人矚目的高度。卜洛克一生獲獎無數。他曾七度榮獲愛倫坡獎、十次夏姆斯獎、四次安東尼獎、兩次馬爾他之鷹獎、二○○四年英國犯罪作家協會鑽石匕首獎,以及法、德、日等國所頒發推理大獎。二○○二年,繼一九九四年愛倫坡獎當局頒發終身大師獎之後,他也獲得夏姆斯終身成就獎。二○○五年,知名線上雜誌《Mystery Ink》警察獎(Gumshoe Award)同樣以「終身成就獎」表彰他對犯罪推理小說的貢獻。
「馬修.史卡徳」是卜洛克最受歡迎的系列。透過一名無牌私家偵探的戒酒歷程,寫盡紐約的豐饒、蒼涼和深沉。此系列從一九七○年代一路寫到新世紀,在線性時間流淌聲裡,顯現人性的複雜明暗,以及人間命運交叉的種種因緣起滅。論者以為其勝處已超越犯罪小說範疇,而達於文學經典地位。
相關著作:《聚散有時》《烈酒一滴》《繁花將盡》《死亡的渴望》《每個人都死了》《向邪惡追索》《一長串的死者》《惡魔預知死亡》《行過死蔭之地【《鐵血神探》電影原著小說】》《屠宰場之舞》《到墳場的車票》《刀鋒之先》《黑名單》《八百萬種死法》《酒店關門之後》《謀殺與創造之時》《黑暗之刺》《在死亡之中》《父之罪》《八百萬種死法》
譯者簡介:
│易萃雯
湖南省攸縣人,曾任中廣編譯,譯作有《惡之源》、《丹恩咒詛》、《強力毒藥》、《八百萬種死法》、《父之罪》、《蝙蝠俠的幫手》、《烈酒一滴》等書。
│劉麗真
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資深編輯工作者。譯有《死亡的渴望》《奪命旅人》《譚納的非常泰冒險》《卜洛克的小說學堂》《改變歷史的聲音》等書。
章節試閱
葛洛根的最後一夜
我們在巴黎綠吃晚餐。這家餐廳位於我們第九街公寓南邊的幾條街上。我點了甜麵包,心下狐疑,不明白這個名字打哪來,不甜也就罷了,壓根也不是麵包。伊蓮說,我只要上GOOGLE,不到三十秒,就會知道答案。再兩小時吧,我回她,等我把其他更有趣的問題弄明白了再說。
當天的魚類精選是阿拉斯加比目魚,正是伊蓮點的主餐。好些年前,一個營養學家終於說服她,把魚類視為蔬菜。起初,她把這個忠告當是美食版的誘導性毒品(gateway drug,譯註:像是大麻,容易誘惑使用者嘗試海洛因等更烈性的毒品);過沒多久,她就會劈開牛骨,吸吮骨髓。目前,她還沒進展成肉食主義者,每週大概吃個兩次魚。
八點鐘左右,蓋瑞領我們到餐桌;一個小時以後,我們對甜點說不,對義式咖啡說好。伊蓮不怎麼喝咖啡,尤其是這麼晚的時間;我的訝異一定寫在臉上。「等會兒是漫長的一夜,」她說,「我想還是保持清醒比較好。」
「我看得出來妳有多期待。」
「應該跟你差不多吧。有點像是沒有屍體的守靈夜。認真說起來,守靈夜應該是昨天,所以,今天算什麼?葬禮?」
「我猜是。」
「我一直覺得愛爾蘭式守靈,著實有幾分道理。大口大口的灌酒,直到你靈感湧現,能對逝者美言幾句。我的同胞會用布把鏡子蓋上,團團坐在硬木頭板凳上,食物一個勁兒的往嘴裡塞。我真想知道昨晚是怎樣的情景。」
「我確定他會告訴我們。」
我們喝盡咖啡,招來女侍,準備結帳。帳單由蓋瑞親自送來。我們認識他多少年?每個月固定光顧這家餐廳兩次,又有幾年的歷史?
我覺得他跟這家餐廳好像都沒變。他的神情永遠是剛想起個笑話似的;藍色眼珠閃出的光彩,多年來沒有半點渾濁。但掛在他戽斗下巴,像是金鶯鳥巢的鬍子,終究是灰白了,眼角周邊也顯出年紀來。今天晚上好像特別容易注意到這種事。
「昨晚我沒看見你。」他說,「當然啦,我是餐廳關門之後趕過去的。您那時可能已經回家了。」
「你說的是──」
「大塊頭的那地方。您朋友,不是嗎?還是我弄錯了?我這個人常犯糊塗。」
「我們是很要好的朋友。」我說,「只是不知道你們兩個也那麼熟。」
「其實還好,就是點頭之交。但他已經融入我們這裡了,不是嗎?這些年來,我只去過葛洛根十來次,但昨天一定得去一趟。」
「去致敬嗎?」伊蓮的口氣不大確定。
「順便看看街坊鄰居在酒吧前,無限暢飲。至於是看扁了人性,還是提升了對人性的期待,就看你站在哪個出發點上了。你知道嗎?親身見證一個時代的落幕,是我們這個詞窮的環境裡,用得最濫的俗套。每一齣情境喜劇下檔,總有人說,這是一個時代的落幕。」
「偶爾是會這樣。」她說。
「妳是想到『歡樂單身派對』吧。」
「對耶。」
「那是例外,」他說,「反證這種說法有多氾濫。就跟葛洛根酒吧關門一樣。曾經,它是這個區塊裡,永恆不變的存在;但很快,建築就會不見,沒人記得這裡有這麼間酒吧。我聽說他們給地主一筆超好的價錢,讓他不惜冒著激怒巴先生的風險,明明知道酒吧還在開,還是非賣不可。但我也聽說,不管房地契上是誰的名字,那棟建築的持有者,壓根就是米基。」
「你還真聽了不少傳聞。」我說,「不輸包打聽。」他承認。「很高興向兩位報告,八卦橫行的時代至今生氣勃勃,沒有落幕的跡象。」
早在我認識他之前,我的朋友米基.巴魯就是葛洛根的老闆了。酒吧位於第十大道與五十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落。附近沒地方收留的孤魂野鬼,總愛在那裡盤桓;但也有一部分人,到那裡朝聖,是對老闆表達莫名的敬意。這些年來,周遭的建築變得高大時尚起來,酒吧依舊流露出一種我行我素的自傲。新的住戶搬進重新粉刷裝潢的出租房間,或者身價高不可攀的公寓,還是喜歡進來喝一杯健力士生啤,對著牆上指指點點,研究哪個可能是彈孔,哪個不過是普通的小洞。
米基總喜歡雇用愛爾蘭小夥子當酒保,好些人剛從貝爾法斯特、德里或者斯特拉班移民過來,一口濃重的北愛口音,倒是無礙他們學會調製「野馬」或者「新星落日」。新來的菜鳥喜歡用肚子抵住吧台、挨著酒店常客坐。在地鐵忙活半個世紀的老先生,一肚子稀奇古怪的經歷,可能會告訴你,他為什麼滿手是血、如何徬徨無助。老客人聽膩了這套,只想點杯啤酒,消磨時光,等待下一張退休金支票寄到手上。
「別在星期五過來。」米基告訴我,「那是我們營業的最後一天,保證西城人傾巢而出,全都擠進來。酒吧開到所有的酒類全部倒光,我們甚至還準備了點吃的。」
「所有人都來,偏偏不歡迎我?」
「歡迎兩個字哪能形容我們的誠意?」他說,「但是,你一定痛恨不已,我想連我自己都不喜歡。如果我在這事上有選擇的餘地,保證也會溜之大吉。週六來,帶她一起來。」
「週五是你的最後一夜?」
「是啊。第二天晚上,店裡什麼人都沒有,就我們四個。酒店關門之後,不是我們最美好的時光嗎?」
我們穿過五十街,走上第九大道。在這裡,最後一個街頭市集小販,也把他們的小亭子拆了。「就像是中亞的游牧民族,」伊蓮說,「收拾蒙古包,尋找更豐美的水草。」
「他們放牧的牲口,在這兒,忍飢挨餓好多年,」我說,「有的早被本地的惡狼一口吞了。現在他們改賣T恤、仿冒的Gap,還有越南三明治。地區協會花了好些經費,添購街頭監視器,種植更多的銀杏樹。」
「你看看這些精雕細琢的燈柱,」她說,「跟我們在巴黎看到的好像。」
接近第十大道,葛洛根已經進入眼簾。酒吧位於建築一樓,其上三層的出租套房,面街玻璃全都畫上大大的白色X,向外界宣告,這棟建物即將拆除。X後面一片漆黑,葛洛根看起來也沒有燈光。我懷疑米基是不是改變主意回家去了,就在這個時候,我發現前門小窗戶,閃出黯淡的光線。
我們在人行道上裹足不前,儘管眼前根本沒有任何車輛經過。伊蓮回應我沒道破的心思。「我們一定得去。」她說。
應門的是克莉絲汀。鉛玻璃燈罩裡,流洩出柔和的燈光,照亮酒吧後方一張桌子,周邊放了四把椅子。也就這四把還在地上,其他的椅子全都翻在桌上。米基沒在桌邊,事實上,我連他的人影都沒看見。
「好高興你們兩個還是來了。」她說,「他也是。」轉轉眼睛,「『他也是』喔,聽我講,好嗎?他在辦公室裡,馬上出來。既然你們已經到了──」
她找來一個「休息」的標示,遮住小窗戶。「雙重保障。」她說。「告訴外面的人,我們打烊了,燈光也不會透出去。」
「全世界都以為妳是美裔猶太公主,」前伊蓮.馬岱小姐說,「事實證明,卻是天生的愛爾蘭酒吧老闆娘。」
「在多尼戈爾一家小得可憐的村落酒吧,」克莉絲汀說,「緊挨著寒風凜冽的斯威利湖。這是我們最喜歡的幻想。好玩的是:我以為我會樂此不疲,他也會玩得很開心,但最多三個禮拜,他就想一把火把漂亮的屋頂燒掉,打道回府。」
她領我們到桌邊。她的飲料是冰茶,我們說,聽起來很適合我們。米基的十二年尊美醇威士忌放在桌上,還有一個玻璃杯、一把小水壺。尊美醇酒瓶是清澈的玻璃,我可以清楚看到液體的色澤。我還是喜歡上好威士忌的顏色。單就這點來說,劣質威士忌的顏色,諱莫如深,無法分辨品質,只傳達出一個訊息:你很渴,非得來上這麼一杯不可。
克莉絲汀還沒把茶倒回來,米基就已經從後頭的辦公室鑽出頭來,手裡拿著個紙袋。「我花了半天功夫,好不容易找到紙袋。」他說,「好像不用個袋子裝著、把它夾在胳肢窩,招搖上街,是十惡不赦的壞事似的。我們這裡放不下,但這個偏偏又是我的最愛。」
我還沒弄懂他在說什麼,伊蓮就從紙袋子裡抽出一幅九乘十二的愛爾蘭風景畫,還用畫框鑲得好好的。
「丁格爾半島的康納爾山口。」克莉絲汀說,「看起來真像。我覺得那是我這輩子到過最美的地方。」
「這是鋼板畫,手工著色。」伊蓮說,「那時還沒有彩色印刷,所以,只好用人工,一次描上一個顏色。手藝已經失傳,這種著色鋼板畫可以說是異常罕見。」
「有好些藝術還沒失傳,」米基說,「但腦袋瓜子已經被按在斷頭臺上,等著現代科技,手起刀落,斬首示眾。」他的手先移向酒瓶,又轉向水瓶,最後還是決定拿起酒瓶,倒了一點點上好的柯克郡威士忌到玻璃杯裡。
「昨天晚上真的是熱鬧。」他說。
「我正想問。」
「喔,就跟我們愛爾蘭人的正宗派對差不多。進門前繳個二十塊,無限暢飲,把水井喝乾為止。他們其實是來幫忙清倉的。我找四個人來打工,八千塊錢也給他們平分了。」
「才一個晚上,成績不錯。」
「那是漫長的一夜,那夥兒酒客讓他們忙得雞飛狗跳。但他們拿了不少小費。想到酒不要錢,小費出手都很大方。」他舉起杯子,淺啜一口。「我站在門口收錢,整夜他媽的都得應付同一個問題。『又是房東貪得無饜?居然不管你還在開店,就把房子給賣了?』」
克莉絲汀一隻手按住他的胳膊。「從頭到尾,」她說,「在座的這位就是所謂的『貪婪房東』。」
「我是有史以來最棒的房東。」他說,「在我們頭頂三層樓裡,全都是租金管制的住客,冷暖氣帳單比房租還要高,儘管法律允許,我也懶得跟他們調漲租金。」
「聖人。」伊蓮說。
「我是啊。如果造物者有我這個房東一半仁慈,亞當跟夏娃也不會被迫搬離伊甸園了。等我死後下煉獄,要說我做過什麼好事,讓我少受點折磨,多半也是因為我善待房客。此外,還有最後的一點小甜頭:我給每個人五萬塊的搬家費。」
我說這實在是太慷慨了。
「對我來說,簡直微不足道。別問羅森史坦開口跟買家要多少。」
「我不會。」
「反正我也會告訴你。兩千一百萬元。」
「賣到好價錢了。」
「原來的金額,」他說,「兩千萬,也不算壞,只是沒這麼漂亮。然後,羅森史坦回去找買家,說他的客戶偏愛英國的傳統交易方式,喜歡基尼,不愛英鎊。你知不知道基尼這玩意兒?」
「我只知道你不是在說義大利人。」
「基尼是一種金幣。」他說,「一種古早的交易工具,滿接近現代的英鎊;但一基尼等於二十一先令,而不是二十先令。如果用基尼計價,金額會比用英鎊多五趴。我猜這種算法在十進位成為主流之後,就走入歷史;但是某些奢侈高價的頂級交易,還是有人裝模作樣的用基尼。羅森史坦跟我說,姑且一試,他也沒把握對方會吃這一套;反正見好就收,大不了退回去拿兩千萬。糾纏一陣子,他們居然同意用基尼計價。」
「所以,每個房客都拿到小禮物贈別。」
「是啊。」他放下玻璃杯。「你可以把他們想成是贏了威力彩,從每個角度來看,的確也是。不過,裡面有個小癟三,住在四樓左後方,一直覺得可以從我這裡多弄點什麼。『喔,我不知道耶,巴魯先生。你說要我搬哪去呢?我要怎麼樣才能找到付得起又過得去的住處呢?還沒提到搬家、重新安置的費用呢。』」
我好像看到克莉絲汀臉上閃過一抹微笑的陰影。
「我就看著他。」米基說,「有用手壓住他的肩膀嗎?不,我想沒有。我就是眼睛直勾勾的瞪著他看,壓低聲音。我說,我相信他可以搬,而且必須盡快搬,否則他跟他所愛的人,就會看到一個凶神惡煞站在他們面前,這樣不大安全;更何況這個人就是靠威脅恐嚇過日子的,何必鬧得這麼難看?結果,他是全大樓第一個把屋子清空的人。你能想像嗎?」
葛洛根的最後一夜
我們在巴黎綠吃晚餐。這家餐廳位於我們第九街公寓南邊的幾條街上。我點了甜麵包,心下狐疑,不明白這個名字打哪來,不甜也就罷了,壓根也不是麵包。伊蓮說,我只要上GOOGLE,不到三十秒,就會知道答案。再兩小時吧,我回她,等我把其他更有趣的問題弄明白了再說。
當天的魚類精選是阿拉斯加比目魚,正是伊蓮點的主餐。好些年前,一個營養學家終於說服她,把魚類視為蔬菜。起初,她把這個忠告當是美食版的誘導性毒品(gateway drug,譯註:像是大麻,容易誘惑使用者嘗試海洛因等更烈性的毒品);過沒多久,她就會劈開...
推薦序
跟馬修.史卡德一起成長
布萊恩.柯普曼(Brian Koppelman)
一九八〇年,我快滿十四歲的前夕,我說服父母讓我獨自搭乘長島鐵路去曼哈頓,目的地是西五十六街的推理書屋。就在那裡、就在奧圖.潘澤勒(Otto Penzler)第六大道與第七大道間的店裡,我第一次遇見馬修.史卡德。
推理書屋是一個讓人望之生怯的地方,尤其是就書店而言。進了門,下一層階梯,身後沉重的大門猛然關上;書屋裡沒有輕音樂,一片死寂。店內也沒別的顧客。沒有笑臉迎人的服務台,只有一個沉默的大鬍子,坐在櫃臺後面,很神奇(也有些微的干擾),模樣像煞了一九七〇年代史蒂芬.金的作者宣傳照。我得這麼說:書屋就是個賣書的地方,何必把氣氛弄得那麼緊張。
那時候,我多半讀的是諜報小說。但我踏上處女行程,搭乘長島鐵路華盛頓港線,卻想開發新的閱讀領域。至於目標是什麼,卻也沒個準兒;顯然不妙,因為這意味著我得走到櫃臺前,跟那位有點陰森森的史蒂芬.金老闆攀談。他手上的書讀得正入神,一副完全不想被來自拿索郡小鬼打擾的模樣。
我不知所措,在櫃臺前,站也不是,走也不是;好不容易,他的眼神才從書本上抬起來,遊移一會兒。我鼓起勇氣,請他推薦。
「你喜歡哪種書?」他問。
我支支吾吾、這個那個的,自己也講不清楚。
「你是喜歡逗趣的嗎?」
「不盡然。」我說,「我想讀些能感受到真實社會情況的小說。」
「喔,」他說,「你大概準備好了,可以讀點冷硬派的作品。」
「冷硬派」。在此之前,我還沒聽過這個名詞,但感覺起來好像很對味。尤其是我還得「準備好」才能去看。
「好,」我說,「請給我一些冷硬派的作品。」
他伸手到櫃臺後方,取出三本書。
「這就是你要的。」他說。他遞給我的三本書,分別是:《父之罪》、《謀殺與創造之時》與《在死亡之中》。「這是勞倫斯.卜洛克的作品。」
我付了錢,朝賓州車站走去,搭上停在月台的列車,找了個位子,就開始讀《父之罪》。過了一會兒,列車才啟動。
五十五分鐘後,我幾乎錯過我家那站。
我媽開車到車站接我,一路上,我想我應該沒跟她講上兩句話,始終埋頭苦讀。我只記得我走進大門,跟我的姐姐妹妹點點頭,直直走進我的臥室,把整本書一口氣讀完。
孿生史蒂芬.金真沒說錯。馬修.史卡德真的就是我要的。
我風急雨驟的讀完這幾本書。我不大明白:為什麼我跟史卡德的經歷,絕無重疊之處,卻能被他的遭遇緊緊鎖住,無法自拔──我沒喝過一杯烈酒、沒殺過人(無論是蓄意還是失手)、幾乎沒親過女孩 ── 不知道為什麼,馬修的一舉一動,就是能說服我。
也許因為在他身上,我看不到半點虛假。馬修想要喝酒,他就來一杯;想要打架,就動手。他不想跟你講話,就不開口。就算你是他的客戶,他也不想討好你,不想跟你吹噓他一定能解決你的疑難雜症,甚至不願意承諾他會盡力幫你。
史卡德並不天真。他知道這世界本質上就是扭曲的,只是他不屑跟著變形去適應。他可能會向警察行賄,套點消息;但他絕不欺騙自己。因為他知道一旦對自己也不肯誠實相待,最終會付出難以估量的慘痛代價。
像我這樣十幾歲的青少年,正在承受外界鋪天蓋地的壓力,迫使你宣稱要成為最好的自己、迫使你懷疑所有成人都是騙子。史卡德拒絕跟這些狗屁妥協,精準的打中我的心坎。他一身缺點,是那樣破碎的英雄。我閱讀諜報小說,裡面的間諜全都是超人,史卡德只是緊緊揪住他僅存的人性、技能與格調。他心知肚明。誠實以告讀者。我就是欣賞他這一點。
至今,我對馬修的喜愛,不曾改變。在讀完《在死亡之中》,我下定決心要讀遍馬修.史卡德的小說。不像我在十來歲時立下的其他誓言,這個承諾,我始終信守。在某個時間點上,不確定是自覺或無意,勞倫斯.卜洛克決定把自身最巨大、最深刻的部分,融進這個角色中。馬修.史卡德年歲漸長,不再喝酒、不再召妓、不再……幾乎戒斷了所有誘惑;只有在他義憤填膺或者基於休戚與共的關切,才會誘使他重操舊業。
即便我造訪推理書屋(現在已經搬離下城)的頻率,不像以往密集;即便我讀小說的時間越來越短;現在的我距離十四歲的我,越來越遙遠,但我眷戀的眼光,始終不曾離開我的老朋友。
我現在已經有了個十五歲的兒子。兩週前,他展開人生第一次的個人火車之旅。這一趟,目的地是華盛頓DC,路上想找本書讀。我陪他走到書架旁,抽出《父之罪》。「這就是你要的。」他微笑。我想他渴求的程度應該不及我當年的一半。
合集的最後一個故事,講的是馬修跟巴魯。兩人的交情超過二十年,已經成為這個系列的靈魂,比起小說中其他有關友情的描述,我的感觸更深。勞倫斯.卜洛克在馬修.史卡德系列中,寫下兩人生死以之的交往,這一頁傳奇讓無數讀者為之動容。這是人與人之間的諸多可能、相互扶持、兄弟情懷,乃至接納、榮譽與真誠的一種肯定。更重要的,其中還有寬容。兩人對坐終夜,正是寬容的具體展現。他們長談,偶爾放聲大笑,偶爾相對無語,直到破曉的曙光,鑽進葛洛根的窗戶。這是我們所有人的避風港,沒人需要接受審判與譴責,我們大可從容做自己,儘管遍體鱗傷、滿身罪孽、落魄潦倒。他們有缺點,馬修與米基,但他們也完美。花時間跟他們作伴,我相信我們也是。
閱讀馬修.史卡德
冬陽(推理評論人,前臉譜出版主編)
我與馬修.史卡德的相識,當然是從閱讀開始。
一九九七年,剛考上大學的那年暑假,我在高雄的明儀書店見到一本酒紅色書封,一對銳利的眼睛浮現其上,英文書名「EIGHT MILLION WAYS TO DIE」斗大、中文書名「八百萬種死法」像只是點綴,陳列在翻譯小說新書區。「好大的口氣。」我心想。在推理小說裡讀到千奇百怪的死法並不稀奇,數量可以到八百萬?是要挑戰世界紀錄嗎?
我翻開書,讀起唐諾撰寫的導讀,這段話解開了我的疑惑:「為什麼是八百萬?答案是,八百萬是整個紐約市的總人口數(當時),全紐約人全死光是什麼意思?當然,小說沒這麼狠,這只是說一種可能性、一種合情合理的假設,真正的意思接近台灣名小說家朱天心所說的:免於隨時隨地皆可死去的自由。」很好,這段文字打動了我,或說徹底勾起了我的好奇,於是從平台上挑選一本結帳去。
如果我的記憶沒遭到扭曲變造,應該是用兩個晚上熬夜讀完了這本書。然後,在闔上書的那一刻,我做了跟馬修一樣的事──就寫在這本小說的最後一行。
那兩個晚上,顛倒了我對推理小說的看法與感受,彷彿倒置過來的沙漏,偵探的形象與犯罪的陳述和解決帶給我強烈的衝擊。這是作者勞倫斯.卜洛克熟悉推理書寫脈絡而有意為之的安排,尤其待全書系繁體中文版出版告一段落、我重新按寫作時間序順讀下來後更是確信。
奧古斯都.杜賓、夏洛克.福爾摩斯、赫丘勒.白羅、艾勒里.昆恩之流的大偵探,處在浪漫古典的國度中,信仰純粹的邏輯理性,用提出批評的旁觀角度檢視犯罪,視凶手為對弈且必為手下敗將的高尚人士,自己是那撥亂反正的絕對力量。他們幾乎不沾染,甚或偶爾凌駕法律裁罰,建立起一種獨特的階級身分出入欲望滿溢的人性幽微,連帶讓閱讀者享受童話般的純淨美好,裡頭只不過有幾具遭精心謀殺的屍體爾爾。
馬修.史卡德則置身於存在八百萬種死法的紐約。他從巡邏員警幹起,腰上少了一塊鐵就覺得不對勁,送到眼前的錢他不會拒絕,否則怎能靠微薄的薪水安養妻小。同僚間的許多事他可以睜眼閉眼,唯獨謀殺這事沒法妥協,當了十五年條子選擇離開並不是突然想通不該再同流合污,而是一發沒擊中搶匪的流彈射進了七歲女童軟綿綿的眼裡腦裡,也就此離開他當丈夫與父親的身分,蝸居在五十七街上的一間旅館。
他能怎麼餬口過活?過去的本領還堪用,於是在阿姆斯壯酒吧一隅喝著加了波本威士忌的咖啡,聆聽委託人的陳述。他拒絕的次數比同意還多,幫不喜歡的人忙相對比較沒負擔,沒有私家偵探的執照、不會提供格式完整的報告、就連收費也沒個標準可言,到手的錢則是固定會去幾個地方:寄張匯票給前妻、付清長期租住旅館的費用、捐出十分之一給當時還開門營業的教堂,順便為自己記得的死者點上蠟燭祈福。
馬修.史卡德經手的案件──更精確地說,是寫在書冊供讀者參與其中的案件──總先設立一個前提,那就是委託人不見得能得到想要的答案,更可能觸及無法預料、極可能難以承受的不堪黑暗。這段從馬修口中提出的告誡不只說給委託人聽,同時也聽在陳述者自己耳裡,並且透過文字進到閱讀者的腦海中。當偵探「抬起屁股去敲門」、追尋可能拼湊出真相的零散線索時,也展開了一場紐約這城的巡禮,晃晃悠悠地見識到形形色色的人、光怪陸離的事,調查時而前進時而停頓甚至倒退,馬修也時而查案時而耽溺在自己瀕臨崩毀的信念裡。
於是,閱讀馬修.史卡德的故事,令我變得與他貼近起來。不是華生醫師緊跟福爾摩斯擔任助手兼記錄者般的貼近,而是一種宛如朋友的熟稔,知曉他的思路、猜想他的行動、預測他接下來要說的話。尤其經歷過作者卜洛克第一次訪台時近距離的接待陪伴(那時我正好任職於臉譜出版)、趁出差之便走訪史卡德熟悉的紐約──一晃眼二十三年過去,有時會令我納悶,我與馬修.史卡德的關係,究竟是閱讀還是交往。
也許就是因為這種心情,我在十二年前(二○○八)很僭越地做了一件事:編選馬修.史卡德短篇探案集《蝙蝠俠的幫手》。當時距離卜洛克第一次訪台宣傳《繁花將盡》已相隔四年,遲遲盼不到史卡德系列新作問世,於是我向主管提出一個想法:能否集結未曾中譯的史卡德短篇故事在台出版?主管同意了,作者也欣然答應,但該怎麼為這本書取書名呢?我仿效了福爾摩斯短篇集,安上了「The Case Book of Matthew Scudder」這個英文書名,並選取其中一個短篇做為中文書名,也就是「蝙蝠俠的幫手」。
之後,我為此後悔了十二年。
後悔的原因有二。一是我不該拿〈蝙蝠俠的幫手〉當書名,這實在太取巧、太不史卡德了不是嗎?卜洛克後來在二○一三年拿〈夜晚與音樂〉(The Night and the Music)當成他自己編選、也就是現在這個新版史卡德短篇集的英文書名時,我更深刻體認到當年的魯莽不成熟。二是當年未向卜洛克邀寫一篇談這些個故事的創作始末,還意外地收進一篇〈立於不敗之地〉──那應是卜洛克所寫的第一個短篇故事,但並非史卡德探案,所幸這些錯誤與補遺都在這本新版的著作中得到了遲來的修正。
因此,我們得以藉此獲悉馬修.史卡德最完整的訊息,理解他在長篇故事之間的轉折停歇日常回憶云云,又一次挑戰自我信念的冒險、另一段令人興味盎然的機巧對話、與親密夥伴重逢相聚的交心時刻……同時提醒你望向書架上那可能還有作者親簽的成排小說,是不是該抽個空會一會這位老朋友了?
跟馬修.史卡德一起成長
布萊恩.柯普曼(Brian Koppelman)
一九八〇年,我快滿十四歲的前夕,我說服父母讓我獨自搭乘長島鐵路去曼哈頓,目的地是西五十六街的推理書屋。就在那裡、就在奧圖.潘澤勒(Otto Penzler)第六大道與第七大道間的店裡,我第一次遇見馬修.史卡德。
推理書屋是一個讓人望之生怯的地方,尤其是就書店而言。進了門,下一層階梯,身後沉重的大門猛然關上;書屋裡沒有輕音樂,一片死寂。店內也沒別的顧客。沒有笑臉迎人的服務台,只有一個沉默的大鬍子,坐在櫃臺後面,很神奇(也有些微的干擾),模樣像煞了一九...
目錄
窗外
給袋婦的一支蠟燭
黎明的第一道曙光
蝙蝠俠的幫手
慈悲的死亡天使
夜晚與音樂
尋找大衛
夢幻泡影
一時糊塗
米基.巴魯瞪著空白螢光幕
葛洛根的最後一夜
窗外
給袋婦的一支蠟燭
黎明的第一道曙光
蝙蝠俠的幫手
慈悲的死亡天使
夜晚與音樂
尋找大衛
夢幻泡影
一時糊塗
米基.巴魯瞪著空白螢光幕
葛洛根的最後一夜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5收藏
5收藏

 9二手徵求有驚喜
9二手徵求有驚喜




 5收藏
5收藏

 9二手徵求有驚喜
9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