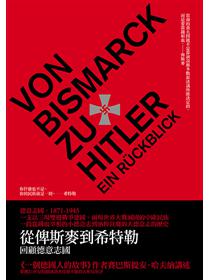讓你睡意全無、不敢喘氣、數度淚崩的懸疑推理小說
拷問人性的光明與黑暗、純真與複雜
同名電視劇拍攝中 2021即將上線鄭執,「匿名作家計畫」首獎得主
華文創作圈備受矚目、青年暢銷作家
橫跨影視與文學創作,多部作品改編上映二○一三年,一具妙齡屍體橫陳在爛尾樓「鬼樓」的雪坑裡,腹部被刻上了一枚神祕的圖案,作案手法與十年前鬼樓姦殺案如出一轍,當年負責此案的刑警馮國金,在查案過程中失去了一名年輕同袍,關鍵錄影資料憑空消失,疑犯也在追捕中遭槍擊成為植物人。如今兇手再度現身,難道十年前真的抓錯人?
「小孩子的惡是純粹的惡,成年人的善是複雜的善。」黃姝,花樣年華的美麗少女,也是刑警馮國金女兒馮雪嬌的同班好友,自小家庭破碎,寄居舅舅家。秦理,八三大案犯人之子,越級就讀的天才。兩人因悲慘的身世,飽受同學的訕笑與欺凌,遭友人背叛與傷害,殘酷的青春往事歷歷,卻始終相互依持,直到黃姝陳屍鬼樓雪坑,秦理的哥哥秦天成為首號疑犯,秦理也與所有人失去聯繫。
「為了照亮她的生命,你將自己付之一炬。」現實中不存在純粹的光亮。人性的最初都是非黑即白,兩者勢均力敵,大多數成年以後,都是白不勝黑。黃姝與秦理都被現實的黑暗生吞活剝,仍成為照亮彼此生命的點點星光。作者鄭執透過書中五位好友的生命故事,闡釋人性中的「黑白戰爭」,在不純然的善與惡中,每個人都是戴罪之身。
作者簡介:
鄭執
作家,編劇。1987年出生,瀋陽人。19歲出版長篇小說處女作《浮》,2007年至今出版多部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代表作:《生吞》、〈仙症〉等。2018年12月於首屆「匿名作家計畫」大賽中憑藉短篇小說〈仙症〉奪得首獎;2019年獲首屆「鐘山之星文學獎」、「遼寧文學獎」。多部小說已被改編為影視劇,全部由本人擔任編劇。同名小說改編電影《我在時間盡頭當你》已於2020年8月上映,收穫五億人民幣票房;《生吞》改編短劇集即將於本年底開機;〈仙症〉改編電影也將於2021年初開機。
章節試閱
楔子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聖經.新約.約翰福音》
以「金」字頭命名的洗浴中心在本市至少有五家,那還是二○一三年以前,如今可能更多,也可能更少—二○一六年以後,我再沒回去過,所以不清楚。二○一六年我媽搬來深圳給我帶孩子,直接把我爸的墳也遷過來了,擺明沒打算再回去,說那裡已經沒什麼值得掛念,我反正無所謂—說回洗浴中心,那五家金字頭都是同一個老闆,準確說是同一撥,一共七人,部隊裡拜過把子,有錢一起賺,後來陸續復員轉業,其中一人的爹是軍區後勤領導,有資源,由他牽頭,幾人先跟老毛子搞了幾年邊貿,後攬工程搞拆遷,最後進軍餐飲服務業,開酒店,幹洗浴。七兄弟一股繩,社會上沒人敢惹,四十歲以後,出門別人都叫爺。
剛幹洗浴那會兒,七兄弟就對外放話,往後市內所有洗浴中心起名都不准帶「金」字,否則後果自負,所以但凡在本市見到「金」字打頭的場子都是他們的,除非趕上嚴打,平時踏實消費,老闆方方面面擺得平,但萬別想在裡面惹事。七爺排行最小,但歸他名下那家洗浴最大,叫金麒麟,○三年出了次大事,七爺的司機在自家場子裡讓人給砍了,泡澡池子染成紅海,二十米長的景觀魚缸裡養的兩條小鯊魚聞到血腥味都瘋了。砍人者是個中年男人,警察調出監控,男人在前臺領了手牌,換了拖鞋,但沒人注意到他從背後的女款書包裡抽出一把剁骨刀,幾步穿過更衣室,直奔池子裡正泡澡那司機,十三刀,一共不用八秒,司機背後紋的青龍被砍成幾截,後腦那刀最深,在場的幾個小弟沒一個敢上前。男人砍完背回書包,刀隨手扔進中藥池子裡,穿著拖鞋徑直走人,手上的血一路滴至門外的停車場。那天是臘八,剛下過一場大雪,地上像開了一串梅花。
中年男人從始至終沒說一句話。
案子歸馮國金跟,當時他剛剛升市刑警隊副隊長。刀跟鞋都留在現場,相貌也掌握了,人第二天就被逮到,壓根兒沒打算躲,金麒麟的拖鞋還在家穿著呢。帶回去一審,宋某,四十五歲,下崗五年了,在南市場八卦街修自行車,老婆跟人跑了,自己帶閨女,老老實實一人,怎麼跟社會人扯上了?老宋主動交代,女兒讓那司機給欺負了,才十五歲,事後割過一次腕給救回來了。老宋不是沒想過往上告,但那司機往他女兒書包裡塞了兩千塊錢,硬說是嫖,還恐嚇老宋,告也沒用,自己跟七爺的。後來老宋女兒就割腕了,在醫院搶救了一宿,老宋守著沒合眼,直到聽大夫說命救回來了,才紅著眼回到南市場,跟肉檔大老劉借了把剁骨刀,坐了十二站公交到的金麒麟。打車他捨不得,錢得攢著給女兒念大學。馮國金聽了,心如刀絞,他自己也有女兒,叫馮雪嬌,跟我是從小學到高中十二年的同學,小學還是同桌。○三年馮雪嬌十五,跟老宋女兒同歲,所以馮國金越想越難受,但他還是在審完人的第一時間跟七爺通了個電話,七爺也急,自己的人在自己場子裡出事,面子上說不過去。司機沒死,不是人命案子,七爺知道理虧,問有沒有可能私了。馮國金說,老七,這兩碼事,老宋肯定得判。七爺說,那你幫找找人,想辦法少判幾年,錢我出。這事後來馮國金確實幫忙了,就算沒有七爺他一樣會這麼做,他心裡堵得慌。老宋蹲了五年,期間七爺還託人往號子裡送過不少吃用,老宋女兒念大學的學費也是七爺出的,但只出到大二—大二下學期,老宋女兒在學校宿舍跳樓了,因為失戀。老宋出來後,給女兒下了葬,繼續回到八卦街修車,五十出頭,頭髮全白了,看著像七十。馮國金幫老宋介紹過在小區停車場打更的活兒,老宋說心領了,修車挺好,來去自由,夠吃就得。那個司機,傷好後被七爺趕去鄉下農莊餵藏獒,有次籠子沒鎖好,讓一隻瘋的給咬了,染了狂犬病,怕光怕水怕聲響,成天躲屋裡不敢出來,後來聽說是死了。
馮雪嬌跟我憶述整件事時,已經是十年後,二○一三年,在北京。凌晨兩點,兩個人赤裸著躺在漢庭的床上,之前都斷片兒了,做沒做過不記得,後來種種跡象顯示應該是沒做。可是為什麼會脫衣服呢?酒是在高中同學聚會上喝的,大學畢業快三年,混得不好的都找借口不來,就我臉皮厚,工作沒了還有心跟人敘舊,就為貪口酒喝。那段日子我幾乎是在酒精裡泡過來的。馮雪嬌當時剛從美國回來,南加大,影視專業研究生。我們也有三年沒見了。我不明白,馮雪嬌突然給我講起十年前的案子是什麼意思,為避免尷尬,還是別的什麼目的。馮雪嬌解釋說,別人其實不了解,我爸那人心挺軟的,這麼多年,他一喝酒就提老宋。我說,確實沒看出來,我們都怕你爸,長得磣人,要不說是警察,還以為黑社會呢,幸虧你長相沒隨你爸。馮雪嬌在被窩裡踹了我一腳。
我躺在床上抽菸,沒開燈,馮雪嬌跟我要了一根。大概因為沒醒酒,我說了句後來令自己特別難堪的話。我說,嬌嬌啊,我現在沒出息,眼瞅又要回老家了,咱倆沒可能吧?馮雪嬌扭頭衝我,黑暗中我也能感受到她眼睛裡迸出的詫異:你沒毛病吧?就你現在這德行,走大街上絕對不帶多看你一眼的,幸虧有童年回憶給你加分,一分一分扣到現在,還不至於負數,你再這麼混下去,哪天變負分了,可別怪我提褲子不認人。說完提褲子一句,她自己笑了。我好像突然不認識她了,不開燈都快想不起她模樣。為緩解尷尬,我岔一句說,咱們同學裡,這幾年你還跟誰有聯繫?馮雪嬌想都沒想說,秦理,在網上聊過幾次。我承認,當我聽到秦理的名字,還是渾身一震,說不出話,彷彿被一隻從黑暗中伸出的手扼住了喉嚨。
馮雪嬌摸了半天開關,最後按開的是浴室燈,光透過廉價酒店的磨砂玻璃漫上床,馮雪嬌坐直身,又跟我要了根菸,生疏地抽了兩口,神神祕祕地說,我跟你說這個事,你得發誓一定不能跟第三個人說。她的表情好像小學五、六年級時偷偷跟我講咱班誰誰又跟誰誰好了,幼稚得可笑。我說,行了,趕緊吧。馮雪嬌說,我爸最近又跟了一個案子,女孩十九歲,屍體發現時已經凍僵了,扔在鬼樓前的大坑裡,赤身裸體,腹部被人用刀刻了奇怪的圖案,聽著耳熟嗎?我本能反應坐起身,說,跟十年前一模一樣,秦天幹的。馮雪嬌點頭說,對,可是秦天幾年前就死了,死前一直都是植物人。我反問,那又能說明什麼?馮雪嬌說,說明十年前,我爸可能真抓錯人了。
有沒有可能是模仿作案呢,像美國電影裡演的那些變態連環殺手一樣?很快自己又否定這種想法,畢竟我們那裡不是美國,生活也不是電影。馮雪嬌繼續說,要是這個案子翻案,我爸這輩子都過不安生了,你說,秦理他哥不會真是被冤枉了吧?我說,別瞎想了,當年鐵證如山,秦天該死,你爸是英雄,全市人民都知道。馮雪嬌好像聽不見我說話,自己跟自己說,我爸心真挺軟的,除了老宋,這些年他心裡最不踏實的就是秦天、秦理哥兒倆,主要是秦理,以前我爸總說,秦理本來能有大出息。我問她,你餓不餓,給你泡碗麵啊?馮雪嬌說,不餓,記得你答應我,千萬不能跟任何人說。我說,知道。不過我現在還沒醒酒,不確定你剛才講的一切到底是真是假,等我明早睡醒了再想想,太像夢了。馮雪嬌反問,你指哪個不真實?老宋還是秦理?我說,所有一切都不真實,包括你。
水開以後,我給自己泡了碗康師傅,等麵好的三分鐘裡我給馮雪嬌把一杯熱水吹成溫的。馮雪嬌說,以前沒發現,你還挺體貼,壺刷了麼?我說,刷什麼壺?馮雪嬌說,國內賓館裡的壺都得刷過再用,聽說很多變態往裡面放噁心東西,不刷不敢用,除非渴死,我一般都不喝。我說,是不是所有從國外回來的人都跟你一樣矯情?剛說完,我才發現自己是全身赤裸暴露在椅子上,而馮雪嬌靠在床上用被遮住脖子以下,這樣似乎不太公平。馮雪嬌的脖子特別長,她眼帶醉意地盯著我看,我下意識夾緊雙腿,把她給逗樂了。她把菸捻了,說,王頔,聽我一句,回家以後好好找個工作,找個正經女朋友,踏踏實實過日子,要不然白瞎了,知道嗎?
我點點頭。麵泡好了,才發現叉子被我壓麵餅底下了。
我的人生似乎一直在重複犯類似的錯誤,當時看著沒多重大,等發現時已經滿盤皆輸。
大二那年冬天,我爸的生命突然就只剩兩個月了,所有事一瞬間都不歸他說了算了。他的肺和一半的肝上長滿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因為一場半月不退的高燒才查出來,此前他已經有十幾年沒去醫院體檢過了。在我記憶裡,他體壯如牛,力大無窮,我六歲那年,隔壁小區一個經常欺負我的盲流子被他用單手揪到半空中後又丟出去好幾米遠,臉都摔花了,打那之後我都再沒跟他撒過嬌,在學校犯什麼錯誤也變法兒瞞著,怕他把我揪起又丟出去,再也回不來了。如此一副軀體,當得知留在世間行走的時間只剩兩個月後,可能一時間還沒反應過來,繼續推著他那輛倒騎驢,又出去賣了三天炸串,生意居然比平時還好,大概天剛開始轉冷,大家都願意吃點熱乎的。直到後來實在站不住了,才被我媽強行送進醫院,又過半個月,軀體已經無法下床了,我媽才給我打電話,叫我從北京趕緊回去。他去世前的每一個夜裡,我都在他身邊陪床,有幾個晚上我媽回家洗衣服不在,總感覺他有什麼話想交代,但又沒什麼可交代,有一次他跟護士要了紙筆想寫遺囑,下筆卻發現除了「遺囑」兩個字本身,沒什麼好寫的,一沒財產二沒遺願,家裡唯一的老房子寫的是我媽名,最後反覆要我答應照顧好我媽,另外說自己早年買過一份保險,受益人是我,算了算死後能給我留七萬多—七萬四千五百零六塊六,他的命最後值這麼多錢,都放我手裡了。大三那年,我背著我媽拿出其中五萬跟同學合夥在大學校門口開了一間奶茶店,想著錢生錢,給我媽減輕負擔,結果不到半年店就黃了,錢一分不剩。我媽也沒說什麼,繼續每晚推著那輛倒騎驢賣炸串,白天還要掃大街。後來我才知道,我被那個同學給騙了。有天晚上喝醉了回到宿舍,我把那騙子給打了,對方腦袋縫了十七針,我被留校察看。大四最後一個學期,專業課考試,我抄襲被抓,加上之前的處分,畢業時學校只給了我張肄業證,沒學位,去人才市場找工作,進門都費勁。畢業以後,我留在北京打各種零工,最久的一份工作也沒超過八個月,給一家房地產公司寫企畫書,一個月三千五,後來那家公司老闆捲錢跑路了,公司也就沒了。這一路走過來,到底錯在了哪一步,我至今也還是沒想通。以我那幾年的經濟狀況,就該學那些賴在北京不甘心回老家的年輕人一樣去住地下室,但我選擇厚著臉皮賴在高磊家客廳的沙發上,跟他和他的租客三個人住一起,他自己一年有半年都在出差。房子是高磊家買的,我從沒給過房租,每個月請他喝幾頓酒抵了,算是默契。高磊是我初、高中六年的同學,如果非要說一個算得上好朋友的人,那高磊應該就是—其實,本該還有三個人,馮雪嬌,秦理,黃姝。初二那年,加上我跟高磊,五個人一起發過誓,誓言具體內容是什麼不記得了,大概跟七爺和他那六個把兄弟說過的大同小異吧,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今生不離不棄。
但我們誰也不知道,至少我不知道,人生到底從哪一步開始走錯,以至於多年後的我們形同陌路,相遇離別都像發生在夢裡。而如今,其中兩個人也許已經在另一個世界裡重逢,正一起似笑非笑地看著活人繼續享福或是受罪,像看戲一樣。
楔子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聖經.新約.約翰福音》
以「金」字頭命名的洗浴中心在本市至少有五家,那還是二○一三年以前,如今可能更多,也可能更少—二○一六年以後,我再沒回去過,所以不清楚。二○一六年我媽搬來深圳給我帶孩子,直接把我爸的墳也遷過來了,擺明沒打算再回去,說那裡已經沒什麼值得掛念,我反正無所謂—說回洗浴中心,那五家金字頭都是同一個老闆,準確說是同一撥,一共七人,部隊裡拜過把子,有錢一起賺,後來陸續復員轉業,其中一人的爹是軍區後勤領導,...
目錄
楔子
雪墳
無人認領
素未相識的戀人
有光為證
天理
尾聲
楔子
雪墳
無人認領
素未相識的戀人
有光為證
天理
尾聲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2收藏
2收藏

 4二手徵求有驚喜
4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