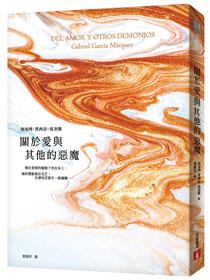母親。女兒。
天使,魔鬼?
沒被母親愛過的我,怎麼愛自己的孩子?
我感覺自己是舉世唯一無法熬過這一切的母親。
深入刻畫一位創傷母親的心靈狀態 英美文學界一出手即驚世駭俗的新聲音!
空降《紐約時報》小說暢銷榜前十大
亞馬遜總榜前百大
英國《星期天日報》暢銷榜
誠品2021年6月選書 博客來2021年1月外文選書 金石堂強力推薦
未出版即售出34國版權,第2本續集售出21國
九方投標競價,影視劇版權由《哈利波特》製片搶下
★ 吳曉樂(小說家)、劉心蕾(諮商心理師)──專序導讀
★ 周慕姿(諮商心理師)、譚光磊(版權經紀人)──傾心推薦
成為母親意謂著什麼?
如果成為人母後,一切不如你所願,甚至發展成你最害怕的情勢呢?
本書是主人翁布萊絲向前夫敘述她身為母親的困境與遭遇,向讀者開展一部懸疑驚悚的家庭故事。
我真的有能力成為好母親嗎?
布萊絲的不安溯源家族三代,她的母親,以及母親的母親都不是稱職的媽媽,每個母親都以防衛甚至折磨的方式對待女兒,而長大後她也成為一位看似神經質的媽媽......
當女兒薇歐列忒出生後,布萊絲的期待破滅了,她感受到雙方不對盤,女兒總是乖戾而拒絕合作,當她抱起女兒想要安撫卻換來尖叫淒厲,她努力想做個好媽媽卻撞得滿身是傷,她甚至覺得自己目睹女兒惡魔般的行為…...然而薇歐列忒在爸爸面前卻表現像個小天使。布萊絲和丈夫談起女兒時被視為是胡思亂想,夫妻之間也逐漸產生裂縫。
弟弟山姆出生了,在兒子身上,布萊絲終於找到期盼已久的親子之愛,姊姊薇歐列忒似乎也愛這位弟弟,看起來往好的方向進展。沒想到,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撕裂了她的家庭,當她重新回想起來驚覺,女兒好像伸手推了這一切。
親子關係是自古以來的課題,愛與恨,教與養,各種心理戰爭,本書帶領讀者進入一位母親的告白,驚悚的氛圍讀來心驚膽戰,故事的轉折讓人感到唏噓,震撼之餘也讓人反思自己與家人的親密關係。
[媒體好評]
2021年最受期待的一本書 ★ 世人往往迴避承認,身為母親,有時是一創傷經驗。《在所有母親之間》罕見地使用第二人稱,布萊絲嘗試對仳離的前夫弗克斯解釋她作為兩人孩子的母親,一路上有多麼孤獨且質疑滿斥。你很難說自己沒有從布萊絲悲傷的呢喃裡品嚐到驚人的苦澀,布萊絲仍想說服弗克斯,以母親而言,她做到最好了。也是在這些黯淡無光的告白中,我們聽見了,布萊絲始終沒有忘記,當初身為女兒的感覺有多麼疼痛。──吳曉樂(小說家)
★ 我讀過很多寫母職的有趣書籍,但《在所有母親之間》是極少數在開頭前幾頁就成功點燃一個主題論戰:人們對母親的高度期待是否合理、母職神話叩問、母性本能探究、何謂「壞母親」、父親角色的變化、祖父母和社會的價值觀等等。這本小說讓我說不完,內容更富於精闢深入的心理觀察,如此扣人心弦,深具破壞力,令人感到蠢動不安,同時害怕自己正見證一件即將到來的可怕災難,令我無法放下、無法停止翻頁地往下追讀作者究竟的布局開展。這完全歸因於小說懸疑敘事的力量,歐娟完美製造了緊張氣氛,結構凝練,她的聲音如此具有個人原創風格,這本出色小說完全征服我!──瑪莉詠.柯勒(Marion Kohler,德國企鵝出版社)
★ 我是男性,身為母親和懷孕生子的感覺,對我是陌生的。我得承認這些我都不曾思索太多。然而讀布萊絲寫給弗克斯的故事,可說是翻轉我生命的經驗。《在所有母親之間》寫得太棒,即使讀畢多時,直到昨夜它對我仍像夢一樣,儘管我常常被嚇到冒汗,有時一頁就有兩處驚悚。讀這本小說幾乎是新的身體體驗。這怎麼可能是一本處女作?我認為艾希莉.歐娟是本世紀新出爐的最有天分的創作者之一,她的聲音如此具有個人風格,刻畫精確,她的故事鋪陳和手法都極具說服力,令人難以置信。──賈柏.利斯曼(Job Lisman,荷蘭普羅米修斯出版社)
★ 本書敘事語調讓人嘆為觀止,我幾乎被它所麻痺,彷彿同時置身白日夢以及夢魘之中,為它的美而背脊發涼。──英國出版社審書編輯
★ 一部觸動所有嚴肅讀書俱樂部的張力十足的心理小說,喜歡《凱文怎麼了》的讀者也會喜愛。──克莉絲汀.漢娜(Kristin Hannah,美國暢銷作家)
★ 一部詩意,閱讀過程中一路刺激我神經的緊湊小說。──莉莎.珠兒(Lisa Jewell,美國暢銷作家)
★ 當一位母親不愛她的女兒會發生什麼事?歐娟的處女作,是一部扣人心弦的驚悚小說,深掘游移在母親主題的黑暗邊緣,透過敘事者布萊絲的故事,她釋出一個教養育兒上的問題:父母的失能是否會過繼到下一代身上?人是不是會繼承父母的失能?挑動所有讀者的神經,彷彿火車衝撞的力道般令人難忘。──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 緊張,寒意逼人……歐娟有種天分,她能捕捉看似微小然而富含張力的時刻,以此探討各種關係──《紐約時報》書評
★ 研密布局、精心刻畫,活靈活現、扣人心弦……《在所有母親之間》以狂暴充滿的歌德式元素鋪陳探索一個母親種種焦慮不安的故事。── 《衛報》
★ 一部無法停止翻讀、寒意逼人的小說,向你拋出所有挑戰問題。── 《Real Simple》雜誌
★ 一部驚悚處女作。── 《哈潑時尚 》雜誌
[本書特色]
英美文學界第一次出手即備受矚目的新作家、新聲音。
以罕見的第二人稱、情感濃烈的文風,為讀者勾勒一幅美國新大陸橫跨三代的母親畫面。
極少見的家庭驚悚小說。
以張力十足的情節帶出小說欲探討的「母親」一職與「親子關係」。
法國哲學家西蒙波娃說,女性不是生而為女性,而是成為女性。英國兒童心理學家溫尼考特曾提出,夠好的母親這樣的客體環境對孩子的人格養成之重要,本書向讀者拋問:
1.「女人」是否需透過「成為母親」來完整她的生命?
2.何謂完美的母親?不管東西方社會,人們對「母親」的標準是不是太多也太高?
3.「母性」、「親子血濃於水」,這些人們以為是天生的情感真是如此嗎?
4.不是每位母親,或每位小孩都很順利、而且幸運,而且都愛他們的母親或小孩?
作者簡介:
艾希莉.歐娟Ashley Audrain
加拿大企鵝(Penguin)圖書出版公司前行銷宣傳部總監,經手作家包括《追風箏的孩子》作者卡勒德‧胡賽尼、《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作家伊麗莎白‧伯特,現居多倫多,和她的伴侶一起養育兩個小孩。《在所有母親之間》是歐娟的第一本小說,未出版即售出34國版權,第二本續集售出21國。她以張力飽滿的驚悚家庭敘事與少見的第二人稱濃烈文風,擄獲多少文學編輯與審書人的心,在全球版權交易市場上其總預付更破紀錄高達三百萬美金,可謂英語世界一顆極具個人風格的小說新星!
譯者簡介:
王娟娟
畢業於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現定居美國加州,為專職譯者。譯作以小說見長,譯有A. S. 拜雅特短篇小說集《元素:冰火同融》、《馬蒂斯故事》、《夜鶯之眼》等三冊,《我要買個母音》、《暗房》、《神祕河流》、《暗礁》、《姊妹》、《沒有男人的夏天》及其他藝術類、語文類譯作共二十餘冊。
章節試閱
你的房子在夜裡發亮,亮得像裡頭所有東西都著了火。
她為窗子挑的窗簾看似麻料,昂貴的亞麻。透光度夠我判讀你的心情了。我看著女孩邊玩馬尾邊做功課。我看著小男孩朝十二呎高的天花板扔網球,而你的妻子穿著緊身運動褲在客廳裡四處走動、整理一天累積的雜亂:玩具回到簍子裡, 靠枕回到沙發上。
不過今晚你們卻沒拉上窗簾。也許是為了看降雪。也許是要讓你女兒找尋麋鹿的蹤影。她早就不相信耶誕老人了,卻願意為你假裝。為你,她什麼都願意。
你們全都特別打扮過。孩子們穿著成套的格子呢,坐在大皮凳上讓你的妻子拿手機拍照。女孩牽著小男孩的手。你在客廳另一頭搞不定黑膠唱機,你的妻子正在跟你說話、而你舉起一隻手指──你馬上就好了。女孩跳起來、你妻子抱起男孩,所有人開始搖擺轉圈。你端起一杯飲料,蘇格蘭威士忌,啜了一口、兩口,然後躡手躡腳走離唱機,當它是好不容易哄睡的嬰兒。你向來是這麼開始跳舞的。你接過男孩。他頭往後仰。你手一鬆,把他頭下腳上放倒。你的女兒踮起腳尖跟爹地索吻,而你的妻子接過你的威士忌。她轉向耶誕樹,調整一條燈串的位置。然後你們全都停了下來,朝向彼此異口同聲喊出同一個字,分秒不差,隨而又恢復動作──這是一首你們都很熟悉的歌。你的妻子溜出客廳,她兒子的臉自動追隨著她。我記得那種感覺。被需要的感覺。
火柴。她回到客廳,點亮裝飾著冷衫樹枝的壁爐架上的蠟燭;不知道那些樹枝是不是真的?聞起來還帶著林場氣味嗎?我放任自己想像,就一下下,想像那些樹枝在今晚你們入睡後熊熊燃起。我想像你的房子原本溫暖的奶油黃光變成一團伴隨爆裂聲的紅色火光。
小男孩拾起撥火棒,女孩在你或你妻子發現之前便溫柔地拿走了鐵棒。好姊姊。幫手。保護者。
我通常不會看這麼久,但今晚的你們好漂亮,我捨不得走開。雪,能黏結成團的雪,能讓她明早堆雪人取悅小弟弟的那種雪。我啟動雨刷,調整暖氣,注意到時鐘從七點二十九分跳到七點半。這時你通常已經為她讀了《北極特快車》。
你的妻子坐在沙發上,看著你們三人在客廳裡蹦蹦跳跳。她笑了,把一頭長捲髮撥到一側。她聞了聞你的酒杯,放在一旁桌上。她微笑。你背對著她、看不到我看到的。我看到她一手護著肚子,看到她輕撫肚子、然後低頭注視,我看到她想著肚子裡正在成長的小生命想到出了神。還只是細胞,卻已經是一切。你轉身,把她的思緒拉回眼前。拉回到她所愛的人們身上。
她打算明早告訴你。
我還是這麼懂她。
我低頭戴手套。再抬起頭來時,女孩已經站在你敞開的大門前。你門牌號碼上方的燈把她的臉照得半亮。她手上的盤子堆滿紅蘿蔔和餅乾。你晚點會在玄關地磚上撒些餅乾屑。你會配合把戲演下去,她也會。
她注視著坐在車裡的我。她冷得打顫。你妻子買給她的洋裝有點太小,我看得出她的臀部變寬了、胸部也正在發育。她伸手把馬尾撥到胸前,這動作屬於女人更勝女孩。
自她出生以來第一次,我感覺我們的女兒像我。
我放下車窗,舉起手算是招呼,祕密的招呼。她把盤子放在腳邊地上,然後再次站直轉身回到屋內。回到她家人身邊。我等著看到窗簾拉上,等著看到你開門走出來,質問我為什麼會在這樣的夜裡出現在你家門外。而我能怎麼說?說我寂寞?說我想她?說你發亮屋裡的母親應該是我?
但她只是腳步輕快地回到客廳,此時你已經說服你妻子離座起身。你倆相擁而舞, 你一隻手隔著襯衫輕撫她的後背,我們的女兒則牽起男孩的手走向客廳大窗正中央。演員就舞臺定位。這一景框得精準完美。
他和山姆好像。尤其眼睛。波浪捲的深色頭髮,那捲起的髮梢是我曾一次又一次用手指圈繞把玩過的。
我一陣反胃。
我們的女兒隔窗看著我,雙手放在你兒子的肩膀上。她彎腰,親吻他的臉頰。一吻。再一吻。男孩享受這樣的寵愛,也習慣受到寵愛。他指著落下的雪花,但她不願把目光從我身上移開。她搓揉他的肩頭,彷彿在為他取暖。像一個母親會做的那樣。
你走到窗邊,在男孩身旁蹲跪下來。你往外看,再往上看。我的車沒有引起你的注意。你指向雪花,和你兒子一樣,然後用手指在天空劃出一道軌跡。你講起雪橇、講麋鹿。他搜尋夜空,想要看到你看到的。你輕搔他的下巴。她的目光依然鎖定我。我往後靠坐,吞了口口水,終於望向一旁。贏的人總是她。
等我再次往窗子看,她還在那裡,凝望我的車。
我以為她會拉上窗簾,但她沒有。我這回不會移開視線。我拿起副駕駛座上那疊厚厚的紙,感覺自己字句的重量。
我來是為了把這交給你。
這是從我看過去的,我們的故事。
一
你坐在椅子上滑過來、用鉛筆一頭敲敲我的教科書,而我盯著書頁,不知道該不該抬頭。「哈囉?」我像接電話似地回應你,把你惹笑了。於是我們就坐在那裡,咯咯傻笑,兩個素昧平生的人在學校圖書館裡,為同一門選修課苦讀。這堂課大概有幾百個學生──我之前從沒見過你。你幾綹捲髮掉到眼前,讓你用鉛筆捲著玩。你的名字好特別。那天下午你陪我走回宿舍,我們一路沒說話。你毫不隱藏對我的著迷,不時衝著我微笑。我從來不曾得到來自任何人的這種關注。你在宿舍門外吻了我的手,我倆就這麼又笑開了。
很快,到你我二十一歲那年,我們已經形影不離。離畢業只剩不到一年。我們 擠在那張宿舍窄床上睡,醒時各據長沙發一端四腿交纏地K書,就這樣度過了一年。我們也會和你朋友去酒吧,但最後總是早退,回到家、在床上享受充滿新鮮感的彼此體溫。我幾乎不喝酒,而你則是玩夠了──你只想要我。我的世界裡倒沒人在乎。我只有一小群說不上是朋友的朋友。我專心維持好成績以免丟了獎學金,沒時間也沒興趣發展典型大學社交生活。在遇到你之前,我想我那幾年從不曾和誰真的親近過。你提供我不一樣的選擇。我們脫離社交常軌,心滿意足地活在兩人世界裡。
我在你身上找到的安適感如此鋪天蓋地──我遇到你時一無所有,於是你輕而易舉成為我的一切。這並不是說你不值得──你值得。你溫柔體貼、總是支持鼓勵我。你是我第一個吐露作家志願的人,而你的反應是:「我無法想像妳做其他事。」我陶醉於女孩們的目光,彷彿我擁有什麼值得嫉妒的東西。我在夜裡嗅聞沉 睡的你的油亮黑髮、在清晨輕觸你的毛渣下巴喚醒你。你令我沉迷。
你為我的生日寫下了你愛我的一百件事。十四,我愛妳剛入睡時淺淺的鼾聲。二十七,我愛妳優美的文字。三十九,我愛用手指在妳背上寫下我的名字。五十九,我愛在上課途中和妳邊走邊分食 一個馬芬糕。七十二,我愛妳星期天起床時的好心情。八十,我愛看妳讀完一本好書後把書緊擁在胸口的模樣。九十二,我愛妳將會是個好母親。
「你為什麼覺得我會是個好母親?」我放下清單,片刻間感覺你或許一點也不了解我。
「妳為什麼不會是個好母親?」你笑著戳戳我的肚子。「妳有愛心,又體貼。我等不及要和妳生小寶寶了。」
我別無選擇,只能擠出微笑。
我從不曾見過像你這樣滿腔熱忱的人。
「總有一天妳會明白,布萊絲。我們這家的女人⋯⋯和別人不同。」
一切還歷歷在目。我母親沾在香菸濾嘴上的橘紅唇膏。煙灰掉進杯子裡、在我喝剩最後一口的柳橙汁裡浮沉。我的吐司烤焦的氣味。
關於我母親瑟西莉雅的事,你只問過我幾次。我的回答僅止於事實:一,她在我十一歲那年離開了;二,那之後我只見過她兩次;三,我不知道她現在在哪裡。
你知道我有所保留卻從未追問──你也怕自己會聽到什麼。我了解。我們都有權對彼此與自己有所期許。對關於母親的一切也是。我們都期許自己擁有好母親、娶個好母親、成為好母親。
一九三九 ─ 一九五八
艾塔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那天。她有一雙大西洋般的藍眼睛,打一出生就臉紅而矮胖。
她愛上她認識的第一個男孩,鎮上醫生的兒子。他的名字叫做路易斯。他和其他男孩不一樣,他彬彬有禮而談吐文雅、也不在意艾塔生來就不是個美人。他每天陪艾塔走路上學,從開學第一天到學期最後一天,一隻手始終放在背後。這樣的舉動打動了艾塔。
她的父親擁有好幾百畝玉米田。十八歲生日後,艾塔告訴父親想要嫁給路易斯,而她父親堅持新女婿必須學會務農。他沒有兒子,因此希望路易斯能接手家族事業。但艾塔認為父親只是想跟年輕人證明一點:經營農場一點也不容易,是份可敬的工作,更不是人人做得來,讀書人尤其不是這種料。艾塔選擇了和父親完全不同的人。
路易斯原本計畫步父親後塵成為醫生,也已經申請到醫學院獎學金。但他想與艾塔共度一生更勝取得醫生執照。艾塔的父親不顧女兒求情,對路易斯操練嚴苛,要求他每天清晨四點起床,進入露水濃濃的田野。艾塔總不忘強調:從清晨四點到日落黃昏,卻一次都不曾抱怨過。路易斯賣掉自己父親傳給他的醫生包與教科書,把錢放進廚房流理臺上的一只玻璃罐裡。他告訴艾塔,這是為他倆未來子女所存的第一筆大學基金。艾塔認為這舉動說明了他是哪一種無私的男人。
一個日出前的秋日清晨,路易斯被芻料搬運車的攪拌葉片絞斷了腿。他躺在無人的玉米田中流血至死。艾塔的父親發現他,回頭吩咐艾塔去穀倉拿塊油布遮蓋屍體。她把路易斯的斷腿帶回家,扔到父親頭上──他原本正忙著拿桶子裝水好清洗搬運車上的血跡。
她還沒讓家人知道肚子裡的小生命。她身形圓胖,超重七十磅,根本看不出來懷孕。四個月後的一個暴風雪日,瑟西莉雅出生在廚房地板上。艾塔抬眼盯著流理臺上那只玻璃錢罐,一邊把小女嬰推送出產道。
艾塔與瑟西莉雅待在農場主屋裡安靜度日,很少去鎮上。偶爾去了倒不難聽到鎮民交頭接耳,說這女人「神經衰弱」。那時日沒人多想,所以也沒什麼好多說。路易斯的父親定期供應鎮定劑,交由艾塔母親按情況給藥。於是艾塔整天躺在從小住的房間裡那張小小的銅架床上,而瑟西莉雅則由她母親照顧。
但艾塔很快明白,像這樣每天吃藥暈沉沉地躺在床上是永遠遇不到下個男人的。她振作起來,終於開始照顧瑟西莉雅,用推車推著尖叫著找外婆的可憐小女嬰在鎮上到處走動。艾塔宣稱自己因為長期不明腹痛、幾個月食不下嚥,所以才會瘦了這麼多。這說法沒人相信,但艾塔才不在乎這些閒言閒語。她剛剛認識了亨利。
亨利剛搬來鎮上,和她上同一間教堂。他是一家糖果工廠的經理,負責管理六十名員工。他打一開始就對艾塔很體貼;他喜歡寶寶,瑟西莉雅長得尤其可愛──到頭來,人人口中的拖油瓶並不是個問題。
沒多久,亨利就為母女倆在鎮上買了一幢有著薄荷綠飾框的都鐸式小屋。艾塔永遠離開了那張銅床,也把失去的體重全都補了回來。她全心投入佈置新家。蓋得結實牢固的前廊垂著鞦韆,每扇窗子都掛上蕾絲窗簾,廚房烤箱時時烤著巧克力碎片餅乾。一回,艾塔訂購的客廳家具給送錯了地址,鄰居太太也老實不客氣讓送貨員把家具搬進地下室擺放妥當。艾塔發現後,顧不得一身家居服和滿頭髮捲便衝出門追卡車,一路高聲咒罵髒話。這事後來讓眾人傳為笑談,到最後連艾塔本人都忍不住笑了。
她非常努力做個符合期望的女人。
好妻子,好母親。
一切看來都不會有問題了。
二
回想最初的我們,幾件事浮上心頭:
你的父母。這對別人來說或許沒這麼重要,但你和你的家人密不可分。於是他們也成了我唯一的家人。大方的禮物,送我飛去某個陽光普照的地方和你們共度假期的機票。你父母家永遠散發著剛洗過床單的溫暖氣息,讓我去了就永遠不想離開。你母親輕碰我髮梢的撫觸令我直想窩到她懷裡。我有時甚至覺得她愛我就跟愛你一樣深。
他們對我父親住在哪裡、對他拒絕一起過節的邀請一句話也沒多說,只是接受而毫不評斷,這樣的善意我感激不盡。當然,瑟西莉雅的名字從不曾被提起;你在你第一次帶我回家前就體貼地交代過他們了。(布萊絲很棒,真的很棒。不過有件事⋯⋯)我母親不是你家人會聊起的那種人物。你們聊的從來不會是不愉快的事。
你們全都如此完美。
你叫你小妹「小可愛」而她崇拜你。你每晚打電話回家,我站在走廊聆聽,好想知道你母親跟你說了什麼讓你笑得這麼開心。你每兩個週末回家一趟,和你父親一起打理粗重家務。你們擁抱。你照顧年幼表弟妹。你熟記你母親的香蕉蛋糕食譜。你記得你父母的結婚紀念日、每年都給他們寄卡片。我父母甚至不曾提起過他們的婚禮。
我父親。我打電話留言告訴他我那年感恩節不回家,他沒有回電,但我卻騙你說他很高興我遇到好對象,騙你說他祝你們一家感恩節快樂。事實是,我認識你後就很少跟他講到話了。我們主要靠彼此的答錄機互通訊息,但內容不脫基本問候, 千篇一律到我不好意思讓你聽到。我至今不明白我和他怎麼會走到這步田地。感恩節的謊言有其必要,一如我後來零零星星撒的謊;我不能讓你知道我家一塌糊塗什麼程度。家人對你太重要了──一旦讓你發現關於我家人的真相,你對我的看法很難不改變,而這是你我都冒不起的險。
第一間公寓。我最愛在那裡的清晨時光。你拉被單遮住頭臉企圖賴床的模樣,你在我們枕頭上留下的濃濃的大男孩氣息。我那時多半日出前即起,跑到冷得要命的長廊形廚房一頭寫作。我穿著你的浴袍,用我在陶瓷彩繪工坊畫給你的馬克杯啜飲熱茶。再過一會,等地板暖起來、而透過百葉窗光線足以讓你看清我的肌膚紋理時,你就會輕喊我的名字。你會把我拉回床上,然後我們一起實驗探索──你大膽堅持,比我還明白我身體的能耐。你令我著迷。你的自信、你的耐心、你對我的原始需索。
葛蕾絲來訪的夜晚。她是我畢業後還保持聯繫的大學朋友。我從沒讓你知道我有多喜歡她,因為你似乎對她和我共度的時光有些嫉妒,也覺得我們喝太多了;雖然以女性友誼的標準來說,我給她的時間一點也不多。但你卻在她和男友分手那年的情人節,為我們兩人都買了花。我大約每個月邀請她過來晚餐一次,你總是坐在翻過來充當第三張椅子的垃圾桶上加入我們,也總會在下班回家路上去買瓶好葡萄酒回家。當聊天進入八卦話題而葛蕾絲拿出香菸,你會禮貌地告退,讀起自己的書。一晚,我倆在屋裡抽菸(很難想像吧?)聽到你在陽臺上和你妹妹講電話。她剛和男友分手,打電話給她的哥哥、也是她最好的朋友訴苦。葛蕾絲問我你到底哪裡有毛病。床技不佳?脾氣壞?一定有哪裡不對,因為世上沒有這麼完美的男人。但你確實沒有哪裡不對。當時沒有,就我瞭解沒有。我只能稱之為運氣;我很幸運。我擁有的不多,但我有你。
你的房子在夜裡發亮,亮得像裡頭所有東西都著了火。
她為窗子挑的窗簾看似麻料,昂貴的亞麻。透光度夠我判讀你的心情了。我看著女孩邊玩馬尾邊做功課。我看著小男孩朝十二呎高的天花板扔網球,而你的妻子穿著緊身運動褲在客廳裡四處走動、整理一天累積的雜亂:玩具回到簍子裡, 靠枕回到沙發上。
不過今晚你們卻沒拉上窗簾。也許是為了看降雪。也許是要讓你女兒找尋麋鹿的蹤影。她早就不相信耶誕老人了,卻願意為你假裝。為你,她什麼都願意。
你們全都特別打扮過。孩子們穿著成套的格子呢,坐在大皮凳上讓你的妻子拿手機拍照。...
推薦序
[推薦序一]
聖母的起點,女人的終點──《在所有母親之間》
吳曉樂(小說家)
作家李維菁寫過一篇文章〈隔壁家的小孩更適合當我媽的女兒〉,描述一女同學,舉止儀度都合於她母親的心水,「她的婚姻觀是我媽喜歡的,她的衣服是我媽喜歡的,她的髮型是我媽喜歡的,功課好又做家事,只微笑不大笑,不發表意見、不強出頭,也是我媽喜歡的」。《在所有母親之間》,女主角布萊絲深深願夢,「隔壁家的女人更適合當我媽」,她把自己畫進鄰居艾靈頓一家的故事裡。布萊絲的母親瑟西莉雅發現女兒把自己畫入黑人家庭,狠砸女兒頭頂。
故事倏地大步橫跨至數十年前,讀者恍然大悟,暴佞的瑟西莉雅也有個壞童年。她的母親艾塔個性寡淡,看似對瑟西莉雅的存在惴慄不安。據瑟西莉雅的看法,艾塔「設法學會讓自己看起來像是個符合母親形象的人」,而其他人早已放棄期待艾塔像個母親。由此可知,艾塔的「表演」並沒有說服誰,瑟西莉雅還沒成年時,艾塔選擇與女兒永別。瑟西莉雅及長,竟也「克紹箕裘」地在布萊絲差不多抵達她失去母親的年紀,拋下一切,遠走高飛。
布萊絲很早就懷疑自己的生命有個大麻煩,與弗克斯墜入情網以後,深埋在體內的警鈴於焉大作:人如何給予自己不曾擁有的事物?沒被母親愛過的我,怎麼愛自己的孩子?
數十年來,心理學者戮力研究孩童與父母的關係如何對他日後的人際發揮影響,二者之間確有關聯。不識母愛的布萊絲,質疑自己是否能模擬出近似母愛的感情?弗克斯做了跟艾塔、瑟西莉雅的丈夫,並無二致的反應:相信眼前這名女子會自然而然地成為一位好母親。弗克斯的語言並不讓人陌生,自工業革命後,性別分工趨向明確二元,男人外出工作從事有償勞動,女人待在家中進行無償付出。資本主義、異性戀霸權等意識形態攜手編寫母愛神話,維持女人在家庭內給予同情、關懷,與孩童保持親密,以維持整個體系立於不墜,經過時間流轉,「母愛」這個社會建構出的名詞,成了許多人心目中的自然生態:一旦生下孩子,母親自會懂得如何給予關懷。
每逢布萊絲陷入瓶頸,弗克斯就會策動母親二字來激勵布萊斯。他一廂情願地認定自己為家庭擘劃完美分工,他出外工作,源源供給經濟資源,布萊絲專注哺育女兒薇奧列忒。諷刺的是,布萊絲成為母親以前,曾坦承自己的作家志願,弗克斯竭誠支持,宣稱「我無法想像妳做其他事」,而在薇奧列忒出生以後,弗克斯態度驟變,處處執意育兒至上。布萊絲恍然大悟,弗克斯諾言裡的「妳」已隨著女兒的誕生而消失於世上,她只能以母親的臉孔活下去。讀者越是深入布萊絲的心聲,越能意識到「父母」二字作為一組名詞是如此投機取巧,雙方從中所領受到的責任是如此雲泥之別,卻在多數場合被並列,彷彿意義相近。歐娟細工描繪親職的懸殊落差,有一段讓人心痛,「你用腦發揮創意,創造空間、視線與視角,你的日子關乎照明、立面圖與完工。你讀的字句都是為成人而寫。你圍著上好質料的圍巾。你有洗澡的理由」。布萊絲在陳述弗克斯生活之完好、她境遇之破碎時,使用機械、抽離的聲腔,像是她也學習了對自己的苦痛置身事外。
世人往往迴避承認,身為母親,有時是一創傷經驗。曾不只一次聽到女人如此形容她們的育兒過程「孩子簡直是來討債的」。對布萊絲而言,薇奧列忒不僅阻斷了她實踐寫作願景,同時她也是個磨娘精(difficult child)。薇奧列忒只渴望父親,頑強拒斥布萊絲的接觸,布萊絲屢屢發出求援訊號,卻被弗克斯置若罔聞。出身幸福家庭的弗克斯心目中對於「完美母親」有具體擘劃,他不惜對布萊絲進行「削足適履」式的批判,只為了將妻子鑲入母親海倫的樣版。
走投無路的布萊絲亦很快地辨識出,「從哪裡失去,就從哪裡尋回」的簡單道理,她刻意忽略薇奧列忒的需求,試圖重建出弗克斯自她身上剝奪的權力感。布萊絲因冷落薇奧列忒而獲得重新掌握人生的狂喜,書中出現了不只一次,歐娟似乎遙指出寬諒艾塔跟瑟西莉雅的蹊徑:若世人把孩子跟母親的關係塑造成「此消彼長」的零和遊戲,我們也一併抹消了皆大歡喜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布萊絲的遭遇也讓人看見神話的結構如此結實,在一望無際的玉米田,在鋼鐵叢林拔地而起的大都會,布萊絲沒有得到比瑟西莉雅和艾塔還充裕的諒解與援助。所有個人的掙扎與吶喊依舊被高於一切、運轉不休的聖母形象所湮沒。
聖母的起點,何嘗不是象徵了女人的終點?
此書的另一懸念在於薇奧列忒是否天生邪惡?威廉馬奇(William March)的《壞種》(The Bad Seed)一書於1954年出版,裡頭壞得入骨的八歲女童蘿達,深刻形象啟發後續無數文本。若我們採信布萊絲的觀點,薇奧列忒之狠毒程度絕不亞於蘿達。她啟動一樁樁事件,促使布萊絲步上瑟西莉雅的後塵,被家庭長久隔絕。然而,我們也應對布萊絲的陳述保持警覺,考慮她敘事殘破、心智搖晃,我們也能臆想為布萊絲墜入自證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陷阱,自始至終,她不曾懷疑自己有逃離家族宿命的機緣,薇奧列忒感應到布萊絲身為一個人(而非身為一名母親)對自己的拒斥,進而有意無意地延續株連四代的人性輓歌。歐娟精描故事輪廓,內裡卻有心留白,間接開展思想迴盪的空間。
《在所有母親之間》罕見地使用第二人稱,布萊絲嘗試對仳離的前夫弗克斯解釋她作為兩人孩子的母親,一路上有多麼孤獨且質疑滿斥。你很難說自己沒有從布萊絲悲傷的呢喃裡品嚐到驚人的苦澀,布萊絲仍想說服弗克斯,以母親而言,她做到最好了。也是在這些黯淡無光的告白中,我們聽見了,布萊絲始終沒有忘記,當初身為女兒的感覺有多麼疼痛。
[推薦序二]
在所有的恨之間
*本文可能透露關鍵情節
劉心蕾(諮商心理師)
這是一本你讀著讀著可能會漸漸發現不太容易消化的小說,它不只是典型的驚悚片,作者艾希莉以一種幾乎像是躺在精神分析躺椅上囈語的風格,大膽碰觸幾乎可說是禁忌的主題:親子之間的恨。
二十多年前我在紐約求學,當時曾去到美國大學女籃賽現場觀賽,即使已經過了那麼久,當時場上球員勇猛衝撞帶給我的震撼感直到今日仍然能清晰感覺到。她們的肢體動作帶著一種剽悍感,整個人仿佛被憤怒燃燒,在幾近失控的邊緣成功地把最大的能量給爆發出來。當年台灣的籃球賽風格還相當保守溫和,相較之下實在一點也不精彩,這樣的文化衝擊讓我不禁開始思考攻擊性在人生中的價值。
在精神分析線上論文資料庫裡十三萬多篇的學術論文中,最常被瀏覽的第五名是英國知名分析師溫尼考特的「反移情當中的恨」。撇開論文中專業艱澀的部分不談,溫尼考特想要說明的是,精神分析師(應該也適用於一般心理治療師)在面對充滿破壞攻擊性的病人時,心中被激起的恨意是具有客觀正當性的。看到這兒你可能會想,分析師不是應該要無條件地同理病人、接納病人嗎?但就像新手媽媽們常常被折騰到喊著想把寶寶塞回肚子裡,一個人真實經驗到被折磨而卻感覺不到恨才是奇怪的事。當然,恨意是件很難消化的事,照顧者可能會自責、自我懷疑,但被激起恨意有時候是人性上的一種必然,這是成長歷程裡關係互動中的魔王關卡。照顧者不僅得要感覺得到自己的恨意,不因為罪惡感而一味潛抑否認,更要承擔得住心裡的強烈情緒,確保在遭受攻擊下還能夠存活下來。作為照顧者的精神分析師是如此,作為照顧者的母親也是。
但媽媽真的會恨她的寶寶嗎?身兼小兒科醫師身分的溫尼考特相當熟悉母子間各種細微的情感,在他的文章中洋洋灑灑列出了十八條媽媽恨寶寶的理由,像是寶寶咬她、抓傷她、生產撕裂她、她失去了自己的世界、得為寶寶付出一切、得清他的大便、寶寶吃飽了就不要她了、她必須像神一般地理解他、滿足他的需要,而他卻視之為理所當然...... 媽媽無法不恨寶寶,雖然同時她也愛他。
小說中的布萊絲幾乎沒漏掉這一大串理由中的任何一個,而艾塔、瑟西莉雅恐怕也一樣。她們恨寶寶,而這恨更不只是他們當下恨著面前的那個寶寶,她們恨寶寶,一如她們恨自已的媽媽,一如媽媽當年恨她們這個寶寶,一如外婆當年恨她媽媽這個寶寶。她們之中沒有人有辦法消化得了這些恨,她們承擔不了,她們遇到的男人也無法為他們承擔。亨利裝作沒事發生,艾塔上吊了,賽柏軟弱無能,瑟西莉雅逃跑了,弗克斯否定他妻子的感受,而布萊絲也無法肯定自己的感覺,在這代代相傳的恨意之下,沒有人存活。這陳年的恨如是沉重,而當下面前的這個寶寶注定要接棒傳承如此強烈的恨意。
愛與恨其實是根源自人類生命的兩股本能,一邊是結合的力量,小自個別的細胞組織出器官,直到性上面的結合都源於這一股本能;而另一邊則是分離的力量,自最基本的細胞分裂、胎兒離開母體出生,直到成年離家都是這一邊的力量在推動。
小說的英文標題「The Push」簡潔有力的濃縮了關鍵的情緒,媽媽將寶寶推出產道,薇奧列忒把伊萊賈推下滑梯、把山姆的推車推向馬路......。這「推」源自於恨,但它的本質是一種分離,而分離原本是成長必須的元素。如同我們常常可以在國家地理頻道上看見的,當小熊長大成熟,熊媽媽會堅定而溫柔的把牠們推開,讓牠們知道不能再賴在媽媽身邊了。小熊之間遊戲打架,溫和的互推,這競爭是學習生存技巧的歷程。恨意不見得是負面的東西,重點在於這「推」必須是溫和的推,而不是真的攻擊。
為什麼這個家族的恨意無法像熊家族一般溫和發揮?為什麼這恨似乎綿延不絕?艾希莉在她的小說一開頭引用了《當女人是鼓手》(When the Drummers Were Women)裡面頗具啟發性的描述:曾經作為一個卵子的我們,是從母親還在祖母的肚子裡時,在她還只是四個月大的胚胎時,就在她的卵巢裡開始了我們生命的歷程。我們隨著母親血流的節奏脈動,甚至早在她出生之前。在生理上、在心理上,在我們知道我是「我」之前,「我」已經開始了漫長的旅程。
不過,我並不是在說小說中的所有這些母親只是被命運決定了而已。我們人生裡的每一個當下,我們在關係中的每一個經驗,都像是一幅自我創作的圖畫,差別只是在於你是否知道你畫筆上的顏料來自何處!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寫道:「我對著阿爾貝蒂娜說話,某個片刻就像是還在貢布雷的那個兒時的我在對著媽媽說話,另一刻又像是我祖母過去對著我說話一般。過了某個年紀之後,我們自己兒時的靈魂與那些孵育我們糾纏我們的家族亡靈,都將隱晦地執著重現於我們現下原創的嶄新情緒中。」我們每個人手中的畫筆就像是沾染了這些靈魂的顏料,但最終那幅畫依然是你本人的創作。
如果在這個故事裡出現了一個人,能打破這恨意無法被消化的循環,事情也許有機會不同。艾靈頓太太似乎差一點辦到了這件事,她有一點像是溫尼考特所說的「夠好的母親」,不是完美的,而是夠好的。夠好的母親能將這個不夠美好的世界慢慢介紹給她的孩子,她不能完全隔絕現實的稜角,她必須能帶來一些可以被忍受的挫折。現實裡不完美的母親具有一種重要的能力,她要可以真心感受對寶寶的恨,但同時又不把恨表現出來真的傷害寶寶,那麼這恨要往何處去?溫尼考特在他的文章末尾提及了一首英國的搖籃曲,他說也許在哼唱這樣的歌謠時,既讓媽媽的恨意得到了釋放的機會,而寶寶又幸運地還沒能聽懂歌詞的意義:
Rock a bye Baby, on the tree top,
When the wind blows the cradle will rock,
When the bough breaks the cradle will fall,
Down will come baby, cradle and all.[1]
[1] 筆者註:「寶寶搖啊搖,高高掛樹梢。風兒吹啊吹,搖籃搖啊搖。樹枝斷,搖籃掉。寶寶、搖籃往下掉。」為英國兒童心理學家溫尼考特在「反移情當中的恨」一文所引用的一首英國搖籃曲,一七六五年的《鵝媽媽童謠》即收錄有這段歌詞。
[推薦序一]
聖母的起點,女人的終點──《在所有母親之間》
吳曉樂(小說家)
作家李維菁寫過一篇文章〈隔壁家的小孩更適合當我媽的女兒〉,描述一女同學,舉止儀度都合於她母親的心水,「她的婚姻觀是我媽喜歡的,她的衣服是我媽喜歡的,她的髮型是我媽喜歡的,功課好又做家事,只微笑不大笑,不發表意見、不強出頭,也是我媽喜歡的」。《在所有母親之間》,女主角布萊絲深深願夢,「隔壁家的女人更適合當我媽」,她把自己畫進鄰居艾靈頓一家的故事裡。布萊絲的母親瑟西莉雅發現女兒把自己畫入黑人家庭,狠砸女兒頭頂。
故事倏地大步...
 7收藏
7收藏

 16二手徵求有驚喜
16二手徵求有驚喜



 7收藏
7收藏

 16二手徵求有驚喜
16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