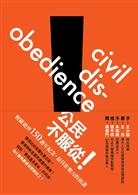我無罪──關於盧梭的《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
吳明益 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
我的靈魂是他們惟一無法從我身上奪走的東西。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記得學生時代,歷史課本提到盧梭,總是附上一幅拉突爾(Maurice Quentin de La Tour, 1704-1788)所繪的畫像,畫裡的盧梭四十一歲(1753),有著細而挺的鼻子,眼神熱情洋溢,彷彿世界對他充滿愛意。此時的他或許還無法預知(或已然預知?)隔年自己將為了「第戎科學院」 (the Academy of Dijon)的徵文寫出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不但未獲獎,還將是他的思維與當時宗教、社會對立、衝突的開始。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出版後不算順利,這本備受爭議的書中提到人類有兩種不平等,一是自然或說是生理上的不平等,另一種是精神與政治上的不平等。對於後者不平等的起因,盧梭判斷「誰第一個把一塊土地圈起來並想說: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個頭腦十分簡單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話,誰就是文明社會真正奠基者。」也就是說,在盧梭眼裡,文明社會不平等的起因就是「財產私有制」。但盧梭並未像一般哲學家幻想把社會倒推回自然階段就算了,因為他認為此刻社會已不可能回去那個自然時代,現代文明必得建立在財產私有制之上。他的思維再往前推進一層,認為文明社會得走向新的契約式的平等。當時盧梭只是隱隱然這麼覺得,當然,多年以後我們可以確知,那個概念將發展成他著名的《社會契約論》(On The Social Contract o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ight)。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並未真正讀過《社會契約論》,這本書據說即使在西方,和達爾文的《物種源始》一樣,都是最多人聽過書名,卻最少人真正讀過內容的經典之一。對學生時代的我而言,當時困擾於各種渾沌不明難以記憶的思想流派,唯有那雙熱情的雙眼令我難以忘記。我跟多數的臺灣讀者一樣,是先接受了他不算高明的小說,卻是動人教育論述的《愛彌兒》,才一步一步地讀完這位啟迪人類新時代的思想家其他著作。
當我讀到這批題為《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的書稿,其中的「漫步之十」甚且是盧梭最後的文章,眼前似乎又浮起盧梭畫像裡那雙熱情的眼睛。不過,事實上寫這批文章時的盧梭已近遲暮,眼神或許只有疲憊也不再熱情。彼時他墜入嚴重的被迫害妄想症中,四處移居。倘若我們發現一年前他剛完成《對話錄》(Dialogues: Rousseau Judge of Jean-Jacques)時,想把書置於聖母院的祭壇上獻給上帝,卻未得其門而入,就可以發現不少人已經把他當成瘋子。
然而彼時盧梭當然並未瘋狂,他只是因為精神上的孤獨而陷入自憐自傷的情緒中。這本書稿的內容大致撰寫於一七七六年到一七七八年之間,其中一部分彷彿是《懺悔錄》(The Confessions)加上《對話錄》的精簡版,充滿了對論敵的回應和矛盾的自我辯解;另一些則是晚年盧梭逼視自己心靈深處的自省與自剖。而最令我著迷的莫過於他從植物標本的採集中,感到那是一項挽救自己心靈的活動。總讓人想到他在《愛彌兒》中寫的:「我把所有一切的書都合起來,只有一本書是打開在大家眼前的,那就是自然的書。正是這本宏偉的著作中我學會了怎樣崇奉它的作者。任何一個人都找不到什麼藉口不讀這本書,因為它向大家講的是人人都懂得的語言。」
我在閱讀文稿時,並沒有刻意用所謂的「文學」觀點去解讀它們,我也不建議讀者光是這麼做(雖然這系列散文確實放在西方散文史上也有很特殊的評價)。相反地,我認為讀者或許身旁若有個簡單的盧梭年表(包括他愛情、教育、著作、移棲的年表),或許才較容易進入這些皆名為「散步」的散文裡,稍稍理解這個擁有不可思議洞見、浪漫又實際,前衛且特立獨行的瘋狂靈魂,在美麗的愛爾蒙維爾(Ermenonville)腦溢血辭世的前兩年,如何逼視自己的一生。
「漫步之一」的第一句便是「我就這樣在這世上落得孤單一人,再也沒有兄弟、鄰人、朋友,沒有任何人可以往來」,充滿了「被棄」的痛苦。而令人難以接受這樣的痛苦的原因是,盧梭自認是「人類最親善、最深情的一個」。我無意在這篇短短的序文裡,一一指出每篇文章的特色,囉唆地提醒讀者,但我認為這是讀這部書稿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那就是即便像盧梭這樣的思想家,都無可避免地陷落在自我評價和他人評價落差中,直至生命消逝。因此,做為與多數人一樣的普通讀者,我每翻一頁,都不免停下來檢視自己心中對自我評價的矛盾。我以為,盧梭在散步中領悟的,不是人生足以消弭這樣的落差,而是人生「得」接受這樣的落差。因此,正如盧梭自己指出的,《對話錄》在標題上雖然是盧梭自己與自己的對話,其實卻是他與下一代人的對話,真正的思想家,有時對話的是非常遙遠的對象。
我想回到四十二歲的盧梭。當時寫作《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時,他認為人類社會的不平等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富人與窮人間的不平等。當土地私有制成立後,農田不再只是生長穀物的豐饒之地,它也成了「奴役和貧困」滋長的場所。一些人靠著取得更多的土地,逐漸變成了壓迫者。第二階段則是壓迫者和服從者間的不平等,這緣自於富人創造了宣稱是「明智的法律」來設立「契約」,漸漸形成統治者與服從者的階級。這時已不再是經濟上的不平等而已,同時還出現了政治上的不平等。第三階段則是合法的權力變成專制的權力,君主或統治者隨心所欲地壓迫統治者,形成一種主人與奴隸的不平等。由於被統治者都變為奴隸似的身份,因此除了統治階級以外的人,又都變成「平等」的了。盧梭認為這個新的狀態,終使被奴役者會群起反抗而推翻專制政府。
這樣的思維以當時的眼光來看,未免太前衛、太危險、太強悍了不是嗎?這樣的心靈,怎麼可能與那個時代順利對上話?
不過,盧梭終究還是在這最後的文稿中,處處留下「徹底、持久」的「自憐自艾的孤寂」。我以為那樣不可消減的孤寂來自於幾方面。首先,出身貧窮的盧梭,雖因好友狄德羅(Denis Diderot)等人的關係而渡過了一段「沙龍生活」(彼時法國的沙龍才是思想家、文學家的成名管道),但終究無法適應而分道揚鑣。那種被富裕生活吸引時同時被自己深層靈魂的反省衝擊的複雜感受,一直存在盧梭的心中,唯有在抄寫樂譜或投入植物調查時,才勉可稍減。其次,盧梭的愛情或許不是根植在那個與他生了孩子,同居二十餘年才結婚的黛蕾絲身上。這也是個沒有解答的遺憾,可以從他的「漫步之十」是寫給華倫夫人這位既是「媽媽」,也是「情人」的女性就可以感覺到。「我在這世上活了七十年,可真正可稱之為生活的,只有七年。」盧梭用這句話來影射了自己的愛情。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他畢竟真的將自己親生的孩子送進育幼院,雖然在「漫步之九」不斷辯駁他是因為貧窮與教養才不得不這麼做,但我相信那在盧梭的生命裡,是難以填實的一個巨大空洞。
這是盧梭最短的書,當然也是他最後一本書。那是在他漫漫長路後,以為可以為自己人生打上句點的珍貴文字。在「散步之七」中,他說在六十五歲的時候,曾想過要把瑞典植物學家穆萊(Murray)的《植物界》熟記在心,「並且認遍世上所有的植物」。這當然是做不到的譫妄之語。據說盧梭在一七六八年陷入精神病症的泥淖時,給外界的信往往以「我無罪!」作結。我並非教徒,但我一向認為,罪的本質在於罪的定義,人的一生要以自認的無罪作結,唯一的可能就是給「罪」下一個極寬鬆的定義,否則根本是做不到的事。
但正因為做不到,盧梭卻如此坦然地說出來,像宣稱自己要認遍世上所有的植物一樣,或許真的驚嚇到整個時代也不一定。就像他後來使用的,超越時代的「公眾意識」(general will)一詞,不但他自己說不清,說實在的,直到現在我們也還說不清。只是此刻我已不覺荒謬,因為歷史讓我們得見像盧梭這樣的人的孤獨身影,像每一種未曾被發現、命名、全然理解的植物,如此獨特地光輝、美麗著,並永遠在某處啟發我們看到一個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