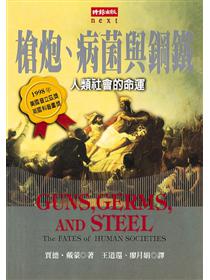第一章 順流而下
我從重慶搭一艘行進遲緩的船順流而下,來到涪陵。那是一九九六年八月底一個溫暖、晴朗無雲的夜晚,星星在長江上方閃爍,而漆黑的江水無法反映微弱的星光。學校派來的一輛車子,載我們沿著自碼頭蜿蜒而上的狹窄街道行進。小城自車窗外匆匆掠過,在星光下顯得幽暗而陌生。
我們有兩個人同行,被派到這兒任教。我們都很年輕,我二十七歲,而亞當.邁爾(Adam Meier)二十二歲。對於涪陵,我們幾乎一無所知。我知道城市的一部分將被新的三峽大壩淹沒,我也知道許多年來涪陵一直對外封閉。除此之外,我們得到的資訊十分有限。
半個世紀以來,沒有一位美國人在涪陵住過。後來,我在城裡遇見了一些年紀較長的人,他們記得在一九四○年代──即一九四九年共產黨解放中國之前,有幾個美國人住在城裡,但是這樣的記憶一直很模糊。我們抵達時,城裡有另一位外國人,一位在當地中學任教了一學期的德國人。但是我們只見過他一次,而且在我們安頓下來後不久,他就離開了。之後,我們就是城裡僅有的外國人。這兒的人口大約有二十萬人,按照中國的標準,這是一座小城。
涪陵沒有鐵路,此城向來是四川省一個貧窮的地區,而公路路況十分惡劣。如果你想去哪兒,得搭船,但是大多時候,你哪兒也不去。在接下來的兩年,這個城市就是我的家。
我們抵達後一週,學校所有人都聚集在前門。一群師生以那年暑假的時間,從涪陵步行到延安──位於山西省北部的革命創始基地;而現在,他們回到了學校。
那是共產黨長征的六十週年紀念。長征是在內戰的最關鍵時期,當國民黨即將摧毀毛澤東的勢力,紅軍展開的一萬公里長途跋涉之旅。儘管困難重重,共產黨員仍然越過中國西部的崇山峻嶺和沙漠,行進到安全之地。他們從延安一路持續擴張兵力,最後,他們的革命襲捲全國,並將國民黨驅逐到台灣。
一整個學期,校園裡不斷舉行特別活動慶祝長征週年紀念日。學生們上關於長征歷史的課,寫關於長征的論文,而在十二月,學校舉辦了一場長征歌唱大賽。為了參加長征歌唱大賽,各系的學生練唱了數週,然後來到禮堂表演。許多表演的歌曲都一模一樣,因為你實在無法以長征為主題創作太多音樂,這一點使得評審很難做出判決。這場歌唱大賽也十分混亂,因為服裝短缺,所以學生不但得共用相同的歌曲,還得共用相同的衣服。先是歷史系的學生穿著乾淨的白襯衫,繫上紅領帶,光鮮亮麗地登臺表演。表演結束,歷史系學生走下舞臺,迅速將襯衫和領帶交給政治系的學生,他們穿上襯衫,繫上領帶,匆匆登上舞臺,表演剛剛表演過的歌曲。那一晚結束時,襯衫已被汙水玷污,而每一位聽眾對於表演的歌典都已耳熟能詳。音樂系獲勝了──向來如此,而英文系差點敬陪末座。在學校舉辦的任何比賽中,英文系都不曾獲勝過。沒有人為長征寫英文歌。
但是,暑假步行到延安不是一種比賽,而涪陵隊的歸來顯然是長征季最盛大的事。他們已在中國夏日的酷熱中行進了一千五百多公里,到了最後,只有十六人走完全程,其中十三位是學生,兩位是老師:中文系黨支部書記,以及數學系的政治輔導員。另有一位低階的行政官員,他在行進中哭了起來,他的不屈不撓使他在當地獲得了某種程度的美名。所有參與者都是男人,有些女學生也想參加,但是校方判定長征不適合女孩子。
集會前的一星期,師範專科學校的李校長去到西安會見行進的學生,因為旅程結束時,他們遇上了麻煩。
我問英文系的傅慕友系主任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說:「學生們有麻煩了,我想他們可能沒錢了。」的確,他們把錢花光了,儘管他們已獲得涪陵的菸草公司──宏聲香菸公司的資助。他們長途跋步了一千五百公里,最後在延安落得身無分文,在我看來,這倒是向中國共產黨歷史致敬十分貼切的一種方式。
但是李校長幫助他們脫離了困境,而現在,師範專科學校的全體學生在前門附近的廣場聚集。這是一所規模很小的師範專科學校,註冊的學生人數僅兩千,於一九七七年開始招收學生,是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摧毀了大多數中國教育系統後創立的諸多學校之一。在中國高等教育系統中,這類專科學校幾乎位居最下層。學生修三年的課,拿到低於學士的學位,而所有學生幾乎都來自四川鄉下的農家。畢業後,他們回到家鄉,成為鄉下中學的老師。
對於許多學生而言,尤其是新生,師範專科學校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地方。校園隔著烏江和涪陵的主城對望,沒有幾位學生曾住在這麼大的城市附近。在週末,學校放映電影,舉辦各種比賽和舞會。經常有政治集會和歡迎長征參與者這類的聚會。學生們在廣場來回打轉著,因為充滿期待而嘰嘰喳喳地說著話。
由八位女學生組成的一個小組,以立正姿勢站在大門旁。她們穿著白衣黑裙,胸前有繡著學校名稱的紅色飾帶;她們被稱為迎賓小姐,是從全體學生中精心挑選出來的。所有的迎賓小姐都長得高挑而美麗,但是沒有人臉上掛著微笑。她們在正式場合代表學校,以完美的陣式站立著,走起路來從容而優雅,為顯貴和要人倒茶。
這是我聽說的另一件關於涪陵的事:涪陵的女人以美貌聞名。至少這是我在成都上中文課時,別人告訴我的。我的一位老師來自東北,她個子嬌小,有高顴骨,說話時溫和而容易激動。即使在夏天,她仍然雙手捧著一瓶熱茶,彷彿是為了取暖。我們叫她尚老師。雖然她沒有去過涪陵,但是她堅稱那兒的女人十分美麗。
「那是因為河流和山的緣故,」她說:「所有有山有水的地方都出產漂亮的女人。」
在成都,我碰到一個在涪陵土生土長的女人,她也這樣告訴我。「但是有時候,那兒的人脾氣壞得很,」她警告我:「那是因為天氣很熱,因為那兒有山。」我常常聽到這樣的話,而這些話暗示著中國人看風景的眼光異於外人。我望著闢成梯田的山丘,注意到人們如何改變大地,將它開墾成一階一階令人眼花撩亂的水稻田;但是中國人望著他們的人民,看到了土地如何塑造他們。當我住在涪陵師範專科學校的早期,有時我會思考這件事,這主要是因為我所有的學生在成長過程中,幾乎都和土地十分親近。我心裡想,高低不平的四川風景究竟對他們造成了什麼影響。同時,我也在想,在這兩年之中,這片風景將對我造成什麼影響。
涪陵市長最先抵達。一輛黑色的奧迪將他載到學校大門,他跨出車子,簡短地對鼓掌的學生揮手致意。當地的新聞電視臺在那兒拍他──一個在九月的高溫中氣喘吁吁的矮胖男人。他迅速走過廣場,向我和亞當打招呼,和我們握握手,歡迎我們來到這個城市。
在我們於涪陵參加的社交場合中,這是常常最先發生的事──歡迎新來的美國人。在長征集會的那一天,我們正要去郊外走走,身上隨便穿著短褲和T恤。出於好奇心,我們過來看個究竟。沒有穿著整齊就來參加這類的集會,真是一個愚蠢的錯誤,而我們早該料到這一點,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不管我們去看什麼,常常成為被看的對象。
長征隊伍抵達時,校園的擴音器大聲播放愛國音樂。他們穿著白色T恤和迷彩勞動服,沒有刮臉,肩膀上掛著破舊的帆布軍人背包。領隊拿著一面褪色的紅旗,旗上寫著師範專科學校以及宏聲香菸公司的名稱。他走到迎賓小姐後,迎賓小姐排成兩排,每排四人,齊步行進,頭部保持平穩,眼睛直視前方,手臂則敏捷地擺動著。其餘的長征參與者排成一排跟隨在後,臉上掛著驕傲的微笑,向群眾揮手。每個人都鼓掌喝彩,而觀眾跟著這支隊伍進入禮堂,禮堂裡的一面旗子宣告著:
誠摯歡迎涪陵師範專科學校
宏聲香菸萬里長征隊凱旋歸來!
我和亞當躲到禮堂後面的座位上,希望避開別人的注意力。我們周圍的學生竊竊私語,轉過頭來望著我們。這種關注擴散開來,旋即禮堂的每個人都伸長脖子看我們;我們在座位上放低身體,將頭上的棒球帽拉低。過了一會兒,竇副校長就領我們上臺了。老實說,他別無選擇,不這麼做,觀眾的注意力會分散。這是我們經常加入當地社交場合的一個原因:這是讓人們集中注意力的一個簡單方式。
我們坐在市長、黨支部書記及其他幹部旁邊。當我們坐下時,群眾一片喧嘩,而長征隊伍鼓掌。迎賓小姐為我們獻茶。我把頭放低,試著將裸露的雙腿藏在桌下。幹部們發表演說,讚美長征隊伍,並提醒群眾,他們正在向偉大的歷史致敬。演說以強而有力的方式進行著,像是放映著老舊的獨裁者影片,而且沒有一位演說者比得上竇副校長。他五十幾歲,個子瘦小,也許體重只有五十公斤,細瘦的胸腔和纖細、輕盈的手臂,使他看起來很像一隻麻雀。但是,他透過麥克風進行了一場十分出色的演講──起初溫和而冷靜,像是在對一群孩童說話;接著音量放大,且緩緩加快手勢,一隻細長的手對著群眾揮舞,幾乎像是在責備他們;最後他大聲叫喊,胳臂用力上下揮舞,眼睛閃閃發光,使得擴音器隆隆作響。現在,演說者和聽眾變成平等了,以同志、愛國者和僕人的身分結合在一起;群眾起立,爆發出一陣歡呼,且瘋狂鼓掌。
我聽到他說出亞當和我的中文名字──梅爾康和何偉。他宣布,美中友好志願者(Peace Corps﹝和平工作團﹞的中文名稱)派我們到涪陵。群眾再度發出一陣喧嘩,現在我們都是同志了,一起為人民服務,建設這個國家。長征隊驕傲地站起來,而顯要們在每一位隊員的胸前別上一條緞帶和一朵紅色的塑膠花。有一個人遞給我一朵花和一條緞帶,另有一個人對我指著一位等在舞臺前的長征隊員。那位長征隊員微笑、鞠躬,且熱情地和我握手。我點頭示意,然後盡速為他別上緞帶和塑膠花,希望群眾不去注意我的短褲。但是群眾再度歡呼,我揮揮手,而鼓掌聲再度爆發開來。我坐下時,臉上已熱呼呼。
典禮結束後,他們拍照紀念。照片中,長征隊和幹部驕傲地站成三排,審慎地分隔開來,那片褪色的紅旗則按照昔日革命部隊的方式攤開。涪陵長征隊穿著乾淨的白色T恤,胸前別著紅色的緞帶。他們沒有笑。最高階的幹部以及我和亞當站在前排。竇副校長和黨支部魏書記微微笑著,而我們則尷尬地咧嘴而笑。亞當穿著涼鞋,而我則穿著一件舊的灰色T恤,我們赤裸的腿打斷了那一排整齊的長褲。其他幹部都沒有笑。照片中沒有女人。
兩年後,當我回到美國,我會拿出這張照片給朋友看,並且試著說出照片裡的故事。但是該從哪裡開始呢?解釋為什麼「後文化革命」時期的學校如此尊崇長征,就像說明山如何變成梯田一樣困難。最後,我會說:這是學校的一個政治集會,而我們意外地參加了這個集會,因為在世界大多數的地方,共產黨的集會不歡迎和平工作團。我的故事就到此為止──這就是我這張照片的故事。
當然,沒有一件事是這麼簡單。人們認為,我是一位和平工作團的志工,但其實我並不是;我們認為,中國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但其實它並不是。沒有一樣東西如表面所呈現的,而這就是我剛到涪陵時的生活。每一件事都是不確定的,都無法融入當地的節奏。
在中國,和平工作團被稱為「和平隊」,這三個簡單的方塊字所代表的意義遠比表面複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當反美的宣傳進入高潮,中國政府對和平工作團表達了許多看法──他們說和平工作團和中央情報局勾結,說它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特工,說美國將他們的年輕人送到國外,好讓他們的理想主義帶動第三世界邁向資本主義(這是你會喜歡的工作中最艱鉅的一種)。現在,中國人不再這麼說了,但是這些話仍然餘音繚繞,且無可救藥地受到了污染。但是,就像中國人一樣,中文也學會了見風轉舵,當和平工作團於一九九三年來到中國,他們發現自己有了另一種稱號──美中友好志願者。這幾個字看似比較複雜,但是涵意都單純多了。校方教導學生不要使用英文或中文的「和平工作團」名稱,而大多數學生都照辦。因此,帶著一個美化的工作頭銜,我來到這所建立在文化大革命灰燼上的學校任教;在這裡,歷史不曾遠離,而你眼目所及處處是政治。
一開始,「友好」這兩個字讓我們大感驚恐。這是「美中友好志願者」這個名稱中很難翻讀或詮釋的部分。前一年,學校有三位外籍教師:一對年老的澳洲夫婦和一位墨西哥中年男子。但是,那時事情比較簡單,因為他們待在那兒不到一年,而且很少去離校園很遠的地方。我們就不一樣了──我們十分年輕,打算在涪陵住兩年,而且美國政府把我們送到這兒,我們的身分是來到中國的和平工作團第三團的成員。學校在最好的建築物裡為我們預備了公寓,黨支部書記和其他最高階的幹部都住在這棟大樓裡。有幾個星期,他們差不多每隔一晚就設宴款待我們。這類的事是按照一套禮儀進行的。我們會在一張桌子旁坐下來,桌上擺滿了中國的開胃小吃:腰果、牛肉乾、菜豆、蓮藕,而韓老師常常會宣布事項。他是學校外事辦的臨時代表,今年二十七歲。學校裡就屬他的英文說得最好,但他是一位剛剛得到權位的焦躁不安的年輕人。他要我們叫他亞伯特。
第一個星期的一個晚上,他在宴會開始前和我們聊天。
他說:「校方剛剛決定為你們買可以打到校外的電話。你們可以打到中國的任何地方。」
我們抗議──那是不必要的,電話很貴,其他學校的志工並沒有電話。他揮揮手,讓我們不要再說了。「這不是問題,」他說:「對你們來說,沒有電話非常不方便。」我和亞當相互看了一眼,聳聳肩。我們謝謝他,然後每個人開始吃東西。隔天,一位修理工人來到我們的公寓安裝電話。
幾天後有另一場宴會,以及另一次的宣告。亞伯特說:「校方決定為亞當買一部洗衣機。」
「我的公寓已經有一部洗衣機,」我說:「我們可以共同使用那一部--沒有必要浪費錢。」
「那不方便,」亞伯特說:「校方已經決定了。」我們的抗議再度被置之不理,所以我們開始吃東西。隔天早上,一部新的洗衣機出現在亞當的門口。
幾天後,亞當和英文系的一些教職人員打牌,張彥書記說校方收到了我們的簡歷和自傳資料,那是自和平工作團寄來的。
「我看到你會打網球,」張書記說:「你一定打得很好。」
上大學時,亞當曾於暑假期間在一個網球營當教練,但是他立刻搖搖頭。「我打得不好,」他說:「好久沒有認真打球了。」
張書記咧嘴而笑,拿起他的牌。他是一個瘦削而肌肉發達的男人,留平頭。我們花了一星期的時間認清關於他的兩項事實:他是所有英文系教職人員中,籃球打得最好的一位,也最會喝中國白酒。他是系上的高階幹部,身為黨支部書記,他對於學術、紀律和政治問題都有主導權。他是那種很少說話,但是一說話就會發生事情的人。現在,他檢查自己的牌,然後屈身向前,擡頭望著亞當。
他輕聲細語地說:「校方已經決定為你買網球!」
他往後坐回椅子上,等著亞當領會這項宣告的含意。但那就是問題所在:他們究竟如何去「買網球」?有一會兒,亞當試著決定如何回應。
「學校真是好心,」他終於說了,語氣顯得很謹慎:「我很感謝你們想為我做點事,但那不必要。你們不必為我買網球,張先生。」
張書記帶著微笑丟出一張牌。
他說:「魏先生關心也許你想打打網球。他想確定你和彼得待在這兒很愉快。」
魏先生是整所師範專科學校的黨支部書記,身為學校最高階的共產黨官員,他必定有許多比為和平工作團志工買網球更重要的事要做。亞當說了像這樣的話,強調沒有網球,他的日子也過得相當愉快。但是張書記十分堅決。
他以淡淡的語氣說:「已經決定了,校方將買網球給你。現在該打牌了。」
隔天早上,亞當的門階上沒有網球的蹤影,但是他不想冒險。他向我談到那次的談話,然後我們一起嘗試和校方溝通。在那兩年裡,我們一再嘗試做類似的事,而結果不一。我們的溝通方式常常是間接的,很少是輕而易舉的。有時候,溝通的結果正好和我們的期望背道而馳。
我們和亞伯特談,我們再度和張書記談,然後我們和系主任及其他英文系教職人員談。我們說網球很貴,而我不會打網球。事實上,亞當甚至不再喜歡打網球了。他上大學時就不再喜歡打網球了,甚至還不如說,他正期待能有好長一段時間不必打網球。那是一種差勁的運動。籃球好多了,還有足球。網球是剝削階級的遊戲──其實,我們還不至於這麼說,但是我們嘗試了其他一切說法,有一整個星期,我們持續為反對買網球而作戰。
我們公寓大樓的隔壁是一座槌球場。毫無疑問地,槌球場是校園裡最好的景點,而那座槌球場也許是我在中國看過最寧靜、和諧的一個場所。在一個人滿為患的國家,你找不到許多這樣的地方──一個只用來享受樂趣的地方。圍成一圈的樹為球場邊緣提供綠蔭,而壓緊的泥土表層十分光滑。這座球場受到細心的照顧,但是它之所以光滑而美麗,最主要是因為許多人來這兒打槌球。每日清晨,退休的師範專科學校教師和工人聚集在槌球場,打一整天的槌球,只在午餐時間稍做休息。他們的球技好得不能再好了,好得似乎與競爭比賽無關,球滾向打球者要它去的地方,就像魔術師的紙牌按照固定動作和技巧間的靜默協調移動著。那是一種日常性的表演,一種神射手的遊戲;那些退休的教師和工人是藝術家;他們已將槌球提升到一個嶄新的境界。但是,這座槌球場幾乎和網球場一樣大。
在最初的幾週,那是我們最擔心的事。我們可以從我們的陽台看到這座球場。每天早上,我們望著外面,擔心看到工人、鏟子、鶴嘴鋤、反鏟挖土機、炸藥──任何和「買網球」有關的東西。我們真的非常擔心,而不確定是最糟糕的部分;「買網球」似乎是一個抽象觀念,但是另一方面,涪陵顯然是那種可以做許多事情來把抽象變成事實的地方。只須看一眼三峽大壩的平面圖,就足以證明這一點。
但是最後,網球沒有買成,而宴會在四週後結束。一個月之內,校方不再為我們的公寓買這買那了。不久,我們就開始像被寵壞的孩子那樣,抱怨沒有人理會我們的需要,但我們只是在校園上方我們的幹部公寓裡,獨自咕咕噥噥地發牢騷。
每天早晨,打槌球的聲響往上飄入我們的公寓──輕輕的擊球聲、硬土上拖腳走路的聲音、退休教師和工人從容打球時輕柔的談話聲和笑聲。那是我所聽過最撫慰人心的聲音。我常常坐在外面的陽台上,除了聆聽之外,什麼也不做──聆聽在斷斷續續的蟬鳴和烏江水流聲的襯托下,那些人打搥球的聲音。船隻喇叭的回音橫越了狹窄的江谷,馬達啪嗒啪嗒地打在水流上,平底船磕隆磕隆地將沙土卸到水邊隆隆作響的卡車上。離我的公寓一公里半的地方,烏江在長江褐色的急流之中消失了蹤影,而我經常聽見自那條大河發出來的寂寞喇叭聲。
起初,對我而言,涪陵大半只是聲音。這是一座吵鬧的城市,但是這裡的噪音異於我以前聽過的任何聲音:建築工地的鑿子持續發出的叮噹聲、大鎚撞破石頭的聲音──一個大半以手工作的地方所發出的聲音。而這是我第一次住在河流旁邊,聽著船隻的噪音,聽著這些聲音如何在江谷回響。
我的公寓位於一棟大樓的頂樓,而這棟大樓位於烏江上方的一座山丘上。烏江是一條美麗的河流,水流湍急而澄淨,流自貴州省南部未開化的山區。烏江另一頭是涪陵的主城──豎立在山坡上亂糟糟的一堆低矮結實的水泥建築物。我眼目所及之處,盡是陡峭的山丘,正北方尤其是如此,在那兒,厚沈沈的白山坪陡陗地聳現在兩條河流匯流處的上方。
那是我從高高在上的位置,從六樓高處,從河流和濱江小城上方,所看到的景物。我的視野不受任何阻擋,這是我之所以聽到這麼多聲音的另一個原因。每天早上,早在槌球聲開始之前,我就聽到了公寓大樓後方的那隻公雞開始啼叫,我聽到了鬧鐘在清晨六點鐘響遍整個校園,我聽到學生們昏昏沈沈地跑到穿過校園的小路上,開始做早操。六點過後不久,擴音器開始播放早操音樂──充滿朝氣、讓人不斷重複做相同動作的音樂,日復一日永不改變的音樂。早操結束後,擴音器傳來宣告事項的聲音,然後是學生吃早餐的聲音;然後,早課的鈴聲響了,而槌球場上傳來第一陣輕柔的回音。
我住在教學大樓隔壁,所以我也聽見那些聲音。我聽見學生們背誦課文,因為在涪陵,學習的方式大半是靠死背。那也是一種撫慰人心的聲音。當他們背誦讀過的課文,我聆聽他們一起忽高忽低的聲音,感覺到十分滿足。而且我喜歡聽見老師們開始上課時的聲音、下課十分鐘那些亂糟糟的吵嘈聲、電動鈴聲,以及學生趕去吃午餐的聲音。
這些聲響不會困擾我。一大早的聲音把我吵醒,但那還好,因為那是學校常規的一部分,聽見這些聲音讓我覺得彷彿跟得上學校的節奏。當然,我無法跟得上學校的節奏──從某些方面來說,我永遠無法跟上這個節奏。但是在最初的那幾個星期,如果沒有我周圍這些不變的常規,我會覺得更加與環境脫節。
每件事都按照一個一絲不苟的時間表進行。早上有早上的例行事項:運動、鈴聲、上課,而在下午,當學生按照學校規定打掃校園,我常常聽見掃帚揮動的聲音。每個星期一和星期四,他們打掃教室。星期天晚上有政治集會,學生聚在一起發表演說、唱唱歌,歌聲在夜間的校園回響。
在一學年的開始,新生必須上軍訓課,每個班級形成一個兵團,男生和女生合在一起,人民解放軍的軍人來教他們行軍禮、走正步、轉彎、以立正姿勢站立。上軍訓課時,他們也學唱歌──這似乎是為共產主義增添樂趣的一種方式。我們的學生常常得為某個組織或機構表演愛國歌曲。
上軍訓課時,新生得穿班服:仿冒的粉藍色愛迪達成套運動服。站在穿著迷彩服、帶著硬梆梆軍人氣息的指導員旁邊,學生們那些鮮艷的制服,以及學生本身,似乎顯得極不搭調。他們都是二十初頭,但是,大多數人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而且他們才剛剛離開農家生活。現在,他們戰戰兢兢地蜷縮在領導者的命令之下。天氣熱時,有些人昏倒了,被擡到陰涼處,其餘的學生則繼續走正步。當為期兩週的訓練結束了,當他們都學會了如何行進,他們步行到磨盤溝一個深邃角落的打靶場。在那兒,他們以火力強大的來福槍拚命地轟擊靶子,來突顯他們加入軍隊的儀式,我也聽見了這些聲音,聽見了一陣陣槍聲淹沒了烏江的水流聲。
到了晚上,校園迅速沈寂下來。宿舍的燈在十一點準熄滅──全部的燈一起熄滅,電被切斷了,一整排的建築物陷入一片漆黑。夜晚時,有時我會坐在外面的陽台上,看著那些燈熄滅,這種規律性也有一種撫慰人心的作用。
從我的陽台看來,夜色中的城市顯得十分美麗。在白天,涪陵是一個骯髒的濱江小城,你可以看出許多建築物過於迅速地建造起來。然而到了夜晚,一切缺點都消失了,只剩下水和光──明亮的燈光和黑漆漆的水,烏江那面深黑的鏡子被加上了紅、黃、白的條紋。有時候,一艘夜船輕輕朝上游滑行,不斷在船頭前方推進著三角形的燈光,而引擎則不斷在幽黑的江谷喀喀作響。大約每隔半小時,長江水面就會出現一艘客輪,一組明亮的燈光在莊嚴的寂靜中漂浮而過。
我不太懂得這些例行事項,我不知道那些船將航向何處,我不知道這所學校為什麼如此規律化。他們打槌球的方式和美國不同,但是,我不曾費心去了解涪陵的規則。我只是喜歡他們每天打槌球──規律性才是最重要的。在我讀到一位學生在日記中描述師範專科學校一個典型的下午之前,他們的軍訓課也不曾引發我太多的思考。這篇日記這樣寫著:
今日艷陽高照,在第一年,學生必須上軍訓課。他們不斷地走了又走。汗水從他們頭上滴落,但是沒有領導者的允許,他們不能停下來。
當然,這樣一來,他們就知道軍中的生活是多麼辛苦。他們可能變得精神不振。
每個人──尤其是大學生──都應該有強烈的愛國情操。我們的國家花了許多錢教育他們。他們應該對祖國忠心耿耿。兵力是一個國家強大與否的象徵,因此學生有必要吸收一些軍事知識。一九八九年,北京有學生運動,在我們這些年輕人看來,他們沒有成熟的思想,沒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此外,他們也無法辨別是非,只一味追求刺激的事。那次的學生運動結束後,我們的國家規定大學生必須上軍訓課,目的是要讓他們明白,達到我們目前的生活水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就是我那一陣子真正聽到的聲音──行進聲和遠方的槍聲是天安門廣場抗議聲的回響。我明白了,學校例行事項的意義比我起初想像的還要複雜。之後,我開始以更慎重的態度,聆聽那些滲入我位於烏江上方高高在上的住處的聲音。
第一章 順流而下我從重慶搭一艘行進遲緩的船順流而下,來到涪陵。那是一九九六年八月底一個溫暖、晴朗無雲的夜晚,星星在長江上方閃爍,而漆黑的江水無法反映微弱的星光。學校派來的一輛車子,載我們沿著自碼頭蜿蜒而上的狹窄街道行進。小城自車窗外匆匆掠過,在星光下顯得幽暗而陌生。我們有兩個人同行,被派到這兒任教。我們都很年輕,我二十七歲,而亞當.邁爾(Adam Meier)二十二歲。對於涪陵,我們幾乎一無所知。我知道城市的一部分將被新的三峽大壩淹沒,我也知道許多年來涪陵一直對外封閉。除此之外,我們得到的資訊十分有限。半...
購物須知
關於二手書說明:
商品建檔資料為新書及二手書共用,因是二手商品,實際狀況可能已與建檔資料有差異,購買二手書時,請務必檢視商品書況、備註說明及書況影片,收到商品將以書況影片內呈現為準。若有差異時僅可提供退貨處理,無法換貨或再補寄。
商品版權法律說明:
TAAZE 單純提供網路二手書託售平台予消費者,並不涉入書本作者與原出版商間之任何糾紛;敬請各界鑒察。
退換貨說明:
二手書籍商品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二手影音商品(例如CD、DVD等),恕不提供10天猶豫期退貨。
二手商品無法提供換貨服務,僅能辦理退貨。如須退貨,請保持該商品及其附件的完整性(包含書籍封底之TAAZE物流條碼)。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
退換貨原則、
二手CD、DVD退換貨說明。
本商品資料由TAAZE會員提供,TAAZE並已依據現貨及一般人之認知對其進行審核;TAAZE對其正確性不負連帶責任。若對商品資料有疑義請聯絡TAAZE客服。
 3收藏
3收藏

 14二手徵求有驚喜
14二手徵求有驚喜





 3收藏
3收藏

 14二手徵求有驚喜
14二手徵求有驚喜